迎接歌唱的第二个春天
——访男高音歌唱家白萌
2017-05-18赵世民

1999年,中国十大男高音歌唱家独唱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我在现场聆听了戴玉强、魏松、程志、丁毅、金永哲、白萌、李初健、黑海涛、杜吉刚、张积民等十位男高音的演唱。在我的现场观摩经历中,那是第一次在同一舞台上聚集了中国十位男高音歌唱家。以前只见过三位男高音同过台,比如1992年我看过中央歌剧院的刘维维、杜吉刚、黄越峰三位男高音在北京音乐厅开独唱音乐会。
这次十位男高音音乐会像打擂,他们分成两场登台;每人唱一首,上半场一轮、下半场一轮。这十位男高音中只有白萌的歌声我没听过,但他唱的两首咏叹调却深深地吸引了我——上半场白萌唱的是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奇妙的和谐》,下半场是古诺歌剧《浮士德》中的咏叹调《贞洁的小屋,我向你致敬》。白萌的音质有别于其他九位男高音,他的声音“肉肉的”“润润的”,极像多明戈的音色。多明戈于1987年在北京音乐厅演唱过这首歌,我对他现场“裸唱”(不带音响)的音色很熟悉。相比之下,白萌只是在“小屋”最后的High C上不太辉煌,我感觉这不是嗓子能力的问题,是High C的技术还不成熟造成的。但我记住了白萌,当时他还不满40岁。
2002年,经中央音乐学院赵登营教授介绍我正式认识了白萌,当时他已是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院长。我发现饭桌上的白萌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问赵登营教学的经验,请他介绍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学的规范,以及国际“美声”教学发展的趋向。我当时想,白萌真够谦虚的,都得过“青歌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的银奖了,又是“中国十大男高音”之一,还这么低调,看来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后来,白萌邀请我给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开设音乐传媒、音乐评论与写作方面的课程,在一门课程的结课仪式上,白萌为我唱了一首《再见吧,可爱的家》(选自歌剧《蝴蝶夫人》)。当时连钢琴伴奏都没有,但白萌的演唱声音饱满、情感缠绵,我眼见着一些女学生眼含泪光。我觉得,白萌唱歌,摄人心魄。
和白萌交往得多了,感觉他做人很厚道。在和朋友的多次聚餐中,他总是抢着付账。而一般邀请他演出,他也从不问报酬,给多少是多少。就连如今“艺考”学生的学费,白萌还是多年前的标准,同级别的教授早已是他的两三倍,甚至更高。于是,大家亲切地给他起了个外号——“白伯伯”(音“bāi”)。
按说人品厚道的人往往专业能力就稍逊色,但白伯伯的专业可是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数一数二的。放眼整个陕西省,重要的庆典音乐会大都少不了他的歌声。我在陕西人民剧场看过白萌参演的原创歌剧《张骞》;看过陕西省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举办的音乐会,白萌穿着30年代的军装领唱《红军不怕远征难》。2006年,我和晁浩建策划主办了“中国十少男高音独唱音乐会”,当年“十大男高音”中只请了白萌做演唱嘉宾,他唱得确实比“十少男高音”水平高一截。那“十少”都是谁呢?包括杨阳、王传越、王凯、王红星、李爽,等等。我当时就觉得,男高音的成熟期还真在40岁以后,因为这时人的嗓子机能最好、人生阅历丰富、情感表达细腻。“世界三高”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于1990年组合,当时前两位已过50岁,卡雷拉斯也“奔五”了。“中国三高”戴玉强、魏松、莫华伦组合时,魏松已过50岁,莫华伦和戴玉强也快50岁了。


女高音歌唱家和慧担任“白萌独唱音乐会”嘉宾(2012)
白伯伯能将嗓子的机能保持如青壮年般,还真得益于厚道。厚道待人前面已经说过,厚道待学问使他在58岁的年纪时仍能不断进步。在白萌的琴房里挂着一张帕瓦罗蒂的巨幅照片,每天帕瓦罗蒂都对着白萌憨憨地微笑。白萌说,他最崇拜帕瓦罗蒂,以获得他那样的高音或接近那样的音质为人生最终理想。为了探寻帕瓦罗蒂声音的秘密,2011年夏,白萌去意大利观摩歌剧、拜访名师,我非常荣幸能与他为伍。我们在维罗纳露天剧院(由古罗马时代的斗兽场改建)看了《塞维利亚理发师》《茶花女》和《纳布科》,看了和慧主演的《阿依达》;在那不勒斯歌剧院看了《丑角》;在一处露天城堡与弗雷尼共同观看了《艺术家的生涯》等。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歌剧,尤其是在维罗纳露天剧院看完演出后,我们惊叹演员的歌声能穿透百人乐队的音墙,辐射到剧场的每一个角落,送到全场30000人的耳朵里。比如和慧唱《阿依达》里的咏叹调《祖国蔚蓝的天空》,有时甚至弱如蚊鸣,观众却照样能听得清清楚楚。我形容和慧那弱音,就像持一把长筒狙击步枪,将那蚊鸣般的歌声“射”入每一位听众的听觉器官。白萌感慨:“意大利歌剧唱法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唱法,不到意大利亲自体验,不会有这么深切的感受。”
有一天,我们去庞贝古城参观。到了古城里的一个圆形露天剧场,导游让我们在指定的一个一平方米不到的圆圈里发声,说:“在这儿发声比在剧场其他地方发声要响亮。”我们挨个儿试,确实神奇,在指定圆圈里发出的声音比在其他地方发出的声音起码大五倍。白萌的儿子是学建筑与环境的,他说:“古罗马的声学建筑太科学了,这个马蹄形的剧场就把人的声音给放大了,完全是用自然的方法。”
在以后的行程中,“马蹄形”成了白萌的口头禅。他说:“你看,意大利的歌剧院,甭管室内的还是露天的,都是马蹄形。维罗纳露天剧院是个椭圆形的,三分之一是舞台,三分之二是观众席,这就是马蹄形。那不勒斯歌剧院也是马蹄形,再联想到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也是马蹄形,这说明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都受古罗马(也就是意大利)的影响。”
白萌还发现一个秘密,马蹄形其实就是“U”型,而美声唱法训练唱“u”母音是打开声音通道的基础手段。其实,意大利歌剧唱法就是把人的身体练成一个马蹄形剧场。声带的发声位置,就相当于马蹄形露天剧场那个发声点,而歌者传声的通道和身体四壁,就相当于马蹄形露天剧场的环形四周。
在那不勒斯,靠海的地方有一个广场,面向海边有半圈马蹄形建筑,中心是一个古老的教堂。白萌在教堂正前方的一个地儿(神父布道的地儿)上唱歌,居然能让四五百米之外海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而换一个地方唱,歌声就没那么大的能量了。
白萌怀揣着意大利歌剧唱法的秘密回到古城西安,每天带着“马蹄形”的意念练声。后来,他再到北京看歌剧或我到西安看音乐会,我俩在交流时,他有了更多的自信,因为他带回了意大利的“马蹄形”。
2012年,白萌在西安开了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他面子真大,居然请来和慧当演唱嘉宾。白萌与和慧唱了歌剧《蝴蝶夫人》中的《爱情二重唱》,这算是他从意大利“偷艺”回来后的正式露面。别看他已是53岁的人了,那个High C稳稳地飘上去,与和慧的声音组成了一朵白里透红的祥云,比我听“十大男高音”那会儿的声音高级多了。
音乐会后,白萌、和慧一行又去了和慧的老家安康,去探访汉江边她曾练声的地方、上过的中学以及老宅,我又有幸与他们为伍。在和慧家附近的一座山上,白萌与和慧对着树林又唱上了,唱的是《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我爱你,中国》等。和慧说:“这是回国后最开心的一天,能在家乡的山上这么自然地唱歌。”
我问和慧:“你这么大的腕儿,能给白萌音乐会当嘉宾,可见白伯伯这人有多厚道了。”和慧说:“对厚道人的回报,我还有其他方式,像白萌这么好音质的男高音,意大利太缺了。如果他能背几部意大利歌剧,我会推荐他去试唱。如果能试上角,演好一部歌剧,那签约的机会就更多。在意大利歌剧界,主要凭实力。再有关系,观众不买账,也会被轰下来的。在意大利站稳了,就可以向欧美发展了。”
和慧说的是实话。在意大利维罗纳,和慧就让她的经纪人听了白萌的演唱,那天唱的是《冰凉的小手》等咏叹调。和慧的经纪人以前当过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的院长,在意大利是慧眼识和慧的第一人。他对白萌的评价是:嗓子、声音都没有问题,只是一要加强语言的修炼,二是在舞台上要更好地“撒开”,以他这种水平,在意大利是有机会的。白萌问,要不要找谁学一学?和慧经纪人说“不用”,但要找一个好的意大利“扣吃”(英文“coach”的音译,意为艺术指导)。
50多岁的白萌,又进步了。有一天在琴房,白萌给我唱了带九个High C的男高音顶级曲目——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里的咏叹调《在这欢乐的节日里》。白萌说,找着唱高音的“窍”了。不久后,白萌在西安曲江音乐厅举办的一场歌剧咏叹调的音乐会上,正式推出了这首《在这欢乐的节日里》,观众们都十分惊讶,白萌老了老了,还能出这种动静儿。白萌心悦了,这算啥呀,咱去意大利探到了“马蹄形”的秘密,这只是刚开始。
除了喜欢听白萌唱歌,我还爱进白萌的课堂。别看在朋友聚会的饭桌上,白萌主要是听别人说,但在自己的课堂上,他是能说会演,说得头头是道、演得栩栩如生。
一个学生在演唱上下句时衔接得不好,白萌说,这就像跑接力,棒子要舒服地交到下一个人手上。学生娄新雨演唱贝利尼的《让她高兴吧》时,白萌针对她“进腔”后不流畅的问题,是这样解析的:“你从转桥上了高速,不要停,要赶快走,不要在嗓子上‘做’,声音需要‘进腔’,就像自来水进管道里一样。”
白萌说要“进”的腔就是指咽腔。咽腔是口腔后部的管道,它的上段跟鼻腔相对的叫鼻咽,中段跟口腔相对的叫口咽,下段在喉的后部叫喉咽。意大利歌剧唱法的威力就在于声音要进咽腔这个通道,这就是马蹄形结构正中那个点,在那个点发声,声音会加倍打远。
谈到娄新雨的音色时,白萌说:“我们要的是意大利肉酱面,这和我们的西红柿打卤面不一样。你别看两种面都有西红柿和肉末,为什么会是两种不同的味道?就是因为意大利肉酱面里还有芝士,味儿一下就‘洋’了。”
白萌说,进了管道声音要往前“放”,到了一定高度要翻上来。他接着说,我在北京听贝尔冈齐上大师课,他老用手做一个拱形的动作,这就是声音的位置。这个拱形就是马蹄形,声音一定要“拢”在这里,就像做前滚翻,要抱成团,成球形,若腿不收怎么能翻过去呢?唱歌像拧瓶盖子,别松;唱歌就像晾衣服,要挂上再松手。声音没“挂”绳儿上,那是因为没“钩儿”,老“挂”不上去,“挂”上去才能省劲儿。
学生唱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里的咏叹调《你知道吗,好妈妈》,白萌说,这是一首急切的咏叹调。桑图扎看见图里杜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跟他妈妈告状,是着急,不是快,不能赶节奏,不能“冲”得刹不住;作品中的三连音要唱准;上一句的结尾是下一句的开始,像接力跑似的,不能掉棒,要“迎”上来、“挂”上去。
学生唱《春思曲》时,白萌说:“只要水进管子,甭管是扁还是细都没事;别怕横,笑起来容易‘挂’上去。注意伴奏中的‘雨滴声’,它既给你速度的提示,又给你情境的暗示。”
学生胡琦唱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时,白萌说:“要绒绒的,飘过去。要找巧劲儿,就像遇到小胡同儿,要绕过去、钻过去。声儿要进腔,不要有口腔的声儿。条件越好的人,越不要加东西,保持就行。”
学生唱《理想佳人》时,白萌说,这首歌要表达啥?要表达的是在梦中寻找自己的爱人。字的衔接,要“迎”上去接,别往下“蹲”一下。要用情唱,别舍不得用。“拿眼睛收”,人的眼睛反应更快。北方人“腔”好,南方人字好,就像多人划船,加字是为了加浆,这样划得快而平稳;有的人唱是加人,人加得越多船越重。

学生唱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中的咏叹调《求爱神给我安慰》时,白萌说,这是伯爵夫人的唱段,很高贵。声音要“立住”,像跳芭蕾舞的感觉,脚尖要立住,不能出民族舞的感觉。咱不是说芭蕾好,民族舞不好,而是风格与规范的问题,审美要往芭蕾那儿靠,不能跑范儿。
学生唱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咏叹调《你就会看到》时,白萌说:“主人公虽然是小姑娘,但也别唱得太闹。‘立着’唱的副作用是容易停住,别停,立着出去。”
学生唱《蓝色爱情海》时,白萌说:“还是芭蕾舞的范儿,不过是中国味儿的。月光下的海面,简单一点儿,别起伏,往前走。张立萍就这样唱!别动你的乐器,别一激动,琴就散架了。情可动,琴不移,歌声滑行入心脾。”
学生刘奇唱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咏叹调《黎明的天空多晴朗》时,白萌说:“你本来唱得很好,但唱‘e’时舌根音会影响你的音色,等于什么菜你都来一把孜然,全是孜然味儿了。要从后移到前面来,宁听鼻音不听喉音。喉音是癌症,鼻音是感冒。”
学生唱《喀什噶尔女郎》时,白萌说:“你唱的感觉像配乐诗朗诵。歌唱和说话最大的区别就是声音进腔,不是声音放大。你不是唱歌的咬字方式,而是朗诵的咬字方式。路走错了,越刻苦越麻烦。后面要‘拽’一下,贴着咽壁唱,别拿嘴唱,带着音色唱。”
学生唱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咏叹调《宝贝》时,白萌说:“你的身体晃动和音乐没关系。这是安慰你的爱人,抚摸她一下、给她擦泪;九度的跳跃,要扣住,别憋,男高音的帅劲儿,就是这么带出来的!”
看白萌上课,很长学问。他说的话在学生唱歌的特定情境中,既有涉及作品的,又有关乎唱法的。白萌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把看不见的发声腔体用形象的比喻让学生可感、可做,把摸不着的情感用恰当的表情、动作让学生意会,并融进演唱里。白萌将以前打篮球的经历,把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和大餐的体验以及人情世故,全用在他对歌唱的理解中。
我知道白萌有20年,交往也有15年,由于他低调,很少谈及自己,所以我只是知道他生在新疆。每次我们在西安坊上(回民街)吃羊肉泡或胡辣汤时,他总要买上半打新疆的烤馕。又通过他每年都参加西安音乐学院教工篮球比赛,知道他以前打过篮球,至于他怎么走上歌唱之路,我一无所知。
2016年10月9日,我和白萌正儿八经地聊起了他的歌唱历史。一聊才知道,19岁以前,他也是个白丁。白萌1959年10月17日生于新疆昌集回族自治县,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现代京剧,像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他背得滚瓜烂熟。
白萌生在新疆昌集回族自治县,是因为他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支边来到了新疆。这么说,白萌也算是精神贵族出身,要不然他总是仪表堂堂,光是皮鞋,每天都要换着穿,可以一个月不重样。
1973年,白萌随父母回到西安,严格地讲是来到西安,因为他老家在河南。他在二十一中、七中读书。1977年高中毕业时,因为有打篮球的特长,被钟表仪器厂录用,成了光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材料工)。后来,中学同学的姐夫(当时在省广播文工团工作)觉得白萌嗓子不错,于是就做了白萌的启蒙声乐老师。
白萌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驼铃》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先后师从马寿琼、季耐雪、倪荣华等老师。那时,白萌的基础很差。你想,他一个材料工人怎么懂视唱练耳、钢琴、乐理?钢琴是到了20岁才学的。但白萌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到三年级时就追上来了。后因毕业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工作了四年,1989年白萌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进修班,曾想拜周小燕为师,但那时周先生大腿摔断了,通过周围人介绍,拜在了倪承丰教授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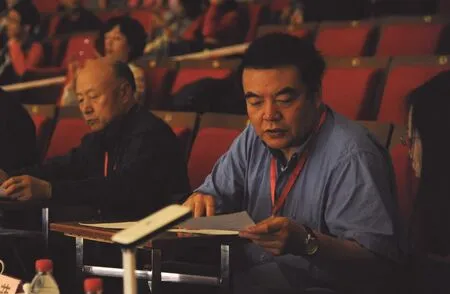
在“第四届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比赛”中担任评委

倪老师虽不像周小燕、沈湘名气那么大,但声音观念是传统的意大利式的。白萌说:“他在发声、咬字、风格等方面‘规整’我,让我找到自己的声音,把我往道儿上引。这期间,我还接受过施鸿鄂老师的指导,他让我声音‘软’一点儿、‘肉’一点儿,顺顺地、滑滑地。他还借助极端的方式让我找到歌唱的感觉,如弯腰发声、肚子顶钢琴唱,目的都是把自己解放出来。那时,上海音乐学院的整体教学氛围很好。”
在上海学习那段时间,白萌浏览了大量的作品。他的艺术指导老师姚志军(曾为多名歌唱家、获奖选手担任艺术指导)每周给他上两节主课,其中一节是伴奏课,每周都得回新作品。姚老师是基督教信徒,因此,白萌接触了很多宗教的东西。白萌说:“教堂、建筑、宗教音乐的审美等在音乐上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开始,我觉得宗教离我很远,经姚老师的熏陶,使我了解到西洋音乐、意大利歌剧等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比如《托斯卡》这部歌剧,男主角是圣像画师,歌手托斯卡是虔诚的信徒,你只有了解了他们的信仰,才能真正表现出音乐的内涵,对作品的处理才能到位。”
1992年,到上海进修的效果显现出来了。白萌参加“第五届央视青歌赛”,得了“美声”专业组银奖。后来上海歌剧院免试录用白萌,但没走成;1994年,总政歌舞团联系他,又没走成;再后来,白萌就一直踏实地在西安音乐学院当教师。
白萌说:“这几十年来,我就琢磨一个问题——‘男高音的嗓子如何保鲜?’男高音吃的就是音色这碗饭,它像纯净水,不能脏,越清澈越金贵。我为什么那么崇拜帕瓦罗蒂,就是因为他的音色令我着迷,那种纯净的音色很煽情,风流倜傥。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要有高音,又不能牺牲音色。像阿宝那样,高音比老帕都高,但他不是老帕那音色。既要音高,又要老帕那音色,太难了。即使难,也要攻克这技术,无高音不过瘾,像喝酒,如果就好这口儿,那不上65度叫没喝。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追寻着这样的音色,加上去意大利探寻他们歌唱的秘密——其实说来特简单,就是‘声儿进腔,水入渠’,把声音放到恰当的位置上,就是咱们悟出来的声音放在马蹄形中间的那个点上。这才能产生最大的共鸣效果。”
白萌说:“要做声音的主人,让声音像天上自由自在飞翔的雄鹰,得先做声音的奴隶,也就是天天练习。这些年,为什么我的声音还能保持年轻,而且唱《在这欢乐的节日里》还能很轻松,就是因为天天都在唱。这已成为我‘养生(声)’的习惯了。你看,意大利人,八九十岁声儿还‘哞哞’的,根本不像咱们有些人说的‘四五十岁不学艺’。你不练,机能当然要老化了。照我这样唱下去,唱到70岁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前两天参加一个比赛,我和胡松华当评委,他86岁了,唱出来的声儿还那么年轻。”
白萌计划从现在到退休以后,要把男高音的经典曲目都拿下来,除上面提到的,还有《柴堆上火焰熊熊》《冰凉的小手》《今夜无人入睡》《圣洁的阿依达》《星光灿烂》等,做出满意的唱片,当教材。
白萌说:“过去觉得多明戈、帕瓦罗蒂的声音遥不可及,自己干脆别唱了,还学什么呀!但当我把他们当成奋斗目标以后,天天唱,慢慢地声音靠近了他们。我发现,他们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时,已经没我这样年轻的声音了,没准儿我歌唱的第二个春天才刚刚到来!”
厚道的白伯伯,低调的白萌,唱出来却这样的高调,我信。
白萌身高1.82米,形象周正,嗓子天赋又好,“美声”信仰坚定,为什么就没成为国内顶级的男高音歌唱家?我六年前专门写过文章分析过。
第一,享小成而缺创业精神,这是从白萌的性格来分析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白萌数次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在上海也有一定影响。当时上海歌剧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都有意调他当职业歌剧演员,或边教学边演唱,但这时白萌没能果断地重新选择。再加上培养他的西安音乐学院承诺重用他,于是白萌选择留下。虽说也有演出的机会,甚至随西安音乐学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也唱过,但影响没有波及全国。
和白萌相反的是丁毅。丁毅也是从西安走出去到北京进修,师从沈湘教授和李晋玮教授。当中央歌剧院调他时,丁毅毅然告别西安音乐学院。他先在中央歌剧院主演歌剧《图兰朵》,又主演歌剧《茶花女》,等等。然后随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到澳大利亚演出,引起了悉尼歌剧院的注意。随后他告别中央歌剧院,签约悉尼歌剧院,出演了多部歌剧的男主角。十年之后,他回到中国,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出演多部歌剧的男主角,如《茶花女》《乡村女教师》等。12年前,丁毅和范竞马、戴玉强组成了“中国三大男高音”。现在丁毅虽然在中国音乐学院当声乐教授,但20多年的歌剧舞台锤炼使丁毅教学经验丰富,演出得心应手。

参加《歌唱艺术》研讨会,与郭淑珍先生合影(2013)
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设想一下,若当年白萌舍弃西安音乐学院的小成,果断地应聘到上海歌剧院重新创业,如今会是怎样的情境?当时,上海歌剧院和美国一家歌剧院有交流合作项目,白萌除了能在上海唱歌剧主角外,再到美国、欧洲进修学习,很有可能就在欧美歌剧院唱上成了角儿。即使再回到国内,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季,我们应该也能看到白萌担纲歌剧男主角。
第二,顾教学而少舞台演出。年纪轻轻就在学校当教师而又兼顾歌剧舞台的也有正面的例子。如同是西安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的陈勇,唱过中央歌剧院排演的《霍夫曼的故事》,也在国家大剧院的《乡村女教师》《赵氏孤儿》《西施》《冰山上的来客》等原创歌剧中出演男主角。
我说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话对白萌是没什么意义了,但对一些年轻的研习意大利歌剧唱法的学生还是有一定启发的。趁着年轻,尽可能地上舞台闯一闯。有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会更有助于今后的歌唱教学。我访过男中音歌唱家孙砾,他说他一年除了要演十部以上的歌剧外,还有不少于50场的音乐会演出,就是这样的演出密度锤炼了他的歌唱机能。
白萌呢?他待人厚道,他说学生投奔自己,就得对得起他们,于是将大量时间投入到教学中。声乐教学和歌剧演出大方向是一致,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职业。虽然男高音之王帕瓦罗蒂在世时到处招弟子(如戴玉强),但他很难静下心来系统地给弟子们上课。
教学为什么和演唱歌剧冲突呢?首先,教学需要大量时间,上课时间就不用说了,不上课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世界级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同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但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奥地利维也纳歌剧院、德国柏林歌剧院、英国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法国巴黎歌剧院等演出《阿依达》《蝴蝶夫人》《托斯卡》《假面舞会》等歌剧的女主角。和慧跟我说,除了排练演出外,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背谱子、研究体验角色上。白萌则是每天课时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背歌剧谱子、研究角色?
其次,教学毁嗓子。我常进白萌的课堂,他教学认真、感情充沛、语言生动、示范准确。教师为了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毛病在哪儿,就要模仿学生的毛病,这对自己的歌唱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破坏。作为一位职业歌剧演员,静心时脑子里储存的多是美妙歌声的印象;但教师每天接触的多是不好的声音,时间长了,也会改变自己的声音形象。一般心理医生隔一段时间就要看更高一级的心理医生,为的是清除自己积攒的心理垃圾。声乐教师也一样,隔一段时间也要找更高一级的声乐大师清除自己存储的音响垃圾。
白萌现年58岁,难道说想成为中国顶级男高音歌唱家就没机会了吗?
杨洪基真正“火”是在53岁,1994年他唱了《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他的歌声恰如长江,一直滚流到今天,现已76岁高龄,仍在国内男中音歌唱家的一线。杨洪基、刘秉义、李光羲现在是金牌组合,晚会邀约不断。
白萌在中国发展也行,多留心寻找原创歌曲。西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季平写的歌催“火”了不少歌唱家。白萌找好词,请赵季平为自己量身打造一首歌曲。如果有白萌原唱的歌在社会上流传,也不用多,三年有一首,那各种晚会年年都会请白萌唱他原唱的歌曲了。国家大剧院每年要上演多部歌剧,白萌可以去试唱,尤其是新创的中国歌剧。如果每年都能在国家大剧院上一部歌剧,那就会引来更多的机会。
人的一生不可重复,我们没有必要苛求58岁以前的白萌没“大火”,但58岁以后的白萌可以重新定位,努力成为一个顶级男高音歌唱家。白萌厚道,我话说重了他不会介意,关键是我多么希望他的名声能与他的歌声相匹配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