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于世道人心
——纪念王小波辞世20周年
2017-05-17张喁图片网络
文_张喁 图片_网络
小说之于世道人心
——纪念王小波辞世20周年
文_张喁 图片_网络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一味地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
大隋朝的人说,洛阳城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但唐朝的人又说,长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宋朝的人说,汴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所以很难搞清到底哪里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洛阳城是泥土筑成的。土是用远处运来的最纯净的黄土,放到笼屉里蒸软后,掺上小孩子屙的屎(这些孩子除了豆面什么都不吃,除了屙屎什么都不干,所以能够屙出最纯净的屎),放进模版筑成城墙。过上一百年,那城就会变成豆青色,可以历千年而不倒。过上一千年,那城墙就会呈古铜色,可以历万年而不倒……
——《红拂夜奔》王小波
在以写作博取名利的时代,王小波维护了小说家这一行当的尊严。2000年,网络上成立“王小波门下走狗“论坛。至今,已出版五辑作品。当年论坛的写手里,走出了一大群媒体主编、出版人、作家、电影编导。
这是王氏小说的文风。20年间,不知有多少“王小波门下走狗”可以大段大段背诵,成为现当代史文学史上极罕见的现象。
一百年前,梁启超的声音至今仍在鼓舞着中国的文人。此后,中国现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以小说改变世道人心,成为那一代作家的使命,并诞生了一大批现代文学家:鲁迅、巴金、茅盾、丁玲、萧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又出现了新一代的先锋小说家:余华、莫言、苏童、格非、韩少功……至90年代以后,有人认为,80年代作家的当代小说对世道人心并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当代诗人也纷纷开始了小说创作,在吸收西方后现代小说的技艺和经验之后,韩东、朱文、杨黎、何小竹等人的小说成为了文坛的另一道不为大众所知的风景。
而在文坛之外,另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说家王小波。
1997年以前,王小波的小说主要以打印稿的方式流传。喜欢的人读得忍俊不禁,爱不释手,并渐渐成为文人们交朋接友的某一个接头暗号。“哦,原来你也喜欢王小波!”遂引为知交。
1995年,笔者将王小波的小说打印稿带回成都,著名诗人柏桦读过之后,说:“这是一位强力诗人!”
所谓“强力诗人”,是指作品对时代或审美的冲击力。典型的莫如塞万提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标志性文学形象。
而生活中的王小波,正是这样一位“愁容骑士”。不同的是,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洋的文学是社会的,中国的文学是人世的。”西方从中世纪的宗教蒙昧走向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小说和戏剧立下了最大的功劳。历史上从无争议。甚至有文学评论家说,如果没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就不会有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没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没有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
而王小波作品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20年过去了,他的小说仍然有人在阅读,文章被引用,其杂文选入了中学课本,对此,需要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答。
突如其来的1997年
1996年起,王小波在媒体上已小有名气,《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设了专栏。而小说仍无法出版,至少有四五部书稿辗转在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之间。
1996年10月,妻子李银河前往英国做访问学者,王小波独自居住在北京顺义的家中。《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刘心武无意在街头书店读到了《黄金时代》,深感作者王小波不是朋友们偶然谈起的“业余作家”,两人认识以后常约在刘心武家楼下小饭馆喝酒聊天。
1997年春,刘心武电话给王小波约酒,王小波回答:“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一周以后刘心武接到王小波的死讯,死因是心肌梗塞。
至于“著名作家王小波”,已是身后事,很多办公室里的女白领都是通过其妻李银河知道王小波的,说起王小波,她们喜欢把王小波给李银河书信的“你好哇,李银河……”挂在嘴边 。
1952年,王小波出生的时候,父亲王方名,新中国知名的逻辑学家,母亲宋华在怀孕期间饱受精神折磨,时常以泪洗面。王小波之名,意在希望父亲的事情尽快过去,平安度过这个小波折。
从小,家人担心王小波缺钙,于是他把钙片当作炒豆子一般吃,最终长成了一米九的大个子。少年时代的王小波逢字必看,却因顶撞语文老师而得1分(最低分)。数学不好,却也得过数学竞赛第一名。不过很快,大家都没书读了。
1969年,17岁的王小波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报名去了云南陇川生产建设兵团插队。
一本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被王小波带到了陇川,并在多年之后,成为其重要的文学资源。这部作品属于西方文学的两大源流之一。后来,还应该加上拉伯雷的《巨人传》和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记》。
王小波曾经写道,自己喜欢的书,大概都是这个命运,他会翻来覆去地看,比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就是被这么活生生地“看没了”,而不喜欢的书,完全不用看完,那是浪费时间,比如托尔斯泰的那些动辄几百页的大部头。
一年后王小波按规定回京探家,家里只有父亲王方名一人在养病,母亲在安徽五七干校。王小波到安徽探望母亲,三天后,又经广西柳州到昆明,再转乘汽车到陇川,腿脚都肿了,随后发作了急性肝炎,当地缺医少药,王小波被批准病退回家。
但回到北京家里的王小波却是“黑户”。户口落不下来,就没有口粮,也不可能有工作,而家中母亲兄妹全都下放插队劳动在外地,只有一个养病的父亲。虽然这期间王小波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但也不能不选择离开。还是只有“上山下乡”,要么集体下乡,比如到陇川那样的生产建设兵团,要么回到原籍参加劳动。王小波只好到母亲的老家山东再次插队。
1973年这次插队,多少还是“凭关系”。实际上在两年的山东牟平青虎沟的插队生涯中,先是参加农业劳动,后到当地中学水道联中任初中物理代课老师,直至回到北京。据烟台的姐姐回忆,这些“关系”,虽无外乎就是两条烟、一件棉衣之类,但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开始认识最具体的社会,而伴随着这段生涯的,只有沉默。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一车粪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就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对于现实生活、对于过去,王小波少有着笔,对山东牟平,还有另外一段:“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人性被逆转后,人就糊涂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当时喜欢的女孩子在山西插队,罹患脑瘤,很快在北京去世。王小波告别体力劳动,任初中物理老师,工资三十多块,抽两毛多的好烟,一天要抽两三包。上课时总是从兜里掏出卷成卷儿的物理教材,也不翻开,凭印象板书、教学。
专业小说家的道路
当王小波回到北京,风华正茂而又前途未卜,脑力旺盛却又没有什么求知渠道,三兄弟都活得不是滋味。慢慢地在本子上写写划划,又逐渐有了一些武侠小说读。兄长王小平回忆当时几兄弟看金庸《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等等,“如十世饿鬼扑向佳肴”,“只恨小说写得太短”。只是读读也就罢了,这种热衷很快发展到动手练功。从小王小波就跟哥哥一起用哑铃健身,现在认识到光有“外功”还不够,内功才是要紧的东西。有时他盘坐在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告诉哥哥自己在练天山童姥的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功,还问哥哥有没有看见自己冲出鼻孔的白气。哥哥只好递给他“大前门”香烟,说这个白气来得更不费功夫。有一阵王小波还用侧掌奋力敲击椅子背,声称自己在练铁砂掌,有一天疼得不行,只好去医院照片子,却是尾指骨折了。
毕竟是知识家庭,恢复高考以后,兄弟姐姐5人都有了新的希望。在工厂当了几年工人的王小波补习了备考的课程,于1978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品检验专业,属于理科。王小波也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李银河。大学毕业后王小波在人民大学附属的一个学校当了两年老师,随后追随妻子到美国求学。
李银河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王小波只是陪读。来到大洋彼岸,换了全新的生活环境,写作的梦还在星星之火阶段,既要学英语,又要谋生活。妻子李银河读博士,同时做助教,在餐馆打工,可谓不是一般地拼。王小波也不能在家当闲人,餐馆打工也尝试过,但似乎并不是他的强项,英文又不好,郁闷总是有的,还是先谋个学位吧。虽然匹大有个东亚语文学系,但是针对洋学生学中文的,对于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写小说的王小波来说并不合适,幸而可以挂在台湾来的研究东亚史和社会史的许倬云教授名下,勉强完成了学位。1986年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夫妻二人自驾游历了美国,还“穷游”过欧洲几个国家。
1988年王小波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进北大,又是因为妻子李银河到北大读费孝通的博士后,安排他进去的,进去了在计算机室,没什么课题,每月工资130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北大帮闲”。到89年终于有机会给研究生代课讲社会统计软件的应用,不过学生好像都听不太懂,很快课又停了。
王小波想回到人大去,他向人大会计系主任展示了自己刚刚出版的小说集《唐人故事》,就留了下来,教英语,也帮系里打点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事情。一个星期统共只有一两节课,他仍然是一个闲人。阅读和写作之外,对计算机应用的热情一直持续,他开发出了供自己写作的软件,还预言未来的阅读都是电子阅读。时间闲,挣钱少,还想过把自己的写作软件卖出去。不过帮忙的朋友认为王小波的写作软件虽然打字快,但是操作复杂,是很难在市场上推广的。
1992年,王小波去人大会计系辞职,只对系主任说了一句:“给您添麻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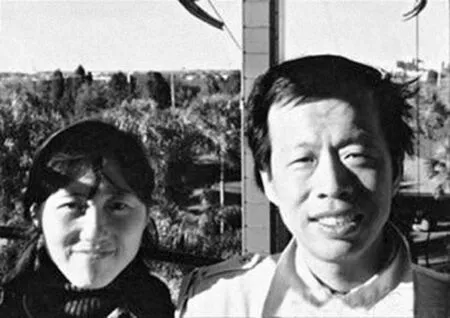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而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这一年,王小波40岁。既然回了国,就要考虑工资、社保,母亲很担心。7年前父亲过世,母亲怕给飘摇中的王小波夫妇增加负担,拖延了很久才告诉实情。
然而王小波觉得自己已经40岁了,“我是能把小说做地道的。”
自此,王小波都把自己开始创作的时间说成是1992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历经10年的断续创作和多次修改,91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最终在香港以《王二风流史》的面貌出版。3年前,王小波还在美国期间寄给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唐人故事》,被编辑包装成民间故事模样的《唐人秘闻故事》,定价2元,印数4000册,且算自费出版物,没有一分钱稿费。而最早的处女作《地久天长》,发表于上大学期间。更早流传于朋友中间的《绿毛水怪》手稿,说明王小波为这个“92年”开始的正式的写作生涯,已经准备了十几载了。从这一年开始,王小波可以简单明了地向人自我介绍:“我过去是个教师,现在在写小说。”
靠着联合报文学奖的25万新台币奖金,王小波似乎证明了写作可以养活自己,并且在北京顺义买了一个小房子,脱离体制的专业写作,似乎成了可能。1995年,王小波的小说《未来世界》第二次获得联合报文学奖。
在集中精力写作了两部仅有的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万寿寺》之后,王小波发现即便自己这两部小说写作速度很快,但还是赶不上出版的速度。最主要的是,“听说有一个文学圈,但我不知道在哪儿”,像自己很多作品的主人公一样,王小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圈的,虽然一些朋友为小说出版的事情四处张罗,但92年之后,王小波只在中国大陆出版过华夏版的《黄金时代》和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1996年秋,花城出版社与王小波签约出版“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稿费千字50元。 1997年4月11日,书稿正在发排,王小波阒然离世。
王小波的志业与遗憾
现在,有80后作家凭一部网络小说的IP挣上亿的资产,也有80后作家可以一夜成名。
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说家,即王小波所说的“把小说写地道”的、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家实在罕见,而王小波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也就是说,在这个以写作博取名利的时代,王小波维护了小说家这一行当的尊严。2000年,网络上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论坛。至今,已出版了五辑作品集,当年混论坛的写手里,走出了一大群媒体主编、出版人、作家、电影编导。
其中一位徐皓峰,后来渐渐摆脱王氏文风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担纲编剧的《一代宗师》,获香港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其所著的小说《道士下山》被陈凯歌改编为电影。去年,其编剧、导演的《师父》《箭士柳白猿》等电影公映,开创了中国电影的硬派武侠一路。
一个人的作品,不应该只是看它在当下卖了多少本,成就了多大的名声,更在于其作品是否可以长久滋养人、迸出新鲜的花朵。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无愧于自己的小说志业。
只有真正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人,才能明白王小波的价值所在。在众声喧哗、追名逐利的时代,王小波在中国社会的少数人心中,为文学建立了一条金线。任何一位作家,哪怕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不在这一条金线之上,自有人心来衡量。
一百年前的五四先贤们,普遍认为西方的文学要高于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伟大的文学名著《堂吉诃德》《莎士比亚全集》《神曲》等等,每部作品竟然是由作者在长达十余年的孤独或者流放中完成。而中国的文学名著如《三国》《西游》等,大多是集体创作、历经数代人而完成的。因此,胡适等人以西方比附中国,在四大名著前加上一个人的名字。
针对五四文人的这一态度,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也实在看不下去,其在《阴翳礼赞》中哀叹:李白和杜甫,是何等伟大的诗人啊。莎翁也好,但丁也好,能有他们那么伟大吗?
就像国家主权一样,一个国家的审美权,没有必要交给西方某个颁奖委员会。文学、电影也是一样,小说和电影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教育意义是深远的,其背后永远有意识形态的争夺。在激烈的争夺之后,于是,在现代读者眼里,西班牙优秀的导演似乎只有一位阿莫多瓦,西方现代小说的经典是卡夫卡、尤利西斯、普鲁斯特……

作家卫慧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正如10年前,很多欧美人以为中国优秀的小说家就是“上海宝贝”卫慧那样的,也许再过20年,中国优秀文学的代表可能只有一位郭敬明被海外推崇。
王小波的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充分呈现了现代汉语的节奏之美。他在《青铜时代》的序言里厘清了自己的师承,在引述杜拉斯《情人》的译文后,他说:
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王道乾)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查良铮)和王先生(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
这段话被经常引用。只是笔者认为,民国翻译家的名字还应该加上梁宗岱、傅雷、朱生豪等等,则更全面。
高晓松曾经在节目里说;“王小波是神一样的存在,中国白话文第一名,且甩开第二名很远。”王小波对现代汉语的贡献,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在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界,大多还在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选择中国的当代作品。现在强调“讲中国故事”,其实,语文教学界正是一个讲中国故事的有效平台。
王小波的写作也存在比较大的遗憾,笔者个人认为有二:
其一,童年过多食用钙片,这不符合中医的健康原则,身形过于高大,易加重心脏的负担,造成了王小波的创作生命不够长。
其二,其应媒体约稿、仓促成章的杂文易误导一些浅见之辈,不必太当真。尤其是他谈论国学《我看国学》《国学与智慧》等。毕竟,王小波是小说大师,他的名字与马尔克斯、卡尔唯诺等放在一起也并不逊色。但国学是体验之学,是实践工夫。不是西方哲学的知解之学,不是凭才华和知识记忆可以获得的。王小波的成长经历里,时代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我看国学》里,他说:
“……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这能看出王小波有传统中国的忠恕之心,对国学,也是抱着先了解再评判的态度。但豆腐,真是劳动人民发明不了的,那是士大夫修道炼丹才能发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