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归信息,爆炸归爆炸
——从“皓首穷经”到数字化阅读 >>>
2017-05-17杨徽图片网络
特约撰稿_杨徽 图片_网络
信息归信息,爆炸归爆炸
——从“皓首穷经”到数字化阅读 >>>
特约撰稿_杨徽 图片_网络

教师教学,和学生沟通,综合教材教辅和与教学相关信息,构思教案、形成课程。面对所谓信息爆炸、“信息焦虑”,计算机虽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处理方式,但在 “有形的信息”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经典阅读和独立思考形成的 “无形的信息”。
苏东坡的“想当然”
苏东坡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大意是说他参加全国科举考试,考官梅尧臣读了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大加称赞,认为可和孟子媲美。其中,苏轼为说明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用了皋陶要杀人而尧劝他宽恕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也非常赞赏,认为应列榜首,但对这个典故却非常疑惑,不知所出何书。
事后,欧阳修又专门询问苏轼,东坡的回答却让他大跌“眼镜”。他给老师讲了一个《三国志》曹操取幽州的故事。袁绍战败,曹操掳获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赐给儿子曹丕,孔融听说后,非常不满,即修书给曹操,编了一个故事,说周武王伐纣后,掳获妲己,赐给其弟周公旦。曹操见信大惑不解,史书明确记载妲己被姜子牙杀了,怎会被赏给周公旦?但孔融是当代大儒,想其话必有依据。结果问起此事,孔融就说:“我以今日之事揣测古人,只是想当然,并无出处。”曹操心悦诚服。
然后,苏轼对欧阳修说,他也是“想当然耳”。
后人传说苏轼文采,遂为美谈。其实这里涉及一个信息处理的本质问题。
现在,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信息爆炸”时代或大数据时代。据统计,全人类每年要产生约10亿—20亿GB的新信息。尽管计算机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处理方式,但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信息我们是一生也不会去看的,而有些只是需要时才看。不论生活还是工作,我们每天都要与百度、微信、微博、各类新闻客户端等信息媒介打交道。人们又称为“数字阅读”或“碎片化阅读”,更有甚者,患上了所谓“手机强迫症”“信息焦虑综合症”。
回到欧阳修和苏轼的问题,其实无论是讨论信息素养,还是数字化的教育,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信息只是知识,而每种知识又有根源,大部分信息只是这些基本知识的重复或衍生。
欧阳修是有名的博学,不仅文章卓著,而且主持编纂《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创设新体例而列为正史。史学讲究爬梳故事,“言必有征”,而苏轼则和孔融一样,更注重以理系事,认为寓言可以托古。穿凿史料肯定是史学家不能允许的,但在文学或哲学中却是成立的。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做史学家、文学家,我们接受的信息也从来真假参半。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穿凿历史的地方占大半。
苏轼提出“想当然耳”。在一个人的阅读上,其实就是经典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训练的问题。古人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对我国古人来说,经典是四书五经,在现代,则还包括西方具有文明起源和复兴性质的经典。如圣经、柏拉图、莎士比亚、歌德等。
我们时代的信息虽然看似杂乱无章,像是要“爆炸”,实则讨论的基本问题和方法不会超出这些经典。信息爆炸、信息焦虑的根源与其说信息太多,不如说正是因为信息唾手可得,我们不知选择,“学而不思则罔”。
“无形的信息”:读书得间
在信息处理方面,史学家可谓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其实,我们现在将数字信息的快速增长称为“信息爆炸”,而对缺乏先进信息处理方式的古人,这一点是同样的。
所谓“皓首穷经”,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编纂国家级文化丛书,先秦时《吕氏春秋》不过20多万字,到清代《四库全书》已达8亿字。信息增长的“爆炸”是一种自然趋势。

所谓“皓首穷经”,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会编纂国家级文化丛书,先秦时《吕氏春秋》不过20多万字,到清代《四库全书》已达8亿字。信息增长的“爆炸”是一种自然趋势。
清代经史学家章实斋就批评说:“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于一种贪多务博。”我们的信息化是否也是“贪多务博”呢?
在历史学界,就曾有一场数字化大讨论,所谓“E考据”,即利用数字化史料做检索和考据。一开始,人们认为,数字化“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有人甚至称为史学革命。但过了一段时间,令人失望的是,“当我们以数字化在一定范围内‘穷尽史料’后,所期待的‘史料大发现’时代却并未到来,我们依旧要在那几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寻求突破;技术手段的更新,也没带来终极意义的学术思维革命……”,于是又提出回归传统。(参见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对媒体从业人员,这一点可能感受尤为真切。尽管每天新闻层出不穷,新媒体“汗牛充栋”,但是,不论是我们称为浅阅读还是深阅读的东西,总不免在重复一些常理,“太阳之下,并无新知”,又或者炮制概念,夸大其词,博人眼球。后者比如有名的“罗辑思维”所谓“认知迭代”“共识税”“认知战”“后真相”。认知真的迭代了吗?认知的战争在哪里?真相后在哪里?
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信息化为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名词,如“慕课”“未来教育”“翻转课堂”“云教育”“自适应学习”……诚然,这其中包涵了技术转型的具体诉求,但这真的就是创新吗?又或者要不离最平常的道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而这些全都包含在《礼记·学记》中。
在这里,我们并非否定信息化为写作、教学研究带来的便利,只是,正如史学一样,我们注意到,这种以“检索”为核心的认知方式带来的局限和危险。我们读到一点“碎片”信息,然后通过关键词搜索,以此形成认识或文章。我们以为,关键词可以帮自己形成知识结构。但关键字机械的一面,恰好是屏蔽了其他知识,割断了知识间的有机联系。现在人开玩笑说这是“智商税”。史学家则把这种东西叫“史纂”,人成为一个“整辑排比”资料的机器。
而史学家给出的解决对我们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启发意义,即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先生所谓“读常见书”“读书得间”。意思是能从“常见书”中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常见书”即一种文化的“元典”和各专业的经典,“间”就是字里行间。换言之,读出“无形的信息”。这都是机械的检索式阅读无法获得的。
“得间”的方法,按史学家,一是比较几种不同信息来源,发现“隐藏”的问题,逆察作者写作的背景和目的,古人谓之“以意逆志”。
其二,有意识地发掘信息来源。通过检索获得信息非常驳杂,很多是重复转帖和摘抄的,必须发现信息的真正来源。换言之,言必有征。
其三,重视抽象概念,消化反证和异说。一个信息包含的论点可能有很多异说和反证,需逆查论据来源,作辩证理解,排除“假问题”和“假概念”。
其四,提防统计学和数据陷阱。统计数据常常是一种讨论问题相关性的假设,数据和结论不具有必然性。
最后,重视知识积累的系统性,博闻而返约。《论语》中,孔子教学生,即总括为“一以贯之”“本立而道生”,这也是“得间”的根本。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满篇寓言,“想当然”,真假参杂,用的是这样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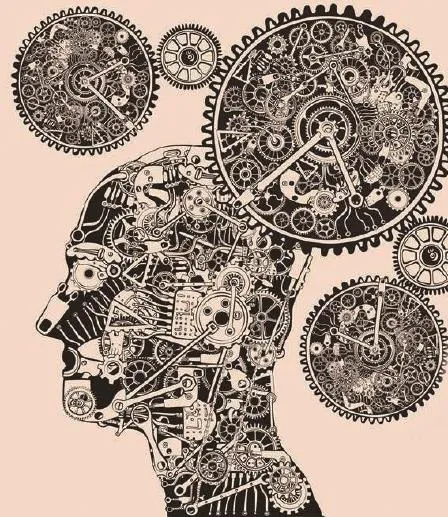
以“检索”为核心的认知方式中,关键词可以帮自己形成知识结构。但关键词机械的一面,恰好是屏蔽了其他知识,割断了知识间的有机联系。现在人开玩笑说这是“智商税”。史学家则把这种东西叫“史纂”,人成为一个“整辑排比”资料的机器。
“缘督以为经”也是一以贯之。庄子说的“督”,就是督脉,全身经脉的根本。民国大武术家薛颠讲“站桩”,也是练这个东西,本固枝荣,流通百脉,谓之“养基立本”。他用的还是《论语》的说法,“本立而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