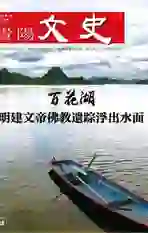河西路“23号”
2017-05-06高宁
高宁
18年18岁,这里是我人生之初的成长摇篮,是我走向生活的启蒙之地。河西路23号的生活烙印,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魂牵梦萦,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个家。
家的印象之一
刚搬到这儿,我们全家三代6口人:老太爷、老太太、在贵阳医学院读书的父亲、已是小学教师的母亲、在中学读书的姑妈、不满一岁的我。两年后添了弟弟高元,再两年半后又添了妹妹高晴。这一年,姑妈工作迁出,3年多后老太爷去世。8年后的1962年,全家人口又相对固定于6口人,直到1972年搬家。
我们家,佃黄家公寓式砖房二楼的两个房间。里间,一张大床,两张三抽桌,一个两开衣柜(现在还在),两对带茶几的木椅(现在也在)。听母亲讲,这对椅子还是搬到这儿时,家具太少,老太太临时到河沿坎买来给他们用的。初期,这间房是父母带着我住;晚上,这儿就是父母办公学习的地方,母亲备课,父亲看书学习。
这个房间,还是我们做自习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河东路小学读书,那时的学制是半天读书半天在家自习,住一条街的同学就组成一个自习小组,轮流到住房相对宽敞的同学家做自习,老师间或上门检查。家有两间房的在同学中不多见,所以很多时候自习都是在我家。
房间的南墙开有一扇窗,打开窗户就可看见隔壁市委宿舍,两层楼的青砖房屋围合成一个大院,带点苏式风格,是那个年代向苏联“一边倒”的作品。站在窗边,甚至可以同住在对面楼上的同学打招呼。放眼望去,远处民国年间修建的贵州银行大楼清晰可见(至今还在,已是工商银行),顶楼墙上楷体“贵州大楼”4字历历在目。
家的印象之二
外间,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个方桌、一个两开柜、一张三抽桌,一张半圆桌、一张老太爷专用的藤椅、几张凳子,门边一个放锅碗的木架、一个水缸,门口一个炉灶,基本上就是全部家当了。这间房,卧室、客厅、厨房、餐厅全在这儿。老太爷、老太太住这间,姑妈大多住校,不常回家住。就这么一间拥挤不堪的屋子,老太太居然还养鸡。最多的时候养了3只,白天赶到楼下,晚上又吆回鸡笼里。有一年,养的一只老母鸡还孵出了一窝小鸡,真把我们高兴坏了,成天就守着这些小鸡,比玩什么玩具都还要兴趣浓厚。
进门处一大水缸,盛得下两挑水(一挑为两桶)。刚搬去时,老太太请粮店隔壁巷子里的一个孤寡老头黄伯伯给家里挑水,从水站到我们家100多米,还要上到二楼。那时候的水1分钱两挑,一挑水黄伯伯收5分钱,可赚4分5厘钱。水缸后面的墙壁上用粉笔划满了“正”字,黄伯伯每挑一次水就画上一笔,十天半月老太太数“正”字给他结账。后来我们长大了,我和弟弟高元就一根扁担一个水桶自己抬水了;再后来我们又长大了些,就一个人挑水了。此时才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那时没有那么多讲究,哪家小孩都得干这种体力活。直到搬家离开,在河西路23号的18年一直是挑水吃。
这间屋的家具没几件(多了也放不下),至今都记得。柜子是梓木材料的,门上刻有诗句,因为是家里唯一的柜子,故餐柜、橱柜、衣柜都是它。最上一层放衣服;第二层是抽屉,放户口簿、购粮证之类的东西;第三层就放碗筷、油盐酱醋;下面一层是暗箱,叫“海底”,揭开中间一块木板就看见像第一层那么大的空间,也放了一些衣服。
老太爷、老太太睡的中式架子床,一年四季都挂蚊帐,看起来像一小房间。“小房间”离西墙约有半米的距离,形成一小巷,作为杂物间,除了堆放杂物,米缸、尿罐都放這儿。过道边的床头下除了堆煤巴,也塞满了杂物。
床边的三抽桌上也摆得满满的,茶盘茶杯、温水瓶,还有一个青花帽筒(至少是民国年间的瓷器啊,后来几经搬家,竟无踪影了)。就是这个帽筒,给我极深印象。每到中秋之时,像变戏法似的,一到晚上老太太就从帽筒中“捞”出一个月饼,于是,嘴馋的我一阵欢呼。原来,这是亲朋好友送给老太太的,她舍不得吃,留待晚上与我分享。分享的结果,自然是我吃大块,老太太吃小块。
窗边的方桌,吃饭的时候是饭桌,老太爷在世时,桌子抬到屋中央,老太爷端坐正中,由老太太或父母给他夹菜,每顿饭有一个咸蛋,而老太爷每每将这个咸蛋吃到一半就给了我——他的长孙;饭后,方桌归位,成了我做作业的课桌;老太太和她的牌友们打麻将,这张方桌就成了她们的牌桌;平常老太太做些针线活,饭前饭后的家务,都在这张方桌上。
整间屋就一盏灯,家家都这样。25瓦的白炽灯吊在屋中央,灯头后的电线很长,方便到处挂:吃饭、打麻将时吊在屋正中(打麻将时还用一张纸将灯泡围一圈以聚光);天黑了炒菜时还得长距离地拉到门口;晚上做作业时牵到窗边;睡觉时又挂到床头……
总之,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东西都得物尽其用。
家的印象之三
就这样的居住条件,煞是让邻居们羡慕,一家6口人两间房,三代人可以分开住。在河西路23号,这种条件的没几家,一是隔壁崔家,七八口人;二是对面三楼吴家,也是七八口人。其他人家,不论人多人少,都是一间房,有些房间还只是我们家房间的一半大。
在楼下的后院,黄家还将他家厨房的一部分隔给我们家使用,但楼下做饭菜,还得端到楼上,很不方便,加上对面就是厕所,后来就当杂物间使用了。
这里房租每月每间房7元,那个年代,这个房租十分昂贵,14元,几乎是一个三口之家的月生活费(1954年的贵阳,2角4分钱可买10个鸡蛋①),好在此时我们家还有大十字祖产租金的收入和母亲的工资,基本上可以应付。
20世纪60年代初,房租涨到了20元,而我们家大十字祖产也被“改造”为“经租房”,房租变成了“定息”,收入顿时少了许多,家里经济情况开始紧张。1962年,老太爷在这儿去世。1963年,母亲调到市府路小学任教。第二年,在学校分到了一间房,父母就搬到了学校的教师宿舍,把他们住的那间房让了出来。老太太仍然住河西路,老姑太从她的侄儿、我三伯伯家搬来与老太太同住。我们三兄妹就两边住了,上学的时候和父母住学校,放假后就回到河西路和老太太住;老太太到瓮安姑妈家时,我们又都回来住。总之,印象中这儿一直是我们的家。
这就是我河西路23号的家——一个艰难岁月中简陋而温馨、遥远且难忘的家。在这里,我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从襁褓之中到踏入社会,18年18岁,这里是我人生之初的成长摇篮,是我走向生活的启蒙之地。以后随父母数次搬家,直至我成家独立出来,住房条件、环境也随之改善,但河西路23号的生活烙印,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魂牵梦萦,无数次在梦中回到这个家。
(未完待续)
注释:
①我59岁生日,侄女婿送一珍贵礼物:我出生当天的《新黔日报》(《贵州日报》前身),报上就有贵阳当天的的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