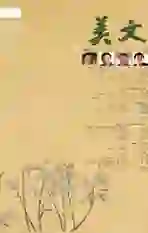冬虫夏草
2017-04-20木兰
滕 瑛 笔名木兰,湖南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24期学员,著有散文集《草木染》。
说起冬虫夏草,原是只会想起它的贵,身份贵、价格贵,是中药界的名贵药材,不知多少人为它趋之若鹜。前几年一位老人喜滋滋地掏出他从传销商那里廉价买来的虫草供我们观赏,那成色实在不敢恭维,黯淡无光,条形干瘪清瘦,可是老人仍然视若珍宝,仿佛得了冬虫夏草,日渐式微的生命就上了道保险,那每一根眉梢上颤抖着的喜悦我至今都记得。
我之所以看不上,是因为我曾经见过最为饱满的虫草,拥有生命张力的饱满。每一条虫草色泽黄亮、丰满肥大、雍容华贵,它们在一个透明盒子里呈扇形排开,像一尊美丽的珊瑚化石,那一小盒就是好几万。我被真诚地许诺无偿赠送一半,我不加思索地婉拒了。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我用不上,对于自己用不上的东西,再好再名贵也是毫无用处。我很欣慰,为这个拒绝我从没有暗自懊恼过。
现在说起冬虫夏草,除了想起这些,我还会想起西藏的山南,想起居住在海拔6000多米高、曾经采虫草为生的珞巴族小伙索朗次仁。
“索朗次仁”按照当地的习俗可以简称为“索次”,这样就顺口多了。索次是我的鲁迅文学院同学,九零后。索次的眼神很特别,像大雨洗过的澄净的天空,眼波里泛着晶莹的光,我的藏族同学拉旺对他眼神的形容更为到位:“他的双眼是雪域藏南,深山密林里的泉水,清澈而宁静。”
曾经每年藏历的三月至四月底,积雪尚未融化,索次就会随着大拨大拨的人流往山上涌去,人流最后一一息止在一棵棵虫草面前。虫草的价格以成色论,成色差的每根最少二十块钱,好的每根一百五十元以上,那时的虫草多而易寻,索次一天的收入都有好几千元。
尽管收入这么丰厚,索次却开始厌倦挖虫草的生活。这和他曾经厌倦后来逃离了父亲的生活一样。
索次的母亲是藏族女子,父亲是珞巴族汉子,父母成婚后分居,父亲离不开他的族人,离不开他的山林。珞巴族人如今已存数不多,全国3000人不到。索次从小便随父亲生活在高山峡谷地带的深山密林里,那里人烟稀少,交通十分不便。架栈桥、过独木、爬天梯、飞溜索、穿藤网都是珞巴族人的绝活,至今他们还在沿袭刀耕火种、狩猎的古老习俗。索次一心要离开父亲身边并非因为深山的日子难熬,而是父亲一次次举起大刀,一刀砍下牛头,牛头应声落地,牛血喷薄而出的情景实在太血腥,索次多次恳求未果,天长日久,索次对这种刽子手式的残忍愈发不能接受,遂毅然离开父亲,走出了山林,那时的他十二岁。
这样,索次便遇见了他的师父,一位佛学高深的苦修者。索次对他的苦修充满了好奇,最初师父并不接纳他,对索次的种种纠缠报以沉默。于是索次就在他面前故意射鸟,师父仍然沉默,索次又故意在他面前烤肉吃,这回师父开始诵读经文,抬脚走了。索次一路苦苦跟随。实在架不住索次的软磨硬泡,88岁的老人将索次留在了身边。在师父的教诲下,索次学会了母语(藏语)、读懂了经文,也看到了师父的世界里对一切生灵的慈悲心。
17岁时,师父说索次该下山独自去看世界了。索次下山后,做过民工,为藏民修过房子;做过演员,在舞台上身着珞巴族人的盛装,腰间佩戴着父亲传给他的花纹精美、个性粗犷的珞巴族大刀,舞台背景是茂密的大森林;挖过虫草,虫草补肺益肾,化痰止咳,可调节免疫系统功能,对于放疗、化疗后的红细胞修复具有相当大的功效,虫草的功效决定了它药品市场的奇货可居,索次身手敏捷,眼尖心明,所以他挖的虫草成色相当好,收益也相当高。这里还要旁涉一笔的是,索次非常喜欢仓央嘉措,非常痴迷他的诗歌,索次每天也会写诗,而把这些诗唱成歌对索次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索次的声线明亮,曲调蜿蜒转折,歌声好像会拐弯,美好得似乎从山南的深山密林的一汩清泉开始,飘悠着对接上了藏区那蔚蓝得不真实的天空上的白云,所以,他也是藏区的歌手。可是这一切都没有让索次停止过对师父的想念,时间过得越久,索次越发想念与师父在一起苦修的日子。
索次决定放下一切,再次回到师父独自苦修的山上,没想到师父竟圆寂西去,遗体正开始腐烂,面对此情此景,索次沧然泪下。索次流着泪悉心清洗了师父的遗体,整理了他的遗物,好像在收拾师父多年来对他的教导和养育之恩,向师父做了最后的叩拜后,索次便把师父背进了有冰的山洞,他则在下面的山洞为师父打坐诵经,不眠不休,不饮不食,整整七天。唯独那七天,他没有写诗,因为掉眼泪的时候不能写诗,眼泪掉下来的時候灵魂就走散了。藏民发现他的时候,他盘着双腿诵经的身躯已经僵硬,整个人枯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被藏民抬出来的时候,和师父一起苦修的时光和洞外明亮的阳光刹时照亮了他的心扉,他要继续他的苦修之路,去寻找他的人生况味。再次下山,索次说,不知何时山南已经传遍了他写的诗,他唱的歌。
我问索次:“你为什么苦修?”
“因为我苦了才能找到甜。生活本身就是苦修,有滋味的人生要修心,心才是你我的力量,轮回成‘我的力量。”
“你师父去世后变成那样子,你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他有一颗慈悲心。肉身腐了,慈悲心还在。他是一生苦修中圆寂的大善人,他能读懂人的心。”
“你怎么知道师父能读懂人心?”
“因为他吃过世间所有的苦。”
“你苦修途中有何感悟?挖虫草足以让你衣食无忧,你如何看待?”
“苦修中的每一天特长,因为我需要长命。苦修中的每一顿饭特香,因为我需要人间的美味。苦修中的旅途特孤独,因为我需要孤独的心灵。挖虫草也是个杀生的罪,钱财是魔,它可以迷你利用你,一生奴隶你。”
“什么是苦修?”
“苦修是一路做善事。小善事,你经过山路时,山上掉下的那些石头搬到路边,后来的行者可以安全地通过。大善事,可以救命,可以帮人。”
我大吃一惊:“你这么小,九零后怎么这么有思想?!”
“我不是九零后的思想,我是从师父的世界走出来的,走的是前方,但我要回头,往仓央嘉措的世界看,这是我的世界。”
善哉索次!美哉索次!索次从师父的世界看到了爱,回报了爱,从仓央嘉措的世界欣赏了美,延续了美。而我,从一株虫草的名贵世界,看到了浊世中索次的高贵,学会了取舍。
卷 白
卷白,顾名思义,和卷心白有共通之处。卷心白是我们家乡对包菜的称呼,这样一想,卷白的大致特征就不难呈现在您面前了。只是我觉得它更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菊花,丝状的“花瓣”蜷缩成拳,团团锦簇,当然,颜色没有菊花的那种五彩缤纷了,灰扑扑的,可是这颜色,实诚。卷白有花的形状,容易蒙蔽您的眼睛,自然也不是卷心白,少了一个“心”字, 不是蔬菜,也不是花。
“它还有一个名字---“打不死”,能治百病,是最好的伤药。卷白长在岩壁上,晒干制药,经半年后,放于阴凉有渗水处又可还阳。”说完这段话,舅舅又无声地笑了,笑容很大,整个嘴都咧开了,稀稀疏疏的三四颗被烟火熏黄了的大牙也不怕人看了去。
舅舅的中草药地摊就摆在高村镇的渔子坡,每逢农历的初四、初九、十四、十九、二十四、二十九日,他都会背上他的中草药袋子准点去县城赶集,和晒山珍、卖竹器的乡人们一起,把他的中草药各自用塑料袋装了,摊在地上,等候需要它们的人。舅舅有时候也去赶乡场,兰里镇的集日是逢农历的“一、六”日,吕家坪镇的集日是逢农历的“二、七”日。这些药有舅舅到山上采的,也有他自己种的,也有他从别处种药人或者卖药人那里收来的。有几年我体虚头晕,舅舅就送了他种的天麻来,喊母亲常为我用天麻炖乌鸡。这些年舅舅老了,85岁了,上不了山采药,也没种药了,于是他就从别处收点药来卖或者用来配外公传授给他的一些土方。卷白,就是舅舅收来的。“是从一个贵州佬那里收来的,当时那贵州佬告诉我这是还魂草,我当然不信啦。”
舅舅说卷白的样子和还魂草很像,虽然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还魂草,但他知道,只要把所谓的“还魂草”置于流水之上就可辨别真伪了。若它能够逆流而上,那就真的是可以起死回生的还魂草;若是顺水而下,那就是卷白。 要找到真正的还魂草,就得找到老喜鹊窝,老喜鹊和老喜鹊“树”的窝如今可难找了,因为只有老喜鹊的功力和耐心才能把窝“树”到三至五层。找老喜鹊窝有什么用呢?老喜鹊窝里有喜鹊蛋,趁老喜鹊觅食去了,偷偷地取来一个,用沸水煮熟,然后偷偷地放回老喜鹊窝,老喜鹊毫不知情,孵了无数日,其他的喜鹊蛋都孵出了小喜鹊,唯独这一个迟迟没动静。老喜鹊着急了,心痛了,会不顾艰辛衔来还魂草,放在熟蛋上一照,就知道这喜鹊蛋出问题了,若时日来得及或可还阳,若是来不及,老喜鹊就只得忍痛把这个熟蛋扔了。偷喜鹊蛋、煮喜鹊蛋以及故意让老喜鹊痛苦这种做法很残忍,可人是无法找到还魂草的,只有老喜鹊认得真正的还魂草。还魂草还可以分阴阳的,如果带着这棵草走在大路上,您会看到有的人是真正的阳间人,而有的人则是阴间的人“越域”窜到了阳间,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是快要去阴间“报到”了的人。
舅舅说的这还魂草不就是仙草嘛!“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还魂草”, 舅舅和卷白一样风尘仆仆的老脸,流露出一丝怅然。这么多年,很多人都知道舅舅梦寐以求想找到还魂草,也有很多人带了“还魂草”来见舅舅,可是都不是舅舅要找的还魂草。舅舅一定是希望这辈子能找到老喜鹊和还魂草的,那样,孝顺能干的小表哥就会还阳,再次侍奉于他膝下,小表嫂也不会丢下小孙子远嫁他乡,舅舅和小孙子也就不会被大表嫂、二表嫂他们不喜欢,只得住在江边竹林里那孤零零的小木屋了。
“当年你舅舅要是心狠一点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1956年的县法院院长叫王志柏,相当欣赏你舅舅的口才和内才,特意把他招到法院当法官,安排你舅舅判决刑事案和离婚案。还没干上一年,你舅舅连连摆手:‘做法官太造孽了!不是让人家哭哭闹闹、妻离子散就是让人家性命不保啊!”。母亲讲舅舅就为这个原因,不顾法院对他的盛情挽留和家人的强烈反对,“炒”了法院的鱿鱼,情愿回到绿溪口乡枫木林村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队队长,后来土地到户,舅舅就这样与“职场”彻底失去了瓜葛。舅舅从小在我精通草药的外公处懂得了一些中草药,治风湿、一些痼疾有两手,在农闲时就给村人治治病痛,用他自制自配的药方为村人按摩推拿,收不到什么钱,舅舅也从不提钱,包括他赶集摆的地摊,有人说:“先试试,用药按摩按摩吧,以后再给钱”,舅舅也没打一次“硬秤”,照旧乐呵呵地服务周到。有的人苦着脸来,被舅舅按摩一阵,一身轻松地走了,道再来,一直没再来。舅舅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放弃和所有人、所有事的时候,还是一脸的笑容,嘴咧得还是很大,皱褶里没一丝抱怨,更别提满怀怨气地诅咒或者愤愤不平地骂骂咧咧了。“慈不掌兵,善不掌财”,枫木林村一村子的人都这么评价我的舅舅。
我几乎没见到舅舅愁眉苦脸过,即使他一辈子家徒四壁,他都会笑眯眯地对着你。唯独小表哥“走”的那个黄昏,我看到夕阳大大地倾斜在他土屋后面,他坐在门槛上,满头白发被风吹得乱糟糟,他矮小瘦削的身影在偌大的门洞里显得凉飕飕的。“舅舅……”我低低地喊了一声,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犹疑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很空洞,可是仍然笑了。“没事,他不要我了,我不怪他的。”这话或许是對我说的,或许也是他自语的。后来再去看舅舅时,他又总是一脸的笑容了,仿佛把小表哥忘记了。
可是慢慢地,就有些种药卖药的人说舅舅放出了信,想找到还魂草。
“唱歌师您为大,天上梭罗有几枝?又有几枝金龙角?又有几枝开金花?”舅舅唱起了山歌调侃那个妄想用卷白代替还魂草的贵州佬,别说贵州佬答不出来,换作我,我也答不出来,我好奇地问舅舅答案是什么。
“唱歌师我为大,天上梭罗十二枝。上有六枝金龙角,下有六枝开金花。”舅舅又用山歌回答了我,果真如村里人所形容,舅舅的山歌好似春江水,取也取不完,大概是看着我欣喜的样子,舅舅那老脸上的笑容更大了,皱纹也更深了。
我相信舅舅,可是不相信世界上真有神奇的还魂草。回来后琢磨了好一阵,也查阅了一些神话故事中能够起死回生的仙草,除了灵芝,再无其他。舅舅说的还魂草会是灵芝吗?不对!舅舅明明也种过灵芝,他的中草药地摊上赫然供着一枝灵芝的呢!
那就从卷白入手,总能找到点蛛丝马迹吧?在度娘那里我查阅到了关于卷白的很多资料,图文并茂,生动翔实。通过比对验证,卷白实际上是“卷柏”,家乡的“白”和“柏”发音都是一个调。卷柏多生于向阳的山坡岩石上或干旱的岩石缝中,随风移动,遇水而荣,在长期干旱后只要根系在水中浸泡后又可舒展,在最后,我赫然看到:“因其生命力极其顽强,故而卷柏又名‘九死还魂草,我心头一震,原来舅舅心心念念要找的还魂草其实就是卷白啊,贵州佬并没有骗他,“还魂草”并不是因为能还魂才叫“还魂草”,而是它自己九死后仍然能“还阳”才叫的“还魂草”啊!
我当然不会去告诉舅舅这个结果,也不会去纠正舅舅这么多年来对“还魂草”的无限遐想。舅舅心中有梦,梦中有“还魂草”的样子,我心中也有“还魂草”的样子,那是舅舅咧开嘴笑的样子、唱山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