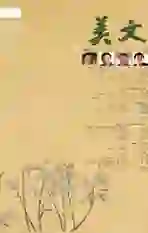世界的世界
2017-04-20李达伟

李达伟 1986年生,现居大理。作品见于《大家》《青年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有长篇系列散文《隐秘的旧城》《潞江坝:心灵书》《暗世界》和《民间》。长篇系列散文《暗世界》获2014年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曾获滇池文学奖、《黄河文学》双年奖,孙犁散文奖、滇西文学奖、保山市文学艺术政府奖等。
1
我意识到已经不能以纯粹的牧人身份再次出现在那里。我远离了那些高山草甸峡谷很长时间。我在种植中草药的人中看到了父亲。父亲跟我说再种一年,明年就不再种了,地荒着就让它荒着了。父亲开始接受了一些现实,他感觉到了身心俱疲。
现在,父亲和我赶着羊群。父亲和我赶着几百只的羊朝草甸更深处走去。除了父亲而外,还有一些狗跟着羊群,那些狗憨态可掬。那时是羊群领着我们进入那片草甸的,但我深信有它们的道理。我们相信羊群的嗅觉以及视觉甚至听觉,它们早已把所有的感觉器官打开。有时会被它们带到一片长有繁茂的草的角落之中,但我们根本不会有丝毫的诧异感。我有强烈的感觉:自己的感觉远远不如那些随时在荒野中经受浸淫的生命。由羊群可以无限拓展出去,在那片山野之中还有众多的生命。
你就在那些地方发呆,你真是发呆过。在那片山野之中,在众多的问题涌现出来时,一只鹰正在山谷之上盘旋着,盘旋了一会儿之后,它暂时停在某棵枯干的枝杈上(那里曾发生过大火,在近百年之后,许多枯干的树木还没有倒下)。你与父亲就在那个山谷之中闲谈着,你们不再去关心羊群,也不再去关心那只鹰,那时父亲只是想消解横亘在你们之间的隔阂。你把头转向了某个方向,你不再把目光对着父亲。父亲不再说话,背影有点落寞。看着父亲的背影时,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背负着茫然、不安与苦痛的背影。我只是暂时的牧人,我也意识到自己只能短暂地帮父亲分担一些事情,而时间这么短暂,其实并不能真正分担什么。有很长的时间,羊群从你们眼前倏然消失,但父亲跟你说不用去管它们,它们会在某个时间里再次出现在你们面前,但父亲也强调了一下,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的话它们就会出现。父亲与你在那一刻,同时想起了有那么几次它们并没有按时回来,其中一次它们消失了将近一个多星期。
你们就那样静等着,你与父亲之间长时间无话,你听到了风呼呼地从群山上面席卷而过,有一棵枯木摇晃了一下,但并没有倒下,枯木上面的啄木鸟依然不停歇地啄着,它似乎应该早已习惯了风与那些枯木之间的拉锯。风声中出现了羊群的声音,羊羔的声音清越柔软却锋利,那些清越的声音锋利地割开了冬日的草甸。羊群出现在了远处的山坡上,那时落日的阳光孱弱地在山坡上滚落,羊群从阳光中退到阴影之中。那种退入的情景成了一种隐喻,羊群成了一种隐喻,山野成了一种隐喻,我也必将只会成为一种隐喻。那时父亲早已不在,那时你必须一个人赶着那些羊回到山谷之中,那时父亲正在垛木房里给你做着晚饭。你和父亲不回家,你和父亲早已把山谷之中简单修建的房屋当成了另外一个家。在面部表情失去作用的黑夜之中,父亲与你躺在两张头正对着的床上,你们很想掏心窝子一会儿。你在假期结束就回学校教书,而父亲依然要在那个山谷之中,他依然会很少回家,而家中只有你的母亲住着。你父亲在那些山野之中不断行走着,你的到来暂时缓解了一下父亲的腿疼痛。他的腿经常疼痛,在那些山野草场之中,他早已感觉到了过量行走的痛楚与尴尬,他早已无法跟上羊群的速度,他从来就不是其中一只羊,即便有时他会把自己当成一只羊。在那些山野之中,他经常学羊叫,他的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那些羊会在他模仿羊叫时停下啃食草而把目光注视着他,那些目光之中有着一些复杂的东西,但突然它们会从山坡上冲下来,它们听懂了父亲的叫声。那时你是在父亲旁边,而在很多时候,父亲只是自己一个人。父亲便真正变成了一只羊,把自己的精神真正放逐在那片山谷之中,那是真正的放逐,那是真正的自我放逐。如果父亲不成为一只羊的话,在那个被密林围裹起来的角落里充盈着的寂静足以击溃父亲内心的强大。在那个山谷之中,寂静真是能击溃任何人。有时,父亲会遇见一些亡魂。还有一些亡魂在那片山野中游荡着,这是某个祭师说的话。
2
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世界。我瞬间被那片高山草甸所吞没。你在那一刻深切地感受到了卑微渺小。我想复活那段时间。那时冬天将要过去。那时父亲暂时隐去。在早晨太阳光线的作用下,大地清丽苍茫。我的前面是一些牧人。他们正进行着的是转场,他们从山下上来,他们要寻找一个好的高山草甸。我有意走在他们身后,远远望着他们的姿态。无界的感觉,他们早已与这个世界无缝对接。那时需要和那个世界和解的似乎就只剩下我一人。他们朝我微笑,我加快了步子混入他们之中。其中一个牧人走在羊群前,有那么一会儿,羊群自觉地跟隨着那个牧人。但那样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太长,羊群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它们不再自觉地跟随着牧人。我不停地东奔西跑着把羊群赶回那条隐约的路上。路早已变得隐约模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很少有人在那条路上行走,很少有牲畜出现在那条路上,也很少有野物在那条路上行走。许多生命在那片高山草甸里,习惯的是自由,它们的眼中有着众多穿过那片高山草甸的路径。而在我们的眼里,那时就只有一条路径,我们正遵循着众多牧人走过的路径穿过那片草甸。你会有进入了世界的世界的感觉。我是在进入世界的世界。世界之外的世界,我是熟稔的,而世界之内,世界的世界我却是陌生的。
在大地上行走的一群人。我们长时间保持沉默。其实我想说话,异常渴望说话。直到来到那片要长时间停留的草甸上把一切安顿好,我才知道那些牧人同样很激动,他们一改前面的沉默,话匣子猛然被打开。他们谈论着那片草甸,他们谈论着那些羊群,他们谈论着某处水源,他们谈论着曾经来过那里。我总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是有距离的。其实距离很近,我只需要稍微改变,距离便会消失。距离感是完全可以得到消解的。那是牧人的世界。我熟悉牧人的生活。我曾经也是一个牧人,并不是外来者。对于这个世界,我早已很熟悉,只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次来到这个世界而已。
我们知道在那些高山草甸上生活着的不仅仅是我们,还生活着很少的高山彝族。我们离他们很近。我听到了他们偶尔在高山之上吆喝的牧歌,或者那不是牧歌,那只是他们虚构或者创造了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跟他们的牲畜进行一些对话。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羊群、牛群、马群。他们的放牧,似乎比我们要简单一些。那些牲畜习惯了被放养,它们一年四季都在山上,他们只是给那些牲畜搭了一些棚屋,为了抵挡冬日的风雪。而我们需要长时间跟随着羊群,我们不敢一年四季把牛马放养在山上。我们慢慢地也学会了他们的放牧方式,我们大声吆喝一声,那些羊群就纷纷把身子转了过来,其中有一些还会朝我们叫几声,叫声意味深长。
我们与那些高山彝族之间有了一些闲聊。那样的闲聊似乎没有多少意味。但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那样的闲聊也在改变着我们彼此。那是那些高山彝族接连搬到了山下之后,我们才猛然意识到的。他们与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他们常年在高山草甸上放牧。而我们会在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回到山下放牧。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山下的世界。对山下的世界,我暂时没有什么牵挂。我看到了那些在草甸上已经干掉的牛屎,那些牛屎在某一刻给了我一些错觉,牛屎图案,就只是图案,牛屎消隐,那是一个异常让人惊诧的图案。在那个世界里,许多东西消隐,我们会产生诸多的错觉。一些牛先于我们来到了这里。不同人的命运,以及一个世界里不同生命的命运。在很多时间里,我的注意力不只是在那些羊群上,我还把注意力放在了诸如那些牛屎身上,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诸如某棵青草之上,某棵青草开始变绿,某片青草开始变绿。我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物。那些牧人会在某些时间里,用这样的方式抗拒着世界的单调。他们会在某些时间里变得恍惚。这只是我的猜测,但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曾看到了某个牧人呆呆地坐着,那时他把目光放在了近处。我把目光放在了远山上。我看到了某个牧人把目光放在了远山上。远山上出现了一些牛羊。远山上还有着另外一些牧人。我们会见面。我们会在远山上见面。我们会在远山上谈论着那些高山草甸。我们会觉得一个牛屎粑粑是有无限美感的。我们会觉得远山上的一切都是美的。
3
我早已熟悉高山彝族聚居的世界,我熟悉他们某些时间里的生活日常,毕竟我也曾是他们生活日常的一部分。他们早已学会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用白族话沟通无碍。他们在来到我的出生地读书时,需要快速掌握白族话,老师会用汉语和白族话(双语教学)交杂着上课。我们看到了他们一开始的迷茫与无措,但那样的迷茫与无措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我们不一样。我看到了他们在那个高山草甸上很短时间的暂住,然后某一天他们赶着自家的牲畜浩浩荡荡离开,很少有高山彝族会在那个世界长时间生活的。他们似乎都有一颗飘荡迁徙的内心。似乎只有不停地迁徙飘荡,才有可能让自己真正安静下来。而在某一天,他们竟跟我说起,他们的迁徙是为了让某些牲畜安静下来。那些牲畜会对一个太过熟悉的世界失望。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我只是相信是他们自己对于一个世界失望了。那些高山彝族几乎相继远离了那个世界。最终只留下了很少的几家人。现在,在那个高山草甸上,我们已经很难遇见彝族牧人,我们更多只是遇见了我们自己。我们有着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我们也有着不同的对于世界的恪守。
我出现在了那些垛木房前。我曾多次出现在了那些高山彝族的垛木房前。我在那些建筑前站立了一会儿,然后擦了擦嘴角便进入了建筑内部。那是他们的火把节,他们过火把节的时间在我们前面,他们杀了一些牛羊。在那个节日里,我们一定能吃到的是苦荞粑粑蘸肉汤,每次参与他们的节日,我们都吃得满嘴流油。我们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但我们并不排斥这样的饮食习惯,他们的饮食习惯里暗含着让人着迷的粗放、热情与美好。在他们的饮食习惯面前,我们显然委婉了些。有人夹给了我一大块牛肉,我抬着碗坐在某个角落里慢慢嚼着。而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匹枣红马正在嚼着那些草。它朝我望了一眼,便继续嚼着草。我也朝它望了一眼之后,继续嚼着我的肉。
这个世界,与我熟悉的世界是有一些区别的,区别不只是饮食。那是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族群所制造的差异。文化就在那样的世界里交汇碰撞。我们也目睹了那种差异的不断被消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相互模仿学习,我们在模仿与学习中让彼此杂糅在了一起。我们的一些东西也被他们改变着。我们成了像他们一样的牧人。我们成了像他们一样只是种植土豆荞麦青稞的人,我们也成了像他们一样在高山之上不断饮酒是为了消解孤独,同时也为了驱赶寒冷的人。
我跟随着羊群进入大地深处。我们便经常在一些高山草甸上相遇。如果你出现在那个世界里,如果没有人有意指出我们所属于族群的不一样的话,你将会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区别。我们早已不再穿白族服饰,他们也早已不再穿彝族服饰。只有在婚礼上,我们才看到仍然坚守的服饰上的差异,但我们都不敢肯定我们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我们似乎只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回到出生地。我们已经与出生地有着一些无法消解的距离。我们似乎已经没有了瞬间消解距离的能力。那些高山彝族的某些人端起了火枪,朝夜空放枪。那是每个火把节时,都要进行的。而某一次,其中一个人把枪对准了人,那人被枪击死亡。他们的那个习俗便在那人被枪击死亡之后消失了。他们意识到了某些习俗所暗含的危险。一些习俗以这样的方式在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们的记忆在时间的流逝面前所出现的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之后,我们似乎忘记了是有那么一些习俗的存在,我们甚至会忘記是曾经有那么一些高山彝族生活在那里,而且里面有那么一些人与我们很熟。记忆到底怎么了?记忆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在我重新成为一个牧人后,一些记忆正重新变得清晰准确。
4
那个冬日里,牧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即便眼前的世界,渺远辽阔,人烟稀少,但我能看到的是成群的牛羊,以及已经苍老或者正在苍老的老倌:放羊的老倌,放马的老倌,放牛的老倌。如果我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的世界将会变化,那些渗透到内心深处的感性都会变化。那时,我就在其中的一座山上,那时正有一些人来到那座山上建一个测试风力的塔,那时隔着我只有几步远的就是那个在山间长时间砍伐古木的外地人。没有人跟他说起不要砍伐那些古木。那时他的眼眶里所透出的竟是清澈与平静。群山与古木似乎早已把他眼眶中的那些锋利与异样的棱角磨平。他似乎早已把自己是一个外地人的事实忘得一干二净。而那时相对于他而言,我才是与这个世界有着距离的人,而且距离异常明显。我早已不顾自己的羊群遁入某片草甸。我想跟他谈谈。我羡慕他那时的状态。而那些来建塔的人在把塔建起之后便离开了。那座塔很醒目。我一眼就看出了那座塔与眼前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东西。当看到一只鹰停留在塔的某个部件上时,我竟然会有几丝隐隐的不安,我竟然看到了两者在那个世界所完成的融合,一只鹰竟那么快就习惯了一座从未在那个世界出现过的塔,而我总是有点不适应。有那么一会儿,我成了那座塔,而那个伐木者成了那只暂时栖息在塔上的鹰。
传言开始在那个群山之间来回冲撞。我们将在那个山谷之间看到风力发电。我是在别处看到了风力发电。而在眼前的群山之上,风力发电一直没有出现,那个用来测试风速的塔也慢慢被弃用。我们总觉得恍惚之间,那个塔上转动的齿轮机翼便停止不动了,那个塔开始真正变为僵硬化的存在。僵硬,冷漠,突兀。但我们曾期待那个塔能转动起来。我们不去考虑风力发电本身。而那个外地人,一定是有这样强烈的渴望的,毕竟在那个山谷之间,即便有鸟兽草木发出的单独声音以及复杂组合的声音。但在他看来,那样的声音还是太单一重复了一点。他不曾想过那样的声响的真正作用,以及那样有着山野草木的气息所对人的重要。
我与那个外地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对眼前的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私底下谈起了在那个世界里混杂繁衍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时间迅猛往前。这人是死了。很多人都在传言。他的死是事实,有关他的传言是别的方面。在传言中,他的性格被重塑。起初当我意识到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时,我有点点感到惊悚,我真不敢真正面對他,而当自己真正面对着他时,我又感觉到了某种程度的平静与不可思议。我想和他好好谈谈的想法,最终成了只是想法。他多年前便驻扎在那个山谷之中,他不停进行着的就是砍伐古木,然后倒卖给别人。此刻我面对着那个他曾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山谷,那时云雾缭绕,群山若隐若现。他的死因有着各种传闻。但人们都相信他是被一些人杀死的。谋财害命。他那简易的房屋被烧毁。烧毁的房屋只是人们制造的假象。有些人说,他在那个群山之间砍伐了那么多的木头,是该遭到一些报应了。你是无法轻易判断眼前的这个人的。你是无法轻易判断已经被人谋杀或者是自杀的这个人的。你甚至已经无法复原那个生活日常的现场。你就只是看到了一个颓丧的现场。你只是看到了一个人最终所能拥有的颓丧。我是忘了问他一些想法,毕竟我们是曾在一起喝过那些高度数的土酒,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是有过袒露内心的想法。我是应该问他要什么时候才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看到了他多次已经表现出来的笑而不语,那种笑是有深意的。我们是希望他早点离开那个世界,而他偏偏就不想顺我们意。而突然之间,他便顺我们的意彻底消失了,并化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其中一种融入眼前的世界的方式。
5
我又成了一个牧人。我的身上携带着一点点不安与迷茫,而那些真正的牧人身上似乎只有从容与平静。我们几家人把羊群赶在一起,我们要在那些高山草甸上一起放牧一段时间。等到在高山草场上让羊群吃得毛色开始亮起来,我们才会再次分开。分开的日子是需要祭师来掐算的,那天我们还要请祭师来那个高山草场帮我们祭祀,那时我们需要祭天祭高山草场祭神灵。举行着那场祭祀的时候,我是有着强烈的敬畏天地的感觉的,我知道自己又有一段时间不能来到那些高山草场了,那时我又开始感觉到了某些不安与失落。在高山草场里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意识到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牧人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同时也意识到了在那个世界中真正的牧人正在消失。我和父亲对坐着,我们谈起了羊价,羊价突然变得惨不忍睹,眼前铺散开的是几百只羊,但我们想到低廉的价格就忍不住唏嘘。我们早已不再到处转场。我们就在其中一个山谷中建起房屋,固定地放牧着牛羊。
6
这时我是一个牧人。我可以是我自己。我也可以是任何一个牧人。苍茫的原野大地,你就孤身一人,我们众多的牧人都将是孤身一人。只有这段时间我们是聚拢在一起的,我们分工明确,而当这段时间转瞬即逝之后,我们将回归孤独,或者回归属于一个人的平静。我们在大地之上自我消解孤独,我们会很长时间不回去。我们还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羊群之上,羊群曾经历了狗灾,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狗在那些高山草甸上围攻羊群,那些狗早已不是猎狗,或者它们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猎狗。没想到的是最后自己家的猎狗也去吃我们的羊了,这无疑是最让我痛心疾首的,当时我把自己的猎狗引诱回来,然后痛下狠手。那一刻只有自己知道那是会让人绝望的孤独。
我杀狗的时候是午后,阳光从那个被古木围着的世界里已经消退,那样的时间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恰好就赶上了那样的时间。我必须动手,它已经捕杀了我的好几只羊了,里面还包括了一只小羊羔。我目睹了那只小羊羔在草地上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并兴奋地抖着尾巴朝母羊走去,我早已见惯了那种场景,但每一次再次见到时,我都会再次感动,莫名的战栗感,有时眼角还会有泪水掉落,只是没人见过我流泪。在羊群的瞳孔里,你看到了类似永恒的东西,即便羊群接连被羊贩赶走。但你必然要适应那样的情景,你掐指一算,一年你至少要三次面对那样的场景,你早已变得冷漠,你早已让自己有所希冀,你早已让那些羊群的离开变得洒脱,即便你看到它们在你面前的犹豫,即便它们似乎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而在无奈地抗拒着。永恒的东西,似乎也在慢慢崩塌。个人的命运便与这些羊群牵扯在了一起,我日复一日进行着的便是放牧。我长时间望着群山、草甸、羊群,只有它们于我才是最有意义。我便是每天从这些东西上面汲取类似力量的东西。在那样貌似不是很广袤,但于一个牧人和几百只羊而言已经很广袤的高山草甸里生活是需要一些力量的。那些羊群的命运便是我的命运,至少可能是我的某种命运。是跟着羊群的过程中,我目睹了群山的日渐稀落和草场的日渐颓败,我突然之间就成了一个在大地之上孤独行走着的悲观主义者。也许是由于自己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人的缘故,我必然要思考一些东西,可能是由于自己胡思乱想多了之后就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只有羊群才会真正能够让我暂时远离那些无处不在的悲观。当我离悲观主义远了,我便离自己的羊群近了。那些狗总是偷偷绕开了我。那些狗来自何处?这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那段时间,我紧紧地跟随着羊群。那段时间,我对众多的狗痛下狠手,那些狗在我变得日渐残忍之后慢慢从那个世界消失。
我的足迹是那些羊群踩踏下来的足迹的一部分。我循着羊群的足迹进入了一些自己平时并不想怎么进入的世界。有些祭师的足迹也循着羊群进入大地深处,那时祭师已经不只是祭师的身份,他们那时也是牧人。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在那些高山草甸上跟着羊群行走的牧人基本都是祭师。他们是祭师,他们的内心深处所充盈着的是敬畏之心。敬畏天地之间的一切生命。在天地的褶皱间,牧人发现了众多生命的蠕动,任何一种生命的蠕动都足以消除牧人的孤独,并让牧人进入某种恍惚之中。在那样的恍惚中,我们只是感觉到充溢的幸福感,那时我们忽略了眼前的世界的凄凉,以及在某些季节里在世界之中飘荡着的凉风。那时我是躲在了某个山谷之中,那时羊群和我一样都躲在了那个山谷之中,我们都在躲避着风的侵袭,但我们同样坚信那些山谷之中的枯木不会在我们出现的时间里折断。我们似乎朝那些无处不在的枯木一望,那些枯木便有了生命,那些枯木在我们离开的时间里先后折断倒地,那时只有一些生命见到了某些枯木的彻底消亡。那些枯木早早地就在那些山谷中等着我了。那些众多的枯木背后是曾经发生的一场大火。我们都只是在口传历中经历过那场大火。如果没有那样一场大火的话……?我会在那些山谷之中呆呆地想着。
牧人会经常情不自禁点起一场大火。我也曾在某个冬日里点起了一把大火。大火把那些草甸上的枯草吞噬得黯淡凄惨,但我们知道在某个时间里,青草会迅疾地把那些凄惨与黯淡覆盖。我看到了另外一些人点起了一把大火。其中就有邻村的那个习惯漫山遍野到处跑的姑娘。她痴痴地看着其中一人点起了火。她向那人要了火,自己也学着那人点起了火。我远远地望着他们点起了火,我看到了那个女人在手舞足蹈。我们都担心那个女人会在别的一些不恰当的时间里把那些高山草甸点燃,而最终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在一次又一次遵循着季节点燃的火面前不断变得清醒。现在我早已看不到她漫山遍野跑的样子。她早已成为别人的妻子。她早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而我会对那样的一场火产生依赖。如果某天我们不再点起火的话,我会不会有点失落?我确实是会有点失落,人们早已不允许我们随意点起火。我们需要更长的時间等着那些青草的再次发绿。我和羊群都有点不适了。但我们必须要适应。而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出现在那个世界之中,现在暮色降临,我和羊群正被暮色吞没。我成了一个多少有点尴尬的牧人。我们都必然要面对身份所带给我们的尴尬与焦虑,只是因为这样的困惑直到现在才来临。作为一个牧人是尴尬的。作为一个孤独的牧人是尴尬的。
7
一个火葬墓群就在我的面前。那些墓碑上刻着的是梵文。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世界里曾经又是怎样的世界。世界被世界覆盖。我们早已很难把握那个过去,我们往往只能把握现在,或者我们连现在都很难把握。我是无意间出现在了那里。那是开始在暮色中沉睡的村庄。但我只是绕了过去,我需要的是再次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羊群身上。羊群在夜色中必须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找到了其中一家人寄宿。我边放牧羊群,边把羊群赶到集市上,这样的经验其实不是很多。我赶了好几天,才把羊群赶到那个集市上。我再次走在返家的路上,我绕过自己的村庄,我直接回到了那个高山草甸。羊群在那个堆积着厚厚的尘土的大道上狂奔着,尘灰飞扬,它们朝着那个集市奔去。远处,草甸中间的土路上,还奔腾着一群黄牛,它们不是朝集市奔去,它们朝着草甸中的某个水源奔去,我望见了它们的饥渴,它们熟悉那片高山草甸上的任何一处水源。我还望见了几匹马慢悠悠地在那些路上走着,我知道它们同样是为了某处水源,可能是它们的饥渴程度没有那些黄牛厉害。如果那些羊群也奔向那些水源?我对这样的情景也异常熟悉,几乎每一天我都要面对着它们奔向水源,饱饮一顿,然后重新在那片草甸上铺开,等着我来把它们赶回圈里。而现在,我赶着它们却是朝集市走去,我意识到了那些羊对于我的信任。我在它们的信任中经过了几个村庄,然后到集市,然后再次回来,回来时,只剩下我自己。我的心情会在短时间里变得复杂。但只需要时间,我又会再次回归平静。我就在这样不断反复中感受着源自反复的力量。
8
你曾有过突然之间就郁郁寡欢的经验?
你曾有过在面对着群山静默时的无助感?
你是否有过在面对着那些转场的牧人时会莫名感动?那些人就是那个世界之中的一部分,我们在内心里有着那种对于那些人的熟识感,我在感觉到了强烈的孤独时,我就会想起那些人,而这段时间,他们正出现在其中一片高山草甸中,他们严格按照着多年来留下的作为牧人的姿态。我远远地看着他们。这时,我就在某个山的垭口,他们就在对面的某片草甸上。我父亲朝他们指了指,我便看见了漫山的羊群,我还看到了漫山的牛马。但在一些季节里,那些羊群牛群马群就会从那座山上消失,我曾多次在那样的季节里出现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我的眼前是空落落的。某一次我眼前出现的是禽鸟,以及正在蛰伏的草木,那时我多少会感到悲伤与孤独。那时最为真切的就是恐惧感,在那个世界里有多少生命?我知道是那些潜藏于暗处的生命,让我感觉到了强烈的孤独。我便有了在这样的世界里郁郁寡欢的经验。我便有了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对着群山的静默所产生的无助感。我想迅速从那个世界中抽离。但我还不能从中抽离。那棵枯树上一只啄木鸟正在啄着朽木,它突然之间停了下来,发出了几声叫声。啄木鸟叫,将会有人来接你,父亲曾这样跟我说起过。我知道父亲正走在来接我的路上。父亲会不会在路上逗留一会儿?毕竟这时我正在呆呆地望着那只啄木鸟,当我感觉略微疲乏了便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别处。而父亲,他在路上行走时,会不会受到了一些东西的干扰?
9
有时会有不属于自己的那种感觉。有时我会沉陷于那种自我的思考之中,也许,太过自我也是不好的。小舅和我两个在那个出租屋里闲着,我知道小舅是有期待的,而我根本就没底,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而最终我的尝试彻底失败,在小舅的女儿那件事上我变得手足无措。小舅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在那些群山之间,疾病很快就能拖垮一家人。小舅是异常疲惫的,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疲惫。小舅与我之间并没有进行过多的交流。我们都感觉到了周围空气的凝固,但我们都疲于应对那些凝固,那时我突然之间就想躺靠在凳子上,沉默,并让我的内部暂时得到休息,而那时最应该休息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应该是小舅。当听到小舅女儿离世的消息时,我的心情异常复杂,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了疲惫与不安。小舅的女儿与我不一样,她早早就外出读书,而她学的是一所卫校,而最终自己还未成为医者时,自己就撒手人寰。她出现在了那个世界,就是那个山谷之中的世界,她对于这样的世界是异常熟悉的,就像我对眼前的这个山谷同样异常熟悉一样。我们都曾经是牧人,只是我们的身份只是暂时的,在成为牧人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逃避着这个世界,说得具体些,我们一直想逃避眼前的那些牛羊。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不可能逃避那些牛羊的。我们把时间花在那些牛羊身上,同时,我们还把时间花在了那个山谷之中,在山谷中,我可以随意沉睡,我不用管那些牛羊,它们在每天的某个时候就会陆续回来。而她作为牧人的时间里,她其实并不轻松,即便她家的羊群不是很多,她要不停地注视着它们,她会担心那些牛羊会闯入某片庄稼地里,或者突然迷失在那个世界之中。她又把自己的牛羊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再次成了牧人。我正堕入一个熟悉而更多是陌生的世界之中。
10
边缘世界。边缘思想。边缘文化。我早已身处边缘之中。我是边缘的一部分。在我成为一个牧人时,我就是边缘的一部分,这时我只是与羊群以及很少的人与物有了一些联系。在那些边缘的世界之中,还有一些孤独甚于任何人的人,也还有一些不曾孤独过的人。那些孤独者的思想。那些不曾孤独过的人的思想。与那些边缘的文化相遇,于我只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只要我有了出现在那些边缘世界中的想法并真正去实践它,我就能与那些边缘的文化相遇。我一直都是游离于现在我所生活的世界之外,我是强烈感觉到自己的肉身与思想的努力挣脱以及溃败。我会受到这些世界的一些暗示与启示。我们其中有一些人就在那个世界里得到了一些暗示与启示,我们崇拜那些天地自然,我们还依然坚守着最为朴素神秘的祭祀活动。某个祭师像我一样坐在了那个群山之间,应该是我像某个祭师一样坐在了那个群山之间,我们要学会听风嗅风,我们在风里就能感受到这些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气息,风里有着青草喷薄而出的声息,风里有着那些牛羊的气息,风里有着那些古木的气息。我们迷恋这些气息。我们一直迷恋这些气息。
曾经有一些人以为那些奔跑着的汽车需要进食,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拿了一把草找寻着车辆的嘴巴,他们一群人跟在那个人的身后来到了那辆汽车旁边,他们努力找寻着,最终他们并没能找到熟识的嘴巴,司机有那么一会儿脸色尴尬,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他只能近乎绝望地摇了摇头,然后开车从他们面前消失。有人给我讲起了这个事情。这是在那个世界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嘿嘿地笑出了声。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会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让人不堪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能佐证着那个世界的曾经边缘化。我们就在那样的边缘化中不断成长。他们曾经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距离竟然如此大。我们就是需要解决距离的事情,时间轻易就把这些事情解决了。我们一直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离开那样的世界,似乎只是为了避免那种类似的尴尬会在那个世界中继续发生。我们不会轻易去找借口。我找不到去找任何借口的理由。世界正在变化着。但我们身处的世界依然是在最为边缘的世界,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成了“偏狭落后边缘”的代表。“边缘”。是有点边缘化了。那是群山之间,与那个世界一样的世界与角落还有很多。我们是很迷恋中心。我们情不自禁就会提到世界的中心。我们在关注边缘文化的过程,其实只是在关注我们自身。我们的理想并不是很深远,我的理想就是以后能伐倒一棵大树,许多人早已轻易就伐倒了许多大树,而我只需要其中一棵便够了,而直到现在,我还依然没能伐倒一棵大树。如果我们伐倒一棵又一棵大树的话,密林早已离我们而去。密林是重要的,特别是于那个世界而言。我们穿过了层层的迷雾。我们要穿过有着密林覆盖的大山。我们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个伐木者。伐木者的角色是我们不能轻易评判的。许多人正在以评判的眼光评价着很多事情。而最终我们一些评判往往错漏百出。那我们索性就不评判了,但我们又控制不住那种评判的欲念。
那时我就坐在那个世界之中。群山之间。林中路上。还有一些高山草甸。我曾以为自己就在那个世界里,以牧羊人的身份或者别的身份一直生活着。对于身份的认知,一直都将是模糊的。我朝远处望了望。我是朝远山上望了望。那里有着一些隐约可见的路。我想沿着那些路进行那些路指向的路径。我知道那些路径会指向那么一些人,一些高山彝族,还指向一些村落。那些高山彝族生活的世界是我熟悉的,又是我所不熟悉的。
那次我一个人来到了某户高山彝族家前面,他们正在建着房子,华丽的彝族服饰,他们朝我望了一眼,我跟他们说起了自己的来意。那时我是提到了自己要越过他们所在的地方往山顶走去。我要去寻找那头走失了好长时间的牛。我问过很多人有没有见过那么一头牛。很多人都对我摇了摇头,很多人都很肯定地对我摇了摇头。我满意于自己能够把一头牛的特质简洁明了地表达。他们只是略作停顿就肯定地回答了我。在我到处寻找那头牛的同时,还有一家人也在到处寻找那么一头牛。他们的牛与我们家的牛惊人的相似。我突然意识到了到处询问一头牛的不好。在面对着那户彝族人家时,我依然把牛的特点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同样摇了摇头。我们还请了一个祭师把我们做了一次祭祀活动。他掐指算了很久,他只是指给了我们大致的方向,我们朝他指的方向望去,那里有一片密林,密林围着一片竹子。父亲摇了摇头,人们似乎从未进入过那片竹林里,那里的竹子太密了。我们早已放弃了进入那片竹林。那片竹林也因此保存得很完整。而现在我们必须要进入那片竹林了。我们进入了那片竹林,但我们一无所获。但我们不会责备一个祭师。那毕竟是一头一直习惯自由的牛。那头牛一年四季几乎都在山上。我们都近乎有点绝望了,而最后我们竟看到了牛从那片竹林里面走了出来。它比消失以前长得更壮了,毛色变得很亮。当我们把它牵回家中之后,另外一家人来到我家。争论不断。但我们也暗自窃喜。消失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牛早已不是原来我们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了。
现在我想再次出现在那户彝族人家生活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搬走了。不知道那户人家还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我将看到的就是一些遗址,一些废墟。遗址与废墟。最终只会是一些废墟,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时间面前,生命都太过脆弱。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只有通过记忆才是最好的返乡方式。我们只有通过老人们的絮叨,回到了那个真正属于我们的故乡。有那么一会儿,我还是多少有点固执,而在那个群山之间静静地坐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我多少变得释然了。遁形者,以及遁形者的故乡,以及遁形者的思想。我们似乎离故乡越远,我们便离边缘越远,但似乎又不是这样。
我还要去寻找一匹马。我们都很着急。天气开始变化。我们许多人抬头望向远方与天空后,他们都肯定地说一场大雪就要降下来了。我们必须要在这场大雪降下来之前找到那匹马。那匹马将要产了。我们一直期待它能顺利产下来,这将是它产下的第一匹马。但我们都很忧虑。情况很糟糕,马会在天气剧变的情形下往高处走。那匹马便是往高处走去了。在那场大雪降下来之前,我们没能找到它。那时我们只能期望山神的保佑了。我们只能通过一个祭师来暂时缓解我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一匹马对于我们意味着很多。一匹刚产下的小马对于我们也意味着很多。我们还曾冒着风雪找它,但随着雪堆积得越来越厚,我们彻底放棄了。我的脸上结着细碎的冰凌,我冻得瑟瑟发抖,当我把手伸向那堆柴火时,手指关节冷得发疼。
11
我强烈感受到了自己正堕入的应该就是会给人强烈的孤独感的世界。那时没有一只飞鸟。如果出现哪怕一只飞鸟,给人的感觉也将会不一样。而我在渴望能见到哪怕一只飞鸟时,飞鸟迟迟未出现。飞鸟,在这里不只是意象,不是那种虚妄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时我只有把目光放低,直接低到那片草甸之上。那时福宝也正把目光放在地上。他正痴痴地拨弄着一些花草。花草的种类在我们低下去的那一刻开始变得丰富庞杂。在那些花草面前,在才九岁不到的福宝面前,我就不应该以孤独者的角色存在着。我是矫情的。很多人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矫情。我的孤独,或者属于人的孤独必然要有原因。我们在那个群山之间开始讨论原因。原因似乎一目了然。破败的山野所给我们带来的孤独与茫然感是强烈的。我们都很难拒绝某些矫情。我们就在那片草甸上在碗里灌满大麦酒,那个烧制的过程正被家里的女人抢去,她们的感觉似乎比我们更好,她们似乎只需要通过轻嗅空气里慢慢变浓的酒精分子,就能判断能否酿制成功。女人酿制酒。而我们只是负责喝。我们就在那片高山草甸就着月色喝酒。我们还想在野外大声唱歌,但我们还是多少有所收敛。但这只是在还未喝酒之前,随着我们不停地喝酒,许多人越喝越兴奋,他们开始放开了喉咙,而我总是在喝一点酒之后就会感觉到疲乏不已,我想睡觉,但他们不让我睡觉,我索性就躺在了略微潮湿的草地上,听着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女人,我们环顾四野,夜色苍茫凝重,但确实没有女人。他们还谈到了草甸本身,草场的沙化,草场在每年的雨季都会遭受一些侵蚀,明年我们的转场又该走向何方?这些情绪在酒精的刺激下在那里释放着。我在人们的叹息声中睡去。而当我睡醒后,他们依然喝着酒,但那时他们已经不再叹息,而是說话断断续续磕磕绊绊。我们在转场的那些时日里经常会这样。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在那些无尽的黑夜里,我们又该如何抚平内心里喷涌的多少想法?在这次转场中,我们又新增了好些羊。在看着那些小生命的诞生,同时我们可以不断触摸它们那毛茸茸的小身子时,是我们感觉到最为幸福的时候。我们的幸福可以被那些羊羔记录,我们所收获的幸福的量远远超出了产下的羊羔的数量。就在转场那段时间,我们对陌生人也特别敏感。我注意到了他,那是留下我一个人在那个临时搭建的屋棚里的时候,他猛然出现了,见到一个陌生人,我是会有点紧张的,那天所有的狗都已经不在,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对峙。他熟悉另外那些牧人。他说自己也是个牧人。口音不同。不是我们那个小世界里的白族。他朝某座山背后指了指,在那个山的背后。我的眼前是一个没有确定的世界。他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人。虽然我们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我还是多少还有点固执,有很长一会儿,我们之间并没有说多少话,他就在屋棚的一角坐着,他要等着他的朋友们回来。我只是有点点拒斥他们。他们不仅仅只是牧人,里面还有很多偷伐木头的人,眼前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地界内不断砍伐,还在我们的地界内不断砍伐。当我们出现在那片高山草甸时,会经常见到砍木头的人群,他们午后的返家显得浩浩荡荡,一个人前面赶着至少两匹马。我就在望着浩浩荡荡的人群时,感觉了某种莫名的不安。不安的理由,其实在那一刻我也没有理清。我只是觉得还是多少有点不安。这时我们可以想想河流流量减少的原因了。这时我们可以好好想想那些经常出现的泥石流了。一片密林是重要的。我们都觉得从草甸中流过的河流都会受到影响了。但不仅仅是这群人。但我至少是因为这群人而排斥眼前的那个人。我是与他们有着强烈的不同的。但能轻易去评判他们吗?我感到有点点沮丧的是竟然没有任何人会在私底下去谈论他们。他们一直存在着。
12
最后的牧人,远去的牧人,以及那些远去的人与自然。有无数的细节。牧羊人因为草场的荒漠化以及别的诸多原因而消失。他哭了,那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牧人身份已经成了过去,以及短暂的现在,那时他的羊群还在他面前,但这些羊的价钱他早已和人谈妥了。放了这么多年的羊,总有一天是要与这个身份诀别的,他早已知道自己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形的,只是他不曾想过当这个时刻真正来临时,充斥于内心的苦痛与复杂。最后的牧人都要面对这样的情形。他索性在那片山野之中,大声地痛哭起来。他痛哭那些与羊群有关的无数细节,他痛哭自己在那天里的最后的牧人身份,他痛哭自己将要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是一个命题,那些羊同样也要面对这个命题,而羊群最终的去向似乎最为简洁与残忍,但那是作为牧人的他必然要面对的,他早已不去想象它们的结局,羊贩子会来那里把羊群赶走,就像现在这样。而我并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情形。我只是暂时的牧人,我无法懂得那个牧人的内心。在那些群山之间,有着多少这样的牧人?我们只能在一些口述史中知道这个群体数量的庞大,其实他们不只是面对着羊群,他们还要面对着时间与空间所制造的诗意以及与诗意无关的众多东西。那些牧人的心灵史?我根本无法懂得那群人的心灵史。我与他们之间一直有着一些无法消磨的裂痕,我都没能真正解决好那些裂痕,在我出现在其中一些人面前时,他们本想变得真实些,但似乎他们也会在突然之间就变得不再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