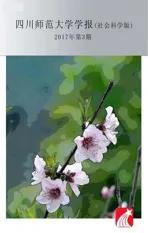但凭彩笔成新论,谨作昆仑睥睨人
——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评述
2017-04-14柴剑虹
李 军,柴剑虹
(1.四川师范大学 a.国际教育学院,b.文学院,成都 610066;2.中华书局,北京 100073)
但凭彩笔成新论,谨作昆仑睥睨人
——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评述
李 军1a,b,柴剑虹2
(1.四川师范大学 a.国际教育学院,b.文学院,成都 610066;2.中华书局,北京 100073)
先秦楚辞自屈原时代创起以后,各类楚辞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尤其最近数十年来随着欧亚大陆上古史研究的不断推进,随着先秦时代中外文化交流考察与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多学科针对这一空间范围所展开的研究,业已揭示出屈原时代乃至先秦更早时期,处于东亚核心区域的中原华夏文化与西域以西广大地域就已存在着事实上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基于人们既有思想的不断更新,现代宏阔的学术视野、学科观照,以及一种广义的知识学结构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条件在当代学术中的成熟,我们今天对先秦文化的考察,包括对屈辞的研究,都可以突破单纯的版本、考据、训诂、章句疏解,或者突破其形式与内容方面纯文学化、文学史化的诠释局限,突破旧式文献、文学研究禁锢的传统路数,从而在一种更广义、综合的宏观层面上展开,并借以通向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化同时也更具可能性的探讨空间。职是之故,笔者欣喜地发现,中华书局新近出版汤洪所著《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以下简称《屈辞》)一书,正是以这种新的研究理念与模式,利用最新获得的新材料、新证据,包括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新成果于屈辞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具体说来,《屈辞》一书的理论创见、方法论创新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该书以屈辞文本中的重要地名昆仑为坐标基点,综合考察流沙、赤水、不周、西海、崦嵫、西极、冬暖之所、夏寒之所、黑水、三危等屈辞中不时出现的域外重要古地名,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破立结合,详细论证,大胆否定传统屈辞注疏者对这些地名所做的杂乱解释。作者认为:在延续2000余年的屈辞诠释史中,传统注疏就有关地名解释与认定的繁芜、散乱与自相矛盾,实际所暗示的正是词义真相的隐匿与缺失,由此必然需要一种更具解释力、更有宏观统摄性的知识诠释系统来加以揭示。作者提到,该书之所以“昆仑”为坐标原点,正是因为在屈辞代表作《离骚》中“诗人的神游线路始终以昆仑为中心”[1]22。因此在第二章针对昆仑的详考中,作者的结论是:屈辞“昆仑”,与传统楚辞注疏所谓祁连山、黄河之源、缥缈仙山、日没之山、和田南山、西极之山、阿耨达山、西域之国等繁乱说法皆不相关。屈辞“昆仑”与诸籍所载青海湖以西之国名或山名、西域民族名、帕米尔高原、葱岭,以及其他概念化之高邈大山、大昆仑、小昆仑、海内昆仑、海外昆仑等等诸说也没有必然关系。中国境内之昆仑,首为汉武帝官方追寻河源所认定,以后历代直至清朝,官方皆多有循此痕迹追寻河源、认定昆仑的举动。种种纠结,无非源于学者死守黄河导源于昆仑之信条所致,黄河源头有不同认定,昆仑就随之而变化。中国现今之昆仑亦仅只为德国学者洪博德于19世纪晚近时期所主观认定,这与屈辞文本中“昆仑”的原初本意,早已风马牛不相及。从语言学角度看,通过检讨“昆仑”一词的语音索源,通过考察该词语本身书写之混乱,以及比较语言学上“昆仑”在不同语言中造词所呈现的特殊形式,皆可以推知昆仑当为音译外来语词,其原型应为上古先秦时代自西亚文化圈传入的外来语汇。由此,作者依据苏雪林等前辈学者的考证基础,提出了一个以西亚古巴比伦阿拉拉特山或为上古时代昆仑神话地理原型的解释模式。以此“昆仑”为该地理坐标的原点,作者继而通过广泛的证据考究,进一步尝试性地提出屈辞所言流沙或为阿拉伯沙漠;赤水或为红海;不周或为东非大裂谷;西海或为印度洋或大西洋;崦嵫本为西海之神,其后演化为大地极西之山;西极或为大地极西之地;何所冬暖或为赤道;何所夏寒或为北冰洋;黑水或为吉瑞尔河;三危或为西极之山……。最终,在《屈辞》一书里,作者以逐层推演,步步跟进的论证方式,针对屈辞文本中众多蕴含神话色彩的域外地理词汇系统,大胆建构起一整套空间秩序明晰、结构得当、逻辑严整、指示详尽的泛欧亚大陆地理解释模型。
第二,通过对屈辞文本2000余年传统文献注疏的梳理考究,《屈辞》作者发现在这些混乱芜杂、歧义互生的域外地名诠释的背后,根本上折射出的却是一种历史、政治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意志,以及某种文化的、民族的认知变更痕迹与无意识绵延。换言之,自汉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屈辞注疏者,其各自针对这些域外地名的解释都并非只是与注疏家个人研究习得、学术理念,乃至其有关历史、地理知识储备与文化学养相联系,而且还深刻关联着注疏家所处的不同时代特征,如政治局面、历史条件、国家大一统处境、民族与种族观念、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历史观、地理观,以及时代知识运作状况等。“国人对于地理地名的认识、理解总是与时代、政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228。“后世学者对于屈辞域外地名的解释充满着大量的主观性、随意性、当下性以及不确定性色彩。……其深层处却无不关涉着不同时期学者和学术所处时代、社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宏大背景。……无不与其所处特定历史语境密切关联。”[1]228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2,任何对于历史、经典的解说,都不过是阐释者所处时代社会思想的一种曲折反映。这一观念用在文献学领域,在有关屈辞文本、屈辞地名词汇的理解和阐说上,也大致无二。
以该书第十一章为例,作者认为“三危”一语,从先秦汉初文献所指本为“大地极西之山”这一模糊语义,到唐代最终定型为“敦煌县东南三十里”的“三峰”之山,大致经历了近千年的注疏演化和语义讹变历程。其间第一次较为明显的变化是汉末郑玄引《地记书》的说法:“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同时相关文献引郑玄语也认为:“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这一解释正是将“三危“具体化为中国政治版图境内实际地理称谓的第一案例”[1]170。到晋代杜预、郭璞等学者那里,“三危”的释义已从“鸟鼠之西”的相对模糊说法进一步迁移到瓜州敦煌[1]171,这是“三危”语义出现明显变迁的第二阶段,但其后还仍旧处在释义不断转换的过程中,直到唐代李泰、张守节等相互引证中所提示出来的“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1]172这一明确的地理方位解释为止,原本属于域外模糊指义的“三危”一词,最终被坐实为中华大唐国境之内的一个具体地点。“三危”以外,屈辞文本及先秦文献中有关“西海”、“西极”、“崦嵫”、“流沙”、“赤水”等诸多原义本为域外宽泛指称的地理名词,经由两千余年的注疏流变,也同样都经历了大致类似的中国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阐释讹变过程。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并非只在于注疏家个人的某些主观因素,而更在于其背后某种宏大的国家话语意志、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的潜在支配。“汉代以后,特别是像汉唐明清这样的盛世王朝时代,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以及中华文化自身的统合性内在驱动力也必然要求将一切异域之物、神怪之说、不经之谈、迂阔之论整合到一种严整通透的言说秩序之中,甚至于使之成为一种权威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而任何经典文献的注疏阐释历史,……正是这种国家意识和历史意识自足流转演变的具体显现”[1]175。
第三,在具体论证环节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屈辞》一书就有关屈原使齐的两次经历以及对于稷下学宫与邹衍“大九州”学说的了解接受这方面的详细论证。从逻辑上讲,为了证实屈辞有关域外地名所包含的世界性原初地理意义,就需要从诗人主体,也就是创作者自身知识形成的角度,讨论屈原是否拥有这样一种“世界性”地理意识与广阔的历史时空观念,是否主观上就首先具备充分的域外文化知识结构。因此在该书第十三章第二点,作者针对邹衍“大九州”理论对屈辞的影响所展开的实证研究,就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创见意义,而且在文中还起到了理论沟通与逻辑衔接的重要作用。在这一小节,作者充分引用司马迁《史记》、桓宽《盐铁论》、王充《论衡》、刘向《新序》等文献中的相关材料,通过一种“三段论”式的推论,准确发掘出屈原使齐、稷下学宫、邹衍大九州学说的盛行等事件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历史性交集,通过指出这些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为屈原内在性世界地理观的论证找到一条坚实有效的证据链。第一,屈原所处的战国中后期,正是一个学术开放、文化人士与知识群体信息流通极为便捷,人们知识系统和思想视野相当超前、广阔,具备世界性眼界的历史时代,其中以邹衍“《禹贡》九州之外,复更有八州”[3]473-474的“大九州”理论为最具代表性。第二,同样是这一时代,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七雄之一的齐国,其“稷下学宫”这一特定学术机构,对当时各诸侯国、所有知识人士都具有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其间,屈原作为楚国外交使臣的两次使齐经历,必然同样受到齐国“稷下学宫”中各种学说、理论、思想主张的深刻影响。第三,在“稷下学宫”这一学术机构里,作为“稷下学术”重要内容之一的邹衍“大九州”理论,以及由“大九州”理论所延伸开来的世界性地理知识与天下观念,必然深刻影响到屈原思想及其诗歌创作。由此,作者通过这部分文字从文本创作主体,从知识发生学角度为其主干论述提供了颇具效力的内在依据。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旁证。“通过考察屈原齐国之行及其在稷下学宫的可能性游历生活,通过深入探讨屈原与邹衍及其学说之间的深刻渊源,我们显然已找到诗人屈原世界性地理知识的一种显明确切的来源渠道,‘大九州’学说在战国时期中原各地的盛行流传显然为屈原作品中所呈现的世界性地理意识提供了学理上的重要依据,一种堪称‘有典可查’、清晰可辨的推理论断。”[1]198-199
第四,作者通过该书所表现出的宏观、整体性的研究策略与论证模式,这一点也值得肯定。如前所评,本书的最终论证落脚点在于尝试给出有关“屈辞”中系列域外地理名词的真实指义,将思考触点指向于早在战国之前更早时代的外来文化传播遗痕,从而对屈辞中既有明显域外文化因素又具有神话绚丽色彩的系列地名做出具体明晰的世界地理学界定。作者在该书中所得出的结论,虽然表面上看似天马行空,出人意表,但这些观点的提出,首先是在扎实的文献考证、章句训诂以及全面梳理和详细比较各种屈辞材料的前提下展开的。作者面对2000多年来浩瀚繁多的屈辞注疏史料,以及当代学术背景下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资料,力图做到举重若轻,得心应手;同时,作者在具体研究处理这些材料之时,又能不拘泥于文献,不沉陷于材料,而是以一种历史的、总体性和俯瞰式的学术眼光与气度大胆展开学术推衍,通过综合运用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现象还原、哲学诠释、文本细读、语言学对比、神话原型考察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因此在我们看来,《屈辞》一书中虽然某些具体结论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思考途径和处理方式上,作者敢于突破传统文学与文献研究之门径,敢于运用最新的多学科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尝试开创出一种新的楚辞研究范式——屈辞学术的泛文化研究模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我们选择“范式”这个词语,正是“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4]9。结合《屈辞》一书的论证,虽然目前还不能准确评估这种屈辞研究范式的成熟程度及其学术开创性意义,但是毕竟在这里,通过多种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引入,以及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最新方法论的综合使用,对于从事楚辞研究的相关传统模式(如经典训诂、版本考订、释义辨析、作家或文本考察、文学史影响等)而言,本书无疑更具有一种突出的现代气息、学术品质与思想高度。我们由此认为《屈辞》一书真正尝试性地开创了一种研究楚辞的新范式,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当然,本书也同样还存在着一些白璧微瑕之处。例如,在尝试指出屈辞中每一个域外地名之明确的地理原型方面,作者的论证力度还显得较为薄弱。文中所用于正面立论的依据,就屈辞研究这一具体论域而言,毕竟仍属于一种间接、旁涉、或然性的论证材料,相对缺乏更多的、尤其是更直接有效的证据支撑。另外,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作者显然还难于把握上古汉语与同时期西亚多种语言之间的对应与关联,难于确定“昆仑”等语词的准确语源。因此,本书在论述到末尾时,确乎就显出了一些仓促的局面。对此,作者本人也是同样有所自觉的(见该书结语)。但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掩盖全书的创新光芒。我们有理由认为,该书正是近年楚辞学研究领域一部较为优秀、颇具分量的重要论著。
[1]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唐 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