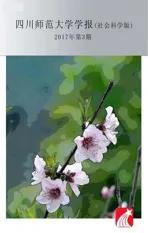当前台湾电影创作的文化趋向
2017-04-14谢建华
谢 建 华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播学院,成都 610066)
当前台湾电影创作的文化趋向
谢 建 华
(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与传播学院,成都 610066)
当前台湾电影表现出更强烈的文化表达欲望,在思潮化、模式性的创作实践中,阐述台湾电影对地方、自我与国族建构的重大转变。其文化趋向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怀旧,作为一种文化修辞,创作者通过丰富而纠结的历史怀旧想象,试图重构台湾的历史定位和地域关系;二是发现台湾,通过富有台湾特色的环岛体叙事和富于地方色彩的民俗、传统植入故事,持续进行发现台湾的文化写作;三是“鲁蛇”励志,通过一群乌合之众从溃散经团结走向成功的故事,将台湾社会的集体挫败感浪漫化。这些现象延续近些年台湾电影由“中国叙事”向“台湾叙事”转变的惯性,其表现出的文化离心力必须引起警惕。
21世纪;台湾电影;文化趋向;创作实践
近20年来,波诡云谲、风云激荡的社会文化剧变,在台湾艺术生产领域产生了链锁性的断裂和冲突。电影创作常常在“统”与“独”、“中国历史”与“本土台湾”、“后现代”与“后殖民”、“国族”与性别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纠结对立中随风起舞,陷入历史迷思和思想焦虑,这对我们的台湾电影观感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
1.台湾电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一方面,随着台湾电影语言发音的大幅改变,闽南话台湾方言、客家话、原住少数民族语混杂在一起,替代之前的国语(普通话),成为台湾电影的主体声音。参映两岸影展的台湾电影也一改惯常做法,不配国语,语言已成我们观看台湾电影的最大障碍。台湾电影到底是通常意义上的“国语片”,还是地方性的少数民族电影?语言似乎已溢出台湾电影的既定理论框架,对台湾“国片”命名所对应的地理、文化、国族、认同提出质疑和挑战。
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电影的人才架构和资本渠道更为多元开放,多数台湾电影具有合拍背景,台湾电影的辨识越来越困难。例如在岛内以台片上映的《被偷走的那五年》、《101次求婚》,都有大陆中影集团、华谊兄弟的身影。这些影片是台湾电影,还是应该叫“泛亚电影”,或更宽泛的“华语电影”?
2.台湾电影的艺术趣味到底是什么?
查阅近几年台湾本土市场流行的影片票房数据,带有强烈殖民怀旧色彩、艺术质量上乘的《嘉农》(KANO)卖得好能理解,以历史穿越为噱头的《大岛埕》票房傲人、严肃历史反思片《军中乐园》票房惨淡就无法理解;如果以猪哥亮为卖点的主流商业片《大尾鲈鳗》创造票房奇迹符合市场的话,故事松散、艺术低劣的《闺蜜》广受追捧就让人大跌眼镜;甚至像《做你爱做的事》这样学生作业式的低门槛影片也能收获149万新台币的票房①,而同期岛内上映的大陆电影《致青春》却只有42万票房。台湾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影片?他们的观影趣味是什么?
3.大陆电影在台湾的市场境遇为何越来越差?
2014年,台湾最卖座电影的前十名均为清一色的美国片,仅《变形金刚4》单片就收获20亿票房。华语片票房前十名中,台湾电影7部,香港电影3部,没有一部大陆电影入围。放映的7部大陆影片仅占当年台湾华语电影票房的0.59%,而美国片以占比34%的演映数分享了高达87%的票房总量,排名第二的日本也以74部影片占据整个市场3.42%的份额。全年岛内大型影展16次(场),多数以日韩巨星或欧美名导为主题,除台湾片商佳映娱乐举办的小型“贾樟柯影展”外,没有一次跟大陆电影有关。大陆电影在台湾市场的这种惨淡状况,已成近年来的常态,甚至不如20年前两岸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在国民党当局执政八年、大陆释放众多红利的背景下,这一境遇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这些疑问和困惑,表面上攸关资本、制作、演映和观众等电影产业的诸多具体问题,实则是台湾电影文化心态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实际上,近几年的台湾电影也的确表现出更强烈的文化表达欲望,在思潮化、模式性的创作实践中阐述台湾电影对地方、自我与国族建构的重大转变,电影生产的政治性在此获得深刻的阐释,这才是我们该引起重视的核心问题。
一 历史怀旧
按照文学批评家柏姆的说法,怀旧是一种欲走还留的意识活动,往往透过空间往返、时间交错来表达“一种失落与错置的情绪,但它同时也是个人想象的罗曼史”[1]14。近些年的台湾电影明显表现出对历史怀旧的迷恋和执念,创作者往往通过回复性和反思性的怀旧叙事,以史观表达为主要诉求,藉由离散个体的时空穿梭结构提供离返辩证中的生命经验,实质是台湾历史重述中的情绪表达和政治想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批判气息。应该说,历史怀旧已成当下台湾电影的一种文化修辞,巧妙而又别有用心地将坚硬的政治宣言埋伏在温暖的怀旧故事中,通过丰富而纠结的历史怀旧想象,试图重构台湾的历史定位和地域关系。
魏德圣、叶天伦等导演的创作路径,即勾勒了台湾电影企图全方位重述台湾历史的宏大野心。按照导演魏德圣的说法,《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嘉农》均聚焦“日治时期的台湾”,致力于将那个所谓“最精彩、最有趣的时代”还原出来,重释“台湾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的个体经验[2]51。《嘉农》根据1931年台湾嘉农棒球队进军日本甲子园赛事的真实事件改编,由1944年殖民历史行将结束时驻守基隆港的一个日军开始回溯历史,引发了一个长达184分钟暖色调的怀旧叙事。一个严肃不苟、温情理性的日本教练,一支溃不成军、却亟需正名的“鸡尾酒球队”(汉人、番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殖民“混编国族团”),几乎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殖民景观。“魔鬼教练”近藤带领这支“野球队”进军决赛、赢得尊严的主事件线,扣连着八田技师主导的台湾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嘉南大圳开闸放水的喜悦场面,启蒙与开化、身体规训和精神改造、殖民者的垦拓荣耀与“帝国子民”的幸福回望,《嘉农》以被殖民者的视角,回复性地闪现了台湾对日本殖民“成果”的膜拜和怀念。作为魏德圣标志性的艺术模式,《嘉农》和他“殖民怀旧三部曲”中的其它两部影片(《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一样,均以一种浓郁的历史抒情诗风格,显示了其所谓重建历史记忆、重构文化认同的一贯努力。回溯历史的目的不是追忆一个破碎的事件片断或是一段被遮蔽的情感瞬间,而是透过叙事主体、视角和方式的选择与变动,重建一套完整的历史认知体系。
面对“媚日”指责,魏德圣一直回避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偏向,辩称“自己在电影里描写的主题就是冲突而已”,但他的电影创作一直有强烈的情绪表达,也有明显为当局所谓“台湾意识”站台背书的痕迹。他努力在娱乐与言志、叙事与史观之间建立平衡,强调拍电影是为了讲述“日本人在台湾的台湾史,不是日本人在台湾的日本史”。他说,“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台湾的人没有存在感,没有自信心。要让自己有存在感,有自信心,就是有历史观。我们在做的工作是在传递一种历史观,从历史观里面你来重新认识自己,重新了解自己,然后自会产生存在感,那种想要重新创造价值的一种力量就会开始出现”[2]42。因此,不管是魏德胜的“殖民怀旧”系列以及他未来筹划完成的“台湾三部曲”(分别以荷兰人、汉人、原住民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还是叶天伦导演聚焦殖民历史的《大岛埕》和《一八九五》,目的都在于“以通俗煽情的电影语言勾勒出台湾历史的不同区块”[3]16。比起更具象的人物和事件,他们更偏向于抽象的情感抒发和理念表达。尤其是当近20年的台湾电影史呈现为从“中国叙事”向“台湾叙事”的重大转变[4-5],日本形象的银幕建构便被赋予探寻所谓“台湾意识”的重任,带有怀旧色彩的殖民叙事当仁不让地成为叙事焦点,观众在这一叙事进程中“则被诱导着去赋予日本形象以温情气质和崇高品质”[6]。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怀旧是一种批判的姿态:它象征历史性(historicity),而不是重现历史,它的目的是为了对当下进行批评。他说,“历史性,事实上,既不是过去的重现也不是未来的替现:它最应该被当作一种视现在为历史(the present as history)的理解;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与现在的关系,历史性让现在变得陌生,而使得某种距离能够出现在我们与当下的立即关系之中。这个距离可以被称为历史观点”[7]284。历史怀旧、青春怀旧、旅行怀旧、民俗怀旧这些眼花缭乱的怀旧戏,仿如台湾电影的必备包装元素,显示了台湾社会藉由历史感的承续,积极回归现实、介入当下,并重新想象历史、定位自己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怀旧情绪带有明显的台湾在地色彩,被裹挟在越来越浓厚的“台湾意识”论述里,让人很容易将其与当前的台湾政治现实扣连在一起,应当引起我们警惕。
二 发现台湾
2013年上映的一部台湾纪录片《看见台湾》开篇,有一段吴念真先生配音的旁白:“请不要讶异,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如果你没有看过,或许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作为第一部影院演映就大获成功的纪录片,这部自称要“化身飞鸟、看见台湾,一起体验台湾的美丽与哀愁”的纪录片,上映两月票房就突破2亿,远远超越当年上映的热门剧情片,稳稳占据当年岛内票房前十的位置。《看见台湾》的成功秘诀既不是环保主题,也不是时尚的航拍技术和高清画质,而是导演齐柏林所命名的题目——“看见台湾”对当前岛内主流思潮的有力回应:看见台湾、发现自己。全高空拍摄的高山、海洋、湖泊、街道、公路、森林、稻田等台湾景观,配合吴念真略带忧伤的叙述,像是当下台湾电影文化宣言投下的倒影,生动鲜活的技术手段为当前流行的“台湾论述”提供了可资着陆的有效空间。
除了诸如《看见台湾》、《鸟瞰台湾》、《台湾散步》、《台湾:山海交汇》这些景观“发现”外,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硕果仅存的反主流纪录片制作团体”,萤火虫影像体所建立的三大类型题材库里,离岛影像、草根生活影像和政治议题纪录,均宣称以“人民性”为出发点,实质上也是21世纪以来“发现台湾”思潮的一个支脉[8]。它们的目的在于以更感性的方式,建构展现地方主体性的管道,进而为置放所谓“台湾意识”为主体的政治论述框架提供场域。
与此同时,剧情片通过富有台湾特色的环岛体叙事和富于地方色彩的民俗、传统植入故事,持续进行发现台湾的文化写作。
所谓“环岛体叙事”,是台湾电影近年来流行的一种以环岛旅行为时空链的剧情模式。《练习曲》就是一个听障年轻人的单车环岛旅行日志,它既是一首散文诗,也是一部从东岸到西岸的台湾风光名片集,以12段清淡的偶遇谱写简洁的台岛旋律。被称为《练习曲》姊妹篇的《最遥远的距离》,同样将爱情弥合的过程设置在都市女孩从台北到台东的环岛旅程中,她捡拾爱情、寻找自我,将环岛收集来的各地不一样的声音录音带命名为“福尔摩沙之音”,而“福尔摩沙”正是葡萄牙语台湾的另一称呼。《对面的女孩杀过来》以寻找奶奶初恋情人的名义,开始寻访台湾老眷村、小镇、山城、夜市等跨海之旅,打开彼此的心结。《阵头》中的一群年轻人不但背着沉重的阵头行头步履环岛,寻找成长动力,还从台湾走向世界,在片尾完成行销台湾的“壮举”。《霓虹心》、《乱青春》、《第36个故事》、《台北飘雪》中或轻或重的旅行元素,还有纪录片《不老骑士》别有用心地用具有历史感的族群结构发现一个“和解”的台湾,环岛体背后的叙事动机昭然若揭。
很显然,环岛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路片架构,作为一种故事结构模式,其目的在于重新发现和认识作为故乡的台湾,而这种再认识是以20世纪80年代台湾电影以“中国叙事”为前提的再出发。正如《练习曲》导演陈怀恩所说的,“骑单车环岛游的方式就像传送带,动态的方式呈现多元文化结构中每个地方的生活和魅力”[2]138。
另一些以两岸恋情为故事架构的剧情,通过两岸互识互恋的叙事模式,赋予大陆“发现台湾”、认识“台湾在地历史”的重要契机。《爱在垦丁——痞子遇到爱》讲述一个北京男孩和台湾男孩的台湾打工纪行,既推广台湾风光,也贩卖台湾元素。《回到爱开始的地方》变为大陆女孩和台北男孩的旅程,《对面女孩杀过来》则是北京女孩和台湾男孩的爱情行进线,《大喜临门》是高雄台湾妹李淑芬与北京大陆仔高飞的跨海爱情波折,《涩女郎电影版:男生女生骗》又变为成都女孩台湾“寻夫”的离奇之旅。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结构虽然脱离不开2000年以来着眼两岸市场的合拍化、功利性操作,但已超越粗糙僵硬的“贴牌”模式,被注入更鲜活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情绪。不管是为了“来台湾寻找奶奶的初恋情人”,还是为了提亲和道歉、追寻一名台湾老人的初恋故事,或是结婚狂寻找魔术师未婚夫,均捎带出强烈的“发现台湾、认识台湾”的信息。尽管略显做作,但这些台湾创作者技巧性地揉合了真实与想象、情感与政治,将跨海追寻视为主人公了解彼此历史、取得过往记忆的必要途径,在建构台湾形象方面有令人惊奇的默契。在这里,台湾既是一个实体的地理空间,也是一组抽象的文化概念。
当前的台湾电影一直保持对空间的高敏感度,似乎努力用视听描摹出一个更清晰的台湾媒介地理景观。不管是环岛游历,还是跨海追寻,台湾电影叙事突出的依然是一个时间链上的空间文化概念。不管是《大岛埕》、《西门町》、《港都》、《爱在垦丁》、《海角七号》、《嘉农》、《艋舺》这样具有空间即视感的影片,还是《到不了的地方》之类的空间装置影片,台湾的都市与乡村都像一个巨大的天幕将情感故事包裹其中,导演进一步强调了空间在叙事体系中的隐喻功能。周美玲的《花漾》甚至“架构出一则象征意味浓厚的海岛寓言,倾其所能企图打造一个从‘本土’出发,与传统中原观点古装片截然不同的世界观”[9]27。《花漾》中的“化外之岛”作为一个符号感极强的所指,已与侯孝贤的《海上花》中的海岛隐喻相去甚远。大陆遁去,台湾浮现,“中国”议题已被眼花缭乱的岛内空间替代和瓦解。稍微对比一下20世纪80至90年代台湾电影中国叙事对大陆空间的深情想象和重笔渲染,以及随后古装片对中国典故和中国场景的再书写、眷村电影对“中国”的发觉与回望,不仅让人唏嘘不已。
与此同时,台湾地方民俗与传统文化成为台湾电影“发现台湾”的另一种载体。《总铺师》中的办桌文化、《阵头》中的庙会文化、《鸡排英雄》中的夜市文化,甚至《海角七号》中的沙滩音乐、《赛德克·巴莱》中的原住民部落文化、《大喜临门》中的台湾婚俗、《逗阵儿》中的学校体育文化,这些电影无疑通过强有力地植入民俗与文化元素,放大叙事中的“台湾”主题,回应岛内社会声浪日高的“回归台湾”或“台湾再发现”运动。《逗阵儿》与《鸡排英雄》、《阵头》构成“台湾人情系列”,以更加立体的方式行销台湾,模塑在地的精神价值和历史传统,夹带更丰富的历史政治内涵。
黄朝亮导演的《大喜临门》有意将两岸交流的文化障碍落实到更为微观的习俗细节上,通过跨海恋情中大陆人面对的台湾地方文化“面试”——民俗、传统和语言徐徐展开,台湾的办桌、提亲、大订小订习俗与北京的满族婚礼环节交互呈现,再加上贯穿全片的普通话与闽南话误读,什么“你们的规矩”、“我们的流程”,地域区隔的意味异常明显。故事上了无新意的《大喜临门》,似乎不是一个爱情片,而更像一个直观的两岸论述,再现两岸恶感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的同时,致力于通过人物关系的巧妙设置,抬升台湾在两岸对话中的“地位”。作为台湾地方文化符号的民俗与传统,在这里是高度仪式化的。
这反映出台湾电影日趋本土化的取材倾向,台湾的人、社团和事件,甚至作为地方感性的新闻事实,均已置换为“发现台湾”的重要素材,成为台湾电影本土书写的重要内容。讲述景美女中拔河队的《志气》,表现嘉义东石高中棒球队的《天后之战》,表现台湾知名面包师吴宝春的《世界第一方》,还原台南百年仁德糖厂的音乐爱情片《加油!男孩》,表现盲人钢琴师裕翔的《逆光飞翔》……这些号称改编自真人真事的拟实电影,被罐装进“本土温暖”与“励志热血”两个元素后,显现出更热切的本地文化史编纂愿望。
三 “鲁蛇励志”
“鲁蛇电影”在台湾被称为Loser undergo film,即以失意草根或屌丝从危机走向胜利为主体内容的电影。自《海角七号》后,台湾电影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类型操作模式,故事上着力表现一群乌合之众从溃散经团结走向成功的过程,风格上将“鲁蛇”励志与乡土喜剧混搭,爆发出惊人的艺术影响力。
台湾著名影评人郑秉泓指出,魏德圣的《海角七号》就是一段“台湾人的乡愁”,它所讲述的一群玩音乐的“杂牌军奋起”剧情,“本就是激励人心充满正面能量的励志故事”[10]52。魏德圣担任编剧和出品人的《嘉农》,同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loser undergo film,从遭受创伤失败的一群屌丝起步,终止于完成正名、赢得尊严的场面仪式,设定的是完全雷同的情节进程。台湾电影俨然将本土草根(故事层面)和励志喜剧(价值层面)当作市场万能药,所有主流类型均可见到清晰的“鲁蛇”身影。诸如《逆光飞翔》、《志气》、《破风》这些青春励志片,甚至《总铺师》、《阵头》、《鸡排英雄》这样的民俗片,还有《逗阵儿》、《男朋友女朋友》、《被偷走的那五年》等怀旧片,《我的少女时代》、《对面女孩杀过来》、《车拼》等爱情片,均有意无意地通过故事将台湾社会的集体挫败感浪漫化,以更虚无或更阿Q式的结尾给整个社会最热情的抚慰和激励。
和《总铺师》一样,《阵头》也是一部子代承续父代、终于熬出头的故事,结构上都以两个人或团体的对决比拼为主线,也都有一条爱情的副线调节气氛,风格上遵循的依然是当下台湾电影一成不变的主旋律——“鲁蛇”励志。联想一下《海角七号》中乐队重排走向成功的动人场面,或《嘉农》中球队崛起迎接新生的辉煌瞬间,不难发现台湾电影已经在叙事、抒情和人物寓意间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式,勾连起一个情绪饱满的价值表达体系。故事往往从被歧视、被踢馆等台湾草根的危机开始,经由挫折困顿延宕出这个社会亟待表达的勇气、坚韧和智慧,走向既定的仪式性高潮。每一部“鲁蛇”电影结尾都有一场带有仪式感的华丽“演出”,将loser的挫败感、失意感扫荡排空。《阵头》是时任台中市长胡志强鸣锣的亚洲表演大赛,观众席中十几个细部表情特写联结的社会振奋情绪,和舞台上流光溢彩的阵头表演交相辉映,伴随着“是甘是苦我不怕,咱们世界最车赢”,“是青春是成功咱斗阵追。现在是咱的世界。属于你的我的拢兔歹势”(闽南语)的豪迈歌声。被称为台湾版《三目丁的夕阳》的《逗阵儿》,将结尾亮亮一个人的马拉松升华为一首全民抒情诗:“献给一直坚持为这块土地付出的人们。这份情神,将永远长存!”这些字幕或声音饶有意味地将一个幽微的家庭情感史生硬地转变为“60年代台湾族群团结”的社会史。《鸡排英雄》既穿插有泛滥的草根抒情:“艰苦人也是人,可以没钱,不能没志气”;也擅长借逛台湾夜市的陆客之口自我安慰:“台湾好,台湾好,台湾真是个复兴岛。我们受温暖的海风,我们听雄壮的海涛。我们爱国的情绪比那阿里山高,比那阿里山高。”当我们看到夹杂着东北音、北京话的大陆游客,在“中华民国”的巨幅背景板拍照留念,泪流满面地宣泄激动的感受,影片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励志范畴,变成畸形的自我表扬。正如郑秉泓评价《逗阵儿》时所言:“极度煽情狂灌狗血宣扬族群和解的本土电影,意识形态过时陈腐到了极点,仿佛取材自三十年前的国小生活与伦理教本,充斥‘选择性遗忘’、一厢情愿忆苦思甜‘粉饰太平’的乡愿。……也因编、导、演的全面性失控,令这部贺岁电影沦为一部仿佛走错时空的戒严时期主旋律电影,它的存在于是显得如此虚假、令人难堪而不合时宜。”[10]31
励志作为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在剧情片和纪录片、电视剧领域均有明显表现。以台湾著名残疾马拉松名将邱淑容为中心人物的纪录片《看不见的跑道》,纪录其重回职场、重建信心的励志道路。纪录片《正面迎击》则是一群摔跤热血男儿的励志故事。《拔一条河》将高雄甲仙拔河小将放置在移民小镇重建的背景下,凸显台湾女性的韧性与勇气。《一首摇滚上月球》讲述的是“小人物完成大梦想”的励志故事,由六位患有罕见疾病孩子父亲组成的“睏熊霸”乐团,最终登上海洋音乐祭的舞台,实现不可能的梦。如果我们将这些纪录片和剧情片联系起来,发现它们尽管分属不同的体裁,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诉求,叙事模式甚至是复制性的。它们映射了台湾社会在集体挫败情绪激发下怀有的焦虑感,不管是职场、赛场、舞台还是爱情场域,创作者通过固定不变的叙事程式,表达了岛内社会失落与错置的心理状态。
励志的背后是困顿与失意。如果我们留心观察《总铺师》和《逗阵》的海报或剧照,剧中人物都是一副怒气向前冲的阵势。这说明了什么?“鲁蛇”励志电影虽然包装了异常坚实的喜剧外壳,仍然无法摆脱内在的精神萎靡。《对面女孩杀过来》、《车拼》、《大喜临门》几乎都设定了一样的情节动力(人物困境):大陆、台湾孰优孰劣的争论。《车拼》中,徐州男孩陈赵中、台中女孩陈心怡的恋情因跨区商务展开,却因大陆人一句“台湾赶不上大陆”闹翻。剧情随后被拖曳入一个喜剧的框架:大陆男孩面对一个由激进“台独”、维持现状派和外省背景构成的台湾家庭的畸形政治复合体,在未婚先孕、亲友团旅台炫富挽救危机无效之后,最终靠台湾爷爷一段复杂纠结的历史成全了这段跨海峡婚姻。悲情性的戏剧内核和狂欢式的喜剧线索搅拌在一起,形成一种奇怪的阅读体验。也许“鲁蛇”励志模式触动的是台湾社会最复杂纠结的部分,它才成为台湾电影最大的文化表达方式之一。
四 结语
追寻台湾电影纷繁杂乱的文化动因,理清台湾电影创作者文化书写的脉络,既要重视台湾电影自身的历史线索,也无法回避当前世界电影全球化的浪潮,只有将其置于世界电影的格局中,才能理解近几年台湾电影发生的巨大变动。
追溯台湾电影的历史,才能弄清当下台湾电影的症结。自日据时期有电影以来,台湾电影创作形成了四个群落:最早的一代由来台接收电影产业的大陆影人和日据时代即在台工作的本地影人构成,包括房勉、徐欣夫、宗由、袁丛美、张英、唐绍华等。作为台湾电影的奠基人,他们群体特点模糊。李行、白景瑞、李翰祥等属于台湾电影的第二代,他们的电影创作属于威权时期的主旋律或者政策性生产,他们多是30年代生人,创作生命至80年代前后结束,个别目前仍活跃于影坛幕后。第三代是台湾电影的“塔尖”,李安、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陈坤厚、万仁、王童、朱延平等将台湾电影推向前台、带来荣耀,在艺术探索与文化书写方面丰富了台湾电影的面向。第四代是目前台湾电影创作的主力,形成了类型探索与多元本土创作的主流。这一代有两大类:一类是影视行业世家或科班背景的,如蔡岳勋、钮承泽、魏德圣、冯凯、瞿友宁均出自杨德昌或侯孝贤、王童名下,杨雅喆、戴立忍、王毓雅等则毕业于电影名校;另一大类是具有多元跨界背景的新导演,由哲学、海洋、工程、文学、音乐转投电影,如李鼎、李岗、黄朝亮、周杰伦、陈宏一。
随着老一代电影人悄然谢幕,年轻一代华丽登场,台湾电影开始开创不同格局的电影新纪元。“后侯孝贤时代”的台湾电影,创作者甩下历史包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洒脱或随意。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台湾方言,调配在地元素,紧跟文化变动的踪迹,与年龄层不断迭变的观众遥相呼应,形成了愈发内向的文化倾向。正如台湾著名电影制作人李烈所言,“台湾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为止,就是身上背负着太过沉重的问题,在这个岛上的很多人都会有点喘不过气”,“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拒绝承担上一辈的历史纠葛,刚好这些年轻导演的作品可以符合他们的需求”[2]192-193。因此,题材多数与“我”有关,市场口味更加狭隘,不断强调本土共鸣的台湾电影创作终成为本土元素过度倾销的卖场。
另一方面,当前的台湾电影也是世界电影的回声。我们既可以在其中看到大陆电影和日韩电影的某种风暴,也能窥见当今主流好莱坞电影的视听语言变化和流行的故事讲述方式。张荣吉的校园犯罪悬疑片《共犯》、张世导演的《妒忌私家侦探社:活路》与近年来流行的日式校园推理片极度相似,《我的少女时代》、《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又与郭在容执导的那些韩日青春爱情类型片高度相似。像《大尾鲈鳗》这样制作粗糙、又缺乏国际性电影语言的影片之所以大获成功,最主要还是制作者对当前商业电影经验的准确运用:除了综艺明星猪哥亮太过本土以外,互换身份、黑帮复仇的情节桥段,语言谐音游戏所造成的段子化,节奏快捷的动作剪辑,以及带有明显网络感的场景单元设置,都说明了台湾电影里不仅仅只有台湾。
注释:
①文中所有票房数据,均来自《台湾电影年鉴》,仅指大台北地区票房,非全岛票房。大台北地区以外的票房数字,因无详细统计数字可资核查,一般以大台北地区票房乘以1.3至1.4倍推估。
[1]BOYM S.TheFutureofNostalgia[M].NewYork:BasicBooks, 2001.
[2]野岛刚.银幕上的新台湾:新世纪台湾电影中的台湾新形象[M].张雅婷,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
[3]闻天祥.2014台湾剧情长片:绝境还是出路?[G]//2015台湾电影年鉴.台北:“财团法人国家电影中心”,2015.
[4]谢建华.中国怀想——台湾主流电影的中国叙事(1979-1995)[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4).
[5]谢建华.模糊的大陆与清晰的台湾——台湾电影的中国叙事(1995年以来)[J].文艺研究,2014,(2).
[6]谢建华,倪婷.诗化的历史——新世纪以来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J].当代电影,2016,(12).
[7]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吴美真,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8.
[8]罗祎英.论台湾萤火虫映像体纪录片的创作与美学[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4).
[9]郑秉泓.2013年台湾电影:成也本土,败也本土[G]//2014台湾电影年鉴.台北:“财团法人国家电影中心”,2014.
[10]郑秉泓.2014台湾电影:临界点上的抉择[G]//2015台湾电影年鉴.台北:“财团法人国家电影中心”,2015.
[责任编辑:唐 普]
2016-12-31
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度重点培育基金扶持项目“台湾电影心理流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谢建华(1976—),男,河南南阳人,电影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与传播。
J909.2
A
1000-5315(2017)03-01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