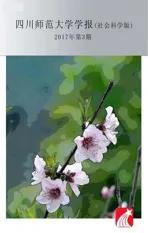德国古典美学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2017-04-14黄小洲
黄 小 洲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德国古典美学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黄 小 洲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诗与哲学之争是德国古典美学论争的重要内容。康德既强调审美判断不是认识判断,但又把审美所依赖的判断力视为人的认识能力之一;既强调美与善相区分,但又认为可以由自然美过渡到道德。席勒打破了康德这种调和折中的立场,主张美不仅没有败坏道德,反倒是自由的基础。谢林抬出上帝来作为美与艺术的护身符,从而筑起让人顶礼膜拜的艺术神坛。黑格尔在理性精神与辩证法精神的引领下使得诗与哲学之争得以和解。
德国古典美学;诗与哲学之争;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
在西方,诗与哲学的论争可谓源远流长①,但是最著名的要数柏拉图。我们知道柏拉图对诗或艺术(在古希腊,诗可以泛指一切艺术)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艺术有两大罪状:一是艺术没有告诉人们真理,它向人们展露的不过是些不真实的幻象;二是艺术危害人的心灵,它会搅乱人心灵与社会的和谐,缺乏善。正是基于这两个重大理由,柏拉图不让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
显然,柏拉图引发的诗与哲学之争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哲学对艺术或诗艺的大批判,既包含认识论或真理论的批判,又包含有道德或社会的批判。尽管锡德尼力图发现诗是哲学之保姆,一切知识的起源,最初光明的给予者[1]5,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挡哲学对诗发起的攻击。尽管陈中梅先生也说诗与哲学的结合是柏拉图隐而不宣的心愿[2],但是这个隐秘的心愿却被柏拉图公开的批判所淹没。虽然艺术家们十分讨厌柏拉图加在艺术身上的这副魔咒,但是诗与哲学之争这个论题却影响深远。德国古典美学家们在美学或艺术哲学方面的探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这个论题的不同回应。
一
在诗与哲学之争这个论题上,康德美学可以看作是柏拉图艺术批判立场的激进化或彻底化。如果说柏拉图认为艺术还处于真理的第三层位置上,那么康德则彻底砍断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关联。在《判断力批判》第一卷美的分析论中,按照质的契机来看,康德把鉴赏判断或审美判断视为与认识判断无关的情感判断,不是逻辑判断,而是主观的感性判断[3]37-38。
为了与传统的经验派客观主义美学相区分,康德反复强调审美判断只是一种主观的情感判断,它对对象的认识没有丝毫贡献。例如我们说:“这朵郁金香真美呀!”经验派美学会认为,这个判断是一个关于这朵郁金香花的认识判断,它表明美是这朵花的一个客观属性。反之,康德则认为这个审美判断并没有标明客体(这朵郁金香花)的任何客观属性,我们并不能通过这个判断而获得关于这朵花的颜色、气味、形状、大小、重量等等客观认知。康德甚至主张,在纯粹的审美判断中,对象是否实际存在都是无关重要的,因而美不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只属于人的主观情感范畴。总之,“美不是什么有关客体的概念,鉴赏判断也决不是认识判断。”[3]132由此看来,康德把西方由毕达哥拉斯所开创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美学彻底颠倒成人的主观情感主义。
然而,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中,康德对审美判断与认识判断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如此激进,而是展现出某种复杂的、温和的乃至有时互相矛盾的见解。尽管《判断力批判》处于沟通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与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的桥梁与中介位置,但是显然,在康德的哲学划分中并没有一种审美的形而上学。所以,康德主张没有美的科学,只有美的批判。如果说康德把审美与认识区分开来似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对艺术家的松绑,那么不存在审美的形而上学这一结论本身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柏拉图。然而,康德又强调与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结合着的判断力也是一种认识能力,而且是作为诸认识能力协调一致的调节性原则,从而实现从认识向道德、从自然向自由过渡。这样一来,康德似乎又离传统的认识论美学不远。因此,戴茂堂先生作出调和说:“美是真,但不是客观的真而是情感的真;审美是判断,但审美不是认识判断而是情感判断;故而,美学是科学,但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4]389
与强调审美判断不是认识判断相一致,康德同样主张审美判断不是道德判断,从而与理性派的完善论美学相区别,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缓和了柏拉图对诗的批判。在这里,康德既拒斥审美的功利主义化,也拒斥审美的道德主义化,而主张审美判断所带来的愉悦是不带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为此,康德区分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愉悦:功利的愉悦、道德的愉悦和审美的愉悦。功利的愉悦造成的是一种快适。比如饥渴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一种快适,它遵行的是刺激-满足的病理学或生理学机制,它是爱好的对象,因而功利的愉悦连动物也适用。道德的愉悦造就的是一种纯粹实践性的愉悦。比如由诚实、公正、友谊等造成的愉悦就属于这类,它遵行的是定言命令的普遍法则,因而它是敬重的对象,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包括精灵天使)。审美的愉悦则是一种类似于静观的愉悦。它对对象的存在与否毫不关心,它遵循一种无利害的、自由的情感原则,因而美仅仅适用于人类这种既有动物性又有理性的存在者。
然而,康德又强调美可以作为德性-善的象征,从而使得审美判断可以向道德判断过渡。正是在此意义上,邓晓芒先生说康德在对美感的分析中头两个契机非常接近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即把对象的存在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5]35,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丢弃。康德区分了两种美:自由美与依附美。花朵、鸟类、贝壳、希腊式的线描、无标题的幻想曲、无词的音乐等等,可以视为自由美、纯粹美、形式美、流动之美或无条件的美。而像一匹马、一座宫殿、一首诗、一幅画、一个人等的美,则可以视为依附美、杂多的美、以完善性概念为前提的美、质料美、固着之美或有条件的美。
从康德对依附美的承认与崇高感中包含的道德亲和力来看,那么他似乎与理性派的完善论美学有着共同的走向,并且再度恢复了柏拉图的魔咒。他说:“我们经常用一些像是以道德评判为基础的名称来称呼自然或艺术的美的对象。我们把大厦或树木称之为庄严的和宏伟的,或把原野称之为欢笑的和快活的;甚至颜色也被称为贞洁的、谦虚的、温柔的,因为它们激起的那些感觉包含有某种类似于对由道德判断所引起的心情的意识的东西。鉴赏仿佛使感性魅力到习惯性的道德兴趣的过渡无须一个太猛烈的飞跃而成为可能。”[3]65尽管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只是具有类比性,但是康德却要求清除一切艺术中造成道德堕落的虚伪造作与揉糜奢侈。这样,康德就与卢梭、柏拉图一样共同走在艺术道德批判的道路上。
二
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席勒并不扮演康德美学的单纯阐释者,毋宁说他是一个革命者,他在审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紧密关联中冲开了柏拉图与康德所设置的防线,从而颠倒了诗与哲学的批判走向。在传统哲学对艺术的批判压力下,席勒迫切需要在人的感觉方式中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摧毁柏拉图加在艺术身上的魔咒,从而拯救美学。我们看到,康德的审美主体化和费希特的冲动学说为席勒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对现代世界和人性充满历史感的敏锐洞察,则为席勒著名的《审美教育书简》找到了现实的突破口。诚如邓晓芒先生指出:“席勒终究向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接近了一步,人类学被社会学所充实,审美心理学走向了艺术社会学。”[6]94
席勒描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分裂与不和谐:在人性的内部,知性的规范力与审美的想像力互相为敌,在社会的外部,职业的分工使人沦为国家机器中的碎片;有教养的人可能是一个卑鄙之徒;唯物主义伦理学把人降格为一种动物。人是分裂的,人格的完整性不复存在。这是现代社会的罪恶,它是脱离了审美教化而造成的结果。因此,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病、拯救现代人的重任恰恰只能依靠审美的教化,不能单靠知性的理论教化和理性的道德教化。这是席勒对柏拉图审美符咒的大逆转。他说:“我违抗这迷人的诱惑并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人们在经验中要求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7]21让美在自由和真理之前先行,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审美的教化,真理与自由就永远到达不了,审美的教化成为现代社会和人性的第一要求。哈贝马斯说,在席勒这里,“艺术本身就是通过教化使人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的中介”[8]52。
对此,席勒分析说,现代社会只知道片面发展人性当中的感性冲动(sinnlicherTrieb)和形式冲动(Formtrieb),而不知道其实人性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第三冲动即游戏冲动(Spieltrieb)。感性冲动把人放在时间之中,造成个案,要求变化,使人变成物质,使人感受到自身的动物需求,因此它也可以称为物质冲动。启蒙的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此主张得最多。形式冲动要求真理与合理性,渴望建立法则,扬弃时间和变化,发出永恒的命令,从而使人保持人格和自由。康德的道德哲学对此贯彻得最为严格,他不允许任何私利的冲动混进道德中来。
但是,这两个冲动造就的是两个互相割裂的王国。一个是自然力的可怕王国,它服从机械的因果律,完全无视自由的存在;另一个是道德法则的神圣王国,它蔑视任何感性形象,摆脱任何物质束缚,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席勒指出,必须要有一个第三种冲动打通这二者,重新恢复人性的完整,这就是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以美或活的形象为对象,因此它也可以称为艺术冲动或审美冲动,它能使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与生存的最高丰富性结合起来。毋宁说,艺术冲动就是自由的代名词。
虽然艺术冲动营造的是假象的快乐王国,但是它能让人性自由地游戏、舒展。审美教化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的整体。所以,席勒着重地宣布:“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7]122这就使得审美教化或艺术教化成为社会和人性的一种必须,并且能够避免粗野和乖戾这两个极端。“发达的美感能够移风易俗……古代的一些民族中最有教化的民族,它们的美感也最发展。”[7]79席勒希望通过审美的教化来建立真正的自由,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7]19。在《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席勒明确主张,诗不仅是娱乐和休息的工具,而且也是提高人的道德的工具[9]348-349。因此,美与善、艺术与道德不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对立关系,毋宁说一切道德或善必须从艺术或美中推导出来。
审美的教化不仅能建立自由,而且还能产生真理。席勒说:“真理按其功能已在美之中了。”[7]209通常人们认为,审美对知性不会提供任何结果,美不干涉思维的事务,但是席勒认为美能赋予知性以功能,没有审美的这种功能,知性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因此,席勒大胆地断定:“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7]181
由此可见,审美在认识与道德方面可以结出最丰硕的果实,这样一来,柏拉图加在审美身上的魔咒不仅被席勒解除了,而且完全颠倒了过来。诗与哲学之争的天平毫无保留地往诗艺这边倾斜。审美不再是低层次的东西,反过来成为人性的最高需求。人通往神圣的道路是通过审美教化打开的。席勒不由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惟独美的沟通能够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惟有美才会使全世界幸福,因为谁要是受了美的魔力,谁就会忘记自己的局限。”[7]236-238
三
朱光潜先生洞见到:“过分夸大艺术和美的作用是浪漫运动时期的一种通病,‘始作俑者’正是席勒。”[10]436虽然席勒不是浪漫主义者,但给浪漫主义美学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谢林才真正是浪漫主义美学在哲学上的总代表。在传统的诗与哲学之争中,如果说席勒更多是在美与善、艺术与道德方面炸开了一个缺口,那么谢林则更多地强调美与真、艺术与哲学的绝对同一而彻底冲垮柏拉图的防线,而且吊诡的是,谢林是在大大利用柏拉图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才做到的。在谢林的美学中,美或艺术披着上帝的光鲜外衣,被安放在高高的神座上,一切都是那么神圣与奥秘。
谢林毫不隐讳地宣称:“任何艺术的直接始因乃是上帝。……上帝乃是直接的始因、任何艺术的有限可能,他本身乃是任何美的源泉。”[11]42上帝成了艺术的始因和美的源泉。借助中世纪基督教唯一的至圣神的力量,与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兄弟、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等人相呼应,谢林给美和艺术赋予了一张荣耀的出生证,这使得艺术彻底地浪漫主义化了。如此一来,美和艺术就不是柏拉图贬斥的那样是所谓低贱父母所生的低贱孩子了,而摇身一变成为一切科学的正统和大宗。诺瓦利斯对浪漫主义的界定再恰当不过:“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12]封底
谢林一再强调美与真具有最高的统一性,在永恒的理念中,真与美是同一个东西。“美与真本身,即依据理念,乃是一致的”[11]40。通过反复论证的同一哲学,谢林主张美与真在永恒的、超时间的理念意义上是绝对同一的,艺术绝不是理念的影子,美就是理念本身。1917年,罗森茨威格整理出版了一个未署名的纲要笔记,即《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纲领》,并且认为作者是谢林,卡西尔认为是荷尔德林[13]316,有人猜测黑格尔也参与起草。其中说到:“统一一切的理念,美的理念,在更高的柏拉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坚信,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的行动,理性这里统摄了所有的理念,而真与善只有在美之中才能结成姊妹。哲学必须像诗人一样具备同等的审美力量。”[14]282这里,美成为超越真善的至高理念,审美与理性合一,艺术成为了一种新的神话、新的宗教。无疑,这些观点更靠近谢林而不是黑格尔。
关于艺术的地位,谢林旗帜高扬地说:“哲学的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乃是艺术哲学。”[15]15如果说在康德那里,整个哲学大厦的拱顶石是自由,那么在谢林这里,自由就要让位给艺术。他甚至热情洋溢地赞颂道:“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15]276如此一来,谢林就给艺术筑起了一座高高的祭坛,让美直通隐秘的上帝。
这种美的神话或艺术的宗教,它与理性或哲学是协调一致的,毋宁说是绝对同一的,没有任何差别。在一种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主导观念下,谢林强调宗教保存在神秘学里,与哲学拥有同一座神庙。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强调,最早的哲学家就是神秘学的制定者,柏拉图就是这样人,喜欢从神秘学推导出自己的神圣学说[16]256。这样一来,在谢林眼中,柏拉图以哲学的身份来批判诗艺就成为一种假象或表象,艺术宗教的神秘学才是柏拉图的真实面目。为此,谢林把哲学装扮成在本性上也是隐微的、神秘的、奥秘的,因此本质上与神话相等同。
谢林强调哲学发端于一个神秘莫测的、无法用概念言说或理解的绝对同一体。但是,它如何才能为人知晓?谢林的回答是理智直观。谢林区分了两类理智直观:一类以绝对同一体为对象,也叫内在的直观或第一直观,但是一般人类是很难达到的;一类是美感直观或艺术直观,绝对同一体通过美感的创造而外化为整个自然,于是成为客观的,所以又叫做客观的理智直观或第二直观[15]273-274。在谢林看来,艺术就是理智直观普遍承认的、无可否认的客观性。
作为绝对同一体的上帝,它把自身启示在整个宇宙自然中,因而把自身客观化了。借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和斯宾诺莎神即自然的泛神论,谢林把上帝装扮成了一个奇妙的艺术大师,认为整个宇宙自然不过是上帝流溢出来的艺术作品[17]20;“宇宙作为绝对的艺术品建立在上帝中,并建立在永恒的美中”[11]41。因此,相对于康德的美学主观唯心主义,谢林开启了一条充满神秘色彩的美学客观唯心主义道路,美学不仅是至高的科学或形而上学,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神学、一种艺术新神话。
四
众所周知,艺术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处于认识的最高层次,即绝对精神层次。就艺术与认识、美与真的相关性而言,黑格尔认为艺术与宗教、哲学处于同一境界,它能表现人类最深刻的旨趣和心灵最宽广的真理。简言之,艺术表达着真理。黑格尔说:“在艺术作品中,各民族留下了他们的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18]10艺术蕴藏见解和思想,是解开宗教奥秘和思辨哲理的钥匙。由此可见,黑格尔绝不赞同柏拉图主张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的看法,也不赞同康德认为美无关认识的观点。
尽管艺术诉诸感觉、情感、知觉和想象等表现方式,但是它绝不只是幻象、虚假的欺骗人的东西,艺术仍可以表达真实。为此,黑格尔借用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观点:“诗比历史更真实。”他说:“艺术的功用就在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因此,艺术不仅不是空洞的显现(外形),而且比起日常现实世界反而是更高的实在,更真实的客观存在。”[18]12艺术显现的是心灵的真实,是一种比日常世界更高级、更真实的客观存在。显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是支持谢林的努力方向的。
但是,黑格尔认为,艺术不是表达真理的最高方式,艺术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理智直观,而是需要概念、理性与反思的,“完美的认识只属于用概念进行认识的理性的纯粹思维”[19]263。就此而言,黑格尔与谢林分道扬镳。尽管黑格尔把艺术放在绝对精神之中,但是我们要注意它不是最高环节,在这之上是天启宗教和哲学。黑格尔明确说:“我们一方面虽然给与艺术以这样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提醒这个事实: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就形式来说,艺术都还不是心灵认识到它的真正旨趣的最高的绝对的方式。”[18]13艺术是自我认识在智性上的朴素形态,因此不能对艺术真理作过高的估价。扒下谢林给艺术披上的神秘主义外衣,从而拆掉美的神坛,这是黑格尔美学的重要工作之一。
他严厉批判谢林非理性主义的天才直观说:“放弃了概念的严肃性和思想的清醒性,而代之以无聊的幻想,并把这些无聊的幻想当作深刻的直觉,高远的预见,并当作美的诗。他们自以为他们正处在中心,其实他们却只在表面上。”[20]370黑格尔把艺术中这些灵感、本能、直觉、天才的无意识创作等嘲讽为“从手枪发射子弹”,狂言呓语,思维混乱,任意拼凑。他认为,这样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既不是鱼也不是肉,既不是诗也不是哲学的虚构怪物[21]47。浪漫主义把个人瞬间的偶发奇想或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视为神圣之物,它蔑视理性与反思的艰苦劳作,并且把这视为笨拙、机械和僵死的无价值东西丢弃一边。它以为个体的想像力摆脱了反思思维的束缚后会飞得更高更远,殊不知这样给艺术带来的更多是个人病态的情感呻吟和无聊,从而使得艺术重新落入柏拉图的魔咒之中。
关于艺术的社会功能,黑格尔非常清楚柏拉图、卢梭、康德等人对艺术的道德评判。他们认为,艺术造就的是精神松弛涣散,于人生和社会的重要事务无关,是多余的东西,甚至是有害之物;对美的玩赏软化了人的心灵,给社会带来奢侈糜烂、虚伪造作的风气,因而是伤风败俗的东西。黑格尔明确主张艺术美要高于自然美,因为在艺术美中表现出了人高贵的精神活动和心灵的自由。显然,与康德的艺术堕落论相反,黑格尔承认艺术有着严肃高尚的目的,它与道德、宗教、自由有相通之处。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直接把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
黑格尔进一步阐发说:“在生活的一切活动中,美和艺术诚然象一个友好的护神,把内外一切环境都装饰得明朗些,对生活的严肃和现实的纠纷可以起缓和作用,以娱乐的方式来排遣厌倦,虽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东西,至少可以代替坏的东西,这究竟还是聊胜于无。”[18]6美和艺术不仅可以装扮我们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过得舒坦爽朗,而且是人类生活的友好守护神,它让人们从生活的过分严肃、过分紧张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得以休息,让痛苦悲伤等不良情绪得以宣泄,从而净化人的心灵、恢复人心的和谐平衡,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一个和谐的个人难道不正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前提吗?美与艺术难道不能因此配享崇高之名吗?从黑格尔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亚里士多德艺术净化说的踪影。
不仅如此,与席勒的艺术自由说相呼应,黑格尔还提出艺术的家园论和解放论。他说:“艺术天才和观赏者在艺术作品已给它以表达的崇高神性里,有一种特别的如同回到了家园的感觉和感受,得到了满足和解放。”[19]376在艺术中,人们会有一种自在舒适、温馨宜人的家园感,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某种满足、获得了某种暂时的解放。但是,黑格尔清醒地知道,审美的自由不能取代现实的政治自由。“美的艺术只是一个解放的阶段,而不是最高的解放本身”[19]377。由此,黑格尔限制了席勒对审美自由的过分膨胀,从而与席勒相区别。总而言之,在一种辩证精神的约束之下,黑格尔维护了一种美与真、善,艺术与认识、道德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超越他的时代的各种片面美学观。后来,斯特劳斯派的罗森也说,诗处于哲学与政治之间,三者要保持适度距离,分离则导致人灵魂的肢解和政治的扭曲[22]前言,3。
综上所述,诗与哲学之争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美学论争的重要内容,德国古典美学家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柏拉图明确标明出来的千年难题。康德一方面强调没有美的科学,审美判断不是认识判断,但是另一方面又把审美所依赖的判断力视为人的认识能力之一;康德一方面强调审美判断是不带任何厉害关系的,从而将美与善区分开来,但是另一方又区分了自由美和依附美,并且认为人们可以由自然美过渡到道德。席勒打破了康德这种调和折中的立场,主张美不仅没有败坏道德,反倒是自由的基础,政治自由必须假道审美才能实现。如果说席勒从现实生活的左路进攻柏拉图的艺术魔咒,那么谢林就是从历史神话的右路猛攻柏拉图有关诗与哲学的论断。谢林抬出上帝来作为美与艺术的护身符,他借助神秘莫测的理智直观而让宇宙自然摇身一变成为上帝的艺术创造,从而筑起让人顶礼膜拜的艺术神坛。黑格尔在理性精神与辩证法精神的引领下使得诗与哲学之争得以和解,认为艺术是精神认识自身的高级方式,却不是最高方式;艺术给予人类一种自由感和解放感,但同样不是最高的自由和解放。
注释:
①可参阅:张奎志《西方思想史中诗与哲学的论争与融合》(张政文教授指导,黑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他发表的相关论文《海德格尔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颠覆》(《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世界哲学》2006年第2期)等,论述上至古希腊下至现当代,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发展概览与线索。
[1]锡德尼.为诗辩护[M].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陈中梅.诗与哲学的结合——柏拉图的心愿[J].外国文学评论,1995,(4):116-124.
[3]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戴茂堂.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5]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邓晓芒.西方美学史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9]席勒美学文集[M].张玉能,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1]谢林.艺术哲学[M].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2]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M].卫茂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13]阿斯穆斯.康德[M].孙鼎国,译.王太庆,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4]荷尔德林文集[M].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6]先刚.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哲学与宗教》释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7]谢林.布鲁诺对话:论事物的神性原理和本性原理[M].邓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8]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9]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2]罗森.诗与哲学之争:从柏拉图到尼采、海德格尔[M].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帅 巍]
2016-11-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黑格尔与现代解释学关系研究”(15XZX012)的阶段性成果。
黄小洲(1981—),男,广东茂名人,哲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与解释学。
B
A
1000-5315(2017)03-00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