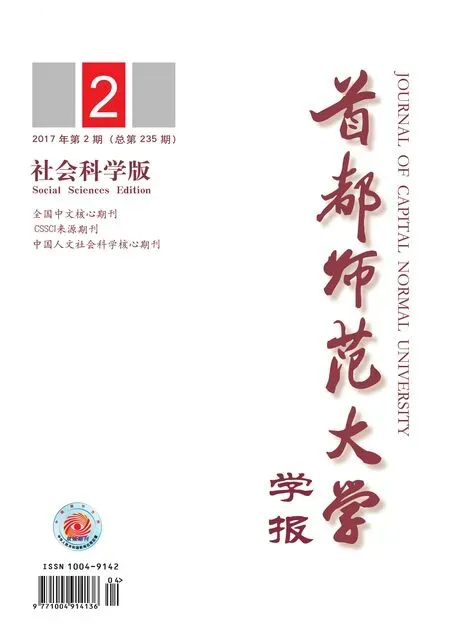反思文艺学研究中的两种不良倾向
2017-04-14王洪岳
王洪岳
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自有其专属于自身的独特性。自古迄今关于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就是对于文学这种语言的艺术性即特殊性的研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学又作为人类所创造的关于人的整个存在世界的言说和表达,它必然又具有和人类其他领域息息相关的关联性或“间性”。文学的道德伦理之维、社会历史之维,乃至隐秘心理之维等维度的研究,则试图把文学当作其他领域的友军,来一起构筑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大厦。实际上,无论哪种研究方法或思路,都是对于文学这一人类文化的主要形式的有效探索。20世纪以降的作家传记(生平)研究、作品形式研究、读者接受研究和文学世界来源研究,都是对于文学的某一方面存在特征的揭示。而作为既古又新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依然有效,文学离开了人及其周围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近年来文艺理论领域却出现了两种倾向。其一是文学研究唯有回到所谓本体领域,才是真正文学的、审美的,而所谓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形式存在或存在形式,因此只有研究文学存在的本体即文学的形式以及文学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否则,任何其他的研究和探索就是阐释不当,走入歧途。我们可以简约为新世纪的新审美主义。其二是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只应关注其特殊的存在,因为不同时代和社会的文学具有特殊性、国情性,而不能通过这种研究和理论探索来讲求普遍价值或普世价值,或者说,并不能通过特殊的文学研究而得出具有普适性的共同价值。我们将其简约为新民粹主义。细究之,这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否认文学及文学研究实际上所具有的关于人性或人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如果说审美主义或形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中尚具有某些重要的促进作用的话;而民粹主义自近代以来就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更多地起着或强或弱的搅局的负面作用,值得我们警惕。
文学的本体研究或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研究,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时期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之初,王国维倡导“无用之用”的美术观、艺术观、文学观,倡导“无功利的”美学和美育来取代特别注重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这一观念无疑具有冲破几千年来正统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艺观的重要学术和思想意义。再比如,文革刚刚结束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理论上的审美论虽然夹杂着意识形态论而形成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认识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倡导审美论或形式本体论,自然具有冲破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禁锢的重要学术价值和作用。随之而来的形式主义文论、小说零度叙述理论、语言乌托邦论等作为纠偏的理论倾向,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简而言之,文学审美论已然成为一个学术的共识或常识,已经不是今天的文学研究的学术问题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今天,文学研究同一般文化研究、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日益趋于消弭的情况下,再片面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就与时代有了很大的隔阂,也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嫌了。这种新式审美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构成了一种缺乏理性的新左派激进幼稚病。
笔者认为这种倾向实际上反映了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相应的政法配套改革并不到位的情况下,人文学界一部分人士要强行推出自己的理论纲领和主张的急迫心态。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正在醒目地构成悖论。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二,而我们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文研究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一种实质性的跃升,在人文产品产量大跃进的表面,隐藏着的是人文指标的下滑,按照2009年的数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在世界第92位[注]李敏:《中国人文发展指数世界排位提前》,《中国统计》,2009年第12期。;而到了2014年的数据,则下降到了101位[注]杨家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调研世界》,2014年第1期。。这种经济指标和人文指数的不对称现象,近年来不断加剧,强拆、严重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极度不公平、虚假选举等等,层出不穷。而真正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恰恰是要关注、揭示和批判这些不公正和邪恶的存在,以“引起疗救者”即当今的政治家的良善治理。但是,在这种GDP至上的思维引导下,某些人文研究者就产生了超过自身应有的理性的思维膨胀症,或者类似于列宁所批判过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只不过讲这种所谓文化自信的大跃进所采取的是所谓“政治正确”的方式,在目下是绝对安全的。其巧妙和“智慧”也正是在这里。在中国,长期以来往往学人们如果采取左的姿态,宣扬左的话语,是政治正确的,也是安全的。而右派或自由主义的思想则往往受到抑制甚或取缔,其命运往往是多舛的、坎坷的,甚至是悲剧的、毁灭性的。所以,某些依然遗传了左派幼稚病基因的人士,宁左勿右,其行为往往是见风使舵、媚上欺下的,体现在其文章中,往往就是不顾事实、不讲逻辑、假大空冒、强词夺理,反正有政治正确罩着做护身符。前些年的输出中国模式,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曾经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最后似乎偃旗息鼓。然而没想到它蔓延至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领域,目前正在这些领域里继续发酵、盛行。
这种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基础。笔者曾经针对莫言小说的阅读情况在一些乡镇科局、县处级以及少数厅级领导干部当中做过调查。他们一般知道或看过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有的还看过莫言的《丰乳肥臀》这一名称让人有些诧异的长篇小说。然而,十有八九他们会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无非是因为他把中国描写的愚昧、落后,写得不美,甚至丑陋、恶心、恐怖,这哪里是什么好作家?简直是十足的低俗的坏作家!瑞典给他这个大奖简直是寒碜中国,云云。等到你问,读过莫言上世纪80年代就出版过的《天堂蒜薹之歌》吗?看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檀香刑》等长篇小说吗?看过莫言的《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师傅越来越幽默》《欢乐》等中篇小说吗?他们基本上大摇其头。或许他们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莫言文集》之类的图书,但这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基层干部没有时间或不屑于去读,因为早在他们看了《红高粱》之后就业已形成印象——亵渎我们中华民族,从此就有一种拒绝看莫言作品的思维定势。这种受到传统媒体意识形态宣传所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他们大小是个领导的保护意识,就拒绝认真地、深入地阅读和评价莫言作品。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存在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领导干部心中的民粹主义作祟。另外,受到某种意识形态全天候的宣传而在一般底层百姓中也会产生民粹主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这种官员和基层的民粹主义思想意识作为理论性的民粹主义的基础,使其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甚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再地在关键时刻阻遏这一过程。
有学者认为:“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民众有且只有一个纯洁的愿望。而自由民主的假设则正好相反:要容忍不同观点和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民粹主义者的想象中,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都不属于他们‘民众’这个群体。”[注]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ueller):《民粹主义里没有“人民”》,《南风窗》,2013年第10期。问题的实质出来了,即想象性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演化,就变为打着基层民众旗号的民粹主义,它拒斥不同的观点,更拒绝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文学研究中,民粹主义表现为不能容忍那种借鉴自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理论,也拒绝认同和认真对待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近年来的新式形式论或审美论其实就是这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思维定势的反映。
这与前些年盛行的文学批评的犬儒主义有不谋而合的效果。犬儒主义往往陷于身体感官之维,打着所谓“自由”的幌子,行的是将人的自由降低为动物本能肉欲的勾当。文学批评的犬儒主义者其实清楚自己是作为搅局者而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本能写作、力比多写作,和清代色情小说《肉蒲团》之类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动物(狗)的器官上再敷上一层皮肉,以强化身体器官的粗壮?糜烂如《肉蒲团》的性解放,也表征着产生这种文化的基因有着根本性的问题。在每一个时代的晚期,在中国文化的演变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糜烂透顶的所谓审美文化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及批评中的这种纵欲主义和犬儒主义,就是时代晚期病症的体现。[注]王洪岳:《当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与犬儒主义》,《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好在近些年来这种喧嚣的声音不再为文学研究界和批评界所关注。
文学是一种表现人的自由本性的语言的艺术,这种自由本性是渗透于人与世界方方面面的关系上,文学就是要充分表达出这种种关系的复杂性和全息性,由此就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文学的方式方法和理论观点。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所流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文论已经做出了卓越的阐释和贡献。而古今中外所诞生的许许多多堪称经典的伟大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可谓代表了人类生活/生存世界所构建的立体的、全息的价值体系,也就是普世价值观念。因此,好的、伟大的作品必须基于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但是又必须超越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从而达到人类在知情意或真善美价值方面的普适性。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近些年来,打开一些报章则会发现:反普世性(普适性)价值观的言论和观点铺天盖地。这里我们就需要返顾康德美学理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力图寻找到一种可以超越个体或特殊性的审美的普遍性的依据,他为此从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由此审美是一种非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同时是不用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而且具有必然性的感性或感觉形式。这是康德对于狭义的美即优美(纯粹美)的鉴赏的分析和判断。然而康德并没有停留于此,他其实更注重于分析和判断的是依附美即道德美。所以他在《判断力批判》的上卷倒数第二节即第五十九节专门论及“美是道德的象征(形式)”(“论美作为道德性的象征”),其旨在从自然走向社会,从自然美走向社会美(道德美),从而从优美走向崇高,崇高正是社会美或道德美的范畴。如此理解康德美学,才能较为完整和准确。而仅仅局限于所谓狭义的美(优美)、形式美,而忽视其崇高论或道德美论,很显然是片面的。康德美学既强调了美学研究和审美的形式性、自律性和神圣性,又顾及到美学和审美与人类的生存世界、生命世界息息相关的现实,并将美学、审美和艺术放置在人类文明和价值的普遍性的大背景下去观照,因而,才显得绵密严谨、深沉深刻又高屋建瓴、视野开阔。
康德美学正是把自己关于美和审美鉴赏的理论建筑于人类的共同感、必然性、普遍性基础上,所以才取得了为审美和艺术立法的哲学、美学价值。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康德美学等德国古典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精神虽然与康德美学有所不同,但是同样有一个指向共同感的思维方式,即“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既作为文艺批评的原则,也作为美学建构的原则,这里“历史”亦可理解为“实践”,由此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美学。这同样是具有人类普适性和普遍性的美学思想,而且在一百余年的美学理论话语建构中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学者参与而日益得到壮大。无论从两百多年来的康德美学,还是一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世界美学和艺术发展的实际表明,康德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极大地解放了艺术和审美领域,前者使之走向了自律的、具有尊严和高度的地位,后者使之建基于社会实践之上而更接地气。与此同时,康德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并没有忽视美和审美、艺术与社会、道德、伦理维度的联系,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近现代审美和艺术的演变方向。某个国家或民族什么时候真正将康德的美学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获得坚韧而颇富张力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和伟大作品、伟大审美精神的不断诞生过程当中;反之,背离了康德美学及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和时代的美学和艺术,就要陷于偏执的泥淖或混乱的渊薮当中。
世界文明包括文艺学发展延续至今,许多根本问题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这背后自然是因为有人类所必然产生和依存的根本性的共同之处所决定的。在关乎人类生存世界尤其是情感世界的文学艺术当中,人性的复杂性、爱情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乃至自我世界的复杂性等,日益得到充分的表现。在那些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中,上述的复杂性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把文学当作本体、形式或审美的方面来观照,当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仅仅局限于这种审美形式的研究,而断然否弃其他视域或路径的研究,比如社会学的、道德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历史学的、信息学的、系统论的、控制论的、统计学的等等,则显然不能够全面地穿透和把握这种立体的复杂的文学世界。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存在法则和标准正在于这种复杂性和全息性。对此波兰现象学家英加登鲜明地指出:文学作品除了具有字音及其高一级语音组合、意义单元、多重图式化面貌、再现客体等四个层面之外,还可能存在“形而上的特质”(metaphysical quality),即作品中所表现的崇高、悲剧性、喜剧性、恐怖、震惊、玄奥、丑、神圣性和悲悯性等九大要素,这种“形而上质”就是“伟大的文学”区别于一般作品的特质。[注]Roman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Translated by George G. Grabowicz.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0.英加登所涉及的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不但顾及了文学作品的形式层、意义层、形象层,而且提出了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的再现客体——在某些文论家那里称之为“第二文本”,还进一步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提出了九大要素来评判伟大的文学。英加登所讨论和设立的4+1分析批评模式和理论,尤其是后一种标准,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神圣性和悲悯性的民族及其文化来说,对于我们廓清种种狭隘的形式主义、审美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迷雾,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所以,如果认真地从康德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汲取思想资源并引导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我们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陷阱或弊端,诸如唯我独尊、张扬跋扈、犬儒主义、民粹主义等,而能以伟大的气度、开阔的胸怀、坚定的目标、执着的作为、理性的态度,构建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一致的伟大的学术思想包括文艺学思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