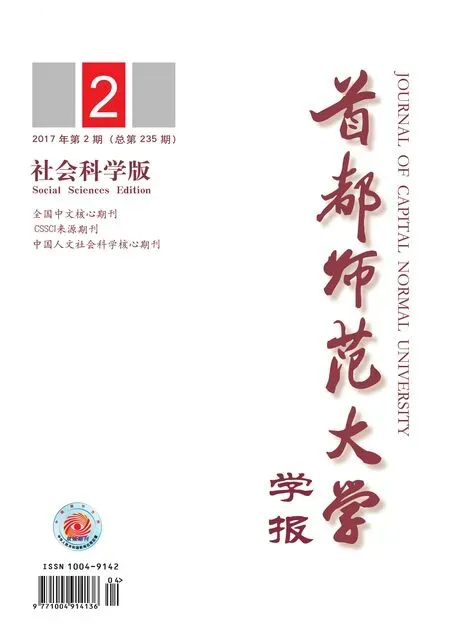唐宋国家礼仪的习学与演练研究——以朝仪与亲郊的习仪为例
2017-04-14吴羽
吴 羽
本论题由北宋大学者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的一段话引发,他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接着,他解释了这样说的缘故,这是因为,他认为三代礼乐渗透到了上至朝廷、下至庶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三代之后,三代的那些礼乐只是“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而已,“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即使是参与其中的缙绅士大夫也“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根本不知道礼的本意,礼也就起不到“教化以成俗”的作用[注]《新唐书》卷11《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7-308页。。
然而,众所周知,郊庙、朝廷礼仪中的“降登揖让、拜俛伏兴之节”乃庙堂常行之仪。这就意味着,尽管这些“礼之末节”并非欧阳修所珍视的那种“礼”,却是牵涉到当时众多缙绅士大夫的“史”。有鉴于此,唐宋人关于郊庙、朝廷礼仪的习学与演练理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至于欧阳修此番痛心疾首之论,其背后蕴含着对古今文化、政治的深沉思考,有着独特的历史情境,所涉繁芜,本文不拟讨论。
如果说前贤关于国家礼仪的研究重点在礼仪的制定、举行及其象征意义,那么我们关注的则是国家礼仪举行前的准备,以及国家礼仪怎样作用到相关的人。我们也试图借此考察礼意能不能表达,如何表达,国家礼仪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意义。
详细叙说每种国家礼仪的习学与演练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现仅以朝见皇帝礼仪(下简称朝仪)和皇帝亲郊大礼为例,凸显唐宋国家礼仪习学与演练的一些侧面。为说明唐宋国家礼仪的演练其来有自,我们将先以朝仪为例对汉魏六朝的习仪及其意蕴作一简略回顾。
一、汉魏六朝时期朝仪演习的意蕴
汉代以降,言国家礼仪者无不论及叔孙通与诸儒生共起朝仪,绝大多数论者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施行朝仪之后刘邦所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上,借此凸显国家礼仪,尤其是朝仪的重要性,这基本上是从皇帝的角度解读朝仪的意义。我们认为,汉初朝仪的创立,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观察,即从皇帝、群臣、有志维护朝仪秩序的学者三个角度,考察他们对朝仪的认识与感知。下面我们就稍作分析。
《史记》对叔孙通创制朝仪的背景有精要地记载:
汉五年(前202),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注]《史记》卷99《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2页。
“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是新朝仪得以创制的最重要前提,叔孙通最初建议的是“就其仪号”,所谓的“仪号”今难确知,但是就“高帝悉去秦苛仪法”来看,显然叔孙通最初创制的汉仪基本上是秦之旧制,然而这种建议并没有得到刘邦的采纳,而是做了大量的精简。很明显,刘邦是想通过“悉去秦苛仪法”的举动,凸显自己有别于秦皇帝的新形象,传递简易治国的新理念。群臣在朝仪中“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恐难视为对刘邦权威的轻视,而应视为一些人对自己在群臣中的相对地位不满。这就意味着,大臣在朝仪中关注的重点并非刘邦要传达的政治信号,而是自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身份地位。刘邦看到群臣的表现后“患之”,说明刘邦既认识到现行朝仪是失败的,又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这与群臣的真实想法并不完全符合。叔孙通发现“上益厌之”,则又说明有志维护朝仪秩序的学者官僚,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在王朝中的位置,更注重从中解读皇帝的想法。
如此看来,叔孙通进一步改革朝仪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要维护皇帝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朝仪来规范群臣之间的身份、权力差别,并借此显示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秩序。
什么样的朝仪才能既与秦仪有别,能够凸显汉皇帝与秦皇帝的不同,又能达到反映新权力结构的目的呢?叔孙通的意见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对此,刘邦回应了含义丰富的十四个字:“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可试为之”,表明刘邦对叔孙通的建议想尝试,又不完全相信,因为自己所定的简易之法效果不彰,可是古礼繁缛,未必能行,秦仪又是刘邦之前不愿采纳的。“令易知”则是刘邦给与的原则性指导,要维持自己之前的理念,不能太繁琐,且要容易修习。“度吾所能行为之”,是告诉叔孙通,必须考虑实行性问题,而且自己具有最后的决断权。
接着,《史记》有以下记载:
(叔孙通)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注]《史记》卷99《叔孙通列传》,第2723页。
新的朝仪在创制之后必须先培训一批熟悉仪式的专才,进行预演,成熟之后迎来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观者——皇帝。刘邦说“吾能为此”,表明叔孙通和儒生共起的朝仪符合了皇帝的想法。正因为刘邦已经完全确立了权威,所以能令“群臣习肄”。在“习肄”中,皇帝虽然不在场,但是皇帝下令“习肄”,却明白无误地传递了一个消息,这个仪式是皇帝本人想要大臣们做的,大臣们应该将仪式的焦点集中到“皇帝”身上,而不是更多关心自己的身份差别,习仪完成了群臣在仪式中关注焦点的集中。“习肄”的过程,朝臣既是学习者,又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更是熟悉自己在当时权力结构中位置的过程。
汉代以降,随着国家权力结构地不断变化,不断有新人进入朝仪的行列,群臣必须不断熟悉自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身份,习仪就显得非常必要。例如《隋书》记载:
陈制,先元会十日,百官并习仪注,令仆已下,悉公服监之。设庭燎,街阙、城上、殿前皆严兵,百官各设部位而朝。宫人皆于东堂,隔绮疏而观。宫门既无籍,外人但绛衣者,亦得入观。是日,上事人发白兽樽。自余亦多依梁礼云。[注]《隋书》卷9《礼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3页。
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习仪,这显然是要熟悉陈的新规制,在其中进一步认知自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习仪的官员们不仅仅是要熟悉自己应行的礼仪,还要顾及那些“隔绮疏而观”的宫人,乃至“绛衣”入观的人们的观感。
新加入朝见皇帝行列的官员原本就对朝仪不熟悉,而有资格朝见皇帝的官员却未必完全清楚自己在盛大朝仪中的确切位置、应行礼仪,所以汉代以降,练达朝仪是一种学识与身份的象征,现举两例如下,以见其概。《晋书》载孔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注]《晋书》卷91《孔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59页。。《宋书》载:
王准之……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注]《宋书》卷60《王准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3—1624页。
足证练悉朝仪是身份、学识的一种表征。
也正因为朝仪并非普及性知识,所以是否熟悉朝仪成为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的一种界限,文官与武将的区别,《南齐书》记载:“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注]《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73页。不仅可以佐证上述判断,而且可以说明,一般的地方武将没有被专门教习朝仪,周围也没有习练朝仪的氛围,只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偷偷练习,即使如此,还不免被“妾侍窃窥笑焉”。
总而言之,朝仪,尤其是大型朝仪一直都不是普及性很强的礼仪,对皇帝之外的人来讲,习仪不仅仅是熟悉仪节,学习如何向皇帝致敬,更重要的是熟悉和体认自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身份。我们认为,唐宋的习仪也具有类似的意蕴,下面我们将稍加分析。
二、唐宋朝仪的习学与演练
唐代朝仪的习学与演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原本很少有机会或刚刚获得资格朝见皇帝的官员对具体仪节的习学,另一方面是大型朝会前所有官员都必须参加的演练。下面我们就进行一些考察。
时人认为习练朝仪对塑造忠于皇帝的性格具有重要的作用。《旧唐书》载褚遂良云建议太宗将年齿尚幼的儿子留在京师,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可以“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注]《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1页。。
事实上,皇帝和朝臣也通过臣下朝见皇帝的仪节来观察该人对皇帝的态度。《新唐书》曰:
韩思彦字英远,邓州南阳人。游太学,事博士谷那律……授监察御史……思彦久去朝,仪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诋外戚擅权,后恶之。[注]《新唐书》卷112《韩思彦传》,第4163—4164页。
武则天“恶”韩思彦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诋外戚擅权”,但是“仪矩梗野,拜忘蹈舞”也是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使得武则天感觉韩思彦对自己不够尊重。《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六载(747):
禄山见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为不拜?”禄山曰:“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也,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注]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这是一条学界熟知的材料,安禄山的表现和对答被当时很多人理解为有反叛之心,或装疯卖傻,也说明人们通过朝仪来观察臣下对王朝的忠诚与尊重程度。
原来很少有机会或刚刚获得资格朝见皇帝的官员对礼仪的习学,既是一种姿体语言的练习,也是对自己新身份与社会角色进行体认的过程,例如白居易在《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中言到:“忽忆烟霄路,常陪剑履行。登朝思检束,入閤学趋跄。命偶风云会,恩覃雨露霶。沾枯发枝叶,磨钝起锋芒。”[注]白居易撰,朱金城箋:《白居易集箋校》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74页。对自己的新身份和社会角色充满期待。
而对朝仪的熟悉又成为晋身官场的一种优势,《旧唐书》记载李德裕说:“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注]《旧唐书》卷18上《武宗》,第603页。李德裕以此为理由希望武宗重视公卿子弟,说明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也说明熟悉朝仪本身是一种优势。
唐代大型朝仪牵涉人数众多,是对国家核心权力结构的一次总展示,即使那些经常有机会朝见皇帝的官员也需要进行事先演练,一方面是熟悉自己在复杂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二是弄清楚,在这一礼仪中,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履行何种礼仪。韩愈在为董晋所写的行状中说:
初,公为宰相时,五月朔会朝,天子在位,公卿、百执事在廷,侍中赞百僚贺。中书侍郎平章事窦参摄中书令,当传诏,疾作不能事。凡将大朝会,当事者既受命,皆先日习仪。于时未有诏,公卿相顾。公逡巡进,北面言曰:“摄中书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请代某事。”于是南面宣致诏词。事已,复位,进退甚详。[注]韩愈撰,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赠太傅董公行状》,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
宰臣犹须在大朝会之前习仪,更勿论他人。《文苑英华》有《国公嘉礼判》四道,判题为“国公有嘉礼,谒者不示仪式。科之,云非五品已上。仰处分”[注]李昉:《文苑英华》卷507《国公嘉礼判》,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595页。。也说明 “有司”有向行礼者解释仪式的职责。董晋的表现也说明,在唐代的习仪中,群臣在仪式中不仅仅关注皇帝,也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份与应行礼仪。
中晚唐时期,随着中央权威的渐趋衰落,武人地位的提升,武人对习学朝仪的热情有所下降。《旧唐书》记载:
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十七年(801),全义自陈州班师……全义武臣,不达朝仪,托以足疾,不任谒见。全义司马崔放入对,德宗劳问……自还至辞,都不谒见而去。[注]《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第4247—4249页。
韩全义因不达朝仪竟然托口足疾不朝见德宗,说明当时武人不识朝仪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说韩全义是跋扈武人,代表性不足,那唐宪宗时期平定西川刘辟之乱的高崇文便更具代表性,《旧唐书》记载: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从平卢军。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西蜀平……崇文不通文字……乞居塞上以扞边戍,恳疏累上。二年(807)冬,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宁庆三州节度观察等使,仍充京西都统……以不习朝仪,惮于入觐,优诏令便道之镇。[注]《旧唐书》卷151《高崇文传》,第4051—4053页。
忠于唐中央王朝的高崇文亦不习朝仪,甚至“惮于入觐”,表明随着中央王朝的持续衰落,导致武臣习学、演练朝仪的热情在降低。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我们这里说武人,主要是指那些地方武人和中央无资格经常入朝的武将。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认为地方官员和武人没有学习朝仪的条件和途径。一方面,地方有不少曾在京任职的官员,节度使、刺史幕中亦多熟悉朝廷典章制度之人,如前揭韩全义的司马崔放便熟悉朝仪。另一方面,唐五代国家的礼典和与朝仪相关的文献曾在谈不上是唐王朝文化核心区的敦煌、吐鲁番流布,荣新江先生和刘安志先生先后发现并研究了敦煌、吐鲁番所出《大唐开元礼》残片[注]荣新江撰,森部丰译:《唐写本中の〈唐律〉〈唐礼〉及びその他》,《东洋学报》85:2,2003.9,第1-17页,图1—4;《唐写本〈唐律〉〈唐礼〉及其他(增订本)》,《文献》,2009年第4期。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周一良先生、赵和平先生和吴丽娱先生则整理、研究了敦煌所出后唐时期的《刺史书仪》[注]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0页;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209页;吴丽娱:《唐礼摭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56—561页。,承史睿先生教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有《监门宿卫式》[注]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亦与朝仪相关。可以推断,在其他地方也曾流传相关的文献。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吴丽娱先生指出,晚唐五代“节度使统治下的藩镇就是地方的小朝廷,它的一切制度均参照中央执行,所以节度使在地方对下的权力、仪制也与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大朝廷没有两样”[注]吴丽娱:《唐礼摭遗》,第581页。。我们对吴先生研究的理解是,地方藩镇在日渐加强下属对自己的应行礼仪时,形成了一种藩镇僚佐对藩镇之主的变形的朝仪。又如吴丽娱先生所揭示的,晚唐五代藩镇还发展出了客司、客使这样的礼仪职司,“他们接待中央及他镇来使,赞导宾客来仪”,是“藩镇的礼仪之官”,客将“在接待中也要掌握具体仪节”[注]吴丽娱:《唐礼摭遗》,第609—615页。。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晚唐五代中央的閤门使、地方藩镇的中门使在藩僚朝见藩镇之主仪式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对此我们另有专门研究,此不赘述。。也就是说,中晚唐时期朝仪习学呈现出一个相反相成的局面,一方面,武人对学习朝仪普遍热情不高;另一方面,在藩镇之中,唐王朝朝仪的简化和变形形式却备受藩镇重视,使得这种变形的朝仪,成为供职藩镇中的文武僚佐必学之礼,这是五代构建朝仪的历史前提。
五代政权均起家藩镇,大多数官僚并不熟悉在唐代朝仪基础上重新构建的朝仪,他们必须通过习仪认识自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身份,所以仍然需要有司进行专门教习,《五代会要》记载:
(长兴三年,932)十二月三十日,礼部贡院奏:“准《会要》,长寿二年(693)十月十日,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已来,天下诸州府所贡物,已至元日皆陈在御前,唯贡人独于朝堂列拜。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贡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曰:‘可。’近年直至临锁院前,赴应天门外朝见。今后请令举人复赴正仗。仍缘今岁已晩,贡士未齐,欲具见到人点引,牒送四方馆,至元日,请令通事舍人一员引伸朝贺,列于贡物之前,或以人数不少,即请只取诸科解头一人就列,其余续到者,候齐日别令朝见。如蒙俞允,当司祗于都省点引习仪。”奉敕:“宜准元勅处分,余宜依。”[注]《五代会要》卷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68—369页。
地方并不专门教习朝仪,朝廷也不认为他们应该懂朝仪,所以才要让他们事先在都省习仪。
北宋构建朝仪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情形与唐代有类似之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祐四年(1089)十月甲寅:
户部尚书吕公孺言:“朝谒之制曰,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其未有差遣升朝官并朝参。缘每岁朔参,除假故外,遇视朝日方赴。其朝臣中颇有自元丰(1078—1085)年出外,近到京参部未久,复授差遣出外者,于朝仪元不知习。乞以望参为六参,朔参为望参,别不增减仪制,于职事亦无妨废。”诏礼部、御史台、閤门同共详定以闻。其后,诏朔参官并兼赴望参,望参兼赴六参。[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4,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465页。
那些不常在京师或较少参与各种大型朝仪者,仍然必须通过习仪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确切地位。至于一般的读书人,对朝仪就更加陌生,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閤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番人、骆驼。[注]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
正因如此,《宋会要辑稿》仪制9之7记载宋代规定“举人群见者,前一日习仪,至日俟崇政殿奏公事退引见”。同时,《梦溪笔谈》的记载表明閤门和有司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临时培训、监督朝见者习学礼仪的功能。
即使是经常参与朝会的人,遇到比较大型的朝参礼仪还是要先到即将行礼的地方习仪,《宋会要辑稿》仪制2之22至23记载乾道二年(1166)垂拱殿四参,合赴四参官需要到垂拱殿习仪。大朝会参与人员众多,更是需要经过教习、演练、正式行礼的过程,直至南宋均是如此,事参《宋会要辑稿》礼8之7至8所收《中兴礼书》,此不赘引史料。
朝参或大朝会还仅是觐见皇帝的仪式,而皇帝亲郊大礼牵涉到的人员更多,情况更复杂,下面我们就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三、唐宋亲郊大礼的习仪
《唐六典》规定:“凡国有大祭祀之礼,皇帝亲祭……皆祀前习礼、沐浴。”[注]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4页。有材料证明,这并非具文,《元稹集》卷47《王永太常博士》载:
勅:前东都留守推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王永:朕明年有事于南郊,谒清宫、朝太庙,繁文缛礼,予心懵然。虽旧章具存,而每事思问,求可以教诸生习仪于朝廷者,有司以永来上。永其勉慎所职,无令观听者有云。可守太常博士。[注]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47《王永太常博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7—508页。
本制也表明,亲郊之前要太常博士先培训一批人习仪吗,然后再渐次展开相关的礼仪演练,与汉代习仪相类。
天祐二年(905)哀帝拟亲郊事可与前揭材料相互证发,由于比较重要,现不避冗长,引之于后:
(天祐二年六月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弘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壬辰,敕:“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刺史等,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资朝官,敕到后三日内发遣赴阙,仍差人监送。所在州县不得停住,苟或稽违,必议贬黜。付所司。”……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栁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优诏嘉之……七月戊午朔,辛酉……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八月丁亥朔……洛苑使奏榖水屯地内嘉禾合颖。…癸卯,勅太常卿张廷范宜充南郊礼仪使……九月……乙酉敕先择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备物之间,有所未办,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十一月乙卯朔……丁卯……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圜丘。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已备。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而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蒋玄晖、张廷范、柳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晖、栁璨大惧。庚午,敕曰:“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虽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付所司。”[注]《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第796—801页。
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即位,次年亲郊,乃是惯例,天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冬至[注]此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唐代南郊祭天一般在正月上辛或十一月冬至[注]参金子修一:《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第175—179页。,哀帝等最初决定在十月九日,不合旧规,原因待考,推迟在十一月十九日,合冬至祭天旧制,再拖至次年正月上辛,正月上辛祭天亦为故例,不同寻常的是郊期一变再变,尤其是第二次改变显然是因为朱全忠的原因。但是哀帝这次未能举行的亲郊,恰恰较为详细地展示了亲郊前的准备工作。从时间上来看,十月举行亲郊,至迟六月已经必须开始相关工作的准备,八月奏祥瑞,九月时发现难以准备充分,不得不推迟到十一月十九日,准备充分之后,真正举行之前要在南郊坛“习仪”,即事先演练,十一月乙卯朔,戊辰为十四日,也就是说正式举行仪式前五天习仪。《资治通鉴》亦载此事,胡三省注云:“唐制:大祀,百官皆先习仪,受誓戒,散斋,致斋,而后行事。”[注]《资治通鉴》卷265,北京:中华书局,1956版,第8651页。联系前揭史料,胡三省的理解准确无误。五代亲郊之前依然需要习仪,事参《新五代史》卷28《萧希甫传》。
宋代亲郊习仪的材料就更多,能让我们观察到更多历史细部。《宋会要辑稿》礼28之5记载景德二年(1005)“十一月三日,亲郊前七日,百官习仪于郊坛。是日大雪,诏改用次日习仪”。《宋会要辑稿》礼1之4载:
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崔宪言:“近差行事官,或初登仕路,或久在外官,不习祠祭礼仪。望自今并先赴斋宫习仪。”从之。
足以说明,由于仪式繁缛,必须习仪,而且很早就需要安排。习仪的场所是在郊坛或其附近的斋宫,与唐代基本相同。其实,虽然正式习仪是在正式开始斋戒之前一日,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此时才开始学习礼仪细节,《宋会要辑稿》礼1之9载元丰三年(1080)皇帝亲郊,在正式习仪之前半月,“供官”就要开始接受培训,学习相关仪式。
南宋初由于政局不稳、财力有限,草草郊见之后,郊天之礼在一段时间内被明堂礼代替,绍兴十年(1140)明堂大礼对后来亲郊有重要影响,“执事宗室、侍祠朝臣、应奉人”需要提前一个月开始学习相关礼仪,教习地点在法惠寺,之后一段时间亲郊之前都在法惠寺,绍兴二十八年(1158)郊祀改在礼部宫苑,绍兴三十一年(1161)又改在原来的敕令所[注]礼部太常寺:《中兴礼书》卷43《吉礼四十三·郊祀杂录》,《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宋金绍兴议和底定之后的绍兴十三年(1143)正式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皇帝亲郊礼仪,那些“捧执笾豆俎官”、“举鼎官”、“奉礼郎”、“龛壝木爵官”等也是提前一个月开始学习相关礼仪,事见《宋会要辑稿》礼1之18至19。郊祀大礼中的“执擎仪仗人马官司”提前两个月必须安排妥当,提前四十日就开始在候潮门外大校场内习仪[注]礼部太常寺:《中兴礼书》卷19《吉礼十九·郊祀大驾卤簿二》,第90页。。而“奉宝次供辇官”、“授卫、传喝、亲从官”则需要提前两个月就接受培训,进行练习,事见《宋会要辑稿》礼2之28所收《中兴礼书》。南宋郊祀的乐工、舞人多为临时招募,不懂雅乐,需太常寺教习,按照制度,“所有节奏乐正……乐工、引舞、二舞共用四百六十四人”,教习九十余日[注]礼部太常寺:《中兴礼书》卷14《吉礼十四·郊祀大乐三》,第60页。。孝宗时郊祀大礼之后还要到德寿宫“进胙上寿饮福”,也要事先到德寿宫习仪[注]礼部太常寺:《中兴礼书》卷39《吉礼三十九·郊祀进胙上寿饮福》,第177页。。
虽然相关人员的培训早已开始,但是还不是正式的郊天习仪,在受誓斋戒之前还要举行正式的演习,就是所谓的正习仪,《中兴礼书》载绍兴十三年依北宋东京旧例在尚书省正式习郊祀前朝献景灵宫、朝享太庙仪,在郊坛习南郊仪,又载淳熙十二年(1185)十一月初六在尚书省习太庙仪,初九日在丽正门习肆赦仪[注]礼部太常寺:《中兴礼书》卷43《吉礼四十三·郊祀杂录》,第190、195页。。可证正习仪是亲郊的预演,与一般的教习仪节有所不同。
习仪的时间也直接决定从何时开始支付相关钱物,事见《宋会要辑稿》礼1之22,此不赘引。
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参与习仪者究竟有什么表现?是什么想法?所谓的礼意能不能在习仪中顺利表达?这是我们下面想考察的问题。
四、宋代亲郊习仪中的众生相与礼意表达
习仪并非正式举行礼仪,在习仪过程中,参与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不少人很不认真,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治平二年(1065)十一月:
壬申,祀天地于圜丘……先是,百官习仪尚书省,赐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饱呕吐,御史前劾失仪,及是,宰相韩琦以闻。上曰:“已赦罪也。”琦言:“故事,失仪不以赦原。”上曰:“失仪,薄罚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过,难施面目矣。”卒赦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7—5008页。
郎官王易知在习仪时候竟然醉酒呕吐,可见此人态度极不严肃。王易知被御史弹劾表明,在制度上非常重视习仪,将之作为正式礼仪来看待。不过,在实际上,皇帝并不想因此责罚王易知,也就是说,起码在此时、此事上,皇帝并没有太重视百官在习仪中的表现。
这并非特例,不少官员并不郑重看待习仪,《中兴礼书》中的一段记载对此表现的更加充分: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监察御史谢谔奏:“臣愚不肖,职在礼察,窃睹弹奏条有大礼两项,内应文武百官不严不恪、立班交语、侧身相揖,以及卫士、诸司言辞喧嚣、乖违仪式之类,悉合弹奏。今来大礼在近,伏见初六日于尚书省习太庙仪,时虽微雨,旋即开霁,因得从容。夫何百官执事未及归班,未唱礼毕,未曾躬身虚揖,未喝班退,而诸厅随行人从群众开(笔者按,当为哄)然而起,尽行冲散。当此之时,纷扰不辩,多有官员回避不及,颠仆于地,仅免践踏。谓之习仪,而所习未全。其所谓哄然者,虽有皇城司兵士号为弹压,而仓卒之间,寡不足以敌众,莫知姓名,无从根究。朝市传之,无不怪骇。至初九日,在丽正门外习肆赦仪,天晴人乐,初亦齐整,拜舞之后,百官尚未复归东西立班,其两畔即已哄然而起。行礼方毕,东西立班者未退,忽有皂衣头帽之人数十辈,奔走冲突,遂使百官失措,颠倒衣裳,比于初六日,又有甚焉。臣窃谓,当此盛时,欣遇大礼,陛下精勤恭钦,有司奉行,不敢不加肃洁,中外拭目,无不耸瞻,而班别之间,乃有不严如此,不可不行措置。缘随行人从群众,往往恃其所辖之官有权势者,因敢凌轹,无复忌惮。况所差皇城司兵士止有二十人,未能足用。臣愚欲乞睿慈特降指挥,自今大礼以及将来一应礼仪,百官立班,于未退已退之间,许御史台密窃识认,仍每番增差皇城司兵士共五十人弹压,遇有随行人从群起冲突,即收执送大理寺根究施行。如皇城司兵士客从,亦须惩戒,庶得礼仪之处,本末如一,而百官无冲突颠仆之患。谨具觉察以闻,伏候勅旨。”诏依。[注]礼部太常寺《中兴礼书》卷43《吉礼四十三·郊祀杂录》,第195页。
人员太多,况且演习者不少位高权重,随从众多,也使得不易监督。这起码表明,在这个习仪的空间里,那些随从人员根本不理习仪,关心的是自己的主人。这种情况传出去之后,据说“朝市传之,无不怪骇”,又说明普通的老百姓对习仪也觉得习仪应该是很严肃的,百官在习仪中的表现,直接影响百姓对大礼的观感。
正因为在制度上对习仪很重视,实际上很多人不严肃对待,所以如果在习仪期间表现认真,便会得到高度评价,这使得习仪成为一些人进行表演的重要场合。《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戊辰:
翰林学士钱惟演言:“正阳门习仪,皇太子立于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气暄煦,持繖障日,太子不许,复遮以扇,太子又以手却之。文武在列,无不瞻睹。有司设马台于太庙内,太子乘马至门,命移出萧屛外,下马步进。及南郊坛,前驱者解青绳将入外壝,太子亟止之,将及外壝,即下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资,谦恭之志,实遵圣训。虽汉储被诏不绝驰道,五官正服以见侍臣,比兹巨美,不可同日而语矣。昔桓荣以储宫专精博学,谓之国家福祐,书于史册。今太子持谦秉礼,发自至诚,士民传说,充溢都邑。伏望宣付史馆,以彰盛德。”诏奖皇太子,仍优答惟演。[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71页。
太子的微小举动便赢得了具有“英睿之德”这样良好的声誉,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的表演。钱惟演特别强调“士民传说,充溢都邑”,又一次说明,一般的民众不仅仅通过正式的郊礼观察参与者,也通过演习观察参与者的形象。
有些皇帝也借亲郊习仪来表达自己对礼仪的重视,以树立自己的形象。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第一次亲郊,便特别和辅臣说自己也要习仪,令礼官“草具以闻”[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8页。,在制度上,并没有皇帝习仪的规定,更没有故事可依,仁宗主动要求在禁中习仪,显然是想借此树立自己重视礼仪的形象。
正式的习仪是在景灵宫、太庙、郊坛,因为习仪毕竟不是正式礼仪,会出现各种不严肃的情况,有人认为在这些神圣的地方习仪有渎神之嫌。仁宗在嘉祐四年(1059)九月采纳了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邵必言的建议,将在景灵宫、太庙进行的习仪改在了尚书省[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94页。。据《宋会要辑稿》礼14之53记载元丰五年(1082)将南郊坛的正式习仪改在了南郊坛附近的青城斋宫。南宋南郊习仪又改在了郊坛,史料见前揭《中兴礼书》卷43《吉礼四十三·郊祀杂录》。
对不少大臣来讲,亲郊礼仪前的习仪,也是表现、体认自己身份地位的机会。《齐东野语》载:
淳熙九年(1182),明堂大礼,以曾觌为鹵簿使,李彦颕顿递使。习仪之际,曾以李为参预,漫尔逊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当者久之。在列悉以顾忌,皆不敢有所决择。太常寺礼直官某人者,忽进曰:“参政,宰执也。观瞻所系,开府之逊良是。”径揖李以前。时曾方有盛眷,翌日入愬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几误矣!”即日批出:“李彦颕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顿递使,礼直官某人,特转一官。”其改过不吝,盖如此云。[注]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孝宗命曾觌为鹵簿使,显然疏忽了李彦颕与曾觌的身份差别,但是群臣却对自己在仪式中的身份差别非常敏感,观者也对这种身份差别非常在意。皇帝在仪式中的表现,也被时人和后人拿来评头论足,其评论的未必是皇帝对仪式象征意义的理解,而是皇帝本人的某些特质。
总而言之,皇帝亲郊大礼各色人等在习仪中的表现是有差别的,礼的本意是否能与习仪者心中所念相合,实难肯定。但是,在这种演习的过程中,却可以表现各种权力和政治意图。
五、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汉宋之间,国家礼仪,尤其是大型国家礼仪,普及性极低。正因只有少数人熟悉国家礼仪的仪节,反而使熟悉国家礼仪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自然分开了各色人的等级与身份,有助于将都城、宫城与一般的城市、衙门拉开距离,分出界限,显示其独特的权威性和向心力。
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国家礼仪对皇帝的意义,也应充分注意礼仪中群臣的想法,他们往往更关注自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身份地位。
通过亲郊习仪中各色人等的表现,我们感觉,不宜认为参加仪式的人具有同质化的想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仅仅是行礼如仪,连具体的仪节都不懂,也就谈不上透彻理解这些礼仪所想透露出来的政治信号与学术理念。在这个本来应该是敬天祈福的场合中,皇帝、太子、高官想传达的往往并非对祭天本身的重视,而是各自的政治形象。也就是说,仪式运行的时间和空间里,仪式本应有的象征意义和他能传达的意义,不一定是相合的。
民众对国家礼仪的关注和审视并不仅仅是通过观看正式仪式,其实在礼仪准备时期,已经开始感受到国家礼仪走近的脚步,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到国家礼仪。也是从国家礼仪开始准备时,民众已经开始审视行事者的行为,并作出和礼仪本身的象征意义未必有关的解读。
关注正式举行的礼仪,仔细探讨确定仪注时的学术争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发现制定仪式的人想表达的政治信号与学术理念。然而,对国家礼仪的运行进行研究也同样重要,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有效检视这些政治信号与学术理念,怎样传递,多大程度上传递,能传递给谁?
中晚唐朝仪和亲郊礼仪举行的艰困,再一次提醒我们,国家礼仪植根于权力结构,本是表达权力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权力延续的决定力量,仪式再生权力的能力不宜高估。当然,仪式传达并表现既有权力结构和观念的力量则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