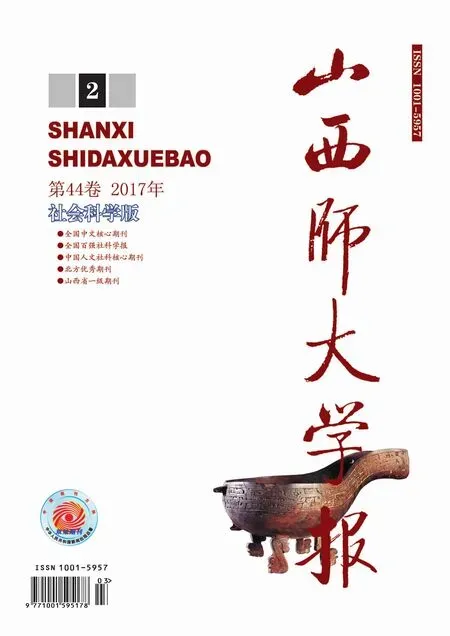从三晋方足布的分布情况看战国中原人口的迁徙
2017-04-14段颖龙
段 颖 龙
(北京阳光书苑,北京 100013)
三晋方足布是战国时期流通的一种布币,其形制为平首,平肩,方足,方裆的片状,因其面文多为三晋地名,故被定为三晋货币。研究三晋方足布,可以丰富我们对战国地理地名的认知。然而,三晋方足布是如何流通的?面文上的地名是否暗示其所流通的地域?如果我们需要结合古文献与其出土分布来还原战国货币的流通与人口迁徙的情况,以上问题自然可解。
一、从都邑到边塞的方足布分布
自春秋以降,诸侯大国的都城或一些都邑内就已经使用金属钱币了。如山西侯马春秋晋国都城新田遗址[1]46,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2]124等都曾出土春秋空首布币。至战国时代,一些都城没落了,如侯马晋都新田;还有一些都城继续兴盛,如新郑郑韩故城,在春秋时期为郑国都城,战国时期继续作为韩国都城;另有一些新兴的都城或都邑,如邯郸赵王城、易县燕下都等,在这些都城和都邑遗址内,都曾出土有三晋方足布。
在都城或都邑内出土方足布币,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以及集市贸易繁盛的体现。当然,都邑也是钱币发生与发展的原点。然而战国钱币出土分布却不仅限于列国都城,很多已伸向了边远地区。如山西阳高、祁县、原平,河北灵寿、鹿泉,内蒙古包头、凉城、和林格尔,辽宁铁岭等地都曾出土方足布(据《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先秦铸币出土简况表》及其图注资料,以下方足布出土地信息皆同)。以上地点在战国时悉属赵、燕两国边塞。
在一些诸侯国边关要塞遗址附近出土的战国窖藏的钱币数量巨大,且有些甚至多于都邑出土的窖藏钱币。这说明,在出征或在边境驻扎的军队中,必然存在着大量使用货币交易的情况。《商君书·垦令》即记载了在秦国军队的驻地附近,有供军士购买日用品的“军市”,那么军队在军市中可以使用钱币,应是与列国都邑内的集市用钱如出一辙。
关于东周集市钱币的使用方式,据拙文《东周钱币起源“契券”考》对先秦金属钱币的起源问题所作的综合性研究,通过大量钱币铭文考释并结合古文献、训诂学、货币经济学的相关论证,我们得出所有先秦钱币最早源于具有信用性质的“质剂”“傅别”这类契券的结论。[3]根据《周礼·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待不时而买者”及货币经济学原理,推测周代泉府是将集市交易后的滞销商品按平价以支付布匹的形式收购,以等待那些需要这些商品的人来购买。再据《周礼·质人》的记述,知周代质人管理集市中的货贿、珍异等商品,用质剂作为买卖者交易的信用凭证。再据《周礼·泉府》描述周代泉府经营“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的记载,知泉府可赊买祭祀和丧葬用品。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亦载:“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贞《索隐》:“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属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可知汉代“尚方”是生产和销售丧葬品和其他器物的官营作坊。那么周代泉府恐怕也有生产和销售各类丧葬、生活物资的可能,出土的战国和汉代墓葬中也不乏印有“某府”字样的随葬器物。综合以上几点考虑,我们认为,泉府的经营模式是兼典当、生产作坊和商铺于一身的。据此所复原的东周集市贸易的基本形态为:普通商品交易是用布、谷作支付媒介或干脆用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而在购买一些市场鲜有的祭祀、丧葬用的奢侈品时,就需要到泉府中用实物来订购这类商品以换取契券作为商品债务凭证。泉府在约定期限内为订购者收购或订做所需奢侈品,比如丝绸锦缎。到约定期后,买家便携券来泉府领取所订做的物品。久而久之,泉府的这种经营模式就会转变为典当的机制,而这种具有信用性质的用于异时领取货品的契券凭证也就演变为钱币了。[3]百姓用布匹从泉府中换来的钱币可在集市中流通,钱币几经易手,最终还会回流到泉府。[3]所以最初钱币的流通范围也仅限于泉府和集市。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就应是都邑集市和泉府所运作的钱币。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各大诸侯国都出现了在边境长期驻扎军队的情况,战国长城的建置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那么在边关要塞附近设置“军市”的原因,就是方便戍边部队日常生活。由于军中不可能每名将士都携带大量布帛或谷物作为日常耗用,所以将泉府发行钱币的经营机制移植到边塞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因为钱币小而便于携带,且有契券的信用性,国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任意赋予钱币以购买力,所以将士们只要携带少量的钱币就可以供应较长时间的日常消耗了。战国边塞军市钱币的使用表明,春秋以来钱币流通区域从大都邑的集市迅疾远播到边疆地区,使得钱币的流通范围骤然扩张。战国时期边塞地区大量钱币窖藏的出现,既是钱币走出大都邑而流通至边远地区的重要标志,又是汉代以后钱币空前普及的关键性起点,也是战国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明证。
战国军队中普遍使用钱币的现象,还能在出土的秦简文献中找到相关情况的蛛丝马迹。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了两枚秦国士兵写给家里的木牍信件,信的内容透露出秦军使用钱币的原因,其中一枚木牍文曰:
……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4]83
信是秦军士兵黑夫写给家中的老母,他希望母亲能寄来钱币与夏天的衣服。信中强调如果布昂贵,就寄来更多的钱币,他自己买布做衣服。“直佐淮阳,攻反城久”即黑夫所属的秦军已经驻兵于楚国的淮阳,并以此为据点,进攻楚国其他反叛的城池。这是秦将王翦发动的第二次灭楚战争中发生的事。由此可见,战国时的军中士兵很可能需要自备衣物。而除了衣服之外,仍需要家中供应钱币,这些钱币应是用于士兵们购买军粮的。当然,军队的大量生活物资是需要通过后方补给线由陆路的辎重车或水路的运输船供应的。但由这篇书信可知,这些军用生活物资对将士来说并非是免费的。因为在军队实行募兵制以前,军需都是要靠士兵自备的。如果长期在前线征战,士兵无法携带足够的粮食,只能靠后勤粮草补给线维持,而军粮是需要士兵出钱来购买的。所以黑夫写家信要求母亲寄衣外,似乎寄更多的钱币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些钱币正是维系士兵生存的口粮钱。
同样,长期在外服徭役,民夫们无暇种地,粮食供应也需要靠家人或官府。服徭役离家较远的,则必须都由官府统一供应粮食。这些粮食也需要民夫用钱币来购买。《云梦秦简》中有关于服徭役的民夫饮食用餐制度的记载:
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於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云梦秦简·司空》6)
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劳与垣等者,旦半夕参。(《云梦秦简·仓律》21)
《司空》中说,为赎罪和需要给官府偿债的人可到官府干活,能带饭的每日给八个工钱,需要官府供应餐饭的,每日可领到六个工钱。这些工钱都是为抵罪和还债之用,并非是为购买日用品的。既然须由官府供给一日餐饭者要比带饭者每日少二钱,那也就是说,一日餐饭的费用约值二钱。《仓律》又说,给修筑城垣的徭役工人供应的口粮是早饭半升(旦半),晚饭三分之一升(夕参),说明工人每天吃两餐饭。这样算下来,平均一餐饭大概价值就是一个钱。秦国当时流行的钱币是“秦半两”,大概一枚“秦半两”的购买力在当时就是一顿饭的费用。这种推测得到了另一批秦简文献的佐证:“受米一石,臧(赃)直(值)百卌,得。”(《里耶秦简》8-2015)这里明确说,一石米的市值是140钱。若参比《仓律》,一个普通劳动者一餐早饭食量为半升,晚饭为三分之一升,按一日早、晚两餐花费二钱来算,一石(100升为一石)米约花费167钱。这与简文所记一石米140钱的价值极为相近。
依据以上结论,在军事要塞和工程遗址附近出土的窖藏钱币,也许就是驻扎于当地的士兵和民夫们在营地里集体享用最后一餐饭的耗费。所以文章认为,窖藏钱币的数量等于在此营地驻扎的士兵或民夫的人数。那么在山西阳高、原平,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等偏远地区集中出土的方足布币窖藏和墓葬所陪葬的方足布就可以解释为是军队在戍守边疆时日常所用。士兵在边疆死亡后,亦可将钱币作为陪葬品下葬。
二、燕下都出土三晋方足布的历史解释
20世纪60—80年代初,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内先后有25次出土窖藏燕刀币,共计33315枚。[5]布币共出土1100多枚,其中燕国安阳布149枚,赵国尖足布和方足布400多枚,韩、魏布币各数十枚。[6]
燕下都出土货币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但燕、三晋、两周货币共存,而且还发现过戎狄刀币。一座都邑能同时发现多国钱币,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国际贸易繁盛的结果,各国货币可以自由汇兑。但是,造成货币汇兑这一现象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两国货币成色必须相当,大小必须一样或成比例,它强调的是货币自身的实际价值;一是不必考虑两国货币形制与成色,但须有对每种货币的购买力所达成的国际共识。初看东周各国货币,其形制殊异,大小也不同,甚至不同窖藏出土的同种形制钱币也存在大小及成色上的差异,故第一种条件在东周时期是不具备的。而在汉代以后,不同朝代和国家铸造的钱币往往可以混杂在一起使用,这正是由于钱币的大小和形制的统一所决定的。前代成色好且制作精良的钱币自然可以一直流通,其汇兑比率应是1∶1。最典型的实例出现在宋代,1983年河南息县郑寨熊庄出土南宋钱币窖藏,清理出的650余公斤铜钱中,年代最早的有西汉半两,最晚的为南宋淳熙元宝,而从北宋太祖到南宋孝宗各朝的钱币皆有。[2]353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新城子镇发现的辽代钱币窖藏出土古钱775.75公斤,计有20余万枚。这些钱币有226个品种,以唐代和与窖藏同时期的宋代钱币为最多,而辽钱计有10种,246枚。[7]这些窖藏钱币虽然年代跨度较大,但钱型皆为圆形方孔,大小轻重也十分近似,故可混同使用。而东周时期诸侯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时战时和。况且很多国家本国尚有若干种形制的钱币,恐难有后世对某些钱币形成的国际共识。所以推测东周不同类别的钱币根本无法实现汇兑。
既然东周钱币无法实现兑换,那又如何解释燕下都一座都邑会出现多国钱币呢?据前文的考证,东周钱币作为信用货币由泉府发行,流通范围也仅在集市中,所以这个现象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每种钱币在一个特有信用体系下独自流通。事实上,《史记》《战国策》《韩诗外传》《说苑》等“各书虽然都记载了燕昭王招贤纳士这件事,但并未说明燕昭王是在燕国的什么地方接待各国的贤士,只有《水经注》中明确记载燕昭王接待各国贤士的地点是在燕下都,燕昭王为了接待‘诸侯之客’,因而‘修建下都,馆之南垂’”[8]187。燕下都位于燕国南部,地近于中原,燕昭王为振兴燕国而励精图治,营建燕下都作为吸引中原诸侯之民的都邑,故燕下都同时出土燕刀币、三晋两周方足布、赵国刀币及戎狄刀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些中原和北方国家的贤士在燕下都受到礼遇,更刺激了这些国家的底层平民成批涌向这里定居下来,进而在燕下都形成新的社区里坊,各自通行本族群的货币。在发现于燕下都的三晋方足布上的三晋古地名相对应的如今所在地上,却从未出土过三晋钱币,所以推测徙居燕下都的三晋移民原本在故乡不通行钱币,但他们移居到燕下都后,可能为了标明自己的来源及身份,才铸造了面文为其祖居地名称的方足布。
三、避难性战争移民对方足布流通扩张的影响
秦钱的流通与分布呈东渐的态势,而中原诸国的钱币发展则呈现出两种现象:一是一地同出两国甚至多国钱币;二是列国在后期开辟的新领地上,钱币的发展与扩张较迅速,分布也较为广泛和密集。这些现象必然与广大平民的活动不无关系。燕下都出土的三晋布币已经证明是三晋之民为趋利而汇聚并定居在燕下都,从而在此通行方足布。那么,其他地方方足布的分布和扩张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一)一地同出多国钱币的原因
在一些大都邑遗址中,经常会出现一处钱币窖藏中有两个分装着不同国家钱币的陶罐。典型的案例有:1957年北京市朝阳门外呼家楼出土一坑战国钱币窖穴,其中有刀币2884枚,布币992枚。除燕、赵刀币与赵国尖足布外,余皆为三晋方足布。面文有“大阴”“兹氏”“莆子”“皮氏”“北屈”“屯留”“长子”等三晋地名[9];2006年7月,北京市宣武区广义街出土窖藏两陶罐,内藏战国中晚期燕、三晋、周等国钱币约三万枚,其中一罐藏方足、尖足布币,方足布中有铸“屯留”“宅阳”“奇氏”“皮氏”“莆子”“北屈”等三晋地名者。另一罐藏燕、赵刀币。[10]这种不同地区的货币却同藏于一处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一国都邑内同时出土多国钱币,一贯被学者看作是国际贸易的见证,在集市中进行货币汇兑的结果。而前文已证,每种体系货币都由其所经营的泉府发行,它们只能各自在集市中流通,两个不同国家的钱币分别由各自国家的泉府机构所掌握。在流通时,二者并行不悖,似乎也并不能产生汇兑关系。前文还证明,燕下都出土三晋钱币是移民的结果。那么北京市出土燕、三晋货币是否也是移民的结果呢?答案可以从东周墓葬考古中得到蛛丝马迹。分布于山西侯马及以南的万荣、闻喜、曲沃一带的战国早、中期平民墓葬明显是晋文化的分支,当是晋国魏氏家族所管辖的百姓及后来魏国的墓葬。[11]123—124据《史记·魏世家》载,由于魏国受到西面日益强大的秦国所逼,故于公元前361年“徙治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魏昭王六年(公元前290年),魏国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河东地区正与此系魏人墓葬区地域相合,而其墓葬区衰落时间也大抵近于公元前290年。考古工作者将山西万荣庙前村,侯马乔村、上马墓地,闻喜邱家庄、上郭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一系陶器墓葬(H2组)的类型定为Ab亚类型,即由晋文化分支出来的魏人统治下的晋遗民墓。[11]53,124而此系墓葬亚类型在河东衰落后,却在中原的周都洛阳、郑韩以及魏国河内地区获得很大发展。[11]112在豫北古属河内地区的辉县琉璃阁、固围村、褚邱、赵固和新乡杨岗等一组战国早期延至战国晚期早段的墓地(A2组)发现了同样的Ab亚类型[11]70,93,111。其时间跨度之所以大,是由于这里既有自战国前期晚段“三家分晋”时就从河东迁徙而来的魏人,又有战国中期从安邑迁都大梁时东迁的魏人,更有战国中期晚段魏国割让河东后东迁的魏人遗存。而分布于郑州地区二里冈、岗杜两地相对独立墓区的一组战国中晚期墓地(Z5组)及洛阳烧沟、孙旗屯、中州路、涧东、玻璃厂及老城环卫站的一组战国中晚期墓(L2组)也发现了Ab亚类型。[11]60,66故A2组、Z5组、L2组的墓葬年代上承H2组墓地[11]111,前三者与后者必然存在渊源关系,应是河东地区的魏人迁徙并滞留此三地而获得特殊发展的文化遗存。[11]124这是先后因属地的重新划分、迁都和割地而导致的三次集体大移民。
由于受晋南中条山、豫西山地等地形的阻隔,河东的迁徙之民不可能沿道路崎岖的山脉而行,其所选择的迁徙路径应是平坦易行的河道水路。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战国时的魏国漕运十分发达,其境内开凿鸿沟以连接黄河与淮河。而魏国对农田水利建设也极为重视,“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出土战国早期魏国错红铜水陆攻战纹铜鉴,铜鉴上有战船水战场景,再次证明魏国在河内地区的水上运输及水面作战能力极强。故魏人的迁徙路径大概是:自晋南黄河干流向东迁徙至洛阳;进而通过黄河支流及运河漕运迁至郑州;再一部分通过古黄河水道向北迁至河内地区及今开封一带的大梁。辉县、新乡是战国中晚期魏国在中原的统治中心河内地区之所在,洛阳时为周王城所在地,郑州及南部的新郑则为韩国属地和都城所在地。魏人的集体迁徙,正可以解释在辉县、洛阳、新郑和郑州地区出土的许多典型魏国桥裆布币。如河南辉县固围墓地M1和M2均出土魏国的“梁正尚百当寽”桥裆布[12]图版肆捌,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内亦出土“梁正尚百当寽”桥裆布币范及铸有魏国河东地名的方足布币范[13]81—85,图5—图9。况且洛阳、新郑还同时出土各国铸币的钱范,进一步证明这些外国移民已长期定居此两地,在新居地铸造本族群的钱币以通行。
如果是集体移民,而且到了新的移居点仍然不易俗,连墓葬风格及随葬品都保持不变的话,就只能说明这些为避难而迁居的魏人到新居地仍聚居一处,而且生活方式保持高度独立性,连陶器等生活用品都只在族群内部交易,那钱币就更不可能在异族之间交易汇兑了。这就是说,客居的移民虽与土著居民同处一城,但却各自保持自身传统习俗,至少不会很快交融到一起的。那么同理,北京市区同时出土燕刀币和三晋方足布币,只能证明三晋之民曾大批移居燕都。史书中虽无直接证据,但结合历史史实便可大致推测:秦国发动的灭六国之战,三晋首当其冲。尤其是秦灭赵战争,秦国打得赵国丧失了太行山以西的所有土地。赵民必然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不愿归秦,很可能逃难到燕国。赵民在燕都建立独立的社区里坊,他们在单独一个时间进入集市中使用赵币交易赵族群内部间生产的商品是很自然的事。这种小范围内的商业贸易应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贸易形式和特征。战国时期富商大贾跨国远程贸易固然有,但他们绝不会使用钱币作为交易媒介。《管子·山至数》云:“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刀”应指齐国钱币刀币,“布”即实物货币麻、葛布,而“币”也指丝绸布帛,“谷”是同样可作为实物货币的粮食,而“金”即指贵金属。后面“谷、币、金”三者并称,证明“币”只能指布帛而不是金属刀币。国家控制的府库垄断了大部分布帛和所有钱币的供应,而商贾手里掌握的是私人制作的布帛及各类商品,他们并不能操控钱币。
(二)燕国新辟土地上方足布的扩张
三晋方足布除了在华北地区有大面积分布外,在辽宁一带也都有发现。其中,“平阴”方足布曾在辽宁铁岭出土[14],从其名称和形制上看,显系三晋风格。然而辽河流域属燕,在燕昭王统治时期,“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这才占据了辽东。另据辽宁朝阳袁台子墓地的第二期战国墓葬的形制、遗物的特征与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极为相似[15]231,而百家村墓地的族属显系战国时期的赵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判定,在燕国设置辽东郡之后,曾有赵人远徙于此。
结合史实推测,既然方足布大量出现在燕都蓟城,那么出土于辽宁铁岭的方足布就有可能是由燕都的方足布使用者携带过去的。之所以从燕都移居到偏僻的辽东,其最大的可能就是避战乱。《史记·燕召公世家》:“(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很显然,蓟城被秦军攻破后,蓟城居民只能与燕王一道逃往辽东。而铁岭位于辽宁省东北部,境内的后山屯就曾发现有战国燕长城遗迹。此外,在铁岭新台子遗址等地也发现有战国至秦汉长城的踪迹。在燕国东北边境长城沿线出土方足布,说明三晋之民徙居燕国后,有不少加入燕军或服徭役,为燕国戍守边疆。为避战争之难而迁徙的三晋移民,在不断的战争中,将本族群使用的钱币播撒到蛮荒之地,从而为钱币的扩张与普及做出了贡献。
四、方足布所昭示的三晋人口迁徙历程
三晋方足布的分布面积甚广,北至辽宁、内蒙古中部,南达流经河南到山东西南部的黄河两岸。欲求这个现象的解释,我们可先以“皮氏”方足布为主,其他方足布为辅,来探究方足布的流通状况,进而描述战国时期三晋人口的迁徙历程。“皮氏”布在山西阳高、灵石、河南洛阳及北京市等地出土,而皮氏之地则在今山西河津,位于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战国时属魏国之河东(今山西侯马以南至黄河一带)。《史记》多处记载秦、魏两国争夺皮氏。皮氏属秦后,这里成为秦国进入魏国河东地区的一个跳板。由此向南可直逼魏都安邑,向东、向北则可进入汾河谷地,插入三晋腹地,可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山西河津东辛封村曾发现窖藏秦半两13公斤,总数约至少2000余枚。[16]按前文所证,边关钱币窖藏中的钱币数量应为营垒驻军人数,秦军在这处营垒驻屯2000多人是完全有可能的。1963年山西阳高天桥村出土平首布币13000枚,其中仅方足布的面文种类就有36种之多[17],这里面就有“皮氏”方足布。阳高县在山西省北部,境内有战国长城遗址,应是赵国北长城的一处重要关塞。在赵国的北疆居然出土了带有魏国河东地区地名的方足布,这不得不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去找寻魏国河东与赵国北疆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
赵国在北长城沿线抵御匈奴的赵军是战国时期的一支劲旅,“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白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赵奢李牧列传》)可见赵长城边防部队人数之众,军力之强。阳高县出土的13000枚布币表明,赵国在其北长城关塞一处营地驻扎13000人的部队,也是可以想见的。在阳高县出土的36种方足布面文内容均为地名,如“平陶”“彘”“土匀”“襄垣”等皆为赵国地名,而另有“皮氏”“奇(猗)氏”等位于魏国的河东地区;“马雍”“长子”则皆位于山西省南部,战国时属韩国的上党郡。[18]108,140,215,225,230,232这或许说明,在这个长城关塞戍守的赵国部队中,有来自赵国内地、魏国河东以及韩国上党郡的人。而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亦为赵国边塞,该县土城子遗址出土战国墓葬的人骨经过体质人类学研究,为“古中原类型”。他们很可能是赵国移民,在赵武灵王时移民戍边,他们是长期屯驻边塞的军事移民。通过葬俗,我们又可断定,这些戍卒的来源地可能是赵国都城邯郸及邯郸以南的赵国属地。[19]101,109这说明,赵边塞军事移民都来自赵国内地。赵边塞出土带有三晋地名的方足布,证明逃难来的韩、魏移民移居赵都及附近地区,后又与本土赵人共同加入戍边队伍,并来到赵北疆戍边。由于强秦的威逼,魏国割让了河东四百里,河东之民很可能大量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河东之地南接黄河,可联通魏国的河内地区和韩国都城所在的河南地区;北接汾河谷地,可直接进入赵国的太原之地。故带有河东诸地名的方足布可能是逃难于赵国的魏人为标明祖籍地而铸。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从沁河下游切断了韩国南北水路交通,使韩国北方领土上党郡孤悬于本土之外。上党郡守冯亭不愿归顺秦国,便将上党郡委命于赵。所以韩国上党郡诸属县之民遂投靠赵国,铸有韩国上党郡诸县地名的方足布即是他们在加入赵国军队后出现的。
前文已经根据东周墓葬考古发掘,发现河东地区与河南洛阳、郑州一带的部分平民墓存在渊源关系,证明了包括皮氏在内的河东之民曾迁徙到中原地区。而我们另从时间与历史背景来看,魏献河东四百里后的河东之民大迁徙也是十分合理的。《商君书·徕民》是一篇由三个不同时期上奏给秦王的奏章所组成的策论,文中记述秦国四代君主连续对三晋用兵,都取得完胜。然而由于秦法严苛,三晋之民便大量逃亡,使得秦国占领下的大片三晋故地地广人稀,无人耕种。作者建议秦王通过奖励措施,吸引三晋之民回归故土务农,为秦国增加粮食生产。文中提到秦对三晋的“华军之胜”、“周军之胜”和“长平之胜”三大军事胜利,它们分别指华阳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其中长平之战发生最晚,结束于公元前260年,说明《徕民》完成于公元前260年之后。而此前秦国占领三晋故地的状况诚如《徕民》所言,“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那么“魏献河东四百里予秦”发生在公元前290年,早于长平之战30年,显然河东之民的状况也只能如《徕民》所述,逃亡他地。
根据“皮氏”布的出土分布分析,秦国占领皮氏城后,皮氏族群之一部沿着黄河向南迁往洛阳周王城,另一部则沿汾河谷地向北迁往赵国,灵石即位于河东地区北部汾河沿岸的赵国境内;在赵国的皮氏人有可能被征兵派往赵国北疆戍边,所以至今尚留存战国长城遗址的阳高县境内会出土“皮氏”方足布;秦灭赵后,居住在赵国的皮氏人还可能随众逃往燕国都城蓟,即今北京市。北京出土的“皮氏”方足布恐怕就是在那时出现的。
根据上文分析的结论,方足布上的地名文字很可能是迁徙族群的祖居地,他们移民到新的土地上,勿忘先祖,在钱币上铸祖居地名以纪念,为本族群(河东之民)内部流通。除“皮氏”方足布外,魏国的“北屈”“莆子”“奇氏”方足布上的这些地名也都处在魏国河东地区*“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莆子”在今山西隰县或蒲县;“奇氏”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县南。这些地方都位于山西西南部,即古代的河东地区,战国时属魏国。,而这些方足布的出土地也不在其面文所指地,而是分布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如“北屈”“莆子”方足布发现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奇氏”方足布在山西灵石、祁县、阳高,河北灵寿及北京市都曾出土过。[18]176—177,256,232在河北灵寿出土的“奇氏”布,也能证明魏国一部分猗氏人早先曾移居赵国。灵寿县在战国时期属赵国的番吾,《史记·赵世家》记载:“番吾君自代来。”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常山有番吾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县东二十里。”[20]1797—1798隋始置房山县,即今河北平山县,其东北部毗邻灵寿县,与《括地志》所云在“房山县东二十里”完全吻合。《赵世家》又云,“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说明番吾是赵国的军事重镇。今河北灵寿故城村战国古城遗址当即赵国的番吾城。灵寿西邻井陉关,是阻遏太行山以西的秦军进入冀中平原,进而从北面威胁赵都邯郸的重要防线。赵国在番吾部署的大量军队,很可能也吸纳了原先移居赵地的魏国河东之民。另外,灵寿故城村古城遗址只在西面有烽燧遗迹,也说明这座具有军事意义的城市是专门防御来自西面井陉关外的秦军的。
五、方足布使用者的归属
三晋方足布因面文分别有韩、赵、魏、东周四国地名,所以其使用者即三晋、两周之民无疑。但前已论述,铸铭地名的方足布,皆为该地三晋移民迁徙到新址后所铸,那么可以推知,他们在迁徙之前可能并不使用青铜钱币。以魏国的河东地区为例,带有河东地区地名的方足布甚多,但这个地区却几乎无方足布出土。如山西夏县处古代河东地区,战国中期以前是魏都安邑的所在地,这里恰恰被“安邑一釿”“安邑二釿”“安邑半釿”等魏国大型釿布所覆盖。“安邑”釿布的出土地不但分布于河东,还在河南洛阳、新郑有出土[18]236—237;“阴晋半釿”“虞一釿”(或谓“陕一釿”)布币上的地名“阴晋”“虞”“陕”皆属魏地,这几类钱币也曾在洛阳、新郑出土。[18]198—199“阴晋”位于今陕西华阴,而“陕”位于今河南三门峡一带,虽皆不属河东,但也先后被秦军攻取,如“秦侵阴晋”[20]713、“相张仪将兵取陕”[20]730,说明釿布才是河东地区原本通行的钱币,而且主要流通于都城安邑及附近地区,边缘地带可能仍只使用布帛作为货币。应该说,方足布的通行仅在原本不使用钱币的三晋迁徙族群中。
综上所述,三晋方足布与其他类型钱币共出的窖藏,不能解释为不同货币之间可以汇兑,而是每种钱币在各自族群内部流通。方足布上多铸有地名,应是原居该地的战争移民在新居地上使用新款钱币时加铸的故乡名,并非该地通行的钱币。此外,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以及方足布的广泛分布可证,战国钱币的流通过程实际上是由普遍使用实物转变到大规模使用金属钱币,由都邑平民享用到影响乡鄙、边塞军民的钱币普及化的历程。同时,战国钱币的普及化也为秦汉统一形制的钱币在全国的推广和流通奠定了普遍而深厚的心理基础。
[1] 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朱活.古钱新典(上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3] 段颖龙.东周钱币起源“契券”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1).
[4] 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 石永士,王素芳.试论“ ”字刀化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3,(6).
[6] 高婉瑜.布币流通的历史解释[J].中国钱币,2003,(2).
[7] 吴宗信.三道营子窖藏古钱清理简报[J].中国钱币,1986,(2).
[8] 王彩梅.燕国简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朝阳门外出土的战国货币[J].考古,1962,(5).
[10] 程纪中,梁学义.北京广安门内燕蓟古城遗址出土数万枚战国刀币布币[J].中国钱币,2009,(2).
[11] 张辛.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3] 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新出土东周钱范[A].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14] 吴良宝.三晋方足小布的种类统计与国别考辨[J].文物世界,2002,(1).
[1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袁台子.战国西汉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墓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6] 胡振祺.山西河津县发现秦半两钱[J].中国钱币,1986,(1).
[1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阳高天桥出土的战国货币[J].考古,1965,(4).
[18] 马保春.晋国地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19] 顾玉才.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战国时期人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0] (汉)司马迁.史记(全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