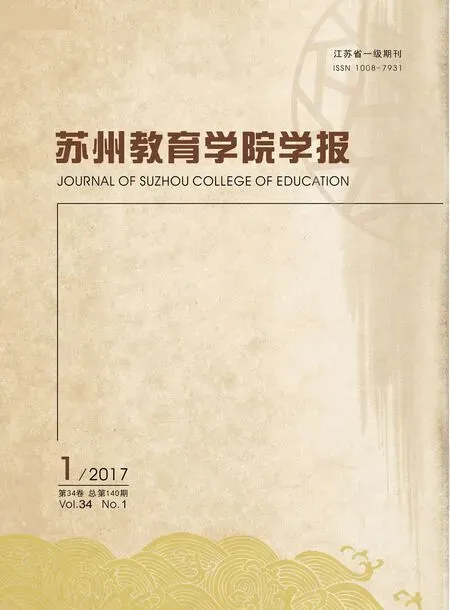论周良的苏州评弹研究
2017-04-14潘讯
潘 讯
(中共苏州市委 研究室,江苏 苏州 215004)
论周良的苏州评弹研究
潘 讯
(中共苏州市委 研究室,江苏 苏州 215004)
周良先生从事苏州评弹研究近四十年,他的研究从搜集整理史料入手,进而探索评弹的艺术特征,撰述苏州评弹史,对作为“非遗”的评弹传承保护形成了系统思考,并以多方位的贡献与成就,荣膺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苏州评弹;周良;史料;艺术特征;艺术史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周良先生先后出版了《苏州评弹旧闻钞》《苏州评弹艺术初探》《论苏州评弹书目》《弹词经眼录》《苏州评弹史话》《话说评弹》《苏州评弹艺术论》《苏州评话弹词史》等十余部专著。1984年至今,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主编《评弹艺术》专刊,至今已至51集。为抢救和保护苏州评弹传统书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良主持了《苏州评弹书目选》的选稿和编辑工作;近年来,他又投入很大精力主编《苏州评弹书目库》,现已出5辑,内含传统长篇书目二十余部,总字数逾五百万言。为抢救、记录评弹艺术家宝贵的艺术经验,周良先后主编了《艺海聚珍》《书坛口述历史》《演员口述历史及传记》等。近年来,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为保护与传承苏州评弹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周良又先后编撰《苏州评弹研究六十年》《保护好苏州评弹》等书刊。卅载辛苦不寻常,周良以其多方面的贡献与成就,荣膺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一
《苏州评弹旧闻钞》(以下简称《旧闻钞》)是周良的第一部评弹研究专著,出版于1980年。“旧闻钞”体例源于鲁迅,鲁迅先生有《小说旧闻钞》,其价值堪与《中国小说史略》相为呼应表里。鲁迅曾于该书再版序言中写道:“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并认为:“学子得此,或足省其浬重寻检之劳焉。”[1]周良的《旧闻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是“十年磨一剑”的精心之作。对评弹研究界来说,《旧闻钞》的价值不仅可以“省其浬重寻检之劳”,而且该书本身就是一部具有学术分量的著作。
增补本《旧闻钞》①本文以下所引据《苏州评弹旧闻钞》皆为“增补本”,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引述资料758条,搜罗广富,其中还有不少稀见的稿本、手抄本、孤本。比如,《二痴札记》为苏州古旧书店藏光绪十六年(1890)稿本,《开卷得乐》为苏州古旧书店藏同治间稿本,天悔生《金蹏逸史》为清咸丰同治间稿本,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为宁波天一阁藏抄本等。不少援引书目,虽是刊本,但因存世稀少也不易寻觅。如《海陵竹枝词》为清同治三年(1864)刻本,《新刊古本刘成美忠杰全传》系康熙五十九年(1720)姑苏千钟书屋刻本,
《旧闻钞》还从遗存的历代碑文、布告中发掘评弹史料。不少碑文对评弹史研究极富价值,如第130条“《复兴光裕社》”碑文[2]67,此碑立于1936年,记录了评弹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江南这一特殊时段的生存状态,具名人有吴小舫、魏含英、王雪春、钟子亮等,引人注目的是碑文全用白话,且原碑已失,已成孤本。还有许多资料见于当年小范围流行的小报,周良也一一钩沉,发掘出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如第136条《铁报》1947年1月20日报道光裕社改选的消息[2]68,这条资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记载了普余社创始人钱锦章当选光裕社理事长,宣告两社合流,当年光裕社禁止男女合演的旧规自然也烟消云散,这是评弹发展史中的重要一步。
《旧闻钞》不是简单的资料蒐集与罗列,周良在条目下加写了大量按语,这些按语有裁断,有辨析,且与本文相互生发,新见迭出,引人入胜。如评弹界素知传统长篇弹词《三笑》有“王派”“谢派”两大系脉,“王派”创始人王丽泉为清乾、嘉间艺人吴毓昌的传人,因时代久远,吴毓昌的资料匮乏,可是在《旧闻钞》第180条“吴毓昌《绣像三笑新编》”周良的按语中,引述了一首《鹧鸪天》,为了解吴氏生平提供了资料:“何许先生吴毓昌,近来不做猢狲王……”[2]85由此可知吴氏极有可能是一位作苜蓿生涯的教书先生。
有些按语既是本文的重要补充,本身又构成一条重要史料。如第87条“《光裕公所颠末》”下缀一长按语,提供了光裕社附设益裕社的重要资料,且移录了益裕社章程的主要内容。由按语可知,益裕社“成立于1910年,到1928年止,共办了17年”,益裕社倡导“热心毅力好义急公”,“每个社员每年存2角钱,以15年为期。艺人故世后,不问入所时间的长短,存入多少,家属可以领取补贴50元到100元。艺人家属,凡清寒者,每年终可领取救济金米二至三斗”。[2]42这条资料不仅为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评弹艺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佐证,也是研究清末民初苏州行业公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旧闻钞》不仅收集了大量资料,而且通过对资料的科学整理和分类,对评弹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呈现。如女弹词是评弹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对于女弹词的源流,前人没有作过系统研究,周良在《旧闻钞》中专辟“妓女弹词”门类,展示了清代中叶以来女弹词的分流和历史,还原了她们光怪陆离的生存状态。“一掐檀痕便有情,佳名艳羡唤先生。如何未嫁浮梁贾,也觉琵琶带怨声。”(《申江杂咏女说书》)[2]256写出了女弹词艺人的辛酸与哀怨。“愈时髦矣愈矜怜,巾帼衣冠任倒颠。不信但看弹词女,拜年也用小红笺。”(慈湖小隐《续沪北竹枝词》)[2]257又写出了女艺人的时髦与风流。“卖嘴原来不卖身,此中声价独超伦。谁知几曲琵琶后,一样桃源可问津。”(苕溪醉墨生《青楼竹枝词》)[2]259则是女弹词与妓女合流的明证。清末民初,针对女弹词的花榜品评之风盛行,这是女弹词兴盛的一个侧面,但史料已如鸿爪雪泥,渺然难寻,周良经过搜求,在第716条“公之放《上海书仙花榜》(1877)”引述所谓“二十八品”女弹词艺人的名氏及评语后,还在按语中引述了其他相近资料,计有持平叟《女弹词小志》提及女弹词24人、免痴道人《摘鸿雪词题二十四女品花图》、吴兴纫秋居士评定之《书仙红楼榜》涉及女弹词24人、曼陀罗馆词客《沪北词史金钗册》汇评女弹词36人、湘南泥中仙子于《申报》介绍女弹词15人以及《寰宇琐记》第四册《洋场书寓》涉及女弹词50人。[1]259此外,见之于词咏的还有梅花香里听琴客《沪北名花十咏》、西泠翠梦生《海上名花十友词》、苕上芦林生《花筵十咏》以及《申江十美赞》等[2]260,将这些资料贯串参校,即勾勒出一部19世纪下半叶上海书坛女弹词小史。
周良评弹史料研究工作的另一力作是《弹词目录汇抄•弹词经眼录》(以下分别简称《目录汇抄》《经眼录》)。《目录汇抄》将前人10种资料汇为一帙,不仅便于翻检,且增补新的资料,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将此项工作又推进一步;《经眼录》对弹词研究的贡献尤其不小,书内不仅收录弹词目录,而且附列了与之相关的小说、宣卷、戏曲等书目,对于开展比较研究和厘清弹词书目的系脉,价值甚大。《经眼录》所收书目不仅详注了版本、藏地,有的还引了序言、回目、跋语等,使读者对藏本了然于胸。如“三笑”条,不仅列出了经眼弹词本如乾隆刊本《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嘉庆癸酉(1814)本《绣像三笑新编》、道光甲辰年(1844)四友轩本《合欢图》、光绪四年(1878)重梓本《绣像三笑新编》、光绪戊子年(1888)上海书店本《新增笑中缘图咏》以及最新出1992年江苏文艺版徐云志、王鹰演出本《三笑》,而且还附与之相关的小说《唐祝文周四杰传》《三笑姻缘九美图》《言情小说绘图新三笑》,宝卷《三笑才子》《三笑唱情》以及戏曲作品《花前一笑》《文星现》等。[3]34《经眼录》中还有不少稀见版本,为我们了解一部书早年的演出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玉蜻蜓”条下有道光丙申(1836)重刊本《绣像芙蓉洞》,在回目中有“遇祟”“游狱”“滴血”等[3]46,这些内容已为今天演出本所不载,或仅见于解放初期的书场演出中,为我们进一步探寻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
在搜集、整理评弹史料的同时,周良也开始探索苏州评弹的艺术特征。1988年出版了《苏州评弹艺术初探》(中国曲艺出版社),1996年又出版了《再论苏州评弹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这些研究分别从历史、书目、演出、理论等角度立体呈现了苏州评弹艺术的概貌和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版于2007年的《苏州评弹艺术论》再一次展现了周良对于评弹艺术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堪称到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一部评弹艺术论。纵观三十多年来周良在评弹艺术研究中的不懈探索,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始终坚守评弹艺术的本体性,他鲜明地反对形形色色的对评弹艺术的曲解与异化,为苏州评弹正本清源,细心呵护着这朵江南曲艺奇葩。
其一,周良是在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中定位评弹艺术的本体性。一门艺术的本体性是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完善、定型的,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少不了向其他艺术门类学习,但学习的结果不应消弭了自己的个性,而是要让自己的个性愈加彰显。周良对评弹艺术本体的探索,首先是从与之临近的叙事艺术比较中来定位的。纵观周良的评弹文献,有关评弹与小说、戏曲异同的论述最多,而且再三申论,不断完善。他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表述为:
苏州评弹词和小说的不同在于:①评弹用口头语言,小说用书面语言。②小说的作者作为叙述者,不和读者见面,以客观叙述为主,少主观叙述。苏州评弹的叙述者为演员,直面听众,常用第一人称,与听众对话。③苏州评弹又是表演艺术,创作和欣赏同时进行,同时完成。苏州评弹和小说的相同之处,是创造艺术形象的方法及其被欣赏者所感知的方法相同。口头语言和文字,都是符号,都是思维工具。叙述者的叙事、描写、形容、刻画,借助欣赏者(听众和读者)的生活经历和艺术欣赏经验、欣赏者的想象力,共同创造形象和艺术意境,都是想象艺术。[4]296
这段话的精要之处在于,提炼出评弹艺术的本质是通过演员的口头语言展开叙事,演员的口头语言是评弹创造形象和意境的主要工具,因此,评弹不仅是一般的表演艺术,更是借助语言符号的想象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评弹更近于小说,语言成为这门艺术的生命源泉。
而评弹与戏曲同为舞台表演艺术,其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周良对于评弹与戏曲异同的论述也更为精彩独到:
苏州评弹和戏曲的相同点,两者都是表演艺术。两者的不同在于:①评弹演员作为叙述者,演出是讲故事。不是故事中的某一人物。演戏的演员,装扮成故事中的某一人物,是角色。②评弹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说书人也用第一人称出来说话,都用全知视角。这两种语言,戏曲是不用的。演戏,都是故事中人物(脚色)的话,都用限知视角。③评弹以顺时序叙事为主,辅之以多时空灵活转换的往复叙事。未来先说,过去重谈,既有故事中的现在时,又有说书人的现在时。[4]297
毋庸讳言,新中国建立以来,评弹艺术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戏曲化”的不良倾向也在潜滋暗长,甚至愈演愈烈。在不少艺人的表演中说书成了演戏,演员的口语叙事(说表)被削弱了,评弹作为说书艺术的本体性被扭曲了。对于评弹与戏曲的区别,周良站在捍卫评弹艺术本体性、原真性的严肃立场上,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复论述。评弹与戏曲的不同,前辈老艺人曾有过简括传神的表述,即一为说法现身(评弹),一为现身说法(戏曲)。应该说,是否“现身”是评弹与戏曲的本质区别所在,在评弹中即便“起脚色”也是“登台面目依然我”,与戏曲的演员肉身化表演有着本质不同。此外,由于演员口语是评弹最主要的表演工具,由此形成的一系列特殊的叙事技巧和表演方式也是戏曲中所没有的。
其二,随着研究的深入,周良逐渐把握了评弹本体的两个关键特征,即评弹“以长篇为主”和“以说表为主”,二者是维系评弹艺术的生命线。从艺术史看,评弹以说长篇为主,似乎毋庸置疑,但是在一定时期却成为争论的焦点。长篇虽然是一个艺术实践问题,但要令人信服,还必须从理论上予以深入阐述。周良则着重从评弹传统书目的形成历史、观众心理学等方面论述了长篇是评弹的存在方式。不仅如此,对传统书目的逐步推衍和伸长的过程,周良也作了详尽的分析:
评弹长篇扩展的过程,包括了:①故事中情节的发展,主干上生出枝节,一条线变两条线、多条线。②细节描写逐渐细致丰富。而且细节描写的段落,往往是艺术上精彩的段落。③对人物的描写,对人物心理和思想状态的描写。刻画人物愈益细致、生动、鲜明,在提高艺术性的同时,伸长了篇幅。④人称的灵活转换和叙事方式的更加细致,说书人的穿插和评价、议论,以说表为主的叙述,使书目也逐渐伸长。[5]188
以上深入而细致的论证,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评弹何以要“以长篇为主”,“以长篇为主”使得对评弹艺术本体性的把握更进了一层,也为评弹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指明了方向。不能不提及的是,在今天强调评弹“以长篇为主”还具有另一层现实意义。在各种艺术节展、评奖会演繁多的创作环境中,评弹歌曲化、短篇化愈益成为困扰艺术发展的阻碍,而所谓获奖作品大多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造成巨大的艺术浪费。
评弹本质是说书,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却不然。近代以来,评弹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存在轻说表、重弹唱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因“戏曲化”而加剧。2004年周良在与吴文科的通信中,对评弹“以说表为主”进行了深入阐述:“说书人的叙述语言,在整个语言中,在数量上占多数;在叙述中的作用,也占统领作用,起支配作用。”“说书人的叙述语言,作用包括:叙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环境;通过描述人物、细节,展开故事;故事的发生及演变的前因后果;描述人物的外形和内心活动、心理状态;对代言体语言,即人物的话作解释、补充以及评论。”①周良、吴文科:《关于苏州评弹艺术特征的通信》,《评弹艺术》第三十七集,内部出版物,2004年,第21页。“以说表为主”之所以成为维系评弹艺术的又一条生命线,也是与评弹艺术本体性紧密联系的,“说表”是评弹艺术最核心最独特最具魅力的创作手段,评弹艺术的精华主要体现在语言成就即艺人的说表上。离开了说表,评弹艺术杰出的文学性就荡然无存,评弹所借以塑造的无数鲜活形象就失去依托,评弹作为叙事艺术的独特价值就无从体现。
其三,以说表为主和以长篇为主的两大特征进一步决定了评弹的叙述方式,在此基础上,周良开展了深入研究,并提炼出一些重要观点。周良为此阅读了大量评弹脚本,其涉猎之广,钻研之精,可以说并世无第二人,他的研究绝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建立在充分而扎实的资料基础上的。
在评弹叙事时空的研究中,周良提出评弹叙事中常常出现的“两个现在时”[4]297问题,即故事的现在时和叙述者的现在时。按照叙事学理论,通常叙事作品中的时间具有二元性,即本文时间和叙事时间,而在评弹等口头叙事艺术中,本文时间的内涵已经大为丰富,本文时间成为“两个现在时”的叠加。周良没有照搬西方叙事学理论,而是从实例分析出发,给人豁然洞开之感。对此,周良举了评话《英烈•八卦楼》(丁冠渔演出本)中的一例,并在夹注中予以解说:“‘今朝已是正月半,南京城里灯彩扎满,各地得讯南京兴灯,全赶来白相,所以更加热闹。’这是故事中的现在时。‘说书人关照,出灯谜人家不过是好白相,想勿到朱元璋亲自看见,到明朝险遭灭门之祸,真危险。’说书人的议论,是说书人的现在时,但议论还是当时的情境而发的,是故事的现在时。”[6]121
评弹的叙述不仅有不同的人称,还有多种人称的灵活转换,这种转换,既出现在说书人的叙述语言和故事中的角色语言之间,又发生在说书人的客观叙述和主观叙述之间。周良从大量实例中提炼出评弹叙事人称转换的一些特点,绝不是空穴来风。他举了《西厢记•游殿》(黄异庵演出本)一例:“今朝天气晴朗,春光明媚。听店小二说离城不远有座普救寺,当家长老满腹经纶,不愿为官,出家为僧。……张君瑞想,不如乘今朝大好天气去拜访方丈,请他讲讲经文,再和他吟诗作对,一解途中之闷。”周良在评注中对此作了分析:“从说书人的客观叙述开始,‘张君瑞想’后转为用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讲述,是一次人称转换。”[6]122
至于评弹叙事频率最大的特征就是对于核心情节的反复渲染,周良以《珍珠塔》中对“前见姑”这一核心事件的反复渲染为例。现在的评弹演出本中,没有“前见姑”情节,而是通过几十次的反复叙述,加深听众的印象。而且评弹艺人的高超在于从不同人物口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复叙述,或简或繁,或浓或淡,或深或浅,或欹或正,做到“意叠语不叠,事复句不复”,使描写和叙述丰富多样,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反复渲染的叙事特征是与评弹“以长篇为主”的结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失去了长篇艺术形式,这种叙事艺术也将不复存在。
评弹叙事时序惯常的特点是“旧事重提”(回叙)和“未来先说”(预叙)兼具。周良举了评话《三国•古城会》(王雄飞演出本)中的例子:“旗下,一人骑在马上,手持丈八蛇矛。一身镔铁甲,圆睁环眼,燕颔虎须,一看正是三将军张飞。张飞怎么会来到此地?原来,张飞和刘备在小沛偷劫曹营,误中曹操之计,一场大败,弟兄失散。张飞突破重围……”[6]123这段叙述的后半段即是“旧事重提”。至于“未来先说”,周良举了评话《武松•大闹飞云浦》(吴君玉演出本)的例子:“施恩要等爹死脱,去十字坡,投奔孙二娘。后来一道上二龙山,后书我先交待。”[6]124“后来一道上二龙山”即是预叙,是以后的情节。这两种颇有意味的叙事特点也与长篇形式密不可分。
三
周良为评弹撰史始于“文革”结束后,20世纪80年代初他写过《苏州评弹史话》,2002年又出版了《苏州评弹史稿》(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应江苏省文联约请,又新撰一部《苏州评话弹词史》(中国戏剧出版社),侧重以总结经验为主。周良的评弹研究起步于史料搜集整理,在治史中他也充分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言必有据,不妄下论断。这从他的《苏州评话弹词史》中所附的大事记、书目表、系脉表等参考文献中即可见一斑。虽然是一门地方曲艺史,但是周良笔下呈现出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书中既注重从艺人、书目等角度展开叙述,也试图从行会、艺术等视角切入分析。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评弹四百年历程。周良的评弹史在详略繁简的安排上也独具匠心,以《苏州评话弹词史》为例,全书11章中,“古代的苏州评弹”“近、现代的苏州评弹”仅各占一章,更多的是叙述1949年之后的评弹发展,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苏州评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苏州评弹”,其余章节则为“评弹队伍的组织起来和管理”“评弹的历史和艺术研究工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学习陈云的评弹观”等,既梳理出历时态的评弹发展史,又对当下评弹生态作了多棱呈现。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三长”,即“史才”“史识”“史学”[7],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史识”。治史不仅要注重史料的选择与运用,而且要有论断,有见识。如周良认为苏州评话、苏州弹词形成于明末清初,且评话早于弹词,提出了三大论据,依次为“清乾隆时期,出现了有苏州话的弹词刻本。在评弹的传统书目中,其传承关系有的能上溯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了一批知名的有成就的艺人。清乾隆年间,苏州评弹艺人已经就积累的经验开始艺术总结,出现了王周士的《书品•书忌》。此为苏州评话、弹词趋向成熟的标帜”[5]242,从书目、艺人、理论等三方面判定一门艺术的成熟时期,当为不刊之论。
又如,近代以来评话发展滞后,弹词逐渐兴起,从客观上说,是评弹进入城市,接受群体发生变化之后的必然趋势,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电台兴起后,电台上出现了只唱不说的节目,又加剧了这一趋势。周良则进一步从艺术本身对这一现象作了论述,他认为,在近现代评话书目中,讲史的传统中断,侠客书一时蜂拥而出,艺术上多显粗糙,而同时弹词书目如《杨乃武》等多以揭露统治黑暗、弘扬社会正义为旨归,赢得了听众的欢迎。又加之近代以来弹词音乐及表演艺术获得很大发展,而评话的“噱”却陷入恶趣。同时,弹词书目因为得到文人的帮助,出现了雅化倾向,而评话书目则少有这种现象。因而,评话艺术就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走向衰落。[5]140这种分析完全从书目实际出发,而且有论断、有见地,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周良的评弹史还呈现出鲜明的反思精神。周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担任苏州市文化局领导工作,是评弹60年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有的事件不仅亲历,而且还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周良就曾因对“评弹以中、短篇为主”的观点持保留态度,而在“文革”中成为其一大罪状,遭到口诛笔伐。作为当事人,周良深知错误的政治路线对文艺的戕害之剧,并为之痛心疾首。他在评弹史撰述中,就用较大篇幅反思了建国以来评弹工作的失误和教训。在近来与笔者的谈话中,又重申了以下看法:
①建国初期的“斩尾巴”,1964年停说传统书,忽视传统书、传统艺术的继承,忽视传统艺术形式和特色的继承。传统书目淘汰、剔除过快、过多,传统艺术流失。②新书目的创编,脱离传统基础。“为政治服务”的急功近利,搞了大量的短小作品,大都不能在书场演出,不能保留。搞群众性的创作运动,但往往忽视书场演出的长篇书目建设。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阻塞了竞争机制,束缚了演员的积极性和艺术创造力。吃大锅饭,把人养懒、养穷。④艺术创造中的行政干预多,缺乏艺术民主,束缚了艺术创造力。[4]300
其实,这些弊病不仅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评弹工作中,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类似错误的做法主导了整个文艺事业。周良作为一定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执行者,作为体制内人,对于其中的甘苦冷暖自然比局外人更多一层体会。虽然上述表述看似平凡质朴,或许还有人认为这种写法不合乎撰史的体例和文笔,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字字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之论,历史的最高境界不正在于此吗?
周良的评弹史研究还体现出强烈的保护意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评弹在经历了“文革”后的短暂复兴又遭遇危机,观众群体老化流失,演员转业,引起了陈云同志的强烈关注。在《苏州评话弹词史》中周良用较大篇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顾,并总结了经验教训。进入21世纪,尤其是评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评弹保护工作又面临新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是保护资金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却是评弹艺术水准的持续下降,评弹艺术形式的异化、功利化的泛滥,艺术内涵和精髓在流失。对于如何保护苏州评弹,在理论界和艺术实践中都存在误区和混乱,作为前辈,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周良对此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警惕,他站在保护“非遗”的高度,对苏州评弹的保护作了新的思考和归纳,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评弹的要点:“抢救、传承传统书目;抢救、传承评弹传统艺术,包括传统艺术形式及其特色,艺术传承发展的规律;让评弹主要在书场里流传发展。”[5]274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州评弹保护画出了清晰的路径图,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可操作性。
[1] 鲁迅.小说旧闻钞[M].济南:齐鲁书社,1997:2.
[2] 周良.苏州评弹旧闻钞(增补本)[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
[3] 周良.弹词目录汇抄•弹词经眼录[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
[4] 周良.伴评弹而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 周良.苏州评话弹词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6] 周良.苏州评弹[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0.
[7] 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8.
(责任编辑:时 新)
A Discussion on Zhou Liang’s Study of Suzhou Pingtan
PAN Xun
(Research Off i ce, CPC Su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uzhou 215004, China)
Zhou Liang has been studying Suzhou Pingtan for forty years. He started by collecting and sorting data, moved on to pro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ingtan, and then began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it. He developed the systematic ref l ec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uzhou Pingtan,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ore, he has been presented with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f Peony Award of Chinese Opera for his multidimensional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Suzhou Pingtan; Zhou Liang; historical data; art characteristics; art history
J80
A
1008-7931(2017)01-0054-07
10.16217/j.cnki.szxbsk.2017.01.007
2016-12-20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YSC002)
潘 讯(1981—),男,安徽泾县人,硕士,研究方向:江南社会文化。
潘讯.论周良先生的苏州评弹研究[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1):54-60.周秉鉴《甫里逸诗》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易安书屋活字印本,天笑主人《忠孝节义二度梅》为嘉庆五年(1800)福文堂刊本,《绣像十五贯》为清咸丰甲寅(1854)惜阴书屋刊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