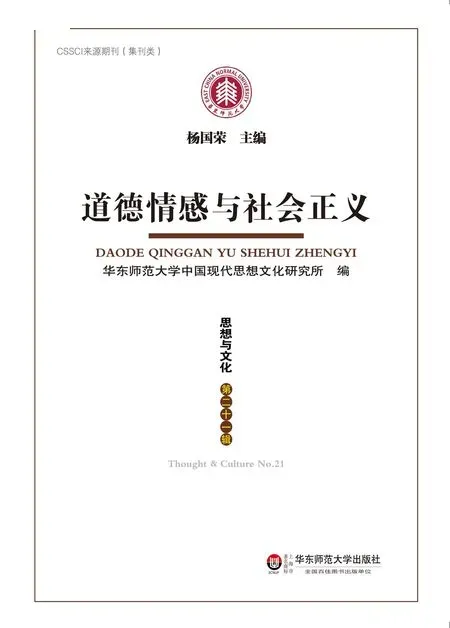儒家传统中的人权思想
2017-04-12
[]
一、引言
研究当代中国关于人权的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以研究中国传统中的人权问题作为开篇呢?答案必然是人权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有别于当下的人权理论和实践。例如,也许是传统阻碍了人权发展,也可能传统从一开始就支持人权?近年来,学术圈和政界都为这两个相反的立场发过声,也表达过各种介于这两极之间较为缓和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这些观点划分为三种不同的进路:(1)中国传统是人权发展的障碍;(2)中国传统是人权的一种替代;(3)中国传统是人权思想的源泉。一些学者支持这种或那种进路,而我认为以上三者都有合理之处。中国传统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一次性永久地决定当下中国人对于人权的思考,但是毫无疑问,传统对今天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影响,而且在今后还将继续影响着人们。本文的目的在于解释在何种意义上以上三种进路都是有道理的,以便为下面的章节更细致地考察当代人权话语奠定基础。
为了均衡起见,序言部分将完成两个任务:一是阐明本文提出的关键概念的含义,二是论述某些构建人权与传统之辩框架的现代历史背景。首先要厘清的是,何为“人权”?何为“中国传统”?为完成本文的目标,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权的哲学定义,也不是什么样的权利才算得上“人权”的冗长细目,而是一种基本的理解。首先,让我们承认人权是对我们最基本的价值与利益的特殊保护——全人类都需要的保护,这点毫无异议。*无论是从有什么样的权利的角度,还是从这些权利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的角度,关于人权的理论论述不尽相同,但我所强调的三个特征(特殊保护、全人类共有、可申明的)是多数论述共同的特征。参见Henry Shue,1996.Basic Rights:Subsistence,Affluence,and U.S.Foreign Policy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罗列一系列关于人权的具体观点是较为概括的做法,将人权与其他道德或政治概念区分开则是较为具体的做法。人权概念在很多方面与自由、人的尊严、人性、伦理的善、个人及社会利益、个人与集体义务以及道德上的正义等概念相关,但与这些概念又都不相同,模糊人权与其他道德概念之间的界线并在此基础上声明所有的文化都承认人权只会引起困惑。*例如,以下著作就模糊了这一界线:Paul Gordon Laure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Visions See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8。尽管我们得承认,这些概念中的某一个或某些今天可能用来佐证为什么所有人都拥有权利,人们拥有的权利又是什么。我们想在对中国传统中的人权进行质疑的背景下确定人权范围,一般的做法是对于在传统中找到关于人权的讨论持开放态度,具体的做法是呈现在传统中找不到人权的可能性——或者可能发现关于人权的讨论在某个地方出现过。毕竟,很多人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所说的)人权概念在欧美也是很晚才凸显出来。*Jack Donnell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传统”这个概念的三个特征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第一,也是最明显的特征是,传统涉及在当下重新援用过去的概念与价值。每一代人不是胡乱涂画出属于他们时代的核心概念和价值:我们是从长者那里学会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参见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梅杰(Phillipe Major)所做的修正亦很有帮助,参见Phillipe Major,“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Tradi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Democrac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odern China (1895-1925)”,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47:3,2016,pp.156-157。梅杰提醒我们不要过于强调动因与由动因构成的传统之间的分别;他引用伽达默尔的“偏见”概念强调传统总是在塑造我们。第二个特征是,重新援用是一个现实的、往往充满争议的过程,而不是像某个软件那样自动编程的过程。当支持传统的持续性重新援用的制度改变或者瘫痪的时候,传统反过来会受到影响。即使在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传统所依赖的推理自身会出现很多问题和挑战,往往导致传统内部重大的改变。*Alasdair C.MacIntyre,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8.因此,传统的第三个特征是:传统是充满活力的,其内部是多样化的,而不是静止的、整体不可分化的。在中国尤为如此,思想与实践传统数千年来一直处于嬗变中。
然而,本文会以重要的方式概括中国传统的多样性。几乎所有关于人权和中国传统的关系的讨论都聚焦儒学,我也会遵循这一惯例。这不是说儒学等同于中国传统或文化整体,也不是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儒学是中国传统中最好的东西。原因在于儒学在以往涉及人权问题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显然,中国传统中非儒学的价值与概念——诸如,道家、法家和墨家,也许还包括中国佛教——在诸多方面与人权相关,也许政治思想家或社会活动家将来都会沿着这些路径探索。过去及当下的中国,对人权或褒或贬的讨论主要是在儒学传统内展开的。将我们的讨论限定在儒学并非意味着要摒弃传统是充满活力且具有多样性的这一观点,因为拥有2500年历史的儒学传统本身就充满活力和多样性。为了展现儒学传统的这些特征,让我做一个扼要的历史性论述,并且要着重强调我所说的儒学传统的“永久性”。换言之,儒学和所有活着的传统一样,从未停止过与其他传统的交流和碰撞,无论是与更广泛的中国传统的其他组成部分,还是与更久远的源头话语。事实上,儒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发展演变的。在儒学的古典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发展了儒学核心概念与价值以应对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的挑战。*Loubna El Amine, Classical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A New Interpret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儒学创造性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是“宋明理学”时期,即公元11世纪至18世纪,在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下,儒学经历了复杂的复苏。这个时期,儒家以各种方式努力回应来自印度佛教中国化流派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挑战:要注意到中国与欧洲文明的碰撞并不是儒学第一次遭遇这样大规模的挑战和机遇,这一点很重要。*Stephen C.Angle and Justin Tiwald,Neo-Confucianism: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Oxford:Polity Press,2017.20世纪至21世纪可以称之为“现代儒学”时期。
在序言部分的结尾,我将较为详细地描绘现代儒学的发展脉络,部分原因在于正是现代儒家构成了当下人权与中国传统之辩的主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于1911年覆灭之后,中国思想家于1915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寻求中国价值、习俗乃至汉语的根本性改变。在很多方面,这场运动也可称之为文化革命,比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渗透面更广。“现代文明”价值在这场运动中兴起,像儒学这样的古老传统遭到了彻底的批判。*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参见Chen Duxiu,“The Constitution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 eds.Steph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Armonk,New York:M.E.Sharpe,2001,pp.67-76。现代儒学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诞生了。20世纪中叶,大多数现代儒家都认为儒学应该吸收人权、宪政民主等现代政治概念,因为人权和立宪主义所承诺的个人安全和选择是实现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目标所必需的。*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参见Liang Shuming,“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In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 eds.Steph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Armonk,New York:M.E.Sharpe,2001,pp.101-114; Zhang Junmai,“Human Rights Are the Basis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Documents and Commentary,1900-2000, eds.Steph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 Armonk,New York:M.E.Sharpe,2001,pp.197-201。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样的现代儒学思潮主要限于台湾和香港。自20世纪末始,主张“亚洲价值”阻碍了人权并导致对人权的不同理解的思潮出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有时也出现在中国。*Michael Jacobsen and Bruun Ole, (eds.)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Contes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Asia.Richmond:Curzon,2000.最近,中国政府官员及儒家学者都对(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做出过类似的批判。*Stephen C.Angle,“Western,Chinese,and Universal Values”, Telos, 2015,pp.171,1-6.曾亦、郭晓东编著:《何为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展开这一系列的人权理论和实践研究时,关于现代儒家的人权立场还没有达成共识,下文将更详细地考察这一点。
二、儒学传统是人权发展的障碍
人权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之辩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最为普遍的观点是传统阻碍了人权概念及制度的发展。*本文第四部分概述了人权之辩在中国的出现。有些人认为,人权与儒学传统难以融合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与人权相对的是一个可以将之取代的规范性秩序,在他们看来这一秩序比基于人权之上的秩序更为优越。本文第三部分将会考察主张传统内部存在积极的、可替代人权的因素的辩论,这个部分主要集中讨论四个消极论点——旨在证明在儒学基础上建立人权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儒学建立在等级礼制之上;(2)儒学中没有人权概念;(3)儒学断然不允许人权概念超越其他价值;(4)儒学关系论与人权不可融合。
1916年陈独秀在他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写道:“儒学的核心是礼教”,礼教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度,结果,等级制度与平等、民主和人权是不可调和的。*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参见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eds.Steph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 Armonk New York:M.E.Sharpe,pp.67-76。有人早于陈独秀十几年,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参见Anonymous,“On Rights.” In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 eds.Steph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Armonk,New York:M.E.Sharpe,2001,pp.15-23。另见Marina Svensson,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A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anham,MD:Roman & Littlefield,2002。陈独秀意识到会有人批判这一论断。他说,礼教与等级观念很早就是儒学的核心,虽然直到汉、宋儒者阐明了礼教与等级制度的关键前提,才把儒学发展成“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参见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eds.Stephen C.Angle and Marina Svensson, Armonk,New York:M.E.Sharpe,p.72。在陈独秀看来,儒学所强调的德目不是儒学或中国独有的,“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同上,第73页。陈独秀言下之意是,继续发扬这些德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儒学的基本礼制架构必须根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支持欧洲模式基础上的立宪制的公共文化。
陈独秀主张基于等级“礼教”的儒学与人权是不可调和的,这一论断非常犀利,至今在儒学内部仍然回响不断,有人批判也有人支持。例如,当代保守派儒家认为中国应抵制人权规范,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拒绝儒家的等级思想。*曾亦、郭晓东编:《何为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避开这一论断的方法之一是强调儒学德目是独特的,事实上,是这些德目而不是具体礼制才是儒学的核心。在本文第四部分,我将阐明更为激进的现代儒家是如何通过发展这一思想进路来囊括儒学与人权的。
陈独秀从礼制出发,论证儒学是人权的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观点:(1)古汉语中没有“权利”、“人权”等词;(2)因此也没有关于“权利”、“人权”等概念的讨论;(3)19世纪,人们试图将这些概念译成汉语时,发现困难重重;(4)最终,“rights”一词被译为“权利”,实际上是比较糟糕的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译法。总之,人权概念和中国传统及语言之间难以调和,造成了中国人权话语的障碍。
为了评价这些观点,让我们做一个有益的划分:与(19世纪之前的)传统形态相关的观点;与翻译及概念创新相关的观点。我们先分析与传统相关的观点,实际上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观点(1),但是观点(2)颇有争议。中国哲学家罗忠恕于194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争的论文,这篇文章自发表后就被广泛引用,罗忠恕承认中国古代思想家确实很少讨论人权问题,但他又说中国很早就有人权思想。*罗忠恕:《中国传统的人权思想》,参见Human Right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86。罗忠恕广泛地引用早期文献来论证他所说的君主的天职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罗忠恕也指出,人民推翻暴君的权利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虽然他提到早期文献都没有清晰地阐明这种“权利”,但显然他想到了《孟子》中广为人知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显然,这段话是在说,人民的福祉是极其重要的,任何君王都应该确保这一福祉才能保住王位。然而,在我看来,《孟子》中有些文字说明了:这一段话并不认为反抗是人民的权利。首先,《孟子》稍后明确说明了对于有过之君,异姓臣子能做的是反复告诫,而王室宗族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关于《孟子》中更换统治者的各种限制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Justin Tiwald,“A Right of Rebellion in the Mengzi?” 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7:3,2008,pp.269-282。此外,《孟子》也暗示了尽管推翻暴君的人不应遭受谴责,但他们的行为也是不义的。下面这段话明确地批判了君王“独乐乐”:“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孟子·梁惠王下》)还有一处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强调的是君王对人民的责任,而不是人民拥有的相关权利。批判一个暴君也是错误的,这样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大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虽然言论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上文(1)和(2)是符合事实的:中国传统中没有关于人权的讨论。在本文第四部分,我将会谈到中国传统中有几个本身可以作为人权基础的价值,但是儒学沿着另一个思想路径发展了,即围绕人际关系和责任而不是权利思想。但是,按照这一思路发展而来的(3)和(4)是正确的吗?传统中缺乏明确的人权词汇是否构成了现代人权话语发展的障碍?
这些问题相当复杂,详尽的回答需要专门写本书。*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回答,参见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我们不应该断定有一个精确定义的人权概念是某一个共同体拥有或缺乏的,我们也不应该断定翻译只是一个将“源语言”中业已存在的概念精确地复制到“目标语言”的过程。语言学演变及概念创新不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断言也忽视了从事翻译的动力和贡献。中国学者不是要生搬硬套地挪用欧美思想,而是要学习他国的经验和思想,形成中国剧变的特殊环境下合理的思想、价值和制度。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借鉴了传统,也有意识地发展出新概念,这些概念在传统中没有明确的解释,有些时候只有借助他们的创新概念才能清晰地表达(新思想)。*梅杰强调了传统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的论述大有裨益。参见Phillipe Major,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Tradi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Democrac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odern China (1895-1925)”,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47:3,2016,pp.153-65。总之,在中国形成明确的人权话语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过程,但缺乏一个原先就有的明确的人权概念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断定现代“权利”和“人权”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不是欧美的“rights”和“human rights”等概念的精确复制。
即使把这些概念发展的问题暂时搁置,在另一个意义上,儒学可能为接受人权思想设置了一个潜在的障碍。正如上文所说,人权是对我们某些基本价值或利益的一种特殊保护。在如何表达这一特殊保护的问题上,理论家未达成一致,但他们思想的核心都是人权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他价值并且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根据一些儒学诠释者的解读,在传统上儒学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价值领域,我们称之为“伦理”价值。*Stephen C.Angle,Sagehoo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因此,儒家在解释为什么存在人权方面面临一个挑战。不是儒家忽略了人们普遍意识到的价值间冲突的存在,例如孝道和公共责任似乎处于两个方向,而是传统趋向于认为,当我们了解并正确地看待具体情况时,总是能找到一个和谐的解决办法。*关于传统中的某些思想驳斥这一“和谐命题”,参见Michael Ing,The Vulnerability of Integrity in Early Confucian Though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这一框架似乎没有空间装下一系列特殊的受保护的利益。可以肯定,儒家已经说过我们需要充满仁爱地关心全人类的福祉,但这个责任需要与其他类型的具体社会责任协调。这一协调过程是非常具体的,需要基于具体情况进行。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直接的、共同的甚至难以摆脱的限制,这样的观点与儒学框架格格不入。
让我来梳理一下。第一个障碍的基础是把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礼教”等同于整个儒学,继而得出等级礼教与人权不相容的结论。跨越这一障碍的可能进路是领悟儒学传统的核心是现行礼教之外的其他事物,下文将会提到这一点。第二个障碍涉及传统儒学中缺乏一个清晰的人权概念,这一障碍可以通过概念创新来克服。第三个障碍来自于儒学的价值与对任一既定伦理问题的具体方案形成的整体,与人权格格不入。现代儒家采用两种途径应对这一挑战,两者都要求重大的创新:一把人权当作“备用设备”植入儒学,二是论证儒家应该把人权作为必要的“自我约束”之一予以支持,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对此作详细讨论。现在来谈一谈最后一个潜在的障碍,它深植于儒学对人际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强调。如果说儒学坚信人只有在关系中才能被理解,而人权则是基于人是原子那样的个体,那么推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不存在儒学人权思想,一切人权思想都应该摒弃儒学。
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得先接受这两个论点的前提:(1)儒学只通过人的角色和人际关系来了解人;(2)人权的基础是认为人只是孤立的个体。有些学者的确表达过这么极端的观点*Henry Rosemont Jr., “Why Take Rights Seriously? A Confucian Critiqu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ed.Leroy S.Rouner,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167-182.较早提出此类反对儒学人权的观点,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但都遭到了批判。例如,陈祖为(Joseph Chan)认为:
儒家认为,一切责任和权利的唯一来源是社会角色——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儒家关于仁的伦理学最根本的基础是共同的人性,而不是不同的社会角色——人性有着超越角色之上的伦理意蕴……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仁”是在诸如父子、夫妇等人际关系中实现的,但在非人际关系的场合,道德行为也受到“仁”的制约。*Joseph Chan, Confu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7-118.
批判关系是人权的障碍的另一个进路是否定这一论点的第二个前提。例如,纳多(Randall Nadeau)指出,儒家可以认为团体中的个体能获得人权,强调道德的自我实现只能发生在关系当中,因此团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必须借由人权得到保护才能发展成一个有道德的人。*Randall Nadeau, Confucianism and the Problem of Human Right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1:2,2002,pp.107-111.
即使我们同意陈祖为或纳多的观点——关系论的激进版本并没有把人权排除出去,这里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蒂瓦尔德(Justin Tiwald)提出人权有着清晰的行为准则,光是这一点就会削弱儒家认为的在成人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各种人际关系。他设想了一种情形:一个富有的姐姐在考虑要不要为她贫病交加的弟弟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他指出,如果姐姐或弟弟从可获得的权利的角度来考虑,就有可能鼓励他们去考虑与他人相冲突的自身利益,这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从根本上扭曲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和动机”。*Justin Tiwald,“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Human Rights,eds.Thomas Cushman,New York:Routledge,2011.也许蒂瓦尔德考虑的是这个弟弟会就他的状况提出控诉以获得充足的医疗资源,姐姐则认为这是在减少她的资源;或许蒂瓦尔德设想的是儒家权利制度,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制度明确规定家庭成员有责任相互关照。*事实上蒂瓦尔德指出弟弟能挪用姐姐的工资,因此他考虑的可能是后一种情况。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既然家庭关系及其他亲密关系在儒家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扭曲这些关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儒家必须从根本上反对人权?
我认为对这一挑战的合理回应是谨记中国传统上不存在明确的人权规范。人权和儒学这样的传统该如何融合是一个新问题,因此应该由随着新思想的涌现和社会变迁不断发展的现代儒学来解答;本文第四部分将会讨论这样的进路。这一部分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传统没有运用人权思想;第二,支持人权的现代儒家面临种种挑战。
三、儒学传统是人权的替代方案
认为中国传统阻碍了人权发展的思想家也有不同的主张,有些认为中国人应该摒弃传统,另一些则认为儒家不需要人权,因为儒学已经用另外的方式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规范性秩序。的确,这些思想家认为,这一替代方案避免了以权利为基础的秩序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这一理论在英语哲学界的起点是1988年发表的两篇论文:罗思文的《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权利?——儒家的批判》*Henry Rosemont Jr., “Why Take Rights Seriously? A Confucian Critiqu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ed.Leroy S.Rouner,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167-182.和安乐哲的《礼作为权利:一种儒家式的替代》*Roger T.Ames,“Rites as Rights:The Confucian Alternativ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 eds.Leroy S.Rouner,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199-216.。
罗思文和安乐哲论述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协调并规定这些角色的“礼”。正如罗思文所说,“在抽象意义上,对于早期儒家而言,不存在一个孤立的‘我’:我是在自身与具体的他人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总和”。他又说:
我们与他人——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人——的关系都受到“礼”的调节,礼就是随着历史延绵不断地展开,我们共有传承的礼貌、风俗和传统;履行这些关系所定义的责任,我们就……遵循了人“道”。*Henry Rosemont Jr., “Why Take Rights Seriously? A Confucian Critiqu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ed.Rouner,Leroy 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167-182.
安乐哲更明确地指出不能把礼看作是硬生生地加在被动接受的主体上的;相反,执行礼就是“置身于礼所包含的关系类型中,继而对社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礼不是指被动地顺从外部规范。正是社会的形成过程要求人们投入自我并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Roger T.Ames,“Rites as Rights:The Confucian Alternativ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 eds.Rouner,Leroy 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200.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思文和安乐哲之间微妙的差别,他们的立场与上文提到的陈祖为的立场都不同。问题在于:在何种程度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我”能拥有全人类都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又不限于我们的特定角色?罗思文的立场是我们只是我们的角色,而陈则认为除了角色之外,我们还有责任(很可能还有权利):“儒家伦理的‘仁’最终是基于共同的人性而不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安乐哲的立场则介于罗思文和陈祖为之间,主张个人投身于礼和角色,既然这样做要求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角色的“自我”概念,安乐哲确信这个“自我”恰恰是通过在社会中执行自己的角色而得以充分实现的。*近期对于这些问题的微妙处理,参看 Robert Cummings Neville,“Individuation and Ritual”, In The Good Is One,Its Manifestations Many:Confucian Essays on Metaphysics,Morals,Rituals,Institutions,and Gende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6,pp.143-157。
这里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如何理解罗思文和安乐哲所说的儒学式“替代”;二是判断这一个替代仅凭其自身是否足够,还是必须用人权加以补充。毫无疑问,儒学传统内部的主流思潮是以罗思文和安乐哲所说的方式强调角色和礼。《论语》中有一句名言表达了这一观点:“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用强制的命令指导人民,当人民不服从命令的时候用刑法惩罚他们,不会使人民内化出一种羞耻感,因此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人民会毫无羞耻感地违背政令。按照《论语》所说,与这种做法相反的是,用道德和礼制引导人民,其结果是人们变得有道德、能自我规范。儒家还认为一个礼制秩序也会影响统治者,因为他们参与了礼制,内化出了道德(因而变得更有道德),也因为统治者与臣民一起参与一种公共礼制文化使得臣民有能力要求统治者遵守礼制。有学者论证,礼制化事实上的确赋予了个人权利并限制了帝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Ron Guey Chu,“Rites and Rights in Ming China”, In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eds.De Bary,Wm.Theodore,and Tu,Wei-m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69-178.
显然,关于儒家政治伦理的理论和实践能讨论的还有很多,这里最紧要的问题在于儒家这样的执政办法在今天是否足以治民,而不需要诉诸人权。罗思文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儒学“丰富且多样”的语言使它能“充分地表达我的道德观点,而不需要人权话语”;尤其是,儒学提供了“一套丰富的专业术语来抨击”道德败坏和政治上的违法行为,包括政府在内。*Henry Rosemont Jr., “Why Take Rights Seriously? A Confucian Critiqu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ed.Rouner,Leroy 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64.尽管如此,由于人性的不可靠,强制性法律依然是必要的,即便是在《论语》中也有这样的暗示,在别的文献中则有更清晰的表达。的确,有些儒家比儒学主流思想更强调公共的外部的标准和制度的必要性。*狄百瑞指出,后期新儒家例如吕留良和黄宗羲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参见Wm.Theodore De Bary,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我和蒂瓦尔德也细致地考察过某些相关的思想。参见Stephen C.Angle and Justin Tiwald,Neo-Confucianism: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Oxford:Polity Press,2017。我们得承认,这些法律和其他标准并不是根据“人权”在历史进程中概念化的;如果人权思想是必要的,传统内部存在这股思潮就明显暗示着有进一步发展人权思想的空间。而安乐哲则非常不愿意强调人权。他写道:
依靠施行法律并运用人权作为法律的辅助,远远算不上是一种实现人的尊严的途径,而且在根本上是违反、削弱人性的,因为它是通过弱化我们具体的责任,进而提供相互和解的可能性而来定义什么是妥当的行为的。*Roger T.Ames,“Rites as Rights:The Confucian Alternative”,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 eds.Rouner,Leroy 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213.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蒂瓦尔德的观点的雏形。然而,安乐哲没有在范畴上排斥人权的运用。寥寥数语之后,他就力捧儒学模式,因为“它提供了合理的替代方案,缓和了个人为寻求法律途径所做的准备”。正如上文所说,现代儒家会赞同,我们诉诸法律的诉求应该要得到缓和,但是我不赞同安乐哲的激进观点——任何对人权的诉求都是“在根本上反人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个人和小群体面临巨大的威胁时,他们需要人权的明确有力的保护。礼制最终不能抵抗暴君,但法律体系可以。儒学可以尊重,甚至欣赏法律的重要性,有不少现代儒家已经指出必须这样做。*Randall Peerenboom, “Confucian Harmony and Freedom of Thought:The Right to Think Versus Right Thinking”, In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eds.Wm.Theodore De Bary and Tu Wei-m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5-260.非常强调礼制和权利的必要性。现代有影响力的儒学家就法律和权利的必要性做了重要论述,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关于牟宗三的某些思想的发展历程,可参见Stephen C.Angle,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
四、儒学是人权思想的源泉
在本文开头部分我已经对某些学者的观点做出过一定的批判:他们对人权的讨论是不精确的,认为人权思想在包含人性价值的任何传统中都能产生。我已经论证过儒学传统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人权思想。然而,只要现代儒家或者更宽泛的现代中国理论家用正确的方式发展某些学者的思想——认为儒学传统内部有些价值可作为人权的源泉或基础,现在是时候相信他们的主张了。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三个独特的儒学价值有可能作为人权基础:尊严、合法利益和德性。*第四个价值“人身自由”有时也会提到,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基于后来奠定人权框架所需的激进的人身自由概念论证人权和儒学的关联性。陈祖为讨论了在现代儒学中补充较为温和的“个人人身自由”概念的可能性,参见Joseph Chan,Confu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但是,这不能算作他为儒学人权思想所做的辩论,下文将会提到这一点。我们考察其中每个价值的时候,重要的是要牢记这个价值是否只是让儒学变得和人权融洽了——也就是说,如果单个价值对人权有着单独的奉献,它就可以没有自相矛盾地支持人权和儒学——或者证明(现代)儒学事实上需要人权。
现代西方很多对人权的辩护是在“人的尊严”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华霭仁(Irene Bloom)提出如下问题:能否在早期儒学中找到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并找到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结果,她说儒学的根本直觉与《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现代文本是“一致的,而且前者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支持”后者。*Irene Bloom, “Fundamental Intuitions and Consensus Statements:Mencian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In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eds.Ne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11.华霭仁非常关注《孟子》,多次引用《孟子》来论证人类社会赋予我们一种特殊的有别于阶层和世俗荣耀的高贵和荣誉感。她解释道:“孟子式的尊严是基于道德潜力的,更具体地说,是基于个体心灵内部对道德潜力在心理上的意识。”*Ibid.,p.107.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形式的荣誉不是只有充分发挥我们的道德潜力后才能拥有的东西;正如华霭仁对文本的解读,我们的道德潜力本身就是每个人的“天爵”的源泉。她还说,一个人是有可能通过自我贬低及不道德的行为失去其尊严的,但是像旅行者和乞丐之类的故事说明,在一个人不情愿的情况下,是不能夺去他的尊严的。总之,孟子式的尊严概念与康德的尊严概念有着极为关键的相似之处,后者常与人权联系起来。
华霭仁明确认为,为了关注孟子的尊严概念搁置了很多东西,而且在孟子的时代,尊严概念并没有引发人权思想(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本文开头部分讨论的人权障碍)。尽管华霭仁的目标在于证明如果有人想为《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现代“共识文本”中的人权找一个儒学基础,不妨从人的尊严着手,这是个很好的开端。*在分析独特的传统资源以达成人权共识方面,泰勒做了有影响力的讨论,参见Charles Taylor,“Conditions on an Unforced Consensus on Human Rights”, In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eds.Joanne R.Bauer and Daniel A.Bell,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4-144。即便是这么局限的结论也受到倪培民的挑战,在他最近一篇论文中,他主张一种非同寻常的儒家对于尊严的理解——是通过修养获得的。在倪培民看来,他关于替代性的儒学尊严概念的论述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促进了强烈的个人责任意识,而且避免了现代西方的“尊严”(human dignity,或德语Menschenwürde)概念引发的一些问题。*Paimin Ni,“Seek and You Will Find It; Let Go and You Will Lose It:Exploring a Confucian Approach to Human Dignity”, 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3:2,2014,pp.186-187.由于成功地修饬自己的人也可能缺乏这种尊严(或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尊严),倪培民对儒家尊严的理解似乎不能成为脱离世界人权的观点。这里不便对儒家“尊严”的两种不同观点的任何一种展开详细谈论,但我敢说依照我的判断,倪培民的论点并没有排除华霭仁在文献中找到的尊严概念。同时我坚信,真正地在华霭仁所说的尊严的基础上建立人权思想方面,我们能做的有很多,而且我接下来要考察的另外两个进路是更有希望的。让我们暂且搁置尊严之辩。
接下来要考察的人权的传统源泉是对个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众所周知,儒学反对追求利益,并把自私自利看作是恶行的根源。《孟子》开篇就讲述了孟子批评了一个为国家谋求利益的统治者。孟子说:“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关于“私”的问题,早在传统儒学中就可以看到对此的关注,事实上所有的宋明理学家都明确地把它作为核心论题加以讨论。尽管儒家对利益和自私自利表示担忧,却也一直承认我们有合法的利益,并且实现合法利益是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我的《人权与中国思想》(HumanRightsandChineseThought)一书的核心论题之一是论证儒家传统中的这股思潮在宋明理学后期中更为凸显,最终有助于解释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对权利(rights)和人权(human rights)的兴趣。*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牢记这一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何现代儒家把对利益的保护看作是对人权的辩护。
为发展这一思想路线做出最大贡献的当代思想家要数陈祖为(Joseph Chan)。从1999年他发表一篇重要的论文开始,就致力于发展这一思想路径,尤其是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论证了现代儒学对人权的支持。他的出发点是下列关键前提:
1.《世界人权宣言》所表达的人权不是以“人身自由”概念为基础的,也不是以其他与儒学相冲突的概念为基础的。
2.“在儒学伦理中,个人的善和公共的善之间不存在冲突(换言之,只有依据安全、物品、社会关系和公平对待来确认和保护人民的利益,才能取得社会秩序与和谐)。”*Joseph Chan, Confu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20.
3.“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合乎道德的关系破裂了,调解也不能解决冲突,人权可以作为备用工具保护人的基本利益。”*Ibid.,p.129.
陈祖为近期关于人权的讨论中,“理想”与“不理想”之间的差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我更欣赏他早期的分析,这种分析清晰地阐明了道德和权利何以同时运行;毕竟,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总是在某些方面是“不理想”的,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做个有道德的人:
在儒家看来,为了保持互爱互信的精神,我们首先应该努力通过教育、调解和妥协的手段来解决冲突,但是这不应该误导我们相信人权工具是不重要的。人权和道德在重建的儒家伦理学中都非常重要,而且两者彼此需要。道德并非总是能起作用,因此在保护人的利益方面弥足珍贵。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道德来指导拥有权利的人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的行为。*Joseph Chan,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eds.Joanne R.Bauer and Daniel A.Bel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2-240.
上述两种表述中,道德和协调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人权只是当事情变得极为糟糕时的“后备方案”。
有两个问题关涉陈祖为在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人权讨论。一是他的回答是否足以应对本文第二部分结尾提到的蒂瓦尔德的挑战:即使存在明确的人权规范也会损害核心人际关系。陈指出“我们首先应该努力通过教育解决冲突”,但是要怎样做才能实施这一“应该”呢,尤其是当实际情况“不理想”时?这个问题不足以推翻陈祖为的概念,但确实给他带来压力,令他难以解释他对人权的理解如何避免给儒学带来强烈的冲击(即对儒学中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造成过多损害)。*在《儒家至善论》中,陈祖为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明确回应了蒂瓦尔德的挑战。参见Joseph Chan, Confu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2014,pp.126-129。另一个问题意味着他的人权观实际上太过温和:什么可以保证儒家必须接纳人权呢?毕竟,儒学已经有各种机制来保护人民的利益;何以证明儒家必须把人权放入他们的“工具箱”呢?陈祖为论述的核心在于人权和儒学在“不理想”的情况下的兼容性;他明确指出“在儒家理想的社会中,人们不需要人权,人权不是人的尊严或构成人的德性所必需的”。*Joseph Chan, Confu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29.因此,既然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想对人权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那么儒家能接受人权,但是他没有证明儒家必须接受人权。如果我们想得到至少为人权提供更为坚实的儒学基础的论证,那么我们需要转向第三条进路——基于道德。
儒学重视道德修养,这样的看法相对说来不会有争议。的确,根据某些解读,儒学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宇宙中每个人的德性。*当下出现儒学伦理是否是一种形式的“道德伦理”的辩论,但即使是批判这一表述过于个人化的人也会赞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培养“德性”是儒学的核心(Roger T.Ames,Confucian Role Ethics:A Vocabular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1)。显然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概括儒学目标的特征,例如,实现“天理”、“平天下”等,但正如《大学》等文献的分析,唯一达成这些目标的途径是道德修养,除了通过实践我们的道德之外,我们无法仅凭自己真正地完成这些目标。对此的某些讨论,参见Stephen C.Angle, Sagehoo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把这一目标与人权联系起来的学者是西姆(May Sim),她在一系列论文中指出,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是“创造培养诸多儒学道德的条件所必需的”,因此儒家能而且必须承认人权。*参见May Sim, “Rival Confucian Rights:Left or Right Confucianism?”,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1:1,2011,pp.1-18;May Sim,“A Confucian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21:4,2014,pp.337-356; May Sim,Confuc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67,2013,pp.3-27.Marina Svensson, Deba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A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anham,MD:Roman & Littlefield,2002。范瑞平为人权道德路线所作的辩护,参见Fan Ruiping,Reconstructionist Confucianism:Rethinking Morality After the West.Dordrecht:Springer,2010;我简单讨论过他的思想,参见Stephen C.Angle,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pp.82-84。西姆对这一结论的具体论证显得过于仓促,因而说服力不是那么强,但她显然触及了一种论证儒家必须接纳人权的思路(如果成功的话)。事实上,类似的观点可见于20世纪有影响力的现代儒家,例如,徐复观和牟宗三。1957年,徐复观指出,我们需要人权来保护公民免受压迫(包括政府的压迫),而且缺乏人权已成为儒学何以在历史上无法达成广义道德发展的目标的重要原因。*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牟宗三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政道与治道》中作过类似的论述。
我们之前问过陈祖为和与他想法类似的主张合法利益路线的学者,我们也可以向主张儒家人权道德路线的学者问两个同样的问题:该如何回答蒂瓦尔德提出的问题?人权是否真的必要?让我们先分析第二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能否表达某人自己,在不受折磨的境况下生活,或者有一份有益于提升道德的工作;问题在于拥有确切的表达、免受折磨和获得雇佣的权利对于培养道德是必要的。毕竟,在没有这些权利的社会中有很多人仍然能表达他们自己、避免折磨,也能工作。为什么儒家说他们还不能培养道德呢?西姆引用梅尔登(A.I.Melden)的人权概念做了回答,在别处我也借用了牟宗三的某些观点来表达我的观点,我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人能否具备儒学道德取决于所有人具备儒学道德的可能性,而只能通过人权框架才能确保这一可能性。*May Sim,“A Confucian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21:4,2004,pp.337-56; Stephen C.Angle,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这一路径的论证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此处无需赘述;现在我们只要做出令人满意的论证,就有充足的理由说中国传统的这一维度能够为人权的必要性奠定基础。
最后,让我们分析蒂瓦尔德的问题:只要有明确的可声明的人权存在就会削弱西姆和我主张的儒学路径吗?此处,我为自己辩护,我的回答是“否”,但重要的是这个答案不能仅靠追溯传统得到证实。我想现代儒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人权环境下以最佳的方式实现道德?我们可以得到两种答案。第一,需要在社会内部理解维护人权的法律制度,我称之为“第二诉求体制”。法律和司法程序的构建必须鼓励道德乃至德性发展,但要避免陷入规避法律诉求的“最终诉求”陷阱。*Stephen C.Angle,Sagehoo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第二,儒家需要学会在深层次上尊重法律,认识到它对生活在易遭受私欲和权力侵袭的社区里容易犯错的人们的成长和福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尊重权利和法律并不意味着把它们看作是唯一掌控我们的东西:现代儒家的关键责任是教会我们欣赏道德、法律和礼制在生活中所起的迥异但互补的作用。*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参见Stephen C.Angle,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尤其是最后一章。
在本文的结尾要谈的是从中国传统的角度如何看待特定的人权内容。换言之,承认传统中有人权(不管得到何种程度上的证实),儒学有可能指引我们期待某些特定的权利受到别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关注吗?这一问题的常见解答方式是思考儒学强调价值的方式可能引向具体的人权,例如李晨阳说儒家应接受人有受教育的权利,陈祖为讨论了老年人的权利。*Li Chenyang,Education as a Human Right:A Confucian Perspective.Philosophy East & West 67:1,pp.37-46; Joseph Chan,“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eds.Bauer,Joanne R.,and Bell,Daniel 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5-236.出于几个原因,陈也主张儒家应该偏爱较简短的人权清单,该清单由下列权利组成:(1)(避免受到公权力侵害)的权利,剥夺这样的权利会严重阻碍社会秩序并损害个人利益;(2)最容易由法律实施、保护的权利。*Joseph Chan, Confucian Perfectionism: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27.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关注公民和政治权利,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权利致力于实现人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有些人因为儒学传统长期强调人们的经济福祉,提出儒家(或者生活在具有儒学传承的社会中的人)应该相较于公民—政治权利,更偏好社会—经济权利。*Daniel A.Bell,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最后,我在别处已经说过,现代儒家思考人权内容的正确方式不是直接由先前就有的儒学价值推导出人权,继而使其普及,而是在一个包容性的过程中参与具有普遍性、世界性视角的谈判。这一进路尊重不同的群体加入这个过程带来的多样化视角,并且在最佳程度上实现所有参与者授权的一系列可制度化的全球性原则。*参见Stephen C.Angle,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pp.87-90。我在书中进一步论述,自1948年起全球表达人权规范的实际过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儒家应该会支持的这种过程。
五、结语
本文是围绕中国传统和人权之辩的三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传统是人权的障碍、代替抑或是源泉——展开的。每种形式的障碍——等级礼制、缺乏概念、统一价值领域和关系论——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无法跨越,实际上我已经论证过儒家应该支持儒学传统朝着向人权话语开放的方向发展。中国传统也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可代替人权的方案,但是我赞同一些学者所说的,儒学式“替代”和人权规范联合起来是现代世界所必需的。通过不同途径寻找中国传统中的人权资源——尊严、利益和道德——都显示出某种希望,尽管这些途径单个来看都不能证明儒学在新时代已经做好了吸收人权思想的准备。这些资源是现代儒家支持人权之辩良好的着手点(我大概已经指出,人权在范围和具体内容上和其他的权利不同),但再次说明传统要接纳人权的话,就需要发展和调整。总之,本文关于中国传统和人权的关系的讨论还留下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儒学——乃至中国传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将会如何发展?传统不会只是给我们人权方面的启示继而归于沉寂;传统是充满活力和争议的,而且并未远离我们。现代中国人权话语呈现出独特的形态,部分原因在于传统遗产,一系列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因素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中国人权之辩下一个篇章的谱写中,我希望现代儒学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