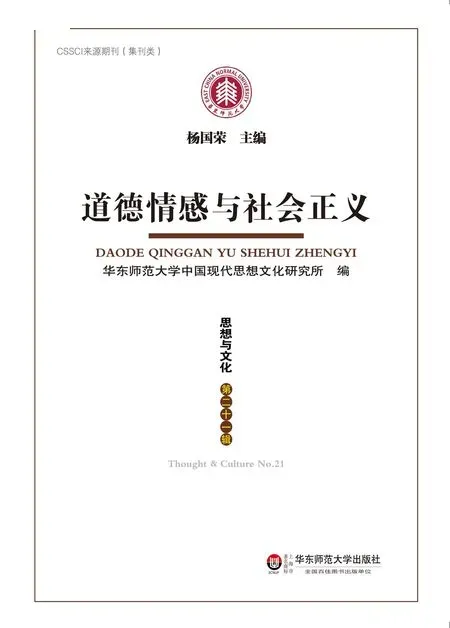历史书写中的语言张力
——《左传》历史美学解读(三)*
2017-05-29
引言
语言为历史书写之骨干。我国第一部史学著作《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是为中国传统史学历史书写之楷模。《左传》且富含“历史美学”——借用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诸要素。本文拟以《左传》关于晋国前期历史(至晋文公以前)之书写为样本,剖析并鉴赏其叙事语言之特色,以及以语言为骨干联动之“动作”、“情致”及其“情节”的展开,归根结底赏析《左传》如何叙事,怎样写“人”,体味其中的历史美学意味,以为当今史学之镜鉴。
黑格尔《美学》曾经说过:“语文毕竟是最易理解的最适合于精神的手段,能掌握住而且表达出高深领域的一切认识活动和内心世界中的一切东西。”*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页。“语文这种弹性最大的材料(媒介)也是直接属于精神的,是最有能力掌握精神的旨趣和活动,并且显现出它们在内心中那种生动鲜明模样的。”*同上书,第19页。
史著亦“精神产品”,“语言”也同样是显示史家“精神旨趣”、“内心中那种生动鲜明模样”的“最适合手段”。《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记言”和“记事”同等重要。700年后刘知幾撰《史通》,他在独家所创,同时也是《史通》纲领性篇章的《六家》、《二体》之后,紧接着的是《载言》,起手便云: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乣(通“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
按,齐桓公、晋文公“乣合同盟”称霸是谓“事”,然必待“言”其“事”乃可成,《尚书》却“阙纪”,此处未“言”即缺“事”;秦穆公之“言”,亦必有其败绩之“事”为起因而不能发其“诫誓”,《春秋》却“靡录”,此处未“言”即缺“言”。一失史家之“言”,一失历史人物之“言”。“言”即“事”,“事”亦“言”。直到《左传》,其“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的“历史书写”方法,才弥补了《尚书》、《春秋》的不足。与此同时,刘知幾特别强调了《左传》的语言魅力:“言事相兼,烦省合理,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申左》则云:“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任何“表达”都是从痛感和快感中分泌出来的。史家也一样。清代史家兼诗家赵翼(瓯北)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实,在遭遇沧桑之变的历史大关口,史家的感悟要比诗家来得更加锐利而深刻。史家既生活在现实之中,同时也在“历史”之中生活。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史家当有一种悲欣交集的观感。他写作,他撰史,是他生命燃烧的一种形式,根本上只听命于他心灵的呼唤。是故赵瓯北之诗可改题为“国家不幸史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我们读《左传》,《左传》叙事像一部轰鸣的交响曲,大气朗然,将善恶美丑放在一个调色盘内,融入笔下的史著之中。她不仅对《史记》以下的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先导性、典范性的影响,而且在理解语言本身也能够撬动“历史”使之跌宕起伏(此为借助美学审视“历史”)方面,在鉴赏性阅读过程中能够带给读者强烈的美感体验(此为用美学眼光看“历史学”)方面,《左传》都给人极深刻的启迪。
黑氏论诗人用“语言”展现灵魂:“诗人因此能深入到精神内容意蕴的深处,把隐藏在那里的东西搜寻出来,带到意识的光辉里。……语文毕竟是最易理解的最适合于精神的手段,能掌握住而且表达出高深领域的一切意识活动和内心世界中的一切东西。”*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52页。黑格尔又特别强调有“两种散文”——“历史写作的艺术和说话修辞的艺术”,它们“在各自的界限之内最能接近艺术”。*同上书,第38页。而在黑格尔的美学观念中,“诗”即艺术。若将黑氏之“诗人”替换成史家,史家实与诗人一样,他们同样运用“语言”,“深入到精神内容意蕴的深处,把隐藏在那里的东西搜寻出来,带到意识的光辉里”。因此可以认定:语言是构成“历史叙事”的骨干,能够衬映出史家学养的深浅,并且直接制约着史著的文野高下。《左传》关于晋国前期历史(至晋文公以前)之书写,正是可以用作样本的剖析对象。
一、成师灭仇与晋武公之崛起
我们看春秋时的晋国早期历史,就是一部骨肉相残、兄弟阋墙史。黑格尔说过:“弟兄间的仇恨在各时代都是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的冲突”,“从《旧约》里该隐杀他的兄弟伯亚就已开始了”,黑氏将其归类为一种“自然(即人无可选择的“家庭出身”——笔者)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64页。它曾经作为戏剧的主题久演不衰。实际上,同根相煎不仅大量存在于艺术史上的经典剧作中,它在历史中也比比皆是。因其中折射出人性的洁净与龌龊,光明和阴暗,故成为中国传统史家高度关注的对象。《左传》描述的晋国早期史就是一个典型。
晋为周武王子唐叔之后。周成王灭唐,分封庶兄唐叔于此。唐叔之子改唐为晋(今之太原市)。晋首次出现于春秋的历史记载见《左传·隐公五年》。有关晋的载记至此方才出现,这却并不是说晋国此前无“史”,而是因为晋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晋不及来告鲁,因此鲁《不修春秋》不载晋事,孔子据《不修春秋》所撰《春秋经》自然不书。《经》不书《左传》却书之凿凿,足见《左传》必有除《春秋经》外的其他史料来源,这是理解《经》不书《传》何以书这一经学重要现象的关键。一直到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前,晋经历了惨烈的火并内乱。从长兄仇一支与亲兄弟成师一支内斗开始,至成师后裔晋武公彻底征服仇一支,完成了晋内部的统一,内乱方告一段落。仅这一段,时间就达长达六十七年之久(据《史记·晋世家》)。
1.成师灭仇。《左传·桓公二年》:
初,晋穆侯(晋穆侯伐条戎在周宣王二十三年)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取名必合于义),义以出礼(义出从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衰微)乎!”
按,《竹书纪年》有“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王师败逃”的记载。周宣王败逃,则晋穆侯亦必随之败逃。出师不利,故穆侯名其子曰“仇”。又据《史记·晋世家》: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晋人师服曰:“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今適庶(“適”同“嫡”,长子;弟为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
师服一语成谶,晋内乱开始。《左传·桓公二年》:
惠(惠,鲁惠公)之二十四年(周平王二十六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天子分封诸侯为“国”,是谓“建国”),诸侯立家(诸侯分封采邑予卿大夫,是谓“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史记·晋世家》: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谨按,桓叔即成师,与长兄仇不和,周天子不会不知,却封桓叔于曲沃。晋国都在翼,曲沃地盘却大于翼,且为晋宗祠所在。师服所谓“天子建国”,所谓“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左氏均借晋事而暗讽天子。缘此,文中“故”字有深意,所用精当:一谓天子直接插手了晋内乱;二指天子“故意”于晋国边再立一“国”,此“国”又非国家之国,而系“耦国”之国——足以与国都翼抗衡之大城曲沃。(《左传·隐公元年》:“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面对侯国内部矛盾,周王火上浇油,且存心扶植非长子、非“正统”之成师,大失君德,上梁不正。左氏借师服之口,批判矛头实指天子。
桓叔被封于曲沃,为成师一支崛起之始。其人“好德”得民心,“晋国之众皆附”,又有根据地与晋侯相颉颃,故虽有对立面之屡屡反抗,最终无功而返,成师一支彻底剪灭了仇一支。《左传·桓公二年》:
惠(鲁惠公)之三十年,晋潘父弒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史记·晋世家》: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曲沃桓叔子),弒孝侯。……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之弟缗为晋侯。……晋侯二十八年(鲁庄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按,周王待晋政出二门,前后矛盾:先封桓叔于曲沃,挑起晋内乱;后见武公伐翼,藐视最高统帅,失却颜面,心有不甘,故扮出一副“老大”嘴脸,授命虢公为首伐武公。*按《左传·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次年“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虢后成晋世仇,“唇亡齿寒”,晋借虞道伐虢并灭之,皆结仇于此。晋武公灭缗,尽以其宝器贿赂周王,周王贪利受贿,并不得不承认现实,遂命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
2.晋武公立“军”。《左传·庄公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
按《周礼·夏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晋武公(曲沃武公)本有一军,但此非晋军而为“曲沃军”;现周王承认武公可制一军,“曲沃军”升格成为“国军”,晋军至此合法化。
《史记·晋世家》:
武公代晋二岁,卒。……子献公诡诸立。
晋献公继位,晋国开始新内讧。
二、晋献公时的内讧
就成师一支而言,从晋献公继位后内部火并就未曾消停过。献公残忍、固执、专断,在位凡二十六年(鲁庄公十八年—鲁僖公九年)。二十六年间,他先灭“外亲”,即与献公有叔伯亲属关系之群公子;再诛“内亲”,杀害太子申生,甚于虎毒。
1.诛灭桓(桓叔)、庄(庄伯)之族。据《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晋桓(桓叔)、庄(庄伯)之族偪”,压迫公室,献公患之,谋于士蔿,先剪除了桓、庄族群公子的谋士富子。次年,复挑唆群公子杀桓、庄同党“游氏之二子”之后,《左传·庄公二十五年》:
晋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聚,邑名)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按,士蔿“城聚”时已经预谋将群公子“聚”而歼之。“围聚”二字,正可作“城聚”之注脚。“处”,一字二训:“处于”之处,意在“聚”上;“处置”之处,诛灭也。《史通·叙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左氏笔力简洁雄健,足以当之。
2.强娶骊姬。献公尤其好色,类似康德所诅咒的“老年散荡之徒”*康德:《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载曹俊峰译:《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他不听史苏之劝讨伐骊戎,娶骊姬,将祸水引入国门,影响最恶劣。《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齐姜,晋武公妾,太子申生母。《史记》谓齐姜为齐桓公女。章太炎另有解:晋武公灭翼统一晋国后“必兼得其内”,认为“齐姜非哀侯之妾,则小子侯之妾耳。武公志大,情不系色;献公志本淫昏,取之宜也”。见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载《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页。,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按,此条史料提示晋侯原育有三子一女,而太子申生与秦穆夫人为亲兄妹。然同年《传》又载:
晋伐骊戎,骊戎男(人名)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骊姬男宠)。
关于骊姬,《公羊传·僖公十年》:“骊姬者,国色也。”何休《公羊解诂》解“国色”:“其颜色,一国之选也。”在娶骊姬前献公曾卜且筮之。《左传·僖公四年》: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长,灵验),不如从长。”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按,“筮”,“筮草”;“龟”,灵龟,均用为卜占。然一为植物,一为动物,龟卜要于筮占,是谓“筮短龟长”。康德曾经嘲笑那些色鬼,说他们“只是在把异性看做可享乐的对象时才爱异性”*康德:《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载《康德美学文集》,第12页。,不啻是谓献公。对于这种只是“在根本上与性的吸引力有关”并足以“销魂”(康德语)者,献公根本不考虑其“过度的诱惑力”可能成为“造成不良倾向和不幸的源泉”*同上书,第41页。——献公早已色迷心窍,又孰愿从龟而弃筮哉?
骊姬被立为夫人,后宫局面立刻失衡,导致王室内部“所涉及的各种力量之间原有的和谐”被彻底“否定或消除掉”了,双方“转到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从此每一动作在具体情况下都要实现一种目的或性格,……由于各有独立的定性,就片面孤立化了,这就必然激发对方的对立情致,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6页。,并使“分裂和由分裂来的定性终于形成了情境的本质,因而使情境见出一种冲突(重点号为黑格尔所加),冲突又导致反应动作,这就形成真正动作的出发点和转化过程”*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55页。,这一“真正动作的出发点和转化过程”的“冲突”此刻即表现为后宫争宠和接踵而来的王子争立。
3.骊姬妒忌析。妒忌是人类最恶劣的秉性之一。叔本华说:“恶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妒忌;或者更确切地说,妒忌自身就是恶意。由看到别人的快乐、财富或优势所燃起。”“人是绝对有妒忌心的。希罗多德早就说过:‘妒忌是人类伊始就自然生长出来的。’”“看到别人痛苦便称心地、由衷地感到高兴,这是一个坏透的心肠和道德极为卑微的标志。应该永远躲开这种人。”*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任立、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4—225页。妒忌和幸灾乐祸,“前者是人所特有的,而后者则是恶魔性的”。*同上书,第225页。有学者认为妒忌起源于雄性动物对雌性的绝对占有欲和雌性动物对于其他同类同性的绝对排他性,此说当否勿论,但说妒忌主要反映人动物性的一面,事涉男女关系时尤其如此,则确然无疑。康德曾经幽默地认为“婚前”的嫉妒可由“作为恋人的快乐和希望之间的痛苦”,“是一种调料”,“但在婚后生活中却变成了毒药”。*康德:《实用人类学》,载《康德美学文集》,第193页。
骊姬因觊觎王储位而生妒忌,太子申生首当其冲,成为她必须铲灭的对象。正是通过处心积虑铲除申生的描述,《左传》成功塑造了骊姬的丰满形象,并借骊姬一身种种恶根之揭露,透出左丘明关注人性的“意蕴”或曰“史义”。女性特有的细心,则使骊姬之恶如虎添翼,恶上加恶。她深思熟虑,步步为营,先将非她所出之申生、重耳、夷吾及“群公子”统统排挤出国都,以便垄断她对晋侯的影响力。(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然后进一步实施深构太子去而除之的预谋。献公则对骊姬言听计从,害死了亲生子申生。
三、残害太子申生
1.申生“将”军与作。《左传·闵公元年》: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
按,献公并未通过周王,“自说自话”由一军而“作”二军。王室衰微,对其扩军只能听之任之。献公使申生将下军,为太子“城曲沃”,士蔿老谋深算,立刻探得了献公明升暗废的心思,知“太子不得立矣”!当初士蔿助献公为虐,杀富子、游氏,“聚歼”群公子,何等心狠手辣!现见申生将遭厄运,戚戚焉又油然而生同情。善与恶本冰炭不容,士蔿却一身集之,这正是人性丰富性、复杂性的表现。
《庄子·列御寇》载孔子论人心难知所言: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转引自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1页。
“人心”源于“人性”。人性的多面相好比一块块切片。左丘明深知世界之复杂莫过于人。对于人性,他并不报不切实际的奢望与幻想,也不作空泛的夸张与提升,只是用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划分出人性的切片,用史笔告知我们:诺,人就是这副模样!因此《左传》中的人才显得如此丰满与鲜活。

2.伐东山皋落氏。《左传·闵公二年》: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太子奉冢祀(冢,大)、社稷之粢盛(粢,祭祀品),以朝夕视君膳者也(太子亲问君王之膳),故曰冢子。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
献公命申生伐狄,主意出自骊姬。《国语·晋语一》:
骊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君盍使之伐狄,以观其果于众也,与众之信辑睦焉。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若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厚图(省略申生)也。……公说。是故使申生伐东山。”
而“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献公欲废太子至此已经呼之欲出。《左传·闵公二年》:
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叹曰:“……衣之尨服(黑白杂色,狂人亦不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罕夷曰:“尨奇无常,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狂夫不衣)。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可内谗,不如违之。”
“尨凉,冬杀,金寒,玦离”,一字一顿,一顿一义,“翩翩奕奕,良可咏也”(借用《史通》赞班固语)。而其叙事之巧妙,钱钟书有言:
狐突叹曰:“……虽欲勉之,狄可尽乎?”……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狄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谗,不如违之。”观先丹木之语即针对晋侯之命而发。先此献公面命申生一段情事,不加叙述,而以傍人语中一“曰”字达之,《史通·叙事》篇赞《左传》“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事外”,此可以当之。*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80页。
用语言对话本身来叙事(这种史学传统中西皆然,如《尚书》,如希罗多德,而以吾国出类而拔其萃),这是《左传》的高明之处,也是传统史学的突出特点。它方便了读者从对话中理解对话人的品质、性格,味出其中的人性,并因此促成读者本人理解历史事件时的“角色代入”,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如钱钟书所说:
用对话体来发表思想,比较容易打动读者的兴趣,因为对话中包含几个角色,带些戏剧的成分。……我们读的时候……兴味并不在辩论的胜负是非,倒在辩论中闪烁着各角色的性质品格,一种人的兴味代替了硬性的学术研究,像读戏剧一样。*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以此再来体悟献公之意,其实他最希望申生战死,如上文中的冬战(冬气肃杀,不宜战)、尨衣、金玦(玦当以玉质,玉性温润;金,铜质,性寒。以金为玦,涵绝离义),均为不祥之物兆;面喻申生“尽敌而反”,即敌未尽而勿反,同样暗伏杀机。
对于献公用心,申生并非不察。但是,人总要有精神依托,其主要内容便是坚守不移的“价值”。大君子当有翛然于生死之际的大境界,一旦价值破灭,用生命捍卫价值就是一种必然。此刻,肉身存在的生命形式就会成为“价值体现”的对象而表现为“崇高”,即坦然面对死亡。申生明知此一战凶多吉少,仍然准备拼死一战,狐突强谏之弗听,即“价值”使然。谓为不信,且看《国语·晋语一》:
狐突谏曰:“不可。突闻之……”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是故赐我奇服,而告我权。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谮在中矣,君故生心,……不若战也。不成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
3.申生遇害。献公、骊姬一对男女狼狈为奸,必去除申生,可谓念兹在兹!
《左传·僖公四年》: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宦官),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按,《左传》此段叙事虽仅寥寥百余字,却要言不烦,可谓字字珠玑,其间悬念迭起,暗潮涌动如“活剧”,以徐而不疾的史笔展示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叙事有背景、有情境、有对话,“历史美学”的意味丰厚。特因其“真实”,遂使发生于2500年前的“真人真事”较一般虚构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更强烈的勾魂摄魄的魅力。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最难把握的是找到“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54页。,它需要“抓住事件、个别人物以及行动的转变和结局所具有的人的旨趣和精神价值,把它表现出来”。*同上书,第37页。黑格尔强调的这些“艺术创作”要领同样也是历史叙事的枢轴而为《左传》所擅长。《左传》利用“情境和动作的演变”,通过太子申生特别是骊姬的形象塑造,使读者并不仅仅根据人的“名字和外表”,而是通过“动作”去认识申生和骊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同上书,第277页。,换言之,左氏的宗旨最终是落在认识“人”及其“类性”上的。例如申生的善良和懦弱,即类似于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在实行方面本身的软弱”;哈姆雷特的“延宕又延宕”,“内倾反省、多愁善感、爱沉思”,“因此不善于采取迅速行动”的秉性,也都能在太子申生身上找到相像的踪影。读者在扼腕痛惜申生秉质的同时,若能像黑格尔一样,体悟出申生也有与哈姆雷特一样“很美的心情”*同上书,第294页。,则不枉辜左氏一片苦心矣!更遑论申生与哈姆雷特有“真”、“假”之别哉?最妙处是左氏拿了申生“善”的秉质,处处与骊姬相比照,以凸显骊姬的“旨趣和精神价值”——她的残忍、贪婪、狭隘,尤其是她的妒忌。这种相互映衬与对比,使整个事件借助善恶的冲突,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性效果”。骊姬自是主角,申生只作为她的陪衬。这里,《左传》并不回避“丑”而选择骊姬为主角,即如艺术作品“在表现外在情况时可以走到单纯的丑”*同上书,第261页。一样,意在用申生之“美”烘托骊姬之“丑”,昭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阴暗面,使读者理解人性的复杂面相,却除阴霾,纯净秉性,回复如申生之“善”。*同上书,第232页。《左传》抓住最能反映“情境”所需要的“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之诸要素,用“具象”的史实使其“抽象”的“意蕴”隐隐“透”出:(1)骊姬先“与中大夫成谋”而立奚齐,然“成谋”尚处于“策划”阶段,即奚齐“將立”而未立。“及将立”、“既与”,非有此五字作底衬,便叙不得骊姬步步紧逼的后续“动作”。左氏叙事针细缕密,真如金圣叹赞《水浒》第十一回所云:“非非常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摛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施耐庵:《水浒传》(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7页。按,金圣叹本人即极赞赏《左传》之谋篇布局与叙史。此时,借用黑格尔的美学用语,“定性”已经形成,“本质上的差异面(与善相对立的恶),而且与另一面(申生)相对立”,“冲突”已在所难免。但“冲突”毕竟“还不是‘动作’,它只是包含着一种动作的开端和前提”——它还只是整个事件的“背景”。*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60页。(2)骊姬必须进一步采取构陷太子的“动作”,借晋侯之手除而杀之;复因“动作”“起源于心灵”,故最能显现骊姬作为“人”的“最深刻的方面”*同上书,第278页。。骊姬为此分四步行动:a.托梦,诓骗申生前往曲沃(晋宗祠所在地)祭母,申生心善中计;b.申生由曲沃带回祭品,入骊姬所设圈套;c.骊姬制毒,献公试毒。她先“寘胙(祭品)六日”,使之变质。犹恐毒性不够,再自行加毒而献之于献公。骊姬之歹毒遂因其心细更见其老辣。“毒而献之”后忽又插入“公祭之地”一事。申生所归之胙,献公何不即食之而试其毒?此处全然省去献公试毒之因,直教读者意会出此必系骊姬的主意。此种叙事法,再借用金圣叹评《水浒》语,“能令读者心前眼前,若有无数事情,无数说话”,“灵心妙笔,一至于此”!*施耐庵:《水浒传》(上册),第122页。试毒对象则由“贱”而“贵”,先“地”后“犬”复“小臣”:“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宦官),小臣亦毙”,一句一顿,一顿一事,紊而不乱。至于献公试毒之前,其腔子内究竟哪副心肝?其脑际又存何种思虑?此等处《左传》一概省略,遂于“留白”式的“用简”(刘知幾赞《左传》运笔语)中腾出让读者充分体悟的空间,并使叙事因此而极具张力。d.骊姬栽赃申生,申生被害。紧接着的“姬泣曰”三字,活脱脱一副娇嗔耍赖、反咬一口的泼妇相,献公平日宠之爱之、唯言是听、唯计是从的昏聩状亦深隐其中。以上四步骤首尾连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显现出作为史家的左氏撰史如撰“剧”,体大思精、严丝合缝、环环相扣的艺术性构想。在叙事中,左氏充分调动了视觉、听觉甚至触觉诸要素。历史学之叙事因带有了此类要素,它与“人”的关系就立刻密切起来,也因此充满了“人味”与“趣味”。读《左传》常能够有“人味”与“趣味”的享受,原因在此。在申生善良软弱的烘托下,骊姬阴险老辣、成谋深算的秉性格外鲜活。(3)骊姬陷害太子全过程始终有语言伴随。比起如金属、颜料、石块、音符等*黑格尔正确指出:金属、颜料、石块、音符等“材料”均可用于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创作,借用黑氏此论,上述“材料”亦能够“再现”历史。,语言作为“材料”(黑格尔《美学》语)最能体现历史主体——人的内在精神。要之,《左传》高超绝伦的情节构思和叙事运笔,归根结底需服务于发掘并表彰那些“可以显现伟大心灵力量的分裂与和解”*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60页。。这就为传统史学从叙事之方法论、撰史目的论上立下了圭臬。
黑格尔认为:“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而动作,由于起源于心灵,也只有在心灵性的表现即语言中才获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明确。”*同上书,第278页。“诗艺要找出一个情节或事件,一个民族的代表人物或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最本质的核心和意义,把周围同时发生作用的一些偶然因素和不关要旨的附带情节以及只是相对的情境和人物性格都一齐抛开,只用能突出地显现主题内在实体的那些人物和事迹,这样就会使得上述最本质的核心和意义通过对外在事物面貌的改造而获得适合的客观存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47—48页。
按,“诗艺”亦“史艺”。为了“突出地显现主题内在实体的那些人物和事迹”,左丘明剪除了叙事的枝枝蔓蔓而紧紧咬住骊姬不放。人性的光辉之巅与黑暗之渊同处一“人”。史家当有慧眼,在相反相成的人性空间中开掘,以此彰显出历史的震撼力。《左传》即处处用申生之善,烘托出骊姬“最本质的核心和意义”。骊姬则设套规局,心思缜密,她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并采取令人眼花缭乱的一连串“动作”,充分显现出其“人性”中“最深刻的方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78页。——她的手腕、心计;她的妒忌、贪婪、狭隘、刻毒;献公的昏庸与残忍则为“虎”作伥,与骊姬相辅相成,终于逼迫申生自缢。所以孔子郑重其事,将申生之死直接归罪于晋侯。《春秋经·僖公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四、骊姬恶报
申生死,但奚齐继位障碍犹存。骊姬故伎重演,再诬重耳(晋文公)、夷吾(晋惠公)为太子同党。《左传·僖公四年》:“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重耳最终奔狄,夷吾奔梁。骊姬机关算尽,终遂心所愿而得逞于一时。虽然,她却不解“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这一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机关算尽却终“害了卿卿性命”;她的膨胀情欲则殃及无辜的奚齐、卓子被杀,应验了平头百姓常说的“远在儿女近在身”的“恶报”。僖公九年九月,晋侯疾。他与骊姬狼狈为奸,害死太子,逼走重耳、夷吾,造孽深重,天怒人怨。献公深知自造的恶业最终将报应在奚齐身上,这成了他的心病。故献公先使重臣荀息为奚齐之傅,临死前再召荀息“托孤”,反复要求其立誓保奚齐。荀息固亦君子有风范,稽首而誓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然晋侯之恶天理难容,荀息以死殉之,虽确如《国语·晋语二》以“君子曰”赞其“不食其言”,但他为恶辩护,毕竟“愚忠”。故对于荀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承诺仍当以左氏的批评为是:“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追悔)也’。荀息有焉。”
《左传·僖公九年》:“晋献公卒。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次,丧次,居丧之草庐,不抹泥。后世谓之“筑庐”)。……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行文至此,笔者忍不住要引用几句曾经利用过的史料。清徐乾学曾说:“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钱大昕引之并指斥蔡京、明成祖之流作恶多端,而谓:“此辈惜未闻斯语!”*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429页。借用晓徵之詈,献公、骊姬辈亦“惜未闻斯语!”人生在世,不过匆匆百年,死后做“鬼”才是“永久”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这不仅为佛家言,更是历史的铁律。太子申生流芳百世,献公、骊姬遗臭万年,并殃及奚齐、卓子,令人唏嘘,应了平头百姓常常挂在嘴边“远在儿女近在身”的“现世报”。各人生前的“自业”于死后之“善”、“恶”报,真真凿凿毫厘不爽!终究逃不脱的是史家如椽之笔的历史评价之“报”。
晋献公子嗣至此已在“窝里斗”中大部凋零,有资格继承君位者仅剩重耳与夷吾。靠秦穆公的扶佐,夷吾首先登上了王位。
五、秦晋交恶及其大逆转
1.夷吾登基。晋献公子嗣已在“窝里斗”中大部凋零,有资格继承君位者仅剩重耳与夷吾。据《左传》,“里克、丕郑欲纳文公(重耳)”。里克、丕郑不看好夷吾,其中除去二人向与重耳“党同”故“伐异”的因素外,就人品优劣而言,重耳与夷吾也的确存在巨大差异。据《国语·晋语二》,奚齐、卓子被杀,里克及丕郑曾“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意欲召之回国继承王位。然此时重耳因受献公、骊姬迫害,早已久经了流亡异国漂泊他乡的锤炼,他的心智已足够成熟,深明政治上迎拒进退的取予之道。本质上重耳也不是一个对王位猴急垂涎的硁硁小人,故在狐偃劝说下,重耳终于婉拒了来使。夷吾的表现则与重耳判若云泥。据《国语·晋语二》,夷吾党羽吕甥及郄称“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召他回国即君位。夷吾告知其追随者冀芮,冀芮即竭力鼓动夷吾应诺,以为乱中取政此正其时,即所谓“非乱何入?非危何安?”为此冀芮替夷吾想出了一个挟秦以自重的馊主意。《国语·晋语二》:
尽国以赂外内,无爱虚(不惜空虚国库)以求入。
此即《左传·僖公九年》所说夷吾“重赂秦以求入(回国)”。夷吾此举背后实有其阴暗的心理私欲。夷吾骨子里认为:
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左传·僖公九年》)
按,夷吾此处之“人”实暗指在王位继承上竞争力超过他的公子重耳。《东周列国志》尝借冀芮语解《左传》谓:“公子不返国,则梁山一匹夫耳,能有晋尺寸之土乎?他人之物,公子何惜焉?”*冯梦龙、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38页。小说家之言亦堪为《左传》作笺释:只要击败重耳“入而能民”,即使卖国割地也在所不惜,故其以重赂许秦穆公及晋大夫。且夷吾谄媚秦使,竟说出了“终君(秦穆公)之重爱,受君之重贶,而群臣受其大德,晋国其谁非君之群隶臣也?”的混账话,恬不知耻,一至于此!
究竟立重耳还是立夷吾?秦穆公自然也有他的算计。重耳“仁”,夷吾“无德”,秦穆公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傀儡。穆公派往考察重耳与夷吾的公子絷一语正中其下怀。《国语·晋语二》:
君若求置晋君而载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晋君以成名于天下,则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进退。
是故穆公“先置公子夷吾,实为惠公”。此一“先”用字精当,已隐涵了日后秦穆公另立重耳为晋君之伏脉。左氏笔力雄健,于此亦可洞见。私欲满腹、大节亏损的俗夫小人夷吾,终于在秦穆公的扶持下登上了王位。因左氏先已对夷吾的宵小秉质作了足够周详的铺垫,是故惠公登位后即原形毕露,恶行不断,就显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读者并不感到意外。“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左传》深副刘知幾《史通》所赞“用晦”之要领而贯穿始终。
2.夷吾作恶
a.“烝”嫂。《左传·僖公十年》:
晋侯(惠公)改葬共太子(申生)。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狐突)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
“夷吾无礼”实暗指惠公烝申生妃贾君,此即《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说: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晋侯烝于贾君。
按,秦穆夫人以亡嫂相托当在夷吾入君之前,夷吾亦当允诺。但入君后他即刻“烝”之,趁人之危欺侮弱寡,禽兽不如!
b.斥“群公子”。《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杨伯峻注:“献公之子九人,除申生、奚齐、卓子已死,夷吾立为君外,尚有重耳等五人,即所谓群公子。”惠公欲排除所有可能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者,尤其是重耳,他当然“不纳”群公子。
c.以怨报德、背信弃义。此为惠公三大恶之尤者。
据《左传·僖公六年》:“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据《国语·晋语二》,夷吾“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为继承王位的条件。但一上台他立刻变卦赖账,“既而不与”。更有甚者,僖公十三年晋国遭遇饥荒,“秦于是乎输粟于晋”。然次年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忘恩负义,幸灾乐祸,这副隔岸观火的嘴脸,激怒了秦穆公,也引起了秦国国人的极大愤慨。次年穆公侵晋,惠公自食恶果,在韩原之战中沦为战俘。
3.韩原之战与穆姬救弟。《春秋经·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左传·僖公十五年》:“(晋军)三败及韩。……秦获晋侯以归。”
秦、晋兵戎相见,晋侯被俘。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原本准备杀惠公以祭天:“穆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斋宿,吾将以晋君祀上帝。”但在秦穆姬——穆公夫人,也是惠公之姊“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以自焚相要挟下,穆公最终打消了此念。《左传·僖公十五年》: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
“免服衰绖,登台履薪”,秦穆夫人肃穆铿锵、堂堂正正迎面而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亟当注意者又在左氏叙事的主观立场:对于穆姬舍命救弟的巾帼豪女英雄气概,左氏竭力凸显并予以了正面的肯定。换言之,作为一位史家,左氏自觉认识到了穆姬此举的正当性并予以了表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此段史实不仅因此显现出动人心魄的悲剧式的“崇高美”,且其中蕴含了《左传》对于“人性”和“战争”取舍评判的重要价值观念。(见后文)康德曾经说过:“女人……美丽,富有魅力,这就够了。”*康德:《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载《康德美学文集》,第46页。“女人身上不应该有火药味,正如男子不应该有麝香味一样。”*同上书,第36页。从这意义上说,女人原本应远离战争。然而,当女人也和男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战争时,她们往往能以柔软而亲和的人性魅力表现出一种不同于男子的坚强与智慧——穆姬即与之。她的刚(以死相逼)柔(婚姻、家庭、子女)相济,以柔(区区女身)克刚(男人、“戎”、战争),用女性特有的阴柔意蕴,用“亲情”式的柔韧去抗衡战争的残忍与非人性,这是与战争的刚烈、火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崇高”。康德说:“一个女人如果有一种女性的魅力,而且那种魅力显示出道德的崇高,这个女人就在‘美’的本来意义上称为美的。”*同上书,2003年,第42页。穆姬大义凛然,有不容予夺、不让须眉的丈夫气,读来令人动容。发生在2500年前的穆姬往事何以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盖因有一“人性”之魂魄贯穿其中故也。
穆姬舍身救弟,是晋国前期骨肉相残的历史暗夜中唯一耀眼的闪光点。现在要问:穆姬何以出此壮举?答曰:“血浓于水”之故也。
(1) “天伦”与“人伦”。中、西方均需面对“亲情”,但各家观念同中有异。黑格尔说:“形成悲剧动作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是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首先是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姊妹之间的亲属爱。”*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4页。黑氏的“亲属爱”中有父母、儿女、兄弟姊妹,这与中国相同。但将夫妻也包括于“亲属爱”中并置于首位,却与中国传统认知相径庭。中国有“亲亲相隐”、“爱有差等”观念,重的是血缘。首先是父母与儿女,然后是兄弟和姊妹,夫妻关系是被排除在外的。《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郭店楚简《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此礼为“亲属容隐”的道德法则。又郭店楚简《六德》:“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郭店楚简与《礼记》合。《礼记·丧服四制》:“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意谓在个人领域私恩压倒公义,于公共领域公义大于私恩。又,《云梦秦简·法律答问》: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杨海:《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转引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23日。
(2) “牉”字训。因为夫妻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以上“血浓于水”之礼均不包括夫妻。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有“夫妻牉合”条,从训诂学角度深刻剖析了夫妻关系:
“牉”当作“片”作“半”,合二体为牉字。《周礼》:“媒氏掌万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是半合为一体也,字作“半”。*段玉裁:《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然“牉”又同“判”。段氏云:
考诸《说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同上书,第35页。
又,《辞海》释“牉”为“一物中分为二”。其“牉合”条曰:
亦作“片合”、“判合”。两性相配合,男女结合成为夫妻。牉,半。一方为半,合其半以成配偶。《仪礼·丧服传》“夫妻牉合也”。
按,段玉裁及《辞海》解“牉”,夫妻“合”“半”为“一体”而成“伴”,则“牉”通“伴”,然其未“合”时非“伴”;又,“半”、“判”亦通解,“半,物中分也”,是夫妻既可以“合”为“伴侣”之“伴”,也能够“物中分也”,由“相合”“判”而为“半”。父母与子女,兄弟和姐妹则不可“牉”——既不可“合”而为“伴”,更不能“分”而为“判”。所以钱钟书正确地指出:
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兄弟”之先于“妻子”,较然可识。*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83页。
按,“天伦”者,“天然”之伦也;“人伦”者,“人为”之伦也。“天然”之伦不能改变,“人为”之伦却可以更张。故就血胤而言,“天伦”重于“人伦”。秦穆姬以自焚相挟拯救惠公的根本原因在此。
秦穆公终于让步,同意以惠公之子为人质而“许晋平”。
4.《左传》战争观剖析。穆姬所言“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以“戎”为“灾”而与“玉帛”相对举,此种厌恶战争、批判战争的立场并不仅仅是穆姬个人的,更是《左传》的。《左传》这一立场值得深加体悟。
《左传》虽亦曾有“兵不可去”即战争不可免方面的认知(如《襄公二十七年》所记),但《左传》中更多的是厌恶战争、批判战争之论述。换言之,类似于穆姬以“戎”为“灾”之论,在《左传》中更多、更普遍。早在《隐公四年》,左氏已借卫州吁之“阻兵而安忍(素心残忍)”发论,谓“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将“兵”即战争拟为“火”而主“戢”,否则“将自焚”,此种理念,《左传》尝一伸再伸。如《襄公二十七年》晋韩宣子论战争: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
按,宣公十二年晋、楚有泌之战,楚大胜,楚将潘党建议楚庄王趁势以“京观”即炫耀武功,并说“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言:“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又,《襄公二十四年》:“陈文子曰:‘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左氏以“兵”拟“火”而主“戢”,甚至以“戢兵”为武功之“七德”之一,借楚庄王口引《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櫜弓矢”以及陈文子所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均与穆姬以“戎”为“灾”之理念相一致,在在表达的是一种否定战争、渴望和平的理念。《左传》以“止戈为武”解“武”字,虽然并不符合“武”字之训诂义,但其中蕴含的“止戈戢兵”即消灭战争的思想却更加伟大。战争是人类自造的最大的社会恶魔。因为战争的本质是杀戮,因此与人性直接对立。本质上,战争乃是人身“动物性”而非“人性”的体现。尤要者,数千年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实际上都是掌握最高公权力的“政治家”或者说“政客”们的“角斗游戏”。*人性中之“好斗”每被政治家用于战争,钱钟书即曾引霍布斯所言“战争非直两军厮杀,人之情性无时不欲争,即‘战’寓也”(The nature of war consisteth not in actual fighting,but in the known disposition thereto during all the time.),“曩日言心理者,莫不以争斗(pugnacity)列为本能(instinct)”,并下断语谓:“吾国先秦诸子早省杀机之伏于寻常言动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224页。喜爱战争追逐战争的是政客,或者说得冠冕堂皇些是“政治家”,而平民百姓则恐惧、厌恶、痛恨战争。然而,最后承担战争带来的所有痛苦与悲怆的却总是平民百姓:“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常建《塞上曲》)“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常建《塞下曲四首》)战争的发动者、追逐者却在无计其数的战争受害者的累累白骨上享受着“角斗游戏”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他们极少或基本上不承担战争责任。人类社会也几乎总是在战争中“进步”,这是一个最为吊诡的悖论。然而无论战争本身“正义”还是“非正义”,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一定不是提倡、鼓励战争,而是约束乃至于消灭战争。作为“类”的“人”的这一崇高理想,2500年前的左丘明已揭示无遗,此即《左传》再三再四凸显的“止戈”、“戢兵”,看清了这一点,才能明了《左传》用骨肉亲情来与战争对抗之苦心孤诣的沉重分量。
5.许晋平。秦穆姬奋力救弟,甚至不惜以身及子女自焚相要挟,穆公对此极为震撼。《左传·僖公十五年》:
大夫请以(晋惠公)入。公曰:“获晋侯以厚(丰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得到)焉?且晋人戚忧以重(施压感动)我,天地以要(约束)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秦穆尝允诺不加害晋惠公),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絷曰:“不如杀之,无聚慝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太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乃许晋平。
秦穆公最终选择以惠公之子为人质而“许晋平”,这绝不仅仅出于穆姬之逼迫,更应视为穆公之理智使然:“既而丧归,焉用之?”大“胜”原应当为“厚归”,但遭遇的却是“丧归”。试问:是丧妻亡子家庭覆灭当紧?还是“享受”战胜国的“荣誉”有趣?这是《左传》借秦穆公之口为读者同时也是为整个人类在2500年前就已经预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又绝非秦穆公一家的“晦气”,秦穆公更看清了两国间化干戈为玉帛即视“兵”如“火”必须“戢之”的重要性。若非如此,类似“丧归”的悲剧将一演再演,则“厚归何用”?康德说:“(女人)心灵的崇高性只表现在她能认识男人独有的崇高品性的价值。”*康德:《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载《康德美学文集》,第46页。秦穆夫人巾帼英杰、慧眼识人,她没有错看秦穆公。秦穆公伟丈夫“铁骨”中的“柔情”最终结晶为理性之举,使秦晋两国关系出现了大逆转,由相互仇恨变为相互友好,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左传》高度肯定的。“秦晋之好”虽最终实现于晋文公时,然在秦穆公“特赦”晋惠公时已经奠定下基础。而尤需切记的是,对终于促成秦晋之好的人性诸要素,左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赞许性评价。
6.晋阴饴甥对话赏析。当然,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秦穆公在许晋平以前还要试探一下晋国的民情,了解晋国内对于此事的看法,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为此他召见了晋大臣。《左传·僖公十五年》: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扩军备战)以立圉也,曰:‘必报雠,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异心)而执之,服而舍(原谅)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服罪者)怀德,贰者畏刑(心怀叵测者害怕再次遭受刑罚)。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纳”、“定”,让惠公回国应君位),(省略“甚至”)废而不立,以德为怨(戴德变成怨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诸侯之礼,牛、羊、猪为一牢)焉。
这是一篇对话美文,类此者《左传》中俯拾尽是,却也因其普遍性,故足以拿它来细细品味,举一反三。
首先,左丘明原惜墨如金,在此却大段引出秦穆公和阴饴甥的对话,其旨意究竟何在?私意以为,借助于二人对话,左丘明意在表彰一种贵族式的幽默。幽默并不是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会讲两句噱头话,而是表现出一种涵养,透露出一种人格精神——机智、优雅、淡定、自信。处事不慌不忙,运辞不卑不亢,于风轻云淡、波澜不惊中蕴藏大智慧,在酒酣说笑间肩负起扭转乾坤的大担当。
“君子”、“小人”之分为此段对话之文眼。此说以论晋何以“不和”为说辞,内蕴五层意涵:(1)“小人”与“君子”各持己见,故谓之“不和”;(2)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故“不惮征缮”,基本立场是“必报雠,宁事戎狄”;(3)君子同样“不惮征缮”而“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可见两“不惮征缮”的目的、性质全然不同。“征缮”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从“利”、“害”的两面割:因势利导可为“利”,逆势而为能变“害”。它既可被小人用来“复仇”,与秦为敌从而成为秦国大隐患;也能被“君子”用来“报德”,变为秦国之大功利:“征缮”适可造成对于秦截然相反的两种后果,最终取决于穆公如何对待惠公;(4)小人认为惠公既已得罪秦,穆公必不肯饶恕且释放之;君子持义则正相反;(5)韩原之战“秦可以霸”,前提是释放——“纳”惠公而“定”之,恢复其王位。若不释放甚至“废而不立”,那么,穆公也是小人,因为他与晋国小人一般见识;秦原本可收感恩戴德之利,却可能恶变为晋国积怨满腹、靠拢戎狄之祸。阴饴甥“秦不其然”直指穆公本人:就看你小肚鸡肠还是宽宏大量,愿意为“君子”还是作“小人”。
晋阴饴甥说辞沉厚内敛,绵里藏针,软硬兼施,一语数关,既诚恳又尖锐,充分显示出语言本身的“历史力量”。阴饴甥一言歆动秦穆公,曰“是吾心也”,惠公因此受到高规格礼遇,由原先拘于灵台而“改馆”并享有诸侯待遇——“馈七牢”。
六、“作爰田”
惠公沦为阶下囚,尽受屈辱,晋亦国将不国。在此紧要关头,惠公先有发自肺腑的自责反省,不经意间又有“调整生产关系”、改革土地制度的关键性“动作”——“作爰田”。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本身撬动历史的巨大影响力不容忽视。《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侯(惠公)使郄乞(晋大臣)告瑕吕饴甥,且召之(瑕吕饴甥)。子金(瑕吕饴甥字)教之(惠公)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周礼·大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门”,此即“朝国人”)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国之贰,即嗣君)圉(惠公子圉)也。’”(省略“郄乞照办”)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担忧),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同悦),晋于是乎作州兵。
《国语·晋语》对“作爰田”描述更具体:
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和解),乃使郄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以子圉为国君。此与《左传》不同)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
对于“作爰田”,当今史家有多种解释,但均认为“作爰田”是春秋历史上第一次变更土地制度。在这一点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认识最典型,但问题也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为解剖样本。
春秋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国史稿》指出:“各种事实证明:新的阶级秩序在形成中,过去享受礼乐的阶级逐逝衰落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慢慢升上去。总之,一切都在变。”*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23页。“面对着这种现实,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社会变化的动向,维系自己的统治。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秦国和晋国打仗,晋惠公战败,被秦俘虏了。晋国的大臣为了挽回这种劣势,便把国人召集起来,假称君命,把田地赏给大家,名之曰‘作爰田’,废除了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配的制度。大家因为受了赏田,纷纷称道晋惠公,情愿为他效命,晋于是‘作州兵’。显然,晋国大臣‘作爰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民众服兵役,因而开了后来按军功赐田宅的先例。”*同上书,第325页。
郭沫若的解释有精当处,如谓“‘作爰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民众服兵役,开了后来按军功赐田宅的先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按军功赐田宅,这是当时政治领域的重大事变,正是礼崩乐坏的典型反映。对这要害问题,郭的眼光很敏锐。
但是,郭说晋国大臣为挽回劣势,“假称君命”而“作爰田”,违背了史实。无论《左传》还是《国语》,都说是惠公“使”——即命令郄乞告吕甥。虽说吕甥“教”之言,但此“言”总要得到惠公的首肯才行,所以不能说吕甥“假称君命”。将“作爰田”解为惠公“主动改革”,也缺乏根据。据《国语·晋语》对《左传》的补充,可知惠公“作爰田”,将土地赏赐国人是取悦他们,并没有“改革”,“废除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配的制度”的意思。《中国史稿》仅着眼于“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秩序”的变化,认为“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社会变化的动向”,对于惠公的忏悔,晋国人悲痛“皆哭”等史实,《史稿》未置一喙,缺乏“同情之理解”。不予措意人性问题,这种缺陷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晋国当时面临的情势看,惠公被俘,国难当头,凝聚人心刻不容缓。“作爰田”的主观目的在此。惠公并不考虑“调整生产关系”、“改革土地制度”这些“宏大目标”,只是在不经意间触动了“生产关系”的按钮,因此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人们在“创造历史”时往往并非事前预谋,却会在不自觉状态下实现历史的“目的性”。(康德语)如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世界是世界古代史上的大事,但柯林武德指出,这一历史事件是“这场或那场战争或政府的个别事件的总和。他们(指罗马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说:‘我在这场大运动里,即在地中海世界被罗马征服之中,扮演了我的角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9页。以此对照“作爰田”,春秋时生产关系、土地制度的确从此发生了本质之变,但却不能说这是晋惠公对之进行的“自觉调整与改革”。
七、重耳流亡与晋文公登基
重耳出逃在外十九年,其中十二年在戎狄(重耳母为狄人),七年在齐、卫、曹、宋、郑、楚、秦七国间辗转流亡。重耳历经磨难,饱尝艰辛,锤炼了意志,提升了品格,这些阅历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他登基后的执政产生了重要影响。流亡期间,既有如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对他的厚礼与尊重,也有如卫文公、曹共公、郑文公的无礼与薄情。以礼遇言,楚成王、秦穆公均用诸侯之礼重待重耳。如《国语·晋语四》:“(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礼(周王享诸侯之礼)享之,九献(献,敬酒),庭实旅百(展现礼物与礼器,此为诸侯间交往之礼)。”因有此一段交往,后在城濮之战中遂有晋文公“退避三舍”之礼让。
秦穆公更胜楚成王一筹。据《国语·晋语四》,秦伯以诸侯之礼设宴款待重耳,赋《诗经·采菽》,“子余使公子降(降阶之堂下),拜(再拜而稽首)。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服,古代不同爵位等级者所穿不同礼服,此指相应的身份待遇)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
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这位怀嬴,就是当年子圉在秦国当人质时的妻子。《左传·僖公十七年》:“夏,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怀嬴因有才,最得秦穆公钟爱。现再改嫁重耳,穆公曾对重耳说:“寡人之适(嫁女),此为才。子圉之辱(“辱”指曾经嫁于人质。意谓怀嬴仅此小疵,别无它欠),备嫔嫱(嫔嫱,宫中女官名)焉。”(《国语·晋语四》)
怀嬴为何改嫁?因为子圉抛弃了她。子圉婚后五年即逃归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遂逃归。”
他为何逃归?原来是为争夺王位。《史记·晋世家》:“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
子圉觊觎王位,与乃父当年同一副猴急相。此事再次开罪了穆公。故在嫁怀嬴后,穆公即准备辅佐重耳。《史记·晋世家》:“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
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穆公从楚国召回重耳送之归晋,又派公子絷赴晋军晓以利害,晋军大“反水”,归顺重耳,重耳杀怀公(子圉),晋文公登上历史舞台。
八、余论
1.史家撰史之“隐身法”。语言之于撰史,其功莫大!但这里必须指出,撰史之“语言”实有两方面内涵:
(1) 它首先自然是指著史者的语言。但史家撰史应当“隐身”。黑格尔在谈《荷马史诗》时有一段提示:
为着显出整部史诗的客观性,诗人作为主体必须从所写对象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表现出来的是诗作品而不是诗人本人,可是在诗里表现出来的毕竟还是他自己的,他按照自己的看法写成了这部作品,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他这样做,并不露痕迹。例如在《伊利亚特》这部史诗里叙述事迹的有时是一位卡尔克斯,有时是一位涅斯特(重点号均为笔者所加),但是真正的叙述者还是诗人自己。*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13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条说得也很中肯,却要比黑格尔更早: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叙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84页。
按,亭林之“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稍不确。此种书写方法非仿于史公而实肇始于《左传》。《左传》因有此特点,配以生动传神的文笔,故具有高度的可读性。
黑格尔凸显了诗家——按照史、诗相通之理就可以是史家——主体对于“客观性”的追求。而黒氏所说的“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是指作者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叙事,透过史实,而非直接表露史作者的“意蕴”即史义。这正是美学中的“鉴赏”原则和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
以此我们看《左传》。尽管左丘明也“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但左氏本人一般并不露出痕迹而是隐在幕后——他自己站在第三方叙事。这表明左氏主观上遵循着尽可能客观的历史学法则。此种叙事方法又不仅能使历史书写更加客观,借用黑格尔的《美学》用语,它还与历史中受人性制约的“情致”涌动和“动作”的发生——其结果即历史“情节”的起承转合——息息相关。
(2) “君子曰”与史学评论。文论人石天强对于小说“每章最后的叙述文字”曾经感到“费解”。这种认识在文论界有相当的普遍性,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处借剖析石论复视《左传》之“君子曰”,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历史叙事的语言运用。石氏指出:
这些文字(笔者按,指“每章最后的叙述文字”)可以理解为叙述人对现实的各种感悟,它们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叙述人不得不站出来现身说法。但这种议论性文字的频繁呈现,却也暗示着叙述的苍白。叙述人所编织的文字难以承担如此沉重的内容,它迫使叙述人破坏叙述的完整性,而以议论的形式出现。而这恰恰意味着叙述的失败。*石天强:《再见了,马原们!》,载《文汇报》2012年4月14日。
按,历史之叙事法实亦似小说,其中并非不可以带有史家本人对于历史的裁断,但一般来说它应当隐藏在叙事之中,在与事件水乳交融的状态下让裁断本身“透出来”。如所周知,《左传》有“君子曰”的史评。论者或谓《左传》之历史叙事之“君子曰”是否也带有某种瑕疵若石论者?
其实这种疑惑可以不必。换言之,我们不能将《左传》的“君子曰”视同为石天强所指责者,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顺着这一逻辑,我们应当接着问:既然脱离事件而纯发议论会“破坏叙事的完整性”,那《左传》能不能不发议论?或者《左传》是否也报着一种“谈事件也不过是为发议论附带性地举例而已”的理念?我们要说:倘若是这样,《左传》的“君子曰”也就真成了黑格尔所讥讽的依附在史著身体上的“赘瘤”,这样,《左传》就不配作中国传统史学的不祧之祖了,也配不上章实斋“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1页。之赞,——《左传》就不是《左传》了!
《左传》的“君子曰”不是这样。《左传》用“君子曰”处并不多,都是在那些极其紧要,事之至此已经不得不“发”的“节骨眼”上才用——《左传》之中并没有脱离事件而空发议论的“君子曰”。也就是说,左丘明叙事至“君子曰”前,若不在此紧要关头“发”一下、“论”一番,那反而“假”了。就好像一个人压抑太久,到了紧要关口,他只有——而且必须——长出一口气才能“解恨”、“解闷”,要不然就要憋屈死了!读者至此若是见不到《左传》有感而发,也会有大遗恨。所以,我们阅读至“君子曰”处,并不觉得它是“赘瘤”,反倒有一种与左丘明一致的“快哉!快哉!”之感。
然而,作为史家,左丘明却又必须“把”(此即如同钱钟书先生强调诗家的“持”)着情感的闸门而不过分,不能像钱钟书先生批评的那种“徒以宣泄为快有如西人所嘲之‘灵魂之便溺’(seelisch auf die Toilette gehen)”*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57—58页。。我们读《左传》的“君子曰”,正有那种“恰到好处”的体会。而且更未曾料到,如此一来,左氏在“不经意”间竟然“自然而然”又创造出了一种新史体——“史评体”。所以,对“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的法则,《左传》运用得得心应手。而我们对于这一法则,则既应“大体”遵循,又不能拘滞不通,“食古不化”。要之,叙事中的史论并不是不能用,而是要看怎么用。所以,对待史家在叙事过程中发“史论”,还是应当像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所说的那样:“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889页。
2.历史人物的语言。撰史无“语言”不成。然亟当留意者,历史书写之“语言”又并非仅指叙事主体的语言,同时也是叙事对象的语言。史家著史叙事时不仅应当“自己说”,更要多让“别人说”,让历史人物自己发言,让他的语言来充当叙事的工具。在这当口,史家无需越俎代庖,喧宾夺主,替代历史人物。前文《左传》中秦穆公、晋阴饴甥等等历史人物的大量对话,在在成功运用了这一叙事方法,黑格尔举卡尔克斯的例子,亦明示了这个道理。用这种手段叙事,根本上遵循的仍然是亭林之“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之法,亦即黑格尔所说“诗人”——史家——“作为主体必须从所写对象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主观上追求的还是那一个字——“真”。
3.现今史著之“语言症结”回省。拿了黑格尔拈出的“叙事”两要素,结合《左传》,我们可以来审视现代中国史学。首先可以见出,中国现代史家并不懂得至少是不甚懂得“隐身”、“从所写对象退到后台”的道理。他们并不懂得至少是不甚懂得,历史书写的一般性质是叙事的而不是说理的,叙事须站在“第三方”;说理的是“第一方”,二者立场不同,方法各异,产生的效果便大相径庭。看当今史著,其中并非没有史实,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他有事实而不够“公正”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史家每每会急不可耐从“后台”走到“前台”充当“主角”,急于做一个历史的裁判员而不是叙述者。因此,他们总想要向读者有选择地“灌输”他们的裁断亦即他们的理念,忘记了让理念“融化”于史实之中,把发言权留给史实本身;他们更不让历史人物自己开口——“以言蕴事”的撰史法,历史人物的对话这一撰史要点,早已经被现代史家彻底干净地剔除于史著之外了!这在20世纪50—80年代初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中最明显。而在传统史学中,不说《史记》、《汉书》,就连学术史(如《明儒学案》等)、典制史(如《通典》、《通志》等)中都有大量情趣盎然的对话。总之,没有了语言以及与语言身影相随的情节,是现今史著的痼疾。
产生这一痼疾之病因又在于现今史家特别是通史和断代史作者的视域重点并不在活生生的人和“人性”上,因此书写用语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而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语言。(例如前文郭沫若论“作爰田”)现代史家不考虑人性,往往只想到“灌输”某种“主义”。像穆姬救弟这样感人肺腑的“小事”不会引起现代史家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初通史、断代史家们的兴趣。早在30多年前,钱钟书先生已经发现了史学界的这个弊端。钱先生有《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该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据题注,该文曾发表于《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写道:如果像诺法利斯(Novalis)那样,认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或像梅里美(Merimee)那样坦白承认:“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这一定会被历史学家嘲笑。因为“在史学家听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是“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的表现。*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66页。
冷漠人性,那现今史家的“兴奋点”在哪里呢?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发展阶段”、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等“大问题”。如钱钟书先生所说:
在人文科学里,历史也许是最早争取有“科学性”的一门。轻视或无视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理论(transpersonal or impersonal theories of history)已成今天的主流,史学家都只探找历史演变的“规律”、“模式”(pattern)或“韵节”(rhythm)了。*同上注。
又因为这些论旨与意识形态、现实的政治利益紧密粘连,此种“利害关系”已经基本上制约了现代史家的视野。受此“利害关系”影响,现代史家会首先认定一些“公理”、“公例”亦即“定律”,诸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必定腐朽,被统治阶级受压迫,阶级斗争等“套路”,先有这个套路,然后“选择”那些符合套路的史料去迎合。这就违背了“鉴赏”的原则。而非“鉴赏”必不“公正”,如前文康德所说“很有偏心”,不公正也就不可能客观。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拿《左传》的叙事语言与现代史著作一番比较了。二者给人感觉大不一样:一家是亲切的,和颜悦色的,像拉家常说故事那样娓娓道来;一家下笔运语则疾言厉色,充斥着“霸气”,一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口吻。《左传》比较鲜活、灵动,充满生气和情趣;现代史著则比较枯涩、干瘪,说的是“套话”,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观感,文字灼眼却不耐看。归根结底,《左传》的核心理念是人性,现代史家,特别是20世纪50—80年代初通史、断代史的史家则缺乏人性关照,“见物不见人”,所以造成了与《左传》的巨大差异。本文以《左传》为范本,体味其历史美学之意谓,初衷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