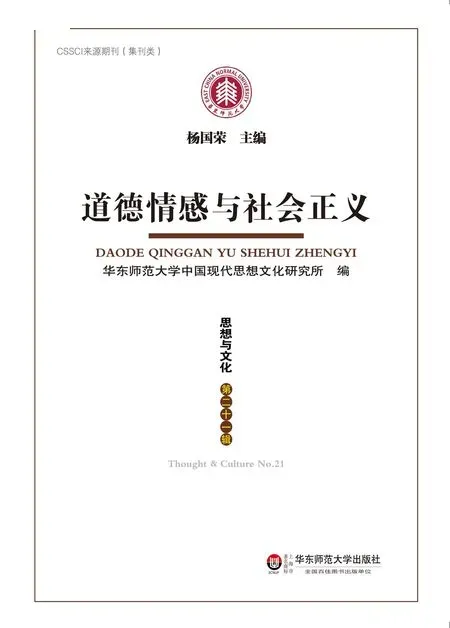重新思考偏见*
2017-04-12·
[]·
今天偏见是不受欢迎的,这很好理解。它往往指的是一系列针对这个或那个群体的仇恨态度和实践。种族偏见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为任何想要在道德和政治判断中给偏见留下一席之地的企图投下了阴影。任何体面的人都不会承认偏见的一席之地,想想你能为它说些什么呢?只要偏见指的是由仇恨引起的思想或行动,答案就是否定的;这样的偏见应受到谴责,而不是为之辩护。但偏见还有一种更广阔的意义。
伊曼努尔·康德很好地把握了偏见的意义。他将“启蒙”定义为“一般来说从偏见中解放出来”。*Immanuel Kant,The 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James Creed Meredit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40,p.152.他所说的“偏见”指的不仅仅是无根据的仇恨。对康德来说,偏见是一种前判断(prejudgment),即其有效性没有得到明确考察和辩护的判断来源。康德考虑的偏见包括传统、习惯、习俗和成长经历,甚至我们自然的欲望——所有试图避开有意识的反思,影响我们判断的企图。康德说,“无偏见思考的精神”和启蒙运动的实质是去超越这些偏见的影响,做到“为自己思考”。*Ibid.
在康德之前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偏见也持类似的态度。例如,培根写道,如果能“去除偏见”,清除他所说的“心灵的偶像”,人类的智能会发展得更好。他所说的“偶像”指的是传统、习惯、语言和教养等产生的影响。培根认为,如果我们的“理解是无偏见的,像一块白板那样”,我们的判断会更接近真理。*Francis Bacon,The New Organon,ed.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8.当他决心摆脱所有的“先入之见”,将知识一块一块地重新建立起来时,勒内·笛卡尔表达了相似的观点。*René Descartes,Discourse on the Method,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trans.John Cottingham,Robert Stoothoff, and Dugald Murdo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6.他呼应了“白板说”的理想,并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能自出生之日起就完全运用我们的理性,并且如果我们只接受理性的指引”*Ibid.,我们的判断就会更加坚定、更少模糊。
康德、培根和笛卡尔阐述的“偏见”比无根据的敌意要广阔得多。它指的是任何其有效性没有得到验证的判断来源。我相信,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消除偏见的愿望是我们这个时代强有力的一种理智理想。当然,我们有理由鄙视被认为是仇恨和歧视的偏见。但是,对偏见的拒斥反映了更深层次、更普遍的假设,即理性判断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偏见的影响,包括我们从传统、习惯、习俗和我们的成长经历中获得的理解及承诺。
这种思考判断和拒斥偏见的方式正是我试图挑战的。我的挑战建立在对判断的两种概念的区分之上。第一种概念也许可以被称之为超然的概念(detached conception)。根据这种概念,当我们的判断不依赖于任何未经明确验证的来源或影响时,我们才能得到最好的判断。这类判断是“超然的”,因为它试图让我们摆脱所有未经验证的影响。
第二种判断概念也许可以被称之为处境化的概念(situated conception)。根据这种概念,以完全超然的方式来获得判断的愿望是具有误导性的;慎思与判断总是在我们生活的处境内展开的。根据处境化的判断概念,我们生活的处境不是理性的障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在此视角内理性才得以可能。
我在这本书中的目标是阐述和捍卫这种处境化的判断概念。但我也希望能表明,我为什么要对比超然的判断概念和处境化的判断概念。如果我能表明处境化的概念是更加合理的,那么康德、培根以及笛卡尔对偏见的拒斥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判断不可避免是处境化的,那么“清除”我们脑中偏见的企图就可能是具有误导性的。有可能我们不应该完全清除心灵的偶像。
在我们的处境/生活环境内进行推理和判断的概念,现在看来还十分模糊。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它说清楚。为了把它说清楚,我会引用两位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著作。他们论辩说,我们的理解和判断总是处在这个世界中的,它们受到了我们所从事的传统、筹划以及实践的影响。这意味着无论何时——评判政治或法律中相竞争的论证时,试图理解一个哲学文本时,考虑在这个或那个环境中如何行动时——我们进行判断,我们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的判断总是受到未被论证过的前概念和承诺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处于我们有意识的关注范围之外。但与看起来相反,偏见作为判断的一个面向并不总是令人遗憾的限制。他们论证说,事实上有一些偏见能带来好的判断而不是阻碍好的判断。
认为好的判断总是超然的这一假设在今天的哲学、政治学以及法学中十分有影响力。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司法体系中找到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被认为应该由那些头脑像白板一样的人组成,他们对这起案件的双方或案件的主题毫不熟悉。对此,法官及法学学者提供的辩护理由是,这种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方式排除了偏见,从而被挑选出来的陪审团成员将以开放的心态来审理案件。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偏见的影响是难以摆脱的,这种方式并不会真的产生出一个无涉偏见的陪审团。它很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个带有错误偏见的陪审团——这个陪审团缺乏做出好的判断及确认相关事实所需的背景理解。
例如,考虑一下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及其馆长1990年被控淫秽一案选择陪审团的方法。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指控这家博物馆及其馆长展示了有争议的照片。法官排除了一名可能当选的陪审团成员,仅仅因为她曾经看过这场展览(不仅仅是那些有争议的照片)。她也是唯一一位号称经常逛博物馆的成员。后来被选中的陪审团团员是一位“从未去过博物馆的人”。*Jeffrey Abramson,We,the Jury (New York:Basic Books,1994),pp.21-22.法官认为那些看过展览的人,甚至那些经常去博物馆的人,都会带有偏见,可能会支持艺术放纵,因此做出不公的裁决。为了避免偏见,这位法官显然给陪审团选出了一位对博物馆(或淫秽法)毫不熟悉的人。
但这样一个陪审团就可以无涉偏见吗?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一个由从未去过博物馆的人组成的陪审团会带有其特定的偏见:这样一个陪审团看似没有什么依据来确定在博物馆展出什么是适当的。那些不熟悉博物馆通常展示的作品类型的人如何可能准确地确定哪幅特定的照片达到了“当代社群的体面标准”呢?他们被要求来诠释这个标准是什么。缺乏背景知识或偏见的法官看上去很难公正地审理这个案件。
我对“偏见”的使用对于那些熟悉其贬义的人来说,无疑听起来很奇怪。我所说的“偏见”仅仅代表的是“背景知识”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的目标正是将这些概念关联起来。但究竟是怎样的背景知识在发挥作用呢?说“我知道”博物馆内通常展示的是哪类作品与“我知道”目前正在展出的照片的名字是不同的。后者仅仅是信息,而前者是对内容的熟悉,了解什么算得上是艺术品,而什么是垃圾。除了负载价值,这类知识不可避免地是处境化的。它意味着你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中长大,经常去博物馆,会诠释艺术品,并发展出何谓“体面的”艺术感。在此意义上,我们也许将这些知识称之为一种“偏见”。此外,由于这些知识是处境化的,它不可能被简化为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的规则或原则。处境化知识的这种特殊性符合我们将“偏见”和偏私性联系在一起的印象。
当今怀疑偏见的第二个例子是普遍存在的对政治修辞的贬低。人们熟悉的一个表达是“这只是修辞”——那些滔滔不绝的废话只是为了劝说特定的听众。这种对修辞的诋毁已经超出了对政治家及其动机的不信任。它反映了一个对政治论证的性质以及应该如何进行政治论说的更深层次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政治论证取决于它们对于某种非修辞化的原则——也即,不诉诸任何令它产生的特殊的场景——的辩护。试图通过故事、图景和参照物来劝说特定听众的修辞至多只能成为这种“真正的论证”的修饰物。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修辞成了一种迎合或欺骗的方式。你可以说,对修辞的怀疑是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即修辞诉诸的是人们的偏见而不是理性。这个论证指出,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以一种有偏倚的方式引导他们的听众做判断——他们会受到自身视角的影响,而其他人并不分享这种视角。我们假设政策和原则应该最终以抽象的方式得到辩护——由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获得的理性来辩护。
但那些雄辩的修辞的例子让我们怀疑这个假设。像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以及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政治人物的演讲,不光是从他们诉诸的原则那里获得道德感染力,更是从诉诸其听众的生活处境这一点上获得了道德感染力。例如,在民权运动中,林登·约翰逊的演讲唤起了听众的道德愤怒。他的演讲与听众的日常角色及实践紧密相联,从而获得了他们的共鸣。众所周知,为了获得与其听众共同的立场,他的演讲甚至操着一口浓重的南部口音。*Bryan Garsten,Saving Persuasion:A Defense of Rhetoric and Judgmen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93.尽管约翰逊面对的听众是特定的,但他用他的修辞挑战了这些听众既有的观点——用一些他们在意的其他实践来谴责种族隔离。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正是通过诉诸听众的偏见,约翰逊的修辞赋予了平等原则以道德力量。
试图挑选出大脑如白板的陪审团团员,以及对政治修辞的怀疑,证明了今天人们对偏见的拒斥。但如我所说,这种拒斥是具有误导性的。为了建立起偏见的合法地位,我首先要揭示的是,超然判断的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偏见——这种渴望受到了有问题的思想传统的影响。追随伽达默尔的步伐,我们在现代早期和启蒙时期找到了这种传统的源头。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直到启蒙运动,偏见这个概念才获得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消极内涵”。*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trans.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rev.ed.(New York:Continuum,1989),p.273.他解释说,“偏见”这个词实际上来自“前见”,它以前“既无褒义也无贬义”。他接着说,直到启蒙运动它的意思才被局限为“无根据的判断”的意思,这种判断被认为无关理性,而受到了人为的权威或传统的影响。*Ibid.
在第一章中,我考察了在现代早期和启蒙思想中针对偏见的例子。*在此“启蒙”指的是这个时代的自我描述,我考察的几位思想家都属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我并非断言我们今天所说的启蒙时期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将通过提供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以偏见对抗偏见”更持久的论述来延续他对偏见的讨论。*Gadamer,Truth and Method, p.273.我的目标不是提供对偏见这个概念详尽的历史梳理,也不是去证明伽达默尔所说的“以偏见对抗偏见”定义了启蒙运动的实质。*Ibid.我之所以转向历史是为了澄清偏见这个概念,并展开对超然的判断理想的论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审视了培根、笛卡尔、亚当·斯密和康德对“偏见”的论述,他们都谈到了偏见或发展了超然判断的理想。
如我们将要见到的,这些思想家试图排除不同的偏见概念。例如,斯密将偏见置于我们对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忠诚之中。他声称,这些偏见是狭隘的和不合理的,它们是盲目的习惯和习俗的产物。*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Ryan Patrick Hanley (New York:Penguin,2009),p.229.斯密并不认为所有非理性的影响都是偏见。事实上,他支持与理性相对照的对人类的爱和“同情”。但斯密保留了作为轻蔑语的“偏见”一词。与之相反,康德认为任何情感——不管有多少人分享这些情感——在原则上是与特殊的欲望和忠诚无区别的偏见。按照他的说法,偏见指的是被超然理性之外的其他来源“给定的”任何东西。*Kant,Critique of Judgment, §40,p.152.
尽管他们对偏见的范围存在分歧,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同意,当我们从我们的处境或生活环境中抽身出来时,我们才能获得最好的判断。斯密将基本的道德情感排除出了“偏见”的范畴,他认为正是情感使得我们的判断得以可能,它们普遍地存在于人类这个物种中。就这样,这些思想家提供了一种独立于习惯、习俗和传统的判断的基础。
除了突出“偏见”的细微差别,我研究的这些思想家给我们指出了两种好的判断感,并回答了为什么逃脱偏见能使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培根、笛卡尔和斯密强调的第一种好的判断感是做出真实的判断。他们论证说,我们的处境尤其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以及传统的权威会导致我们误入歧途。摆脱偏见是获得真理的第一步,无论这个真理是有关宇宙(培根和笛卡尔)还是有关正确的行为方式(斯密)。
第二种好的判断感,如康德看重的,是自由的判断。他论证说,受到偏见影响的判断不光是错误的,也是受限的。自由的判断必须是自主的;它必须来自一个人自身理性的裁决。康德将理性与习惯、习俗、文化甚至欲望相对立。因此,针对偏见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与真理有关,一个与能动性有关。我旨在挑战这两种批评:我要表明偏见可以是具有启发性的,并且它与自由相容。
在通过处境化的判断概念探究偏见的一席之地前,我要考察一个大家熟悉的有关偏见的例子来结束第一章。这种观点无条件地支持传统,并将情感置于理性之上。偏见的“感性”复兴最著名的代言人是埃德蒙德·伯克。他的偏见观念十分重要,它也与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偏见的看法形成了对照。伯克大胆地宣称,“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我完全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是具有天然情感的人;不要抛弃所有旧的偏见,我们相当地珍视它们;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正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才珍视它们。”*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ed.Frank M.Turne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74.
伯克所说的“偏见”不仅是天然的情感,或抽象的情感,而是受到特殊的习惯、习俗以及社会角色影响的情感。他常常用“偏见”来指代习惯、习俗以及社会角色本身。例如,他经常说教会的确立是一种“偏见”,因为它塑造了英国人的实践和判断力。*Ibid.,p.77.
从表面上看,伯克对偏见的捍卫似乎是对前人思维方式的一个激烈挑战。但他事实上分享了他们的核心假设。因为他接受了偏见与理性的彻底区分,而只是将两者的价值颠倒了过来——他用“体面的帷幕”、“天然的情感”以及“愉快的幻觉”来捍卫权威的传统来源。他并没有试图证明理性与偏见交织在一起,而接受了理性与偏见的对立,只不过他声称偏见具有更大的优先性。
这种对偏见的捍卫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如果偏见不过于情感和“愉快的幻觉”,那么为什么它应该被置于理性之上呢?伯克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实际上提供了对偏见的两种捍卫,但两者都没能证明为何偏见应该优于理性。第一种捍卫只是哀叹了偏见的衰败,并唱响了对过去的赞歌。第二种捍卫简单论证了传统的社会功用。尽管伯克坚持认为传统的角色和制度使社会团结一致,他并没有展示出这些角色或制度代表了任何内在的洞见或理由。伯克对偏见的功利主义论证出现于他对教会制度的赞美中。尽管他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但他仍然认为教会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以及所有善与慰藉的来源”。*Ibid.
如果将偏见看作是与理性相对的,那么要接受偏见作为权威的一种合法来源就会变得困难。但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偏见与理性关系的方式。在伯克那里我们找到一种情感主义的偏见观,与之相对,我想要捍卫的是一种诠释学的偏见观。这种偏见观与我所说的处境化的理解概念有关。根据这种概念,偏见是判断不可避免的一种特征;我们总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去判断和理解的。但正如“诠释学的”这个词所示,我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视角,它是向诠释开放的。此外,我们生活环境中的某些特征、某些偏见(习惯、传统、经验),也许事实上能帮助我们去更好地判断。在此意义上,偏见是理性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不是对理性的背叛。
诠释学的偏见概念来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两人都从我们的处境出发来理解偏见——伽达默尔将其称为我们的视域(horizon),海德格尔将其称为我们的世界(world)。*在《存在与时间》中,当海德格尔在综合的意义上使用世界这个词时,他没有使用引号。当他谈到世界的通俗意义时——即我们通常在各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时,他加上了引号(单引号和双引号)。当他谈到我们周围的“实体总体”时,他给‘世界’加上了单引号;当他在综合的意义上谈到具体的世界如农妇的“世界”时,他加上了双引号。(《存在与时间》,第93页)在第二章中,我会从海德格尔那里发展出一种处境化的理解概念,尤其是从他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这个概念中。我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在世存在的诠释,这种诠释将挑战超然判断的理想,并试图解释从我们的生活环境中进行推理到底意味着什么。处于“在世存在”概念核心的是这一看法,即我们最基本的理解模式不是超然地审视我们的信念及其起源,而是从制作物品、将其投入使用、回应我们的处境、致力于某些特定目标中产生的实践性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理解首先并不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它不是那种当我们检查物品并注意到它们的性质(大小、形状、颜色等)时产生的意识。我们实践性的理解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明确的。它处于我们有意识的意识之下。海德格尔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木匠理解他的锤子的方式。当这名木匠在他的长凳子上工作时,他通过使用他的锤子而了解了它。他知道它是制造橱柜的工具,而橱柜是房子的一部分,房子又是生活得好所需要的。当他使用锤子时,这名工匠洞悉所有这一切,即便他有意识的关注处于别处(也许他关心的是即将到来的午餐休息时间,或者天气,或者当天的新闻)。
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的观念及其实践特征令他拒斥我们所熟悉的主客二分。*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Malden,MA:Blackwell, [1927]1962),p.87.他指出,当我们从事我们的活动时,我们并不是考察客体的主体。相反,我们被自己的目的所缠绕,我们处于我们试图理解的世界中。
为了把握这个观念,海德格尔引入了艺术的一个关键词。他用“此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在这儿”)概念来取代主客体的二分。*Ibid.,p.27.此在这个概念表明,我们是由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开展的活动,我们所处的处境,以及我们总体的处境或生活环境——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来定义的。世界是我们参与其中的总体——它包括目的、目标和实践的网络,这些东西将我们的生活定义为一个整体。
理解世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总体性。在此有两件事情是明确的:第一,我们对总体性的理解是实践性的。只有生活其中,“生活在”世界中,我们才能理解它。第二,我们的理解带有综合性。为了理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对世界的整体有某种意识。因为任何特殊的活动或角色都只有在与其他部分、与整个网络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在世存在”表明了我们对这个整体的基本意识——这种意识就体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海德格尔论证说,这种意识是所有行动和理解包括所有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前提。这种反思是在世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把握实在的一种有特权的方式。*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Malden,MA:Blackwell, [1927]1962),pp.86-87.
但世界的网络是如何贯穿起来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对世界的诠释是它像一个活生生的、展开的故事。如此说来,世界有它的目的。它不是一系列任意的习惯、习俗或社会力量,而是一个意义的统一体。但是,这个意义统一体是不会枯竭的。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开放的;没有哪部分是被一劳永逸地定义的。这个故事是开放的,因为此在在其生活的每个步骤都在“书写”自身的故事。世界如何成为一个部分的整体,一个意义尚未完成的统一体,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谜团。我写第三章的目的就在于解释这个谜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目的只是概述出一种叙事性的世界概念,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世界概念不同。根据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为海德格尔的英美读者所熟知,世界是偶然的,它是社会实践不断变换的网络;它没有最终的目的。用霍夫曼的话来说,在世存在暗示着此在“全部的偶然性及无根性”。*Piotr Hoffman,“Death,Time,Historicity:Division II of Being and Tim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ed.Charles B.Guign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239.关于“偶然”观点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版本可参见Hubert Dreyfus,Being-in-the-World: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Division I (Cambridge,MA:MIT Press,1991)。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是错误的。它忽视了海德格尔的核心论点,世界体现了“存在的命运”。海德格尔用“命”(Schicksal)和“命运”(Geschick)来解释世界的看法暗示了一种对我们处境的叙事性理解。但除了与海德格尔的观念相合,我认为,叙事性的理解能最好地解释我们实际的经验。它捕捉到了我们的生活是可理解的且它向解释开放这一特点。
我发展了对在世存在的叙事性解读,以澄清处境化的理解概念并挑战超然判断的理想。因此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考虑在世存在是否为人类能动性留下了空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要挑战的针对偏见的例子而言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如我在第一章所示,针对偏见的一个主要论证是偏见是与自由对立的。如果理解、慎思和判断都不可避免地是处境化的,那么又何来自由呢?
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将自主性归之于一个主体,但我认为他的此在观念暗示了一种能动性概念。这一概念的基础是他对此在的诠释。他将此在诠释为“被抛—筹划”,分别强调了在世存在的消极和积极维度。被抛—筹划抓住了此在既是其命运的产物又是其命运的作者这一点。“被抛”意味着任何判断、意图或行为,无论它多么具有革命性,都只有在“被给定的”情况下(即世界中)才能得到理解。虽然我们可以质疑和修正任何特定的实践、目的、角色或判断,但我们无法扭转事物的整体秩序,或从头开始重新定义自身。
但整体并非我们困于其中的命运。相反,它是某种特定的能动性的来源。海德格尔通过“被抛”这个概念发展了这种能动性观念。即使看上去仅仅只是习惯,或对习俗的简单依附,都包含着某种创造性的适应。不管多么隐晦,我们总是改变着限定我们的世界。因此,被抛包含了一种自由,我建议将这种自由诠释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自主性。通过比较被抛—筹划这种自主性与康德的自主性理想,我想要表明的是海德格尔既破坏了康德的传统,又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它。
我从海德格尔这里获得的能动性概念认为,此在既是完全被动的又是完全主动的。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被抛—筹划的统一性——每一方都依赖于另一方——来解释这种显而易见的冲突。我强调这种统一性,所以此在既非自我创造的也不屈从于任何外在于它的命运。与此同时,我反对那种将此在理解为只能“在其自身文化的种种可能性中”去塑造其认同的解释。*Richard Polt,Heidegger:An Introduction (London:Routledge,1999),p.63.将此在构想为部分自由部分受限的,会带来对被抛性(被给定的)的一种误解,仅仅将其视作对能动性的限制,而不将其视作能动性的来源。
被抛与筹划的统一性指向了海德格尔特别的时间概念,我会在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来诠释它。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关联对于把握海德格尔的人类能动性观念至关重要。通过检视海德格尔的时间、历史、死亡、有限性和永恒等概念,我试图勾画出处境化理解的深层次意蕴。
对那些不熟悉海德格尔思想的人来说,我目前对在世存在、此在、被抛—筹划的预先说明还是显得模糊。说清这些概念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核心要务。在此,我只是为接下来有关在世存在如何澄清处境化的理解概念的讨论做准备。
为了用我们更熟悉的词汇来讨论这个概念,我们也许可以将我们的处境或生活环境刻画为一种视角。理解的处境化概念认为,所有推理、慎思和判断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视角之内。视角这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觉上合理的模型,用以说明我们的处境或世界如何能帮助我们去判断而非阻碍我们去判断。
当我们从视觉上来谈论视角时,我们指的是一个特定的观点——从山谷、山顶或海边望出去。一种视角与从这种视角望出去能看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有趣的。视角本身并不等于它所揭示的事物的总体。作为看的条件,视角无法像被它揭示的事物那样以相同的方式被看见。但是,一种视角是与它所揭示出的事物的总体密不可分的。例如,想想从山顶上看下去。这个视角与脚下站立的土地、这片土地所处的位置、远处的湖,以及更高处的山都密不可分。没有这些,这个视角就不会产生独特的观点。尽管如此,视角或整个视野虽然本身不可见,却让我们看见了它所揭示的事物并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外观。如果我们爬得更高,从而改变了我们的视角,同样的事物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比例。如果我们转过身去,所有事物都会消失不见。
这种奇妙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整体难以捉摸的特性,刻画了我们所说的“生活视角”。所谓“生活视角”,我指的是一种受到许多经验塑造并同时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的特定观点。想象一下一个小孩的视角。这个小孩的视角自然会受到一个孩子从事的典型活动的影响——在学校里为“展示和讲述”做准备,热切地等待放学,玩“躲猫猫”,等待冰淇淋车,看动画片,等等。不做这些小孩做的事情,你就不能获得一个孩子独特的视角。正是通过一个小孩的视角,或像孩子这般的感受性,这些活动才得以“出现”,或唤起孩子的兴趣和兴奋感。一个小孩的视角因此成为许多活动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活动又会影响孩子的视角。
同样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综合的意义上界定了我们所说的“生活视角”:由我们熟悉的经验(例如,活动、角色和实践)塑造的观点。一种生活视角与这些经验是密不可分的,它也赋予了这些经验独特的意义。换言之,任何特定的经验,无论它如何定义我的同一性,只有在我的生活整体内才能得到理解或具有重要性。我们常常通过讲故事来表达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这种我们熟知的经验很好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当我们试图说出特定事物的意义时,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阐明它们嵌入其中的整个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谈谈我们的视角。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视角绝大部分是未被阐明的,对它的叙述也不可能穷尽。就像视觉能力让我们看到东西一样,一种生活视角让我们得以理解某些事情,包括我们阐述这种视角本身的尝试。此外,一种生活视角不能以相同的方式像任何特殊的活动或实践那样被质疑或修正。因为正是我们的视角首先指出了什么是成问题的。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在此意义上是与生活视角类似的东西。这是我想要发展的“处境”的意义。也许用“视角”来理解我们的处境更容易一些。
在日常的言谈中,我们将“更高的”、“更广阔的视角”与“更低的”、“更有限的视角”相区分。想一想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对比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有限的视角是从海底去看太阳和星星,一种更清晰的视角是把头抬出水面去注视上面的世界。*Plato,Phaedo,ed.Jeff rey Henders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 111a-c.尽管有的时候区分哪个视角更好哪个视角更坏是困难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容易地做出区分。虽然我们可能无法确定站立在珠穆朗玛峰上的视角一定好于飞机上的视角,或站在大本营的视角,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视角要好于一个登山者的视角,因为他只能注视他的脚下。
在生活视角的例子中,我们同样也有更高和更低的区分。比较一个孩子的视角和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我们承认,成年人的视角具有优越性,因为它更清楚地或更真实地揭示了某些利益、关切、目标和责任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提供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好的判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长大后回过头去读一本书或看一部电影时,我们发现我们能以一种全新的、更富洞见的方式去诠释它。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以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孩子的视角是有偏颇的,而成年人将其包含在了更全面的意识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的视角是完全不成熟的或具有误导性的。相反,我们承认有些孩童般的感受力可以矫正我们成年人养成的习惯。例如,我们羡慕孩子那种对周围小事情的惊奇感,而我们往往在喧嚣的工作日中将其忽略。但小孩视角的这些特征以及它们独特的魅力只有从一个成年人的观点来看才会出现,在此成年人的观点受到了另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和立场的启发。从这种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一个成年人可以阐明从孩子的视角看待事物所具有的洞见以及缺点。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对世界的基本意识的变化以及我们明显的处境,对生活视角做出相同的区分。对世界的某些特定理解比另一些理解更全面。它们使得更深的理解和更好的判断得以可能。
在某种意义上,从一个视角进行判断似乎意味着被局限,甚至无望地被束缚于一个简单的观点之上。我们熟知的一个表达很好地把握住了处境化理解的有限性,“你必须亲自到此才能真正了解”。在这个表述中,我们承认对某些话题的深刻评论看似预设了一种共享的经验,这种经验很难仅仅通过叙述被完全复制。但要是认为只有我们(其他人被排除在外)才能拥有这种从特定视角出发获得的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忽视了这种可能,即通过对那种处境的叙述,我们邀请不在场的其他人通过诉诸自己类似的经验来理解我们叙述的可能。我们因而邀请他们进入到我们的视角内,与此同时通过他们的叙述我们的视角得以扩展。有可能在听到其他人对这种处境的叙述后,我们会修正我们先前对这一处境的刻画。例如我们都熟悉这样的经验,接受他人的劝说以其他人的方式来看待问题,这证明我们的视角是可以被扩展的。正如海德格尔表明的那样,我们对世界、对自身处境或视角的基本经验是以相同的方式被扩展的。由于一个人的视角不是一种主观的立场而体现在一个人的生活中,至少从原则上说其他人是能分享这种视角的。
判断一种“更广阔”或“更全面”的视角的标准不是某种无条件的真理标准,因为那样会破坏视角这个概念。相反,这个标准是由视角自身给定的,通过揭示出先前视角的偏狭之处(而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换言之,我们得知一种视角是“更全面”的,正是因为它澄清了先前的视角,之前我们看不清的东西现在我们能看得清楚了。只有通过从一种较低的视角转换到一种较高的视角,后者包含且取代了前者,较高视角的优越性才得以显现。由于较高的视角包含了较低的视角,且与较低的视角不可分(正如成年人的视角包含了孩子的视角),视角之间的对抗或不相容问题才不会出现。只有在两种完全陌生的观点之间用一种超然的标准断定一种视角比另一种视角“更高”或“更清楚”时,这个问题才会出现。但当我们谈论“更高”和“更低”的生活视角时,我们之所以认为更高的视角“更高”正是因为它包含了“更低”的视角,揭示了更低的视角的优缺点。更高的视角比更低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了它自己。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理解总是回顾性的。我们总是在更广阔的视角内通过重新把握先前的视角,才掌握了它真正的优点。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来临时才展翅飞翔”。*G.W.F.Hegel,Philosophy of Right,trans.T.M.Knox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p.13.
尽管处境化的判断概念暗示着某些视角与另一些视角更高明,但它并不赞同黑格尔的论断即存在一个最高的视角,在此视角内我们获得了绝对的知识。正如黑格尔所表明的,理解的“处境化”特征不仅意味着理解是参与式的或实践性的,而非超然的,而且还意味着理解不可能是完全的。我们需要花点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实践性的理解本身并不暗示着不完全。虽然我们的理解与我们参与其中的生活(黑格尔称之为“伦理实体”)不可分,但至少我们可以获得对这种生活的明晰理解。黑格尔声称他在他的哲学中获得了这种理解。他坚持认为这种理解是处境化的而不是超然的。因为概念的意义只有对那些参与这种生活形式的人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概念也是从这种生活形式中产生的。但对这样一个人(即黑格尔)来说,至少在历史的终结处,哲学论断将完全清晰、完整地表达这种生活形式。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因此只是证实了我所说的处境化理解的一个维度。只要它的可理解性依赖于实际的生活,绝对知识就是处境化的。但它同时也是完整、完全清晰的,并在此意义上摆脱了偏见。
根据我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出的处境化理解的概念,即便我们最广阔最清晰的视角仍然是部分的和被遮蔽的。用正面的术语来表述,我们的视角从未固定,而总是向进一步的诠释开放。这种开放性应该与理解的开创性或“投射”的维度相联系——任何的理解行为都将重新塑造它得以产生的那个视角。一个视角的偏私性与其实践特征一起,突出了一种视角即一种偏见的意思。
我们可以在伽达默尔那里看到,他明确地将“视角”、“处境”与“偏见”联系在一起。通过援引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伽达默尔得出这个看法,“所有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种偏见(Vorurteil)”。*Gadamer,Truth and Method,p.272.但他说,偏见并非令人遗憾的限制。因为有一些偏见或我们生活环境的某些方面能够促成理解。如他所说,它们可以“令我们获得知识”。*Ibid., 280.我将在第四章表明这一令人费解的说法是合理的。
伽达默尔将在世存在与“偏见”相联系的做法是想要重建判断的来源,因为在启蒙运动中偏见变得不再可信。他主要的目标是去表明受到我们的传统、实践、承诺以及关注影响的生活环境或“视域”是如何促成人类科学中的理解的。他尤其批评那种启蒙时期出现的对历史进行超然研究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伽达默尔称之为“历史主义”,正确的研究方法是从我们的利益、关注和真理概念中抽身出来,以避免将当代的观点强加给过去。历史主义教导我们通过摆脱自身的视角,重建一件历史作品出现的语境,来发现它的“原初”意义。伽达默尔却论证说当代的偏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具有启发性的,从而挑战了历史主义。尽管有些偏见可能会阻碍我们对一件历史作品的理解,但另一些却可能澄清这种理解。
我对伽达默尔的诠释从他对历史主义的大致批评开始。我的目标是指出处境化的理解概念将如何影响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伽达默尔的洞见是处于一个视域中意味着一个人的“现在”总是在运动中。它不是一系列固定不变的“观点和评价”,而是一些接受质疑的综合意识。*Ibid., 305.因此,它不能与过去完全区分开。就像我们自己的同一性是接受质疑的,我们现在与过去不同的程度也是如此。同样,就像过去是可以被理解的,它从未真正走远。在此意义上,过去和现在是属于彼此的。这种归属感暗示着我们历史传统中任何面向的意义都可以在与现在的关联中被重新发掘。所以那种试图通过摆脱我们当今的视角来获得无偏见的历史知识的观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
在大概厘清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后,我会对当今的偏见如何促成历史的理解提供一个具体的分析。伽达默尔独特的贡献使得他的作品对于观念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及那些致力于诠释思想传统的学者来说十分重要。为了突出这种相关性,我将应用他的偏见理论来诠释柏拉图的《理想国》。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某种当代的偏见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柏拉图的“诗学”(《理想国》,第十卷)概念。最后,我将通过仔细地阅读柏拉图有关意见与知识的教诲(《理想国》,第五卷),展示如何克服某种误导人的偏见。我的目标是去澄清伽达默尔关于偏见如何起作用的论述。这一挑战的核心任务是去区分能够启发人的偏见与歪曲人的偏见。我还希望能表明,诠释如何包含了一种知识上的双重收获:对文本的更好理解以及对我们自身的更好理解。
伽达默尔认为过去和现在属于彼此,这种建议激发我在对处境化理解的叙述中采取一个转向。在第五章中,我从二十世纪的德国转向了古希腊,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转向了亚里士多德。尽管亚里士多德看上去距离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很远,但实际上他给出了对他们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较早和强有力的表达。事实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受到亚里士多德很深的影响。他们尤其将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论述看作对知识的超然理想的纠正。追随他们的引领,我尝试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恢复一种关于如何可以从偏见中获得判断的论述。
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严格来说,亚里士多德从未使用过“偏见”或“处境”这样的概念。这两个词都是在现代产生的。“处境化理解”的意义取决于它与“超然”理想的对比,而亚里士多德并不熟悉什么是超然判断的理想。他的著作要早于培根、笛卡尔、斯密和康德的著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不能说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处境化的”理解概念——至少不能用这些术语来表达。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仍然以他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此类概念。它隐含在其他概念中。
最著名的是phronesis或实践智慧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发展了这个概念。*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ed.Jeff rey Henderson,trans.H.Rackha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bk.6.实践智慧这个概念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即道德判断涉及性格倾向(hexis),它受到一个人成长经历(paideia)、习惯(ethos)以及实践(praxis)的影响。因此道德判断的基础不可化约为抽象的原则。它无法通过书本学习或单纯的指导来获得。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处境化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以两种关键方式澄清了处境化的理解概念。首先,他对比了实践智慧与工艺知识(技术),突出了实践理性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性理论”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二者都涉及“实践”——因为它们都关涉一种行为而非沉思,实践智慧是处境化的,工艺知识则不是。工艺知识涉及对产品形式(eidos)的理论把握,随后再将这种知识应用于一些特定的材料,而实践智慧需要对行为处境有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包含着一定的性格倾向(hexis):平衡相竞争的事物与承诺的能力,而这又受到一个人的习惯和成长经历的影响。其次,亚里士多德强调处境化理解与盲目的习惯之间的差别。他表明,尽管道德判断受到习惯和成长经历的影响,但它仍然包含了我们自身的理解和能动性。我们通过判断这种活动而塑造我们的性格。如果能坚持好好地判断和做有美德的行为,我们就能发展出好的性格,这种性格会在第一时间促成我们的判断。*品格的获得因此是循环的。我们通过判断得好获得了好的品格,而只有当我们已经拥有了好的品格我们才能判断得好。亚里士多德看来想要解释这个迷。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通过习惯、通过重复有美德的行为而获得美德的意思。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习惯不是消极地重复完成事情的“方式”。每一个“重复的”行为都包含估量一个与之前相似却不同的处境。
因此第五章一开始先通过一位先驱者来阐明处境化的理解概念,然后再阐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二十世纪的诠释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一些核心部分,否则这些部分的意思可能仍然像个谜。这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自然与习惯的关系,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然正义会发生变化但仍是一样的。通过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理解这些难题,我希望我可以进一步表明,一种特定的“当代”偏见如何能揭示过去的真理。
在最后一章第六章中,我将提出处境化理解对于政治论证的意义。尤其是,偏见是判断的必要特征这一论断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普遍的假设,即诉诸人的特殊激情、利益和承诺而非其理性的政治修辞是一种不合法的论证形式。布莱恩·加尔斯腾(Bryan Garsten)很好地总结了对修辞的怀疑,他注意到了这种怀疑对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政治理论家往往关注论证的理性对话而不是修辞的激情交流。尽管事实上政治家们没有放弃劝说,但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技艺。他们明白,当他们听到一个被称为“修辞”的论证时,这个论证要么被诋毁为是操纵性的,要么被看作是肤浅的。今天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对修辞言论的主流意见是它是政治的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以及对民主协商的一种威胁。*Garsten,Saving Persuasion, p.3.
不足为怪,人们常常将“修辞”这个概念与“偏见”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康德那儿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指责说修辞绕开了人们的理性而基于人们的偏见起作用。他将修辞定义为一种“哄骗人且为了获得利益而使人带有偏见”的技艺。*Kant,Critique of Judgment, §53,p.192.与他对偏见的批评一致,康德论证说修辞会阻碍自主性。他写道,“在关键时刻修辞致使人们像机器一样做出判断,而在平静的反思下这些判断将失去所有的分量”。*Ibid.,p.193.
毫无疑问,当今天我们说“这只是修辞”,意思是它是肤浅的,迎合了人们非理性的欲望。将修辞与迎合联系在一起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将修辞与那时盛行的烹饪术相比较。他认为两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不关心他们的善。*Plato,Gorgias,ed.Jeff rey Henders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465a.但是,诉诸人的激情、性格倾向和忠诚的修辞并不仅仅是反对理性论证的、迎合人的欲望的操纵术。相反,它是一种在人们的视角内进行推理的形式,一种参与他们处境化判断的形式。
通过捍卫这种意义上的修辞概念,我发展了加尔斯腾在《挽救劝说:对修辞和判断的捍卫》一书中的观点。加尔斯腾论证说劝说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人们不光诉诸理性而且还诉诸他们的激情甚至偏见从而改变他们的看法——是一种值得捍卫的政治模式。他接着说,劝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要求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进行论证,而不是认定如果他们足够理性一定会采纳我们的观点”。*Garsten,Saving Persuasion,p.3.我想要通过我捍卫的偏见概念来发展他的这一论点。如果我们将偏见看作是理性的一个面向,那么我们也会重新看待修辞。我们将承认它是定义我们与世界关系的参与式理解的一个有力例证,而不是一种阻碍人们进行超然判断的有害模式。
为了揭示作为处境化理解和判断的典范的修辞,我考察了美国历史上几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演说。我将表明,这些演说不仅从他们援引的原则获得道德力量和劝说的效果,更根本的是他们澄清并诉诸其听众的生活视角。即使是那些看上去仅仅依赖抽象的平等和正义原则的演说,也依赖于人们已有的令这些原则可被人理解的偏见。
通过考察政治修辞,我们获得了对民主政治以及何谓从生活视角内进行推理的更深理解。我们尤其看到了与这种推理概念相联系的能动性概念。我们历史上伟大的修辞时刻实现了劝说的可能,这说明我们从未受制于一个固定的立场。关于我们是如何定义界定我们的视角的,劝说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