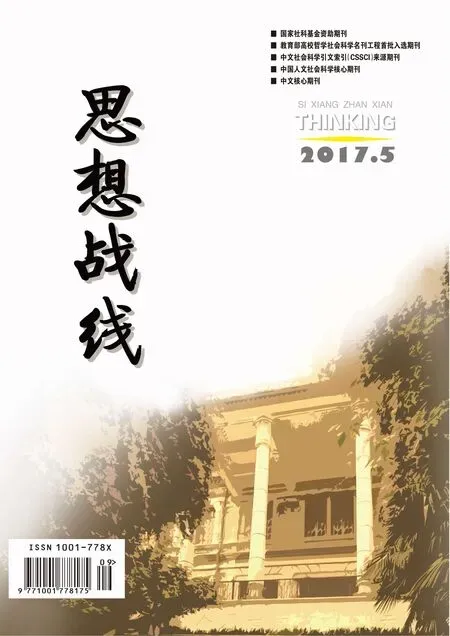另类的“小皇帝”:福利院儿童的零食消费和抚育政治
2017-04-11
另类的“小皇帝”:福利院儿童的零食消费和抚育政治
钱霖亮
儿童福利院中孤儿们的零食消费是一个不太受人关注的行为。利用民族志的方式,将零食消费作为深入描述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永江福利院孤儿们日常生活和经历的手段,展示代表国家的福利院官方机构、保育人员和慈善人士在孤儿养育问题上的互动,也表现出孩子们自身透过食品消费展示出来的能动性。福利院类似独生子女“小皇帝”的物质生活状态和习性,会受到抚育政治的微观影响,在机构养育的儿童身上也会表现出来。进一步省思国家政策、市场化和社会变迁在不同类型儿童身上留下的文化烙印,实现与当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儿童研究进行对话。
福利院;孤儿;零食消费;抚育政治;道德社会化
一、引 言
2011年6月的一天,永江福利院*此福利院为笔者的田野调查点,按学术惯例对其名称进行了处理,这样的处理包括文中提到的人名。来了两位志愿者,给孤儿们送来了一袋炸鸡翅。看到他们手上拎着食物,孩子们纷纷聚拢过来。鸡翅刚分到手,孩子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可很快,就有孩子把才吃了几口的鸡翅扔进垃圾桶。保育员王阿姨见状指责他们不爱惜食物。有个孩子反驳到:“这个鸡翅不正宗,不是肯德基的味道。”*材料来源于田野调查,以下类似引用文字,不再一一注出。志愿者们露出了尴尬的表情。王阿姨笑着告诉他们不要介意,现在福利院的小孩嘴巴都叼得很,因为经常有热心人士送来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食物,他们吃习惯了,反而觉得一般的炸鸡不好吃。*肯德基和麦当劳等西式快餐在中国儿童中一度非常流行,见阎云翔《麦当劳在北京:美国文化的本土化》,载詹姆斯·华生《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祝鹏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罗立波《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志愿者很惊讶,说还以为福利院的孩子生活很艰苦。王阿姨说,家里小孩吃的零食基本上福利院里也都有,许多来访的热心人士会捐赠食品,福利院本身也会买一些。王阿姨抚摸着一个胖嘟嘟小男孩的头说,因为捐赠来的零食太多,孩子们吃得太多,像这个小胖子,刚来的时候因为早产非常瘦弱,但现在都开始担心他患上肥胖症了。*对比中国家长对独生子女肥胖症的忧虑,可参见[美]乔治娅·古尔丹《丰富的悖论:中国婴幼儿养育方式的变迁》,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以往公众对福利院孤儿的印象,多认为他们是一群“可怜人”,大众化的表述也着重表现这些儿童被亲生父母遗弃后的悲惨命运。*关于孤儿院儿童情况的讨论参见Linliang Qian,“Consuming‘the Unfortunate’:The Violence of Philanthropy i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Run Orphanage”,Dialectical Anthropology,vol.38,no.3,2014。一般所谓的福利院儿童/孤儿,既包括生父母死亡的儿童,也包括被生父母遗弃的弃婴儿。永江福利院绝大多数在院儿童属于后一类型。在一些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眼里,这些孩子在国有福利机构当中的生活同样是食不果腹、饱尝艰辛的。*Human Rights Watch Asia,Death by Default:A Policy of Fatal Neglect in China’s State Orphanag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如同上文中两位志愿者,食物缺乏和营养不良,已经成为许多来访永江福利院的慈善人士对机构养育儿童生活的刻板印象,以至于当他们发现实际状况并非如此时倍感诧异。然而学界却鲜有细致探讨福利院孤儿这一群体实际生活的研究。*一些学者曾对中国福利院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较少涉及孤儿们的日常生活。参见尚晓援《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保护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尚晓援《中国孤儿状况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也有学者曾对福利院中保育人员的孤儿养育实践做了一些讨论。参见钱霖亮《建构保育员母亲身份的挣扎:中国福利院儿童照顾者的情感劳动》,《台湾人类学刊》2013年总第11期第2卷。但还未有专门的研究讨论孤儿们的饮食消费状况。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迄今仍集中于讨论家庭儿童的状况,较少涉及非家庭养育儿童的生活。尤其针对家庭当中的独生子女,已有海外的中国研究着重挖掘其作为备受溺爱“小皇帝”的生活状态和习性(譬如挑剔、攀比、恃宠而骄和营养过剩等等),仿佛这一特征为此群体所独有。*海外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研究最近作品包括Vanessa Fong,Only Hope: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Teresa Kuan,Love’s Uncertainty: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Orna Naftali,Children,Rights and Modernity in China:Raising Self-Governing Citizen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4。在中国国内,不少学者已经对这种将独生子女状况问题化的讨论提出质疑,譬如风笑天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基本一致。但他同时也指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某些方面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他们通常可能比非独生子女更“懒惰”“动手能力差”“责任心差”。将家庭养育的独生子女群体作为机构养育儿童的参照对象,笔者所持的立场是既不将独生子女状况问题化,但也部分同意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这一群体的一些性格特性表述。参见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从零食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深入描述在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永江福利院孤儿们的日常生活和经历,展示代表国家的福利院官方机构、保育人员和慈善人士在孤儿养育问题上的互动,以及孩子们自己透过食品消费展示出来的能动性(agency),笔者意图揭示,类似独生子女“小皇帝”的物质生活状态(至少在零食消费的层面上)和习性,同样也可以在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机构养育儿童身上看到。从机构养育儿童和家庭养育儿童的生活习性中寻找共性,这将有助我们把机构养育儿童的生存和成长状态作为一面镜子,进而省思国家政策(譬如终结于2014年的一胎政策)、市场化和社会变迁在不同类型儿童身上留下的文化烙印。
当代中国的儿童机构养育,一般被认为是计划生育的副产品。有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父母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才将二胎子女遗弃。尤其在农村地区,政府的“一个半”胎政策(即第一胎是儿子便不允许再生,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允许再生一胎,但不论男女此后都不可再生育),使得许多深受“重男轻女”文化影响的农民将二胎女儿遗弃,以保留配额再生一个男孩。也因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福利院里,占绝大多数的弃婴都是健康女孩。*Susan Greenhalgh and Edwin Winckler,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Kay Johnson,China’s Hidden Children:Abandonment,Adoption,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Child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大约在2000年以后,进入福利院的弃婴中,健康女孩的比重开始下降,病残儿童(不分性别)的比重开始显著上升。*尚晓援:《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保护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5页。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福利院也是类似的情况,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在2002年以后重病和残疾弃婴儿数量激增。按照他们的说法,病残儿童的增多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婚检和产检放松导致先天缺陷的胎儿不易被发现,出生后由于家庭无力承担医疗和抚养费用而被父母遗弃;也有父母可能是对政策法律不熟悉,以遗弃的方式生育二胎——按政策,第一个孩子有导致其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生理残疾,其家庭可以在通过医学鉴定后申请生育二胎。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许多有病残儿童的家庭由于其病残程度未必能获得二胎准生证。与此同时,不少父母在文化上也不能容忍包括唇腭裂等在内的轻中度残疾症状,迷信地认为这是对自身的某种报应,不仅孩子的长相不堪入目,也会给家庭带来厄运。*Linliang Qian,“Everyday Religiosity in the State Sphere:Folk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a Chinese State-run Orphanage”,China Information,vol.30,no.1,2016.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压力汇集在一起,使得这些病残儿童遭到父母的遗弃,在进入福利院后成为中国社会中另类的人群。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特殊,人生际遇在很多方面也与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截然不同,但在同一个社会大环境中,国家政策和社会变迁的力量会同时作用于这些不同类型的群体,在某些方面他们仍具有相似性。对这些相似性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家力量、社会和市场力量(譬如慈善组织和个体,以及一些做慈善的企业、商会)如何在福利体制转型时期重塑个体的人生经验和能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与计划经济紧密结合的。对孤残儿童这类社会弱势群体,国家包揽了其从成长、教育到就业的所有职责。时至今日,全国大多数的儿童福利院在编制上,仍是全额拨款的国家事业单位,福利院儿童在政策上享受国家最低生活补贴。*尚晓援,李香萍:《永不成年?国家养育的大龄孤儿如何获得经济独立》,《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推行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政策,其主旨在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引入社会和市场力量为公众提供福利资源。这其中,筹资渠道的市场化和政府投资的缩水,使得某些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实质乃是私有化。*Linda Wong,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8.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重新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对儿童福利机构建设的投资和孤残儿童养育的投入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逐渐兴起的慈善之风,也对孤残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照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笔者将这些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救助福利院儿童的活动及其社会政治性的意涵,以及保育人员对儿童的具体养育活动和它背后的权力关系,视为抚育政治(politics of care)的范畴。在这里,抚育(care)的内涵,既包括微观的日常照料实践(daily care practices),也包括宏观(例如救济政策的制定)、中观(例如救济政策的执行)乃至微观(例如具体的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人道主义的生命政治部署(humanitarian and biopolitical deployment of care)。*Elana Bush,“Anthropology of Aging and Car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4,2015.以零食消费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抚育政治的运作和社会政治意义的创造,笔者希望能够展现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在福利院具体的空间场景中如何施展权力,同时这种权力的施展又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生活习性。
正如前文所述,已有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儿童的日常生活来观察社会与文化变迁(譬如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与此同时,心理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作品也开始试图透过儿童的生活习性(比如食物和玩具分享)来考察他们的道德经历(moral experience),以此与生物性主导的发展心理学进行对话。这些学者认为,儿童的习性并不全然是生理本然,而是特定文化塑造的结果,与儿童养育的具体实践密不可分。*Jean Briggs,Inuit Morality Play:The Emotional Education of a Three-Year-O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Naomi Quinn,“Universals of Child Rearing,”Anthropological Theory,vol.5,no.4,2005.针对中国的独生子女群体,最新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国家长和教师的道德化教育理念与儿童实际的功利化习性之间的悬殊差距,而这一差距恰恰根植于成人自身的功利行为。*Jing Xu,“Becoming a Moral Child amidst China’s Moral Crisis:Preschool Discourse and Practices of Sharing in Shanghai”,Ethos,vol.42,no.2,2014.这些研究表明,儿童的生活习性不仅能够反映其所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受到养育者育儿实践的影响,也能在这环境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不全然为成人的意志所主导。尽管如此,这些研究的对象选择还是集中于身体及智力健全的儿童,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病残儿童,尤其是智力损伤的儿童,是否也有相似的道德和习性塑造经历?尤其在面对发展心理学关于残障会影响到儿童的智力和身体发育的强势论断时。通过提供一个详尽的个案,笔者试图说明:尽管受到其病残状态的限制,这些儿童仍旧具有这样的经历,并在这些经历的体验中受到环境和成人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亦展示出自身的能动性。
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是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永江福利院。永江市是该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多年位居所在省的前列。永江福利院是该市境內唯一一家由政府开办的收养弃婴孤儿的社会福利机构,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2011年3月在院儿童80人,约有70%是3岁以下婴幼儿,约95%为病残儿童,病残类型多样,包括脑瘫、唐氏综合症、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所有未被领养滞留在福利院中的大龄儿童,皆有智力残疾或肢体缺陷。该福利院有保育员6人,皆为女性,年龄介于32至55岁之间,都是永江市本地农村居民。笔者于2011年3月经福利院领导批准,在该院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此后亦有数次回访,了解该院的机构运作和福利院儿童的日常生活。
二、福利院儿童饮食的变迁
和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永江福利院儿童的饮食结构在过去的2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景军曾经讨论过中国家庭养育儿童饮食结构的变迁,这与永江福利院儿童的情况颇为相似。参见景 军《引言:当代中国的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iv-vii页。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院到90年代末,该院大龄儿童的饮食结构以谷物和蔬菜为主(婴幼儿则是奶粉和米粉),食堂每周只提供三到四餐的荤菜,一日只有三顿正餐,基本没有点心可吃。根据已退休和在职时间较长的职工们回忆,虽然福利院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由于建制小,没有许多额外收入,单位食堂每餐供应的食品种类十分有限,导致很多孩子营养不良。也因此,当年有不少本地家庭(以及后来的外国家庭)来领养时,都嫌这里的孩子个子小,发育不好。
按院领导的说法,虽然在福利院建院之初的设计中,就有提及要确保儿童的食品供应和营养摄入,但由于经费有限,只能给孩子们维持一个“吃饱”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儿童福利投入的加大,加之涉外送养带来国外领养家庭的捐款,永江福利院有了更充裕的资金用以提高在院儿童的生活品质。从那时开始,福利院儿童的食谱里基本餐餐有肉了,大龄儿童有零食吃,婴幼儿也有营养品。但大约到2006年前后,由于全国多地爆出福利院领导职工挪用涉外领养捐款作小金库的丑闻,中央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对各地福利院财政的监管。这之后,大额捐款开始较少用于儿童食品的购买,转而主要用于病残儿童的手术和康复,以及福利院基础设施的兴建和维修。*在实际操作中,福利院领导还是会做出区分,大额捐款上缴财政局和民政局共同管理的福利院账户;鼓励小额捐款者用捐款直接购买(或在现金入库登记后由工作人员代买)福利院儿童必需或急需的物资,包括一次性纸尿布/裤、儿童洗漱用品和零食等。所谓小额捐款,大约是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尽管如此,永江福利院儿童包括食品供应在内的生活品质并未下降。近10年来,每年政府的儿童养护补助经费都在增加。与此同时,还有持续增长的慈善捐赠。中央制定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使地方福利院对捐赠者大开方便之门,以往封闭的大门如今随时欢迎来访的慈善人士。在笔者调查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来访的捐赠者和志愿者,周末和节假日人数更是剧增。2011年儿童节当天,统计的来访人数就超过了150人。一位老职工告诉笔者,多年以前建院的老院长是乡镇领导调任而来的,有很强的“官本位”,觉得福利院是国家全额拨款的单位,对私人捐赠不屑一顾。“如今的情况就大不同了,你看我们现在的院长,对待慈善人士可热情了。”院长的公关工作卓有成效,2010年全年的捐赠总额将近120万元。而捐赠物资中,最大宗的是各式的零食。这些食品极大地丰富了福利院儿童的饮食种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孩子的饮食品味。以下笔者将着重介绍当前永江福利院大约3岁及以上年龄儿童的零食消费实践。
三、与零食相伴的童年
目前永江福利院儿童的饮食安排,除了正餐以外,还有每天上午(10∶00)和下午(14∶00)两次点心时间。点心的来源,主要是慈善捐赠的零食,此外也有福利院自行采购的水果等。由于正餐多由食堂按计划采购和准备,福利院儿童在正餐饮食选择方面缺乏话语权。与此不同,他们在吃点心时受到较少的限制,也展示出自己更多的能动性。
和其他孩子一样,许多福利院儿童非常爱吃零食,每到点心时间,就会自觉地围绕餐桌等待保育员分发零食,病残儿童也不例外,不少智障儿童也记得这个时间,一到时间,即使是瘸腿的儿童也会飞奔到餐桌边。在吃零食时,尽管不少孩子(尤其年龄较小的和智力损伤较为严重的)似乎并不懂得区分,只要有的吃就行,但也有孩子像文章开篇所述的一样挑剔。除了讲求口味,这些大龄儿童也特别注意零食包装是否新颖有趣。比如碰到印有喜羊羊等卡通形象的,有个孩子就经常舍不得吃,藏在他床底下的一个储物盒里,平时还经常拿出来向其他小孩炫耀。*罗立波曾经讨论过20世纪90年代电视动画形象对中国儿童零食消费的影响。永江福利院的孩子平常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动画片,并且非常喜爱里面的动画形象。参见罗立波《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这就激起了其他孩子的攀比和嫉妒,争抢和偷窃零食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并接受大量的慈善捐赠,永江福利院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来购买儿童所需的日常用品,包括零食。保育员们购买零食时,也知道哪些是儿童特别钟爱的。因为时常被保育员和慈善人士询问喜欢吃什么,那些能说话儿童便开始领会到“说得出来的东西就有的吃”的道理。笔者常常听到,这些儿童时不时地跟保育员唠叨想吃什么零食,或者什么零食好像没有了;在面对慈善人士的询问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不会说话但仍能辨明喜好的孩子,也能够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选择。
对零食的着迷,不仅关系福利院儿童的个人兴趣和爱好,有时它甚至成为某些儿童对福利院依恋感情的一部分,零食在福利院儿童人生体验中的重要性也因此得到提升。2011年5月,由于入院弃婴人数的增加,给保育员造成了沉重的工作负担,福利院领导决定将一批大龄智障儿童送到农村家庭寄养。其中有一名叫晨晓的6岁女孩,属于“中度智障”儿童。在下乡前的几天,她的情绪似乎不太好,会莫名地大哭大叫。因为她缺乏语言能力,我们无法得知她情绪失控的缘由。一天午休后,她不知从哪找来一根绳子绑住了自己的脖子,自己勒自己。保育员们认为,是她知道自己要被送到农村寄养,想不开就用绳子上吊自杀。尽管给出这样的解释,她们仍很疑惑:晨晓之前并没有家庭寄养的经历,她怎么能预见到寄养生活的好坏?到了下乡那天,正赶上点心时间,晨晓吃完后还偷偷抓了两把别人的零食塞在口袋里。负责照顾她的朱阿姨纳闷了,说她平时吃零食并不贪心,怎么今天吃完还要拿别人的?朱阿姨的妈妈是已退休的保育员,晨晓后来就寄养在她家里。在一次回家后朱阿姨告诉笔者,她终于搞清楚当初晨晓为什么要自杀了。她妈妈有时会带小孩在村里走街串巷、访问邻里,有些乡亲见有小孩来就拿出儿童食品给他们吃。朱阿姨形容晨晓的吃相好像是饿了几辈子,见到零食就狼吞虎咽,吃完走了还要捎上一点;路过村里的小卖部时,也是一直盯着零食看,朱阿姨由此认为,晨晓当初行为反常的原因,就是她不愿意去一个可能没有零食吃的地方。
四、儿童饮食、社会关系与抚育政治
作为一项饮食人类学研究,笔者在这里不仅试图向读者介绍永江福利院儿童的零食消费实践,也希望能够展示围绕零食展开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机制。人类学家景军曾经提示后学,饮食人类学不仅关注人们吃什么、怎么吃,同时也关注吃这一行为在特定社会情境当中的文化意涵,以及塑造这一行为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参见景 军《引言:当代中国的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xii-xvi页。作为收养和管理弃婴、孤儿的政府机构,中国福利院的存在和运作本身,即展现出国家对这些失去家庭儿童成长过程的干预,这一直被官方机构和媒体阐释为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胡 键,岳 宗:《每个孩子都应拥有幸福快乐童年》,《南方日报》2009年5月31日,第1版;孙承斌,李 斌:《胡锦涛在北京市考察少年儿童工作时强调,让每一个孩子都在祖国的蓝天下健康幸福成长》,《人民日报》2006年6月1日。食品消费作为福利院儿童抚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备受重视。由国家民政部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院运作指导文件《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即有条目规定儿童的膳食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中国社会福利网,2001年2月6日,http://shfl.mca.gov.cn/article/bzgf/etfl/200807/20080700018266.shtml。此外,该部门也出台了《民政部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每人每月1 000元的福利院儿童最低养育标准,伙食费在所有项目中占过半比例。文件最后的附表,更列出了食品及其他项目详尽的支出参照标准,食品种类中甚至包括了碳酸饮料、冰棍、冰淇淋等零食。这些政策追求的目标,乃是要“维护孤儿、弃婴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我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民政部官方网站,2009年7月9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shflhshsw/200907/20090700032833.shtml。由此可见,这些儿童福利政策在积极提高福利院儿童生活水平的同时,亦有其更广泛的政治、社会效益上的诉求。在政策落实的层面,永江福利院虽然没有专门的文件记载儿童食品消费的项目,但儿童饮食一直被视为儿童抚养工作重要的环节。保证儿童食品的安全、卫生和营养被列入福利院的基本管理制度,工作人员也被要求“严格按照民政部颁发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开展科学护理工作”。*永江福利院:《规章制度及岗位职责》(内部资料),2005年。如果说,国家对家庭当中儿童成长的干预,包括对他们食品消费的干预,意在支撑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合法性,塑造其自身现代化、富有同情心的政府形象,*参见景 军《引言:当代中国的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xii-xvi页。同样的政治心态和合法性诉求,大概也能够在上述这些针对福利院儿童的政策措施中寻找到痕迹。
除了国家和福利院儿童的关系以外,笔者同样关注在福利院内微观的社会联系和互动,并将它们视为抚育政治生产社会与文化意义的场域。以下部分将依次讨论福利院儿童─保育员、儿童─慈善人士,以及儿童之间围绕零食展开的互动。
(一)儿童和保育员
作为主要的照顾人,永江福利院的6位保育员在福利院儿童的饮食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下文将主要关注其作为零食分配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由于保育员是受雇于福利院这个国家单位的,她们实际上是作为国家代理人来具体履行抚育职责。
不同于中西方的许多家庭、学校乃至孤儿院,永江福利院儿童就餐(不论正餐还是点心)时并没有一套很正式的餐桌礼仪,*Paul Daniel and Ulla Gustafsson,“School Lunches:Children’s Services or Children’s Spaces?”,Children’s Geographies,vol.8,no.3,2010;Nika Dorrer,Ian McIntosh,Samantha Punch,and Ruth Emond,“Children and Food Practices in Residential Care:Ambivalence in the ‘Institutional’ Home,”Children’s Geographies,vol.8,no.3,2010;Susan Grieshaber,“Mealtime Rituals: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ltime Rule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8,no.4,1997;Joseph Tobin,David Wu and Dana Davidson,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Japan,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保育员们对孩子的饮食行为放任不管。进餐时大吵大闹、抢夺他人食物的孩子,必定会受到惩罚。有的孩子有挑食习惯,如果事先没有告知,事后又耍赖不吃分配好的食物,就有可能惹怒保育员。这些导致惩罚的状况,虽然都与食物分配有关,但追根究底,是因为触犯了保育员的权威,挑战了她们在儿童饮食安排上的分配权和就餐秩序的管理权。也正因为福利院的机构制度和作为成人的优势,赋予了保育员上述权力,她们转而可以在实际抚养过程中利用这些权力,对福利院儿童进行管理。食物能被用作管理工具,在具体语境中,食物的工具性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它既可以用来表达关爱,亦可以用来施展控制。
用食物来表达关爱这种方式,似乎在中国成人和儿童的互动中非常常见,并且被认为是中国父母宠爱独生子女的重要表现之一。*Vanessa Fong,Only Hope: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尽管不是亲生子女,永江福利院的保育员也常常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宠爱的儿童。4岁的脑瘫患儿国芳是张阿姨最宠爱的孩子,因为“张妈妈”的宠爱,她成为福利院里名副其实的小霸王,一有不如意就哭闹。张阿姨对她百依百顺,在食物分配上也是如此,平时分零食时就会多给国芳一点;在非点心时间,只要是国芳想吃零食,张阿姨也会拿给她,自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她也时常会拿给国芳吃。其他保育员私下认为,过分的宠爱让国芳觉得有相对于其他儿童的特权:其他保育员分食物时她就要多拿一份,别的孩子的食物只要她想吃就是她的,不给她就抢,抢不过就找张阿姨。而张阿姨偶尔还会偏袒、纵容她,有时甚至不惜和其他保育员发生冲突。后来国芳被送去农村家庭寄养,张阿姨依旧对她牵肠挂肚。就在笔者即将结束田野调查,去寄养家庭做最后的探访之际,张阿姨买了许多零食,在笔者出发当天一早又起床煮了一锅花生,再三叮嘱笔者一定要亲手喂给国芳吃。
张阿姨的例子,揭示了作为纽带的食物是如何连接福利院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的。尽管如此,食物分配和它所牵扯出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温情脉脉。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理论视角出发,许多研究者将家庭、学校和孤儿院的饮食安排阐释为规训机制,将成人照顾者和儿童之间的互动理解成压迫者和反抗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Jo Pike,“Foucault, Space and Primary School Dining Rooms”,Children’s Geographies,vol.6,no.4,2008;Samantha Punch and Ian McIntosh,“‘Food is a Funny Thing within Residential Child Care’: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Food Practices in Residential Care”,Childhood,vol.21,no.1,2014.永江福利院部分例子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讨论。比如,一次午休后,方阿姨拒绝给3个大龄儿童发点心,因为他们3人在午休时不睡觉,还把其他人吵醒了。其中两个孩子在阿姨的斥责声中沉默地靠着墙壁站着。但5岁的小雨对不能吃点心感到非常不满,跑去把分给其他小孩的饼干都拍碎了。这一举动惹恼了方阿姨,她把小雨拉到房间里处罚、训斥,然后让他站在餐桌边看其他孩子吃点心。之后她又教育了其他两个孩子,鉴于他们的认错态度比较好,方阿姨在小雨面前给了这两个孩子1人1瓶牛奶。看到小雨一脸不服气的样子,她便故意刺激他,说所有人都有点心吃,就他没有,以后他再这么做,不听话,就永远没有点心吃。从福柯的视角来看,方阿姨的零食分配显然可以理解为一种规训机制,而零食本身也变成了管控工具。它可以用来惩罚午休不睡觉且打扰到他人的孩子,同时也是对下次再犯的警告。然而诚如福柯所总结的,在权力的场域里有压制便有反抗,但小雨的行为招来了更严厉的惩罚。其他两个孩子是规训成功的例子,既是对他们的服从(或至少不反抗)的奖赏,也出于向小雨进一步施展规训的需要,方阿姨在再次警告之后给了他们一些点心。通过食物分配及其他方式来施展权力,树立作为成人保育员的权威,方阿姨在这个过程中维护了她在福利院儿童身上实施的管理秩序。
(二)儿童和慈善人士
中国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和中国社会中兴起的慈善活动,给儿童福利院带来了众多的捐赠人和志愿者。这些慈善人士也常常以给零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福利院儿童的关爱。在永江福利院,包括零食在内的捐赠品,都是慈善人士“献爱心”的载体(有时捐赠的食物直接被称作“爱心食品”)。也因为捐赠的对象是儿童,大部分慈善人士在购买捐赠品时,倾向于购买那些标明或者在大众观念中专门为儿童生产的食品(譬如产品包装上印有卡通图案,广告中有儿童或卡通形象等等)。按一些学者的说法,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已经催生出庞大的儿童食品生产体系。*参见景 军《引言:当代中国的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载景 军《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钱霖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vi页,第xix-xxi页。这个体系的产品,不仅通过慈善人士的消费和捐赠进入福利院,有时工厂和经销商也会直接到院内进行献爱心活动。这种供应链极大地丰富了永江福利院内的零食储备,甚至很多时候保质期较短的食品不得不浪费掉。该院的保育员都是本地农村经济条件一般的居民,笔者常听她们感慨,福利院里有那么多吃不完而过期扔掉的食品,实在是太奢侈了。按她们的说法,永江福利院的饮食条件,虽然可能比不上城里的富裕家庭,但比许多本地农村家庭要好得多,更不要说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村了。
这些“爱心食品”在物质上满足福利院儿童需求的同时,在社会文化上也有其重要的功能。根据笔者的观察,食物在慈善人士和福利院儿童日常互动的过程中,也作为两者建立互信关系的手段而存在。许多慈善人士来福利院时都会带一些零食,在选定一个具体的“献爱心”对象后,把零食喂给他们吃。这个过程可能是慈善人士单向的选择,一般长相可爱的孩子总是更受青睐。更多时候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因为零食对大多数孩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龄儿童会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婴儿床里会吃零食的幼儿也会向他们招手微笑。吃了零食的孩子似乎能够体会到食物所承载的感情,对食物的馈赠者产生亲昵感,愿意和慈善人士一起互动做游戏。有些经常来献爱心的人士,感受到零食可以帮助成人与福利院儿童建立起互信关系,于是将它作为一项交流沟通的技巧传授给新来的人,告诉他们“智障儿童和普通孩子一样,只要有吃的就会和你很亲密”。在这个以零食为媒介建立起来的沟通互信组合里,成人有意识的策略固然具有主导性,但孩子的兴趣和习性也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影响力。见多了分发零食的慈善人士,经历了几次跟着他们就有零食吃的事件后,有的孩子也会有意识地这么做。在田野调查的后期,每逢有慈善人士来访,笔者总会看到有两三个大龄儿童围在门口,殷勤地帮助慈善人士拿捐赠品,然后偷偷摸摸地打开袋子和箱子,来看里面的东西,有零食就会顺手拿一点。开始发零食时,他们又会选择站在离慈善人士最近的位置,以便获得优先选择权或者更多的食品。而挑剔的孩子甚至还会撒娇或者发脾气,拒绝慈善人士给他(她)不喜欢的零食,执意选择他(她)爱吃的。*富晓星曾经讨论志愿者与受助流动儿童之间长期的互动,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演进发生变化。见富晓星《互为中心: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建构》,《青年研究》2015年第6期。来永江福利院献爱心的慈善人士很多在时间安排上并不固定,不少人只是一次性的捐赠。即使是那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访的志愿者,笔者也没有发现福利院儿童对他们的态度有明显的历时性差异。解释这种差别还需后续的研究。有位慈善人士感慨地说:“谁说福利院小孩智力低下?我看一个个人精似的,家里孩子的脾气,他们一点没少有。”*文字来源于田野材料。
然而,除了作为表达关爱的载体、建立互信的媒介等相对积极的角色以外,食物也可能在慈善活动的过程中成为塑造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因素。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部分慈善人士如何将福利院变成旅游景点,将福利院儿童当做旅游景观来获得“慈善旅游”(philanthropic tourism)的乐趣。*钱霖亮:《去孤儿院“观光”:消费弱者的慈善旅游》,《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从这个角度出发,上述给福利院儿童喂零食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成慈善旅游者在福利院中体验特色旅游项目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给婴儿喂奶、抱婴儿、和儿童做游戏,以及观察了解各种病残儿童奇异的残疾特征等,有的慈善人士临走时还感慨,来了一次福利院令人“大开眼界”)。这种旅游体验最极端的结果,是将慈善对象彻底物化(objectification)。比如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有许多家长带其未成年的子女来福利院献爱心,并常常在此过程中鼓励他们和福利院儿童握手、给婴幼儿喂食,教导他们通过感受福利院儿童的不幸生活来反思、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曾目睹一位女士领着她上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在看独臂的女孩端阳。她让男孩和端阳握手,但男孩不肯。她就自己牵了牵端阳的手,让儿子来模仿,于是小男孩就试着和端阳握了手。接着男孩的母亲又建议他给端阳喂饼干。他一连喂了两块饼干,母亲还给他拍了照。小男孩突然对他母亲说,“妈妈,这好像我们去动物园喂动物啊!”女士听了表情很尴尬,说这个小朋友怎么会是动物呢。目睹这一场景的保育员们事后评论说,童言无忌,小孩子往往能说出人最真实的感受。
(三)儿童之间
儿童(主要是幼儿和大龄儿童)之间围绕食物产生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对食物的争夺和分享。食物在儿童之间的流动,在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了这些孩子之间的抚育政治(给予或拒绝给予)。争夺食物是福利院中小孩打架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因为食物不足,按照保育员们的说法,是由于争抢者“永远吃不够,吃吐了还要吃”。此外,福利院儿童吃东西,除了吃本身的意义以外(比如肚子饿想吃、嘴馋、好吃),也是一种游戏。譬如有一次有个孩子口渴,到保育员工作室来问笔者要白开水喝,笔者倒了一杯给他,结果几个站在门外观望的小孩也进来讨水喝。后来站在大厅里的孩子也纷纷跑过来,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凉水壶里的水喝干。笔者对这么多小孩一下子都感到口渴觉得很奇怪,而且是一直喝。目睹这个场景的李阿姨告诉笔者,第一个孩子可能是真口渴,第二个就以为是你给第一个喝什么好喝的东西,他也想喝,再接下来的就是把喝水当游戏了,看到别人喝他们也要喝,别人喝多少他们也要喝多少。李阿姨的解释,不仅揭示了孩子的饮食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背后可能蕴含了一段认知道德的经历:别人有好的东西我也要有,别人有多少我也要有多少,“我”在这里是一个大写的自我。
除了争抢食物,部分福利院儿童之间也存在分享关系。就笔者的观察,这种分享关系有两种类型:“家庭”成员之间的分享和“朋友”之间的分享。在永江福利院,每个孩子入院后都会分配给一个专门的保育员照顾,日复一日的养育过程,使保育员和相当多儿童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系,会说话的孩子对其主管保育员的称呼也是“妈妈”(其他的则称“阿姨”)。这些密集育儿的实践和亲属称谓的使用,加上保育员平时在教养儿童时,也常常有意无意地使用“家”这个概念来区分不同保育员所照顾的儿童群体,久而久之,有些大龄儿童便对同属一位保育员照顾的儿童群体有了作为家人的认同感。*每个保育员所主持的“家”,是福利院中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除了食品是统一保存使用以外,其他物资都会平均分配到每个保育员。有几次在分配物资时,笔者就听到有保育员招呼一些大龄儿童将分配到他们“家”的物资搬运到他们“家”的地方去,而这些儿童都知道所谓他们“家”的地方在哪。福利院婴儿房的空间也是依据“家”来划分的,有两位保育员负责的婴儿房是单独的小间,另外4位则分享两个大间,各自的婴儿床密集排列在房间的两侧。关于福利院保育员和儿童亲密关系的建立,见钱霖亮《建构保育员母亲身份的挣扎: 中国福利院儿童照顾者的情感劳动》,《台湾人类学刊》2013年总第11期第2卷。这种认同也表现在食物分配上。比如,有一次笔者帮保育员给婴儿房里的幼儿喂饭,有个大龄儿童就走过来,告诉笔者不要喂隔壁床的一个幼儿,因为那个孩子不是他们家的。在大龄儿童之间,“家人”身份在食物分享和争夺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要。例如,有一次小霸王国芳抢了一个同龄男孩的零食,和他同属王阿姨照顾的一个女孩非常生气,一把抓住国芳,把猝不及防的国芳摔倒在地上,这个女孩就压在她身上,叫那个男孩抢回零食,两个孩子一起把国芳打了一顿。女孩一边打一边骂:“叫你抢我们家的零食。”保育员们后来制止了这场打架,但是私底下评价王阿姨家的两个孩子时认为,他们虽然被诊断为轻度智障,但却很聪明,有很强的一家人观念,并希望自己照顾的孩子也能有这样的认同意识。
食物分享的另一种类型发生在“朋友”之间,在争夺食物的过程中,“朋友”身份也同样发挥作用。如果“家人”和不属于同个保育员照顾的“朋友”发生冲突,笔者的观察是,有的孩子会更倾向于帮助跟他们关系更亲密的“朋友”。福利院儿童朋友圈的形成,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零食的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患有侏儒症的民燕(大约16岁,在院10多年),被保育员们说成是福利院儿童中的老大,因为不少孩子有零食时都会分给她一些。保育员们认为,这些小孩是在拍她马屁,戏称她在福利院里建了一个小帮派,自认首领。但笔者仔细观察后发现,她和这些孩子之间并没有等级关系,而是用一些小策略发展出一个较大的朋友圈,策略之一就是零食的互惠交换。民燕平时在点心时间吃得不多,储藏盒里存了一堆各式各样的零食。由于其他孩子每一次都吃得很干净没有存货,民燕会在非点心时间拿一些自己储藏的零食给跟她关系好的孩子吃。如果其他孩子问她要,她会要求这些孩子在发了零食之后还给她。笔者注意到她给那些孩子的,也许就是一包饼干中的几片,但等还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整包。也因此,民燕储藏盒中食物的分量只增不减。笔者尝试问了几次,也没搞清楚那些“借贷”零食的孩子是不介意还是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不会说话的孩子无法自我表达,会说话的孩子也不太听得懂我问的),但他们能在非点心时间吃上零食还是很开心的,并和民燕熟稔起来。就此,围绕零食展开的关系网,使得民燕成为了福利院中的孩子王。从争抢食物衍生出的自我意识,到围绕食物展开的“家庭”认同的塑造,再到朋友关系网的营造和维系,这些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常的游戏行为,实际上都是福利院儿童在给定环境中经历和形成自我习性和道德的过程。
五、结 语
民燕的例子呼应了笔者的多项主张。她的零食互惠策略,展示了福利院的病残儿童和家庭当中的独生子女一样,在饮食消费方面具有自我能动性。以自我为中心营建关系网,民燕的能动性表达,既包含了残疾儿童个人的主体性彰显,也可能牵涉到每个个体之间如何关联,以及个体如何融入集体生活的努力。在儿童个体融入福利院集体的过程中,保育员等成人的角色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她们提供“家庭”的概念,营造结构性的氛围;另一方面,她们也通过关爱和规训的手段,构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定出相互之间的职责和义务。儿童融入和体验这种结构的经历,不仅生产出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塑造了他们自我的习性和与他人相处时的道德观念。与其他儿童攀比、争抢和分享食物,向慈善人士索要食物,对保育员恃宠而骄,这些“孩子般”(childish)的稚嫩行为,实际上都是福利院儿童在经历社会化的道德旅行。在其他保育员眼中特别溺爱孩子的张阿姨,有一次也坦诚地对笔者说出了她的担忧。她说,虽然她很爱国芳,但她终要退休,而国芳也会长大,“我不可能永远罩着她,别人也不会永远让着她,以后她如果有能力回归社会,她那种小皇帝一样的脾气谁受得了?以后肯定要吃亏的”。张阿姨的担忧无异于一个母亲对坏脾气的子女难以适应社会的焦虑。而这种担忧恰恰反映出永江福利院近似家庭的机构养育状态。
在社会福利社会化和慈善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永江福利院构造出一幅类家庭的养育场景,这样的养育场景,造成了身居其中儿童的一些类似家庭中独生子女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性。我们从零食消费的角度探究了这幅养育场景,通过考察代表国家的福利院官方机构,代表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慈善人士,以及具体在院内负责养育活动的保育员和儿童之间的互动,展示了抚育政治的运作机制和其创造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义,也是它们塑造了许多福利院儿童的生活习性。而这种生活习性,一方面彰显了他们作为机构养育病残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带着其他学者从独生子女群体身上发现的国家政策、市场化和社会变迁造成的文化烙印——对这些“另类小皇帝”的焦虑,既包括张阿姨对国芳不适应社会的担忧,也有如文章开头,王阿姨对部分福利院儿童由于物质条件太好,而有可能形成不良生活习惯,进而患上其他疾病的隐忧。对比福利机构和家庭养育的环境及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遭遇遗弃而后被国家集中收养以致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另类人群,永江福利院的儿童在其人生际遇和习性养成方面,仍与普通人有着部分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暗含了抚育政治对中国社会中不同类型的儿童群体在人生经历上更为广泛的影响。
进一步说,福利院内围绕零食消费产生的机构与人的互动、成人与儿童的互动、儿童与儿童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广义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一部分。福柯在其早期的研究中,将医院、精神病院、孤儿院等诸多存在明显权力实施印记的封闭和半封闭机构视为规训组织(disciplinary institutions),他断言,这些组织的任务便是保卫“正常社会”,隔绝和教化“不正常的人”。*[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 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 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但后来福柯意识到规训组织存在的意义也许不仅是负面的惩戒,亦包含正面的抚育和照顾。与此同时,它们看似针对个体和小规模的社会群体,但却是整个社会进行人口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作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管理方案的治理术概念。*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笔者在福柯从规训论到治理术的理论脉络之中,探讨中国儿童机构养育的抚育政治:从国家建立福利机构收养弃婴儿以展示“国家关爱”,到保育员在照顾儿童的同时亦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管理,再到慈善人士在献爱心过程中对福利院儿童的利用和消费,最后是儿童之间的关照、攀比和竞争。这些话语和实践,既是永江福利院儿童身体生存和成长的土壤,也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经历社会化和道德教育的环境。在此意义上,笔者意图揭示照顾和管理教化乃是抚育政治的一体两面,在儿童机构养育和家庭养育中都是现实存在的。
在理解机构养育儿童具体生活的层面上,笔者在展现永江福利院儿童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由此形成了一些大众眼中的不良习惯。此外,来自机构、保育员的管控以及慈善人士慈善旅游消费的压力,可能会使院内儿童的能动性受到一定的制约,同时亦有被污名化的可能。笔者相信上述情况会在包括永江福利院在内的不少发达地区儿童福利机构里长期存在,因为相关的话语和实践,符合福利机构运作的制度逻辑和外在的社会氛围。那些对读者来说可能不尽如人意的做法和对福利院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试图改变它们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仅针对福利院儿童“另类小皇帝”的习性,如果它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那么更好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引导。笔者建议,存在此类现象的福利机构,可以适当组织在院儿童参与院外的社会活动,增加其社会经验,令其养成较好的生活习性。同时也让公众能更多地接触这群孩子,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并给予多样化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注意避免让慈善和爱心变成猎奇性的消费。
致谢:感谢富晓星、岳永逸、程瑜等老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责任编辑 陈 斌)
Alternative “Little Emperors”:Snack Consum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in a Chinese Orphanage
QIAN Linliang
Snack consumption among orphans in Chinese state-run orphanages is a poorly studied behavior. This ethnographic research takes snack consumption as a way to show the daily life and experience of a Chinese welfare hous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welfare socializ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s among offi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childcare workers and philanthropists and the orphans’initiatives manifested through snack choices and eat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influenced by the care politics, children under institutionalized care can also live a material life and behave similarly to the “little emperors” or only children in normal families. This discovery may help us further examine the cultural imprints left on children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by the state policies, market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and achieve dialogue with current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childhood.
orphanage,orphanhood,snack consumption,care politics,moral socialization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小学校园暴力发生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A1709)
钱霖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上海,200433)。
C913
:A
:1001-778X(2017)05-0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