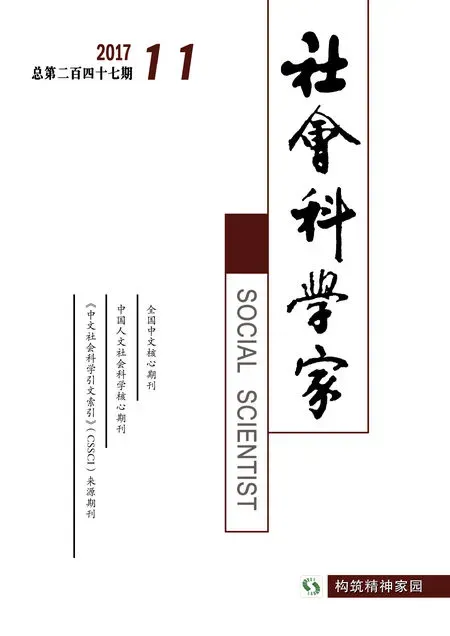丝绸之路研究新探
2017-04-11刘传铭
刘传铭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艺术研究院,上海 201620)
一、丝路非路
从一定意义上讲,丝绸之路并不存在。
至少,丝绸之路不是西方学人标画在地图册上的那样一条横穿欧亚的清晰轨迹,也不是东方诗人所描述的那样:漫无边际的沙漠,一川碎石大如斗,骆驼、马匹和人组成的商队或是迎着斜照夕阳,或是头顶着璀璨星空艰难地跋涉着,身边偶有胡杨的零星枯枝,远处天边的雪峰上空有秃鹰盘旋……道路蜿蜒曲折,通向远方。
丝绸之路非路,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近年来,这个颠覆了人们通常对丝路认知的观点不仅为国内学界认同,也被西方学者视为丝绸之路的新研究成果。笔者于2016年、2017年组织并参与了“丝绸之路·昆仑河源道”和“丝绸之路·天山道”综合科考,跋涉经历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而开宗明义强调这一点,正是要把丝绸之路研究从交通史、民族史、政治史、军事史等“实”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对丝绸之路“虚”的文化解读。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网络,它横跨山川大漠,纵贯海洋风波,变幻不居,时断时续,无迹可寻,无始无终。随着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呼应,关于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有必要做出简单的梳理。
事实上,在那些东起长安西至罗马,东起杭州湾西至地中海的漫长交通线上,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代货物往来的数量并不如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受其影响的更多的是两端和沿线的文化。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就利用了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文书,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考古界的新发现,试图阐释这条“非路之路”是如何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变革力的高速公路的。在关于这条路何以名为“丝路”的质疑中,“丝”其实比“路”更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在这条路上运送的货物远不止丝绸一种。相比玉石、矿物、香料、金属、马具、皮革制品、玻璃和纸这类常见的物资,丝绸的数量绝没有什么优势。当然,运送的货物也应该包括粮食、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甚至还有用来助焊以及鞣革的硇砂。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条路上传播的不仅是货物,还有文化、艺术、宗教、技术。所以,“丝”也好,“路”也好,丝绸之路的名称更应该被视为一个象征。
其实,“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本身就是直到晚近时期才出现的,历史上生活在这些商路沿线的人并不这么称呼它。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路段,不同启始和终点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诚如我们今天在长江流域见到的“一水三江”(即是一条水系的上、中、下游分别有不同的名称)一样。直至十九世纪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一直把这条路称作“撒马尔罕道”,而将由此输送到西方的精美物品称为“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国古代西域更多将这条西行通道称之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通往西方的“南道”或者“北道”,它的往东延伸段则被称为“大海道”和河西走廊。
一直到了1877年,来自德国的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才在他绘制的五卷本地图集《中国》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这个名词。这位地理学家于十九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年在中国工作,主要任务是考察煤矿和港口,其间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文史料,把中国史书里的信息绘入了地图。然而,他未如我们了解的德国学人那样严谨,并没有实地进行过道路勘察,地图上道路的信息部分来自古典地理学者托勒密和马里努斯,部分来自中国史书。在李希霍芬绘制的地图上,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道路显示为一条清晰笔直的大道,他笔下的丝绸之路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前人与马匹用脚踏出来的商路,不如说更像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线。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李希霍芬本人就曾经被委任设计一条铁路线,东起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横贯华北地区的煤矿,西通欧洲大陆,直至德国。可以说,李希霍芬的想象力穿透了时空,他第一次让人们认识了丝绸之路,也让人们相信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史实,而且思想为之定格。
自此,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很快在西方被接受,在20世纪初固定为对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及文化交流的指称,学术界和大众都对此认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根据自己在中亚的经历写了一本游记,其英文版在1938年就以《丝绸之路》为名发表。尽管从被命名之日起,丝绸之路在人印象中就是一条被铺就的、商旅往来不断的大路,以至于它只是被看成是交通史概念,但李希霍芬的结论难免“纸上得来终觉浅”,实际上一百多年来不同国家在沿线经过无数次考古发掘,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一条标识明确、轨迹清晰的道路。既不同于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古罗马时期建造的一条连接罗马与亚得里亚海海港布林迪西的大路),也和中国古代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不同,丝绸之路是由一系列小路所构成,由无数无名的足迹踩踏而成的。因为没有明晰的道路,行人一旦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这道路的网络也一直处于变化中。
遗憾的是,今天仍有不少田野科考的专家,在不倦地寻找着,希望能在地表上发现像长城和大运河那样的道路遗存。因为丝路其实是“因点而存,因点而废”的(这里的点事指历史上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市),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至于今天已然成为“热词”的海上丝绸之路情状更是如此。苍鹰掠过大地,蓝天上没有留下印记;帆樯穿越波涛,大海上踪迹渺然。所以,当代的田野科考如果还是只企图以今人的步履去丈量测绘那条并不存在的路线图,未免有刻舟求剑之愚,本质上还是在重复李希霍芬的错误。
二、清晰又模糊的丝绸之路
既然“丝绸之路”的名称与史实并不贴切,我们是否还要对这条“非路之路”作如是命名呢?关于这一点,如今虽仍有争议,但已无碍大局。持肯定态度的荣新江给出的解释是: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丝织品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多年来总有研究者想用另一个名字来命名这条路,如“玉石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但是都只能反映局部的特征,在涵盖面上都不及“丝绸之路”,也就无法取代这一名称。
顺便说一下,我们千万不要把丝绸的产地作为丝绸之路的原点,更不要把丝绸的产地仅仅理解是太湖流域的江浙和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实新疆的且末、若羌、于阗、“河西走廊”一线的丝绸生产要比我们知道的要早很多。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孟凡人在《丝绸之路史话》中对这一名称仍在质疑: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唐代,中国各朝各代在西域开通了很多重要的交通线,它们当时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的政治和军事而服务的,通常以山川、城镇或行军路线而命名,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同样,通过对中亚史、西亚史和罗马史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无论波斯和罗马向东建设并延伸的交通网,还是入侵中亚的各种势力或是贵霜帝国在中亚建立的交通网,主要也都是为当时的政治军事等方面服务的。因此他认为:
“‘丝绸之路’一称现在已经约定俗成,然而若细究起来这个名称并不那么确切……很显然最初开通这些交通线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商贸活动。但是,在客观上这些交通线又的确成为商贸活动,以及其他诸方面交流活动的重要渠道。就这个时期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活动来说,其内涵和种类是十分广泛的,丝绸贸易只是其中大宗的、影响最大的一种……上述情况表明,除内地外,汉唐时期的今新疆地区,同样也是对外开放的国内丝绸贸易市场,但当时将丝绸大量西运到中亚、西亚和罗马的主角,并不是丝绸产地的中国人。因此,无论从开通这些交通线的本来目的和主要任务,还是从中国人与丝绸大量西运的直接关系来看,将今新疆与内地相连接的交通线称为丝绸之路都是不合适的。”
以上观点显然是把关注点放在物资运输上来确定丝绸之路的范围。这样不仅将丝绸之路形态固化而缩小,同时对公众的认知也是误导的成分居多。比如丝绸之路上还有一种常见的货物就是纸——相比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东汉时期)发明的纸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在公元八世纪,纸就从陆路由中国传入阿拉伯帝国,再跨过地中海进入尚属伊斯兰世界的南欧地区如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直到十四世纪晚期才独立造出了纸。可为什么最后被叫响的却不是“纸张之路”,而是“丝绸之路”呢?
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看起来,丝绸之路作为“路”并非如李希霍芬的地图上标绘的那样清晰过硬,又绝非子虚乌有。同时丝绸之路又是那样穿越时空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那“不知其始为始,不知其终为终”的想象中、争辩中曾被称为“陶瓷之路”“玉石之路”“铜铁之路”“纸张之路”,遂使问题变得无比模糊而复杂。对于中国人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原文化生活圈的人而言,那些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地名,以及不断变化的线路图是足够让人头痛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丝绸之路的魔力,其根本就是文化的魔力!因为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文化传播之路,一条存在于超时空领域的文明之路,一条改变了人类命运并递延伸向未来的道路。从学科建设来说,荣新江、孟凡人等的丝绸之路划定范围的主张,也由于“丝路”的特殊性和延展性,其最佳结果大概也只会被认同是一种“模糊的清晰”。至少,对于丝绸之路的大致路径,目前学界有了基本的共识: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起西汉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一路西行经陇西或固原至金城(今兰州),然后穿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到达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从楼兰再分出南北两道,分居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侧,在疏勒(今喀什)会合。继续走下去,又可以分为两路:往西走,可以穿越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和西亚各国,一直抵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往西南走,则可以一路抵达波斯湾沿岸,或者先往南到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转海路往西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始,丝绸之路就形成了这样的基本路线。
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和政治、宗教形势的变化,不断有新的道路被开通,同时一些旧的道路或是走向有所变化,或是被废弃。东汉初年开通了由敦煌北上的“北新道”,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还有一条①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9-60页。北新道是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出发,先向北到达蒙古高原,再向西经过天山北麓,越过伊犁河进入中亚地区,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南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会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河南道”或者“青海道”。
除了上述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由各条通向西方的海上贸易航线所组成。从广东到印度的航道早在汉代就已开通,宋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阿拉伯海一直到非洲东海岸,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郑和下西洋”的大致航路。
三、如何研究丝绸之路?
千禧年之初,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为本国版画家沃尔夫冈·梯曼设计了一个重走丝绸之路的“纸之回眸,文明的见证”的画展,我在为其出版的画册序言中就坚持了这样的观点:
我敢断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通过“纯粹的阅读”来理解德国版画家沃尔夫冈·梯曼作品的全部含义。其一是因为“纸之回眸”涵盖了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其二是梯曼艺术的语境是表现主义和接受主义美学风行的德国文化背景,因此,诠释梯曼的需要和价值便凸显了出来。
非常荣幸,我们能够率先读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罗尔夫·维尔恩斯得特撰写的“纸之回眸”一文,他在清晰地梳理了自公元十三世纪至八世纪至今天,纸张由中国至中亚,而后又从撒马尔罕,途经波斯、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至西班牙再传入欧洲的文明之路的同时,也将纸张所荷载的佛教文化、穆斯林文化、基督教文化的无与伦比的分量和价值提示了出来。尽管《世界通史》对此早有定论,但对于纸张发明者的中国人来说,无疑会感到自豪和亲切。这便是梯曼作品一定会在中国受到欢迎的精神保证。也许“纸之回眸”比罗尔夫维尔恩斯得特描述得还要久远和漫长,像所有的人类文明一样,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文明传播。所以我们有理由想象广义的纸是自“丝绸之路”开凿的公元前二世纪汉代起就开始向中亚西亚的无腿行走。然而我宁愿相信罗尔夫的观点,因为盛唐时期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留给我的魔力和神话太深刻了。伴随着“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西域荒凉,是更为痛苦和凄婉的战争记忆。如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由梯曼的“纸之回眸”来帮助我们网起浮游在历史烟云深处的、一直默默潜行的文明之薪火便会显得格外珍贵。这也许就是我们和丝绸之路的“缘分”。纸和丝绸都是中国发明的,作为文明的呈现和载体,它们本无雅俗之分,只是丝绸作为财富的象征似乎比纸更能被东西方大众人群所认同,这一点或许被我们忽略了。
这一观点当然不是为了增加丝绸之路研究和传播中的困惑,也不是企图为丝绸之路收名定价。而是想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丝路”是不同人心中的不同存在。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专门的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入门书”以及丝绸之路研究的传播方法越来越被重视。例如,芮传明为解决这一“入门”问题,就从空间、时间、主旨三个方面对自己的研究此作了归纳,而最重要的在于对丝绸之路研究范围的确定。他认为,“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了其繁荣昌盛时期的网络分布地区与中外交往相关的各个领域。这些领域包含了“丝绸之路学”应该研究的各种问题,例如:这些交通道通、阻、盛、衰的历史以及本身之自然环境情况;丝路相连国家、地区、民族对他们的政策、态度、影响以及本身的兴衰存亡;中国及域外诸政权利用丝路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交流的情况;丝路所经地区的政权演变和民族迁徙;其领域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哲学、历史、地理、艺术、语言、民俗、天文、医药和其他科技等等。显而易见,“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过去被称为“中西交通”的研究领域已被“中外关系”的名称所取代。就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而言,地理范围涉及欧、亚、非、美各大洲,内容既涉及经济和政治,又涉及科学和文化,而“(陆上)丝绸之路”则通常被视作古代中外关系的陆路交往部分。由此可以看到,作为研究对象的“丝绸之路”已大大超出了单纯地理名称的范围,还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等。以曾经辉煌于古代世界的“丝绸之路”命名这一专门领域,可以凸显古代欧亚大陆上诸古老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所以,“丝绸之路”既是突出主题,又是象征性的喻称;由此生发出的五花八门的研究领域并不始终拘泥于其字面含义。
芮传明的这些观念是值得肯定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传播应该有确定方向的“指南”,从一开始便要抓住丝路精神之本质。丝绸之路之所以为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冠名权”的问题,“路出多门”、“路出多名”令研究者无从研究起,也无法改变世人“知之者众,迷之者众”的认识怪圈。近年来再加上相当一批专家过度的政治解读热情所导致的简单的“主权宣示”、“宗教宣示”、“民族宣示”,往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便形成了肝胆楚越的“鸡同鸭讲”。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不从“路”入门不行,不从“路上”的物资运输入手也不行,但也绝不能陷入其中而找不到方向。
关于丝绸之路研究和传播首先要解决正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跨时空、跨学科的第一步是陈言务去,如何踢开思想上“拦路虎”的第一脚,不妨按照中国人中医之“外病内治”的思路入手。丝绸之路是一条交通路网,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条中国和世界文明双向行走之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什么是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丝绸之路又是怎样一条穿越时空和地域的线索,同时也是一束穿越愚昧和偏见,探索中华文明发现的智慧之光?当“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家顶级战略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更应当秉承科学的严谨态度。只有抛弃文艺式的幻想和过分的政治热情,对上述问题一一深入,层层推进,才能把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双向行走的漫漫长路,是探索中华文明渊薮的纵深之路,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启迪之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必由之路。
一条丝绸之路,半部世界通史。
[1](美)芮乐伟·韩森(VALERLE HANSEN),张湛.丝绸之路新史译[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美)薛爱华,吴玉贵.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