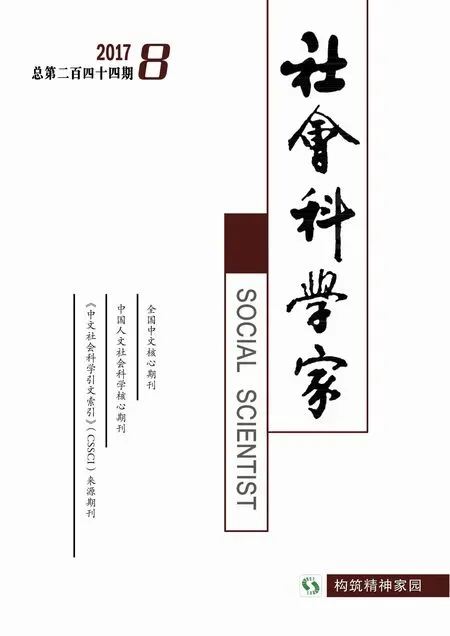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中的人权与发展
2017-04-11余一多
李 龙,余一多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中的人权与发展
李 龙,余一多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然而,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人权事业仍需努力,发展大计任重道远。人权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两大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权事业发展,把人权放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人权与发展经历了“缘悭一面”、“暗通款曲”、“历史会晤”、“携手并肩”等四个历史阶段。坚定不移把人权作为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和重要抓手,把发展作为人权的强大动力支撑和坚实保障,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发展权的基石和生命线,我们必将实现人权事业新发展、开拓历史发展新境界。
人权;发展;法治中国建设
一、人权与发展的“缘悭一面”
人权,2004年载入《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时隔十年,《决定》再次把人权保障纳入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议题。发展,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自此,“发展”成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的时代主题、“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
在很长一段历史长河中,人权与发展动如参商,缘悭一面,相互分离,彼此隔绝。人权的概念从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溯源自始,在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两次世界大战如洪水猛兽般迫岸盈堤,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硝烟和战火让人权陷于齐梁世界、人间地狱,客观上,却让人们对于安全、平等、自由和幸福的渴望和追求更为强烈、更为执着,对于人权尊重和保障的呼吁和要求更为难以释怀、刻骨铭心。二战后,人权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政治和法律术语、世界和时代话题”。[2]
然而,这一时期,人权仍然是作为一项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自然权利而存在,仅仅是政治性和需要付诸实践的术语或权利,尚未加以分析和证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衍生为当前概念。大体上,人权是人的个体及其集合体自由主张或要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资格。具体而言,人权是一种资格,是一种主张或要求,是人的基于自由意志的资格,是以利益主张为内容的资格,是必须主张正当利益的资格。人权的发展按照作用方式分类,分为消极人权、积极人权、社会连带人权三个历史阶段。[3]第一代人权是无须义务人积极作为便可享有和实现的权利,具有被动型、传统性和政治性的基本特征,以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代表。可见,在第一代人权的发展阶段,人权的实现仍是本段前文所言“不证自明”、无须义务人参与的权利,自然也就与本文的另一关键词“发展”并无过多具体联系。
现在看来,“发展”早已成为个人工作生活以及政府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日常用语。在二战落下帷幕的20世纪50年代,“发展”却是一个专有名词。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讲中提出“欠发达地区”的概念,随后,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发展”自此便指国家从欠发达状态到发达状态的进程,成了一项政治上的专业术语。学术理论上,发展理论的进化史如今分为“发达国家发展理论”、“非发达国家发展理论”、“人和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四个演变阶段。[4]然而,在这一理论兴起之初,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经济发展学是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主流观点认为,二战后西方的经济发展分为线性增长、结构变迁、国际依附及市场原教旨主义四个阶段。[5]此时,从事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人群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家及行业有关研究人员,人权理论的研究则由法律人开展。实践上,实务部门也有国际人权组织和发展组织“井水不犯河水”[6]的分类。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政治术语还是理论研究议题,抑或实践中的映射,客观上,二战后的30年间,人权与发展作为相互分离的存在,彼此隔绝,动如参商,缘悭一面。这一阶段,仅停留在“承认人权事业业已存在,却未囊括人权清单”[7]江畔河岸裹足不前的人权与发展的战略性和历史性会晤,仍然有待此后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二、人权与发展的“历史会晤”
经历了“缘悭一面”、“暗通款曲”的历史阶段,第三代人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连接人权与发展的纽带、桥梁,促成了人权与发展的“历史会晤”。第三代人权是积极人权与消极人权相互渗透、交融、支撑形成的社会连带权,需要权利人和义务人共同消极不作为和积极作为方可实现,以发展权为代表。正如一些学者认为,“发展权……把既有国际法和新兴国际政策中的各种支流糅合在一起,二者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为分隔成人权和发展两个领域。”
正如前文所述,“发展”成为政治专业术语,特指国家从欠发达状态到发达状态的进程。为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联合把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定为“发展”,并把6%的经济增长率定为第一个发展十年的主要任务。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带来了系列社会问题,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造成了“人权赤字”。“发展权”应运而生,旨在应对这些多重困难、复杂局面。
然而,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自从产生之初,“发展权”就受到不少质疑:发展权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裁决性。这一质疑基于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权利皆具可裁决性,小前提是发展权没有可裁决性,据此得出结论——发展权不是权利。在法律实证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看来,政治或法律权利才是实在的权利,道德或自然权利只是权利“拟制”,对于这些“拟制”权利而言,“即便我们承认存在,享有和不享有并无不同”。[8]对于权利而言,当法律将其授予某一主体,法律必将授予另一主体以义务”,[8]显然,可裁决性是要有义务主体存在的。故而,权利需要具备可裁决性。然而,长期担任联合国人权顾问的纽约大学教授阿尔斯通认为,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中的人权强调的与其说是可裁决性,不如说是可实现性和监督,二者无须通过诉讼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即可完成这一使命。
众说纷纭,争议交织,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然而,知出乎争,不亦乐乎。“发展权”的提出和《发展权利宣言》的表决通过,为人权与发展关系的发展建立了桥梁、编织了纽带,“发展权”的问世不仅是在“发展”之后加上“权”的“修辞”[9],更是赋予“发展”合法性与正当性。发展权是作为权利而存在的,权利的本质是利益的法律化。[10]当发展权被《发展权利宣言》载明为“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发展权作为人权与发展“历史会晤”的主要成果真正登上了人类人权史的舞台。
当“人权”以“发展权”为橄榄枝向“发展”示好的同时,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人群对于第二代人权的质疑基于冷战时期人权话题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尚未明显改观,“发展”却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了“欲迎还拒”的表示,直到英国经济学家杜德利·西尔斯教授着手对于发展理论的反思和重构,这一局面终于得以扭转。20世纪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发展十年”接近尾声,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人民却未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一反思随之浮出水面——“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观念已经过时。西尔斯教授认为,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消除贫困、促进就业、保障平等三个基本方面。这样一来,尤其在经历了“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需求论”[11]“经济新自由主义”[12]和政府“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理论与实践之后,在“发展”理论研究领域,发展对于人权的态度也重新掀起“犹抱枇杷半遮面”的盖头,逐渐开始更为明确继而坚决。
三、人权与发展的“携手并肩”
时间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持续长达44年的冷战宣告结束,“人权”话题的高度政治敏锐性也随之显著降低,为“发展”进一步走近“人权”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以英国“人权与人道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率先提出“权利本位的发展路径”,并付诸实践,有效推进了人权与发展的深入对话。再者,90年代,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问题而采取的“整体性预案援助模式”把“强化民主机构、培育市民社会成长”作为援助附加条件,客观上从“发展”出发,促进了援助国“人权”水平提升,加强了发展和人权的联系,密切了发展和人权的关系。虽然,此时,人权与发展就像“暗夜中穿行的两艘航船”[13];然而,无疑,二者已然携手并肩,协调共进。
上文提到,非政府组织“权利本位的发展路径”,是发展和人权关系的一个联系点。1995年,在澳大利亚人权理事会的主导下,《以权利的方式实现发展:发展援助的人权路径》出版发行,“发展援助的人权路径”观点首次提出。1998年,英国权利与人道组织在《发展的人权路径》著作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表示要“把人放在第一位,追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承认每个人都享有的、无差别的人类尊严,承认并推动男女之间的平等,致力于所有人的公平机会与选择,促进以经济公平、公共资源的平等共享以及社会正义为基础的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建立”。[14]2001年,这一观点获得了联合国的官方修正和承认。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玛丽·鲁滨逊女士称之为“以权利为本位的发展路径”,认为,以权利为本位的发展路径的概念,既可以在规范上确保人类发展进程与国际人权相关条约的契合,也可以在操作上人类发展的导向之一,即保护人权。
“权利本位的发展路径”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非歧视。发展政策中的非歧视,主要关注妇女、儿童、贫困人口分享发展果实。二是参与和赋权,要求把参与视作一项权利,并赋予人们参与发展的这一权利。三是良好治理,体现在公共部门管理、责任、法律体系、信息和透明等四个领域。“通过帮助打击腐败、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强化司法体制、实现财经部门的现代化,(世界)银行致力于营造各种有利环境,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各项人权。”[15]
联系人权与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能力”。一方面,发展是人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培育人的能力。所谓能力,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另一方面,能力为人权提供了正当性,同时人的基本能力也作为基本权利载入宪法。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人类发展与人权分享同样的视角,目标都是人类自由。在追求能力和实现权利的过程中,这一自由至关重要。人们必须自由践行选择,自由参与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过程。人类发展与人权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幸福和尊严,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自尊和相互尊重。”[16]
上文提到,“发展权”从提出到受到质疑,再到“反思”、“态度明确”,经历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冷战落幕,“发展权”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1993年《维也纳人权宣言》重申“发展权”的重要性。199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的阿琼·森古塔博士作为发展与人权的另一座桥梁、另一条纽带,被任命为合国人权委员会首位发展权独立专家。
森古塔认为,传统发展权是一组权利的集合体,称之为“伞状权利”。“发展权既非独立的公民权和政治权,也非分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是以政治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权的统一”。[17]继而,为了进一步明确发展权和其他人权的界线,提出了“矢量发展权”。首先,发展权是由不同权利和自由构成的矢量,每一项权利和自由都是构成发展权的矢量元素,发展权的实现离不开所有元素的实现。其次,所有元素是相互依存的,所有元素的实现依赖于经济增长。再次,经济增长,得益于权利实现程度。
森古塔认为,发展权是过程性权利,而非结果性权利。发展权不是若干权利的简答叠加,若干权利的实现不等于发展权的实现。“即便作为发展权组成部分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没有获得完全实现或者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合理过程,这一过程又被期待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主张发展权是一项过程性权利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8]由此,发展权是保障集合体的各类权利基于一套程序具有良好结果期待的一项过程性权利。沿着过程性权利的道路奋勇向前,时至21世纪的今天,人权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联系更加普遍、互信更加深入,“携手并肩”,协调共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对于二者的鲜明态度和基本立场。
四、人权与发展的“法治中国实践”
72年前,为维护人类和平、正义、尊严,中国人民同全世界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深知人的价值、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19]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积累了人权事业方面不少宝贵经验。
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发展从强调“又快有好”到侧重“又好又快”,“人的全面发展”受到高度重视。2003年7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人权与发展“法治中国实践”写下历史重要一页。紧随其后,2004年,“人权”载入《宪法》。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然而,中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人权事业仍需努力,发展大计任重道远。要让人权与发展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事业滚滚向前,共同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权与发展的“法治中国实践”,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定不移把人权作为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和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引领民族复兴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共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人权作为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成为全面依法治国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是劳动力的主体。劳动者更好享有人权,主观上为劳动者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增加劳动报酬、维护劳动权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客观上帮助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提高劳动者素质。“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20]只有坚定不移把人权作为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和重要抓手,才能更好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
第二,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人权的强大动力支撑和坚实保障。“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1]一定时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活水平决定人权保障水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发展程度为人权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要导致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联合国发展小组在《联合国对“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开展发展合作”的共同理解》中指出,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方法是指:有关发展的交流与合作要遵守国际人权相关条约,以推动人权实现为目标,以条约原则为指导,以利于“责任承担者”实现责任和“权利享有者”享有权利的能力发展为标准。推行“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方法,推动“人权视野的扩展”[22],为发展作为人权的动力和保障创造条件、畅通渠道,是以生产力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发展促进人权事业水平提高的必然选择。
第三,坚定不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味着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在更高水平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人权事业在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扶贫脱贫、生态保护、医疗教育和人权司法保障等方面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贫困,严重阻挠和干扰人权的充分实现和享有。消除贫困,是亿万斯年以来人类自古迄今的坚定理想,世界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取得了世界减贫事业和人权发展的可喜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积累了通过减贫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历史和实践证明,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要关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享有,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在人权保障水平上落地生根。
第四,坚定不移把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发展权的基石和生命线。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之一。“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寄托着生存和希望。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象征着尊严和荣耀。”发展权是公民、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权利等各项人权的统一,其他各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是发展权实现和享有的前提和基础。
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就是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转化为不断提高的人权保障水平,集中体现为发展权的历史实现,把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发展权的基石和生命线。保障发展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建立健全“发展权保障的立法、战略、规划、计划、司法救济一体化制度体系架构,有效实现经济发展、不断完善政治发展、努力促进文化发展、全面提升社会发展、加快落实绿色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发展”[23],顺应了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事业进步的历史规律,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唯有发展,才能扩展生存的空间;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权的实现;唯有发展,才能把握历史大势、顺应人民期待。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坚定不移尊重和保障人权,让“人权”与“发展”携手并肩、协调共进,使人民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和受益者,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将实现人权事业新发展、开拓历史发展新境界。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2016-07-01/2017-06-14.
[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28.
[3]李龙,汪习根.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444-445.
[4]何中华,张晓华.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J].文史哲,1997:60.
[5]MICHAEL P.TODARO AND STEPHEN C.SMITH,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Addison-Wesley Press,2012.109-133.
[6]SEE PHILIP ALSTON.Ma Making Space for New Human Rights:The Case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M].Harvard Human Rights Yearbook,1988.15-20.
[7]王启富,刘利国.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
[8]C.K.OGDEN.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s[M].London:Routledge Press,2000.119.
[9]PETER UVIN.From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to the rights-Based Approach[J].17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598(2007).
[10]朱庆育.意志抑或利益——权利概念的法学争论[J].法学研究,2009(4):188-190.
[11]陈大冰.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需求论[J].南洋问题研究,1985(2):36-45.
[12]张纯厚.当代西方的两种新自由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对立[J].政治学研究,2010(3):105-109.
[13]PHILIP ALSTON.Ships Passing in the Night: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Debate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27 Human Rights Quarterly,2005.755-829.
[14]JULIA HAUSERMANN.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M].London:Rights and Humanity,1998.33.
[15]WORLD BANK.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M].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8.3.
[16](印)阿玛蒂亚·森,任赜,于真.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5.
[17]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J].2001.9.
[18]汪习根.发展权法理探析[M].法学研究,1999(4):22.
[19]习近平.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的贺信[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6/c_1116583281.htm,2015-09-06/2017-06-14.
[20]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8/c_1115120734.htm,2016-07-01/2017-06-14.
[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12.
[22]常健.发展权对传统人权视野的扩展[EB/OL].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7-01/26/nw.D110000renmrb_20170126_2-11.htm,2017-01-26/2017-06-14.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EB/OL].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532315/1532315.htm,2016-12-01/2017-06-14.
D920.0
A
1002-3240(2017)08-0121-05
2017-06-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神话与秦汉思想研究”(14BZS016)
李龙(1937-),湖南祁阳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余一多(1987-),湖北仙桃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