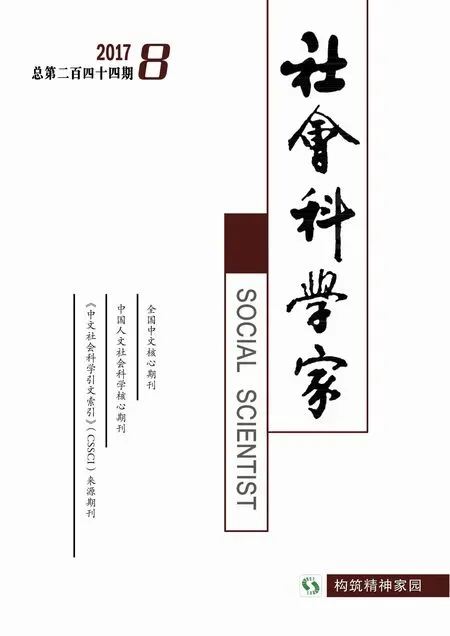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话语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陆建德先生访谈
2017-04-11陆建德
陆建德,石 然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话语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陆建德先生访谈
陆建德,石 然
在陆建德研究员看来,文学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有重要意义,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多元文化借鉴价值极大。其中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和可鉴价值同样不容否认。在文学批评领域,伦理关怀是始终存在的,历史语境是必须牢记的,意识形态的隐性影响亦是无处不在的;文学之“内外划分”也许过于简单,“文学自律”有时过于突出,文学应该对自己有所约束并最终超越自我。陆建德研究院特别强调,不存在“纯文学”的理论。
现代化;伦理关怀;历史语境;意识形态
陆建德(1954-),浙江海宁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主编。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专著:《麻雀啁啾:文学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击中痛处》、《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潜行乌贼》、《思想背后的利益》、《破碎思想的残编》等。主要译著:《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浪漫派、叛逆者、反动派:1760年-1830年英国文学及其背景》等。主要编著:《二十世纪世界散文选》、《托·斯·艾略特文集》等。
石然(以下简称“石”)陆教授在最近的讲座“文学与媒介语言现代化”中指出,人需要离开家乡才能理解自己的固有文化,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不可或缺。作为世界文学的研究专家,您有着广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您是否愿意进一步解释多元文化的可鉴之处?
陆建德(以下简称“陆”):我觉得一个从没离开过家乡的人对家乡的了解可能是很有限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参照物来理解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离开家乡,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结交新的朋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与家乡或者原来所熟悉的一切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候会认识到,以往想当然的事情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也许看过很多书的人是例外。他们通过书本也可以观察外面的世界。当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对差异性必须敏感,所谓的跨文化交际要求我们尊重对方的差异性,但是差异性从来不是绝对的,共性也很重要。我们也可以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互相理解。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中外著作中的相通之处。我自己主要做英美文学研究,有时也写非英语文学的评论。“广阔的视野”还谈不上。日本的特点是特别善于向别人学习。我觉得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不及日本对我们的了解。至于欧美文化,范围太广,有点无从说起的感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恰恰证明欧洲文化有很强的自我分析、批评能力。一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学界还是有着巨大的影响。欧美文化其实都是呈现开放形态的。你刚才说到“固有文化”,我略有异议。文化总是发展变化的,我不大能够接受任何停滞、固定的观念。我们的文化也有很强的自我分析、批评能力。回顾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难道没有沧海巨变吗?这种变化来自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北京大学有个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在美国的赛克勒基金会建议下建立的。赛克勒(1913-1987)是美国企业家,慈善事业赞助人,他说的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在不同文明的民族间建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桥梁。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所有人都应该尽力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建立桥梁——艺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说得多好!钱锺书就是勤勉的搭桥人。只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说我的文明一以贯之,边界清晰。这是坐井观天,不能由复杂的历史进程证实。也有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关注自身的特点,如有人在探讨何为“英国特性”(Englishness),对此提出批评的人也不少。如果主张“英国特性”的人士恐外排外,那就可悲了。我不大愿意说我们应该向其他文化学习什么。我要强调的是必须了解别国文化,包括亚、非、拉美国家的文化。全球化包含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我们最近这些年关于世界各国的书出了不少,这个势头还应该保持下去。
石:《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是您主编的鸿篇巨制。在您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理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怎样进一步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借鉴外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陆: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的序言和后记里都谈到了遗憾。我以为现代化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不同的时候,我们对现代化的标准是不同的。1981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班德与画家大卫·霍克尼访问中国,当时“实现现代化”的话语在全国都非常流行,相关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处处可见。斯班德受邀到一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为“来自远方的客人”献上一台节目,以示“热烈欢迎”之意。斯班德在他的游记里特意提到了一位穿得漂亮的女生如何上台朗诵华兹华斯的小诗《致布谷鸟》,一位男生则用丰富的肢体语言“表演”了雪莱的《西风颂》,其神情就像古建筑前面的石狮子,看起来威严,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为什么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作特别让亚洲人着迷,这是斯班德未能解答的。轮到他上台了,他念了自己一首小诗《词语》,大致说我们使用的词语像一条滑溜溜的小鱼,我们想抓住它,它总是逃掉,甚至还在我们手上咬一口。斯班德接着建议那些好学的中国青年读读艾略特、叶芝和奥登的诗歌,大概这些现代派诗人不再简单相信词语和现实之间完全对应的关系。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有时也感到“现代化”的概念就同斯班德诗里的那条小鱼一样,好像看得真切,却抓不到。不过它要比小鱼厉害多了,一旦被它咬了,伤口可不容易长好。我们原来追求GDP,是不考虑环境、生态代价的,很多地方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现在我们相信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外国文学对我们在文学进程中的借鉴意义是极大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另外,有的国家的经验又表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离不开文学语言。文学涉及方方面面,人的现代化是不容易的。鲁迅当年想改造国民性,现在是不是还应该继续?林纾的域外小说翻译对中国现代化意识发展是关键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与翻译同步进行的。各国现代化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都各有特点,没有标准的道路。这是我主持这一项目后最深的印象。
石:以苏联文学为代表的苏联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东欧剧变以后,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对苏联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持有反思的态度。中国理论界已几乎不再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范畴了。对此,您如何评价苏联文学及其当代价值,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陆:俄罗斯有非常伟大的文学传统,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投入大量时间自学俄文,希望自己能阅读俄文原文著作,但是后来荒废了俄文,太可惜。苏联文学是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鲁迅对俄苏文学评价很高,翻译了俄文的小说和文艺理论著作,俄苏文学确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到了五十年代,苏联文艺界一些流行语进入中国,这些翻译过来的口号、说法如何进入我们的文学批评语言,还应该好好研究。做“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不懂俄文,他们也不大会去关注五十年代的《译文》(后来改名《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现在由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外国文学研究所是在1964年从文学所分出去的。请想一想:《译文》杂志的主编是茅盾。《真理报》一些跟文学创作相关的社论、文章很快就会译成中文。我认为苏联文学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出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也不要把日丹诺夫的作用看得过大。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肖洛霍夫、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家,在这一串名字后面还可以加很多!其他国家拿得出一批能与这些人物比肩的诗人、小说家吗?苏联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也是比较积极的。苏联文学的成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所能概括的。有时候我担心文学上的“主义”一词太单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其喜爱莎士比亚,他们不会说莎士比亚属于什么“主义”。我在七十年代读过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六七十年代的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当时我们没有可以相比的作品。苏联文学里有些作品反映了集体农庄的生活,这是全新的东西,但是也经得起阅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在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启发下写成的。苏联是五十年代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者,吸引了大批欧美左翼作家。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公布文化名人,我国也举办纪念活动,规格之高是现在无法想象的。比如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斐尔丁”(HenryFielding,1707-1754,现在通用译名为菲尔丁)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53年11月底的维也纳会议上决定1954年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三位是德沃夏克、契诃夫和阿里斯多芬)。没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一号召,中国的英国文学学者写关于这位英国作家的论文,会有一定的风险。当时我国文化界的纪念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1954年第9期《译文》(即现在的《世界文学》杂志)刊出苏联学者叶利斯特拉托娃的《菲尔丁论》。1954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青年宫举行隆重纪念大会,这一年的《人民文学》(1954年第6期)和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12期)刊出萧乾的《关于亨利·菲尔丁——读书札记》和黄嘉德的纪念文章《菲尔丁和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纪念亨利·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
石: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中,形式主义批评话语、审美批评话语有着较高的呼声。您依旧坚持文艺的历史批评话语(其中亦可呈现伦理批评话语、意识形态批评话语)。而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文艺的历史研究只是文艺的外部研究,不应该占据文艺学术话语的主要成分。当然这是有失偏颇的。对此,您如何看待历史批评话语在今天的生命力?
陆:中国文艺批评中究竟有没有形式主义批评,还有待观察。我以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翻译、介绍了不少形式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但是真正将形式理论用于批评的例子不多。审美这个词有点宽泛,我不大知道审美批评话语究竟是什么。在欧美理论界,提出审美批评可能是针对过分的政治化解读而言。不管什么批评,都需要细读文本。这已经成为共识。韦勒克和沃伦把文学研究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类,也许过于简单了。新批评难道不注意一首诗的作者和时代吗?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强调作品的历史背景,看重context,而不是text。换句话说,要将作品置于具体的历史之中。对国外的理论,不要有情绪化的反应,不要逢“外”必反,义和团的心态要不得。我们必须重温陈独秀、鲁迅对义和团各种表现的批判。真正读懂一种理论,要清楚它为什么产生,它针对的是什么。我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近几年我的鲁迅研究倒是体现了一点这种历史方法的特点。比如我发现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由受赔国退还给中国,用于教育事业,但是这一笔笔巨款的管理支配权在国内教育界引起纷争,但是大家不明说,有很多暗斗,暗斗一旦浮到表面上就演变为光明正大的口号了。我们不能被那些口号迷惑了。我所了解的文学批评、研究中,伦理的因素或道德关怀一直存在,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势必涉及一个人应该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做人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独立于我们的道德关怀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隐性的,自己也不一定会意识到。在标语口号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宜画上等号。在文艺作品里有的人说话干巴巴的,我们能把那些挂在嘴上的内容等同于意识形态吗?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里一位编辑很会说一些大家十分熟悉、很“正确”的话,她却工于心计,好打小算盘。道德敏感性就是在这些具体实例中慢慢培养、提高的。每个时代的道德敏感性是不大一样的。古代葬礼特别重要,甚至有殉葬的现象,那时的人们不以为这样做太残忍。
石:《思想背后的利益》是您的一本重要著作。您在最近的讲座中也特别提及,一些很细小的东西背后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中国近现代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分别有一种“文学自律”思潮。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思潮背后是否亦有意识形态因素?应如何评价这种文学思潮?
陆:你说得对,一些很细小的东西、习惯成自然的东西,背后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思想背后其实是有复杂利益的,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从来不否认人的超越性,即人类历史上很多观念不能局限在“利益”的范围内讨论。我们经常只看表面的词语是否“正确”,其实是非常容易上当的。近年我写过几篇关于清末保路运动的文章,当时“保路”的宣传做得极好,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是受骗的。改革开放后,有的史学家做相关的研究,还是容易被漂亮的口号、姿态误导。我要提出来的问题是:当时主张保路的极少数绅商对所谓的“路股”有支配权,运动成功以后,那笔资金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让中央政府查账?为什么日本人向留日学生灌输“保路”的思想?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时,我们往往重表面上的动机,轻效果,关心的是它们是否“反封建”,是否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一个运动只要名号响亮,参与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放火打人也不算为过,至于对谁有利,谁获利最多,我们是无暇顾及的。
有一度我们强调“政治挂帅”的方式过于简单,于是很多作家希望自己写作的时候不要概念化,不要主题先行。他们通过提倡“文学自律”来制约政治干预。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历史背景,用超时空的观念来理解某些历史性文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有很多历史教训应该记取。比如文学所的《文学评论》1966年第3期没有刊发一篇学术论文,头四篇文章全部是从其他报刊转载的,其余则是非学界人士大字报式的“檄文”。然后《文学评论》就停刊了。纪念《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还不应忘记这个甲子中间曾经出现过十一年多的空白。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去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该文强调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当今的特殊意义,值得认真阅读。经过“文革”以后,人们渴望“文学自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我不大相信“纯文学”。还有一点我想说一说,“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化”的差别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不会去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席勒有时有此冲动。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是否应该选择“莎士比亚化”?相关的讨论还是不够的。莎士比亚几乎是无我的,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自我”有时过于突出了。“文学自律”让我联想到二十年代梁实秋提出来的“文学纪律”。作家应该对自己有所约束,最终会超越自我。
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您已经主编了多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那么,您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现状一定有着准确而又深刻地把握。在您看来,当前研究中哪些成果最为重要?尚有哪些不足?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陆:我先说一说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讲话发表已经一年多了人,它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长期指针,应不时温习。习总书记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他在引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如何使用历史资料的一段话后告诫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我想说的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现状还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首先我们的文学或文艺修养不够。马克思和恩格斯受过很好的教育,懂多种语言,马克思过五十岁了还学俄文,我们的知识结构还有欠缺。我认为仅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读他们读过的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很多变化,有的变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促成的。英国工人代表进入英国议会让恩格斯很兴奋,英国社会的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是福利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工党之所以能够击败声誉正隆的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主张建立福利社会的《贝弗里奇报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首相后,对英国煤矿、铁路和航空等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在英国建立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政府为每个公民免费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对低收入或无收入家庭提供国民救助。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子女补贴,从此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抚养责任。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英国,把福利社会的建设作为奋进的目标。世界在变,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以不变应万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大家共同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应该向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开放,不断充实、丰富自身。重复一句话:纯文学的理论是不存在的。
石:您曾经把“麻雀啁啾”作为自己文学批评集子的名字。如今,在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界,您已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了。您曾经在《自我的风景》中详谈作家的社会责任。那么,今天的您,是否依然会有“麻雀啁啾”自比?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您将怎样渡过自己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又将如何发挥自己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责任?
陆:我只是一个一般的读者而已,目前还参与《文学评论》的一些工作,但是我已经退休了,迫切希望从编辑事务中解脱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麻雀啁啾》是二十年前出的一本集子,当时有一些特别的考虑。这个名字是从《日瓦戈医生》里一句话借过来的。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些经历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对常见的麻雀还是有点私心,这种性情活泼的小鸟与人类伴生,好群居,长相一般,平时叽叽喳喳,绝无英雄气概,反而比“玄鹤”“鲲鹏”“鸿鹄”之类可爱。传统文人志向太远大,他们是看不起“燕雀”的,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作家是有社会责任的,但是不宜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致落入自我欣赏的陷阱。我没有长远的目标,只想多读一点书。说来难为情,我有大量的书,堆放在办公室里,还没有读过。我有一枚铜质印章,上面的六个字“至乐莫如读书”说出了我的心声。如果读书后有感想,我也会写下来与人分享,也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碰到有的现象,我很想发表观点,有的还是不合时宜的观点。比如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拳击手邹市明的文章,我对他的经纪人有点失望。邹市明应该发扬体育精神,选择最优秀的对手来比赛。我这是在发挥自己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责任吗?能对一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提出自己对“公平竞争”(fairplay)的理解吗?不知道。鲁迅原来说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我不敢苟同。原来文学与体育也是有关联的。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难道不是有助于我们心智的成熟吗?读书、写作都是一种对话的行为,参与这样的对话,是人生一大乐事,以前如此,今后还是如此。
D632.1;F323.89
A
1002-3240(2017)08-0003-05
2017-06-1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023)阶段性成果
陆建德(1954-),浙江海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石然(1987-),山东青岛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