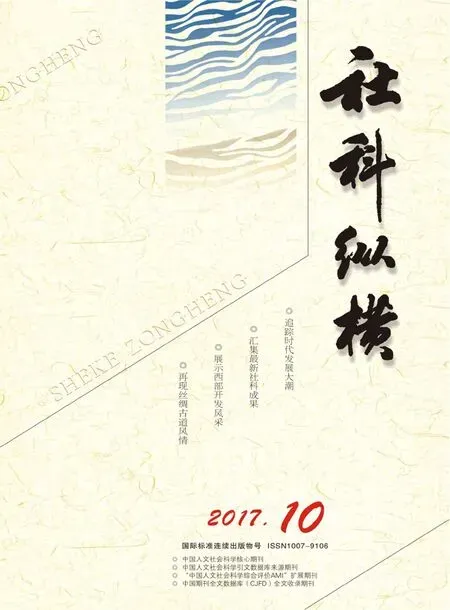鸡鸣三省会议之我观
2017-04-11李光胜
李光胜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四川成都611731)
鸡鸣三省会议之我观
李光胜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四川成都611731)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了一次常委会,中共历史上,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作用非常。但这次会议的具体地点究竟在川滇黔的哪个省,三省各执一词,至今没有定论。对于这样的争论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辨清其中的论据,有自己的见解。当前重要的不是为争论推波助澜,而是要使争论者和谐相处,共同利用、保护好这一名片。
鸡鸣三省共同关注经济发展学理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会议不计其数。而且每次会议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它们共同汇成了一条星光灿烂的银河。在这众多的耀眼明星中,能够与“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乃至成就了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的遵义会议这颗光芒四射的星星相媲美的,恐怕屈指可数。这颗明星也实在是太过抢眼,光亮实在是太过强大而掩盖了它周边本来也十分明亮的其它若干小明星。这些小明星中有一颗就是鸡鸣三省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它同样熠熠生辉,其意义和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本文拟就鸡鸣三省会议具体地点的争论表达笔者的一些看法以飧读者。
一、鸡鸣三省会议川滇黔三省争论说之我观
1935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带领中央红军转战来到贵州的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关系到党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主张,也在理论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后不久,“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这是毛泽东在讲到鸡鸣三省会议时,提到的地点——鸡鸣三省和时间——当年二月,但这两个关键因素却交代得很模糊。即使是周恩来等当事人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这两个关键因素时,同样也不具体。当前又没有查到关于这次会议的原始材料;而这次会议在中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意义重大,地位又十分特殊;加上现在各省普遍挖掘历史资源,打造城市名片,并想借助红色旅游这一助推器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因而川滇黔三省都在据理力争,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自己省份的招牌。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具体地点,目前在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且这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一些无法回避或解释不通的问题。
(一)贵州毕节林口迎丰说
关于鸡鸣三省会议是在贵州毕节林口迎丰召开的一说,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所著的《走走党史:一渡赤水和鸡鸣三省会议——红军长征之七》的大作中,为我们做了非常全面和有说服力的三方面原因的归纳总结。第一,迎丰村的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最好。岔河(鸡鸣三省的核心地带)在迎丰村形成抱胯岩,站在岩顶,其他两省一目了然。而迎丰村就在这岩顶上,并且它在解放前就叫鸡鸣三省,解放后才改称叫迎丰村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名称与周恩来在1943年和1972年的两次报告中所说的名称是完全吻合的。第二,是1979年的全国妇代会期间,邓颖超对毕节县妇联主席说的一句话,即红军长征时到过林口。第三,是1985年7月,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一书,明确地指出了鸡鸣三省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二月五日,在贵州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根据上述几个似乎很确凿的证据,贵州一直坚称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贵州境内召开的。但上述几个证据在认真、深入地思考过后,会发现存在不少问题的。首先,迎丰村即解放前的鸡鸣三省村与周恩来所说的村庄是否是同一个村庄很难确定,况且名称巧合也是可能的。其实,从周恩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鸡鸣三省村应该是广义的鸡鸣三省村,包括迎丰村即解放前的鸡鸣三省村在内,而不是指特定的哪一个村庄。其次,邓颖超的那番谈话无从查起,是当年的毕节县妇联主席转述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大打折扣。最后,国防大学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一书中提到的那个结论,其证据来源于哪里?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当年的任何电报或当事人的回忆等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来证明中央纵队当年到达过林口。人都没去过那里,怎么会在那里开会呢?
(二)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说
2006年8月8日,《云南日报》第9版刊登了一篇题为《“鸡鸣三省”会议地点考证和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的文章。文章通过陈云、毛泽东、周恩来和杨尚昆等会议当事人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和吕黎平、李质忠和曾三等当事人在半个世纪后接受采访时的回忆性说法,以及一些当时的原始电报材料,最后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鸡鸣三省会议是在1935年2月5日于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召开的。乍看上去,论据很充分,很有说服力,几乎没有什么漏洞,但这些材料依然经不住仔细推敲。
首先,在引用陈云、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文章中,句义理解不够准确。如陈云所说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周恩来所说的“遵义会议后到云南”等,这两句话中都有一个“到”字,请注意,“到”是一个动态性的、方向性的和目的性过程,而不是表达结果,它与“到了”、“到达”或“在”是不一样的,即是说还没有到达“威信”和“云南”。毛泽东所说的“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打回马枪”等也是一样,并不能说明这是在云南开的会,因为“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可能还没有进入云南,也可能虽然已进入云南地界,但是云南军队的威胁,中央政治局能够静下来开会?
其次,吕黎平、李质忠和曾三等当事人时隔半个世纪的回忆。虽然三人回忆那次会议的地点不谋而合,可以说有很强的说服力了,甚至可以确定地说就是那个地点。但我们也有质疑之处,即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而且是在三省交界处召开的一次当时看来并不重要的会议,在半个世纪后再去回忆它,其确定性有多大?况且这半个世纪中,先是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乱,再又经历了十多二十年的内乱,其确定性更值得怀疑。
最后,从当时红军的电报和俉云甫、陈伯均的日记我们看出鸡鸣三省会议不在水田寨花房子,而是在四川的石厢子。从1935年2月3日到5日朱德的一系列电报中,可以知道2月4日军委纵队一直在石厢子,直到5日21时半,军委一梯队才到云南的水田寨,五军团这时还在石厢子。可以说,2月5日的白天,水田寨还没有进驻军队,怎么会开会呢?而且,俉云甫和陈伯均的日记都记载有“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小时)”和“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的内容。因此,博古交权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大可能在“运输员们均疲惫不堪无能为力”的“特殊困难情境”下于2月5日21时半以后匆匆做出决定的,而应该是要慎重思考,充分讨论之后才能决定的。
(三)四川叙永石厢子说
认为鸡鸣三省会议是在四川叙永石厢子召开的,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便是前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世鸿老先生了。他首先从区域上排除了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等地方不在鸡鸣三省范围内。因为“人们通常所指的‘鸡鸣三省’是以岔河为中心,离岔河不远的村寨。”而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等地方却在岔河边高山的背后,不属于鸡鸣三省的范畴。同时,他给出了鸡鸣三省会议就是在石厢子召开的非常充分的四个理由:第一,石厢子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到的“庄子”。当年中央纵队进驻石厢子时,这里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和一条小街,能够称得上“庄子”,而滇黔两省的地方当时都只有1户人家,称“庄子”是不大合适的。第二,召开像交权这样大事的会议,既要有充裕的时间,又要有安全保障。当年的中央纵队就是在距离敌军百里之外的石厢子住了两三天。第三,根据当年朱德的一些电报知道,中央纵队绕过崎岖、泥泞的小道,机要部门才于2月5日夜里23时半到达花房子一代。因此那个时间和当时的状态召开重要的会议不大可能。第四,当年的花房子没有庄子,只有一栋三间木方,无法让中央纵队宿营,而石厢子却恰恰有这样的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陈述,何世鸿老先生认为,鸡鸣三省会议只能是在石厢子召开的。
这个说法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时间上与现在能够看到的当年的一些原始的电报材料不太吻合。但与滇黔两省的说法相比较而言,合情合理的、能够经得起推敲的成分更多一些,说服力更强一些。因此,笔者倾向于石厢子说。
二、鸡鸣三省会议之我观
近些年,像上述这样存在较大争议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然而在笔者看来,鸡鸣三省会议究竟在哪个省召开的,其实并非是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摒弃争论,共同守住、开发、利用好这块招牌,为推动本地方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科学发展做贡献。
(一)共同关注民族的未来发展
近年来,各地为鉴定革命圣地、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大张旗鼓、不遗余力,把能够沾上边的材料全部拉到自己身边来,力争能够获得肯定,从而得到政府的各种资助。由此不乏一些名人、先贤的故里,部分古迹遗存、文化名城等也就成了各地争抢的重点对象了。如李白出生地,有关省市就一直在争论不休;当年梁山好汉占领的水泊梁山到底在山东的那个县域内,也一度是考证的对象。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领导者看来,只要自己区域内有了这样的一些招牌和名片,很快就可以名利双收了。这些想法和做法我们可以理解,但其实作用是不大的。因为即使政府把这样的招牌和名片给了你,而你后劲不足,不能很好地保护、开发、利用这个招牌和名片,同样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如同苏联解体后,列宁墓的迁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如果统一俄罗斯党不是畏惧俄罗斯共产党的巨大实力,担心其东山再起,恐怕也不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直接就迁移走了。
再拿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来说,目前虽然川滇黔三省都能拿出证据说当年的会议就是在自己省内召开的,但四川叙永石厢子目前摆出的架势,如研究机构和成果、省市领导的重视度以及在国内的知名度,恐怕是滇黔两省无法比拟的。何况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与滇黔两省相比受益更大,发展更快,为守住鸡鸣三省会议旧址这个招牌和名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这个招牌和名片给四川扛起应该比滇黔两省更合适。
既如此,又何必要为了这个名片是谁的而争论不休呢?与其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争论,还不如转过身来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的发展做些实事。因为除了川滇黔这一不同的省籍身份之外,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鸡鸣三省会议旧址是共同的名片。为何非得要非此即彼,而不能既此又彼呢?难道自己一枝独秀,身边的兄弟姐妹困苦不堪,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吗?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也是相违背的啊。鉴于此,笔者认为,川滇黔三省完全可以通力合作,共同挖掘资源,合力打造名片,共同守住、开发、利用好鸡鸣三省会议旧址,也开发出一个什么三角洲或经济带之类的,共同推进西部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早日跟上东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就是西部各省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吗?
(二)走“利用红色旅游圣地,助推经济发展”的路子
跨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随着国务院节假日时间的调整、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各地经济发展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开发、利用本地的旅游景点吸引游客,以此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托。而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华大地,西部重点就是川滇黔这一带。在这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石厢子召开了一次中国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已经提出,但还没有落实的任务——博古交权,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负党中央的总责。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有非常大的纪念意义,也有极高的隐性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也难怪今天的川滇黔都要力争而不肯放手。
这些想法和做法无非就是要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地方的知名度,甚至吸引一些投资者等,本身也没有什么对与错,但还是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看准目标,估计好自身的实力,如果没有底气与实力,最好还是不要趟浑水。像上述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这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乃至文化现象在国内国际也屡见不鲜,如前面提到的李白出生地的争论,曹操墓的争论,甚至连日本都争论说杨玉环死在他们的国度。虽然这些地方都看到了历史遗迹和文化名片的重要性,想通过这些名片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在现实当中那些由于底气不足、实力不够的地方很快就自动放弃了争论。可见,历史、文化名片不是你想争就能争来的;通过这些名片搞文化产业、由此带动经济发展,也不是你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比如,以鸡鸣三省会议旧址来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四川的泸州还有些基础,有这个可能;而贵州的毕节和云南的威信无论在什么方面与泸州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贵州的毕节,综合实力远在其之上的贵州赤水想合并到泸州下辖的合江县的九支镇,由于九支镇的嫌弃而没能成功。因此,贵州和云南要助推毕节和威信的快速发展,想利用这个红色圣地作为龙头,是不太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既如此,滇黔二省还不如早日调整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重新整合社会资源,恐怕更为切合实际,也更有效果。
(三)缺乏深入的学理研究
争抢鸡鸣三省会议的具体地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把行政区域当做了精神文化区域,这是两个绝对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鸡鸣三省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今天,已经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了,从这个角度分析,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从文化的学理角度分析,鸡鸣三省会议的渊源和未来发展趋势有它自己的模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硬是要把鸡鸣三省会议说成是在某省某市某县某村召开的,一定会失去它在文化和思想上对广大民众的教育和熏陶意义。
当今是开放的时代,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大势所趋,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法完成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自身发展的愿望。试想,如果遵义会议就是遵义的,与其他地方无关,它会有那么巨大的社会效应吗?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说它是党的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它解决的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关键性问题,而不仅是为遵义的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问题。再如,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专家、学者有必要去考证清楚,它起源于哪里,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吗?恐怕也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它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和今天繁荣昌盛的最主要因素。
总之,笔者认为,鸡鸣三省会议,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和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资源,重要的是当前如何来共同地传承和发展,而不是去争抢其原始地。原始地当然重要,而发展应在原始地之后不断发扬光大。鸡鸣三省会议是川滇黔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应该没有争论了。四川也好,云南也好,贵州也罢,大家和谐相处,为本地能有这么难得的一个资源而高兴,齐心协力共同利用好、开发好这个资源,让全民族共享这一资源带来的成果,岂非远远胜于各不相让和争论不休而造成的人、财、物的浪费?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9.
[2]翟昭明.关于博古、洛甫在“鸡鸣三省”交接权时间、地点考证[J].党史文苑,1997(2):36.
D231
A
1007-9106(2017)10-0103-04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度一般项目(SLQ2015B—08)(主持人:李光胜)的最终成果。
李光胜(1975—),男,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