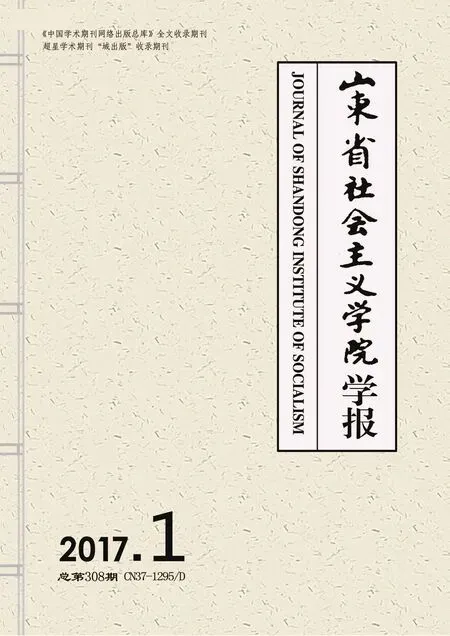《史记·五帝本纪》与中华共同体的形成
2017-04-11陈战峰
陈战峰
《史记·五帝本纪》与中华共同体的形成
陈战峰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第一篇(卷),在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司马迁卓著的史学眼光与时代意识,对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史学与理论基础。其中的“五帝”及其关系清晰而鲜明,显示了史书编撰者的主动调整和自觉建构努力。“五帝”既反映了历史一脉相承,又有重人文、重理性的思想文化特征。在客观与逻辑意义上,《五帝本纪》通过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心理认同,反映并促进了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和巩固具有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统一的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经验智慧,影响深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共同体;认同
《五帝本纪》是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的第一篇(卷),在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司马迁面对当时百家称“黄帝”而文辞不雅驯①“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史记·五帝本纪》)本文所参考《史记》为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后同。,实地考察,对传闻“五帝”现象进行重新的思考和研究。尽管《史记》已经做到“择其言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但毕竟记载了不少传说故事,错讹与矛盾的地方也比较多,不能作为判定客观史实的唯一依据。然而史学作品具有历史重构的本质属性,本身便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需要对其进行思想文化的分析。如果将《五帝本纪》与其紧接着的卷二《夏本纪》、卷三《殷本纪》以及卷四《周本纪》结合起来分析,则反映了司马迁卓著的史学眼光与时代意识。简言之,《五帝本纪》对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史学与理论基础。
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华共同体具体包括历史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以及心理共同体,四个方面融会在秦汉以来以华夏民族(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统一的国家形成进程中,促进了国格意识的形成与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统一体[1]。
一、“五帝”的排序与《五帝本纪》中“五帝”的变化
“五帝”并不是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的概念或提法,而是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完善的。但是,据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相当于“五帝”时期的历史时代是客观存在的。
“五帝”大多指称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上古时期历史人物的合称,具体包括三种说法,即“太皞(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战国策》《吕氏春秋》),“少昊(少皞)、颛顼、高辛(帝喾)、尧、舜”(《伪尚书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等,三种关于“五帝”的排序反映了不同的谱系特点和时代烙印,也体现了“五帝”在战国中晚期至秦汉之际的调整变化的特质。《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与《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顺序一致,与《伪尚书序》也比较接近,是对此前五帝顺序与谱系的重新建构与整合。
二是五方上帝(或五方神)的合称,即中央黄帝(轩辕,属土)、东方青帝(伏羲、属木),南方赤帝(炎帝,一说蚩尤,属火),西方白帝(少昊,属金),北方黑帝(颛顼,属水),自然这里的五方上帝带有明显的五行思想和观念,而且反映了黄帝已经居于中央统摄地位,对四方神具有支配与指导作用。《吕氏春秋·应同》以五行思想解释黄帝、舜、汤、文王以来的历史演变规律,判断代周而兴的当属“水”德。这些都是秦汉之际大一统历史趋势在思想观念上的曲折反映①郭沫若先生认为:“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2-223.)。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及其关系很清晰与鲜明,显示了史书编撰者的主动调整和自觉建构,其中蕴藏的时代感和问题意识值得人们注意。
二、《五帝本纪》历史传承的特色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黄帝”是始祖,“颛顼”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是黄帝之曾孙、玄嚣之孙、蟜极之子,“尧”是帝喾之子(名放勋),“舜”是昌意的七世孙(即黄帝的八世孙),当然,《夏本纪》记载继承“舜”大位的“禹”是昌意的三世孙(即黄帝的四世孙),其间显有错讹与矛盾,则是另一问题,也愈益突显了这个世系与谱系的重构本质。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形象克服了此前“五帝”世系的纷杂与矛盾,而代之以同宗共族的特色,均是共祖“黄帝”的嫡系后裔。虽然这个谱系还有不少历史的空白,有间隔,不连续,但所选取的主要历史人物与历史节点,却具有深刻的思想意涵。显而易见,《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带有浓郁的血缘属性和人文属性,“五帝”重视德行与功业,通过个人的努力、发明和百姓的共同劳动,逐步改善生存生活的环境和境遇,促进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是依靠上天的恩赐或神的庇佑,这都反映了较天命思想以及图腾崇拜、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进步的思想意义,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与实践功能。因此,《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既反映了历史一脉相承,又有重人文、重理性的思想文化特征。这些记载虽然与《诗经》《尚书》记载的在殷商时期依然保留着厚重的图腾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崇拜(《诗经·生民》《诗经·玄鸟》等)不完全一致,却深刻反映了秦汉时期历史叙述重构的思想本质。
这种重构的影响因素大致来源于三个要素,分别是:战国中晚期炎黄信仰的形成发展与黄老之学的兴起,新型国家统一趋势在思想上的诉求和反映,阴阳思想与五行思想的汇合与交融等等。
三、《五帝本纪》在中华共同体形成中的文化功能
在客观与逻辑意义上,《五帝本纪》反映并促进了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认同
历史认同是历史建构与历史重构的基础和前提。炎帝、黄帝等上古帝王,不见于《诗经》《尚书》的记载。炎帝、黄帝的记载,在流传文献中最早见于《国语·周语》①“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国语·晋语》)。司马迁重新梳理勾勒历史。以黄帝为首重建上古史的谱系,既是对五方上帝神观念的扬弃,也是对人文历史认识的自觉化与理性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意义。
关于这种历史重构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例如如何处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司马迁尝试所做的“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2]努力,恰恰反映了对神话传说历史价值尊重和对现实历史价值赋予的双重努力,其中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仅具有表面的史料或观点的不一致,更深层次反映了历史重构在面对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社会需要时的多重考量和曲折努力。当然,《史记》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具有多种演变[3],其中班氏家藏本的改变应被充分考虑在内,这有助于判断和厘清表面冲突后的历史实质。
(二)民族认同
“五帝”时代是氏族部落不断发展和融合的时代。古老部落与新兴部落的结盟、分化与融合,在神话历史传说中表现为世系相传与更迭,反映了氏族部落的延续和变化。部落的首领或盟主带有“共主”的特点,世代相沿不替,所以流传的英雄首领名称便是“共名”,如炎帝和黄帝等,这有助于理解上古传说帝王长寿的故事,尽管荒诞不经,但却蕴藏着对历史的追溯与体认,凝聚着氏族部落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4],中华民族也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五帝本纪》以人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传说历史,将“五帝”构筑为一个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历史,也是民族形成建立的历史,其中的民族认同,为后世历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帝”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体现了对历史的选择和重构,确认和凸显黄帝的历史地位,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
《五帝本纪》以家谱的形式重新梳理历史,既反映了民族认同的加深加剧,“五帝相继作为部落首领而出自同一家族,前后绵绵数百年,这就为一个家族的历史谱系做了最充分的材料准备”[5],也体现了家国观念的发展以及家国一体格局进一步完善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以华夏民族(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秦汉以后多民族融合又保持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影响深远。
(三)文化认同
《五帝本纪》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标志是重视德行,重视功业,重视教化。《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有教化的写照。黄帝“淳化鸟兽虫蛾”①“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颛顼“治气以教化”②“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史记·五帝本纪》),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③“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史记·五帝本纪》),尧“能明驯德”④“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舜“使布五教于四方”⑤“日以笃谨,匪有解”“内行弥谨”“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五帝”均能够德化四方,教化万民⑥其他如《史记》叙述商始祖契重视教化与功业:“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史记·殷本纪》)。这些奠定了内外兼修、本末赅备、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重要文化观念基础。这并非是意味着历史上的氏族首领—五帝客观具有的思想特征,而是生活在汉代,受秦汉思想哺育的史学工作者进行自觉的理论审视与历史重构、文化认同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文化认同在古史体系上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被认为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古史体系”[6]。相传黄帝的大臣仓颉造字、殷代始祖契改进文字书写办法等,也曲折说明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对语言文字符号的发明和改进,促成了稳定有序的文明传承体系的形成,这也是文化认同的表现。
《史记》在《三代世表》中明确强调,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与“三代”天子均是秉承修养德行而代代相传,即使有的时候需要假托“天命”的观念,“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也反复申述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子孙能够“皆复立为天子”,关键是“天之报有德”(《史记·三代世表》)。重德是司马迁自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对“五帝”德行的建构和叙述,形象化地表达理想的道德人格和价值理念,其中呈现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亘古不衰的主体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哲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特征。
这种现象在《史记》的其他各篇也有显著的反映,如关于先周的历史,同《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文王》等比较,《史记·周本纪》对是否具有“令德”①“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史记·周本纪》)当然,这里的史料除来源于《诗经·生民》外,还来自于《尚书·尧典》。的行为很重视,并且作为书写历史贯穿前后的一条主要线索,这既是对《诗经》上述六首英雄史诗的系统把握和深入体会,同时也展示了史学家个人史学建构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四)心理认同
《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虽然其中还有不少龃龉之处。
《夏本纪》将“禹”作为昌意的三世孙(黄帝→昌意→颛顼→鲧→禹),是直接继承黄帝而来。《殷本纪》与《周本纪》中记载的殷始祖契、周始祖弃(后稷)分别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燕卵与元妃姜嫄(原)履迹所生,事迹分别见于《诗经·玄鸟》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 商颂·玄鸟》)《楚辞·天问》③“简狄在台喾何宜, 玄鸟致贻女何喜?”(《楚辞·天问》)与《诗经·生民》④“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大雅·生民》),带有图腾崇拜的深刻烙印,当然也交织和混合着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思想信仰。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这样,将历史上夏商周的三代,通过心理认同系结在“黄帝”的主干上,“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三代世表》),从而使三代成为相互因革而在血缘与文化上又具有连续性的共同体,促使人们在心理上对国家统一性的认识逐渐加强。
《秦本纪》追溯的秦的始祖大业也直接肇源于颛顼的苗裔⑤“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高祖本纪》将汉高祖的降生与神奇的“大泽之陂”的“蛟龙”⑥“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联系在一起,形成与黑帝似有似无的联系⑦当然,《史记·高祖本纪》在汉的统系上有不同认识,同篇高祖被酒斩蛇,后老妪称蛇为白帝子所化,为赤帝子所斩,作为汉代秦的论证,汉则属“赤帝”系统(“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 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终汉一代,人们在“黑帝”与“赤帝”系统上纠葛不清。。
这些都是有意识地论述“五帝”“三代”“秦汉”一脉相承,都是黄帝的子孙与苗裔①“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史记·三代世表》)这说明司马迁对《诗经》记载与流传神话故事的矛盾性有所觉察,而自觉进行了历史的重新建构。。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朝代可以更替,而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不会灭亡。后来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概括的“亡国”与“亡天下”实际恰恰是朝代更迭与亡国的区别②如顾炎武说:“保国者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13“正始”条)。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也保证了中国历经战乱兵燹而绵延不绝的存在状态。
四、结语
司马迁关于“五帝”历史建构和历史叙述的方式,是对汉代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表征,这种“大一统”,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家民族形成的基本规律,也是历史、民族、文化、心理等认同的结晶和影像。“大一统”的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时空性,但也是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在这种意义上,“五帝”谱系所昭示的历史与文化的大一统的共同体观念是与秦汉社会历史与思想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五帝本纪》奠定和反映了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史记》以后,历代官修史书与民间史书在反映这个历史时段时,大多保留或沿袭了《五帝本纪》的基本脉络和谱系框架,保持和巩固了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促进了中华共同体的形成和具有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的统一的新型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为奠定历史上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经验智慧,影响深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2]刘书惠,李广龙.《史记》感生神话矛盾性论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95.
[3]李开元.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J].史学集刊,2012(4):48-58.
[4]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6.
[5]徐军义.《史记·五帝本纪》的主体性构建[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14):9.
[6]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207.
陈战峰,男,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