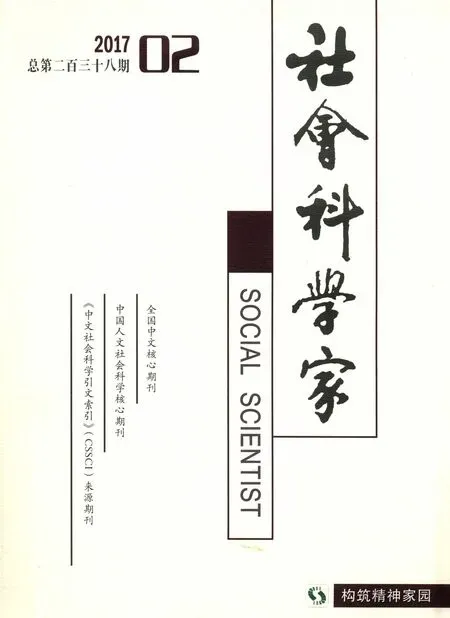新时期戏仿叙事的发生及其价值判断
2017-04-10许燕
许 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新时期戏仿叙事的发生及其价值判断
许 燕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戏仿叙事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的一种戏谑或滑稽模仿,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照经典文本和生活的新视角。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文本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以及对小说的虚构本质和世俗化社会思潮的认同催生了戏仿叙事。戏仿叙事消解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僵硬的教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学空间的开拓,但戏仿叙事同时又可能消解一切价值和主体精神,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特征。
新时期小说;戏仿叙事;世俗化;消解;价值判断
戏仿,或称滑稽模仿和戏谑模仿,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极大拓展了传统小说仿真式文体的张力和意蕴。模仿是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人类各种活动的一种基本模式,而文学中的滑稽模仿则是用戏谑的态度模仿严肃作品,通过变形或改变作品原有的意义,使原来的严肃作品在新的语境下成为一种笑柄。从总体上来说,戏仿叙事属于反讽创作原则,因为“反讽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包含了对立的两项,并通过这悖逆冲突的两项昭示了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1]戏仿叙事中形成反讽效果的对立两项就是已经成为经典的母本和滑稽模仿母本新创作的文本,这两者貌合神离,似是而非,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讽刺性的美学效果,并揭示出社会人生中某些真实的内涵和本真的状态。戏仿叙事突破了经典文本的权威束缚,用另一种视角观照人性和社会生活,激活了人类的思维和日趋麻木的审美感受能力,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促使人们正视历史和现实,重新衡量一切价值。因此,戏仿叙事在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发生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总体看来,戏仿叙事的艺术特征以调侃、戏谑、幽默、滑稽为主,具有比较明显的喜剧色彩,但是在外在的喜剧形式下,内含着对生活和人性真实状态的揭示,充满了辛酸和无奈。喜中有悲,悲中有喜,戏仿叙事这种艺术创作本身就是社会和人生真实状态的表征。当代小说戏仿叙事发生在一个经历过长期封闭和压抑的文化语境中,这种活泼、机智的创作给了当时的人们极大的新鲜感和陌生感,也产生了一些非常有深度的文学作品。然而,当代社会的世俗化潮流冲击着一切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主义的价值选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戏仿叙事如果过于迎合这种时代潮流,停留在浮泛和模式化的层面,它也会走向失重和无聊,缺乏价值建构的文学创作,自身也会失去价值。
一、戏仿叙事的发生学分析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十七年”和“文革”的政治化年代是不太可能出现戏仿叙事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性作品在叙述方式和态度上所要求的首先就是认真和严肃,创作者必须以一种极其认真和虔诚的态度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并坚信自己是在以文学创作再现客观真实生活的方式揭示历史和社会的真理,而他作品中的那些有着忠诚信仰的人物正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崇高英雄形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使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庄重、崇高的风格。因此,在这种语境中戏仿叙事是基本不存在的,并且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一种宏大叙事,在这种叙事模式下创作的经典文本后来往往成为了戏仿叙事的消解对象和母本。
戏仿叙事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现代化”不再仅仅是中国人心中理想化的目标,而是日益成为一种现实之后。“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封闭、紧张和压抑中走向了务实和理性,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社会重新步入追求现代化的轨道,“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也改变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命运。“现代化”的理想和现实加上8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的大量涌入,必然深刻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关于文学和人性的观念也是如此。新时期初,曾经一统文坛的现实主义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某些新变,王蒙、宗璞、谌容、茹志鹃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已经出现了包括意识流、荒诞、变形等在内的现代主义技巧和手法。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主义的技巧和文学观念更是得到了普遍的传播和认同。在技巧的实验和观念的变革过程中,引人注意的是小说等文学样式本体观念的觉醒。此时,传统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决定论被摈弃,小说不再被动地依附和决定于所谓的客观真实和社会现实,其虚构本质得到了认同和强调。“真实的现实消失之后,叙述仅只是虚构的游戏——写作和阅读双重快乐的虚构,小说不是让你认识和重建现实,而是给你提示一次虚构的想象经历。写作和阅读不过是面对虚构的游戏。”[2]这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强调小说的虚构本质,实际上是为小说创作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艺术空间,此时,严格依附于所谓客观社会生活的传统现实主义就显得相当笨重,文学从观念到技巧都酝酿着巨大的变革。
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既然如此,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庄严地宣称揭示了真理、再现了客观现实的宏大叙事的经典文本就变得相当可疑,面目也开始模糊不清,甚至成了被解构和消解的对象。小说既然是虚构,那么同一个对象,同一个事件就可能有不同的虚构方式,小说叙述的人称和视点都可能发生变化,原来严格遵从的物理叙述时间可能被解构,变换成一种心理时间和主体体验时间。关于什么是真实,人们的观念也就不再附着于之前的客观社会现实上。在种种新观念支配下的文学创作所呈现的面目也是各不相同,甚至和经典文本是相互对立的。
此时,戏仿性文本开始大量出现,戏仿叙事成为一种比较显著的现象。究其实质,最大的动因就是应和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关于文学、人性、社会人生和小说叙述,人们的观念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在小说叙述方面,“‘戏仿’文本实质上是对传统经典文本的破坏性颠覆,它采取反叛的姿态,对经典文本进行夸张和变形。经典文本中的主题话语、情节、细节、人物心态均被改变既定形态和叙事走向,这种放大镜或哈哈镜式的艺术处理,使经典文本遭到瓦解,叙事将文本象征化、意象化、寓言化,文化含量增大。”[3]很自然地,中国历史中尤其是现当代革命历史中的很多经典文本就成为了被仿写、重写、戏写、续写的对象,而在诸种写作中,程度不一地带有对经典文本的消解和解构的性质。这些经典性文本主要包括古典浪漫、英雄崇高、传奇历险等几种类型,与之相生而成的戏仿叙事对这些已经成为了成规性审美模式和习惯性思维方式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重叙,从而产生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带有明显反讽审美效果的戏仿文本。
对小说叙述的虚构本质的认同驱动作家对小说经典文本进行重叙,但重叙为什么产生那么多戏仿叙事,戏仿叙事的大量出现不是仅仅认识到小说叙述的虚构本质就能达到的,其中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现实生活本身应该是更深层的原因。现代化的语境下,人们必然关注现实生活中自身的物质利益,人的各种世俗欲望也相应被肯定和鼓励,而这些世俗化的欲望和物质利益无非就是吃穿住行,食色性也。而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和欲望经常会产生冲突,因此也就免不了算计、钻营、势利、倾轧、争夺、伤害甚至杀戮,这个时候社会人生平庸琐碎甚至真实残酷的一面就会显示出来。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场景中,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和人性中平庸卑劣的一面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和认识。社会生活中更多的内容是日常和世俗甚至是严酷的,而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更多显示出平凡、渺小甚至卑微、平庸的人性内涵。更加有意味的是,当人们处于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初期阶段,物质的贫乏和匮缺总是让人感觉生存的艰辛,而当现代化充分发达,人类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又使人感觉压抑和荒谬,感觉到世界的非理性和非人化。人,真能在这个现代世界诗意的栖居?而这些,必然极大地影响到新时期作家的小说创作,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对这些作家而言,“世俗化的冲动更直接地来自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大革命结束后乌托邦理想的衰微,另一个方面是在社会转型中人们的世俗欲望的激活”[4]。
于是,那些蒙盖在真实生活和人性之上的古典浪漫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崇高面具,那些回避了生活真相的传奇伪装就成为了人们调侃和解构的对象,并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开始戏仿叙事,创造出戏仿文本。关于戏仿叙事和经典母本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似是而非、貌合神离之间。似是和貌合是因为戏仿叙事在人物、情节、细节很多方面初看让人感觉仍然是属于一种经典故事,没有离开我们的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但而非和神离是因为戏仿文本中的主题话语、情节、细节、人物命运、故事结局却又走向了和经典文本完全不同的方面,从而在戏仿文本和经典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解构和颠覆的关系。
余华的《古典爱情》就是对才子佳人的古典爱情故事的戏仿叙事。《古典爱情》中的书生落魄、千金小姐钟情、私订终身、赴京赶考等情节给人感觉作者确实在重复一个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古典浪漫爱情故事。然而,故事的悲剧结局和残酷真相却表明余华在这里挑战了我们的审美心理,逼得我们直面现实和人性,这是对经典叙事的一种解构。人们喜欢编织许多美好的神话,并沉醉于其中,以作为对现实生活有所缺失的一种补偿。才子佳人相恋、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属于这种神话。余华的小说却告诉我们社会现实是真实而残酷的,从而揭开了这层古典的浪漫面纱,还生活本来的面目。刘恒的《冬之门》是对经典革命叙事的一种仿写,窝囊懦弱的谷世财是个给日本兵做饭的伙夫,他爱上了美丽刚强的抗日女战士顺英,而顺英却怎么也不会看上这个猥琐的谷世财。于是他就总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让顺英看得起他,而这只有成为抗日的英雄才有可能。当求爱完全失败,他也就变得绝望,于是,他利用自己做菜的机会毒死了大批的日本人,自己也踏地雷死去。在经典革命历史文本中谷世财当然会被塑造成崇高英雄形象,可是在这种戏仿性的叙事中,我们却更多的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偶然。李冯的短篇小说《我作为武松的生活片断》,小说选择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作为叙事基本框架,最初让读者感觉这仍然属于一种经典叙事,但是小说将第三人称叙事改为武松的内心自述,通过这种自述,武松内心的烦躁,行为的鲁莽、酗酒成性等取代了经典小说所塑造的维护正义的传奇英雄形象,一个传奇般的英雄变得平庸、卑琐和委顿,他不再是挺拔、冷峻的英雄,反而更加接近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之辈。解构和颠覆,这正是戏仿叙事乐此不疲的事情。
由此可见,这种戏仿叙事对我们的审美阅读期待视野、审美经验甚至思维方式都形成了某种挑战,逼得我们不得不正视严峻的现实、幽微的历史和芜杂的人性,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审美创造。于是,新的阅读、新的创作、新的文本、主题、人物和情节的出现才有可能,它体现着观念的变革、技巧的创新和视点的位移。这一点,无疑是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创新和发展的。
二、戏仿叙事的价值判断
戏仿叙事是当代文学出现的新现象,其本身反映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革。长期以来,当代文学史上被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所束缚的文学创作已经严重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僵化刻板、形式匮乏、平面浮泛都是这种文学创作模式的缺陷。只有从这种束缚中突围出来,才能为文化的创造和艺术的创新开拓一个广阔的空间,文学才有可能重新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之树上最丰硕的果实。毫无疑问,当代小说的戏仿叙事属于当代小说创作中创新思潮的一个部分,对新的艺术空间的开拓是有着自己的贡献的。要真正认识和判断戏仿叙事的价值,我们仍然需要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角度切入。
如前所述,戏仿叙事的发生最深层的动因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正因为现代化的发展,从物质利益方面充分肯定人的世俗化的欲望和功利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因为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社会对已经走在现代化发展前列的西方社会开放,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以及文化和艺术包括体现在这些文化和艺术之中的思想观念纷纷涌入中国。可以说,正是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变革催生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变革,戏仿叙事也由此发生。但是,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如果陷入非理性状态就会发展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并由此带来道德的滑坡、社会的冷漠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与80年代整体的理想主义氛围相比,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大陆的高歌猛进,世俗化享受和对利益的追逐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也正是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深感忧虑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由此表达了对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批判,90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大论争产生的动因也就在于此。
然而,现代化却仍然是当代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否定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必然性,那么世俗化就仍然会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与之相适应,反映日常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刻画那些日常生活中凡俗平庸的人物的文学创作就会继续繁荣。并且,在另外一些人文学者看来,世俗化的现实也并不像前述的人文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洪水猛兽般的可怕,相反,世俗化充分肯定人性欲望和物质享受,并体现了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世俗化精神恰恰是符合人道主义的,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正是让人类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充分肯定人的世俗欲望和身体感受吗?这不也正是一种世俗化的精神吗?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消极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罪于现代化与世俗化,现代化与世俗化当然也有自身的负面性,但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糟粕的遗留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偏差,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现代化程度还不够。现代化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目标。[5]如此,当代中国的戏仿叙事就有了深厚的社会生活土壤和深刻的思想观念背景。
从外在艺术特征来看,戏仿叙事具有一定的喜剧色彩,轻松、幽默、滑稽,贴近生活,贴近真实的历史和人性,因此,虽然表面具有喜剧性甚至带有一定的油滑色彩,但真正优秀的戏仿叙事作品其内在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意味,是能让人认真思考的,其原因就是戏仿叙事更真切的揭示了生活和人性的本相,这其实是一个严肃主题。经典母本的内容是严肃的,形式一般是单一的,而戏仿叙事往往在外在的戏谑和滑稽的形式之下,包含了严肃的内容和深刻的主旨。在当代文学长期被伪崇高和教条所束缚和压抑的背景下,调侃和戏谑反而体现了一种真实人性的光泽。读者在对戏仿文本的阅读中,首先获得的也是一种轻松和解脱,娱乐和精神消费其实应该是一切精神文化产品的底色。喜剧色彩从作品的各个环节显示出来,给了普通读者一种亵渎的快感和精神的满足。“真正的喜剧精神体现了人类的理性认识的深化和创造精神的勃发。它既表现为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认同和珍视,也表现为人类对自身局限、缺点和荒谬的反思和自嘲,在喜剧制造的笑声中,人性之中的美好内容得到苏醒和恢复,同时在自我反思和否定中,人们的理性认识得到超越,愉快地和过去告别。”[6]也就是说,作家和读者在创作和阅读戏仿文本的过程中,明确了我们应该认同的价值,找到了通往精神自由之路,也嘲讽了人类社会自身那些荒谬和压抑人性的东西,反思了人类自身的处境,从而恢复了美好而真诚的人性。
可以肯定的是,戏仿叙事属于反讽的范畴,“反讽的修辞方式定义,是一个符号表意,表达的非但不是直接指义,而是正好相反的意思。这样的符号就有两层意思:字面义/实际义;表达面/意图面;外延义/内涵义,两者对立而并存,其中之一是主要义。但是究竟何者是反讽的主要意义,却随语境而变化。”[7]戏仿叙事也是在经典母本的基础上发生的,其字面义貌似和经典母本一致,但是在表面依从经典母本叙事的形式下,实际上表达了恰好相反的意思。这种叙事未必是写实层面上的,故事本身也谈不上所谓客观真实,因为创作者一开始就知道小说就是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却可能达到一种更高层面的真实。这种真实就是创作者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体验,以一种理性和智力优越或者也是无奈和苦闷的状态对人类生存的非理性状态进行自嘲,并且在有着相似人生体验的读者的阅读中获得了共鸣。这种对生存的更高层面的真实的书写,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寓言化写作,因为这种故事本身可以视为人类生存状态和真实人性的一种整体象征,它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事实的束缚,从而将读者的思想和审美提升到一个形而上学和哲学思考的层面,获得生存的超越和思想的解放。
当代小说创作已经从单纯描摹外在客观现实的传统套路中突围出来,获得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艺术创造空间,许多作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文本包含更宽广的思想内涵和寓言诗性价值。戏仿叙事是整个文学创作潮流中的一种现象,对文学整体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提升以及文学创作的发展无疑是有价值的。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戏仿叙事价值的同时又必须警惕戏仿叙事中产生的某些不良倾向。戏仿叙事如果用得过多过滥,只注重表面的戏谑和滑稽模仿,只醉心于解构的快感,忘记了作品真实意图和主旨的表达,失去了真正的思考和探索,必然滑向一种无聊而浅薄的语言游戏,读者最终也会对戏仿叙事失去兴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代小说的戏仿叙事所具有的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因素。消解权威、解构神圣、众生狂欢,在一个世俗化时代是有其内在的依据的,这是戏仿叙事和后现代主义相通的地方。在一个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时代,金钱和物质似乎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消费和享乐似乎也成为了生活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杰姆逊曾经指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的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8]
戏仿叙事如果过于注重语言的游戏和情绪的宣泄而失去严肃的内涵,实际上也正是在迎合这种消费、亵渎、游戏和娱乐的心理。如果我们的视野放开一点,看看大众娱乐文化中的其他种种戏仿艺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大众娱乐文化中存在的某些为消费而消费,为享乐而享乐的特征。它消解了一切价值,解构了主体精神,呈现出浓重的享乐主义色彩。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世俗化潮流中的平民心态,肯定戏仿叙事对凡俗人生和生存本相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戏仿叙事不需要批判精神,世俗也不同于媚俗、粗俗和庸俗,戏仿叙事解构了僵硬的教条,但自身也要避免陷入一种新的教条,思维的单一和片面是新旧教条共同的特点。
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反中心、反权威和多元共存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价值,却忘记了人类社会的存在需要价值的建构,艺术的自洽性也在于价值的建构。“以传媒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一种反美学、反文化的艺术。这种精神价值的跌落表明理想主义已经被虚无主义所取代。”[9]虚无主义消解了人内心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人也就变成了一种只会追逐利益、欲望和享乐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当我们重新认识当代小说中的戏仿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理性的甄别,对戏仿叙事中的某些虚无主义的因素必须给予摈弃,而坚持其在喜剧色彩的外表下深刻的思想内涵。另外,戏仿最初只是一种修辞格,后来才衍化成一种创作原则。我们坚持当代艺术创作思潮的异质多样性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戏仿这种修辞艺术在形式论上的价值,它使艺术创作富有活力,生动而充满张力。可以预见,尽管戏仿艺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但是戏仿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却并不会过时。
[1]黄擎.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1):76-80.
[2]陈晓明.仿真的年代[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3]张学昕.当代小说创作的寓言诗性特征[J].文艺研究,2002(5):67-73.
[4]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6]张勇.大众娱乐文化要植入真正的喜剧精神[N].文艺报,2012-11-30.
[7]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王岳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6(3):72-85.
I206.7
A
1002-3240(2017)02-0138-05
2016-04-11
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中河流的地域文化想象”(编号:15ZWE05)
许燕(1980-),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