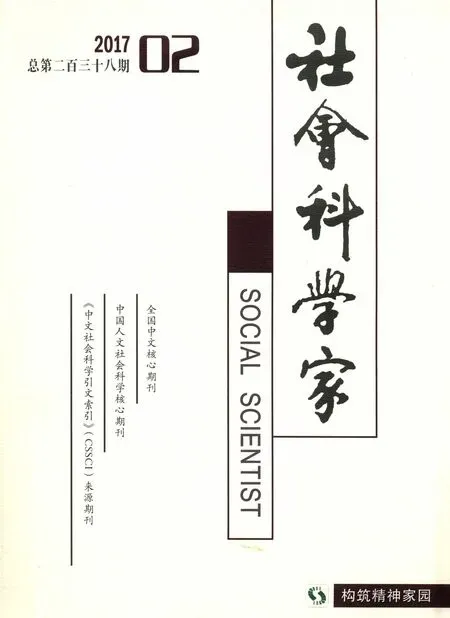哲学变革与语言转换
——从晚期海德格尔讨论班谈起
2017-04-10许小委
许小委
(惠州学院 政法系,广东 惠州 516007)
哲学变革与语言转换
——从晚期海德格尔讨论班谈起
许小委
(惠州学院 政法系,广东 惠州 516007)
新哲学或新思想的发生是否必然伴随着语言上的转换,这在语言哲学和哲学史上是历久弥新的问题。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指引,特别是马克思的原则启示,从语言转换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途径出发,能够对此一问题做出必要的澄清和回答。海德格尔的运思总体上厘定了语言同思想之间“非此不可”的关系。他想要突出思想相对语言的优先性,事实上又陷入了思想和语言相互规定的怪圈;想以新思想召唤出新的语言,却终究只能倚重语言的转变来促成思想之新生。所以,海德格尔既未实现语言转换也未完成思想变革。马克思抓住了更为基础的东西,即语言和思想之共同的外部根据——“感性活动”,由此对语言的“外部守护”和“内在澄清”才成其可能。因此,唯有马克思真正实现了话语的转换,同时也就是哲学变革的完成。
哲学变革;语言转换;必要性;可能性;途径
作者此处要探讨的问题,起源于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的激发。1969年9月7日的讨论班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形而上学之内和之外运用相同的名称,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1]。此一问题之所以凸显为海德格尔的问题,同他从两个方向上转换语言的不成功尝试有关。海德格尔确实把握到“存在的真理”/“大道之音”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因此他很早就有意识地寻求一种新的语言以配合新思想的崭露。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海德格尔首先展开了创造新词的尝试,但此种努力之结果,正如他后来明确表示的那样,“荷尔德林使他领会到,自铸新词是无益的;在《存在与时间》之后,他首先明白了返回语言之本质的简明性的必要性。[1]”也就是说,从其现实效果来看,《存在与时间》当中自创新词的努力收效甚微并引发了新的问题,因此自创新词的努力大体上是失败了。接着在关于《形而上学是什么?》(1928)的演讲中,他使用和黑格尔《逻辑学》中“纯存在与纯无因而是一回事”这一命题相同的词——“存在与无”——来言说某种超出形而上学的思想,然此种试图的完成程度和真实效果却同样是可疑的。因此,海德格尔势必作此一问:“在形而上学之内和之外运用相同的名称,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考虑到此一问题的发问背景,它实际上既是对新思想境域中“旧词新用”之可能性的追问,也隐含了对面向新思想境域而“自铸新词”之可能性的追问。所以问题可转写为:新思想是否必然要求着一种新语言?亦即哲学变革与语言转换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关于这个转写过的问题,海德格尔的某些说法似乎表明他心存疑虑,对主动实施语言转换以适应新思想的工作是否有效也似乎不抱信心。果真如此,他此前所做的诸般努力岂非尽付流水、毫无意义么?他所新创的或经其重新阐释的词语又何以会部分地“获其生命”(对前者是赋生,对后者是促其重生)而得以保存下来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他终其一生都未放弃转换语言的努力?乃至于1930年后“转向”了的海德格尔“发展出一种伽达默尔所谓的‘半诗性的特殊语言’”[2]?因此,事实绝没有这般简单,此中必定存在某种玄机。我们将紧扣“哲学变革与语言转换的本质关系”,并将其析分三个具体问题:即通过语言转换以促成新思想的降生,这件事情终究有无必要?是否可能?又如何发生?以把捉和领悟那真正属于思想之洞见的东西。
一、有无必要
转换话语形式是否必要?要切近回答此一问题,关涉到对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的澄清:一是语言的本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二是转换语言(不论是自铸新词抑或旧词新用)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关语言之本质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正是语言转换问题上的分歧态度之原因所在。对否认话语转换之必要性的那类观点而言,它们通常受制于这样一种先见:将语言看作是某种工具性的存在物。认为语言只是表达和显现思想的手段,它与“存在之真理”或“思维本身的要素”并无关联。此种形式(语言)和内容(思想)截然区分的思维方法,伴随近代以来不同语言间相互交流的扩大、包括不同民族语言相互转译事业的发展,运用不同词语表达同样的思想内容变得至为平常,致使语言和思想之间似乎只余下一种松散的、任意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之工具性的成见。当仅从其工具性方面来理解语言时,语言与存在、思想和世界就只余下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肤浅关系了。处此情势之下,诸如一种思想直接就是一种特定的语言(话语系统),思想必定要求某种非此不可的语言(言语)这类想法,就绝不可能产生出来。相反,为着促成哲学和思想的变革而相应地更新语言,便只能被视作是非必要的和无益的。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从任何方面看都远远超出了上述理解。他始终是从存在和语言在根基上的共通和交融来阐明语言的。在和日本学者手冢富雄的对话中,海德格尔明确提到,存在和语言是其思想的两大主题,并且早在他1915年的授课资格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和含义学说》的标题中,就已经显露出这两个前景[3]。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和语言有着根基上的“亲近”,存在说出语言,语言显明存在。存在乃是作为语言之根据的东西,语言因对存在的言说而成其为语言。语言与存在的本真关系就在于:存在居于(真正的)语言之中。“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4]”或者换种说法,语言就是“大道”的自行言说,语言即“道说”。“我们把语言本质之整体命名为道说(sage)”、“语言之本质现象乃是作为道示的道说。[3]”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就是“存在之真理”的自我显现,或是“大道”从其自身而来的说。语言与“存在”、“大道”自始就有本质上和根底上的关联,因此语言和思想(作为“此在”对“存在”、“大道”之领悟)就实有一种非此不可的紧密关系。说得更明白些,语言乃是思想的自我表达,是“思想”在自行说话,语言只能顺乎和响应思想而有所言说。基于对语言如此这般的理解,亦即体认到语言和思想不可移易的本质关系,主张为促成新哲学(新思想)的诞生而转换更新语言,就是完全合理和正当的了。这也解释了海德格尔何以始终不渝地进行着话话转换的尝试和努力。
以上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问法:是否存在一种特别适合于某种思想的语言?或问,以不同的语言传达(显现)同一思想,假定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在效果上是否并无二致?常识地看,不同语言在揭示同一种思想时,必定存在着效果上的差异,因为它们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有诸多的区别。海涅说过,“拉丁文是将军们发号施令的语言,是行政长官发布指示的语言,是法官对高利贷者的语言,是罗马民族的石头般坚硬的碑铭体的语言。它成了唯物主义的专用语言”、“除开我们可爱的德语外,大自然可能无法用任何其他语言把它那最为神秘的事业显示出来”[5]。透过海涅在此过分的爱国热情,分明还可以发现存在一种尤其适合于某种思想之语言的证据。当然,诗人海涅只是模糊地感受到思想和语言之间功能的适应性,他还远没有触及到语言和思想之间本质的相关性。那种本质的相关性,用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话说就是,“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6]”。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7]。一言以蔽之,语言是思想的语言,思想是处在语言中的思想,语言本身就是思想,因而新的思想必定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新语言。
另外,一切语言都是历史的语言。人类的语言会受到沉积在语词上面的传统内容和含义的纠缠,我将之称作“语言的惰性”。已然固定在语词上的旧有含义和用法就如未曾消散的魂灵,在未被驱逐和清洗之前总是妨碍到其承载和表达新思想的功能。因而不对传统术语作相应的处理,势必带来诸多不便和烦难。所谓语言转换,宽泛说来是对历史的语言之旧有的结构和形式进行处理以执行某种全新的功能。在此意义上,语言转换就是为新思想清理基地,并匡扶配合新思想的光大流行。因此,无论是赋予旧词语以新的意义还是自创新词,都属于话语转换的范畴,只不过是不同的转换方式罢了。更为根本地说,新思想的发生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而真正的语言转换必然意味着新的思想,二者本是同一个过程。新思想直接要求新的语言,新语言总已经是新的思想,两者除非同时到来,否则一个也不会到来。全然未经转换的语言不可能在新思想的体系中取得一个位置,正如新的哲学或新的思想不可能在纯粹旧术语的体系中产生出来。
概括一下,由于语言根本上就是思想,是思想自己在“说话”,因此,新哲学或新思想的出现,天然地伴随着语言的转换和更新;而语言转换的实质,无非就是就是新哲学的发生。转换语言就是革新思想,而革新思想就是变更语言。就此而言,通过语言上的转换以适应哲学变革之任务,此种主张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需的。
二、是否可能
从经验角度看,人类语言始终向变化敞开着大门。正是从不锁闭,永远向变化敞开,才造就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但语言的变化绝非是任意的,演变受制于语言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就是语言同其时代之“思想”若合符节的规定性。新语言和新思想总是一道来临的。因此,无视语言的本质渊源对语言所做的任意改变就总是存在风险。当新的思想还未被召唤出来,或新思想不曾为新词语担保时,强行造出并使用新的语言只会引发两种结果:要么是败坏了语言,要么是搅乱了思想。作为无思想或脱离思想的杜撰与造作,它因此绝不能说是实现了“语言转换”,只能算是语言的“颠倒或迷误”。
那么,真正的语言转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讨论班实际上对此做出了原则性的回答。通过对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相关文本的引用与解读,海德格尔获得了一个基本重要的观点:同一种语言在不改变其形式与结构的情况下,能够履行新的功能。不过这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上,即“内在澄明”与“对外部境况的守护”[1]。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旧的语言就能履行新的功能(履行新功能的旧语言在此就是新语言),亦即语言的转换是能够实现的。
然则海德格尔何以会说“自铸新词是无益的”?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他“自铸新词”的不成功。但它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隐含在海氏对“自铸新词”的理解之中。海德格尔所谓的“自铸新词”,指的乃是在“存在”和“大道”自身尚未显现,新思想之境域尚未崭露的情况下,人为地、无依傍地生造出某些新的词语。此种违逆“思想之天命”的“僭越之举”,显然是无益的,非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至于新思想之视界已变得明晰,形而上学的束缚已被挣脱,此时人类“创造新词”的活动,在海德格尔看来,全然不是“自铸新词”(自行铸造),而是“存在”的自我显现、“大道”之自行“道说”、“思想”的自主发声。或者说,人无法说出新的词语,新词语是自己从人口中涌出的。“不是人‘用’语言,而是语言‘用’人”、“人归属于‘大道’,响应‘大道之说’而有所说”[2]。很清楚,后一种情形下的“创造新词”,即让新词从思想的本质渊源中掉落下来,这件事情简直就是不可违拗的。它也必定对新思想的发生有益,因为它直接就是新思想之发生。因此,“自铸新词”有益抑或无益,实际上仅取决于一点:即新思想之境域是否已经开启。依此而论,海德格尔说“自铸新词是无益的”,所表明的恰是“新思想自身尚未降临”、“尚未超出形而上学的范围”这种基本现实,甚至也可视作是海德格尔终究未能超出形而上学的一条有力证据。
根本而言,语言不可能偏离思想。如同卡西尔指出的,语言“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达思想的不断反复的劳作”、“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Weltansichten)的差异”[8]。由于洞察到“言语的基本框架”与“思想浮现”之间的相似性和内容的同一性,文德勒也说:“言语的对象与思想的对象几乎普遍地同一”、“如果所说出的东西是带着意义说出来的而不仅仅是鹦鹉学舌,那么它就是思想,但它可以不是说话者真实的思想[9]”。可以说,语言是“能思的器官”,本质的语言就是思想、世界观,是对存在和大道最切近的领悟。因此,语言变化注定是和思想变革同步的,哲学上的变革总是伴随着语言上的转换。也就是说,只要存在已经召唤出新的思想,一种语言上的转变就必定是可能的,可能性在此表现为“自然的必然”。当此之时,“自铸新词”和“旧词新用”都是可能的,因为它们有“真正的思”为其担保,是对“存在的召唤”和“大道之呼声”直接响应。
三、如何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那种对哲学变革来说不可或缺的语言转换,如何才能够真实地发生?对此,还得回到海德格尔通过洪堡所赢获的洞见,即真实的语言转换必备的两个条件:“内在澄明”和“对外部境况的守护”。两个条件原则上就是两条道路,是让“自铸新词”变得顺“理”成章和富有意义,从词语的外部形式(语义、词形、结构)变化到本质的语言转换,一句话,是使现成的语言化身为新语言的必由之路。
“内在澄明”,根据海氏的理解,就是要使“存在自身显示出来,换言之,此在要养成《存在与时间》所说的‘存在领悟’的东西”[1]。简单些说,“内在澄明”即让对存在的领悟、“存在之真理”、“思想”本身显现出来。唯有作为“对世界的总体感受方式和立场之变革”的新思想已然降临,它才能自行将新的词语召唤出来,借此也才能实现一种真实的话语转换。海德格尔相信,只要新思想的境域已被打开,那么,新的语言的产生就是随之而来的事情。对此他说得分明:“在《存在与时间》中当作问题提出来的、对作为存在的存在之追问,便如此改进着存在领悟,以至于这种改进因此同时也就要求着更新语言。[1]”也就是说,出于“存在领悟”(思想)的改进,直接就会带出一种新的语言。此种理解当然是无误的。当新哲学在地平线上显露身影,新的语言自然会应运而生,并不需要作为“语言之生物”的人的努力。此时,无论旧词新用还是自创新词,都将变极其简便易行:由于新思想的贯穿和担保,旧语言直接就有了新的内涵,旧语言直接就实现了更新和转换;创造新词这时还有一个便利,它避开了旧词背后的历史沉积,避开了旧思想背景中的含义和用法之纠缠,因此免去了清理这些“纠缠”的烦难。因此,语言转换实际上可以说是思想出于“道说”自身的需要,是由思想自行召唤出来的重新命名。基于此,海德格尔孜孜不倦地从事“内在澄明”的工作,着魔般地要“创制”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不论是早期“从此在来逼问存在”,还是后期“让存在之真理自行发生”,都是海德格尔在不同方向上“使思想自我显身”之努力。
问题的关键乃在于,海德格尔错误地理解了“外部守护”。 在关于“外部守护”的讨论中,海德格尔指出,当前必须考察的两个“外部条件”是:“语言自身的衰败与贫乏”、因为计算机运算作为语言的尺度而引发的“语言脱离其自然生长的可能性而僵化。[1]”首先是语言衰败贫乏的现状,其次是技术对此种境况的加剧。语言的衰败问题是一种历史性遭际。作为历史性的遭际,语言的衰败、贫乏和僵化,根源于语言和旧思想的分离紧张关系,它实际上意味着旧思想的衰弱和退化;技术对语言之衰败境况的加剧,起因于语言自身的错误“尺度”。语言之所以丧失了恰当适宜的尺度,根据就在思想自身之内在尺度的混乱和模棱两可。可见,在海德格尔那里,所谓语言外部境况的破败,说到底无非是思想自身的内部混乱和含糊不清。因此,海德格尔实际上将整顿语言的“历史不清白状态”,亦即对思想自身之“迷雾”的清理,视作是对语言展开的“外部守护”。他梳理和清洗现存语言的句式、意义和用法,以为就是对语言之外部境况的守护,以为语言的自我更新借此就能够实现,而新思想也必定会因此而大获益处。但是,对语言外部运用环境所做的清理,根本说来指向的还是语言背后的思想。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理解的“外部守护”,实际上仍然从属于“内部澄清”。如此就跌入恶之循环:为了新思想的顺利发生,必须促成一种语言的转换,而为了这种语言转换的实现,又不得不乞灵于思想的自我澄清。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海德格尔没有破除思想的内在性,他错过了真正“外部的”东西,那比思想和语言都更为源始和基础的东西。而不能展开真实的“外部守护”,单从语言和思想的内部谋求革新,实际上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底什么是“外部守护”?必须首先懂得什么是“外部”,才有可能进行“外部守护”。唯有马克思真正把握到那个外部的东西,即作为思想和语言的之共同根基的“社会生活”、“感性对象性活动”。因此,马克思也能够揭明和展开真实的“外部守护”:就是要使为思想和语言奠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革命化”。马克思异于和超出海德格尔的地方就在这里。除此之外,在对语言和思想的一般理解上,他同海德格尔并无实质性的分歧。马克思承认语言和思想间的本质渊源。他说:“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7]”很清楚,语言就是“感性意识”的物化,语言就是思想的涌出,就是思想本身。马克思同样有感于语言衰败贫乏之现实。他写道,“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7]”此种状况显然要求改善和疗治,要求从外部进行守护以拯救语言之破败现实。但在对语言病变之原因的分析上,马克思并未拘执于语言和思想的“纠葛”、罩在语言身上的历史尘埃,而是将其推进到思想、语言、“感性意识”的外部根据层面,推进到“现实的社会存在”和“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层面。正是感性活动的异化,社会现实对人之生存的压制,才造就了扭曲的感性意识(思想),才引发了现存语言的非本真性。唯有重建人的本真生存,才能赢获属人的本真语言。而从外部守护语言,就是要守护人的感性活动(生存)。因此,对马克思而言,关于语言的“外部守护”,最终就归结为对人类社会的实存性结构和活动根基的革命性要求:须通过现实的社会运动来改造社会现实,从而实现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和语言的解放,绝不像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以为只需做一些思想的、观念的、或者词句的改变,就能疗治当前语言的顽疾了。
马克思当然也完成了对语言的“内在澄明”。准确地说,正因为马克思实现了对语言的外部守护,他才能真正完成对语言的内在澄清。“内在澄清”和“外部守护”总是相互依存的,任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完成除非同时完成。由于洞察到语言和思想之共同的、坚固的外部根基——感性活动和感性意识,马克思彻底克服了旧形而上学,建立了新的“感性活动”本体论,完成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由于思想的变革在马克思那里已然完成,因此我们看到,其哲学体系中虽留存了不少旧的词语(术语),但这些词语的内涵与意义已决定性地超出了旧范围。在新哲学的背景下、具备新意蕴、承担新功能的旧语言,或称在形而上学之外使用形而上学的语言,虽未曾有语音、结构和形式上的改变,但依其本质而言,早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语言了。因此,马克思也成功地实现了话语转换。或者也可以说,正因为成功实现了话语转换,他才能真实地完成哲学变革。这一切所以可能,关键之关键在于,马克思真正抓住了“内在性”的“外部现实”,把握到作为思想和语言之根基的“感性活动”,包括理论的把握和实践的把握。
讨论至此,我们的结论是:1.就语言和思想的本质关系来看,说“语言就是思想”当然能够成立,但恐怕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揭示或许与遮蔽一样多。它凸显了双方的非此不可的关系,却容易被误解为“同一性”或“同质性”。两者毕竟存在区别,区别不在于思想比语言更基础,不在于思想离源头更近,而在于思想比语言“更充实”或“更丰满”,因为“存在着没有被揭示、没有被表达、没有声音的思想。[9]”也许,更贴切的说法只能是,语言和思想存在天然的“亲近(密)”关系。此种关系与其说是“同一性”或“相互规定”,毋宁说是语言和思想的同源性:二者共同源出于“人之生存”或“感性活动”。由于这种本质同源性,语言和思想就总是显现出某种“暗合”,且能在各自的展开进程中“相互构成”和“彼此影响”。
2.因此,在“感性活动”层面上发生的根基性变化,必定会同时引发语言转换和思想变革。二者总是一道发生的,走着同一条道路,就此而言,哲学变革就是一种话语转换。但出于“语言的惰性”,当新思想的基地开始崭露之时,相应地寻求一种话语转换(包括创造新词和旧词新用)是有益的,相反情形下则注定是毫无意义的。
3.语言转换(思想变革)的实现依赖于“内在澄明”和“外部守护”的同时完成。两者也只能同时完成,否则都不可能完成。因为,“内在澄明”和“外部守护”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用马克思的术语说,所谓“内在澄明”,就是澄清“感性意识”(海氏称为“思想”);而“外部守护”的意思是,对那作为语言和思想之共同的外部根基的“感性活动”展开守护。如同感性活动和感性意识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内在澄明和外部守护也只能在同一过程中完成。
4.海德格尔仅靠“内部澄清”来促成语言的转换,因此他并未实现语言的转换,也未完成思想的变革。由于未曾真正触及“感性活动”领域,他就无法从事真实的“外部守护”,无法开显出语言和思想之“存在”(本质),也就无法“完成”思想变革和语言转换。因为,“完成就是:把一种东西展开出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来,把它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带出来,producere(完成)。因此真正说来只有已经存在的东西才可完成。[4]”
5.马克思做到了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看护语言,因此他无需创造什么新词,就既实现了语言的转换,也完成了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切实把握到“感性活动”这一外部根基,对“感性活动”的理论守护(哲学变革)和实践守护(现实运动),乃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和语言转换的枢机所在。
[1](法)F·费迪耶,丁耘.“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世界哲学,2001(3).
[2]孙周兴.编者引论[A].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5;18-19.
[3](德)海德格尔,孙周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1;252-253.
[4](德)海德格尔,熊伟.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358.
[5](德)海涅,海安.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76.
[6](德)洪堡,姚小平.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2.
[7](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90;183.
[8](德)卡西尔,甘阳.人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168.
[9](美)文德勒,牟博.思想[A].马蒂尼奇.语言哲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80;281.
B516.54
A
1002-3240(2017)02-0035-05
2016-12-12
许小委(1981-),湖南慈利人,哲学博士,惠州学院政法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思想,价值哲学和现代性问题等。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