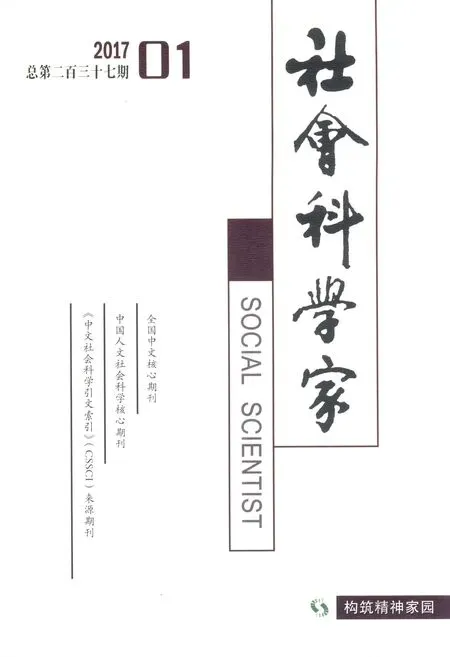从玉教到儒教和道教
——从大传统的信仰神话看华夏思想的原型
2017-04-10叶舒宪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文史论丛】
从玉教到儒教和道教
——从大传统的信仰神话看华夏思想的原型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从源流和演变的历史传承视角,考察史前文化大传统的玉教神话对后代小传统的文化衍生作用:其一是儒教的君子佩玉制和君子比德于玉说,其二是道教信仰的三清宇宙观和主神玉皇大帝。通过其源流和演化过程的具体分析,揭示儒道两家思想的观念原型和物质原型。进而梳理出中国思想史前史的信仰之根。
玉教;君子佩玉;玉皇大帝;国族想象
作为一种先于文明国家而存在的宗教信仰和神话观念体系,玉教神话以物神崇拜的方式(拜物教)在东亚地区传播和延续数千载,这一大传统的遗产,在华夏王朝的精神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玉教的文化基因或文化衍生功能十分明显,不仅对后世文化小传统中出现的各种宗教和准宗教现象如儒释道等,均有母胎一般的孕育催生作用或接引作用,就连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也离不开它的奠基性影响。从秦始皇到清代明代皇帝,两千一百多年的华夏国家王权都是用玉玺来做唯一的象征代表,这就是小传统圣物来自大传统渊源的明证。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此类文化衍生作用。即:从玉教到儒教;从玉教到道教。从查源知流的意义上,将以往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儒家主干说和道教主干说均做出相对化的解构,视为小传统中次生的文化现象,而将史前流行的玉教神话信仰系统,理解为原生的文化现象,确认为考察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宗教史等问题的真正开端。
一、儒家君子佩玉制:玉教的伦理化
儒教又从世俗意义上被称作儒家,它不是华夏国家佩玉制度的首创者,也不是相关规定的发布者。而是相关伦理学说的阐释者与传播者。早在儒教创始人孔孟的时代到来之前,西周到东周早期的出土文物,就给出国家佩玉制度的明显证据。文献方面如《诗经》,其中有不少佩玉礼俗的描写。如《卫风·竹竿》写到巫傩人士的佩玉情况:“巧笑之瑳,佩玉之傩。”[1]傩为中国民间流行的跳神表演,即华夏戏剧文化的古老原型。东周时期文献中的傩之佩玉说,表明是继承史前社会中巫师、萨满一类神职人员的用玉传统。《郑风·有女同车》和《魏风·汾沮洳》都表现的是美女佩玉的情况: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1]
彼其之子,美如玉。[1]
再如《卫风·淇奥》一篇,则用攻玉的实践磨练来比喻君子。其词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同一篇诗还描述君子佩玉的景致::“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1]《齐风·著》云:“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1]这两处的佩玉都指玉耳饰。故曰充耳。从考古发现的大传统实物资料看,切磋琢磨的治玉传统始于八千年前的北方西辽河地区,随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玉耳饰是华夏玉文化最早发展起来的玉器种类。玉耳玦始见于公元前6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随后逐渐地向南方传播,在距今七千年之际抵达江苏、浙江沿海一带。向东跨越海洋,经朝鲜半岛抵达日本。有日本列岛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玉玦实物为证。“若从史前玉器形制上看,则兴隆洼文化的弯条形玉与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单孔璜形玉佩[2],早在8000至7000年前就已经流行,如黑龙江的倭肯哈达洞穴遗址出土玉器,或可视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出土的单孔曲玉之祖型。有些尺寸较小的单孔璜形佩,其功能应该理解为耳坠,因此其原初的佩戴部位不是挂在前胸,而是和玉玦一样的耳饰。”[3]
从整体上考察东亚玉器生产源流的新视角,是建立在史前考古新发现和系统性资料整合基础上的,可以说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当代学术认识。随着层出不穷的新发掘材料的问世,日后将会有更周全的观点推进,这也是可以预期的。过去研究儒家起源的学者,局限在书本知识的有限范围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穿透历史深度的源流认识。
与早期出现的玉耳饰相比,更复杂的佩玉是玉组佩,可用于人的全身,从北方红山文化墓葬中可见其例。考古学称之为“唯玉为葬”。到商周以后还衍生出用于车马仪仗的车马玉饰等现象。后者如《小雅·采芑》所描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1]用玉器和金属器的组合装饰统治阶层使用的车马,其神话想象的蕴含包括“天马行空”一类飞升的幻觉。玉器是出场有助于把现实的交通工具想象升格为神话的载体。同样,新石器时代末期修筑城池的防御性设施,也发现有用玉礼器穿插在城墙之中的奇特礼俗。这显然是要借助于玉器中承载的神圣能量,发挥精神武器的作用,以阻挡城墙之外的敌人[4]。
玉石之中潜在强大正能量的信仰,到了曹雪芹的时代依然继续传承不衰,乃至有文学化的“通灵宝玉”说。如今透过文学表象做还原式的理解:灵即神灵,通灵即通神也。佩戴玉器可以保佑主人身心的民间信仰,至今仍然在中国广泛地流传着。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儒家君子佩玉说的巨大影响力所致,至少是有其推波助澜之功的。《大雅·棫朴》则用金玉的美丽外观比喻君王的风采:“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1]古诗中更多的用法则是以美玉比喻君子。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1]这里突出表达的是儒家君子理想,用“温”这样的物理特征来比喻君子的人格亲和力。这样的比喻基于对新疆和田玉籽料物理特征的认识。这是西周穆王去昆仑山采玉以来,给华夏文明王权带来的新联想。此前的用玉是各自为政式的就地取材现象,在西周王权势力与新疆美玉原产地之间建立联系以后,就地取材的玉器生产逐渐被和田玉独尊的新现实景观所替代。从《尚书·顾命》所反映的西周初年王室珍藏的国家重宝情况看,当时从各地采集来的玉石占据着国家珍宝中的绝对大多数[5]。和田玉独尊的局面尚未形成。到周穆王去昆仑山以后,则情况突变,新疆和田玉后来居上信仰变迁过程,到战国时期成书的《礼记·玉藻》篇,体现为按照和田玉颜色种类来区分社会等级制官方规定,所谓“天子佩白玉”之说,显然是让和田玉中的白玉凌驾到其他颜色玉石之上,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物。[6]
从《诗经》的此类修辞不难看出,周代的诗歌传统中已经形成一种借玉喻人的表达模式,或是突出美人如玉,或是突出君王与君子的完美人格。推究君子佩玉制度的起源,无疑与华夏礼文化的起源有关。巫傩作为社会中的神职人员,应当是最早在佩玉者群体。由神职人员掌握的祭祀礼仪活动,当然也离不开玉礼器。汉字“禮”这个字的字形,从示,从豊。豊字,其形象表达作为容器的豆中,放着成串的物体。文字学家们考证说,豆上的物体,“象三玉之连,其贯也。”[7]古时候的巫,是礼的主持人,他们也被称为“靈”或“灵巫”。“玉”与“礼”、“玉”与“灵巫”的关系非同一般。“礼”字之所以是陈玉于豆而祭,灵巫之所以“以玉事神”,皆是源自史前的文化大传统。到了文献书写的小传统中,各种相关的记载当然是其流而非其源。
《尚书·舜典》有“五玉”之说:“修五礼、五玉。”[1]后者即璜、璧、璋、珪、琮五种造型的玉礼器。《孔传》:“修吉凶宾军嘉之礼,五等诸侯执其玉。”[1]可见用圭璧等构成的“五玉”礼器,既是政治等级制度的标志,又是封建礼仪制度的规定性物质符号。《大雅·云汉》云:“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1]表明了圭璧两种玉器的祭神通神功效。注疏家认为这是说周宣王时天降旱灾饥馑,为了祈求雨水,没有神灵不曾祭奠,没有牺牲不曾奉献,可即使是礼神用的玉圭玉璧都已用尽,天地神灵也不肯听我一言,给我回报。玉礼器成为人神沟通的中介,人神对话的神话信仰之载体,其承载神力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这就给儒家的崇玉学说和佩玉制度找到信仰观念的基础。此类的观念直接承袭自史前文化大传统的玉教意识形态。
既然弄清了玉与神的关联给佩玉制度奠定观念基础,再看上古文献中的如下记述,就可以洞若观火。《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1]为什么周代贵族男性在一出生时就要弄璋?玉器的神圣与祥瑞作用为什么直接表现为君子佩玉制度?如果说古代观念中的人类总体被按照性别,区分为男贵女贱两大类。那么儒家的男尊女卑观就这样类比为物质化的玉与瓦。《礼记》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1]这一段为人熟知的描述,其实也点明了君子佩玉是所以然,即“君子于玉比德”。由于坚信玉中潜含着神圣的天命和天赐生命力——精或德,人便可以充分借助于玉的生命能量,增加自己的人格力量。需要留意的是,在一开始,玉中潜含的“德”本来不是伦理道德之德,而是神圣生命力崇拜之德,即与“精”或“灵”同义。相当于人类学所说的“马那”或“灵力”。由于孔子以后儒家对“德”的再造,“德”便衍生为伦理和品德的意义。玉有五德、七德、九德、十一德的种种说法,从先秦到两汉得以完成。后人一般都不容易洞悉“德”字的本意,所以就都依照伦理化的方式去理解玉德,延续至今。
恢复玉德说的原初本意,需要回到周代人的信仰语境之中。《秦风·终南》云:“佩玉将将,寿考不亡。”[1]说明了佩玉与信仰神圣生命力的关系。《大雅·嵩高》云:“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1]大件的玉礼器如圭璋,虽不用作佩饰,同样有显示天命和保佑的作用。这表明,政权的生命力与个体的生命力,都需要借助于玉的正能量。台湾学者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关注到中国仙道思想的起源与现实地理中的昆仑山有特殊关联,却只讲昆仑山视为月神信仰的神山[8],完全忽略了现实中的昆仑山本来就是产玉之山。要知道,永生不死的象征物,对于东亚先民而言,早自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时代,就已经聚焦到美玉这种物质本身了。
佩玉不仅装饰主人的身体,而且也装点着主人身佩的刀剑。《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1]讲的就是用美玉装饰佩刀的情况。《小雅·瞻彼洛矣》亦云:“君子至止,鞞琫有珌。”[1]《小雅·大东》云:“鞙鞙佩璲,不以其长。”[1]鞙珮指垂挂在刀鞘上的玉珮。它不光有视觉上的效果,还能发出听觉上的信息,行使辟邪防灾的功能。如《晋书·舆服志》所说:“衣兼鞙珮,衡载鸣和,是以闲邪屏弃,不可入也。”[9]《晋书》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玉佩对于主人生命的特殊庇护作用,可以说完全承袭自史前玉教信仰的关键教义。
《大雅·卷阿》云:“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1]《毛诗正义》解释说:“言文王之有圣德,其文如雕琢,其质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叹美之。”[1]因其具有文质双全,表里如一的圣德,故能纲纪严明,统治四方。后例则是颂美成王。“颙颙”,温和恭敬貌,“卬卬”,气宇轩昂貌。此句旨在盛赞周成王有“如圭如璋”的高尚品德,威仪不凡,所以才享有名望和声誉。这是史前期的玉教信仰在儒家礼学小传统中向伦理化的演变方向衍生的典型案例。
清代学者俞樾说:“古人之词,凡所甚美者则以玉言之。《尚书》之‘玉食’,《礼记》之‘玉女’,《仪礼》之‘玉锦’,皆是也。”[10]从俞樾的时代到今日,华夏国家地下出土的玉礼器已经堪称汗牛充栋。在大量出土玉器面前,我们对儒家话语的来源之理解和解释,当然也要大大超越前人。一部15卷本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虽然还远远不是全覆盖式的“全集”,毕竟能够聊胜于无,有助于对各地各个时代的玉器概况提供总体式把握。“玉成”中国的文化真相正在当今时代逐渐被揭开。
二、道教宇宙观与玉皇大帝信仰
从东周时期与儒家并列的道家思想者老子、庄子,到东汉时代道教宗教体系的形成,其信仰要素中同样有来自史前玉教神话的重要原型。其线索体现《道德经》第七十章的名言:“圣人被褐怀玉”[11],以及《庄子》中的比喻:以日月为连璧。首先就道教宇宙观“三清”说而言,玉清、上清、太清的三元划分以玉清为首。这一观念基于以玉为天、以玉为天神世界标志物的大传统信仰。在上古文献叙事中的典型表现则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由此引发出的“玉宇琼楼”想象,这在中国文学和语言中已经呈现为弥漫性的分布。道教崇奉的女神西王母,其原型来自昆仑玉山(现实)崇拜。从新疆昆仑山的“玉山西王母”到后世道教想象的至高男神——“玉皇大帝”,也只是神灵的性别伴随父权制意识形态展开的一种转换而已。《封神演义·玉清道人诗》云:
函关初出至昆仑,一统华夷属道门;
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倒性还存。[12]
这是将道家圣人老子西游的目标落实到出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同时兼顾老子化胡说,将佛教的神话圣山须弥山也统和到“一统华夷”的道家天下系统之中。
对玉的崇拜始于神话观念。早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就有“玉帛为二精”(《国语·楚语》)的公开教义表白。到了屈原楚辞中,更明确地声称要“登昆仑兮食玉英”(《远游》)。这就将昆仑山和田玉神话同后世道教的食玉炼丹求永生信条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据战国文献《竹书纪年》的记录,远在西域昆仑山的西王母曾经在虞舜时代来到中原王朝献上白玉环。同样是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则记录黄帝吃玉膏的细节。这些都给道教徒食玉粉和饮玉露的想象提供深厚的信仰背景。华夏的古礼之源离不开玉器。古人以玉器祭祀天地山川神灵的情况,也见于《山海经》和《礼记》等书。道教仪式活动的操练者当然对此并不陌生。道教信奉的“三清宇宙观”落实在大地山河上,那就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界的三清山,它又名少华山,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三清山,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命名法的产物。而陕西华阴的华山,也是被初民神话想象为玉山的,因为其山体是一块长达25公里的巨大花岗岩构成的,五座山峰犹如向天绽放的五瓣莲花。汉代以后流行的华山玉女传说,华山的寺庙名为玉泉寺,都表明华山即玉山的信仰真相。这也给江西上饶的玉山、三清山、少华山之得名,带来贯通式解读的线索。
元始天尊是道教最高神灵“三清”尊神之一,生于太无之先,禀自然之气,初称元始天王。东晋葛洪《枕中书》云:“昔二仪未分,溟滓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13]后来的道教神话又有更具体的描述:元始天王,开天辟地,治世成功,蜕去躯壳,游行空中,见圣女太元,喜其贞洁,化青光投入其口。圣女怀孕十二年,始化生于背膂之间,言语行动常有彩云护体。因其前身是盘古、元始天王,就称为元始天尊。
在道教信徒看来,元始天尊就是宇宙之祖,神灵之宗。相当于基督教的创世主神耶和华。相传在大罗天形成之时,元始祖尊和太元圣母化育了东王公和西王母。西王母是宇宙西真清圣妙真善美精元衍化,使天地万物演炼而成的女神,东王公是大罗天仙之主。宇宙建成三十六天,其中分布有九天系。元始天尊在大罗天境分化九皇,治理宇宙。从资格和神格地位而言,诸神中没有比这位神灵更尊贵者。还有更晚时期的说法认为,是元始天尊在太初大纪里,与玉皇、斗母等神尊共同实现开天辟地的伟业。
《历代神仙通鉴》称元始天尊为“主宰天界之祖”。在太元诞生前便存在,尊称为元始。在无量劫数来临之时,用天道教化众生,故尊为天尊。道经记载中元始天尊所创立的道教,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三号虽殊,本同为一,都是道的化身。如《道门十规》所云:“玄元始三气化生,其本则一。”[13]
道家和道教分别产生于先秦时代和汉代,其神话基础为中国特有的仙话,成仙得道,永生不死,是其终极的修炼理想。在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时代之前很久,永生不死的神话就一直在大传统中流传,并且始终围绕着一种核心物质——玉,形成源远流长的东亚洲拜物教传统①由于不了解大传统的不死信仰之存在,顾颉刚先生把神仙信仰的起源归结于战国时代的燕国和齐国,并提出两个原因论的解说:一是时代的压迫,二是战国时的思想解放。这显然是就事论事的片面看法。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页。。玉殓葬,这样一种东亚特殊的史前葬俗,就是见证永生不死神话理想的考古实物证明。让玉器伴随着死者在死后升天的全部旅程。等到道教神话谱系在东汉以后得以完备时,国人关于天界最高主神玉皇大帝的信仰,就是采用大传统的物神之名来命名——玉。我们把这种后起的神话与信仰视为文化原型编码的再编码现象。似乎中国人不可能用其他的任何物质的名称,来指代他们心目中的至高无上之存在,只能是“玉”。理由仅此一个就足够了,玉是国人的信仰之根和拜物之本源。
这种以玉为神的现象,还可以在邻国日本的文化方面找到有趣的参照。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一书,其第八段一书第六云:“一书曰:大国主神,亦名大物主神,亦号国作大己贵命,亦曰苇原丑男,亦曰八千戈神,亦曰大国玉神,亦曰顕国玉神。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14]这里一共排列出大国主神的六种别称神名(《古事记》中是五种),其中的第五第六两种都叫“玉神”。玉本为神圣物,用以修饰“神”,暗示着日本神灵信仰的历史深处,隐含着以玉为神的大传统之观念。在《记》《纪》二书中,以玉为名的神不在少数,如玉祖命、布刀玉命、海神之女丰玉毗卖命,等等,其命名的神圣编码意蕴,均可以通过举一反三的方式加以诠释。《日本书纪》第六段一书第二,讲到日神(即天照大御神)躲进天石窟不出,诸神忧之,乃使“忌部远祖,太玉者,造币。玉作部远祖,豊玉者,造玉。”[14]河村秀根集解引《姓氏录右京》“神别”条云:“曰玉作,连高魂,命,孙天,明玉,命之后也。天津彦火,琼琼杵,尊降幸于苇原中国。时与五氏神部,陪从皇孙降来。是时造作王璧,以为神币,故号玉祖连,亦号玉作连。按:《纪》中所载,玉作者或曰羽明玉,或曰丰玉,或曰天明玉,或曰玉屋,或曰栉明玉。盖因所传而异名乎?且别人乎?不知孰是。”[14]从认知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观点看,对同一事物的别称和异名越多,表明此一事物在该文化社会中的重要性越高,引人关注的程度也越高。作为日本上古王权附属机构的玉作部之所以有那样多的不同称谓,充斥于古籍之中,让专业注释家们都感到眼花缭乱和无所适从,这足以说明玉礼器生产对于国家王权建构的举足轻重作用。这一称谓符号现象也反过来有助于理解,日本的神名中多有以玉为名的价值观投射现象。[3]
以玉为神的信仰来自东亚史前大传统,亚洲以外的国家文化中自然不会有这样的信念。当大英帝国的码噶尔尼使团来到北京皇城,获得乾隆皇帝赏赐的玉如意时,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件器物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的价值的意义,以至于当成一件随便打发三流客人的工艺品——玻璃棒子,甚至错误地感觉到好像受了中国统治者的侮辱。如果英国使者知道美玉在中国文化中独尊品格,以及白玉在皇家意识形态中的至高无上价值联想,那么他们或许会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地叩谢乾隆皇帝。
道教神话谱把天神世界想象为琼楼玉宇的物质构造,其中的主神也非玉皇莫属。这方面的道理无需多论,只要看看中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凡是最高峰一律美称“玉皇顶”的现象,就能够心领神会。中国人信奉的多神教以玉皇大帝为统帅,非常放心地让他独掌天地万物的统治权。要问天神如何管理地上的事情?请看下面一个案例:河北省南部流行神码(木版年画的祖型)的内丘县民间,却广泛流传着“后土奶奶”的信仰和相关民间传说。如内丘鹊山的扁鹊庙内,有69岁的农民宁和柱讲述的《大玉皇、小玉皇》:
据说后土奶奶受玉皇大帝教化,消除了思凡的心思。奶奶就想法点化人类,让天下人安居乐业。哪知民间还有一些横行霸道、争权夺势的恶人,常常搅得芸芸众生不得安生。奶奶就借用玉皇大帝的兵马,派天上的神仙下凡来做人间的皇帝或做重要的官宦。后来民间出现什么“文曲星下凡”、“灯笼神下凡”,等等,都是奶奶从玉皇大帝那儿请来的兵。
奶奶为了让人们知道玉皇大帝派了神仙下凡,好让人们弃恶从善,遇事先为别人着想,犯了错不但要承认还要自觉改正,就点化人间有罪恶的人来修玉皇殿。奶奶和玉皇走过三府九县十三省,这一带做过亏心事的人经过点化,都不远千里到玉皇殿来捐钱修庙。[15]
文学人类学一派将民间口传叙事视为考证历史文化的第三重证据。在这个民间传说中,依然保留着文化大传统的两大要素:女神信仰和玉石崇拜,分别体现为后土奶奶的信仰和天界的玉皇大帝崇拜。民间信仰在父权制社会中不免遭遇男性中心价值的制约和改造,但是却明确保留着让天神下凡来做好皇帝和清官的政治理想。玉皇殿的建造以神圣空间的物化符号,无言地讲述着神话意识的社会整合功能和心理功能。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学院派人士对此类活态的神话遗产做专门研究。用当地的学者韩秋长的话说:“国内有不少关于神祇的专著,所论都是广义上的神,诸如儒释道的神,而对内丘神码中大量的民间诸神,这些著作也没有专门的论述。木版年画界虽公认神码为木刻版画之祖,全国十几处木板年画产地也有一部分产神码,但很少涉及对神码的探讨及研究。古代资料中,对神码、纸马只有片言只语的记载,无助于我们的研究。”[16]一个普通的北方小县里居然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神话遗产,中国数以千计的县里总共存在多少我们完全陌生的神话资源呢?可以说,没有什么比玉皇大帝的信仰更加普及流行于中国民间。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的神圣是上帝耶和华。因为他被尊为创造主、创世主。一切生命的赐予者。在中国神话世界,玉皇大帝也后来居上地成为这样的创世主。在中原大地民间收集到的一则题为《盘古山》的神话中,将盘古开天,泥土造人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情节母题融为一体。故事说:盘古开天辟地之时,累得睡着了。玉皇大帝看见盘古的疲惫,就派出他的三女儿认盘古做哥哥。二人遂成兄妹。当时有妖魔鬼怪骚扰,他们就做了一个石狮子看守。石狮子叫盘古每天给它嘴里放一个馍,到了七七四十九天,石狮子告诉盘古说:“等我眼一红,你就赶紧叫你妹妹一块往我肚子里钻。”第二天,石狮子眼真的红了,兄妹二人在石狮子肚子里躲避四十九天才出来。兄妹二人用开天辟地的斧做金针,用葛藤做线,补好了天。又经过石头磨盘的验证,二人结为兄妹婚,捏泥土造人。[17]这则中原地区民间口传的创世神话典型地体现着我国民众信仰的万神殿实况:比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更加高一层次的神明,还是玉皇大帝。没有这位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也不会有盘古的创世成功。
玉皇大帝,就这样通过道教信仰传播和文学传播的双重渠道,成为中国人的万神之主。如今我们既然已经通过考古发现而找到了史前大传统的玉教信仰传承情况,那么玉皇之所以为华夏神谱之主神的奥秘,也就超越道教产生的文化小传统,获得深度透视的机缘。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80.325;341;357;321;321;350;426;514;370;127;127;561;437;1482;373;567;542;479;461;546;515.
[2]周晓晶.倭肯哈达玉器及相关问题探析[A].杨伯达.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C].紫禁城出版社,2001.4(图一).
[3]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56;244
[4]叶舒宪.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A].叶舒宪,古方.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C].中华书局,2015.3-29.
[5]叶舒宪.多元“玉成”一体——玉教神话观对华夏统一国家形成的作用[J].社会科学,2015(3).
[6]叶舒宪.从玉教说到玉教新教革命说——华夏文明起源的神话动力学解释理论[J].民族艺术.2016(1).
[7](汉)许慎,(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0.
[8]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M].台北学生书局,1985.30-31.
[9](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751.
[10]《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群经平议(第35卷)·尔雅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71.
[11](魏)王弼,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中华书局,2008.176.
[12](明)许仲琳.封神演义[M].中华书局,2009.537.
[13](明)张宇初,张宇清,张国祥.道藏·第3卷·元始上真众仙记[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版).269;147.
[14](日)河村秀根.书纪集解(卷)[M].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昭和十一年.71;52-53;53.
[15]冯骥才.中国木板年画集成·内丘神码卷[M].中华书局,2009.346-347.
[16]韩秋长.农耕社会人类的精神家园[A].冯骥才.中国木板年画集成·内丘神码卷[C].中华书局,2009.8.
[17]马卉欣.河南民间故事[A].陶阳.中国创世神话[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5.
B932
A
1002-3240(2017)01-0137-06
2016-12-07
叶舒宪(1954-)北京市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博导,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神话学。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