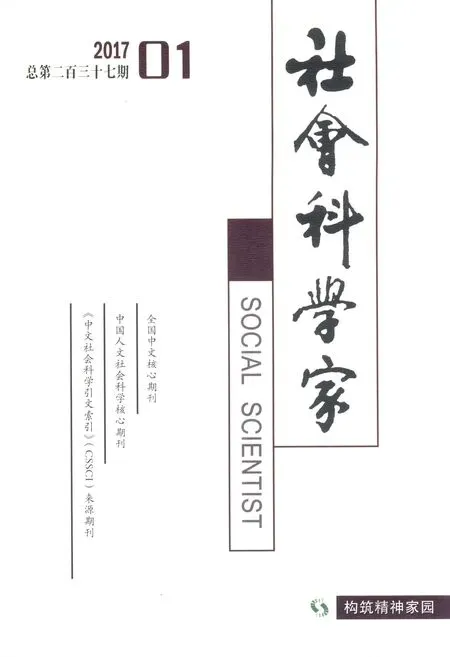论儒家心灵哲学纲领
2017-04-10沈顺福
沈顺福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论儒家心灵哲学纲领
沈顺福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心性关系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心字具有本性与意识双重内涵。早期儒家如孟子心性不分,以本心为性。人心则为本心或性的游离。宋明理学家们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没有区别心与性,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均主张二心说,如朱熹的道心人心说、王阳明的心意说等。其中,朱熹的道心、王阳明的良知便指性或理。而人心、意等则指意识或观念,接近于现代心字的内涵。在主流儒家们看来,作为德性的本心、道心、良知无可挑剔,而作为意识的人心却不可靠,甚至危险。故,他们一致主张德性端正人心,率性、循理便可以正人心。性因此成为人心之主。也就是说,在传统儒家哲学体系中,作为性质的性,通常是作为意识的心的主宰。德性主宰意识。这应该是传统儒家的心灵哲学纲领。
儒家、心、性
心智问题是现代哲学的中心主题。近代笛卡尔将存在建立在心灵思考的基础之上。自此,心灵、思维与意识成为近现代哲学的最强音,并成功地主导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当我们普遍承认人类是理性存在者时,作为理性的表达形式的心灵与意识便成为现代思维的核心。或者说,心灵是我们当代人理解理性人类生存与存在的“阿基米德点”。当我们讲情感(“情”)、善良(“善”)、美好(“美”)、信仰(“信”)、主体(“我”)和灵魂(“神”)等现代概念时,它们通常被理解为心情、心善、心信、心我和心神等。也就是说,理智的心灵是我们理解现代人类存在论中的若干重要学术概念的基石或标准。那么。中国传统儒家的心字具有哪些内涵呢?它与现代心灵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本文将通过梳理心字的若干基本内涵,试图指出:性是心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内涵。同时,当心性分别、心具思虑之意时,传统儒家主张人性为先、心智其次,并且以为人性主导心灵。这便是儒家德性论体系中的心灵哲学基本原理。
我们首先来看看心字的原义。
一、心:器质之心与思维之意
在古汉语中,心的本义是心脏(heart)。《说文》曰:“心,人心也。土藏。[1]在身之中,象形。”心指心脏,简称心。它是人体的一种器官,和“肝、脾、肺、肾”等合为“五藏”[2]。《尚书》曰:“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尚书·商书·盘庚下》)其中并列的“心、腹、肾、肠”,无疑指称五脏六腑类。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类的五脏六腑具有意识属性,比如心具备思维功能,类似于今日的大脑。《黄帝内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2]这类理解残留至今,如侠肝义胆等。其中,心如君主,是人体五脏六腑之主,所有的智慧(“神明”)皆出于此。其余者各司其职。于是,心不仅是生命之元,同时也是思维之本。《黄帝内经》曰:“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2]智、虑、思、意乃是人的思想形式。其载体乃是心。故曰“心有所忆谓之意”,并因此而形成种种思维形式。这便是心思。《尚书》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尚书·周官》)以德事政,便会逸心,以伪事政,则劳心。其中的心无非是大脑的两种状态。
由大脑(心)的活动而产生出意识与观念。《尚书》曰:“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尚书·泰誓上》)三千之众,共有一心。此心指观念。又如《诗经》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诗经·召南·草虫》)“忧心忡忡”、“忧心惴惴”、“我心则悦”、“我心伤悲”等描述了人的主观心灵状态,属于意识。心指意识或观念,它是思维之心的产物。故,古代之心,指称有二。其一指心脏(同时具备大脑功能的heart);其二指由上述器官所产生的意识或观念(mind)。由此,心字在古代文化中通常具备两类基本含义,一是器质载体,即心脏,二是精神现象,即,思维意识等。
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心脏在生命体的生存中具有重要地位,即它是生命体的生存之本。按照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理论,生命的本质在“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有气则生,无气则亡。生存在于气存。《黄帝内经》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2]生命在于精气。此精气,或曰神,或曰魂,或曰魄。精神魂魄皆是气的不同存在方式。气是生存的本质。
按照中医理论,气藏于血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2]成精即精气形成。有了精气便有血气。或者说,精气存于血气之中。故,《黄帝内经》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2]经脉决定人的生死。“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濇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2]血脉昭示了人的生命力。故,中医常以号脉而诊断。
血脉源自心脏。《黄帝内经》曰:“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2]心藏血脉之气。这也符合今日的生物学理论:心脏为血液的流动提供动力。故,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2]血脉源自心脏。脉象即生命的征兆。“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2]由此,古人得出一个结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2]心或心脏乃生存的本源。生存始于心。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心脏乃是生命力的源头。由此,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开发出心的哲学价值,即认为:心是生物体(主要指人)的生存、生长和生成的本源(或本原)。作为本源,心不仅是生存的出发点,更是生存的决定性基础,由此成为生物体生存、生长和生成的主宰者。
二、性是生存之源
这种生物体生存的基础与主宰者,古代儒家哲学通常又称之为性,即生之谓性。于是,心与性产生了联系。汉语的“性”字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心”,另一个是“生”。这两个符号的本义暗示了“性”字的最初内涵,即,心与生。性即初生之心。或者说,初生之心便是性。
性本指生存之初。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皇侃注曰:“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日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恶善既殊,故日相远也。”[3]性指刚生之人,即生存之初。在孔子看来,乍一出生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后天的“习”即行为与驯化等。后来的告子完全继承了这一共同立场,曰:“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性即天生者、初生者。孟子虽然批评了告子的人性观,却也不完全反对这一立场。事实上,孟子也承认,性即天生之材:“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等属于天性、初生者,也可以叫做性。至少在这里,孟子也以为性一定是初生者。当然,孟子以为:并不是所有的初生之材都可以称作性。
后来的荀子也完全接受了生之谓性的立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性即天生的状态,无需作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人性即人天生就具备的东西,接近于生物学中的本能。生即性。或者说,性即初生者。汉代董仲舒将性视作天生之质:“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4]性即天生之质。“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4]性是天生材质,“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4]性如目、如茧、如卵,仅仅是一种初生的质料。《论衡》记载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5]性即天生的状态。
后来的理学家朱熹将性改造为理,原因便在于性字与初生的关系:“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6]性重在生。生存之初便是性。近人傅斯年对先秦遗文进行了一番统计,“统计之结果,识得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皆用生字为之。至于生字之含义,在金文及《诗》、《书》中,并无后人所谓‘性’之一义。而皆属于生之本义。后人所谓性者,其字义自《论语》始有之,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至孟子,此一义始充分发展。”[7]古时只有生字,尚无性字。至孔子始有性字,其内涵接近于生。性即生,或者说,出生之初便是性。
从孟子开始,性不仅指初生之材,而且获得了属性、规定性的内涵,成为主宰事物的生存性质与方向的力量。在孟子看来,初生之质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即,人性是人的规定性,否则的话,“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同时区别于牛马的规定性或属性。人类因为有了这点规定性,便区别于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和动物的差别只有一点点。有了它,人便是人,否则便是禽兽。故,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如果没有这等心(性),人便不再是人。性乃是人的根本属性。在《易传》看来,作为性质的性是成人的基本保证:“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传上》)性是基础。成性是通向仁义的道路:“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周易·系辞传上》)保留了本性便能够成人、成圣。《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性乃上天之命,是上天的规定。人的本性或属性源自天。董仲舒接受了《中庸》等立场,以为:“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月翟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4]性是人秉从于上天的属性或性质,只能够养而不可更改。“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变谓之情,虽持异物,性亦然者,故曰内也,变变之变,谓之外,故虽以情,然不为情说,故曰外物之动性,若神之不守也,积习渐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习忘乃为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4]人情、外物皆可变,其性却在。性如禾、善如米。如果再进一步,性如同种子(魏晋时期的佛教便如此比喻)。禾苗、种子皆突出了事物的性质或规定性。王充亦曰:“用气为性,性成命定。”[5]性是决定性属性。性与质合,便组成了现代汉语的性质。
作为性质,性决定了事物的生存性质与成长方向等,比如人因为人性而成人。其中,性是决定者。因此,性不仅仅是初生者,而且是生存的主宰者、决定者。这是性字的第一个内涵。性字的第二个内涵便是心。性即初生之心。
三、作为性的心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心脏是生存之本。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生存之本却是性。心或性都是生存之本。那么,二者是否一致呢?心性具有怎样的关系呢?答案是:作为本源的心与作为本源的性完全一致。或者说,作为本源的性与作为本源的心是同一个东西。本源之心即是性。或者说,初生之心便是性。
孟子将人的生存本源叫做心(脏)。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贱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贱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人生下来就有四端之心,如同拥有四肢一样。人天生有四心。四心是天生之材。天生之材又叫做性。故,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性便是仁义之根、心。作为根的心(“本心”)便是性。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告子下》)所谓存心便是养性。心与性无异。故,牟宗三曰:“本心即性,心与性为一也。”[8]故,笔者亦曾指出:孟子的“本心主要指作为本原的人性”[9]。心即性。本源之心便是性。
孟子的本心,后来的朱熹称之为“道心”或理:“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10]道心是人心的道理即理,“道心,人心之理。”和“人心便是饥而思食、寒而思衣”相比,道心即“饥而思食后,思量当食与不当食……寒而思衣后,思量当着与不当着,这便是道心。”[10]道心即人心之理。故,朱熹曰:“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心是。”[10]恻隐之心即道心。恻隐之心即性、理。本原之心即理。
王阳明将孟子的本心直接称之为心或良知,曰:“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11]天生禀赋便是性,又叫做心。心性一体。它主宰万事万物。王阳明曰:“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教,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11]事情之理在于心。心、理、性完全统一。本心便是性。
因此,从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心学来看,作为本源的心也可以叫做性,如孟子的本心、张载的天地之心、朱熹的道心、阳明的良知等。或者说,心的部分内涵指称性。心是性。
四、作为指南的意识之心及其不足
作为本源的心指称“本心”、“道心”、“良知”等性。心同性。同时,传统儒家认为这种本源的、材质之心同时具备思维功能,并因此而产生“人心”、“知觉”、“意”等。于是,衍生出思维、意识与观念等内涵。
孟子将意识之心称作人心。它常常与个体的私欲相关,比如民心。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民心依赖于财产,和私欲相关。荀子曰:“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荀子·解蔽》)“未尝不臧”之心包括两项内容:知与臧。所谓知,即知晓。人生有理智。在理智的基础上产生喜好与偏爱。这便是“臧”。因此,“未尝不臧”之心至少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理智,二是喜好。这种理性化的情欲便是欲望。这种人心,后来的朱熹称之为“知觉”。朱熹说:“所谓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10]人心是人的感性意识,包括欲望、感觉等初级意识。这种初级的意识是一种感性的“知觉”:“人心亦只是一个知觉。从饥食渴饮,便是人心。”[10]人心、“知觉”主要指以欲望为主要内容的初级意识。
接受外部影响而形成的心灵状态或观念,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解蔽》)心乃人的形身之主。它发出指令、指导人们的行为。荀子对心灵或观念的实践意义的重视在宋明理学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吸收和继承。二程认为,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观念,知而后行:“故人力行,先须要知。……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12]知先行后。知为行提供方向和指南。行听命于知、心。人类的活动依赖于理性观念。朱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知先行后,但是他将理学家对知的作用的认识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突出强调格物而致知。致知便是格物。格物便是“穷理”:“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3]格物即穷理,然后知至。知至是为人的关键因素之一。
尽管“人心”、“知觉”、“意”等意识对于现实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古人的评价却相当消极。当意识满怀欲望时,这种直接的、感性的、原始的“知觉”或人心,通常以客观对象为内容,因此接受它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不能够得到控制,人可能被带入欲望的洪流中,成为物欲的奴隶,并因此而丧失本心或理性,失去为人之本。因此,对于以经验之物为内容的物欲、私欲之心,孟子不以为然。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孟子·尽心上》)人心有害。其害处类似于饥渴会伤害正味一般。人心也会干扰人们对正常事物的体验。荀子将这种心灵称作“利心”:“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恶》)好利之心便是“利心”。利心即贪欲之心。
现实中的人心有善有恶。朱熹亦说:“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10]人心有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邪恶的。既然有邪恶的可能,那就表明人心有危险。所以说:“人心则危而易陷。”[10]人心危险。王阳明虽然明确反对朱熹的道心人心说,以为只有一个心。但是,事实上,王阳明还是提出了两个和心相关的概念,即“心”与“意”。其所谓“意”,即能够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之意,阳明明确指出,有善有恶:“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1]观念之意有善有恶。
五、性主人心
“人心惟危”。人的主观意识即人心有善有恶,因此比较危险。它需要控制。在正统儒家看来,控制者便是本心、道心或良知。本心、道心或良知又叫性。故,性主宰人心。
孟子好辩。其目的在于“正人心”。纠正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仁声感化:“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仁声便是善气。善气即是性。仁声通之以善气、善性,从而达到改造民心的目的。仁声感化的主要力量便是善性。其二是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断除各种人欲以养心。养心便是养性。这便是去心以存性。或者说,以人性去人心。
情亦是心。对此,王弼提出“性其情”的主张:“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14]情由性定。人心遵循于性。性主心。
朱熹接受了《尚书》的二心说,提出:“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将。”[10]道心如同指挥士兵的将军一般,人心听命于道心。道心是人心之舵:“如何无得!但以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焉耳。”[10]朱熹将道心解读为帝:“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6]能够主宰之道心即是理、性。它是事物的依据、本源和基础,对事物的生存具有决定性。故,道心主人心,即性主心。
王阳明将道心称作“良知”:“道心者,良知之谓也。”[11]“良知”即本源之心。它是本原。王阳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在事便是物。”[11]这里的心便是道心、良知。王阳明认为它是本原和主宰,其发用或呈现便是意。或者说,心是意的本原。心从源头上决定了意。道心便是性、理。王阳明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11]良知、心便是性。良知之性是发用之心的本原。功夫便是人心遵循理或良知。只要人心“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11],只要“好恶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11],人心循理顺性,自然可以致良知。性主心。王阳明甚至从宇宙论的高度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11]心或良知是天地之心,即,它是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是主宰宇宙世界的根本力量。良知是性。以良知为主,其实也是性为主。性主导意。
结论:德性主宰意识
心性关系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心字本有二个内涵,即心脏与意识。其中心脏是生存之本,对于存在者的生存具有决定性地位。早期儒家如孟子心性不分,以本心为性。人心则为本心或性的游离。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们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没有区别心与性,比如朱熹以道心为性或理、王阳明以良知或心为理、性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分别了二心,如朱熹的道心人心说、王阳明的心意说等。其中,朱熹的道心、王阳明的良知便指性或理。而人心、意等则指意识或观念,接近于现代心字的内涵。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二心说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本心为先、为本,人心为后、为末。本心或性是天生的材质或实体。它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即绝对的本源。而人心则是这个本源者产生出的产物,即性生心。心、人心或意识属于性的产品,类似于大脑与意识的关系。尽管后来的理学家用体用论模式解读心性关系,即性是体、心为用,似乎避免了经验的先后关系,但是,从逻辑来看,体依然在先,且是后者的决定者。因此,性与心的天然关联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便是性主心。在儒家们看来,作为德性的本心、道心、良知无可挑剔,而作为意识的人心却不可靠,甚至危险。故,他们一致主张寡欲或正心等。端正人心的法宝便是性,比如孟子的本心、王弼的自然之性、朱熹的道心、王阳明的良知等。在儒家看来,率性、循理便可以正人心。性因此成为人心之主。也就是说,在传统儒家哲学体系中,作为性质的性,通常是作为意识的心的主宰。德性主宰意识。这应该是传统儒家的心灵哲学纲领或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在当代心灵哲学研究中,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心灵哲学的资源。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心字的固有内涵。但是大多数学者却望文生义,简单地将心(heart\brain)理解为mind[15],完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中国传统心论,并建构出所谓的“中国心灵哲学”。他们的中国心灵哲学恰恰遗忘了心的最重要内涵。因此,真实地揭示传统哲学中的心字的内涵有助于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符合中国传统哲学基本实情的心灵哲学或心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心首先是性,然后才是意。观念之意晚于实物或实体之性。这才是中国传统心学或心灵哲学的实情。
[1]许慎.说文解字[Z].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影印版.217.
[2]黄帝内经.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社,1986.879;885;1004;1004;1005;1005;893;895;904;1004;887.
[3]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81.
[4]董仲舒.春秋繁露.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91;792;792;770;808-809.
[5]王充.论衡.诸子集成(7)[M].上海:上海书店,1986.30;13.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82;4.
[7]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510。
[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2.
[9]沈顺福.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J].现代哲学,2014(5).
[1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10;2016;2011;2018;2010;2013;2012;2012;2011.
[1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4;15;117-118;52;6;34;29;29;214.
[1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187-188.
[13]朱熹.大学集注.四书五经(上)[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1.
[14]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631-632.
[15]高新民.中国心灵哲学的“心理多主论”[M].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B222
A
1002-3240(2017)01-0020-06
2016-12-2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比较视野下的儒家哲学基本问题研究”(项目号15BZX052)之阶段成果。
沈顺福(1967-),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