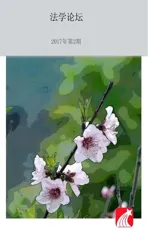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法律构造
2017-04-05侯艳芳
侯艳芳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法律构造
侯艳芳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我国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屡禁不止,社会危害极大,增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具有必要性。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危害行为须同时具备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和胎儿性别示明两个要素;基于公共利益保护而对生育知情权进行的限制应当保持极度克制,胎儿父母不应成为犯罪主体。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主刑的基础刑宜设置为短期自由刑,并宜同时规定加重刑。为保障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有效适用,应当允许运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并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措施。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法律构造;生育权主体去犯罪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
引 言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基于传统文化对性别的特殊偏好等原因,我国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暗箱操作、屡禁不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生命伦理、破坏了生殖规律,而且威胁着母体和胎儿的生命健康,破坏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导致社会管理风险加剧。然而,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现有规制方式仅是行政追责,且存在行政立案门槛高、查处难度大,行政违法成本低、处罚效果不周延,行政处罚力度小、威慑性不足等弊端。面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行政追责乏力的局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实施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胎儿性别终止妊娠行为(以下简称“两非”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我国刑法典缺乏可相衔接的制度设计。“当刑罚威胁的目的在于威慑潜在的违法人员时,那么,只有在实施前就已经尽可能准确地在法律中对被禁止行为加以规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所希望的心理遏制。”*克劳斯·罗可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刑法》没有直接单独将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规定为犯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非法行医罪等相关医事犯罪罪名对其难以进行针对性惩治,增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具有必要性。本文拟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法律构造进行尝试性研究,以推进相关探讨深入进行。
一、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犯罪构成
(一)危害行为的结合性要素: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与胎儿性别示明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危害行为是非基于医学需要而运用鉴定技术确定胎儿性别并将鉴定结果向他人说明的行为,由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和胎儿性别示明两个要素构成。只实施了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而没有将鉴定出的胎儿性别向他人示明,就不可能侵害到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因此不具备刑事可罚性;而不依托于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的单纯胎儿性别示明,只是生活中的一般行为,也不能对其进行刑事评价。
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是利用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判定胎儿性别的单纯医学技术鉴定行为,具体是指在医院或者其他地点(例如装有B超仪器的汽车)运用专用的仪器直接判定胎儿性别的行为。为了适应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外延之确定应当具有“开放性”,将先进的现代医学检测手段(例如“寄血验子”*“寄血验子”是采集母体血液后邮寄到香港,利用DNA产前检测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对于“寄血验子”,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中介人员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可能涉嫌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等罪名。参见范跃红:《为孕妇抽血到香港鉴定胎儿性别,浙江首次以涉嫌非法行医罪依法逮捕此类案件》,载《检察日报》2014年4月23日;黄云峰:《自称“中介”送血样到香港,苍南“寄血验子”案一审开庭》,载《温州都市报》2015年1月8日;朱乐:《“寄血验子”,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载《工人日报》2014年6月21日。)纳入调整范围,而非仅限于当下最为常用的B超等超声波手段。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外延之确定还应当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强调鉴定手段必须能够直接且准确地判定胎儿性别,将通过不能直接反映胎儿性别的B超检查数据*例如,胎儿的长宽比、形状等非直接说明胎儿性别的数据。、母体的饮食偏好等推断出胎儿性别的方式排除出胎儿性别鉴定的外延。“开放性”是对医学检测手段扩容的有效通道,具有入罪的效果,其判断应当以医学领域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为标准,并适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新的医学鉴定手段纳入处罚范围;尊重“谦抑性”强调对医学鉴定手段的限制,具有出罪的效果,其判断应当以医事科学性为标准。
胎儿性别示明是以明示或者默示的形式、用语言或者肢体动作等方式向相关人员表明胎儿性别的行为。胎儿性别示明的对象既包括胎儿性别知情权的主体,也包括其他可能转述胎儿性别的人员。就示明的形式而言,既可以是明示即明确地表示,例如直接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告知;也可以是默示(仅限于作为的默示),即其主张权利或者接受义务的意思表示明确、能够直接根据行为确定意思,例如以点头或者摇头的行为告知。
需要说明的是,惩治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依据在于行为违反了不能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的禁止性规范、破坏了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而行为是否实际对自然生育规律产生了侵害或者侵害危险不是惩治本罪的依据。因此,无论鉴定、示明的胎儿性别是男是女、是否会导致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后果,只要实施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和胎儿性别示明行为且达到法定标准就应当进行刑法评价。胎儿鉴定性别、示明性别与胎儿实际性别是否一致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危害行为的结合性要素决定了其共同犯罪中正犯的认定具有特殊性。2016年5月施行的《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介绍、组织孕妇实施“两非”行为的行政处罚。*《规定》第23条规定,介绍、组织孕妇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增设后,对介绍、组织者应当依照该罪的共同犯罪进行追责。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共同犯罪认定中,行为人必须同时实施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和示明两个行为才可认定为正犯。据此,在实施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的场合,若其他鉴定辅助人员在场,只要该辅助人员并未参与具体的胎儿性别鉴定,即使其从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人处获知胎儿性别并将性别告知相关人员也不能成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正犯,而仅存在成立共犯的可能。
(二)生育权主体的去犯罪化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生育权在本质上是人格权抑或身份权一直为学界所争议,尽管早期有研究认为生育权的主体只能是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公民,*参见张荣芳:《论生育权》,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阳平、杜强强:《生育权之概念分析》,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l0期。但是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生育权是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参见王歌雅:《生育权的理性探究》,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6期;邢玉霞:《从民事权利的角度辨析生育权的性质》,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3期;武秀英:《对生育权的法理阐释》,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王虎、范学谦:《论生育权》,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赵敏:《生育权的本质属性》,载《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生育权包括自由权、共有权、知情权、生殖健康权等多方面权能。生育权在本质上是自我治理之权。人们具有以其喜欢的方式依据善之内涵规划并生活的自由,但是如果善的内涵涉及到影响社会中他人的生活则属例外。*See Alasdair MacIntyre,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8,pp.335-336.权利与义务相伴而生,“任何自由都容易被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对生育权的限制与责任自始即被特别强调。恣意行使生育权不仅会侵害到当代人的发展权、环境权等权利,而且会影响到代际资源的分配。自由且负责是行使生育权的应有之意。
生育权是应然权利,但是该权利的享有与实现之间不能等同,生育权的实现具有条件性,限制与责任是生育权实现过程中的合理法律负担。生育权实现的限制是就国家公权力规制生育权这一私权利而言,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义务履行;生育权实现的责任是就多元主体之间权利实际行使发生冲突时的利益衡量而言,在法律上主要表现为义务冲突。生育权实现过程中的义务冲突主要表现为男女自然人的个人生育权在实现夫妻共同生育权过程中的冲突和生育权主体之权利行使与医务人员之义务承担的冲突两个方面。*生育权实现过程中的义务冲突还表现为生育权的行使与胎儿生存权的冲突,鉴于我国刑法典并不承认胎儿的人格地位,没有将单纯的堕胎行为入罪,因此本文对生育权的行使与胎儿生存权的冲突不予探讨。前者冲突是指,生育权具有共有权性质,但是作为配偶的男女自然人之个人生育权的侵权赔偿诉求在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予支持。*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生育权中生殖健康权能的严重侵害,我国刑法典以侵害生命健康的罪名予以规制,对生育权中其他权能的严重侵害刑法典则未涉及。作为胎儿母体的女性,其生命健康权高于男性个人的生育权,男性个人的生育权具有依附性。而胎儿母体的生命健康权与母体生育权之取舍应当由权利主体进行权衡;后者冲突则指,生育权主体享有胎儿性别知情权,其实现需要医务人员的配合,而医务人员是否应当履行该配合义务具有条件性,由此产生生育权主体之权利行使与医务人员之义务承担的冲突。有观点认为,“生育权的内容涉及到国家对个人生育自主权的干预,因此有必要将生育权确立为民法领域的一项具体的人格权,用民法方法宣示和落实公民的生育权利”。并据此认为,“性别知情权是生育权的基本内涵之一,该权利不损害他人权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应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李益民、张哲:《生育权视角下的胎儿性别鉴定》,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2期。作为生育权权能的性别知情权应当被肯定,但是面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带来的严重法益侵害,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考虑,该权能在我国现阶段的实现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医务人员配合生育权主体实现生育知情权之义务应当条件化,即基于医学需要的义务履行应当被肯定,而基于非医学需要的义务履行则应当被禁止。生育权在本质上是自我治理之权,作为其权能的性别知情权应当受到充分尊重,因此基于公共利益保护而对生育知情权进行的限制应当保持极度克制。即使在其触犯刑法的场合,也要充分尊重生育知情权主体的自由,不宜因生育知情权行使方式的失范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不宜将生育知情权的主体即胎儿父母作为犯罪主体,而应规制其实现该权利的方式,即对因职业而负有有条件地履行生育权实现配合义务之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刑事惩治。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包括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也包括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但不包括胎儿父母,以实现生育权主体的去犯罪化。需要注意的是,胎儿父母的同意不能成为他人实施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阻却事由。尽管基于病人自己决定而实施之医疗行为可阻却违法且胎儿性别鉴定在本质上属于医疗行为,但是限制父母对胎儿性别的知情权具有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因此胎儿父母的同意不能成为他人实施犯罪的阻却事由。
(三)故意与示明性别错误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主观罪过是故意。其中,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认识到胎儿性别鉴定和示明行为的性质并积极追求;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侵害到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而听之任之。行为人对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和胎儿性别示明行为的认知判断应采一般人标准:对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的认知判断,应当以一般医务人员的经验为标准;对胎儿性别示明行为的认知判断中,若行为人采用以语言或者动作暗示的方式,*诸如告知“可以准备粉色的小车了”、“是个强壮的足球运动员”等情形。只要依一般人标准能够依此判明性别即可认定存在认知。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中因主观原因产生的示明性别错误属于认识错误,行为人在实施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运用行为后基于某种主观原因将相反的性别信息向胎儿父母等人进行示明,犯罪仍然成立。尽管存在胎儿性别鉴定结论为“女”而行为人胎儿性别示明为“男”的情形,且该种情形在客观上貌似并没有加剧法益侵害的现状,但是我们不能因该极具主观性的个别化行为违反公平机会原则。“在纯粹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判定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的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而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因严重侵害法益行为而遭受刑事处罚的机会应当公平,对胎儿性别鉴定结论为“女”而行为人胎儿性别示明为“男”的行为,宜依据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不能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的禁止性规范而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
(四)违法性判断
违法包括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形式违法是违反国家法规、违反法制的要求或者禁止规定的行为;实质违法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当其违反规定共同生活目的之法秩序时,破坏或者危害法益才是实体上的违法;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侵害是实体上的违法,如果此等利益是与法秩序目的和人类共同生活目的相适应的。*[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201页。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违法性判断应当追求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的趋同。
作为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之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医学需要”是在例外情形下适用的出罪条件,必须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医学需要”的确定要以实现优生目标、保护母体及胎儿生命健康为原则。优生属于我国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其通过阻止不受欢迎之婴儿的出生,预防性地减轻相关家庭的精神与物质负担、减少衍生的社会问题。优生目标的有效实现仰仗于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因此对于家庭生育中的主要权利人——母体所享有的生命健康权应予以充分尊重。
关于胎儿性别对母体生命健康以及与遗传有关胎儿生命质量的影响在医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伴随性遗传病等只遗传给特定性别后代的疾病,若严重影响到胎儿出生后生命质量,则应当允许胎儿性别鉴定。伴随性遗传病作为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罪的违法阻却事由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实质条件,即伴随性遗传病必须严重影响到胎儿出生后的生命质量,而只是诸如患有色盲(绿色系列型)等一般性的伴随性遗传病尚不足以危害到胎儿出生后生命质量的,不应当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二是形式条件,即应由具备遗传性疾病诊断能力之二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的3名以上执业医生出具关于前述实质条件的书面说明。《规定》第6条规定,“实施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应当由实施机构三人以上的专家组集体审核。”为了保持立法的协调性,对伴随性遗传病严重影响到胎儿出生后生命质量的书面说明应由3名以上执业医生出具。又根据2006年《卫生部关于严禁利用超声等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通知》第三部分的规定,只有具备遗传性疾病诊断能力的二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方可申请开展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因此,对于3名以上执业医生的任职条件应做上述要求。
伴随性遗传病作为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之违法阻却事由应当具备的实质条件应由医事行政法规以明确性列举(对已经形成医学共识的情形)与兜底性描述(其他严重影响母体和胎儿生命健康的情形)的方式直接规定。其中执业医生出具的专家说明是证明性而非判断性的标准,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的行政违法性是刑事可罚性的前提,如果将伴随性遗传病是否严重影响到母体生命健康交由执业医生等判断则容易导致法律实施的异化,使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被虚置。
(五)作为综合性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
行政违法行为进入刑法制裁的领域导致违法相对性判断的弱化,*参见孙万怀:《违法相对性理论的崩溃》,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刑法中行政犯的设立要防止该倾向,应符合“行政违反”和“加重要素”两个层面的要件。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属于行政犯,其危害行为的结合性要素即属“行政违反”的要件。尽管在刑事立法设计时危害行为的具体内容与行政法的规定存在差异,*例如,《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两非”行为并列作为违反行政法的行为,而《刑法》设计时只规定了前者,且增加了“性别示明”行为。但是危害行为的结合性要素显然属于行为的“行政违反”要素而并没有涉及“加重要素”。为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在设置“行政违反”层面要件的基础上,还需设置“加重要素”。“如果认为犯罪构成包括质和量两方面,情节严重可以理解为‘量’上的规定,它的作用是行为达到一定程度而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值得用刑罚来处罚。”*余双彪:《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严重”》,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8期。“情节严重”不是属于犯罪构成某一方面的要件,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件。*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情节严重”这一犯罪构成的综合性要件对犯罪成立之“量”的规定是衡量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其与“加重要素”作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区分标准的作用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中“加重要素”要件宜采“情节严重”的立法方式。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中“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应当在司法解释中予以列明,不宜在刑法典中采用与具体危害行为描述相并列的形式进行规定。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属于医事犯罪,其犯罪形式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变化,在刑法典中采用与具体危害行为描述相并列的形式规定“情节严重”则会因刑事立法的僵化性与医事犯罪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导致法律适用困难,而司法解释的柔韧性恰恰能够弥合该矛盾。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具体列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既能基于其对司法实务的指导性而实现对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又能基于其出台的灵活性而实现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同步适应。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通过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行规定,应当主要从行为的例数、造成的后果、获利数额方面予以考虑,其中行为的例数是行为破坏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法益的主要表现。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应以实施鉴定行为的例数(同一母体、同一胎儿),而不是以实施鉴定行为的次数(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母体、同一胎儿)为标准。原因在于,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由于鉴定技术所限,某些情形下会为辨明胎儿性别而对同一胎儿进行数次鉴定,此时行为人实施鉴定行为的次数与对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法益的破坏程度并不一致,若以实施鉴定行为的次数为标准会扩大犯罪打击面。
二、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刑罚设置
“以刑制罪与由罪生刑构成共存而非对立的关系。”*赵运锋:《以刑制罪法理分析与适用考察》,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1期。“刑罚轻重的相互协调是根本性的,因为预防重罪要优于预防轻罪,预防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应多于预防对社会危害较少的犯罪。”*[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家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205页。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刑罚设置依据在于立法协调性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即对于侵害法益类似、危害性相当的犯罪应当在刑罚设置上具有相当性。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犯罪成立要求情节严重、属于实害犯,其主刑设置宜选择与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和刑事责任大小相适应的自由刑,生命刑的配置显然与该罪不符。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主刑的基础刑宜设置为短期自由刑,即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与管制。原因在于:(1)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设置的资格剥夺性决定了宜设置短期自由刑。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设置重在通过否定性评价对法益侵害行为进行防治,由于胎儿性别鉴定多数是由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者实施,因此否定性评价的最有效方式是对医生执业资格进行剥夺。对于剥夺医生执业资格不足以达到惩治目的或者对于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者,才可考虑适用自由刑。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中自由刑的适用应当具有补充性,而刑期较长的自由刑不宜作为补充性惩罚手段;(2)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无被害人的特点决定了宜设置短期自由刑。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是对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的侵害,对母体和胎儿生命健康的侵害具有偶发性和随机性,多数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无具体的被害人。对于无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不宜规定刑期较长的自由刑;(3)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域外立法借鉴决定了宜设置短期自由刑。将胎儿性别鉴定进行犯罪化的国家数量有限,但纵观其刑罚设置均采短期自由刑。在自由刑的刑度设置方面,印度《预防滥用和管理》法令对胎儿性别鉴定行为规定了入狱3年的处罚;韩国刑法典规定,发现医生采用B超来检查胎儿性别,处3年有期徒刑。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决定了应在主刑基础刑之外规定加重刑,即在主刑中设置第二、三个量刑档次,规定“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在技术上采用相对固定的大型B超设备或者车载B超设备,鉴定技术本身对胎儿及其母体的危害有限。但是新型的性别鉴定技术已经出现且其适用范围正在扩大,例如运用DNA仪器对母体血液进行采集、冷冻进而鉴定胎儿性别的,在采血过程中由于不具备消毒等医疗条件可能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甚至造成就诊人死亡后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针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和“造成就诊人死亡”情形规定相应的加重刑。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刑罚设置在附加刑方面,宜采用财产刑的方式。由于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多出于营利动机,因此,在判处自由刑的同时适用并处罚金实属必要。同时由于该罪是行政犯,在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之间存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于处于入罪临界点的行为,则可适用单处罚金。综上,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附加刑设置中的罚金刑应采取“并处或者单处”的形式。
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宜设置具体的非刑罚措施,即通过行政手段对实施该行为的具有医生职业资格者采取剥夺资格的措施。在我国现有刑罚体系外设置专门的剥夺执业资格的资格刑不仅法律成本过高,而且因扩大资格刑内容的立法时间表不确定会导致该种立法设计最终被虚置。在行为人被认定成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而不论是否判处免刑、缓刑抑或实刑,由医事行政部门剥夺行为人的医生执业资格不仅不具备立法上的障碍,而且由于该剥夺行为是依医事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而为,其施行成本也最低。因此,不宜通过设置刑罚资格刑的方式而应采取作为非刑罚措施的行政性处罚规定医生执业资格的剥夺。
三、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适用保障
(一)运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必要且可行
关于犯罪中危害行为的证据包括三个方面,即行为人实施了一个特殊行为、行为引起了特定后果以及特定条件下行为或者结果发生的证据。*参见Jonathan Herring, Criminal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Fourth Edition), Oxford, 2010,p.73.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隐蔽性很强,提供方和需求方往往达成事先默契且反侦查能力很高,运用常规侦查手段必然会遇到取证难问题。胎儿性别鉴定之危害行为的实施与倡导优生之产前检查行为交织在一起,并不具有独立的高辨识度。目前,胎儿性别鉴定最为常用的技术是B超,该项技术将超声波转换为图像,是一种基于医学影像的判断。而医学影像的形成是合法产前检查的基础,同样以该医学影像为基础进行的胎儿性别鉴定是医师进行的专业技术分析,行为本身往往没有遗留的痕迹可循,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物证与视听资料难以获得。为了逃避处罚,胎儿性别鉴定与示明一般不会形成书面文字,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书证难以获得。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一般是受人请托而进行,不仅没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由于行为人与请托人往往形成攻守同盟,在证明存在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时,获得被害人陈述的可能性也较低。故侦查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时适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具有必要性。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是指已经具有犯罪倾向或者先前犯罪,而仅是提供实施犯罪客观条件的犯罪侦查手段。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本质在于强化犯罪嫌疑人已经产生或者本身具有的犯罪倾向,而非诱发其犯罪意图。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同,其不仅为欧洲国家所承认,而且在我国也应当具有合法性。*参见翟金鹏、简远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行为非犯罪化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桑本谦:《“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研究》,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朱孝清:《论诱惑侦查及其法律规制》,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适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应当满足以下条件: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必须仅限于社会危害性足以担保或平衡诱惑侦查可能产生的危险的那些犯罪”,即应仅限于一些无具体被害人或者经被害人同意的犯罪;适用的案件必须是针对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参见古志军:《诱惑侦查研究》,载《公安研究》2004年第2期。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是无具体被害人的犯罪,而且相当隐蔽极难侦破,符合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适用案件之性质。因此,侦查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时适用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具有可行性。
依据适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分为事先有犯意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事先有行为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事先有犯意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不应当在侦查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时适用。尽管行为人事先已有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犯意,但是该犯意的实施仍然具有或然性,其并不必然外化为行为。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实施对于请托人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因行为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最终是否将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犯意转化为行为也具有极大随意性。如果行为人仅仅是事先有胎儿性别鉴定之犯意而没有实施具体行为,那么就不能关心行为人是否存有犯意而对其进行刑事评价。因此,在侦查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时不应当适用事先有犯意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而仅适用事先有行为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
(二)行政执法监督措施应多管齐下
出于徇私情、徇私利或者地方保护等原因,针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相关行政执法主体可能会选择性地行政不执法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这是导致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屡禁不止、惩治不力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应从规范、监督行政执法方面保障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适用。
其一,应规范行政执法,重视对非法买卖胎儿性别鉴定仪器的管理工作,对鉴定工具加强监管。1994年印度就颁布法律规定未经注册私自购买或者出售可以用于测定婴儿性别的仪器构成犯罪,最高可以被判3年监禁,再犯时,将被判处5年监禁。*参见丁利才:《鉴定胎儿性别入罪难在实施》,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年5月8日。尽管在我国不宜将非法购买或者出售胎儿性别鉴定仪器这一法益侵害性较小的行为进行犯罪化,但是加强对其行政监管实属必要。规范行政执法,还要重视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广告的管理工作,从鉴定途径的角度加强监管,针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的营利性特征,严格限制网络和社会生活中鉴定胎儿性别广告业务。
其二,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是在其他制裁手段调整效果欠佳而必须动用刑事手段时进行的调整,我们不能对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入罪后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掉以轻心。例如,家庭对胎儿性别具有明显偏好,在难以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时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对待已经出生的女婴。对此,应从加大对出生婴儿的管理力度、督促公安机关加强对婴儿意外身亡等案件的刑事排查工作以及规范收养行为等诸方面展开相关工作。
再者,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基于徇私情、寻私利的动机而实施的,因此,有效打击徇私情、寻私利的行为是惩治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的关键所在。医务人员等直接实施胎儿性别鉴定者,由于其行为自身的特点同时符合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和受贿罪(或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属于想象竞合犯,应当择一重处断。对于负有查处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罪之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查处,同时收受贿赂构成受贿罪的,以相关渎职犯罪和受贿犯罪数罪并罚。*自2013年1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结语
人口问题须基于科学数据上的前瞻性判断,其危害性的全面爆发往往远远滞后于问题初现端倪时,人口问题的发现与提出需要极具专业水平的预断。人口政策的调整应对专业性预断具有高度敏感性,应密切关注人口问题的非良性动向并积极回应人口问题的成熟性预判。我国应出台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刑法规制已经被人口学专家不断提出并极力呼吁。然而,关于人口问题存在的严重认识分歧抓住了立法的仓促性这一短板,致使刑法典的修改被搁置,令人惋惜。
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带来的危害不仅没有消弭,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科学家认为,女性社会地位会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会有更多女孩入学,她们长大后能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随着卫生保健的改善,分娩期间母亲的死亡率会下降。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中,妇女拥有避孕的权利,她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上,育儿数量会更少。See Mara Hvistendahl. Unnatural Selection,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Too Many Men, Public Affairs, 2012, p.5.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人口政策不畅通、行政规制欠强力的情形下,刑法应成为规制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的重要推动力。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Legal Structure of Medical Fetus Gender Test without Medical Needs
Author & unit:HOU Yanfang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In China, medical fetus gender test without medical needs did not stop despite of repeated prohibitions, causing great harm to the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add the crime of testing fetus gender without medical needs into the Criminal Law. The dangerous act of this crime should b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elem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for fetus gender test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fetus gender. We should minimize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know in matern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The parents should not be the subject of this crime. The principal penalty for testing fetus gender without medical needs should be short-term sentence restricting freedom, with conditions that may aggravate the sentence. To ensure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this crime, entrapment by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should be permitted, along with strengthening measures to supervis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medical fetus gender test without medical needs; legal structure; decrimin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to give birth; entrapment by providing opportunity
2016-12-08
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 “我国新型医事犯罪的法律对策研究”(IFW12096)的阶段性成果。
侯艳芳(1982-),女,山东滕州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36
A
1009-8003(2017)02-01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