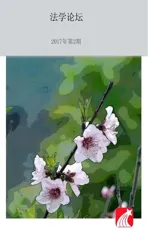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2017-04-05章志远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特别策划·“政府法治论”与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新发展】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过度介入法治实践既耗散了行政法学的有生力量,也影响了行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行政法治建设提档升级的时代,应当警惕“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庸俗化理解。行政法学须将《纲要》对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憧憬转化为相应层次的学术命题,并在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基本范畴、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模式上实现研究的创新。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论争中的重要学说,“政府法治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曾经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用。在法治政府即将基本建成的前夜,政府法治论当在核心内涵和实证基础上继续深挖,进而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思潮。
法治政府;行政法学;基础理论;政府法治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尤其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被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后,行政法治发展迅速步入了快车道,行政法学也呈现一派“显学”的发展态势。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既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明确了路线图和施工图,也为中国本土化行政法治道路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课题。*章志远:《法治政府建设的三重根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载《法治研究》2016年第2期。对中国行政法学而言,能否在深入观察行政法治本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不仅事关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变迁中的重构,而且关系到中国式法治政府的精神气质。不无担忧的是,晚近行政法学研究在整体法学时局图谱中日陷边缘处境,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集体深思。*以中国法学创新网对当下主流法学期刊发表论文的统计数据为例,2012-2014年间,行政法学论文仅占6.08%,与民法学(16.71%)、刑法学(13.75%)、经济法学(9.78%)、刑事诉讼法学(7.58%)甚至宪法学(7.14%)存在很大差距;2015年,行政法学论文仅占6.64%,与民法学(17.55%)、刑法学(15.58%)、经济法学(10.39%)、刑事诉讼法学(8.55%)、宪法学(7.89%)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笔者认为,在行政法治实践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实用主义研究进路保有警惕、重拾对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情,或许是实现行政法学凤凰涅槃的必经之道。
一、“问题导向型”行政法学研究进路的冷思考
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事业的大力推进,近年来行政法学者参与法治实践的机会越来越多,社会影响力较之过去明显增强。总体而言,除担任兼职律师亲自办理行政案件外,当下行政法学者介入法治政府建设实务主要有五种途径:一是承担法治宣讲。在中央紧抓“关键的少数”法治思维的刚性要求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教育培训工作,行政法学者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种规格的法治讲堂。对于普遍缺乏法科背景的领导干部而言,授课通俗易懂、能接地气自然是其首要需求,也是宣讲者能否持续获得聘请的重要因素。二是起草法规草案。《立法法》修订之后,所有的地级市都拥有了地方立法权。基于立法需求的迫切和立法能力的不足,很多地方都采用“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草案”的做法,行政法学者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府的首选合作对象,进而以承担横向课题的方式服务于地方立法质量的提高。三是决策咨询论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随后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智库,鼓励学者积极建言献策获得领导批示,行政法学者或依托智库或通过个人渠道,为各级党政机关提供各种决策咨询和论证意见。四是担任各类顾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办、国办新近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法律顾问,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行政法学者受聘各级政府兼职法律顾问(包括立法咨询专家、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行政执法监督员等),能够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五是外出挂职锻炼。通过“双千计划”或其他官方渠道,行政法学者深入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在一到两年的固定周期内亲身参与所在部门的法治实践。
就积极意义而言,行政法学者无论是通过担任法治宣讲、起草法规草案、参与决策咨询等方式提供“一锤子”服务,还是通过担任政府顾问、挂职锻炼等方式提供“一揽子”服务,都能够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行政法学者自身也通过介入实务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并有望进一步开阔其学术研究的视野。而且,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实践对行政法学者的需求更加旺盛,学者参与实践的机会和舞台也更加宽广。但是,过度参与实践也会对学者自身带来某种负面效应:除了分散研究精力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学者思维模式、话语体系和研究进路的影响。学者参与法治实践越深,就越容易形成“实践依赖症”,“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疯长即可佐证。如果以社会服务统称学者参与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学术研究与其之间的差异大体上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时效性和持久性。社会服务活动强调时效性,要求服务提供者及时发声;学术研究活动则强调持久性,要求研究者能够积数年之功奉献成熟的作品。二是碎片性和整体性。社会服务活动往往聚焦于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破解,“术”的技巧更为看重;学术研究活动则需要针对研究对象展开体系化的抽象思考,“学”的成分更为凸显。三是实战性和引领性。社会服务活动强调实战性,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为旨趣;学术研究活动则强调引领性,以提供具有引领性的学术思想为依归。四是建设性和反思性。社会服务活动强调“顾客至上”,要求为政府行动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学术研究活动更加强调“价值中立”,要求研究者站在客观立场审视法治实践活动。经验观察显示,真正能够在社会服务和学术研究之间保持游刃有余的状态并非易事。
值得警惕的是,一种庸俗理解“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现象在当下的行政法学研究中或隐或现,甚至存在继续弥漫的趋势。除了排斥纯粹的“坐而论道式”研究进路外,“解决实际问题”、“接地气”、“影响法治实践”甚至“获得重要批示”被奉为圭臬。这种现象的滋生,除了社会转型时期法治政府建设急迫的客观需求外,也与学者过度参与实践、陷入自我迷失境地甚至被实践俘获有关。诚如学者所言:“中国行政法学面临着多重的学术任务,一方面其尚未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建构, 即理论内容本身尚未达将行政法提升到价值统一性和逻辑一致性的层面。另一方面又必须针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复杂化的问题,直接进入各个具体的行政领域进行理论归纳尝试。”*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在这种双重学术任务的挤压下,过分强调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并不完全合乎时宜,反而可能加剧行政法学研究的“体系焦虑”。*《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2-2013)》,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由于过分强调“短、平、快”的实务导向型研究,行政法学近年来在知识增量、话语权和影响立法进程方面的作用并不容乐观。例如,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阵营中出现了较为激烈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其中,法教义学是一种“法学内的法学”,主张认真对待法律规范,坚信现行法律规范秩序的合理性、旨在将法律素材体系化和强调面向司法个案提供建议与答案;社科法学是一种“法学外的法学”,主张认真对待社会事实,从现实出发、立足社会变迁,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观察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从论争参与者来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学者、刑法学者、法理学者和宪法学者,行政法学者鲜有涉及。*《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均刊发“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的学术笔谈,力图展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真实图景。参见王启梁:《中国需要社科法学吗》,雷磊:《什么是我们所认同的法教义学》,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载《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泮伟江:《社科法学的贡献与局限》,孙少石:《另眼旁观——对社科法学的一个反思》,白斌:《方衲圆凿: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攻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0日。另可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又如,理论研究准备的总体不足,使得《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问题导向被固化,“双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等很多新制因规定过于仓促而引发实施的困境,修法作业依旧只能是“一次未竟的制度转型”。*章志远:《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转型:基于新〈行政诉讼法〉的视角》,载《山东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可见,“问题导向”的片面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行政法学在整个法学研究格局中的边缘化。
笔者认为,面对当下急速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需要,行政法学应当保持一份独有的清醒。诚然,“书斋式”的空发议论乃至“书生气”的一味批判固不可取,但完全“迁就式”的实践需要乃至“犬儒般”的应声附和更需反思。身处信息爆炸、浮躁盛行的时代,重拾经典、回归理论当是一个学人最重要的生活。“读书,是摆脱庸俗、肤浅和过分世俗的唯一出路。读书,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行政法学研究当然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中国实践并非中国理论,中国理论也并非照搬西方。真正的中国理论自信,需要从单向度的学习、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迈向以适应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自主型法治进路的实质,就是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与治理的要求渗透到法律及其运作的整个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法治体系。”*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为此,亲身观察实践而非完全融入实践、全面掌握经验事实而非片面摘取局部事实、提炼本土理论模式而非照搬西方固有模式应当成为未来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从经验事实、问题、中国经验到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二、“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与行政法学研究的创新
《纲要》的发布,表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如期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对于行政法学科而言,能否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为依托,实现学术研究的全面创新,不仅关系到行政法学自身的快速发展,而且关系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兴衰成败。《纲要》既有总体目标和衡量标准,也有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理应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宝库”。《纲要》的初步解读显示,行政法学研究亟待在如下四个层面进行创新:
(一)行政法制度研究创新
法治的精义在于良法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善治是良法的延续。从《纲要》列举的法治政府建设7大主要任务和40项具体措施上看,行政法学亟需对以下传统和新兴的制度展开深入研究:
一方面,行政法学需要继续关注若干传统的制度研究,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权力清单制度、行政组织制度、行政程序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公众参与政府立法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综合行政执法制度、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柔性执法制度、行政权力监督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裁决制度、信访制度等。近年来,《纲要》所列举的这些制度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但仍然存在很多学术生长的空间。例如,信访制度近年来备受法学界关注,在信访制度存在正当性、权利属性、功能、类型化、改革、信访立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参见张宗林、章志远等:《中国信访理论的新发展(2005-201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相比较法理学、宪法学而言,行政法学参与信访问题的讨论还明显不够,有关信访法治化的路径、目标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信访的官民矛盾化解和权利救济功能,还需要行政法学者立足中国国情和信访运作实践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又如,行政组织制度研究一直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短板”,今后应当从行政权力科学的纵向、横向配置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县改区/市的设置标准、各类管委会的去留、各类内设委员会和督察机构的角色定位等重大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行政法学需要及时关注若干新兴的制度研究,包括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制度、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辅助行政执法制度等。这些新制度对于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促进政府依法全面履职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在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及时实现制度的成文化和规范化。例如,上述很多制度都体现了社会力量承担行政任务履行的要义,诸如行政任务私人履行的界限、方式、法律规制等议题就应纳入行政法学的分析视野。
(二)行政法学范畴研究创新
基本范畴的精细化和体系化是行政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尽管行政法制实践在不断推进,但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仍然需要加以精心提炼。其实,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已经为行政法学基本范畴的精准理解提供了契机。特别是“行政行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协议”等范畴的法律化,使得这项学术任务更加迫切。*例如,围绕“行政行为”概念的法律化,学者已经就此展开了初步的论争。参见闫尔宝:《论作为行政诉讼法基础概念的“行政行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王万华:《新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行为”辨析——兼论我国应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章志远:《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对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纲要》的发布同样倒逼着行政法基本范畴研究的创新。例如,传统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二元结构的法律关系图谱已经模糊,“行政主体-承担行政任务履行的私人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承担第三方审查义务的私人主体-提供服务的私人主体-行政相对人”等新类型的法律关系结构频繁出现;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检查等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行政手段在“执法必严”的引领下继续适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和解、行政评估、行政约谈等新兴的协商激励型行政手段在“创新执法方式”的引领下不断涌现。这些游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组织方式和行政手段挑战着既有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亟需在基本范畴的理论界定上迈开步伐。
(三)行政法学体系研究创新
《纲要》的实施不仅推动着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范畴的微观研究,而且还直接催生了行政法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的更新。面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时代要求,特别是公私合作的全面推进,需要开发新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补强传统的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不足。一方面,行政法学需要及时引入“辅助性原则”,体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要求。行政法上的辅助性原则揭示了个人相对于社会和国家、较小的下位组织相对于较大的上位组织所具有的事务处理优先权。具体言之,当公民个人或较小的下位组织能够胜任某项事务的处理时,社会、国家或较大的上位组织就不应介入;反之,只有当个人或较小的下位组织无法胜任某项事务的处理时,社会、国家或较大的上位组织才能够积极支援协助,必要时亲自接手完成相关任务。*参见詹镇荣:《民营化与管制革新》,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85页。事实上,《纲要》有关“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向社会购买”、“确需政府参与的,实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规定,宣示了辅助性原则在所有行政活动领域中的适用,使得“个人——市场——社会——国家”的行政任务履行谱系得以生成。另一方面,行政法学需要及时引入“合作性原则”,体现政社互动、多元共治的改革要求。“在行政法实施过程中个人保护和全面考虑关系人利益的前提是行政对话和合作性的行政结构,惟由此才能建立因国家高权和权力垄断而很少产生的合作关系。明确行政的责任与公民的责任属于行政法的重要任务,这有助于将合作原则上升为一般的行政原则。”*[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事实上,《纲要》有关借助外部力量全面参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及纠纷化解的规定,宣示了合作性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广泛运用,初步摹绘了“合作国家”的脸谱。
在范畴提炼和原则更新的基础上,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同样面临着修缮乃至重构的抉择。*诚如研究者所言:“中国行政法学体系本身就存在先天的整体性不足的弊病,随后又受到新的行政转型潮流的进一步冲击,一些新兴的规制领域,甚至在西方也未能形成成熟的体系化论述。”参见《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2-2013)》,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作为传统行政法学的基石性概念,行政行为在构筑行政法学体系上曾经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关于行政行为的理论是全部行政法学理论的精髓和柱石。“行政之行为形式理论乃基于法概念操作技术之方便性,就行政机关为达成一定行政目的或任务所实施之各种活动中,选定某一特定时点之行为,作为控制行政活动适法范围或界限时之审查对象(基本单元),以达成对行政机关进行适法性控制之目的。因此,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之任务主要藉由厘清各种行政活动基本单元之概念内涵与外延、容许性与适法性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等问题,以确保依法行政要求,并同时保障人民权利。”*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3页。面对大量未形式化行政手段的涌现,尤其是各类新型规制工具的采用,行政行为形式论必须回应内部如何有效调适的挑战。同时,面对法律关系论和行政过程论“取而代之”的双重挤压,行政行为形式论也必须作出有力的理论反击。透过《纲要》的任务和措施清单,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修缮将成为无法绕开的学术任务。
(四)行政法治模式研究创新
行政法学是经世致用之学,行政法学研究成果理应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纲要》为2020年基本建成的“法治政府”确立了六项目标——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同时,《纲要》又将“实行法治政府建设与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相结合”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些新的论断既为法治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本土化行政法治模式的生成提供了契机。法治政府建设的细节问题固然重要,但模式问题则更为紧迫。在此过程中,域外已有的行政法治建设经验可资借鉴,但其本身并非中国模式的具体答案。为此,在历经制度、范畴和体系层面的创新性研究之后,行政法学还必须进入行政法治模式研究层面,回归行政法学的“元命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行政法学、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只有通过对中国本土化行政法治模式的探索,才能解决法治政府建设的道路问题,避免行政法治变革陷入盲动境地。
尽管目前还无法精准摹绘出中国行政法治模式的图景,但其主要精神特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自制性与他治性的结合。现行政治体制安排的特殊性,决定了单纯依托司法审查的他治性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事实上,自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行以来,一种寄望于行政机关自我革命达至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思潮渐次泛起,行政裁量基准、行政执法案例指导、行政问责、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权力清单、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行政系统自生自发制度变革的兴起便是明证。这些体现“自制”精神的改革是行政系统面对社会转型所作出的本能回应,与他治性措施一起共同担负起催生法治政府的重任。第二,合法性与最佳性的统合。行政权长期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首要课题就是将行政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实现“有限行政”和“有责行政”;同时,急速转型所累积的大量社会问题又需要强有力的行政及时进行有效应对,实现“有为行政”和“有效行政”。为此,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坚持合法性与最佳性的统合,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善治。第三,合作性和回应性的聚合。“官贵民贱”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润,加剧了官民关系的紧张和社会治理的风险。为此,重塑开放、包容的政府形象是优化行政法治建设环境的急迫任务。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从封闭、对抗和压制向开放、合作与回应的根本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全方位合作、积极回应转型社会提出的各种诉求,寻找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大公约数。
三、“政府法治论”在法治新时代的贡献与发展
当代中国行政法学术史的回溯显示,“行政法理论基础”课题的研究既是剧烈社会变革所“倒逼”出来的,也是行政法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在由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由对策研究向原理研究、由自说自话向学术对话的嬗变过程中,这一重大课题才得以应运而生。一方面,上述学术转型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智识基础;另一方面,行政法理论基础课题研究本身也成为上述学术转型的重大标志。可以说,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是我国行政法学界主动回应社会变革的一次自觉的‘集体行动’。”*章志远:《行政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这场发轫于30年前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学术大讨论,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之后行政法学发展的全部历程,对中国行政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更新乃至行政法学精神气质的塑造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也对当代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指导作用。
在这场弥足珍贵的学术论争中,著名行政法学家杨海坤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准的概括能力,及时提出并不断完善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学说——“政府法治论”。在政府法治论的集大成之作《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一书中,论者系统回顾了政府法治论的发展历程、指明了政府法治论的努力方向,深入阐述了政府法治论的核心思想——政府依法律产生(民主型政府)、政府由法律控制(有限型政府)、政府依法律善治(善治型政府)、政府对法律负责(责任型政府)、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平权型政府),并结合行政许可和行政程序立法实践对政府法治论展开了可贵的实证研究。就理论脉络而言,政府法治论以现代行政过程论为分析工具,以“有限行政”与“有效行政”为分析元点,将政府的活动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并在每一个具体环节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法律要求,从而使政府的权力处于全方位的法律监控之下,符合行政法理论基础所应具有的整体性、全面性特点。政府法治论正是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系统地回答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追问,从而全面揭示了现代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时,政府法治论通过动态地考察行政与法的关系,完整地阐释了行政活动中行政权的授予、运用、控制、使命、责任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环节,从而为建立科学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创造了基本条件。*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近年来,年逾古稀的杨海坤教授依旧奋战在行政法学研究的第一线,不断挖掘政府法治论与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之间共生共长的紧密关系,以学者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引领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有关杨海坤教授新近法治政府论的著述,可参见杨海坤:《走向法治政府:历史回顾、现实反思、未来展望——写在中国行政法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载《山东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杨海坤:《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历程、反思与展望》,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6期;杨海坤等:《法治政府: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1期。
尽管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在行政法理论基础不同学说的激烈角逐中,政府法治论依旧能够成长为一种极具理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学说。其中,前者表现为政府法治论自身的系统性、持续性研究,后者表现为政府法治论与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之间最为直接的关联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中国法学新发展”系列中,论者将政府法治论视为与“平衡论”、“控权论”相并列的三大“论述完备、影响深刻”的行政法理论派别之一。*参见周汉华主编:《行政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如果仔细对比《纲要》的论述与“政府法治论”的核心命题,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高度契合度,这也证明了政府法治论的理论魅力。
当然,回顾政府法治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影响,并非沾沾自喜于往昔的辉煌,而是为了谋求政府法治论在法治建设新时代的自我超越和发展。诚如学者新近在反思“平衡论”的挑战和发展时所言:“必须对新行政法中的新现象给予自洽的理论阐释,并重新界定行政法的本质、功能、体系和发展方向。当然,这一任务也摆在政府法治论、公共利益本位论、公共权力论等学说和学派面前。”*成协中:《行政法平衡理论:功能、挑战与超越》,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在《纲要》全面贯彻落实的法治新时代,面对“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挑战和多重学术任务的挤压,行政法学依旧需要秉承理想主义的情怀继续展开体系化的整体思考,推动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真正以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厚重理论成果引领法治政府建设事业。作为政府法治论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笔者认为,今后需要从大量经验事实的持续观察与缜密梳理中,提炼中国本土的行政法治元素,进一步充实政府法治论的核心内涵,使之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新思潮。
第一,关于“政府依法律产生”的内涵。继“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权力话语体系之后,“权为民所授”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话语。伴随着执政党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入推进,“民主型政府”的观念已成社会共识。但在急速社会转型的当下,尤其是在应对经济下行和矛盾上行双重压力的现实挑战中,行政组织的建制时常在自主与法定之间摇摆。从新《行政诉讼法》将“授权组织”的规范依据延伸到规章、行政区划频繁调整、各类管委会有增无减、大量机构自行设置的现实来看,“权为民所授”的政治理念与“政府依法律产生”的法治理念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张力。为此,政府法治论需要继续弘扬独立批判的精神,坚守法治底线思维和红线思维,引领法治政府建设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第二,关于“政府由法律控制”的内涵。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始终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旋律,“有限政府”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值得关注的是,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更多的利益权衡需要引入行政活动过程之中,行政法“惩恶”与“扬善”的任务同等重要。为此,政府法治论需要深入观察行政法治进程中类似许可交易、执法和解等诸多权力柔性行使甚至“软化”的新现象,不断拓展对“有限型政府”内涵的认知。
第三,关于“政府依法律善治”的内涵。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善治”,反映了人类社会对公权力运行规律认知的变迁。从《纲要》“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的法治政府衡量标准上看,一个“有为”、“有效”、“有德”的政府更加值得期待。面对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风险,需要从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手段创新入手,切实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为此,政府法治论需要不断总结各地区、各领域的社会治理新做法,形成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善治经验,不断丰富“善治型政府”的理论内涵。
第四,关于“政府对法律负责”的内涵。“权责法定”既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政府法治论的一大核心要义。伴随着新型行政活动方式的增加,如何区分不同种类行为、不同层次的责任归属实有必要。尤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对责任内涵的精准把握对于激励政府行善、抑制政府作恶大有裨益。一方面,在“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治话语体系下,必须区分行政乱作为的法律责任和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行政处理行为的法律责任和行政决策行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在政府与私人主体合作履行行政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区分国家的“履行责任”、“担保责任”、“监督责任”和“承接责任”,防止国家责任的转嫁和逃逸。
第五,关于“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的内涵。传统行政法希冀通过不同形式的公众参与,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平等化,进而达到平权型政府的理想状态。在现代行政法上,除了政府主导的公众参与之外,大量的公私合作履行行政任务的情形正在不同行政领域不断发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出现,打破了政府单一中心的格局,多中心的治理图谱正在形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合作”,现代行政法所依存的公共行政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平权型政府的实现前景可期。
四、结语:时代变革呼唤伟大理论
“公共行政既是行政法学者研究的有效对象,也是他们需要保持回应性的事项。重要的是,行政法应与其行政背景同步。”*[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6页。回望三十年前行政法学界掀起行政法理论基础大讨论的热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息息相关。如今,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度进入快车道。形势既喜人,形势更逼人。行政法学能否在伟大的时代变革中,提出解释、指导、引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伟大理论,不仅事关行政法学自身的发展前景,而且关涉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质量。
放眼当下的行政法学研究,除了警惕“问题导向”的庸俗理解之外,还要倡导各种不同行政法研究进路之间的共生与互补。一段时间以来,面向司法的行政法学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学、立足外国法的比较行政法学与立足本土的中国行政法学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甚至在行政法学知识生产谱系中暗自较劲。其实,面向行政也好面向司法也罢,本土也好域外也罢,都是行政法学理提升的基础资源而已,不同研究进路的合作与互补更为必要。《纲要》所提出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研究”,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理论的生成当然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也并不排斥对域外行政法治理论学说和制度经验的借鉴,更不会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行政和司法两种面向的实践厚此薄彼。只有通过多种研究资源的综合利用,包括“政府法治论”在内的既有行政法学说才能够在时代变迁中实现新生,而更多全新的行政法学说完全可期。
[责任编辑:吴 岩]
Subject:The General Success in Constructing Law-based Governments Calls for the Innovations in Basic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Law
Author & unit:ZHANG Zhiyua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Excessive interference in legal practice consumes the effective strength as well as affecting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era w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based governments is upgraded, it is important to avoid stodgy understanding of "question-oriented" research method. Administrative law should transfer the hope of generally constructing law-based governments in The Outline to academic thesis in the same level, and realize research innovations in legal system, basic category, jurisprudence system and mode of rule of law of administrative law. A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theory of law-based governments"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perfecting jurisprudence system and developing legal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eve when the law-based governments will soon be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law-based governmen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on its core connotation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o that it can be developed to an ideological trend in administrative law with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impacts.
law-based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law; basic theory; the theory of law-based governments
2016-12-16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13-0924)的成果之一。
章志远(1975-),男,安徽贵池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
D912.1
A
1009-8003(2017)02-0005-08
编者按:“政府法治论”经过系统总结提炼之后,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理论学说。在“政府法治论”酝酿推出三十周年之际,刊发三篇佳作,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国内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并借此推动国内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深化。章志远教授和黄学贤教授的论文立足宏观,分别探讨了政府法治论核心内涵在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新时代的发展及其对行政法治实践的方向引领,为政府法治论勾画出美好的发展蓝图;王太高教授的论文立足微观,探讨了政府法治论如何具体指导权力清单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政府法治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三位作者现已成长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论文既体现出学术研究薪火相传的特性,也彰显出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