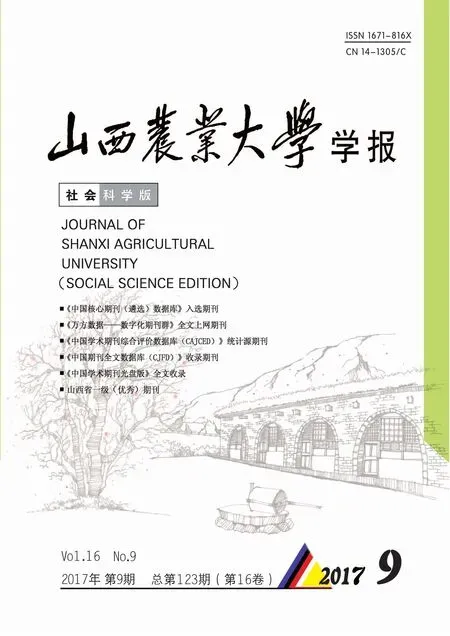对制定《社区矫正法》的几点思考
2017-04-05李训伟
李训伟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法律系,山西 太原 030031)
对制定《社区矫正法》的几点思考
李训伟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法律系,山西 太原 030031)
《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应当彰显行刑轻缓化和行刑教育化的指导思想,并确立教育刑罚观的主导思想。社区矫正工作应遵循三个原则,即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相结合的原则、适当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的原则、维护公共安全与保障个体权益相统一的原则。社区矫正工作应构建四个制度,即有效的工作衔接制度、健全的检察监督制度、规范的执法制度和区别对待制度。通过制定指导思想、明确工作原则和建立工作制度,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必将取得长足进展。
《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指导思想;社区矫正工作原则;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2016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在众多学者、实务人员的千呼万唤之下,《社区矫正法》作为国务院的立法计划终于付诸实践。《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其意义之重大,可概括为:一是完善了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体系,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法律依据之规格将提升至“法律”,而不是之前的“部门规章”,实现了与国外社区矫正立法体系的接轨[1];二是提升了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质量,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03年公布实施)基础上制定的《社区矫正法》,确立了社区矫正工作更为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工作制度,增强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操作性,并且缩减了社区矫正规范的条文数量,使之立法用语更为规范、精炼;三是回应了十几年来众多学者关于修改《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倡议和呼吁,《社区矫正法》的规定内容凸显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创新性、前瞻性、时代性。限于篇幅,本研究主要围绕第二点意义展开。
一、《社区矫正法》的指导思想
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是我国早已确立的改造罪犯的刑事政策,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传统的司法实践惯例则具有“重惩罚、轻教育”的本性,这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与“重惩罚、轻教育”的刑罚执行本性互为表里的是“监狱改造时代”的确立。“监狱改造时代”即在监狱中服刑是刑罚执行的唯一方式,监狱是刑罚执行的唯一场所,受这种单一、狭隘的刑罚执行观念的影响,致使在“监狱改造时代”的再犯率、重犯率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刑罚执行效率低下。“监狱改造时代”遗留的罪犯改造问题颇多,例如,执行成本高昂、交叉感染严重、改造环境一般等,迫使我国亟需改良传统的罪犯改造模式,探索并完善新的罪犯改造模式。2003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北京等六省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展开,我国的罪犯改造模式由单一的监狱改造转变为监狱改造与社区矫正并重,由此拉开了我国明确轻微犯罪人与严重犯罪人应区别刑罚的序幕,即我国对轻微罪犯的改造工作进入“社区矫正时代”,对严重犯罪人的改造仍沿用监狱改造模式。
社区矫正作为传统监狱改造的替代性措施,对于犯轻微罪的罪犯来说,其刑罚的惩治性有所淡化、刑罚的严厉性有所减弱[2]。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创新刑罚方式,秉持了教育刑罚观的要旨,即社区矫正的指导思想为“以刑罚的教育功能为主,兼顾刑罚的惩治功能”。以教育刑罚观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展开,顺应了当今行刑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刑罚改革的世界潮流[3]。
《社区矫正法》第一条开宗明义的指出,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是“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实践中,经过监狱改造,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成功率不高,主要原因在于监狱改造制造了“罪犯与社会之间有效社会关联性的隔裂”。由于接受监狱改造的罪犯将在一定的期限内处于相对封闭的有限空间,其有效获取社会信息的及时性、数量性、种类性、必需性等遭受严重制约,其与家庭成员、社区公民、社会组织的有益社会性联系也必将遇到阻碍。基于上述监狱改造所引致的负面效应,罪犯一旦重启新的人生,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变迁,将面临成功融入社会的巨大阻力,例如,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生活方式、难以接受新的社会观念等,无形中增加了国家预防其再犯、重犯的难度。因此,《社区矫正法》第二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实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的社区矫正活动。”将轻微犯罪人的服刑场所由监狱调至社区,恰是立法者秉持教育刑罚观的表征。[4]轻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即使将其放在社区来执行刑罚,并不足以对社区造成危害。此外,轻微犯罪人在社区服刑,通过参加社区服务等活动,可以有效修复其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可以消弭其与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裂隙”,可以有效、及时、全面获取社会信息以便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最终达致顺利回归社会、避免可能再犯和重犯之社区矫正成效[5]。
二、《社区矫正法》的工作原则
(一)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的原则
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是《社区矫正法》确定的工作原则之一,监督管理强调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惩罚色彩,表征了社区矫正依然具有的刑罚性;教育帮扶则突出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宗旨,彰显了社区矫正教育刑罚观的本义[6]。
1.监督管理
社区矫正人员毕竟是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受惩罚的罪犯,基于报应主义的刑罚思想,惩罚是对犯罪的成本报应。因此,监督管理的目的是施加一定的“痛苦”于社区矫正人员,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恶行,从而在社区矫正中矫治其犯罪心理及行为恶习。例如,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电子定位,限制其会客、外出、迁居,组织其对时事政治、法律知识的学习,定期参加社区义务劳动等。
2.教育帮扶
社区矫正的适用群体是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决定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从其承受的刑罚内容来看,该类罪犯的罪行、社会危害并未达到严重程度,足以表明该类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较低,即使将其放在社区服刑也未必造成社会危险性,而且便宜该类罪犯修复已造成的社会损害、修补已破坏的社会联系[7]。此外,受困于社会既成的对罪犯的歧视状况,通过社区矫正,可以培养该类罪犯重掌工作技能,为其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社区矫正法》第四章详尽规定了国家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帮扶内容。
(二)适当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的原则
在我国,社区矫正仍实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一元矫正模式”,例如,《社区矫正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区矫正工作”。社会组织、公众有效参与社区矫正的机会较少。我国在对社区矫正中可利用的资源的考虑中忽视了社会组织、社会公众这一潜在力量,如能对之挖掘并加以善用,必将极大丰富我国社区矫正的资源总量,必能破解我国社区矫正司法资源紧张的困顿。虽然,《社区矫正法》分别在第六条作出了“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区矫正”和在第三十三条作出了“国家给予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组织一定的优惠政策”的规定,但是,对于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区矫正的方式、广度、深度等具体问题并未给予明确说明;对于参与社区矫正、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帮扶的社会组织所享有的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未能予以充分明确,需要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予以细化。
(三)维护公共安全与保障个体权益相统一的原则
《社区矫正法》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刑法》的执行法,是对判处管制刑、宣告缓刑、决定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行刑的规范性文件。因此,《社区矫正法》与《刑法》具有同样的使命,即有机统摄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功能。
1.维护公共安全
《社区矫正法》对于罪犯的惩罚功能或维护公共安全的功能主要通过第三章“监督管理”予以体现,例如,该法第十三条关于给予警告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撤销缓刑假释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收监执行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禁止令及会客等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关于离开居所或迁居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预防脱离监管的规定,即是《社区矫正法》对维护公共安全功能的体现。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将向你展示如何用几百张照片拼成一张图片。主图是几年前我们在印度旅行时拍摄的。构成这幅肖像的其余照片也是在那次旅行中拍摄的,拍的是当地的孩子和我们参观过的地方。
2.保障个体权益
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与维护当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因此,《社区矫正法》对于在社区行刑的罪犯的个体权益的保障也做了相当的规定,例如,该法第七条第二款关于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执业准则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关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申诉控告检举权的规定,特别是在第四章,《社区矫正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国家、社会、个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帮扶。当然,《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侵犯社区矫正人员的行为并未作出惩罚性规定,有必要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予以明确。
三、《社区矫正法》的工作制度
(一)衔接配合制度
社区矫正实现了对轻微犯罪人的创新惩罚模式,即社区作为服刑人接受惩罚的场所替代了监狱,这就使刑罚执行工作变得复杂化了,例如,社区对服刑人的接收、检察院对刑罚执行的监督、法院和公安机关对变更刑罚执行的协助、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管理等,这些是开展社区矫正必须面对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为了更好的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并使之具有长效性,《社区矫正法》第四条第二款对此作了总则性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协调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法》第二章全面、细致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衔接配合工作制度。此外,早在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该文件就社区矫正工作中公、检、法、司四机关的衔接配合工作作了较为具体、详尽的规定,例如,加强社区矫正适用前的衔接配合管理工作、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交付接收的衔接配合管理工作、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的衔接配合工作、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收监执行的衔接配合管理工作,基本建立了社区矫正前、中、后三个阶段的衔接配合工作制度,实现了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工作制度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二)检察监督制度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罚执行的监督工作一般通过驻监检察来完成。面对社区矫正这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工作也应该有所转变和创新[8],例如,《社区矫正法》第十一条至第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工作制度。不可否认的是,上述规定检察监督制度的法律条文中多次使用了“抄送”一词,反映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消极性和被动性,遮蔽了检察监督的能动性,具有制约社区矫正工作良性运行之虞。可以考虑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对此问题予以细化、完善,变被动为主动,保证人民检察院有效行使检察监督权,例如,可以建立检察监督联络人制度,就社区矫正工作的进展及时向人民检察院汇报、及时传达人民检察院关于社区矫正的工作精神;构架社区矫正的法律评价体系,即从检察职业的角度出发,制定社区矫正效果的评价指标,以此作为督促社区矫正机构认真履行社区矫正职责的外部评价制度;违法问题发现纠正机制,即通过联系人制度和法律评价体系,及时发现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并向社区矫正机构发出检察监督建议书,责令其改正,如果涉嫌犯罪的,则可依法进行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生更为严重的侵犯社区矫正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检察监督流程的规范化,即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虽然人民检察院并非社区矫正的主导机关,但作为依据《宪法》享有法律监督权的专门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流程应当尽量做到规范、顺畅,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制定《人民检察院监督社区矫正工作流程》。
(三)社区矫正执法制度
1.规范的执法队伍
根据《社区矫正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可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在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中起主导和主要作用的人员,包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公、检、法三机关的工作人员;二是在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中起协助作用的人员,包括居(村)委会、被矫正对象的家庭成员(监护人、保证人、所在单位),如果被矫正对象是在校学生的,还包括其就读学校。此外,根据“适当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的原则”,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由上可知,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人员组成涵盖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层面,既有国家机构又有社会组织,既有机关组织又有社会个人,既有公、检、法、司四机关的专业执法人员又有大量的社会普通民众。另外,建议在吸收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时应优先考虑具有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知识背景的人员,以便完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知识结构。相比较《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法》在建设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探索中极大的充实了社区矫正的执法队伍力量,有效挖掘并吸收了大量的社会潜在力量,发动了群众,节省了司法资源。为了保证社区矫正执法的规范性,建议以《通知》的形式具体规定“从思想道德、法律知识、管理技能、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等方面加强对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培训,尤为重视对社区矫正执法队伍中处于辅助或协助地位的执法人员的培训”。相信在公、检、法、司四机关专业执法人员的指导下,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规范性建设必将有所建树。
根据现阶段的社区矫正执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日常执法工作基本是由社区的工作人员完成的,公、检、法、司四机关的社区矫正执法职能存在“虚置”之嫌。可以考虑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明确“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工作应成立矫正小组,且公、检、法、司四机关工作人员须为组员之一。”很明显,《社区矫正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并未就此予以明确。
2.规范的执法措施
规范的执法措施是社区矫正取得理想矫正效果的有力保障。《社区矫正法》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基础上规定了更为合理、多样化的社区矫正措施,例如,第二十九条的亲情感化和道德引导、第三十条的利用社区资源进行帮扶、第三十二条的政府公开择优购买社区矫正社会服务、第三十五条的协助申请社会福利待遇等。尤其是《社区矫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社区矫正社会服务项目由政府购买,切实贯彻了《社区矫正法》的三个工作原则,将成功的、优质的社会服务项目引入社区矫正,保证了社区矫正执法措施的规范性和实效性,必能极大推进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9]。
社区矫正执法措施的规范性还应考虑到社区矫正执法措施的影响力,即注重对优质的社区矫正执法措施的推广和普及。我国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社区矫正工作很难实现全国性执法措施的同一性、同步性。因此,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部)有必要组织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厅)每年召开一次“全国社区矫正执法措施交流会”,力争缩短各地社区矫正执法措施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差距。
(四)区别对待制度
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群体为轻微犯罪人,这其中必然包含较为复杂的犯罪人类型,如果毫不加以区分的盲目适用社区矫正措施,将难以保证各类犯罪人的社区矫正成效。基于此,《社区矫正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形式应当充分考虑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类型、个体特征、日常表现等实际情况。”第二十五条也规定,“(三)(对未成年人的—作者加)监督管理应当与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分开进行;(四)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年龄、心理特点和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采取有益于其发展的矫正措施。”遵照《社区矫正法》的相关规定,考虑到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的实际情况,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有针对性的制定社区矫正方案,制定专门社区矫正方案时应考虑犯罪个体的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社会影响、犯罪严重性、犯罪后的认罪认罚态度、是否初犯、偶犯、被害人谅解程度等诸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社区矫正方案在制定与适用上的区别对待。当然,这就要求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具有较高的执法能力和养成较高的执法素养。
综上,社区矫正工作应该建立并坚持社区矫正的全面区别对待工作制度,具体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以年龄、性别作为执行区别对待工作制度的必要因素,即区别对待成年犯罪人和未成年犯罪人、区别对待男性犯罪人和女性犯罪人、区别对待老年犯罪人、中年犯罪人和青少年犯罪人;微观层面,以个体犯罪的具体情状作为执行区别对待工作制度的必要因素,即综合考察个体犯罪的动机、手段、结果、影响、认罪认罚态度、被害人谅解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贯彻区别对待工作制度,才能助推三个面向的良性的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一是保证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助推规范化的执法队伍建设;二是保证社区矫正措施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助推规范化的执法措施建设;三是助推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和个体合法权益维护的统一性[10]。
[1]李训伟.社区矫正效果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608-612.
[2]朱艳萍.从无序到有序:非监禁刑执行对接程序之规范化[J].法律适用,2017(5):90-95.
[3]胡印富,张广超.社区矫正跨区域衔接问题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7(1):93-100.
[4]张凯.检视与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深化路径之探讨[J].河北法学,2016(2):189-200.
[5]皮艺尚.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完善路径[J].人民论坛,2016(11):92-93.
[6]戴香智.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与消解[J].湖南社会科学,2016(5):94-98.
[7]匡敦校.中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1):42-48.
[8]李晓莉.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J].兰州学刊,2015(4):90-97.
[9]武玉红.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62-172.
[10]周国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4-57.
(编辑:武云侠)
ReflectionsonCommunityCorrectionLaw
Li Xunwei
(SchoolofLaw,TheBusinessCollegeof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31,China)
The formul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should show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lightness of execution and education of excecution, and establish the education-oriented punishment notion . Work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ree working principles, namely, combination of supervision with education, permiss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interest. Meanwh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 should build four working systems: effective work connection system, sound procur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normative enforcement system and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system.
CommunityCorrectionLaw; Community correction guiding ideology;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ing principles;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ing systems
D914
:A
:1671-816X(2017)09-0066-05
2017-04-10
李训伟(1979-),男(汉),江苏沛县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刑法学方面的研究。
2016年度山西省法学会法学研究一般课题(SXLS(2016)B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