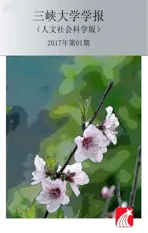《王子壮日记》中的宜昌沦陷始末
2017-04-02赵楚
赵 楚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王子壮日记》中的宜昌沦陷始末
赵 楚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1940年5~6月,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枣宜会战期间。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高层,王子壮在日记中较为详细真实地记载了这场会战的过程、结果及其背后的心理较量,为宜昌沦陷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侧面的材料。通过对《王子壮日记》中相关内容的分析,不仅可以梳理出宜昌沦陷的客观过程,更可以对抗战后方对此的同步认知有更全面的了解。宜昌的战斗对抗战后方来说不仅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更从心理上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并从而成为宜昌最终沦陷与被长期占领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子壮日记》; 枣宜会战; 宜昌沦陷
前言
王子壮,名德本,字子壮。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1901年2月2日),卒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八月四日。自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后,历任国民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常委兼青年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铨叙部政务次长、考试院副秘书长。王子壮保持了从民国四年(1915)开始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长达数十年的写日记的习惯,其间虽然有因日久播迁和时局扰攘而造成的中断、遗失,但仍有大量得以妥善保留,尤其是1935年至1946年7月24日间的日记完整无缺。由于王子壮长期身居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并历经中国巨变,加上他详尽连续的日记记录,使得其日记成为民国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军发动的“冬季攻势”声势颇大,获得一定战果。甚至日方也总结“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因此“特别有一种‘敌尚强大’之感”,“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1]第一分册80-94。王子壮在其日记中也写道:“一年以来之军事迭有进展,敌人将屈一筹莫展之境”[2]126。针对国军的冬季攻势,日军“第十一军企图立即实施一次大的反击作战”[1]第二分册1,此即在1940年5~6月间由日军挑起的“枣宜会战(日方称之为宜昌作战)”。
此间王子壮正寓居陪都重庆,作为能与闻机要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高层,他在枣宜会战期间曾在日记中对战事有过若干记载和评论,颇能反映“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1]第一分册28之状况下,抗战后方对宜昌沦陷整个过程的即时而直观的感受。
一、前奏:襄河以东的战况
1940年5月1日,日军准备多时的“宜昌作战”第一期作战正式开始,其第十一军之第3、第13、第39师团及若干支队大致兵分三路向襄阳附近进军,在经过了数天战斗后,至8日,攻占了襄东、枣阳地区,国军则向侧面回避,跳出了日军的合围。但是从日军的目的来看,“第一次会战(汉水东岸作战)不是这次作战的主要部分。这次鄂西会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汉水西岸之敌。为了保证作战的左侧背的安全,所以先有此第一次会战”[1]第二分册28。因而日军第十一军马上就下达了准备第二期作战(汉水西岸作战)的命令,并开始在襄河东岸地区整补准备。此时国军判断日军即将同一年前随枣会战时一样,撤回原驻防地区,于是蒋介石下达了反攻围歼日军于襄东地区的命令,并在随后几日中,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战果。
利用有利天气和日军第3师团大举深入的态势,蒋已于5月10日向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下达了“……况近日天雨,敌军战车等及重武器皆失效用,且其已进攻十日,后方接济已断绝,前方士气必颓丧,此正我军歼敌之唯一良机……”[3]468的指示。王子壮在其5月13日的日记中正记载了蒋对此次行动的乐观估计:“纪念周(即总理纪念周,笔者注)……礼成开谈话会……最后由总裁说明……目前正在进行之豫鄂大战……豫鄂战事,已将敌人包围,大约尚有三五日即可完全胜利。现所知者,因天雨五日,敌人之汽车有二十余辆为我所得,重兵器如坦克等均不能用,以是敌之粮弹均缺,必然失败。因当地之公路雨后十日始能通行也。”[2]第六册134事实上此一阶段前线战事发展,也正朝着较为乐观的方向在发展,“……本(十)日……我110D(吴绍周)午前八时克复新野……泌阳城当被我李军(92A)廖部(暂14D)占领……于真(十一)日令张军长(13A)指挥N1D、110D、79D向枣阳及其以东地区猛力进击,以92A即以枣、柏为目的猛力追击……”[3]469(D,Division,即师;A,Army,即军;N,New,N1D即新一师,笔者注)至5月17日,汤恩伯也认为“纵不能将敌完全歼灭,而予敌以大量之伤亡,及精神上之打击,当亦不小”[3]470。王子壮在当天日记里详尽记载了他在后方的听闻与感想:“今午后忽传攻克枣阳之捷报,闻之欣然。是豫鄂大会战已得到确定的胜利也。此战在日方已筹备达数月之久,纠集各方兵力于武汉,并于皖南、宜沙、晋南作佯攻以分散我之注意力,而以主力集中于武汉、信阳、钟祥分三路向西北以包围我在桐柏山、大洪山之精锐部队而消灭之。如我张自忠、孙连仲、汤恩伯等之主力均在此,予武汉一重大之威胁。敌欲得而甘心,以下南阳、襄樊、宜沙者也。蒋先生料敌如神,当敌人佯攻之际,我之主力已分散于敌人包围之外圈,迨五月一日起敌人五路攻入,不能发现我军之主力,已为之心慌。我一方诱敌深入,至唐河、新野一带,一面以精锐部队断其归路。于是缩紧包围,予敌以围攻,确山、泌阳、唐河、新野先后攻克并占武胜关以断其豫鄂之联络。敌于失败之余集合其主力于枣阳计数万人以图负隅,更以调其在京沪之驻军赶速增援,以夹击打破我军,其计已甚辣。故星期四(5月15日)何部长之报告,谓望枣阳之战迅速得一结果,援军之到达尚有数日也。在此方面主要集团军总司令为张荩忱(张自忠字荩忱)先生,彼素以勇敢善战著闻。今果奋其大勇,身先士卒,将负隅之敌,作彻底之击溃。我荩忱先生竟以殉国……”[2]第六册138-139
但实际上,王感叹“豫鄂大会战已得到确定的胜利也”,且在描述中处处置国军于主动位置,正侧面说明了重庆方面对日军此次作战最终目的的认识,并没有明确;对襄东战斗渐近尾声后国军应作如何行动,也没有十足的考量。甚至王子壮在5月17日记载这一所谓“确定的胜利”后,都没有再在日记中关注后续局势,直到6月5日日军度过襄河猛力向宜昌进击时才又开始在日记中记述。所以,如果说张自忠的牺牲与21日枣阳的再度失陷尚属于襄东激战中战术层面的失误与不敌,那么国军在此之后直到6月1日日军开始实施其第二期作战计划之间,对襄河防务和宜昌地区守备几毫无动作的表现,则完全属于战略疏忽。王子壮的日记正表明了这一点:17日记载中之“何部长”,当指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可以看出,他的报告也主要在关注京沪方面从东而来的日军援军,且始终着眼襄河以东的战斗“得一结果”。而日军的考虑,显然不止于此。
二、宜昌沦陷背后的心理因素
再看日军方面,第十一军军部在21日晚下达停止追击并向原驻地转移的命令后,经过短暂的争论,于23日深夜决定按计划实施第二期作战。嗣后在国军几乎毫无干扰动作的情况下,轻易集储了一千多吨的物资,又调来四个步兵与山炮大队[4]1005,并于5月31日夜至6月4日兵分多路纷纷度过襄河(汉水)。“三十一日,以主力于宜城襄阳附近,西渡襄河,六月一日陷襄阳;继以第3、第39两师团,分沿襄阳、南漳、远安道及宜城、荆门、当阳道,进攻宜昌。第13师团于白沙洋附近渡襄河,向西直取宜昌。国军江防军兵力劣势,不能有效阻止日军前进”[5]39。日军对于其一路攻占之襄阳、南漳、宜城等地,并未着意据守,而是以压缩国军主力并消灭之的心态,兵锋直指宜昌。6月5日,王子壮在日记里记载了日军渡河以来的动作:“枣阳为我夺回以后,彼乃猛渡襄河,攻占襄阳、宜城,意在沙市、宜昌之攻取。据报襄阳我已克复,是彼意在西下,襄河西岸之大战目前正在进行。”[2]第六册157
日军这一着,完全出乎国军意料,使其猛然醒悟到襄东暂时的沉寂只是假象,日军的真实目的,是指向宜昌。王子壮是如何看待这一突然状况的呢?他在日记中分析道:“我此次对日大战,已亘三年,在我国历史上所未有之大战,亦即兴替所关之枢纽。今日人眼看久拖足以招祸,故此次对于湖北不断予以攻击……最后如能予以彻底歼灭,必足以动摇敌人之信念也。”[2]第六册157可以看出,这基本代表了自中日全面开战以来,国民党对日军心态的整体把握。日军本就有“南进”“北进”等角逐世界的想法,而国力不敷。淞沪会战后执意突进南京也好,攻占济南后又发动徐州会战也好,凡此种种,无非想通过歼灭国军主力而迫使中国投降。至武汉城破、广州陆沉,眼看国力兵力愈是难支、国际形势愈为不利,乃改行不扩大方针,而妄图用零散敲打和政治诱降来达其抽身中国的目的。在王子壮看来,如果对日军这种本就已退而求其次的敲打,亦“能予以彻底歼灭,必足以动摇敌人之信念也”。
可以说,此时的宜昌之战,中日双方都延续了一直以来求一心理结果的态势。如果说这种心理上有不同以往、感觉强烈之处,则因为宜昌是陪都重庆的峡江门户;并且同南京的防线不同,宜昌背后的大后方,是退无可退的。宜昌失守后后方重庆的舆论,可见其一斑:“因宜昌之失守及敌机之来袭,人心不免有若干之摇动。复有奸人广布谣言,意志稍有弱者不免顿陷悲观。……而浅见者目不及此,动辄惑于目前之变动,陷于悲观之境地,适中敌人之阴谋。”[2]第六册168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子壮关于宜昌之战记述之密集,也从侧面印证了后方对宜昌的关切心理。整场枣宜会战,五月初至六月初日军未渡襄河之时,王子壮分别在5月5日、13日、17日提到三次;待六月初日军度过襄河指向宜昌直到宜昌沦陷成为定局之七月初,他分别在6月5日、13日、16日、17日、19日及7月5日记述达六次。
此外,宜昌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最西端,又扼长江水运之咽喉,失陷后,我豫南鄂北与鄂南湘北的交通及水运入川的中转,均会受到严重阻断。王子壮甚至将其与西南国际交通线相提并论:“交通情形,因敌人之攻下南宁、宜昌以及强迫英法断我之国防交通路线,故我受非常之影响”[2]第六册187。
正因为以上原因,在日军攻占宜昌前后,国军对日军进攻之顽强抵挡,以及宜昌失守后之立即反攻,均显示出极大能量。“鄂西战事,进行甚猛。敌以全力进攻宜昌,似有不守之势。据本星期一(6月10日,笔者注)何先生言,不久有好消息,将予敌人以彻底的打击。现正激战于当阳宜昌一带,主力的接触,似尚不分胜负也。关于军事方面蒋先生认为有把握,或于最近之将来获得开展。”[2]第六册165这是王子壮6月13日的日记,宜昌本已于12日沦陷,但因为他并非直接的军事负责人及当时信息传播所限,记载的“激战于当阳宜昌一带”等正似宜昌沦陷前几日的情形。此时蒋介石与何应钦对宜昌之战均有乐观估计,是因为在经历了日军度过襄河之初短暂的慌乱后,不仅立即作出了相应部署,还速调了在川的第18军增援,蒋介石的心腹大将陈诚也奉命于6月1日赶赴宜昌坐镇[6]957-959。除此之外,蒋介石更令第九战区薛岳发动牵制攻击,期使敌不能全力[6]962。但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的作战方案,不能适应战场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仍然是传统的正面阻击、侧面攻击相结合、扰乱敌后方迟滞日军行动的方案。但日军采取的是几乎不要后方、全力南下的作战方略”[7]。此外,武器装备的差距仍然巨大,如日军在进攻宜昌最激烈的几日间,甚至调来飞机进行不间断的助攻:“敌机终日袭击宜昌市区及近郊”,“归于毁灭者,实不可以数计”[8]。所以,即使拼死力战者有之(如宜昌东北峡口地区一部约五千人的守军)[1]第二分册18,因其他战区配合不力(如第九战区“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策应第五战区,自7日半夜起以相当大的兵力转向攻势,但均在日军的反击下,于11日暂时恢复平静。”)[1]第二分册29,更因由上而下误信日军不占或不久占宜昌而导致的消极、迟缓、领导不力等问题[6]971,宜昌还是于12日陷于敌手。
三、日军对宜昌长期占领的开始与国军第一次反攻
此时,发生在1940年6月12日的万里之外的另一件大事,使宜昌沦陷的过程又平添了一道波折:这一天,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军攻占。中日在襄西激战之时,也正是德军大逞闪电战淫威之日,法国战局急转,世界为之震惊。先前日军从4月10日大本营的“大陆命第四百二十六号”,到6月10日第十一军的“吕集作命甲第七百二十二号”,对于宜昌都秉持着一贯的攻占后迅速保持机动态势的态度,日本天皇也曾在4月15日告诫“宜昌这样的地方,最好不要插手”[1]第二分册1,18。但随着欧洲战局的激变,至迟从6月7日开始,日军对是否占领宜昌已开始了重新考虑与一系列的争论。15日,日本天皇的态度也开始改变,曾问道:“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办法吗?”最终,日军大本营在16日下达了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1]第二分册20-28。
对此,6月19日,王子壮写道:“……法之巴黎已失……欧战结束提前,中日战事亦可不至延之过久。日阀希望于欧战结束前用种种方法威胁我国以资结束者,不啻又为一场幻梦。此日人闻此消息,深惧列强将来得机干涉远东,极现惶急之状也。”虽然他对欧战后续的预测不合事实,但对中日双方此时基于国际局势而被激化的心理拿捏得非常准确。这天其实已经处于日军决心保有宜昌、国军正在艰难反攻的战斗中了。
具体的战斗过程颇具戏剧性:日军原定计划既是不占领宜昌,待16日突然更改命令、周折下达(因命令下达之时是傍晚,已经错过第十一军军部与第13师团无线电例行联络时间,而飞机亦因晨后才能起飞,无奈最后令骑兵传达)[1]第二分册26之后,先前攻入宜昌城内的日军第13师团已经撤出。接到命令后,日军第13师团立即部署折返。国军此时对日军占领宜昌的新目标并不知情,仍然按照先前的命令尾随反攻而入,如6月13日、14日蒋数次分别命令李宗仁、陈诚、汤恩伯反攻宜昌,甚至有“各部应不顾一切,猛力进攻,不可失机”[6]962、“宜昌必在最近期内无论任何牺牲,非决心克服不可也”[3]468等语;并且由于日军收缩撤退预兆在先,如毁坏宜昌军事交通通信设施、焚烧抛弃军事物资、第13师团从16日黄昏逐次收缩第一线等[1]第二分册26-27,所以国军对此种尾随进入式的反攻宜昌的成功颇有信心。“……今晨总裁之训词,据述其大致如下:……四、宜昌战事,我昨已下令反攻,不日可得极佳之战果,军事方面毋庸顾虑……”[2]第二分册169。这是他17日的日记,实际蒋在前几日即已下令反攻,而大约就在蒋训词称毋庸顾虑的同时,日军第13师团接到了确保宜昌的命令(17日上午7时[1]第二分册26)。至当天上午九时,从陈诚致蒋介石的电文“当面之敌昨日以来开始退却,宜昌于本日午前三时完全克复”[6]966来看,日军都尚未反转城中。
而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时间差的背后,却已经宣告了宜昌最终沦陷的不可避免。两军随后在宜昌城内迎头碰上,激烈战斗持续至24日,国军败北,蒋下达了“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6]968的命令。29日,日军第13师团渡至宜昌南岸,占领了可瞰制宜昌城区的磨基山。7月1日,原驻佳木斯的日军第4师团列入第十一军[1]第二分册28,作好了由暂时转向长期占领宜昌的准备。至此,宜昌沦陷已成定局。对后方来说,宜昌之战已无转机,作为关注热点已慢慢降温。7月5日,王子壮日记中“敌人攻下南宁、宜昌”等寥寥数语,惨淡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至于7月13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大陆命第四百三十六号中长期确保宜昌的命令,则是对这段已经书就的历史事实,点上了一个正式的句号。
四、结语
如前所述,宜昌之沦陷,进而被日军决定长期占领,以及国军对此之激烈抵抗与反攻,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其在武汉会战后,成为华中地区乃至中国国防交通的重要枢纽;二是其为拱卫陪都乃至大后方的门户。欧战变局对日军关于宜昌之既有战略的改变,实际也是基于宜昌从以上两点而言的重要性。这两点均间接或直接指向宜昌地区的军事态势对后方党、政、军、民心理上的重大影响。《王子壮日记》中对宜昌会战的记述,正是这种心理影响的一个鲜活侧面。
事实上,也正因如此,宜昌的沦陷与初次反攻只是中日双方围绕这一关键地区反复搏斗的开始。尽管宜昌城区始终为日军所盘踞,但中方的政治、军事存在仍顽强持存于此地区[9],并力图恢复。从此至抗战结束,仅在宜昌展开的特别重大战斗就有1941年国军反攻宜昌、1943年鄂西会战等,更遑论零星的战斗与双方围绕宜昌拟定未实施的作战计划。而这一切,在王子壮1940年春夏间的日记中,已经可以窥出些许端绪了。
[1]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M].田琪之,译.宋绍柏,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4]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5]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7] 柯育芳.枣宜会战论述(下)[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2).
[8] 湖北省国民政府.湖北省1941年统计提要[R].1941.档案号二(1)-50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9] 湖北省国民政府社会处编.湖北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纲要[R].1945.档案号LS6-2-836.湖北省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刘自兵]
K 265.6
A
1672-6219(2017)01-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