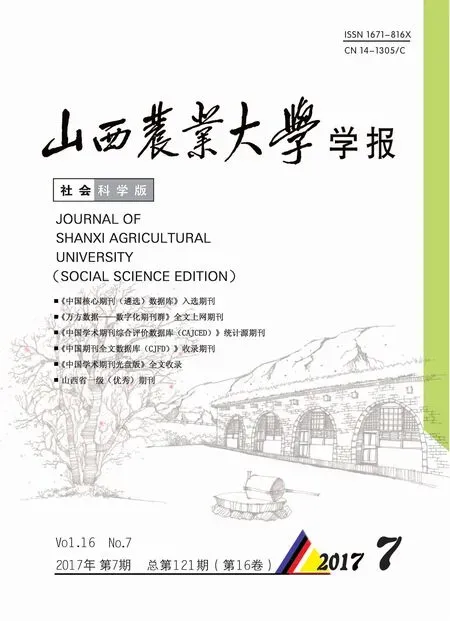新时期农村家庭伦理观念透视
——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的考察
2017-04-02李卫朝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李卫朝(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新时期农村家庭伦理观念透视
——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的考察
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农民的主体性有了极大的提升,促使其家庭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家庭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从父权制、夫权制走向平权制,从传统伦理观念走向现代伦理观念等。但是,在主体性强势崛起的过程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农民未能很好地处理义与利、理与欲、主体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的主体性走向了扭曲、沦陷和旁落,致使其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出现了很多偏差。因此,未来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农民正确处理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的关系,使主体性的提升与欲望、情感的满足处于平衡的状态。
农民;家庭伦理;主体性;家庭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对家庭生活尤其是农村家庭生活的改造,一直是社会主义改造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提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1]。”如果说人民公社化对农村家庭的改造因为狂热的群众运动淹没了农民个性的发展,并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但多年的改造却使家庭关系与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家庭不再担当过去的许多社会功能,老一代权威性的下降、年轻一代自主性的增加、青年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角色担当等,已经在农民的家庭观念中萌芽。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表面上看是传统家庭的回归,而实质上是全新家庭观念萌芽的迅猛生长,只不过推行家庭农业,并没有复兴原先的大家庭式生活。“今日中国农村家庭生活中的许多变化其实并非始自于经济改革,所以我们不应该将集体化时期与后集体化时期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两个阶段[2]。”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干预淡出家庭改造之后,留下了巨大的社会真空与道德真空,农村家庭反而真正实现了质的变化:从传统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小家庭,从社会组织形式转变为私人生活空间,从纵向的父子关系结构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结构,从长者为重的代际伦理重心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等等。这种转变在极大程度上引发了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的诸多矛盾和激烈冲突,如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父权制(夫权制)与平权制之间的冲突、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的冲突、婚姻家庭中的代际之间的冲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物质利益与情感欲望之间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在农村现实地呈现为令人诟病的诸多不良社会道德现象:天经地义的孝道不再,子女虐待老人屡见不鲜;名利欲望凌驾于夫妻感情之上,离婚率迅速提高;因竞逐物质利益而“兄弟反目、手足阋墙”时有发生等等。
农村社会这种道德滑坡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批评、反思和研究。更多的研究者都从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与现代家庭伦理道德的矛盾与冲突入手,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物欲主义等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导致农民的血缘亲情淡化、家庭责任感与道德感丧失、农村家庭伦理生活失范,从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乃至于社会问题。而反映了人们自然的家庭道德情感的传统伦理道德,其“家庭和谐、仁爱礼让、孝敬父母、勤俭持家等传统家庭伦理理念将有助于化解现代家庭问题”[3]。所以,应当“立足于传统家庭伦理基础之上”[4],“重新阐释儒家家庭伦理中的基本观念和积极成分,使之具备现代形态和解释力并成为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一部分”[5],“从而实现传统与时代的整合”[6],以唤起农民的家庭亲情,挽救农村家庭伦理道德的失落等等。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解决当前农村家庭伦理失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且不说陈瑛先生早在2002年就警示,“把挽救现代家庭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儒家的家庭伦理上,只能是一厢情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7],即使在今天我们致力于挖掘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资源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传统家庭伦理是建基于家庭本位之上的,其极大地压抑了家庭成员的个性成长,而这与现代核心家庭解放和促进个性生长是相矛盾的。因此,要创造性地实现传统家庭伦理中和为贵、仁与礼、孝与慈、勤与俭等原则与规范的现代性转化,发挥其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厘清这一基本矛盾。
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农村家庭所经历的种种转型,一定程度上将农民从传统的家庭本位、父权制、夫权制中解放出来,其主体性得以巨大的提升。正是在这种主体性的支撑下,农民的情感、欲望得以释放,开始摆脱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桎梏与束缚,不断追求自由、平等的权益,从而构建了新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农民在处理家庭与个人、传统与现代、物质与情感、责任与义务等等关系问题上的无力感,导致新生的家庭伦理观念有失偏颇甚至存在很多问题,在现实中呈现出家庭伦理失范的现象。由此可见,农民的主体性是贯穿农村家庭伦理观念变迁的一条主线,也是影响农民家庭伦理观念变化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和变量。当前不论是继承传统家庭伦理的精神文化,还是借鉴西方现代家庭伦理的他山之石,都应该围绕着“主体性”这个核心要素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伦理的变迁进行分析与梳理,以为建构现代新型的家庭伦理、确立切实可行的家庭道德规范奠定基础。
二、父子平权与主体性的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核心小家庭的迅猛增长,为农民主体性的提升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空间。因为,“农民主体功能单位大小不同,其成员主体性的强弱也不同”[8]。核心小家庭代替传统大家庭不再承担社会组织的功能,真正成为农民私人生活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成员也更多地具有了自主性。原来依附于大家庭的农民的主体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个性及个体权利观念的蓬勃兴起,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突破和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建构。
从父子伦理关系而言,“父慈子孝”是传统家庭伦理的轴心。传统农村家庭伦理是“父为子纲”与“父慈子孝”并重。一方面规定了父亲权威的绝对性与子女义务的绝对性,另一方面强调父母以仁爱之心照料、抚养、教育子女,子女以敬爱为上孝敬、赡养、慰藉父母。然而,由于传统家庭的宗法等级结构,不论是“父为子纲”还是“父慈子孝”,父与子的关系均有严格的尊卑之别,无形中压抑了子女个性的生长,导致依附型人格的形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母一代的权力、权威、地位日益衰落,子女组建的核心小家庭的经营生产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开始摆脱父母的权威掌控,主体性逐渐确立。生产上的自主、经济上的独立,使年轻一代农民的主体性不断延伸至自身的权利、情感、消费等领域,在婚恋上挣脱父母之命走向自由恋爱,在家庭地位上追求自身的权利,在消费上逐渐溢出勤俭的古训,等等。尤其是进城务工的生活,使他们在接受到现代生活的熏陶之后,更激发了他们突破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勇气和冲动,追求自由、平等、富裕的渴望使其主体性得到提升。
但是,这种新兴的主体性却呈现出扭曲的形态。年轻一代农民主体性的高扬导致父权衰落,主要呈现为家庭经营生产、配偶选择、婚后居住、家庭财产管理、家庭内部关系处理等方面绝对自主权的获得。权利意识的提高是青年农民主体性确立的主要标志。家庭财产分割、居住空间的私密等都反映了青年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加。尤其是在推进市场经济、法治中国的氛围里,传统建基于自然情感基础上的父子关系逐渐被权利、义务所替代;老有所养、幼有所恃的传统相互赡养机制已经被新的道德逻辑与交换关系取代。然而可悲的是,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承担却往往被耽于物欲的青年农民所忽略。一方面是只注重从父辈那里争得更多的权利,以提升自身的地位、保障自身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却往往忽视了为人子女应当承担的与自身权利相应的义务。“由于新兴的主体性强调的多是个人权利与利益,而不重视个人对他人的义务,所以这种个人主义是扭曲的[2]。”孝道不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扭曲的主体性的最为突出的恶果,“老而不养”屡见不鲜,“养而不敬”则更为普遍。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青年农民为追逐幸福生活而抛家舍业进城务工,身体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留守老人不仅得不到儿女的照料,而且还不得不重新扛起家庭的生活重担,甚至还要承担对孙辈的教育抚养。由此,本应由青年农民承担的孝敬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因为离家千里而当然地放弃了。即使留守家庭也由于生产、生活的压力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导致代际倾斜、错位严重,代际伦理重心向下代转移,往昔的以孝为本转为以子女为中心,只注重子女成长而忽略父辈赡养,呈现出“爱幼有余、敬老不足”的倾向,甚至出现“爱幼不敬老”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变化,父母一辈找出了各种办法来积蓄养老,传统的孝道也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农民在父子伦理之维中的主体性,在家庭伦理观念中也因而走向了缺场,留下的只是老一代农民的悲凉余生。正所谓“个人主义无视家庭的存在并由此而超越于其赖以依存的环境的时候,社会道德注定沦丧”[9]。
由上观之,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青年农民在父子之维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这种主体性因为缺失了伦理道德的规约而走向了扭曲,甚至在家庭伦理中的缺场,导致原来维持父子关系的孝慈原则丧失殆尽。在只注重个人权利和利益而忽视相应义务承担的思维框架里,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关系岌岌可危。深入分析,这种由主体性提升带来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偏颇,其根本原因在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当青年农民因主体觉醒开始追求自由、平等、富裕的时候,受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的影响与诱导,将自身的功利追求凌驾于家庭伦理道德之上,失去价值理性依托的功利追求必然导致家庭伦理观念面目全非,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已经被名利私欲的洪流冲淡。
三、夫权的衰落与女性主体性的沦陷
在传统家庭伦理中,夫妻关系是居于父子关系之下的又一重要伦理关系,常常被父子关系所支配。换言之,父子关系是传统大家庭的轴心,夫妻关系是这一轴心之外的重要一维。其受“父为子纲”的影响,注重“夫为妻纲”,虽然追求夫义妻顺、相敬如宾的理想境界,但历史中妻子往往依附于丈夫而丧失了自身的主体人格,一切唯丈夫之命是从。在传统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转变的过程中,父权的衰落导致传统的纵向的父子关系被横向的夫妻关系所取代而成为家庭的轴心。夫妻关系开始在核心小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转折点[2]。”过去在传统大家庭中地位低下的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活动空间,其主体性得以极大提升,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了更多自主权,而且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直接影响着她们的家庭伦理观念。
在婚恋观上,年轻妇女择偶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自主性的获得,使她们情感世界的丰富成为可能,个人情感欲望以及对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已经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她们不再受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摆布,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在夫妻关系上,年轻妇女追求夫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观念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随着核心小家庭逐渐成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妻子逐渐获得了与丈夫对等甚而更高的地位,不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消费中,妻子都具有发言权,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婚姻关系上,年轻妇女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不仅追求结婚自由,随着社会的发展更是把离婚自由作为普遍认同,不再视离婚为丑恶、羞耻,甚至支持、促进无感情婚姻的尽快解体。在婆媳关系上,年轻妇女不再等待“年轻媳妇熬成婆”的漫长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掌控着家庭的话语大权。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婆婆让着媳妇”直至今天的“婆婆依着媳妇”,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推动了家庭代际关系重心的完全下移。
农村女性主体性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夫妻关系的变化,是农村家庭伦理观念变化的重要原因。伴随着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显著提高,核心家庭权力结构趋于平衡,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趋于平等,这些都将导致农村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在不断提升的主体性支撑下,逐步突破父权、夫权的制约,确立独立人格、建构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与父子之伦的转变相同,在夫妻之伦中,妇女主体性在支撑其不断突破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凌越了家庭伦理道德的规约,致使其滑向了功利主义、纵欲主义的深渊。虽然在夫妻关系中情感要求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并不必然伴随夫妻关系稳定性的提高;虽然婚姻自主性和自由度增强,但在外在束缚减弱的同时,女性主体性却没有在伦理道德的自我约束方面相应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尽情享受情爱愉悦,另一方面却是对夫妻、家庭、社会的责任义务担当的缺失,从而造成了夫妻伦理的情、理失调。因追逐金钱、名利而背叛婚姻、破坏家庭的现象在农村屡屡发生,离婚率的激增很大一部分就源于此。“功利主义的婚姻家庭观正在损害和侵蚀着以感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经济的伦理在部分家庭中正取代家庭的道德伦理[10]。”近些年来在外出打工者中出现的“临时夫妻”,更充分暴露了家庭伦理道德规约的丧失。这种只注重情感欲望满足而忽视家庭责任义务的情、理失调,同时表现为不孝敬赡养老人。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绝对话语权,孝道不再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家庭妇女。
妇女主体性的提升为其在家庭伦理的夫妻之维中追求情感生活、满足物质欲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是,这种为追逐欲望的满足溢出了或者说凌越了基本的家庭伦理道德的规约,势必造成情理之间的失衡、婚姻道德观念的混乱,引发很多家庭矛盾甚至道德败坏。如果说公开表达情感、追求欲望满足是个人主体性提升的标志,那么,主体性在支撑其满足欲望的同时,还应该在伦理道德上对其进行外在的调适与规制。否则,主体性的提升只会导致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欲望的同时,忽视对他人、家庭、社会的道德责任。
四、兄弟之伦与主体性的旁落
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重要一维是兄弟之伦,注重兄友弟恭,即所谓“悌”。《论语·学而》有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可见,“悌”所维系的首要是传统血缘宗法家庭中的等级秩序。如果说“父为子纲”调节的是传统宗法大家庭中纵向的尊卑秩序,那么“兄友弟恭”则调解的是横向的长幼秩序。传统大家庭中,兄弟人数众多,如何维持长幼之间的和谐关系决定着整个大家庭的和谐稳定。“兄友弟恭”作为维系兄弟之伦的道德准则,强调的是“兄者爱弟”与“弟者敬兄”。与传统父子之伦的权威高压相异,兄弟之伦虽然也强调弟对兄的恭敬、顺从,但更多着眼的是彼此对等的伦理关系,强调血缘亲情基础上兄弟之间的情感寄托和精神依靠。《诗经·小雅·常棣》中“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就形象地描述了血肉之亲的兄弟之伦同根连枝、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手足之情。
改革开放以来,相较于父子、夫妻之维,农村家庭中的兄弟之伦在这三十多年的变化是直接而简单的。因为核心小家庭的产生,直接将兄弟婚后共处一个家庭所可能面对的矛盾冲消了,即使在未结婚之前共处在一个核心小家庭中,其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往往凝聚着兄弟之间的关系交往,兄友弟恭是一种常态。如果说在传统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伦还可能因为宗法等级权威产生对主体性的伤害,那么,核心家庭的产生将这种可能彻底取消,兄弟各自在独立的家庭中生产生活,其主体性完全得以解放。与此同时,传统大家庭所承担的亲情关怀、合作协调、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也一并丧失,失去了家庭平台的兄弟之间应有的、自然的情感交流则日益生疏。并且,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其作为“国家重新塑造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的重要途径”[2],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当“多子多福”的观念被颠覆,原来兄弟众多的家庭已不复存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使兄弟之间应有的、自然的情感交流由生疏而走向了缺失,原来通过亲情互助而在精神上相互依赖的兄弟之情也因而在家庭伦理中缺场。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原来的兄弟之伦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确立,开始向姊妹之间辐射。数目本来就很少的兄弟姊妹家庭之间的关系往来、生产互助、经济资助等横向联系日益紧密起来。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由于进城务工而带来的劳动力缺失,另一方面是为了兄弟姊妹之间无处安放的血浓于水的情感寄托。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兄弟之间因为家庭财产分割而忘却手足亲情、反目成仇,甚而大打出手、对簿公堂的现象几乎消失殆尽。2000年之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着兄弟姊妹家庭之间的互通有无、相互扶持的景象,“我们是一家”在心理上、感情上重新成为农村家庭凝聚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突破核心家庭的范围,开始向同宗同族辐射,甚而延及到纷繁的亲属网络关系。这种现象表明,兄弟姊妹之间那种因血缘关系而特有的情感交流和心灵抚慰,是作为主体的农民所不可或缺的,不论是在家务农,还是进城务工,抑或是投身商场,其主体性的提升并不能抹煞或取消农民对于兄弟姊妹之间的来自于家庭的情感需求,反而会因为离家在外、兄弟姊妹缺少而激发对这种情感的渴望。
由上观之,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尤其是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农村家庭伦理中的兄弟之维,因兄弟姊妹人数的锐减和独立核心家庭的生产生活模式,致使农民的主体性得不到来自于血亲之情的浇灌而走向失落。这种失落促使农民在当前又产生了回归亲情的家庭观念。此之所谓传统家庭的“私人生活转型呈现的并不总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在这个过程里,充满了困惑、愤怒、绝望,以及人们在情感与物质方面的损失[2]。”
五、结论和讨论
通过以上对农村家庭伦理的父子、夫妻、兄弟三伦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农民的主体性有了极大的提升,并且在这种主体性的支撑下,农民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在主体性强势崛起的过程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农民未能很好地处理义与利、理与欲、主体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的主体性走向了扭曲、沦陷和旁落,致使其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出现了很多偏差。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上述对父子、夫妻、兄弟三伦的考察都分别突出了某一个方面,比如将父子之伦化约到义与利的冲突、将夫妻之伦化约到理与欲的冲突、将兄弟之伦化约到主体性与情感的冲突等,但是,现实家庭伦理中的任何一维都是很复杂的,都会牵涉到义与利、理与欲、主体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因此,未来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过程中,农民一方面要继续提高主体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处理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的关系,使主体性的提升与欲望、情感的满足处于平衡的状态。
首先,要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家庭道义与个体私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家庭之“大我”与个体之“小我”的关系,在家庭伦理观念中实现义和利的统一。如果说传统大家庭的伦理道德因更加强调价值原则而使农民个体之利遭受了压抑,导致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出现了割裂,“大我”压倒了“小我”,那么,新时期以来,农民主体性的抬升使其在家庭中追求自身之利的同时却忽视了价值原则的规约,同样使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出现了割裂,“小我”溢出了“大我”。这种割裂,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就是因为农民在摆脱传统家庭伦理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过程中,目的(工具)理性溢出了或者说淹没了价值理性所引发的恶果。根据法国启蒙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的观点,就是因为农民对“自主的渴求使得认知摆脱道德的监管,对真的追求脱离善的需要”[11],从而提高主体性的过程中,不仅摆脱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束缚,甚至将一切道德的监管都抛弃了。因此,应该积极引导农民将对自身权益的追求自觉置于家庭伦理道德、社会道德的规约之下,实现价值原则和价值承担的统一,实现家庭之“大我”与个体之“小我”的统一,从而保证农民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正确性。
其次,要积极引导农民正确处理道德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道德我”与“功利我”的关系,在家庭伦理观念中实现理和欲的统一。如前文所述,传统社会和传统的大家庭更加强调价值原则,出现了“天理”压倒了“人欲”的现象,“道德”压倒了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因此,当前主体性的提升为农民原来被压抑的感性欲望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空间,农民可以自主地追求名利欲望的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功利我”得到了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只一味地竞逐名利欲望而不顾及家庭伦理规范,“功利我”的急剧膨胀遮蔽了“道德我”,则势必滑向物欲主义的深渊,导致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在当前农民构建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过程中,要自觉运用家庭伦理道德规约自己的名利欲望,实现理和欲的统一。
末次,要注意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主体性提升与家庭亲情交流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地运用血缘亲情浇灌主体性的生长。“人类的这种血缘亲情和家庭伦理道德关系是源于动物性又高于动物性的关系和感情”[7],当这种感情被家庭伦理原则化和秩序化,就会对人主体人格的成长造成限制和压抑,相反,彻底摒弃这种血缘亲情不仅不会促进主体性的提升,反而会使主体性的生长失去养分。当前农村面临的血缘亲情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只剩下空巢老人和青少年儿童,原来圆融的家庭亲情纽带被空间的距离所割裂,他们对老人和子女的关照主要是采用寄钱寄物的方式,缺乏情感的直接交流。二是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很多孩子缺乏平等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情感交流、精神寄托,从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在主体性急剧提升的同时,也漠视了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个人中心主义严重。因此,未来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进行改革,让青年农民能够和他们的父母、孩子共处于一个大家庭中,让老人、孩子能够享受到亲情的温暖。
欣慰的是,文章完成之时,恰逢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和《居住证暂行条例》的颁布,这不仅能够满足家庭伦理中兄弟姊妹之伦的情感需要,而且将会促进父子、夫妻之伦在感情上的进一步融合,这对于构建农村新型的家庭伦理观念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
[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
[3]汪怀君.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价值[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4):71-75.
[4]王苏.现代家庭伦理探析[J].兰州学刊,2009(3):122-126.
[5]张冬玲.论我国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2011(9):126-128.
[6]朱贻庭.现代家庭伦理与传统亲子、夫妻伦理的现代价值[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20-32.
[7]陈瑛.怎样看待儒家家庭伦理在当今的作用[J].高校理论战线,2002(9):44-46.
[8]黄琳.现代性视域中的农民主体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65.
[9]冉光芬.家庭伦理及其构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增刊):25-26.
[10]赵子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婚姻家庭演进的态势[J].社会科学辑刊,1997(3):27-30.
[11][法]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M].马利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3.
(编辑:程俐萍)
On rural family ethical concept in the new period
Li Weichao
(SchoolofMarxism,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1,China)
With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farmers' subjectivity has improved which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 on their family ethical concept: from family-centered to individual-centered, from patriarchy to equal rights, from traditional ethical concept to modern ethical concept. But owing to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auses, farmers' failure to deal wit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principle and desire, subject and emotion in the subjectivity rising resulted in the crises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and the deviation of the ethical concept.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improving farmers' subjectivity on the one hand, and pay attention to guide farmers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 principle and value undertaking on the other hand to balance subjectivity improvement and gratification of the desire and emo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new concept of family ethics in future.
Farmer; Family ethics; Subjectivity; Family values
2017-03-13
李卫朝(1974-),男(汉),山西芮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农民启蒙方面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X081)
D422.7
A
1671-816X(2017)07-00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