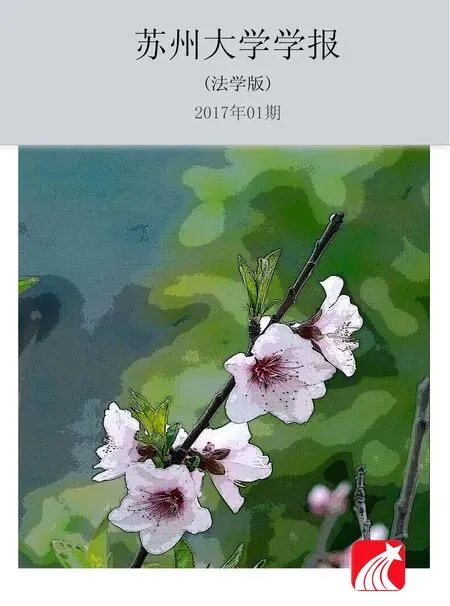共同正犯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2017-04-02桥爪隆著王昭武
[日]桥爪隆著 王昭武* 译
● 域外译文
共同正犯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日]桥爪隆**著 王昭武***译
如何处理数人参与防卫行为的情形,涉及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判断与共犯关系的处理之间的竞合,尤其是在各参与者的主观方面不一致的情况下,问题更为复杂。首先,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在共同正犯之间是可以相对化的;而且,应该以实际实施的防卫行为作为判断标准;再者,无论是实行共同正犯还是共谋共同正犯或者狭义的共犯,违法性阻却的效果也是相对的,并不必然连带作用于其他共犯;最后,在数人共同实施了防卫过当行为的场合,如果对过当性存在认识上的不同,就有必要探讨当初的共谋的射程是否及于该过当行为。
共同正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违法评价的相对性
一、引言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数人参与防卫行为的,在法律上如何处理?该问题涉及正当防卫、①日本《刑法》第36条规定,“对于急迫的非法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而不得已实施的行为,不处罚”(第1款);“超过防卫限度的行为,根据情节,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译者注防卫过当的判断与共犯关系的处理的竞合,因而对刑法学习者而言,可谓刑法总论中的“绊脚石”之一。亦即,按照判例立场,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不能仅凭防卫行为阶段的客观状况来判断,还应该既考虑非法侵害趋于紧迫之前的状况(当然,各个参与者的具体情况有可能不同),也同时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情况。②详见橋爪隆:《正当防衛状況の判断について》,载《法学教室》第405号(2014年),第102页(译文参见桥爪隆:《刑法总论之困惑(二)》,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2期。——译者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人支持判例所谓“积极的加害意思论”,本文暂不讨论该问题。因此,根据各参与者发展至防卫状况的过程及其主观方面的不同,对正当防卫的判断也有可能不同;而且,虽说同属共犯关系,但既有在现场分担防卫行为的情形,也有完全是作为共谋共同正犯而参与的情形,还有只是作为狭义的共犯而参与③日文原文为“加功”,这里翻译为“参与”。——译者注的情形,因而会呈现各种具体类型。本文力图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探讨,提出一种问题的解决路径。④另见橋爪隆:《正当防衛状況における複数人の関与》,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1)》,成文堂2006年版,第635页以下。
二、对最高裁判所1992年决定的解读
(一)案件事实
对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而言,最决平成4年(1992年)6月5日刑集46卷4号245页属于重要的判例,因而首先有必要对该决定进行探讨。该案的案件事实大致如下:
1989年1月1日凌晨4时左右,被告X从朋友Y的房间给A餐馆打电话,当与在该餐馆工作的女友通话之时,因电话被该餐馆的店长B挂断,而与B发生口头争执。X为B的侮辱性言语所激怒,怒吼着要去杀了B,决意冲往A店,并说服有些不太情愿一同前往的Y,让其拿着菜刀一同搭乘出租车前往A店。X明明未见过B,却在出租车内对Y说,“因为他们认得我,你先进去。如果你和他们吵起来,我不会袖手旁观!”。并且,出于如果到时候要杀B那也是没办法的意思,X说服并指示Y,“如果被打了,就用刀!”当日凌晨5时左右,到达A店之后,X让Y先去店门口,自己则在稍远的地方伺机而动。Y尽管没有自己冲进去对B施加暴力的意思,但同时也考虑到,自己与B从未见过面,想必B不会突然对自己暴力相向,于是,在A店门口等待X的进一步指令。但出乎意料的是,Y被从店内出来的B错认作是X,遭到了B的暴力:被突然抓住衣领来回拖拽,并被摔倒在水泥地上,遭到拳打脚踢。Y出于防卫自己生命、身体的意思,迅速掏出菜刀,按照X的前述指示,基于即便是用刀杀了B那也是没办法的决意,用菜刀数次捅刺B的左胸,将其杀害。
一审(东京地判平成元年〔1989年〕7月13日刑集46卷4号256页)认定:X与Y在到达A店之前,在出租车内就已经“相互都具有用刀杀了被害人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一意思,并达成了杀害被害人的共谋”;并且,Y虽预见到会与B发生争执,且已经想到,乘此机会杀了B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仍赶赴现场,因而也能认定Y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进而否定成立防卫过当。反之,二审(东京高判平成2年〔1990年〕6月5日判时1371号148页)则认定:就X而言,在乘坐出租车前往A店的途中,就已经产生了针对B的未必的杀人故意;而就Y而言,其到达A店之前未曾想到,会突然与B发生争执,而是在突然遭到B的暴力攻击之时,始产生杀害B的决意,因而X与Y也是在该阶段方成立有关杀害B的共谋。这样,对Y来说,能够否定存在事前的共谋,且由于Y并未充分预见到B的侵害,因而不能认定其存在针对B的积极的加害意思,能够成立防卫过当(由于Y并未提出上告,控诉审即二审针对Y的判决已经确定)。相反,对X来说,“是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而面对侵害,因而对X而言,B针对Y的暴力不具有紧迫性”,并以此为理由否定其成立防卫过当。
(二)决定要旨
对于二审判决,X提出上告,最高裁判所驳回上告,并依据职权做出了如下判断:“在成立共同正犯的场合,防卫过当之成立与否,应该就各个共同正犯人分别探讨其是否符合要件而决定,即便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成立防卫过当,并不当然导致其他共同正犯亦成立防卫过当的结果。按照二审判决的认定,被告已经预见到B的攻击,并意图利用该机会让Y用菜刀对B实施反击,是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而面对侵害,因此,B对Y实施的暴力,即便对不具有积极的加害意思的Y而言属于紧迫的非法侵害,但对被告而言则不具有紧迫性……因此,认定Y成立防卫过当而否定X成立防卫过当的二审判断是正当的,可以予以肯定。”
(三)探讨
1.共谋的认定
在本案中,重要的问题是,X与Y之间的共谋成立于何时?①关于这一点,参见橋本正博:《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024号(1993年),第167页。亦即,如果X与Y自始便对B的侵害行为存在预见,却仍然准备凶器赶往A店,那么,Y也是虽预见到侵害却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而面对非法侵害,因此,按照判例(最决昭和52年〔1977年〕7月21日刑集31卷4号747页)立场,对于Y,也应该否定B的侵害具有紧迫性。一审判决正是基于此前提,也否定Y成立防卫过当,但二审判决则认定,Y在现场面对B的侵害之时才成立有关杀人罪的共谋。也就是,二审的理解是:尽管X在出租车内向Y提出了有关杀害B的共谋,但在该阶段,Y并未认识到,事态会最终发展至杀害B的阶段,因而并未认真听取X的指示,但在案发现场真正面对B的侵害的阶段,Y才真正接受X的杀害B的提议,进而二人之间达成共谋。这样,二审判决通过认定X与Y各自达成共谋的时间存在“时间差”,进而得出了X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而Y不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这一结论。例如,P具体指示Q实施一定犯罪,Q没有马上决定实施犯罪,但犹豫了几天之后,终于确定犯意,且付诸实施。在该场合,一般认为,在Q决意实施犯罪的阶段,P与Q之间的共谋才得以成立。①对于该场合,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理解:不过是Q单方面地确定犯意且实施犯罪,并不能充分认定,P与Q之间存在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但是,原本来说,要成立共同正犯,总是要求双方之间存在利用关系,是鲜有此必要的。Q受P的具体指示的影响,且将该指示实际付诸实施的场合,P就对Q施加了强烈的心理因果性,而且,二人之间也能认定存在强烈的共同性,因而完全有可能认定成立共同正犯。对于本案,基本上也可以做相同理解。在出租车内,Y并没有真正接受X的指示,但在现场实际面对B的侵害的瞬间,X的指示回响在脑间,从而在现场达成了共谋,并在此基础之上实施了杀害行为。对于该认定,也许会给人一种过于投机取巧的印象,②类似批判意见,参见福田平、大塚仁:《〔対談〕最近の重要判例に見る刑法理論上の諸問題(1)》,载《現代刑事法》第26号(2001年),第11页〔福田观点〕;山中敬一:《判批》,载《法学セミナー》第452号(1992年),第135页;等等。不过,Y携刀赶往现场,在面对B的侵害之际实施了持刀对抗的行为,该事实完全就是X事前指示的内容。而且,从该事实得以实现也可以看到,在实行行为的瞬间,X对Y的心理性作用也在持续地发挥作用。
2.防卫过当判断的相对化
最高裁判所的决定认为,对于共同正犯,应个别地判断各自是否成立防卫过当。在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上,本决定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围绕防卫过当的刑罚减免根据,存在违法减少说、责任减少说以及违法与责任减少说之间的对立。按照重视责任减少的观点,想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本来说,责任减少的存在与否及其程度,应该是就各个行为人个别判断,因而,是否成立防卫过当,理所当然也应该进行个别判断。③提出此观点者,参见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第4版〕,有斐閣2008年版,第395页注6;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265页;等等。
然而,本决定并非是对防卫过当的刑罚减免根据做出具体判断,因而我们不能说,以责任减少说为前提的上述理解就是必然的结论。毋宁说,有无侵害的紧迫性,其判断有可能根据参与者是否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而被相对化,本决定的结论就正是基于这一点而推导出来的。在本文看来,本决定只是就是否成立防卫过当而做出的判断,④本案的最高裁判所调查官的解说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参见小川正持:《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4年度),第45页以下。既然侵害的紧迫性要件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共同的前提要件,即便是实行担当者Y的对抗行为能被评价为正当防卫的场合,正当防卫的判断仍然被相对化,对于具有积极的加害意思的X,也否定了其成立正当防卫。⑤参见山口厚:《基本判例に学ぶ刑法総論》,成文堂2010年版,第254页;井田良:《刑法講義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468页注28;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78页;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第6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296页;等等。
这样,如果认为,做出本决定的前提是,对于正当防卫的判断在共同正犯之间也可以相对化,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共同正犯之间承认违法性评价的相对化,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之间也能成立共同正犯。围绕是否承认这种违法性评价的相对化,以及对于背后者是狭义的共犯的情形应该如何理解等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应该说,对于思考共同正犯与狭义的共犯的异同,以及共同正犯的本质等,这些都属于重要的问题。
不过,本案还存在更为重要的问题:虽说是参与者之间个别判断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要件,但具体应如何判断呢?如果X、Y二人共同实施了防卫行为,对此也许会出现这样的理解:个别评价各自的防卫行为,进而评价是否满足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的要件(当然,这种场合下,为何应对共同实施的防卫行为进行个别评价,其根据也会成为问题。这一点留待下文(“四、实行共同正犯的正当防卫的判断”)进行探讨。但是,在本案中,完全只有Y实际面对非法侵害,且实施了防卫行为。在该场合下,对没有实际面对侵害,且没有实际分担防卫行为的X而言,如果个别判断其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那么,以X在什么阶段以及什么内容的参与为前提,来判断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呢?关于这一点,下面专门论述。
三、共谋共同正犯的正当防卫之判断
(一)正当防卫的个别判断?
1.以共谋行为作为标准的观点
出于便于探讨的考虑,这里想对1992年最高裁判所决定的案件事实做如下改动:Y针对B实施的防卫行为满足了相当性要件,属于能被评价为正当防卫的情形(【案例1】)。在该案中,基于对X、Y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要进行个别判断这一前提,对于X应如何判断呢?
有可能出现的一种观点是:X作为共同正犯的参与,最终仅限于在出租车内将菜刀交给Y,并指示Y杀害B的行为,因此,应该以这种事前的动作(作用)为标准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但是,如果立足于这种理解,既然在出租车内当时侵害尚不紧迫,该阶段的动作当然没有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那么,对于本案那样以事前的动作作为问题的案件,不用等到探讨是否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就基本上能够否定X成立正当防卫。①承认这种结论的观点,参见福田平、大塚仁:《〔対談〕最近の重要判例に見る刑法理論上の諸問題(1)》,载《現代刑事法》第26号(2001年),第12页〔福田观点〕;明照博章:《共同正犯と正当防衛》,载《松山大学論集》第25卷第6号(2014年),第110页以下;等等。就这一点而言,也许存在这样理解的余地:对于事前出于伤害、杀人等的故意而实施动作的参与者,能够认定其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因此,作为结论来说,当然否定成立正当防卫。但是,也并非是说,因为存在共谋,所以能直接肯定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例如,就是在本案中,也完全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如果B的侵害程度、内容远远超出了X的预见,那么,即便X事前存在未必的杀人故意,对于具体的侵害,也不能认定其存在积极的加害意思。即便是这样的情形,也以在事先动作的时点侵害尚不具有紧迫性为理由,而一律否定存在违法性阻却的余地,显然是不妥的。
那么,X虽未分担防卫行为,但在侵害行为被现实化的阶段实施了某种动作的,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案情:X、Y在对B的侵害毫无预见的情况下赶赴A店,但Y(也仅仅是Y)遭到了B的攻击,为此,X在现场对Y做出指示:“用你的刀!”“捅B!”(【案例2】)。在该场合下,在X实施指示行为的阶段,非法侵害已经迫近,因而能够以此为标准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但是,就指示行为而言,如何判断是否具有防卫行为的相当性呢?指示行为本身当然不属于防卫行为。为此,想必不能就指示行为的样态、内容(声音的大小?)本身判断是否具有相当性。最终就不得不以基于X的指示引起了Y的何种防卫行为这一点作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满足相当性要件。
这样,无论是哪一阶段的动作,我们都不能以其本身根本不能被评价为防卫行为的共谋行为作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结果就是,应该以实际的防卫行为作为判断标准。
2.共同实行的假设性思考
那么,如果认为只能以实际的防卫行为而非指示命令行为本身作为判断对象,判例结论如何得以正当化呢?对于共谋共同正犯的根据,练马事件判例(最大判昭和33年〔1958年〕5月28日刑集12卷8号1718页)判定,“即便是没有直接参与实行行为者,在将他人行为作为自己手段而实施了犯罪这一意义上,就没有理由认为,其间在刑事责任之成立上应该存在差异。”按照该判例观点,就有推导出下述理解的余地:共谋共同正犯也是通过将实行行为者的行为作为手段而利用,由此可以等视为自己亲自实施了实行行为。也就是,共谋共同正犯虽未实际分担实行行为,但可以规范地评价为,与实行行为者一同亲自实施了实行行为。按照这种理解,在前述【案例1】中,虽然是Y单独实际实施了防卫行为,但可以规范地评价为,X与Y共同实施了防卫行为,为此,就应从“如果是X实施了Y所实施的防卫行为,那该如何评价呢?”这一视角,来判断X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亦即,是这样一种构想:虽以实际由Y实施的防卫行为作为判断对象,但是在将行为主体由Y置换至X的基础上,来判断正当防卫之成立与否。按照这种理解,在【案例1】中,即便对Y而言,B对Y实施的侵害属于紧迫的非法侵害,但如果该行为主体是具有积极加害意思的X,由于对X而言不具有侵害的紧迫性,因而就应否定X成立正当防卫。并且,如果将这种观点往前更进一步,想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防卫行为的客观要件,是以Y实际实施的防卫行为为标准连带地进行判断,但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等“人的因素”,则就各个参与者个别地进行判断。①从最终结论上采取这种立场的,参见川端博:《正当防衛の再生》,成文堂1998年,第271页。另外,桥田久也认为,虽以实际实施的防卫行为为标准,但就主观要件更容易接受个别判断(参见橋田久:《判批》,载《甲南法学》第35卷第1号〔1994年〕,第108页)。
然而,本文认为,这种观点也不妥当。上述观点是以这样的理解作为其出发点:共同正犯属于分担实行行为的参与类型,共谋共同正犯也可以等视为分担实行行为的情形,但原本来说,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疑问。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在就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引起(以实行担当者的行为为媒介)具有间接因果性的类型之中,将那些因果性贡献尤其重要,且参与者之间能认定具有共同性的类型,作为正犯予以处罚。鲜有特意经由“如果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那该如何评价呢?”这种假定性判断之必要。
而且,如果以这种观点为前提,例如,如果上述【案例2】的案情是这样的:X在现场对Y喊叫“用你的刀!”之际,X实际上对于保护Y的生命、身体毫不关心,一心想的是,最好就此造成B死伤的结果,也就是,完全是出于加害B的目的而向Y发出了指示(【案例3】)。那么,对X而言,就可以通过个别地判断是否存在防卫意思(基于防卫意思必要说的立场)而否定成立正当防卫。但是,对于该结论也是存在疑问的。在本文看来,即便是立足于防卫意思必要说的立场,是否存在防卫意思,最终也应该是就实际实施了防卫行为的主体的主观进行判断,而不应该考虑并未分担防卫行为的X的认识与动机。对本案来说,如果Y的对抗行为能被评价为正当防卫,那么,X就不过是指示Y实施正当防卫行为,不管X是出于何种动机或者目的,难道不都应该承认违法性阻却的连带适用吗?在这种情形下,处罚X无疑意味着,仅仅是以X的内心的不当性作为处罚根据,因而该结论难以被正当化。
这样考虑的话,对于并未实际分担防卫行为的参与者,就难以个别地判断其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最终就只能是以防卫行为的实际担当者的行为作为标准。毋宁说,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就各个参与者个别地判断正当防卫要件,而在于在实行分担者成立正当防卫的场合,是否应该将其阻却违法性的效果连带地作用于其背后者,或者,是否承认违法性阻却的效果存在个别地、属人地发挥作用的余地?
(二)违法性阻却的连带性
在认定实行分担者Y因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性的场合,其违法性阻却的效果是否也应连带地作用于位于其背后的X呢?我们一般认为,共犯之间违法性连带作用,这种观点的意义及其界限正是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
正如此前的论文已经谈到的那样,①参见橋爪隆:《共謀の意義について(1)》,载《法学教室》第412号(2015年),第126页以下(译文参见桥爪隆:《共谋的意义》,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第112页以下。——译者注)。共犯也是就自己的参与承担罪责,而非就他人的参与承担连带责任。为此,违法性评价也是个别进行,这是违法性评价的出发点。然而,共犯是以实行分担者为中介而间接地引起法益侵害,参与者是就共同引起的结果被追究罪责。这样,由于法益侵害结果是共同的(相同的),因而,虽说是就各个参与者个别地判断违法性,但几乎所有场合下,参与者之间的违法性评价都是一致的。诸如正当防卫那样,在违法性阻却成为问题的场合,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对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根据尚存争议,但本文认为,正当防卫是通过侵害“不正”(非法)的侵害者的法益而保护“正”(合法)的被侵害者的法益,如果以这种“正对不正”(合法对非法)的关系为前提,就可以认为与前者(侵害者)的利益相比,后者(被侵害者)的利益是得到优先保护的,因此,实现了优越性利益这一点就属于违法性阻却的根据。②持这种观点者,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113页以下;橋爪隆:《正当防衛論の基礎》,有斐閣2007年版,第71页以下;等等。亦即,防卫行为人同时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结果无价值)与防卫效果(结果价值),后者的价值优越于前者,因此,行为的违法性被阻却。这样的话,对于作为(广义的)共犯参与正当防卫行为的参与者而言,也是以实行担当者的行为作为中介,对于法益侵害结果与防卫效果两者都施加因果性,因此,属于(间接地)实现了优越性利益,因正当防卫而阻却违法性这一点也应该连带地适用于此类参与者。町野朔教授以背后者“引起的是实行分担者的正当防卫所造成的合法结果,而非引起违法结果。不能认定他利用正当防卫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为理由,强调违法性阻却的连带性,③参见町野朔:《惹起説の整備·点検》,载《刑事法学の現代的状況·内藤謙先生古稀祝賀》,有斐閣1994年版,第122页。想必正是出于此旨趣。④不过,町野朔教授后来改弦易辙,转而支持后述岛田聪一郎教授的观点。参见町野朔:《違法性の概念》,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33页。在这种观点看来,最高裁判所1992年决定毕竟只是从责任减少的角度来理解过当防卫,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而言,还是应该在共同正犯之间连带地进行判断。⑤持这种观点者,参见前田雅英:《正当防衛と共同正犯》,载《刑事法学の現代的状況·内藤謙先生古稀祝賀》,有斐閣1994年版,第175页以下;浅田和茂:《共犯論覚書》,载《中山研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3)》,成文堂1997年版,第281页;曽根威彦:《刑事違法論の研究》,成文堂1998年版,第274页以下;山中敬一:《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802页。另外,高桥则夫认为,对于合法行为(由于能否定结果归属)否定具有共同正犯性,其结果就是,违法的背后者被作为单独犯进行评价,止于成立杀人罪预备(参见高橋則夫:《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13年版,第460页)。
然而,如前所述,违法评价的连带性并非共犯的本质性要素,而不过是一种一般性倾向:事实上,违法性评价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为此,对于那些存在一定合理理由的情形,完全有可能承认违法性评价的个别化。例如,在购买淫秽物品的场合,我们一般认为,不能将淫秽物品的购买者作为散发猥亵物等罪的共犯予以处罚,其理由就在于,实质上,购买者这一地位同时也属于散发猥亵物等罪的被害人的地位,因而立足于购买者的立场,就不能将散发淫秽物品的行为评价为违法行为。⑥有关这种观点,参见平野龍一:《刑法 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379页;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339页;等等。这里实质上是站在被害人的立场,⑦由于散发猥亵物等罪是针对社会法益的犯罪,因而终究是“实质上的”被害人。如果是完全涉及侵犯个人法益的案件,由于被害人的同意阻却了违法性,因而实行担当者的行为的违法性也被阻却。而推导出违法性评价的个别化(个别性)这一结论。
并且,对于那些违法性阻却事由成为问题的情形,如果背后者没有正当理由而创造了违法性阻却的前提情况,也完全有可能相对地理解违法性阻却的效果。虽说是正当防卫状况,但也并非完全否定侵害者的法益的受保护性。终究只是因为有必要优先保护被侵害者的法益,而且,正因为是为了保护被侵害者的法益而有必要侵犯侵害者的法益,才例外地肯定法益侵害行为阻却违法性。这样考虑的话,X出于争吵打斗的目的而让防卫行为人Y前往现场,并与B发生争斗,从而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创造了紧急状况的,对于这种情形,就应该认为,即便Y成立正当防卫阻却违法性,其效果也不及于X。这是因为,对于自己创造紧急状况的X而言,如果以该紧急状况作为前提的违法性阻却的效果及于X,做有利于X的处理,显失妥当。对于这一点,岛田聪一郎教授主张,在“只有由背后者才会创造出违法阻却的前提状况”的场合,背后者将利益冲突状况“掌握在自己股掌之中,而原本来说,是不应该引发这种冲突状况的。为此,在那种场合下,背后者就不能将行为媒介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援引……应该认为是,违法地实施了行为”,①参见島田聡一郎:《正犯·共犯論の基礎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198页。这种理解是正确的。②另见松原芳博:《判批》,载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第7版〕,有斐閣2014年版,第179页。另外,对于最高裁判所1992年决定的案件,林幹人也认为,“应该否定背后者成立防卫过当的根据在于,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状况:正是他将实施防卫过当的行为人的法益置于遭受对方攻击的危险之下”(林幹人:《刑法総論》〔第2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423页注120),想必基本上是同样旨趣。进一步而言,在那些能认定实行担当者减少了违法性的场合,基于同样的理解,对于不必要地创造了违法性减少的前提状况的背后者,也会否定对其连带适用违法性减少这一效果。
这里想就上述三个案件确认具体如何适用上述理解。在【案例1】中,尽管没有正当理由,但X出于争吵打斗的目的,让Y前往B所在之地,不必要地创造了Y与B之间的利益冲突状况。因此,X不能将Y的防卫行为所引起的防卫效果(结果价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援用,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效果不连带作用于X。反之,如果X存在诸如必须与B当面交涉等不得不去A店的正当理由,由于创造紧急状况本身是被允许的,因而就不属于这种例外状况,Y的违法性阻却的效果也应连带作用于X。那么,既然重视紧急状况的创造,对【案例2】而言,Y的违法性阻却的效果当然也连带作用于X;而且,即便是诸如【案例3】那样,在Y实施防卫行为之际,X持有不当的动机或者目的的场合,这一结论也不会改变。
行文至此,可见本文的理解是,对于背后者X,不应个别地判断其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而应该是完全以防卫行为人Y为标准来判断正当防卫的要件(包括主观性要件在内),在此基础之上,再探讨Y的违法性阻却的效果是否连带作用于背后者X这一问题。在此意义上,这里探讨的不是正当防卫的要件论,而是事关违法性阻却一般原理的问题。③提出这一点的学者,参见小林憲太郎:《刑法総論》,新世社2014年版,第163页。不过,正当防卫中的所谓积极的加害意思论或者自招侵害论,都是以“那些通过自己的先行行为不必要地创造出紧急状况者,在法律上不应受到正当防卫的保护”这种价值判断为前提,因此,就可以认为,下述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以同一原理作为其理论支撑的:(1)作为正当防卫的要件论,主张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2)作为违法性阻却的一般原理,否定连带适用于创造出紧急状况者。④作为违法性阻却的一般原理,西田典之倡导避免义务原则(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第2版〕,弘文堂2010年版,第134页)。本文以为,西田教授的这种观点包摄了本文所提出的这两种情形。并且,正因为两者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对于最高裁判所1992年决定做出的“根据有无积极的加害意思而个别地判断是否具有紧迫性”这一判断,就并不感到特别突兀难以接受,也能够将之转换成另外一种解读:“根据事前的创造行为而个别地判断有无违法性阻却”。不过,从本文立场来看,原本还是希望判例采用的是后一种表述。
(三)狭义共犯的场合
那么,如果【案例1】中的X不是共谋共同正犯,而是被评价为教唆犯,那又如何处理呢?对此,完全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观点:在上述情形下,X通过让Y赶往现场而不必要地创造了紧急状况这一点并无不同,因而即便X只是狭义的共犯,也要否定Y之违法性阻却的效果连带适用于X。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是Y因成立正当防卫而阻却了违法性的场合,对于位于其背后的X而言,仍要成立教唆犯。①参见島田聡一郎:《正犯·共犯論の基礎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198页。支持这种观点者,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79页。围绕狭义的共犯的要素从属性,②作为共犯从属性的内容,平野龙一率先提出其实质内容包括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罪名从属性,并认为三者属于不同理论层面:实行从属性是指成立共犯是否以存在正犯的实行行为为必要,这相当于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之间的对立;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最小从属性说是围绕要素从属性的争议,属于共犯的成立要件问题;罪名从属性探讨的是正犯与共犯是否必须保持同一罪名的问题,其理论基础在于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参见平野龍一:《刑法 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345页以下。——译者注理论上存在激烈论争。③关于共犯的性质,大陆法系国家一度存在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之间的对立,但随着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衰退,从属性说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从属性说内部也有纷争,主要是关于从属性的实质内容,尤其是要素从属性的内涵。要素从属性又称共犯的从属性程度,是指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必须具备犯罪成立要件中的哪些要素。对此,德国刑法学家M·E·迈耶总结出夸张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最小从属性说等四种从属形式。当今的德日刑法理论通说采取限制从属性说,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虽无需具有有责性,但须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但随着日本刑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共犯的从属性问题上,最小从属性说的影响日益扩大,该说主张,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正犯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即可,既无需有责性也无需违法性。其中,限制从属性说之所以要求正犯既符合构成要件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其最大理由在于:对于参与他人的合法行为的共犯并无处罚之必要。随着违法的相对性理论的提出,不少学者开始对限制从属性说的理论基础,即“违法连带作用、责任个别作用”这一原则提出质疑,并进而主张最小从属性说。该说与最小从属性说之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承认违法的相对性。参见王昭武:《论共犯的最小从属性说——日本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发展与借鉴》,载《法学》2007年第11期。——译者注作为学界有力观点,限制从属性说主张,限于能认定正犯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的场合,才能认定共犯之成立。与此相反,上述观点则主张,即便是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能阻却违法性的场合,也能认定背后者成立共犯(最小从属性说)。④作为支持最小从属性说的观点,参见平野龍一:《刑法 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358页;西田典之:《刑法総論》〔第2版〕,弘文堂2010年版,第395页;大谷實:《最小限従属性説について》,载《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2)》,成文堂1998年版,第472页以下;等等。不过,这些观点虽承认违法性评价一般是连带作用的,但限于极其例外的场合,试图承认处于合法行为之背后的背后者有成立共犯的余地。
当然无法否定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理由。然而,如果重视狭义的共犯毕竟只是一种补充性的处罚规定,那么,在正犯的违法性得以阻却的场合,亦即,连正犯行为都没有处罚之必要的场合,还要追究位于其背后的背后者的共犯之责,显然鲜有此必要。⑤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混合引起说要求,不仅从共犯来看属于违法,而且,从正犯来看,也必须是引起了违法的法益侵害。立足于混合引起说,就会支持限制从属性说(事实上,限制从属性说不过是将混合引起说的结论换一种说法而已)。立足于重视共犯的这种“第二性的责任”的性质的立场,想必是维持限制从属性说,在X止于狭义的共犯的场合,否定X成立共犯。⑥持这种观点者,参见林幹人:《適法行為を利用する違法行為》,载林幹人:《刑法の現代的課題》,有斐閣1991年版,第117页以下;松宮孝明:《共犯の「従属性」について》,载松宮孝明:《刑事立法と犯罪体系》,成文堂2003年版,第253页以下;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340页;等等。非要对此进行解释的话,就应该是,尽管X的参与实质上不能谓之为应该阻却违法性的参与,但这里是从共犯的补充性、从属性的角度否定对X的处罚。⑦另外,如果背后者特意创造出利益冲突状况的,原本来说,几乎所有场合都有将背后者作为共同正犯予以处罚的可能,因此,即便认为狭义的共犯一律不可罚,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处罚漏洞。指出了这一点者,参见林幹人:《刑法総論》〔第2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425页。
另外,在以这种理解作为前提的场合,像最高裁判所1992年决定的案件那样,在Y的防卫行为被评价为防卫过当的情况下,我们假设X的参与能被评价为教唆犯,那么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如前所述,对于防卫过当的刑罚减免根据,如果认为完全是因为责任的减少,那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即便只是部分性地考虑违法性的减少,基于其立场,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理解:违法性减少的效果有必要连带作用于狭义的共犯。然而,本文以为,限制从属性说不过是主张,要成立共犯,以正犯实施了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为必要,但并不包含共犯的违法性程度不得超出正犯这种内容。⑧有关这一点,参见小川正持:《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4年度),第41页。那么,按照本文这种理解,即便对正犯能认定违法性减少,但对于创造了那种状况的位于正犯背后的共犯,违法性减少的效果不会连带作用。
四、实行共同正犯的正当防卫之判断
(一)问题之所在
下面想继续探讨X、Y作为实行共同正犯而共同实施了防卫行为的情形。
例如,X、Y面对B的侵害,二人共同实施了暴力、伤害行为,但前提情况是,X事前已经预想到B的侵害,具有积极的加害意思,仍带着不知情的Y前往现场(【案例4】)。在该场合下,X与Y在构成要件层面共同实施了伤害行为。并且,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作为防卫行为是违法性阻却的评价对象,因此,不是将X、Y的构成要件行为予以个别化,而是在对二人的整个行为进行整体评价的基础上,来判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为此,对于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判断,参与者之间连带判断就成为一种原则。
然而,基于那种主张作为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情况(积极的加害意思、防卫意思等)的立场,就可能根据参与者在主观方面的差异,而出现评价相对化的余地:即便对Y而言能评价为正当防卫,但对X而言不能谓之为合法行为。对于前述【案例1】,本文曾提到,由于实际的防卫行为完全是由Y实施的,因而,判断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就只能以Y的行为为标准,但在【案例4】中,由于X实施的防卫行为与Y实施的防卫行为实际处于竞合状态,因而,对于防卫行为本身的法律评价,完全有可能因为各人主观方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按照防卫意思必要说的立场,仅限于对抗行为能为防卫意思所覆盖的场合,该行为才会被评价为合法行为,因此,在具有防卫意思的A与不具有防卫意思的B共同实施防卫行为的场合,想必结论就应该是:从A的角度来看,该行为被评价为合法的防卫行为,但从B的角度来看,该行为则被评价为违法的侵害行为。
(二)正当防卫的限制标准
不过,对于像【案例4】那样,积极的加害意思如何限制正当防卫这一点成为问题的案件,还有更值得探讨的问题。亦即,问题在于,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究竟是应该以防卫行为人的主观为标准,还是应该以被侵害人的主观为标准呢?具体而言,在通常的正当防卫的案件中,是被侵害人本人为了防卫自己的生命、身体等而实施防卫行为,因而被侵害人就是防卫行为人,这一问题还不太突出,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为了第三者而实施正当防卫的情形,那么,究竟以谁的主观为标准来判断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就属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该问题,本文无法详尽论述,①虽然论述得不够充分,但作为本人对此进行了一定探讨的论文,参见橋爪隆:《正当防衛状況における複数人の関与》,载《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1)》,成文堂2006年版,第639页以下。但在虽对侵害存在预期,仍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直接面对侵害的场合,如果按照针对该人的法益侵害危险“是该人敢于接受的结果,因而就应该让行为人甘愿接受其结果”这种理解,②参见香川敏麿:《正当防衛における急迫性》,载小林充、香川敏麿编:《刑事事実認定(上)》,判例タイムズ社1992年版,第263页。就有必要以保护被侵害人的法益的必要性为标准来探讨对正当防卫的限制。③反之,如果重视防卫行为人是否具有行使正当防卫权的资格或者权限这一视角,毋宁说,是否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就会以防卫行为人的主观为标准来决定。可以说,防卫意思必要说就属于重视这一点的观点。而且,通过法确证原理来解释正当防卫的观点里,这种倾向也很强烈。亦即,对于那些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虽已经预想到侵害,仍挺身面对这种侵害的人的法益,就鲜有通过正当防卫予以保护之必要。最高裁判所也有下面这样一个判例:被告的长子A与B发生争吵打斗,在此过程中,A逐渐落入下风,遭到携带菜刀的B的追逼,看到这种情况,被告误以为A完全是遭受B单方面的攻击,遂手持猎枪向B开枪,致B重伤。对于此案,最高裁判所判定,“对于被告的本案行为,二审判决认定属于假想防卫,但超过了防卫限度,判定按照刑法第36条第2款进行处断,这是适当的”(最决昭和41年〔1966年〕7月7日刑集20卷6号554页)。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之所以认定本案属于假想防卫,想必是以这一点作为前提:本案中,B针对A实施的侵害,是A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所招致,不过是争吵打斗的一个过程而已,因而不能认定具有侵害的紧迫性。这里也是与本文的立场一样,是以被侵害人的情况为标准,来判断有无侵害的紧迫性。在此基础之上,由于被告对于不存在侵害的紧迫性这一点并无认识,因而本决定以被告对于侵害的紧迫性存在错误认识(假想)为理由,认定成立假想防卫过当。①有关本决定,参见船田三雄:《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41年度),第108页以下。
这样,在“以被侵害人的情况为标准来探讨可否实施正当防卫”这种观点作为前提的场合,对于【案例4】,也会认为,对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而自己招致侵害的X而言,其法益鲜有通过正当防卫予以保护之必要,因而,由X、Y二人实施的防卫行为就会在法律上被评价为,完全是为了保护Y之生命或者身体的行为。②另外,有学者将该问题作为由认定成立正当防卫的主体(A)与否定成立正当防卫的主体(B)之共同实行的问题来把握,仅以B所引起的侵害作为处罚对象(参见山口厚:《共同正犯の基本問題》,载山口厚等编:《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16页以下)。基本的问题意识与本文是相通的,但本文的理解是,不是以“谁实施了防卫”而是以“对谁实施了防卫”作为标准,将违法的法益侵害分割开来。为此,由X、Y二人共同实施的防卫行为,(不考虑保护X的法益)如果作为仅仅是为了保护Y之生命或者身体的防卫手段也具有相当性,那么,Y是能成立正当防卫的。③假如虽然作为保护X与Y二人的法益的手段是相当的,但作为保护Y个人的利益的手段超出了相当性的范围,在该场合下,Y的行为就会被评价为防卫过当。进一步而言,如果Y对于X的积极的加害意思等并无认识,由于对超出相当性这一点缺少认识,因而会阻却故意。反之,在对于X的防卫行为的评价这一点上,(1)就为了保护X自身的法益的防卫手段而言,如前所述,由于丧失了通过正当防卫这种法律保护的必要性,该行为不能被正当化;(2)就为了保护Y之法益的防卫手段而言,由于能够评价为,X是出于积极的加害意思,自己创造了针对Y的侵害,因而该防卫行为也不能被正当化。最终来说,就只能是全面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④反之,也可能存在这样的观点:在X的积极的加害意思之外,另外还独立存在Y的法益的要保护性,因而,对于X也应该允许其实施为了保护Y之法益的防卫行为(尤其是,针对Y的紧迫侵害对X而言也是出乎意料的场合)。这一点还有必要进一步思考。
五、共同正犯之间认识的不一致
最后,想就下面这种情形简单做些探讨:数人共同实施了被评价为防卫过当的行为,但对过当这一点存在认识上的不同。例如,X、Y突然遭受B的侵害,二人通过现场共谋,共同实施了防卫行为,其中,Y的行为超出了相当性(超出了防卫限度),且由该行为导致了B的死亡(【案例5】)。在该场合下,有必要探讨X、Y的共谋的射程原本是否及于Y的行为。假设案情是这样的:X与Y在现场共谋徒手进行防卫,在共同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情绪激动的Y突然掏出菜刀,数次砍向B的胸部。在该情形下,(当然取决于具体的案件事实)很多时候就可能以Y的捅刺行为不是基于X、Y的共谋的行为,而是基于Y在现场独自的意思决定的行为作为理由,否定共谋的射程及于该行为。⑤对于所谓共同正犯的量的过当的案件(最判平成6年〔1994年〕12月6日刑集48卷8号509页),如前所述(参见橋爪隆:《共謀の意義について(1)》,载《法学教室》第412号(2015年),第133页),也能够理解为,当初的共谋的射程不及于侵害结束之后的追击行为。在该场合下,就Y而言,通过将整个防卫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认定其成立防卫过当,但X仅仅与正当防卫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会认定其阻却违法性。
反之,如果X与Y当初实施的防卫行为逐渐升级,结果发展至Y实施了用刀捅刺B这种防卫过当的行为,对于该情形,想必大多能够以从当初的共谋以及基于该共谋的防卫行为来看,防卫行为的程度完全有可能逐步扩大作为理由,肯定共谋的射程也及于防卫过当的结果(即B的死亡结果)。也就是,在该场合下,X与Y是基于共谋(在构成要件层面)共同引起了伤害致死的构成要件该当事实。并且,只要成立共同正犯,对X、Y而言,其追责范围就不再限于各自分担的行为及其结果,而是应就二人的整个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因此,就应该以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或者结果为对象,判断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为此,从客观上来说,不仅是Y,对于X的参与也要否定具有防卫行为的相当性,X与Y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①关于这一点,参见高橋則夫:《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13年版,第461页注109。
不过,对X而言,有时候也可能对Y实施防卫过当的行为不存在预见。在该场合下,对于由自己参与的共谋以及基于该共谋的共同实行行为所导致的过当结果,X并无认识,因此,X就缺少对防卫过当(过当性)的认识,应否定成立故意犯罪。关于这一点,曾有这样一个判例:由于同居在一起的亲属D醉酒闹事,A、B、C三人为控制D而合力将其摁倒在地,但由于C强力压迫面部朝下倒在地上的D的后颈部,由此造成D窒息而死,②在C摁住D的后颈部的过程中,虽然D的侵害已经结束,C仍然继续摁住D的后颈部,进而造成D的死亡,如果这一事实明确的话,本案就属于量的过当的类型,但如果D的侵害的结束时间不明确,就可能被评价为质的过当的类型(不过,对于量的过当,判例、通说认为,在防卫意思仍在持续的限度之内,应适用第36条第2款,为此,按照这种观点,质的过当与量的过当的区别就并不重要)。但对于C如此强力地摁住D的后颈部这一事实,A与B并无认识。对于此案,东京地判平成14年〔2002年〕11月21日判时1823号156页认为,“在数人……共同实施反击行为的场合,对于属于相当性判断之基础的事实有无认识,应该就各人个别判断,因此,如果其中某人的反击行为超出了防卫行为之相当性的范围,对于这种防卫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即便客观上无法否定与共同实施反击行为的其他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共同实施反击行为的其他人对于属于相当性判断之基础的事实存在错误认识,而且,按照这种认识的话,就没有超出相当性范围的,那么,就应该作为假想防卫的一种情形,对于这里的其他人,不能就实际造成的结果追究故意之责”,以此为理由,对于就C的行为并无认识的A、B,进一步判定,“不能追究针对D的伤害致死罪的故意责任”。该判决立足于A、B、C共同实施了防卫过当行为这一前提,对于A、B二人,以对于被认定具有过当性的基础事实不存在认识为理由,否定成立故意犯罪,应该说是正确的判断。
另外,立足于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是在故意相一致的限度之内成立共同正犯,如果对部分参与者否定成立故意犯罪,那么,其结论难道不应该是,由于没有故意的一致因而不成立共同正犯吗?例如,在【案例5】中,如果以X对过当性没有认识为理由而认定其阻却故意,其结果就是,X要么不可罚要么仅承担过失致死的罪责,但在该情形下,Y应该在什么范围之内承担共同正犯的罪责呢?如果坚持要求罪名一致,那么,假如X存在过失,其结论是否应该是:二人在过失致死罪的限度之内成立共同正犯,在此基础上,Y另外再承担伤害致死罪的单独犯的罪责呢(假如X不存在过失,那么,Y是否完全被评价为单独正犯呢)?在这一点上,原本来说,部分犯罪共同说是基于什么根据,而且,是在什么阶段要求存在认识的共同,这一点并不明确,因而要具体进行探讨是很困难的。但在本文看来,如果认为共同正犯终究只是涉及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问题,只要存在对于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认识的一致即可,那么,在【案例5】中,由于在构成要件的层面对于暴力的构成要件该当事实存在一致的认识,(与X的罪责无关)Y应承担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的罪责。③提出这一点者,参见島田聡一郎:《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5号(2006年),第124页。应该说,这种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已经表明,部分犯罪共同说要求存在故意的共同本身,就并没有正确把握共同正犯的构造。
(责任编辑:钱叶六)
The Joint Principal Offence and Justifiable Defense and Excessive Defense
[Japan]Hashizume Takashi(Author) Wang Zhao-wu(Translator)
When it comes to deal with several people involved in defense behavior,there is concurrence on the judgment of justifiable defense or excessive defense and the treatment of joint offence relation. It is more complicated especially in the occasion that the subjective aspect of individual participant is inconsistent. First of all,whether justifiable defense could be established or not is relative between joint principal offenders. Besides,we should take the defense behavior actually implemented as a judgment standard. Furthermore,no matter it is an executive co-principal,collusive co-principal or joint offence in a narrow sense,the effect of elimination of illegality is also relative.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interdependent function on other joint principal offenders. At last,in the occasion that several people implement excessive defense behavior jointly,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whether the original range of joint offence is included by this excessive defense behavior if there are different cognitions.
Joint Principal Offence;Justifiable Defense;Excessive Defense;Relativity of Illegality Evaluation
D924.1
A
2095-7076(2017)01-0125-12
10.19563/j.cnki.sdfx.2017.01.011
*本文原载于日本《法学教室》2015年第5号(总第416号)。
**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