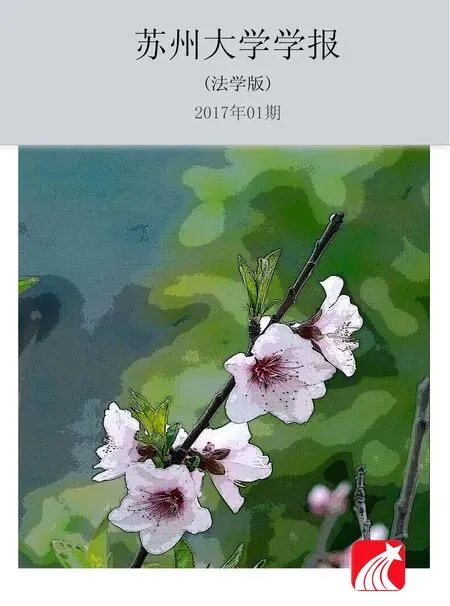于不确定处寻确定:论司法的本质是自由裁断
2017-04-02周赟
周赟
● 学术专论
于不确定处寻确定:论司法的本质是自由裁断
周赟*
规范实证主义者已经就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断问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而现实主义法学者则就事实的不确定性与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断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判断。但一方面二者的研究系分别且独立地从法律以及事实的不确定性角度进行;另一方面,他们关于司法过程中自由裁断的基本观点保留在或然性层面;再一方面,他们都没有关注到法官不仅仅面对法律或事实问题时需要自由裁断,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逻辑关联的证成也是一种典型的自由裁断。可以说,司法的本质就在于在具有种种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通过自由裁断寻求最具有可接受性的确定性结论。
司法;实践理性;自由裁断;不确定性;确定(性)
“所有的(现代)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①Karl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Routledge,1962,p.34.
——波普尔(Karl Popper)
“也许可以肯定地认为,这种对确定的、确实的必然性的逃避,这种含糊和不确定的倾向,正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危机状况;或者正好相反:这些理论同今天的(自然)科学相一致,表现了人们对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和认知模式采取开放态度的积极能力,表现了人们有效地努力推进自己的选择余地和自己的新境界的进程的积极能力”。②[意]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艾柯(Umberto Eco)
引言:从法律乃实践理性说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谈及正义问题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指出,尽管在很多情形中法律即意味着正义,但“遵循制定法并不总是意味着正义,因为立法必须是普适性(universal)的,而具体个案并不总是可以恰切地为这些普适性的立法所规范”,因此,有时“衡平的正义比形式正义(也即依法而为)更为可取”。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法律之治是一种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之治”的命题。而所谓实践智慧,与单纯的具有必然性和可口耳相传属性的知识(knowledge)明显不同,“它是关于人类心智(mind)的一种状态,它关联着理性(reason,所以人们更习惯于称之为“实践理性”——引者注)以及恰切的行动,并以对主体有益或不利的事物为指向”,对于实践智慧而言,并没有外在于行动本身的、悬设的良善判准,“因为‘作出适切的行动’(well-doing)就是它本身的目的和判准”。①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Trans. by D. P. Chase,China Social,pp.126-127、135.
时至今日,可以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或“法治是一种实践理性之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一个被普遍传播的教条。在这里,“教条”的意思是:尽管某种观念或判断被广为接受,但这种接受就如迷信现象中主体对有关对象的接受一样,并不建立在主体自身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仅仅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的普遍存在。之所以作出这一判定,是因为如下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或“法治是一种实践理性之治”已被广为接受,这可以从各种法学教科书、著作和论文中广泛援引该论断这一现象得到明证;但另一方面,根据这一命题的许多逻辑推论却并没有被接受,甚至被强烈地拒斥——关联着本文的主题,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推论是:司法至少有时是一种充盈着自由裁断(discretion)的活动;进而对司法而言,有时其实并没有所谓正确答案,更不要说唯一正确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与“司法有时是一种充盈着自由裁断的活动”并没有必然关联,更不用说后者是前者的逻辑推论,因而接受前者并不意味着必定需要对后者的接受。对于这种可能的说法,可以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如下内在逻辑关系的揭示予以预先的回应:当亚里士多德说法律乃实践理性或法治乃实践理性之治时,他的实质意思是,一方面,由于普适性的法律面对具体的个案时总是可能存在“不合拍”,因而需要用法者(以下统一以司法以及法官为例)去寻求并揭示不合拍时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在进行这种揭示并最终裁断个案时,不应片面地以制定法的形式上之规定为唯一判准,还应充分考虑具体个案的各种具体情况,从而更好地对具体个案“作出适切的行动”、也即作出最符合实质正义的结论。从如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本来“不合拍”的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必须首先被加工为至少看起来合拍以至于可以择取某一或某些条文来裁判当前案件,这种加工实际上就是一个自由裁断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得出正义结论时到底应当考虑哪些具体情况、又如何考虑这些具体情况,显然亦是一个自由裁断的过程。因此,如果接受“法律乃实践理性”或“法治乃实践理性之治”的说法,从逻辑上讲,就当然意味着对“司法有时是一种充盈着自由裁断的活动”的接受。
也许有人会问,本文得出尚有许多人目前并没有接受、甚至拒斥“司法有时是一种充盈着自由裁断的活动”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可以从各种立法以及关于司(用)法活动的分析、宣传看出。以2012年修订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例:作为一部新近修改的法案,它仍然保留了大量“正确”、“准确”、“属实”、“清楚”、“确实”、“充分”等对于裁判活动及其结论的限定词,典型条文如修订后的第2条、48条、53条、168条、172条等。另外,在许多学术作品中我们也仍然不时可以看到“司法是否应当/可以能动”、“法官有没有法律解释权”或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如果预设或接受了司法有时充盈着自由裁断,这些问题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和意义;不仅如此,舆论宣传中也同样高频度地出现“严格依法判案”、“铁案”、“铁证如山”之类的文学化但却实际上代表着舆论制造者之心声的修辞。
当然,也许还有人会质疑,即便如上诸种现象确实与“司法有时充盈着自由裁断”命题相悖,但这并不足以推导出前者一定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也有可能是后者本就不成立,或根本是一个假命题——总不能仅仅因为它得自一个经典命题而这一命题又为亚里士多德作出就注定成立吧?这意味着,有必要对后者进行分析、证成。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出现在当下立法、法学研究以及法治宣传中的如上现象当然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本文基本赞成“司法有时充盈着自由裁断”这一命题。之所以是“基本”赞成,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司法并不是“有时”充盈着自由裁断,毋宁说,它根本上就是一种自由裁断活动,因为司法的根本任务正是面对不确定的法律和事实世界得出确定的答案,或者借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谈及法国法院系统的任务时所作的判断,是“使不确定性得以确定”。①[法]利科:《论公正》,程春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也就是说,本文的立论——司法的本质是自由裁量——比起亚里士多德经典命题的如上论断更进一步;当然,也正是这种“更进一步”构成了本文的根本挑战并使本文的分析、论证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展开下文的详尽讨论之前,也许应当对“自由裁断”一词作一必要的说明、限定。按照德沃金(R. Dworkin)的考察,“自由裁断(discretion)是实证主义者从日常语言中借用过来并成为一个专业术语的。……它本来的意思是指:根据(subject to)由某种权威设定的某种标准作决定的过程或其内容”,“自由裁断,正如面包圈(doughnut)中的那个空,如果没有外面的一圈面包(原则)划出界限,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所谓自由裁断并不是可以无视某些权威标准而作出任意的裁量”。②R. Dworkin,Is Law a System of Rules?,in Ronald Dworkin ed.,The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52、54.也就是说,这个词语最初可能主要用来指称法官对立法内容的判定过程。而弗兰克(J. Frank)则指出了该词语的另一重意思,他说,所谓自由裁判就是初审法院“在不同的可能性事实之间进行决断的权力”③Jerome Frank,Law and Modern Mind,Anchor Books edition:1963,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rentano’s Inc.,1930,Preface to Sixth Printing,P. XV。此处或值一提的是,就目前来看,国内似乎更倾向于将“discretion”译为“自由心证”而非“自由裁断”,但本文认为由于“自由心证”习惯上往往被用来专门指称事实认定过程中的自由裁断,而不用来指称法律规范内容判定过程中的自由裁断,因此,也许“自由裁断”或“自由裁量”才是“discretion”更为贴切、全面的翻译。。本文所谓的自由裁量综合了如上两位学者的认识,具体来说可分析如下:第一,法官对立法内容或事实的认定直接取决于其主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法官基于主观的认定可以或应当不受任何制约,事实上,任何法官都必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这就正如卡多佐所言,“无拘无束、不受羁束的完全自由是不存在的。成文的法典、先例、模糊的习惯或无法溯源的技巧,成百上千的限定条件约束着我们、限制着我们,即使在我们自以为可以自由自在漫游的时候,法律的职业观念对我们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空气一样,即使我们没有留意它的份量。分配给我们的任何自由都是有局限的”。④[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一、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司法的本质
对于法官而言,他(或她,下同)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法律问题,因为他必须根据法律展开一切司法活动,而这可能也正是汉语“司-法”一词的本来构词逻辑。按照“严格依法判案”说法的路数,先在的法律是不应存在不确定性的,因为如果法律本身本就不确定,何来“严格”依法判案?但应该看到,自法社会学以及现实主义法学兴起、尤其是哈特(H. L. A. Hart)等人提出法律语言结构中的空缺结构(open texture)理论⑤[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35页。以来,“法律是确定的”这一被哈特称为“高贵之梦”(noble dream)⑥关于这一术语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惊悚之梦”(nightmare),可参见H. L. A. Hart,American Jurisprudence through English Eyes:the Nightmare and the Noble Dream,11 Ga. L. Rev. 1976-1977.的观念已经越来越被怀疑。可以说,在今天,即便是最刻板、保守之人也至多宣称“法律具有确定性”而不会再坚称“法律是确定的”。
如果如上描述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官面对法律时的自由裁断本质是一个已然得到充分论证的成熟命题?进而言之,本文这里的第一部分论说岂非没有必要?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一则一个已经得到接受的命题可能建立在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论证基础上,也就是说,人们误以为一种相应的论证是成立的进而接受了该命题,与此同时该命题本来又恰恰能够成立故而这种理论上的接受并没有带来明显不利之后果;二则就算已经有了一种相对完美的论证,如果能对这一命题提出别种进路的论证,则这后一种论证当然也有其价值和必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关于法律不确定性的既有研究或证成而言,似乎这两方面的可能都存在:就第一方面讲,既有相关研究、论证采取的几乎都是一种语义学的进路,最典型的就是哈特的“意义中心”与“意义边缘”理论——正是因为所有的术语都有意义中心和意义边缘,因此,至少在意义边缘处法律会呈现为不确定的。这种论证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是因为意义边缘才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的存在,则所谓法律的不确定性似乎就仅仅是一种或然性属性,因为至少意义中心就不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申言之,既有研究其实并没有能够从逻辑上证成法律必然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命题。就第二方面讲,则正如理论常识告诉我们的,对任何命题的证立都存在多种可能的路径。同样地,对法律的不确定性命题之证立,除了语义学的论证进路,当然还有其他可能的进路。
在笔者看来,从语义学角度分析、证成法律的不确定性注定比较困难,因为对于以实施、运用为生命的法律来讲,它的不确定性恰恰根本地体现在被运用的过程中,因而相对静态的语义学就注定无法较为清楚系统地揭示出它的不确定性;比较而言,从动态角度研究语言的语用学理论则可能更适合承担这种角色。
对于语用学(Pragmatics),有学者指出,“语用学的诞生,源于人们不能从语义和语法角度去解释许多语言现象,只好另辟蹊径”①钱冠连:《语用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展望》,载《现代外语》1990年第2期。;吉列·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则用“场合”、“事件”、“行为”对语用学的理论构成进行归纳。②[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页。可以说,语用学与传统语义学“不考虑说话者的言语情境、措辞以及语境、要求、对话角色和所持立场”不同的是,它试图从语境的角度去分析、解释某些语言现象,所谓“语用学想让形式语义学从事另外一种研究,即从事经验研究”。③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譬如,欲准确理解散步中的热恋女孩嗔怒地对男孩说“你真讨厌”这句话,就只有结合语境“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在散步,女方嗔怒地对男方说”,我们才可以清楚地对之展开分析并得出具有可接受性的理解。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不妨根据如上语用学的理路,将语句分为“语法语句”和“语用语句”,其中前者是指严格依据语法规则进行构造并可以按照语法规则进行理解的“标准”语句,可以对译为英文单词“sentence”;而后者则是指具体主体在具体语境当中用以表达个性化意图的语句,可以对译为英文单词“utterance”。考虑到人与人的交往其实总是语境化的(也许语言教学可以除外),因此可以认为任何一个交际语句之意义都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把握、也即其意义必定只能显现于一定的语境之中。从逻辑上讲,这种“显现”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仍以语法语句中的概念为根据,进而参酌语境对有关概念具体化,如两个中国人讲“国庆节不见不散”中的“国庆节”之语义就应该是“西历10月1日”——应该说此时的语义大体还是与字面语义相对应的;另一种则只能尽可能地结合语境中的因素进行推导,如对前述例子中的“真讨厌”就只能进行推导,得出的意思也可能离该词的字面意义相距甚远。如果“语用句”这种提法是可接受的,那么可以说,用以表述法律规范的立法语言就是一种典型的语用性语言,因为任何纸面上的法律都必须、也只有在运用过程中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或者说真正的行为规范。这意味着,任何法律规范的意义都必须面对具体个案(语用环境)并结合具体语用环境才能最后得到确定。脱离了语境的所谓“确定”、“清楚”充其量不过是语法意义上的确定、清楚,对于面对具体个案的法官而言,这种确定、清楚充其量仅仅具有参考价值,而绝不是可以简单照搬意义上的确定、清楚。举例来说,“机动车辆不得入内”这一规定,从语法角度看,其语义不可谓不清楚、确定,但其实“机动车辆”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在面对具体案件之前并无法全然确定:一辆典型的机动车可能不属于这里的机动车,如救护车、警车或儿童玩具机动车;一辆本来不属于机动车范畴的车可能因为该规定而不得入内,譬如一辆体积过大的马车。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一个法律规范具有语法意义上的确定、清楚,那么它至少在典型案件中可以照搬套用。换言之,在典型案件——即可以简单照搬适用立法规范而不至于引起较大争议的案件中,法律可能确定、清楚,因而也不需要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方能适用。再换言之,一如本文所尝试超越的语义学研究进路,本文上述分析所表明的仍然不过是法律具有的是或然的不确定性:面对典型案件时可能是确定的,面对非典型案件时则是不确定的。就这种可能的争辩,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反驳:第一,所谓“典型案件”是一个典型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①“理想类型”是韦伯(Max Weber)创设的一个社会科学术语,用来指称那些在经验中没有严格存在但却是人们构造理论或用来描述经验世界必不可少的概念工具,最典型的理想类型是经济学中的各种模型、规律。详可参见[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尤其是第38-42页。或司法实践中的辩论技巧/修辞,现实中不可能有一个案件只可能是典型案件,而不可能是非典型案件。这一判断的实质是,只要一个法律人足够高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所谓典型案件都可以被论证为非典型案件——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为“典型案件的非典型化”;相对应地,只要一个法律人足够高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非典型案件也都可以被抽象、论证为典型案件——我们不妨称之为“非典型案件的典型化”②前者如当年轰动一时的“王海现象”(知假买假然后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赔二”规定索赔的“专业”活动),按照王海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则本案是典型的可以适用消权法“假一赔二”条款的案件。换言之,此时如果商家及其代理人循着王海一方的思路,则官司输定了,因为该案确实看起来是典型的“假一赔二”案。但“幸运”的是,商家的代理人较为高明,他提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代理思路:由于王海并非以消费者身份而是以“XX公司”工作人员身份购买产品的,因而根本不属于消费者,进而该案只能适用一般合同法的违约条款(这意味着赔偿金大大降低)。可以看到,“王海现象”本来似乎是一个典型案例,但通过商家的“加工”,却变成了一个非典型案例(至少对法官而言是如此)。对于后者,则可以说,任何对非典型、也即法律适用上引起较大争议案件的妥善解决,都意味着从纷繁复杂的案情中抽象出典型的“情节”,进而可以无甚争议地适用于某些或某个规范。关于典型案件与非典型案件的关系问题,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详可参见周赟:《非典型案件与典型案件:术语、成因及其关系》,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如果此处的分析可以接受,那么,所谓“法律面对典型案件具有确定性”这一命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理想类型,而并非法律世界的真实状况。第二,就算典型案件可能存在,单纯就法律语言本身来讲,它的语境意义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的确定性。对此,我们可以从语言学中关于“语言之语”与“语言之言”二分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证立。索绪尔(F. de Saussure)在讨论语言问题时指出,人类语言现象中始终包含两个部分,即“语言之语”(langue)与“语言之言”(parole),其中前者大体指的是人类语言的语素、语范、语法等所组成的一个系统,后者则是指特定的言说者根据前者而具体表达出来的内容。很显然,前者是社会性的、规范性的,后者是个人性的、创造性的,因此后者必须遵从前者的规约,因为只有如此后者才可被理解,与此同时前者又必须通过后者的累积才能形成。③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42页。简言之,个性化的语言之言根本上必须依托于作为其基础的语言之语方能传达其意义,而一个社会的语言之语本身又是可变的。表现在法律领域,则可以说用来表述法律规范的法律之言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必定取决于特定情境中的法律之语。考虑到一方面这些法律之语本就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另一方面,或许也更重要的是,法官对于一个社会的语言之语作何种把握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判断、自由裁断的过程——当法官的裁量结果正好与大部分人相同时,他可能对于这种裁量的主观性不自觉也不自知,但这种不自觉或不自知并不能从反面消解此一过程的自由裁断本性。概言之,无论面对典型案件或非典型案件,法律规范意义的不确定性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所不同者仅仅在于,面对非典型案件时,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感受到或发现法官对自由裁量的运用,以及进一步发现立法之法的不确定性;而面对典型案件时,由于法官通过自由裁断所得出的结论正好与特定语境中大部分人的结论一致,因而不会引起争论进而也容易给人如下错觉:“法官在典型案件中并没有自由裁断”或“立法之法(至少)在面对典型案件时意义是确定的”。
如上的分析已经表明,立法之法的规范意义应该也只有在面对案件事实的解释过程中才可得以彰显;并且经过此一过程而形成的“规范意义”早已超越或至少不同于立法之法的语法意义。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每一次用法者根据案件事实对法律进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续写、确定法律之规范意图的过程。申言之,对于法官而言,先在的立法之法总是具有不确定性,而非如哈特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法律只有在意义边缘处方不确定;进而言之,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之一正是面对案件事实,通过自由裁断确定这些本来不确定之法律的规范意义。
事实上,也只有理解了法律语言的语用本性以及不确定性本性,我们才能理解何以加达默尔(Hans-G. Gadamer)一口咬定,“法律……的实际运用总是需要解释,这反过来又说明,任何实际运用总已包括了解释。司法实践、先例适用或迄今为止的执法都一直具有一种法律创作的功能”;①[德]加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6页。进而才能理解A. W. B. Simpson的如下感慨,“法律解释(实即面对具体案件释放立法之法的语义,引者注)之难,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如何让它适用于当下案件事实”。②[美]比克斯:《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相应地,只有理解了法律语言的语用本性,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现实主义法学者的那个看似极端的观点“法官说什么,法律就变成了什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进而也才能理解即便是认为实证规范可以成为一张“无缝之网”的规范实证主义者凯尔森(Hans Kelsen)居然也特别强调:“不论一般规范打算如何具体,但司法判决所创造的个别规范始终将加上某些新的东西”。③Hans Kelsen,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p.38.
如果承认法律本身是不确定的,而所有审判结论当然是确定的(否则无法执行),再考虑到不确定的前提不可能通过三段论得出确定的结论,则可以反向推知作为审判结论大前提的审判规范④所谓“审判规范”,也称“裁判规范”,是肇始于法社会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一个术语,其大意是指“法官在司法中所援引或构造的、适用于当下案情裁判的规则”。审判规范可能并不与立法规范保持严格的一致,因为至少在非典型案件之中,法官就必须对立法规范进行适当的加工方有可能生成作为案件结论大前提的审判规范。详可参见谢晖:《论民间法与裁判规范》,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它由法官根据立法之法并通过实践理性智慧的运用而构造——也一定是确定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审判规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作为其重要基础的立法之法又是不确定的。相应的结论就只能是:法官通过自己的加工、其实也就是通过自由裁断赋予了不确定的立法之法以确定性。换言之,至少面对法律问题时,法官的工作具有自由裁量之本性。
二、事实的不确定性与司法的本质
事实的不确定性命题首先因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的研究才引起广泛关注并最终导致了相关认识的转向。弗兰克等现实主义法学者主张,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并不具有像传统法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具有确定性。弗兰克自己就曾以证人证言为例,对确定性事实之所以不可得作出了如下三重分析、说明:第一,证人不是机械的记录机器,因而在事件发生时,他对过去事件的观察就已经发生了错误。即便证人的观察本身也许是可靠的,但第二,证人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当然,就算证人记忆也没有出现偏差,他也仍然有可能第三,在出庭作证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作出了有偏差的陈述。⑤参见[美]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19-23页。
基于对事实的如上分析以及相关的其他研究(如所谓司法过程中的恋父情节、又如法官个人人格因素等⑥可分别参见Jerome Frank,Law and Modern Mind,Anchor Books edition:1963,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rentano’s Inc.,1930,Preface to Sixth Printing,pp.264-269;[美]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章《揭开正义的面纱》。),弗兰克相信,法官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自由裁断空间,甚至可以说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就是“猜测”:证据正如谜面,据以得出裁判结论的事实则如谜底,这一谜底系法官根据谜面猜测而来。弗兰克进而断言,“不管正式的法律规则是多么的准确和明晰,不管这些正式的规则背后存在着什么能够发现的一致性,由于判决所依赖的事实令人捉摸不定,因此在绝大多数还没有提起或审理的诉讼案件中,现在要预测将来的判决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在将来也通常是不可能”①[美]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申言之,在弗兰克看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上不具有确定性,因为它从根本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断。
弗兰克等现实主义者的贡献在于,几乎凭一己之力使人们对于事实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一个转向:通过他们的研究,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事实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其局限则在于,他们仅仅通过对诉讼、也许尤其是疑难案件的诉讼作一种经验主义式的观察并进而通过归纳得出了事实的不确定性结论,却没能或至少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一经验性命题进行更为系统的说明以及更有逻辑的证成,因而从根本上说,弗兰克等人充其量只是认为不确定性只是事实的偶然属性。现实主义者的这种不足之处,也正是本文作出努力的空间。
总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事实的必然不确定性命题进行分析、论证:第一,作为事实构成基础的证据取决于所有诉讼参加人员②本文所称“诉讼参加人员”与诉讼法(理论)中的“诉讼参加(与)人”有所不同,泛指所有实际参与到诉讼活动中的所有人员,包括法官、证人、诉讼双造等。之择取,而事实本身又取决于诉讼参加人员依据证据而展开的想象、回构。这也正是当年弗兰克等人对事实的不确定性进行论证时的主要着力点所在:在收集原始证明材料的过程中,证据必定有所遗漏;在认定证据的过程中,这些证明材料也当然要经过一定的筛选,至少不具有合法律性的证明材料就将摒弃;究竟多少个怎样的证据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至于充分到可以依据这些证据认定某种事实是一个只有依赖司法者主观能动的问题;最后,在通过这些证据回构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司法者必定需要揉入较多的主观能动性,方有可能根据有限的证据猜测出作品(案件事实)的“本来样子”。
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参照法国学者利科(Paul Ricoeur)关于历史的认识来进行理解。利科曾这样描述、评定历史(学),“历史是一种‘痕迹的知识’的术语,……历史学家不面对过去的对象,而是面对过去的痕迹的这种明显限制使历史学失去了科学的资格:在历史文献的痕迹中理解过去,确切地说是一种观察,因为观察并不意味着记录一个原始事实”,“历史的目标不受再现一系列过去的事实,而是重组和重建,即组成和构成(造)一系列过去的事实”。③参见[意]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历史学家不具有“科学的资格”、无法达致客观确定的历史,法律实践者何尝不如是?
第二,司法过程中事实的不确定性,根本上也为诉讼逻辑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诉讼根本上是一种对抗性活动,这种对抗不仅仅发生在原告(或检控官)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间——所谓“诉讼是一场战斗”——其实也同样发生在原告与法官、被告与法官之间:尽管最终的事实认定权属于法官,但在整个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实际上的主导者却可能是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可以肯定,这三方的预设立场具有明显的不同:原告与被告是对立意义上的不同;而原告—被告与法官则是根本追求上的不同,前者以追求自身合法合理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后者则以通过纠纷的解决维续法律的权威以及法治的运转为圭臬。可以说,正是这种立场的根本不同,使得各种诉讼参加人员也许作为一个普通人时也可能倾向于对案件事实作出同一的认定,但其特定的诉讼参加人员之身份却使得他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必定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也就是说,司法过程中事实所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还取决于司法本身的逻辑结构。
第三,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并不是赤裸的生活事实(brute fact)本身,而是所谓的“法律事实”,因而它并不为原始作者(当事人)独立完成,而必定需要司法过程中其他诉讼参加人员的参与方能最后完成。尽管当前学界对何谓法律事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则不妨以如下一种相对得到更多认同的界定为基础:“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所框定的,而又经过法律职业群体(法官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证明的‘客观’事实。这其中的法律规范反映了立法者对什么是法律事实的框架性认识,而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的则是客观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意义”①陈金钊:《论法律事实》,载《法学家》2000年第2期。也许有必要明确的是,如果不考虑本文这里的主题而仅仅从概念上讲,则笔者并不全然赞成这种界定,因为按照这种界定,我们几乎只能看到司法过程中法律对事实的作用,而很可能忽略司法过程中事实对法律所具有的积极的反作用。详可参见周赟:《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事实关系》,载《求是学刊》2012年第6期。。根据这种界定,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其实是一种为诉讼参加人员赋予了特定法律意义的事实。换言之,这种意义并非事实的原始作者(当事人)一开始就独立且充分设定好的,而必得经过司法过程、也即经过事实的读者(所有诉讼参加人员)的接续、加工方能生成。这意味着,即便一个案件证据的收集、认定以及根据这些证据所回构出的赤裸案情本身可能由于物证技术的高度发达或案件本身的过于澄明而无法产生争议,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作为司法结论之小前提的“事实”本身就不具有可争辩性:无论物证技术多么发达,无论案件本身多么澄明,进而言之也无论作为生活事实意义上的案情本身多么没有争议,对这些事实之法律意义的赋予也仍然是可以争辩的。换言之,事实的法律意义也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②举例而言,“Tom砍了Mike一刀”这个生活事实也许因为物证技术的完善可以“铁证如山”进而“完全的”具有确定性,但这一事实作为小前提进入判决结论中时却是不确定的,因为它的法律意义几乎“一切皆有可能”:它可能意味着Tom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过失伤害、过失杀人,可能意味着Tom正当防卫、见义勇为,当然也可能意味着Tom实施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它甚至可能意味着Tom在履行合同(如Tom是外科大夫而根据与Mike签订的医疗合同实施手术)……。考虑到司法过程中诠释出来的“法律意义”又恰恰正是“事实”本身的有效构成部分(生活事实本身根本无法成为审判结论的小前提),因此可以说,在法官自由裁断之前,所谓“事实”可能并不存在,更不用说事实的确定性。
总之,一如面对法律问题时法官必得通过自由裁断方能确定其规范意义,面对事实问题时,法官也同样需要大量地自由裁断方可能“认定”作为审判结论小前提的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在谈到西方初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时的如下论断实可谓精辟地道出了其自由裁断之本质:“对事实构成作出判断,是以经验的情况、对行为所作的证言和类似的直观材料为依据的,或者更以另一些事实为依据,从这些事实就可以推断有关行为,并大体上确定其行为之真伪。这里所应达到的是确信,而不是更高意义的真理。……这里的这种确信乃是主观信念、良心,而问题在于这种确信在法院中应采取什么形式”。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5页。
三、法律—事实逻辑关系的不确定性与司法的本质
如上我分别从法律、事实两个方面对法官司法工作过程中的自由裁断本质进行了剖析、说明。当然,司法的自由裁断本质并不仅仅限于这两个方面,它也同样、甚至可以说更明显地体现在如下这一方面:对法律与事实相互关系的裁定。
尽管目前学界对司法过程的认识存在一些争议,但应该说基本都认同司法工作的基本框架内含着一个逻辑三段论:以立法之法(法律)为大前提或大前提的主要组成成分;④正如前文的一个脚注所已经指出的,此处之所以认定立法之法可能只是大前提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因为真正作为审判结论大前提的不是简单地对立法规范的照搬,而是法官根据当前案件事实、语境对立法规范进行适当加工而形成的审判规范。关于“审判规范”,可参见谢晖:《论民间法与裁判规范》,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以已经被赋予了法律意义的事实为小前提;通过演绎推理得出审判结论。从逻辑上讲,为了保证演绎结论的可靠性,就必须保证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存在一种充分的内在逻辑关联。举例来说,我们不能以法律规定是“杀人者死”为大前提,以事实是“Tom买了一个苹果”为小前提,得出“Tom应当被处死”的结论,因为“买了一个苹果”这一事实与“杀人者”这一规范没有充分的内在逻辑关联(包含关系)。而如果现在事实是“Tom故意杀害了Mike”,则可以“杀人者死”为大前提得出“Tom应当被处死”的结论。
因此,司法的核心任务除了确定法律的规范意义、认定事实①此处之所以不是“根据证据认定法律事实”而仅仅是“认定事实”(也即作为生活事实的案件事实基本情况),是因为“法律事实”本身就是根据法律认定的,换言之,在认定法律事实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一个论证某一或某些规范与当前案件事实存在充足、内在逻辑关联的过程。外,还包括判定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包含关系。在笔者看来,当下案件事实可以为哪个或哪些规范所包含,以及哪个或哪些规范与当下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最为严密,从根本上注定只能是一个自由裁断的问题。
之所以如此肯定地认为规范与事实逻辑关系的判定注定只能是一个自由裁断过程,首先是因为法律规范作为一种规范——请注意,此处不是规范的载体而是“规范”本身——只能存在于人的理念世界,也就是说,只能通过人的思维进行把握;而案件事实、尤其是尚未赋予法律意义的案件事实则只能存在于经验世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通过人的感觉进行把握的对象,这意味着“规范”与“事实”分处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既如此,则两者之间怎么可能存在一种不可争辩、无需主观判定的逻辑包含关系?
考夫曼(Arthur Kaufmann)在考察司法过程中的类推时曾敏锐地意识到,“类推的有效性相当根本地取决于比较点的选择,而且取决于确定被比较者之特征。比较点的确定主要不是根据一个理性的认识,而是很大程度地根据决断,因而取决于权力的运用,而这绝大部分都未被反思过”。②[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笔者以为,对规范与事实内在逻辑关系的判定与此颇为一致:因为两者根本上处于不同世界,进而使得对它们内在逻辑关系的判定就只能是“点”或者“关节点”上的判定,而一个事实的哪些组成部分才可称之为它的关节点以及需要多少个这样的关节点上的一致才可以判定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逻辑包含关系,当然“很大程度地根据决断”。举例来说,当下中国的法官在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往往从主观、主体、客观、客体四个关节点上进行,而事实上,第一,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并且只需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该法第13条对“犯罪”的定义是:“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也许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个定义并结合该法第二章“犯罪”的其他规定归纳出犯罪的如上四个构成要件,并且也许归纳成四要件比或远比其他四要件或三要件、七要件合理,但无论如何,这毕竟都不过是法官所选择的一种对于该法的解读。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可能有很多内容、客观上也可能包括很多方面,法官注定只能择取其中的一些进行关节点的认定,进而得出是否已经构成充足的四要件之判断。很显然,这里的“择取”、“充足”等措辞已经鲜明地表达出其中的自由裁断意味。
其次则因为一如当年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早在他的《哲学研究》中就已经指出的,如果一条规则是完全确定、毫不含糊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供它的应用者裁量——那么,应用者就需要另一条规则来决定这条规则的应用,如此以至于无穷。③[德]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这就是说,无论规则本身怎么详尽,它(们)的实现从逻辑上讲都必须仰赖运用者的“运用”、并且是“能动地”运用,而无法建基于对运用者能动性的无视或消解之上。申言之,规则的运用逻辑上一定包含着自由裁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罗蒂(Richard Rorty)的如下这个论断:“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皮尔斯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理解和规则的遵守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不能通过假设任何确定的实体来加以消除,因为原本的不确定性会在这个新的实体的层次上重新出现。无论是假设精神状态,还是假设理性语言的塑造规则,或假设莱布尼茨式的本质,人们要加以排除的那种模糊性,总会在用来进行排除的工具中再度出现”。④孙伟平编:《罗蒂文选》,孙伟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总之,在制定法体系中,作为逻辑三段论可能展开之前提的规范-事实间逻辑关系的判定,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由裁断的过程。而这大概也正是卡多佐(B. Cardozo)如下论断的实质所在——“法典和制定法的存在并不使法官显得多余,法官的工作也并非草率和机械。会有需要填补的空白,也会有需要澄清的疑问和含混,还会有需要淡化——如果不是回避的话——的难点和错误”。①[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页。
考虑到本文针对的是“司法”而非法典法系或法典法意味更为明显之国家或社会的司法,因而接下来,也许还有必要就判例法系的相关情况作一连带的剖析、说明。如我们所知,在判例法系的实践中,司法工作的核心可以抽象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案件事实的认定;第二,先例的选定;第三,从先例中发现、归纳出规范;第四,根据规范和事实得出结论。在这四项内容中,应该说第一、四项与制定法系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所不同者仅仅在于第二、三项。其中第二项的实质是判定先例中的案件事实与当前案例事实具有足够的相似性,而对这种相似性的判定同样取决于关节点的比较。一如前文讨论的制定法系中规范与事实之关节点的比较,这种比较同样充盈着主观性。举例说来,假设现在法官要处理一个名叫“长条凳”的案子(也即涉及的案件事实是“长条凳”),然后他到浩瀚的判决汇编中去寻找相关的先前判决,他找到了两个可能可以用来裁判本案的先前案例②此处之所以是“先前案例”而非“先例”,是因为一个先前案例只有在被当下法官接纳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来源时才能被恰切地称为“先例”。,一个叫“小狗”,另一个叫“蚯蚓”。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援引“蚯蚓”案来裁决本案是法官所愿意看到的结局,那么,他完全可以说,“在‘长条凳’一案中,凳子的形状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是本案的关节点。因此尽管‘蚯蚓’与‘长条凳’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在身体呈长条形这一关节点上两者是相似的,并且如此相似,所以可以认定,‘蚯蚓’案与‘长条凳’案两案构成相似关系,而前者的判决理由也因此可以适用于后者”。我们当然也可以假设,如果“小狗”案的判决理由可以用来追求法官想要的结果,那么,此时他完全可以说,“‘长条凳’一案中,凳子是一种有四条腿的物件这一因素是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是本案的关节点。尽管‘小狗’与‘长条凳’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在具有四条腿这一关节点上两者是相似的,并且如此相似,因此可以认定,‘小狗’案与‘长条凳’案两案构成相似关系,而前者的判决理由也因此可以适用于后者”。不难想象,何止“小狗”、“蚯蚓”可能可以被认定为在关节点上与“长条凳”相似,从理论上讲,世间任何东西都存在这种可能。而这“无限的”可能则清楚且充分地表明两个案件是否足够相似是一个需要通过自由裁断方能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上第三项内容,则可以用一个美国学者所举的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其自由裁断本质:A的父亲劝导(induced)她不要嫁给她曾许诺嫁给的B。当这位父亲这样做时,我们,或者说一个被限定为只能以该案为先例的法官,至少可以从中推导出这样一系列的规则,进而适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第一,父亲有权劝导女儿违反婚约;第二,父母都有权这样做;第三,父母也有权对儿子这样做;第四,父母对于子女的所有的契约都有权这样做;第五,所有人对于所有契约都有权这样做;第六,所有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契约都有权这样做。③H. Opliphant,“A Return to Stare Decisis”,i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14(1928).在实践中,如上这些规则中的某些可能难于接受,但必须承认,该案例非常清楚地表明,法官在识别先例的判决理由并进行确定时确实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
至此,可以看到,无论在制定法法系还是判例法法系,对规范与事实之间逻辑关系的判定,本质上都是一个自由裁断的过程,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或明显度④这种关于两大法系司法本质上具有实质的相通性之结论也正呼应了当年梅里曼(John Merrryman)的一个曾引起学界争议的、且梅里曼自己始终未作详细论证的判断,“两大法系在司法程序中的重大差异,并不在于两种法院实际上在做什么,而在于它们各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习俗观念要求法院应该做些什么”。[美]梅里曼:《大陆法系》(第二版),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有时这种自由裁量的本质体现得更明显,有时则以相对隐蔽的方式体现出来——这种“隐蔽”,有时甚至只能通过仔细推敲、考究才能发现。
四、结论及本文的研究意义
概言之,对法官而言,他首先面对的必定是一个充盈着可变动性、不确定性的世界:立法之法本身也许是确定的,但立法之法的规范意义却始终是不确定的;经验事实本身也许是确定的,但可以依据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却是不确定的——更重要的也许是,经验事实的法律意义始终是不确定的;存在一个或一些立法规范与本案具有充分的逻辑关联也许是确定的,但到底哪些立法规范与当前案件具有更为充分的逻辑关联却始终是不确定的;最后,尽管前文并未专门展开论述但显而易见的是,就某些本身包含有裁量幅度的规范而言,到底应择取该幅度范围内的哪一个节点作为最终标准也是不确定的。但尽管法官必须面对如上种种不确定因素,他作出的所有判决结论又注定只能是确定的——正是这两大方面决定了法官工作或司法决策的实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寻求确定的结论,而达致这种确定性的途径则只可能在于法官的自由裁断。
从理论方面看,本文的分析及结论在如下几个方面或许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第一,正如本文导言所已经指出的,本文尝试着超越既有的“司法有时存在着自由裁断”这一判断,而提出并试图通过前文的分析尝试着证立“司法的本质属性在于自由裁断”。①应该说,在西方或至少在英美世界,“司法有时充盈着自由裁断”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共识(详可参见[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7等页;[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35页;[美]阿德里安·沃缪勒:《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六章“法官、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等),而就国内而言,则大概只有部分法理学学者以及很少一部分部门法学者开始接受这种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断。换言之,如果本文仅仅以提出并证成该判断为目的,则不过是对既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已。通过这种证立,第二,提出了一种可能更加具有解释力的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按照既有的经典司法过程理论,法官在典型案件中是不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只有在非典型案例中,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才有必要“启动”。②这几乎可见于目前所有关于司法能动性之讨论的文献,典型者如张榕:《司法能动性何以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基础》,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周汉华:《论建立独立、开放与能动的司法制度》,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B. Schwartz,A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76;[美]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Kermit Roosevelt III,The Myth of Judicial Activ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2-21;等等。按照这种理论,逻辑上的结论就只能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实际上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面对典型案件时他只需要“严格依法判案”就可,而面对非典型案件时则必须适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造法判案”;而按照本文的分析,则法官无论面对何种案件,其实都必得仰赖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即必得通过自由裁断方可能达致确定性的结论。笔者之所以认定本文的分析更具有解释力,一则因为正如前述,典型案例与非典型案例之间本无截然的界限;二则因为本文的结论不仅仅对于非典型案件的裁决过程具有解释力,对于典型案件的裁决亦具有同样的解释力:在典型案件的裁决过程中,法官通过自由裁断得出的结论正好与大部分人的预期一致因而其自由裁断属性看起来不甚明显;三则也因为按照本文的分析,法官并不需要在面对不同案件时扮演多少具有“人格分裂”属性的两种不同角色。
关联着如上理论尝试,其次,本文对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可能启示则在于:第一,我们关于司法制度设计的指导精神大概有必要作出适当的调整。从我国目前相关的制度安排来看,诉讼过程中似乎仍以追求“客观事实”、“准确判决”为圭臬,这可以从前文引言中已经提及的“正确”、“准确”、“属实”、“清楚”、“确实”、“充分”等词语被广泛使用来表述诉讼法或各种证据规则现象中看出。而本文的分析则表明,司法过程实际上充盈着法官的主观能动和自由裁断,因此,也许相关的制度设计应该以“合理性”、“可接受性”等更弱但也更为务实的标准来进行。颇令人欣慰的是,在最近一次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于第53条规定了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容;但令人遗憾的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反映前述追求的措辞和规范,而这些措辞或规范一方面当然与“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具有内在的冲突,更重要的也许是,它们根本上仍然建立在与本文相左的司法过程认识论基础上。与此同时,第二,正因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司法的自由裁断本性,并建议以“合理性”、“可接受性”等相对较弱的标准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完善诉讼制度时应当加大法官的说理义务,从而通过说理这一柔性机制来既回应司法的自由裁断本性,也反过来限制法官滥用其自由裁断;同时,当然也应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上诉等刚性制度,进而为法官的自由裁断带上一个看得见的“紧箍咒”。第三,也只有明确了司法的自由裁断本性,我们才能更为冷静地看待、解释如下问题/现象:为什么特定的司法形式(包装)对于司法权威是必要的?为什么有些案件存在多种具有几乎同样程度可接受性的法律之下的结论?或者,为什么一个好律师对于当事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相对应地,为什么法官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以及为什么电脑程序判案不可能?为什么充分的庭审论辩对于司法结论的得出是必要的步骤?为什么还要尽可能地完善各种诉讼监督程序?为什么法官应当是德沃金所谓的赫尔克勒斯(Hercules)式的人物?为什么并非所有的被上诉审推翻或改判的案件之主审法官都应当承担“错判”或“误判”责任①遗憾的是,当前司法系统推行的错案责任倒查机制似乎并没考虑到这一点,而倾向于只要改判就可能导致错案责任的追加。笔者以为,追究前审法官错案责任的条件不应仅限于后审法官得出了不同、甚或相反的结论本身(按照本文逻辑,这很正常,甚至可以说这才是常态),更应注重的其实应该是对前审法官主观恶意的认定(如明显违反程序办案等)。?最后,笔者相信,本文的分析及结论至少有助于引起人们对司法过程本身事实上是怎样的予以更多的关注,从而为设计更好的司法制度或改善司法决策的过程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本文或许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于法治的美好期待,但正如弗兰克所言:“消除司法体制中那些可以消除的缺陷的最好方式,就是使我们的全体公民被告知司法体制现在是如何运作的”,换言之,“试图通过愚民政策来树立和维持公众对法院的尊重是错误的”。②[美]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赵承寿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责任编辑:许小亮)
Seeking Certainty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y:On the Discretion Essence of Judicature
Zhou Yun
To some degree,legal analytic positivism has sho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tion in justice and uncertainty in law,while legal realism has found out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fact in justice could lead to the judicial discretion. However,it seems that the uncertainty and discretion in justice is just an incidental substance of judicature for both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 fact,all important parts of judicature,includ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law,the fa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norm and case fact,are only able to be done by discretion. That is,judicature is full of discretion and the latter is just the essence of the former.
Judicature;Practical Wisdom;Discretion;Uncertainty;Certainty
D90
A
2095-7076(2017)01-0044-12
10.19563/j.cnki.sdfx.2017.01.004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司法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得到了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错案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FJ2015B108)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