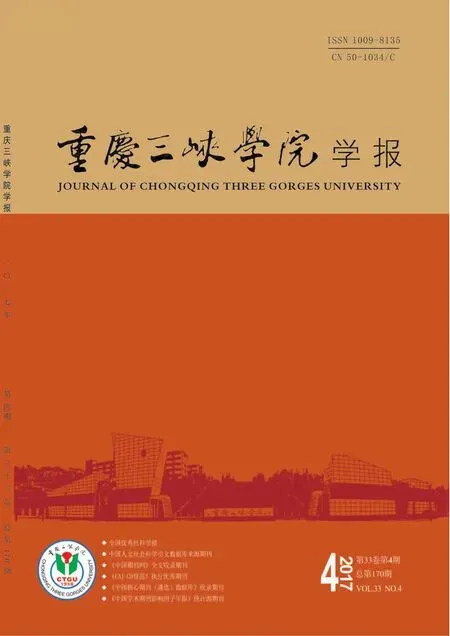老子的言道观与体道观
2017-03-29姚海涛
姚海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青岛 266106)
(青岛康成书院文化研究中心,山东青岛 266106)
老子的言道观与体道观
姚海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青岛 266106)
(青岛康成书院文化研究中心,山东青岛 266106)
老子认为日常语言无法对“道”进行言说。这是由道的先在性与语言的局限性共同决定的。一方面,道之于万物的存在具有逻辑先在性与时间先在性。另一方面,语言作为具体生存际遇之物无法通达形上畛域。这与春秋时代的人文背景与老子的史官经历都有直接的关联性。有鉴于此,老子另辟蹊径,提出体道的根本方法是负的方法,体道之工夫是损的工夫与复的工夫。
道;道本无言;体道
“道”字不见于甲骨文,出现于金文中,原始意义为“道路”。老子将之抽象改造、理论超拔为一个绝对超越性的存在,从而使“道”涵具了本体论以及宇宙发生论的双重意义。老子从逻辑先在与时间先在的角度对“道”的含义进行了革命式改造,所以老子之“道”关于本体的界定与言说也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及特色。
一、道的先在性与语言的局限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53《道德经》首章开宗明义地指出“道”的特殊性,认为日常语言所表达的“道”与“名”并非“常道”“常名”。老子强调“常道”根本不在日常语言论域,为道家哲学体系的整体建构确立起了思想基调。
老子何以会有如此违反常识的论点?《韩非子·解老》解释说,“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惜不衰者谓常。”[2]148所谓“常”即指绝对的超越性,其与天地共生共存。“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道也。”[2]148“常道”之所以不可道,因其超越现实、超越名言是以“不可道”。何谓“常道”?老子解释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1]114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居于本体位置的“道”是渺渺茫茫、无以名状,根本不同于现实中任何具体存在物。它是没有确定形状的形状,不可归结于具体存在的显象,即使人随其左右,永远也无法看到它的模样。总之,这个混沌玄妙之道作为一个人类居于其中的世界最终母体,之于我们而言具有逻辑的先在性——绝对的无从面对、无从言说的超越性。
不仅如此,老子还认为“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1]75,指出“道”在天帝之前就已存在,比所有具体存在物都幽深、久远。这进一步从时间先在角度肯定了“道”的绝对性质。“道”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是“无”。正因为其本“无”,“道”才具有无限的容纳性与创造性,也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之本体。
也正因为“道”本“无”,人类语言在言说“道”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语言都是在具体的生存际遇中形成,它所能表达的也必然限制在具体生活之域,一旦进入形上学之“无”论域,语言就理屈辞穷、苍白无力。正如《管子·内业》中所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3]271老子之“道”是无色、无声、无形、无光、无体、无味,而又不占时间、空间,也可以说“道”并非物质形态,而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的“惚恍”。它远离现实世界,语言根本不可摹状,经验感觉无法把握。这样就阻塞了“道”在感性基础上认知的可能性。同时,道作为“不可致诘”的存在,只能强名之为“道”,具有无上的整体性、超验性与先在性。“道”已超越语言论域,进入了不可言说的形上论域。这样,老子就合理地得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结论。王弼对此的解释更为直观,“名义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4]65以语言来论“道”,实质只能得道之一偏、一隅,实质不过是对于“道”的毁坏罢了,都是割裂了道所具有的完美性、整体性。
二、道本无言的时代背景与老子的个人经历
老子道不可言说的结论虽然有些惊世骇俗,但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或臆想。其所要表达者乃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总结与思想提炼。
老子所处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礼崩乐坏、学问下行、人心思变,各种思想正处于无序萌发、混乱碰撞状态。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出了问题,道家一眼看到把我们的生命落在虚伪造作上是个最大的不自在,人天天疲于奔命,疲于虚伪形式的空架子之中。”[5]87在老子看来,这是因为“名”被滥用以至于远离本真存在,否则老子不会说出“美言可以市尊”[1]303。他所要表达的正是对于这种所谓“美言”的痛斥。面对这些语言“异化”现象,老子深有感触,所以老子才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134。那些为人所吹捧的“仁义”“智慧”都不过是对大道的违背,都远远偏离了真正的“道”之本旨,故不足取。此类语言异化只能使“大道”沦丧,人心败坏,这就是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212。更有甚者,还有所谓“先物行,先理动”的“前识”,“无缘而妄意度”[2]134,造成混乱。老子认为这只是“道之华,而愚之始”[1]212,强调只有“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1]212,排除这种浮华现象而取用敦厚质实才能回归“大道”。韩非在《解老》中举出了詹何猜黑牛白在其角的例子,指出“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2]134。
面对思想界的这种混乱,老子发出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61,“多言数穷”[1]78的感慨。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老子作出了“知者不言,言者不知”[1]280的著名论断。老子发现了语言的局限性及其滥用的后果,其时的语言早已沉沦为无缘而妄意度的想象,开始了其异化过程。那些所谓的善恶、是非观念对于这个永恒的道来说是不具有真正价值的,反而是有害而无益。所以他才主张以超然之心来体道以超越这些语言异化现象。
老子道本无言的结论与其个人经历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的职业是周史官似确定无疑。而史官是古代星历占卜之术的执掌者。其对于天之本质与星相之运行,也就是宇宙之学有深刻的体验。同时,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其对社会变迁、历史演变有着深刻体察。所以史官有可能从宇宙、社会的具体观察中领悟出隐秘于天地、人事之中而不彰之“道”。通过对宇宙之道的体验而追求世道、人道的统一原则,使老子更清楚地了解纷繁芜杂语言之于“道”的遮蔽,排除具体现象而直接见“道”,从社会历史、宇宙本体的角度来体验“道”之永恒性。
于是老子担当了“正名”之重任,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语言的局限性与道之本体间存在永恒的矛盾。语言的最大弊病就是挂一漏万式的“遮蔽”。对于绝对性的存在之道而言,说明的越多就意味着丧失的越多。道的无限性和语言的有穷性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因为语言根本无法承载“道”,所以,老子所主张的就是“行不言之教”[1]64。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开辟了一个本体与语言关系新范式。老子“道”之不可言说乃是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突兀的存在。也正基于此,老子阐发的这一重要思想才有发展的土壤,得以发扬光大。老子的这一著名论断虽然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但是却具有绝对的普遍意义,由于它阐述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所以成为后期各家所竞相阐发的对象,也为道家哲学赋予了独特的生命力。这一论断包括对于普通的具体知识的针砭,但是更多地蕴含的是对真正智慧的希求。
三、体道的根本方法:负的方法
《老子》认为本体不可言说,那么实际上他又在不断言说。从一开始他便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并力图加以解释,他对此的态度就是“强为之名”,目的是给后学指明修学路径。正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1]114。“知古始”即是要懂得返本复初以保有初始的能动。只要能懂得返本复初,也就抓住了维系于道的基本点。也就是说既然不能站在具体存在的角度面对道,那就只能转回身靠近道、体念道、回归道。
道作为最高的原则,必定是隐蔽而不彰显,而不可能显现于普通事物的表面。虽然不离万物但是不可直接说出来,“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是不可以用平常的方法来言说的,因此只能采取曲线之方法。这里所言说之“本体”绝对不可以与本体本身划等号,而只是作为我们接近本体的一个不得已的途径而已。必须有所言,否则“道”也就无从表达,但是这种表达不可以正面、直接的方法,而只能是通过否定和间接的方法。如说“道”不是什么,进而领悟道的存在,达到至高境界,也就是利用一层一层剥落式的“负的方法”,或曰由否定入肯定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即使老子直接论道的语言也都是模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借喻而论道。老子论述“道”是“无名”“无形”“无状”“无象”“无物”“无为”等都是通过一步步地否定,一步步地剥落“道”的有限性,以最终达到“道”的普遍性和无限性,从而进入深奥玄妙的本体。老子正是通过这个方法,使“道”的本质不断地暴露出来。他依靠的就是不断否定“道”的具体内容,从而提升“道”的层次,反而为“道”注入了无限之品行,当然这种无限之品性还是需要人去体认。
老子虽然把“道”的本质定为“无”,但其并非是绝对的虚无,而是有其功用的无。“有”是最为真实的实有,是不言不行却无时不在运行,是万物始之无形、成之有形、入之无形的最终法则和根据。它是“先天地生”,是万物之主宰,是“众妙之门”,有其“有体而致用”的现实一面,不是离我们很远的另一时空的存在,而是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中普遍起作用,万物所共遵守者。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63。这就为论道打开了方便之门,人们虽不可直接言“道”,但却可以体道。
在《老子》中体、用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本体虽不可言说,但“用”却可以说,“用”总是“体”之用,故通过对“用”之言说,就可以接近体。理念上的“道”用语言无法描述,但可以从“道”化生万有的作用来体会到它的存在之真实不虚。“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1]157狂风刮不了一清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而人更是如此。老子认为作为域中之“四大”的天、地、人所法的都是至上的“道”,因此这三者的表现都是道体所致,而这三者都是“不能久”者。世事变化无常,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他们所遵循的就是自然无为之法则。人立身处世,就要以自然为法,而不可以用人力强求,这样就可以从天、地、人上升到“道”。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令之而自均。”[1]194万物所遵守的都是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天下莫能臣”的“道”更是如此,处于质朴之状态,这里从万物无为自化的境界中讲述“道”的存在的。老子对道的论述是从道的功用入手,讲道法自然是强调万物“自宾”“自化”,剩下的就是靠我们自己去领悟了。老子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开道的论述,让人们通过“道”的功用来略窥“道”的本体,这全是从万物自在无为的状态来明示道的存在的,但我们切不可停留或逐于物象而得“道”。
四、体道工夫:损、复
既然人的感官无法触及“无形”之“体”,也无法明了“无象”之“道”,那么老子就另辟蹊径,开拓了全新的“体道”方法。“道”是以自然无为为根本特征的,体“道”就要做到同于道。老子提出“涤除玄鉴”,就是要求保持思想的明澈、纯净,保持内心之空灵状态,这样才可不被外物所扰,从而超越“有形”之外物的限制而达于“无形”之“道”。老子认为道本无言,那些言道之言都不过是对“道”的偏见,要想体“道”就必须排除这些小识,排除日常之见解,这也就是“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1]265。老子对此提出的具体原则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250“道”本不属于知识之范围,它作为超越时空的绝对本体,遵循的只是“自然”的法则,人要达于“道”,就必须“自然无为”,排除一切人为的东西。而知识是人为的产物,知识愈多也就愈会违法“自然”的本性,因而离“道”也就愈远,即所谓“智慧出,有大伪”。因此“为道”与“为学”恰好相反,不断地将具体的知识“损之又损”以至剔除殆尽,一层层地摒弃经验之知、闻见之识,一步步地否定具体知识所固有的有限性、虚假性,不让具体之学障蔽“道”体,最后使认知在高度纯净、毫无芥蒂的状态中得到升华和飞跃,上升到“无形”之本体,豁然将整体之“道”把握,达到“大智”的境界。这种通过否定世俗小智来达到道体之大智的方法正反映了老子的独特思维方式。
要达到与“道”同体,老子认为不仅要排除一切人为的知识,还要排除违反自然本性的那些道德伦理规范,“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1]134,仁义、智慧等等也是人为的东西,也同样违反了自然之法则,也使人们远离了“道”,因此体道之内容也必然包括了否定了这些道德规范,也就是“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136。老子在这里并没有结束,进一步需要否定的是人的欲望。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106。对于物欲的过分贪求都是对于自然本性的戕害,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逐与外物而不自知,与“道”渐行渐远。所以必须排除这些物欲,返回“朴素”,才能达到真之境界。总之,老子的“涤除玄览”就是要排除一切人为,使人们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状态,才不会为偏见所伤。老子有如此的认识根本上都是源于时代之感受,人们对于感官和外物的不断追逐,使人们丧失了“明智”而不自知,远离了人本然状态而不知悔改,沉迷于名利而不能明了人的生存本质和精神自由。
经过上述的一系列的否定,排除了一切杂念,扫清了玄妙之心上的尘垢,做到“常无,欲以观其妙”[1]53,回归大道,达到“虚心”之境界。这里的虚心并非是真的虚而无有,而是使心灵达到虚灵不昧的境界,使心灵免受那些“学”的遮蔽,追求与“道”同体。这种减损工夫,损的是后天人为,回归的是自然本性。其并非一日之功,要终生勤而行之,损到无可再损,则先天道性全体呈露。
除了“损”的工夫外,老子还提出了“复”的观念,所谓“归根曰静,是谓复命”[1]124,“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1]124。这是对直觉的体道方法作了说明,所要“复”的本命,就是要返还到先天、父母未生时的本来面目,这里的根本要求就要保持虚静、无为之境界,把“静”作为一切的主导者。指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1]248,进一步区别了“道”与“学”的不同维度,提出证道可以通过某种闭门静修或禅证契会的方式达成,所注重的正是静观。做到虚静就可以回到本初状态,那就是与“道”一体的状态,不受外物所扰,而直接从整体上一下子把握“道”的存在,从“道”来关照万物就会无所不通。静修不可能增加有关世界的具体知识,但却可以有效地摆脱习惯固着的存在经验而增加人的智慧,使人们体会出原本与道同一的状态。因为外在的琐碎知识会扰乱对“道”整体存在的把捉。只有体验到了“道”之“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样的知才能算作真知,才算“大智”。这显然是一种认识论的彻底转向,也提出了直接领悟“道”的可能性,也就是“万物静观皆自得”,所观的是万物的本真状态。
“损”和“复”的方法是破除人为障蔽、恢复自然大道相辅相成的两种方法。“损”乃损人为,“复”乃复自然,后天人性减损一分,先天道性就显露一分。当后天人为障蔽减损殆尽,就与大道合真,最终回归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这是是对人存在状态的终极人文关切,达到这一境界才是“道”的真义所在。
无论是“损”还是“复”,老子体道观都不曾远离“道可道,非常道”的本言。正因为其不可道,我们才需要“体”。而“体”也不可拘泥于具体之言之物。老子的体道观绝非让人们毫无作为的冥想,不能只停留在学问上,必须脚踏实地地去修炼。“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1]203,道用语言讲出来,淡而无味,根本也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就是要努力不懈的实行,决不间断,把自己调整到虚静至极的自然状态,最终契得“忘言”之意。
老子的体道观绝非神秘主义认识论,他也没有人为设定一个绝对的存在,因此体道就要从虚处立脚以察万物之自然情态,“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1]194。从万物入手,悟道也要从这些自然状态中来领悟道,从天道推及人道、世道,进而领悟最终统一之大道,也就是“复命”了。
五、结 语
老子体道观所要表达的是对日常语言的否定和对语言沉沦现象的痛惜,更是对大“道”的赞扬。当要表达“道”时,自然就会产生言与不可言之间的矛盾。老子开启了全新的方式来论述“道”的存在,否定了识“道”的可能,却提出了体“道”的观念,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学说架构。体“道”根本上不是认识“道”,只是体悟而已,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里显示了道家哲学对于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不同的认知,它没有局限于有形的事物,而是以敏锐的直觉达到了无限,达到了最高的智慧。悲愤出诗人,乱世见思想[6]1。老子道论是时代文化背景的缩影,是当时哲学思想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总结和概括。其通过宇宙之道的体验,对直觉和体悟的重视,达成对于天道、人道的终极理解。所以老子体道观有大用。其不仅是人类认识论的演进,更是生命境界的升华,也表达出了老子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老子留下五千言的真意。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李山.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李朝平)
Laozi’s Views on Using Language to Express and Experience Tao
YAO Haitao
(Qin dao college,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106, China)
( Qingdao Zheng kang-cheng Colleg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Qingdao, Shandong 266106, China)
Lao Zi thinks that daily language is not capable of expressing “Tao”. This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o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anguage. On the one hand, Tao’s existence is logicall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first in time, earlier than other things in the universe. On the other hand, language as a concrete living tool cannot reach the realm of metaphysics. Thi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Laozi’s professional historian experience. In view of this, Lao zi took a different approach and put forward that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experiencing Tao was negative. To experience Tao is to lose and then to repair.
Tao; Tao is beyond the words; to experience Tao
B223.1
A
1009-8135(2017)04-0124-05
2017-05-11
姚海涛(1981—),男,山东高密人,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先秦哲学。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齐鲁文化合流中荀子的关键作用研究”(1607293);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理工类独立学院人文通识教育模式研究”(2016001A)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