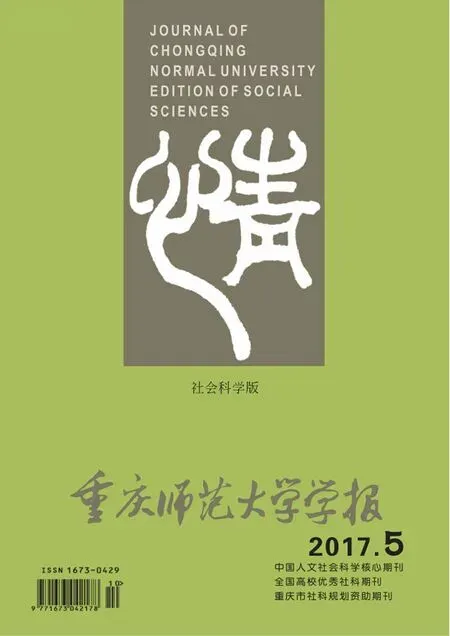《新华日报》1940年有关冰心的两则报道绎读
2017-03-29熊飞宇
熊 飞 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2017-07-14
熊飞宇(1974-),男,四川省南江县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战文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批准号:16ZDA19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抗战文学”(13XJC751001)。
《新华日报》1940年有关冰心的两则报道绎读
熊 飞 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1940年的《新华日报》有关冰心的报道,主要有《妇指委会局部改组》以及《全国文协茶会欢迎来渝作家》。通过文献的援引与参证,既可还原历史的现场,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将获得较为清晰的呈现。两则报道,为重庆时期冰心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新华日报》;冰心;1940年
1940年的《新华日报》,曾有两则关于冰心的报道,对于冰心研究非常重要,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现略作考述。
一、《妇指委会局部改组:谢冰心胡惇五分任组长,增设妇女文化事业委会》
(中央社讯)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组组长与儿童保育会总干事,原由指导会副总干事陈纪彝兼任,兹陈以指导会工作日繁,不暇兼理保育事宜,已辞去兼职,闻该组组长与该会总干事,改由胡惇五女士继任,又指导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现聘定谢冰心女士担任,并设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由指导长蒋夫人兼任主任委员,谢女士兼任秘书,胡谢两女士不日可到会视事。
该报道见于《新华日报》1940年10月7日第二版,消息则来自“中央社”。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七日 中央日报 星期一 第三版”亦有《妇女指导会局部改组》,内容相同,文字小异,主要是称呼语上的省略,如“谢冰心女士”作“谢冰心”,“胡谢两女士”作“胡谢”。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妇指委会”是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报道带出的问题在于:事前经过了怎样的协商,方才达成对冰心的这项任命?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其来龙去脉,都未能探晓。随着冰心佚文《我所见到的蒋夫人》的发现,有关过程,才开始明朗:“一九四○年秋天,我突然收到重庆友人的来信。信上写道,他与蒋介石见了面,在和蒋夫人的谈话中,蒋夫人说她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现在需要一名文化事业部部长。当我朋友和蒋夫人提到我的名字时,夫人十分高兴,希望我能坐飞机到重庆和她见面。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离开昆明,也不知道这个工作的性质。”[1]103“正巧吴文藻因为学术会议也要去重庆,我们就迟迟地出发了。”[1]103到达重庆后,“蒋夫人派自己的秘书钱用和女士来接我们。这天晚上,我们在重庆的朋友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钱女士来接我们,然后和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总干事、部长等人同行来到了郊外蒋夫人的官邸”[1]103。两人“握手后对面而坐”,交谈中,“夫人希望我也能参加她主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且劝我来重庆和她一起工作一个月”[1]104。“我和蒋夫人以及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吃了午饭”[1]105。“因为下午有约,所以我先告辞了。对于夫人的规劝,我表示考虑之后再做答复。三天后,因为夫人派人来询问结果,所以我再次去了黄山”[1]105。“我说了一些实际问题”,“夫人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表示“交通问题再多也能为你解决”,“你的工作是一时的还是怎样我们以后商量”[1]105。“这天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他们俩和文藻也约好让我们俩去黄山。第三次是我与文藻同行,和蒋委员长夫妇还有二三位友人共进午餐。我们从昆明搬至重庆的搬家计划在那天决定了”[1]106。
在此过程中,《新华日报》有过相当频密的报道。宋青红在其博士论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以下简称“宋文”)中,曾做详细的梳理。1940年9月26日,《新华日报》第二版的“简讯”第八条,即“女作家谢冰心近自昆明来渝,将就妇指委会文化事业组组长”。次日,第二版的“简讯”之七,亦为同条报道。10月5日,《新华日报》第二版的“简讯”,其四为“谢冰心有缓就妇指委会文化事业组组长说”。[2]98上述报道,可与冰心的自述互为参证。
事件的进展,还可见于后续的相关报道。
《广东妇女》第2卷第6期的“妇女动态”,其中云:“女作家谢冰心女士于十一月廿二日左右抵渝,据云谒见蒋夫人后即将就任新运妇女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妇女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3]60据此可知:冰心一家迁居重庆的时间是1940年11月22日左右。
摘 要: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教育改革的要求,不断提高县域内“送培下乡”培训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座谈、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方式回顾了近年来县域内“送培下乡”的培训情况,希望通过查找问题走出困境,思考信息化背景下县域内“送培下乡”培训活动的举措。
《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6日第二版,有“本报讯”《女作家谢冰□来渝就新》(按:宋文第98页的注释,该报道的标题作《女作家谢冰心来渝就新运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新职》,不知缘何衍出这许多文字):“新运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妇女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女作家谢冰心女士已于日前抵渝,日内将谒见蒋夫人,然后即将视事。”题中“谢冰心”之“心”字,已成墨团,故以“□”代替。
《妇女新运》周刊第83号(《中央日报》1940年12月2日第四版),有《本会消息》,其第五条:“文化事业组组长谢冰心女士,于上月二十六日首次到会,不日即将正式到会领导该组工作。”由此可进一步确知:冰心到会的时间是1940年11月26日。需要注意的是,同日《新华日报》的报道,只是对冰心行程安排的介绍,尚无可能言及当日冰心到会一事。
上述报道将冰心称为“妇女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则存有疑问。按前引中央社的消息,所设机构名为“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宋美龄,谢冰心兼任秘书。《妇女新运通讯》第3、4期合刊(1941年2月出版),对十五位女参政员之十三的谢冰心也有这般介绍:“福建人,现年四十一岁。亦毕业于美国厄士莱大学(引者按:即Wellesley College,现译作‘韦尔斯利学院’、‘威尔斯利学院’等),与蒋夫人前后同学。早岁以女作家名于世。现任全国妇女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4]5而“全国妇女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应即“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秘书”。至于“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暂未找到详细的介绍。
“一九四○年十一月廿七至廿九日”的《新民报》,曾发表“熙”(即浦熙修)的【本报特写:访问谢冰心】,提供了不少相关信息,兹全文引述如下:
谢冰(心)女士,虽然中年的人了,但温婉得其人恰如其文,一口南方音的北平话,清脆、悦耳。这次应蒋夫人之邀,来渝主持全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事及任妇指委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当记者前往拜访时,她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先出来招待着,“冰心身体不大好,下午是常常要休息一刻的。”
果然刚刚一刻钟,冰心女士出来了,穿着蓝布旗袍,平底黄皮鞋,潇洒得带点大学生风度,但清癯,消瘦,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们从云南的情况,谈到她抗战前在各地漫游的经过,及抗战以来,中国的进步;又从妇女职业问题的意见谈到关于文化事业委员会的计划。
“我今天已去妇指委会文化事业组看了一遍,原来的工作都做得很好,我仅仅答应蒋夫人三个月,无所谓是组长,在这过渡期间帮帮忙。”
“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全国性的,但这要等蒋夫人回来才能谈到工作计划,同时我也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与反响。”
“但谢先生总有个成竹在胸呢”,记者紧逼着问。“这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譬如第一步调查与登记工作,调查全国的女学生所学习的科目,女文学家,女艺术家,女科学家分布的情形如何,并且提倡各学校单为女子而设奖学金等,男女所学的科目是不应完全相同的。
“譬如编辑些妇女与儿童的丛书之类,但这些都是最初步的工作。”
她在这里又强调,她决不呆板地坐办公桌的,有计划有问题,可随时商酌着办理。
“抗战真是好,暴露了一切,在云南看见一些同事的太太们,以前好像显着能干的,但现在吃不了苦,要回上海去;平常看着不能干的,但真能吃苦,下河洗衣服,倒马桶,把家庭处置得井井有条。等警报来时吧,在昆明,城里的都跑到乡下去,有的太太们在小小的一间房子吧,招呼着自己的孩子,还和颜悦色地招呼着一大屋子客人,她不抱怨,她不烦恼,这就是尽了抗战的责任啊!”
“我已是中年的人了,毫没有意气也不想出风头,只求脚踏实地的做点工作。理论唱得多高,于实际是毫无补的,譬如女学生吧,我认为要添习家事科,常常一个大学生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不但女子,就是男子也该学家事,他到没办法时,不是也要自己做饭吗?”
“职业与家务不能兼顾时,那要看当时的情景,那方面重要,就顾那方面。托儿所是需要的,但托儿事业,不是家事的一种吗,所谓学习家事,是家事要科学化,怎样以最小的劳力得最大的效果。
“我在抗战前三年漫游世界各国,就是抗战的那一年六月间才从苏联回北平。”
“现在写游记吗,一些材料都还在昆明,在这时候写以前的事,于环境也不适合,并且有了孩子的母亲,再不能有秩序地写,恐怕以后也只能写写应时的杂文之类。”吴文藻先生在旁答道。
“在这里住多久吗,抗战一了,我是要回北平去的,要回去的时候,我就要回去,我喜欢北平。”
在夜色的笼罩中,记者告辞回去,这温柔清脆的北平话,也使我深深地追忆着北平,我们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回去了吧。[5]62-63
从上文可知,1940年11月26日上午,冰心首次到新运妇指会了解情况。下午至傍晚,又接受了浦熙修的采访。
冰心到重庆,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学者们曾持有歧见。现在可以明确,冰心的重庆之行应是两次,且“第一次是面谈,第二次才是搬家”[6]95-96。从《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来看,时间是“一九四○年秋天”,而任命的消息,则是在10月7日正式发布。结合《新华日报》的报道,冰心第一次到重庆的时间,可大致圈定在九月底十月初。第二次是在十一月下旬。这次搬家,就冰心而言,是为了在“过渡期间帮帮忙”,暂时出任新运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组长以及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秘书;在吴文藻方面,则是:“1940年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了干扰,不能继续,那时有在重庆工作的许多清华同学,动员我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我们就搬到重庆去了。”[7]50
最后,夏蓉在《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离合”》中谈到:1940年10月6日,宋美龄赴港医病。而在第二天,“中共方面立即披露了妇指会改组的消息,颇耐人寻味”[8]139。这一说法,有过度阐释的嫌疑。论者忘记了《新华日报》的报道,是据“中央社讯”;同时也未注意到,同日《中央日报》亦有相关报道。
二、《全国文协茶会欢迎来渝作家,茅盾巴金冰心等均莅会》
(本报讯)全国文协昨日下午三时假中法比瑞文化协会茶会举行欢迎新自各地来渝作家茅盾、巴金、谢冰心、安娥、徐迟、袁水拍、马耳、柳倩等。到老舍、郭沫若、吴文藻、田汉、张西曼、冯乃超、阳翰笙、靳以、白薇、葛一虹、向林冰、姚蓬子、华林、王平陵、黄芝岗、常任侠、光未然、以群、艾青、马宗融、潘梓年、戈宝权等七十余人,周恩来同志亦莅临参加。盛会并无仪式,但空气[至]为融洽热烈。老舍先生致介绍词[后],冰心等均[相]继答谢,并一致谓在抗日旗帜下,全国作家[理当携手]并进,为抗战胜利而奋斗,□□□□,□为兴奋。
该报道见于《新华日报》1940年12月8日第三版。所谓“全国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关于这次欢迎会,后来者却有不同的叙述。陈恕的《冰心全传》是:1940年12月7日,由老舍主持的“文协”在中法比瑞同学会举办茶话会,欢迎近期从外地来重庆的会员茅盾、巴金、冰心、徐迟等人。郭沫若、田汉、阳翰笙、洪深、艾青、冯乃超等一百多人出席这次活动。[9]202
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的记载是:12月7日,“‘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会举行茶话会,欢迎茅盾、冰心、巴金等来渝作家。到会者有周恩来、郭沫若、老舍、吴文藻、田汉、张西曼、冯乃超等七十余人。大家互相恳谈,表示要为抗战胜利而奋斗”[10]163。
两说在人数上有较大的差距,而文天行的记载则与《新华日报》的报道相近,应该更为可取。三者所列举的参会人员,实可相互补充。至于茶会举行的地点,虽云“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但并不具体。笔者在《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中,借助《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会刊》,将其考定为“重庆上石板街42号”[11]89。
冰心在这次欢迎茶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对于这次见面,1976年12月22日,冰心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有过追忆。1991年,她在《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再次谈到会面的情形。两者的文字大同小异。后来,时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新华日报》记者、《群众》杂志编辑的张颖,在《他心中装着多少人——周恩来与冰心、常书鸿》一文中,以见证人的身份,从另一角度对会面的情形做了补充:
1941年四五月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欢迎外地作家到重庆的欢迎会,主要是欢迎冰心、巴金、沙汀等,地点就在全国文协所在地。那天上午,周恩来刚起床即询问我,是否全国文协要开个欢迎会,并说他准备和我一起去参加。这种事我一点不觉得奇怪,我只是说,去全国文协汽车不能直达,要走一段长长的台阶。我是怕有特务跟踪。他却毫不在意地点点头。吃过午饭,他带着副官和我去了。下了汽车,走过长长的台阶,临近文协门口时,我快走几步,好去通知老舍和叶以群。我走进那间小小的会议室,见到已经坐满了人,来不及细看就把以群叫出来,告诉他恩来同志来了。他说了句,真的来了!转身就进去告诉大家。这时,周恩来已进入会议室。在座的许多人,如阳翰笙、陈白尘、郑君里、史东山等都是老熟人,立刻欢呼地站起来,周恩来笑着和大家握手,随即快步走到冰心身旁。她是一位眉目清秀、端庄娴雅的女性,我是第一次见到她,虽然身材矮小些,瘦瘦的身躯挺直。她面对着周恩来,瞪着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甚至周恩来伸出右手,她都没有注意到,还是旁边一位朋友为她介绍了,才有点吃惊地和他紧紧握手。周恩来朗朗笑道: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呀。那次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室外的阴霾和愁云,新老朋友聚在一起,无拘无束,还请周恩来讲了话。他除了对刚到重庆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外,着重谈了国内形势的逆转,又满怀信心地说到光明前途,为大家鼓劲。只要是有周恩来参加的聚会,大家都会尽欢而散。
不久,我又见到冰心,她谈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开心又抱歉地说,怎么能够这样没有礼貌呢,居然忘记握手了,我是见到陌生人,一时发呆。我说这也是常有的事,说不上没有礼貌。从此以后,她渐渐地和周恩来熟悉了,也成为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客人。[12]192
上述回忆,或是因为年代久远,时间与地点都与实情不符,至于具体情状的描摹,则可供参考。
从报道可知,常任侠曾与会,但其日记却着墨不多,仅记其事而已:“下午一时入城”,“参加欢迎茅盾、巴金、冰心等文艺界茶会,到者甚众,并摄影多张。晚间参加政治部招待盛会,到三百五十人,为空前之大会。孙科演说,对囤米资本家,颇多抨击。宴后游艺。夜深始散。”[13]290如此看来,是日不仅有“文协”的茶会,晚间还有政治部的招待会,但不知冰心等是否参加。
参会者还有阳翰笙。不过,由于《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所收其抗战时期的日记,起自1942年,故阳翰笙对此有何记叙,暂未可知。但冰心在1987年11月4日,作有《我的朋友阳翰笙》,曾回顾说:“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40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同一个小圆桌边上。”[14]98所谓“文艺团体的集会”,不知是否就是这次欢迎会?
茅盾也参加了这次茶会。检其晚年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并未提及。不过,1938年底,茅盾从香港去新疆,路经昆明,12月28日晚,出席文协云南分会的“洗尘”晚宴,见到朱自清、沈从文等朋友。29日上午参加文协分会的茶话会,下午是新老朋友来访。30日上午,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顾颉刚前来看望,晚上观话剧《黑地狱》。[15]22331日上午回拜顾颉刚,并由顾颉刚陪同拜访了朱自清;朱自清“又派人去请冰心、闻一多和吴晗,冰心不在家”[15]227,故失之交臂。
此外,据张彦林《锦心秀女赵清阁》,正是在这此茶话会上,冰心第一次见到赵清阁。[16]115但关于二人的初识,众说纷纭,此为其中一说。
后来,冰心与“文协”又有所交集。1941年3月15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三周年之际,“文协”通过信函选举的办法,选出在重庆的理事,冰心同老舍、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等25人当选。[9]203
1945年5月7日,“文协”于文艺节举行第七届年会,选出理监事。叶楚伧、冯玉祥、张道藩、柳亚子、潘梓年、张恨水、华林、谢冰心、黄芝冈(引者按:或作“岗”)九人为监事。陈望道、史东山、聂绀弩、张西曼四人为候补监事。[17]381-38210日,“文协”召开第一次理监事会议,张道藩、华林、黄芝冈为常务监事。[17]382
[1] 谢冰心.我所见到的蒋夫人[J].虞萍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6).
[2] 宋青红.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年)[D].上海:复旦大学,2012-05-10.
[3] 妇女动态:女作家谢冰心[J].广东妇女,1941,(6).
[4] 十五位女参政员介绍[J].妇女新运通讯,1941,(3/4).
[5] 袁冬林,袁士杰.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6] 王炳根.谢冰心与宋美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6).
[7]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J].晋阳学刊,1982,(6).
[8] 夏蓉.皖南事变前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离合”[J].学术研究,2016,(6).
[9] 陈恕.冰心全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10] 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11] 熊飞宇.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2] 章文晋,张颖.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补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3] 常任侠.战云纪事[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14] 冰心.冰心全集(第七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15]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 张彦林.锦心秀女赵清阁[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
[17] 龙红,廖科.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OntheTwoPiecesofReportaboutBingxininXinhuaDailyin1940
Xiong Feiyu
(Research Center of Sino-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ongqi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There were two main pieces of special reports about Bingxin published inXinhuaDailyin 1940. One wasTheLocalReorganizationofWomen'sAdvisoryCommitteeoftheGeneral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the other wasTheNationalAnti-JapaneseAssociationofWritersandArtistsHeldaTeaPartytoWelcometheWritersRecentlyCametoChongqing. Referred to other documents, the historical scene can be restored, and its context will also be more clearly presented. The two pieces of reports provide a valuable clue for the Bingxin study in her Chongqing period.
XinhuaDaily; Bingxin; in 1940
K265
A
1673—0429(2017)05—0026—05
[责任编辑:朱丕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