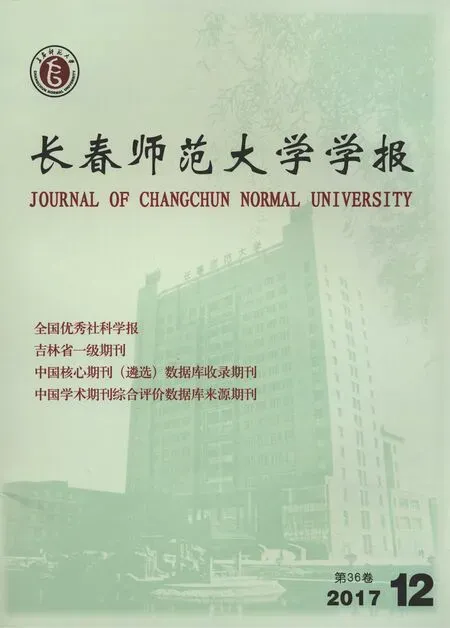论音乐社会学视角下我国民族音乐传承的价值与意义
2017-03-29胡东冶
胡东冶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辽宁沈阳 110818)
论音乐社会学视角下我国民族音乐传承的价值与意义
胡东冶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辽宁沈阳 110818)
音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以及无可替代的作用、价值和意义。音乐社会学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音乐与社会无论在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是有机结合、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音乐教育层面上的民族音乐教育,既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实用性的作用、价值和意义。
民族音乐;社会学;民族文化;文化传承;音乐教育
“音乐社会学(sociology of music)是以受到社会制约的诸种音乐现象、形态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社会与音乐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在社会学向专科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既是社会学也是音乐学的一个门类。这门科学目前仍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其研究方向及重点也各有不同的理解”[1]。
音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音乐社会学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任何种类、形式、类型、风格的音乐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每种音乐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社会背景、社会需要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音乐种类、类型和风格。同时,音乐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属性与特征,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属性特征以及不同阶层人群的思想、情感及精神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音乐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对各个社会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精神生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影响和引导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审美情趣、审美境界、审美趋向、思维习惯。可以说,音乐对于社会而言也同样具有引导或引领作用。
对于优秀的艺术家而言,其为人们创造出的优秀音乐作品绝不应该是低俗的或者是媚俗的,但也绝不能脱离人们最基本的社会生活状态。真正优秀的音乐艺术应该是“让听众跳起一点才能摘到的桃子”,这样的音乐艺术能够为人们带来真正艺术感官享受和艺术享受,能够真正使人们产生精神愉悦,能够为人们的精神、思想、情感带来真正提升和养分[2]。音乐与社会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类型、民族和国家,都是有机结合的、密不可分的,能够起到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据有效的文字记载,我国在几千年以前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王国与社会组织结构。早在商周时期,在当时的神州大地上就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农耕社会和农耕文明。这种社会形态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富足,在此基础上,相伴相生的各种社会劳动形式也开始蓬勃发展,手工业、商业等使人们的社会生产资料与社会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和丰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开始更加注重自身精神生活的质量。因此,在商周时期,我国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音乐教育制度与音乐等级制度。素有“青铜王朝”之称的商朝在金属冶炼和锻造技术方面的革命性进步、发展和成熟,为周朝礼乐的形成和乐器制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从周朝开始直至秦汉,编钟乐器和礼乐艺术成为当时上层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审美情趣,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生活水平等。
从秦朝开始,我国形成了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真正的大一统国家[3]。由此,“大一统”的概念、意识和理念开始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里根深蒂固。虽然此后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屡经王朝更迭,但我们的社会始终保持着延续性的统一状态,无论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自我朝代更替,还是由于外族入侵而形成的朝代更迭,我国始终在文化、精神、思想上保持着惊人的延续性、一致性和统一性。这也使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状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延续、一致和统一。这使得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文化延续千年而至今仍然得到较为完整的延续,并仍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而没有淹没在浩瀚的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以当前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例,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实质上指的是世界上四个文明发源地。之所以要在中国以外的三个国家前面加上一个“古”字,是因为当前除了我国以外,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不能完全代表文明古国,他们的文明都没有我国这样的延续性与一致性。四大文明古国或文明体系都在漫长的世界历史长河中拥有过自己的辉煌,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四种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真正经受住了历史的沉淀与考验,保证了自身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文化的延续、一致和传承最大限度地使人们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与依托感,这也间接地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反之,社会的稳定也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延续与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讲,包括艺术、音乐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与社会的关系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力的文明或文化,必然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稳定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一个社会的稳定也会最直接地保证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弘扬。
“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从音乐教育层面,社会学是我们必须着眼的角度”[4]。而由音乐教育所衍生出来的音乐教育学是一门具有更强实践性与应用性的音乐学科。其理论体系源自音乐实践教育活动,同时在形成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与架构以后,又能够反哺音乐教育实践活动。音乐教育学本质上就是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化形态,是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学术延伸与发展,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与发展也能够使其得到极大的充实与丰富。同时,音乐教育学术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能够对音乐教育实践活动起到极为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与音乐教育理论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有机融合的关系。没有了所谓的实践基础,那么一切学术理论研究都无异于纸上谈兵;而只有实践活动,不进行科学的、专业的、系统的、规范的、有组织的学术理论研究与归纳,那么实践活动也会非常容易偏离正确的方向和轨道。
由此可见,民族音乐,作为最能够体现民族特色、民族情感、民族思维的社会文化艺术,必然要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音乐教育层面上的民族音乐教育,既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实用性的价值。
[1]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
[2]白宁.燕南芝庵《唱论》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15-16.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55-65.
[4]钱仁康.中国音乐欣赏丛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154-156.
J60
A
2095-7602(2017)12-0179-02
2017-07-19
辽宁省级计划一般项目“中国民族音乐艺术新发展研究”(16BB056)。
胡东冶(1980- ),男,讲师,从事声乐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