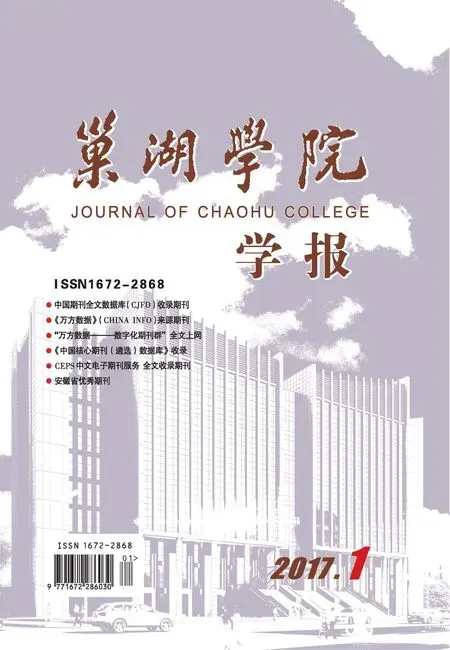中国古代物体系建构方式与赋体书写策略之生成刍议
2017-03-29任树民
任树民
(北华大学,吉林 吉林 132013)
中国古代物体系建构方式与赋体书写策略之生成刍议
任树民
(北华大学,吉林 吉林 132013)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需要从“物”的背景出发补充一个“物”的维度。中国古代的物体系建构联接着“天——人”两端,一方面基于可经验世界,以类相从,另一方面力图在“天人”架构下形塑成一个形而上的“类应”秩序。跃入先秦文史作品,这一“天人”架构下既连类又比类的物类呈现方式,已经形塑成了一个颇能建构的书写策略或曰作品生成方式。考索赋体的运思模式,先秦时期这一既连类又比类的物类呈现方式在塑成为一种书写策略后直接影响了赋体的体物书写。
物体系;建构方式;书写策略;赋体;体物传统
五四以来,受欧洲浪漫主义强调文学是思想情感表现理论的影响,“文学”的定义越来越突出情感主线。可以说,在中西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框架下建构的“中国抒情传统论”就是这一“文学”界域的自然延伸。然而,中国文学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外,还有一个“体物”传统。“体物”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最早由陆机拈出,针对的文类是赋。“赋体物”是中国文学体物传统的直接发生背景,那么“赋体物”的发生背景又是什么呢?本文拟从“物”的背景出发,探索一下赋体“体物”书写策略的发生背景和生成机制,以期为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提供一个“物”的维度。
1 中国古代物体系的建构方式
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是物也。物囊括了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一切存在。物世界不依赖人的感觉而存在,然而,物又被人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所以,物实际上又是人在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的一种经验和体验。当追问“是什么物”,进而得知“物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凭借的是什么?显然是经验或体验世界里的一种以类相从或以类相别意识。《礼记·月令》:“乃命宰祝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察物色”意思是说,宰和太祝巡视准备祭祀的牺牲时要察看牺牲的毛色。而透过色泽的差异,是要对“物”加以分别。“必比类”孔颖达疏:“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随曰类。 ”[1]这就是说,“必比类”,方能将物性区别出。反言之,区别出的“物”以类相从,物类体系才能得以建构。而这,也就使得“类”成为“物”的字义发展脉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义项:“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2]贾公彦疏曰:“六者皆有毛物不同”,亦即透过毛的色泽差异来分类。是故,文中六处“物”字皆可释为“类”。“物”一方面与“类”字在名词上意思相通,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动词性的用法。动词性的用法具有观察、分辨的意思。《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晋国负责增修成周围墙:“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杜预:“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远近之宜。 ”[3]“相”即观察。
充盈天地之间的,皆是物也。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亦一物也。从物性来说,世界由物组成,人不异物,然而,人文世界的建构却由人来完成。换言之,物世界由于人的参与而使得意义敞开。于是,在太古洪荒之初,“名物”,即为这个世界架构秩序、形塑物类体系就非常人所能。《尚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4]在古人看来,伯夷、禹、稷这些传说中的各族始祖都是上帝为了帮助下民而派到下土来的。他们都具有“生而知之”的不寻常的能力,对“万物”都具有天生的知识,能够治理、育化万物,进而能命名山川万物,使得山川万物这一物类体系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格物”,亦即能够招致物的到来:比如众神、凤凰、甘露,甚至禾、黍或麦子等。由是我们看到,从知物,名物,再到“格物”,这一神话学背景下的物类认知体系就绾合着“物”字的类别与分辨意涵,为物世界建立了以“类应”为架构的世界秩序。征之于文献载记,这种物类架构模式体现于先秦两汉诸多典籍之中。例如《周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5]再如《庄子》“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6];《荀子》“君子絜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7]。 到了《吕氏春秋》《应同》《召类》等篇,在吸收以往表述的基础上就变得更加精致了。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第五十七》则是更加具有理论高度而系统化了。正如郑毓瑜所指出:“先秦以来,从‘类物’到‘类应’的说法,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认知或经验‘物’世界的基本模式。”[8]但是,细绎上述《周易》《庄子》《吕氏春秋》等处的文字表述,可以发现,这一“类应”的物类世界有的地方非常神秘,属于难以稽查的神话背景下的“瑞应”物类体系,而有的地方却浅显易懂,能够征验于物。例如,“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师之所处,必生棘楚”;“水云鱼鳞,旱云烟火”;就是物类世界直接经验的反映,而以“类固相召”“神气相应”来解说上古帝王的兴起显然还是德能致物的“瑞应”体系。可考察上引文献,很容易发现,可经验的物类体系是占大多数的。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殷周之际的 “天人”革命。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走出宗教的匍匐,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参与着历史过程,并从自己的行为中寻绎历史变动的因果性。春秋时期,“天道远,人道迩”,周公以来的重人而轻神的天人相分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是,到了战国就出现了“物至知知”的说法:“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1]“物至知知”是说有事物作用于人,人的知觉才能起作用。这就告诉我们,物类体系的显现开始让位于经验世界了。但是,总体而言,先秦两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物类体系就始终没有脱离以人为中心的天人“类应”架构。
要之,中国古代物体系的建构联接着“天—人”两端,一方面基于可经验世界,以类相从,另一方面力图在“天人”架构下形塑成一个形而上的“类应”秩序。“类应”秩序的建构显然是要为经验界的事物关联提出一个根源性的解释,然而,这一看似完整的系统架构,却往往经不住事理推敲。这一点考察《大戴记》中的《夏小正》《周书·时训》《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淮南子·时则训》中有关物候的描述即可见一斑。对此,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批评道:“凭藉联想,而牵强附会上去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一看法过于“科学性”,而缺乏多维视域下的“同情性”之理解。相比之下,倒是葛兰言,尤其是李约瑟等治中国思想的海外汉学家由于“距离”而更接近于古人这一运思方式。具体可参看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关联式的思考及其意义:董仲舒》一节,此处不赘。
2 以类运思的物体系呈现形态
就中国古代物体系呈现而言,既分类又连类的以类运思显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引譬连类”,一是援类揽物。
我们先看“引譬连类”。“引譬连类”语出孔安国释孔子 “诗可以兴”的“兴”。“引譬连类”就是比譬、比类,亦即以某物及其所表征的义理比譬或比类勾联出另外物象和义理。可以说,“引譬连类”,以类运思是先哲用来观察世界获取社会人生义理的一种基本哲思方式。儒、墨、道、名及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的杂家等莫不如此。例如《墨子》一书,“譬之”“譬犹”“是犹”等词所在多是,以“引譬”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思想是墨子入思的根植所在。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以烹小鲜来比类治大国。《淮南子·要略》:“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9]而以比类的方式来建构自家的思想体系,儒家尤为突出。不仅如此,儒家还有着明确的理论认识。《礼记·经解》指出,“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荀子·正名》则明言“推类而不悖”[7],而《荀子·法行》中的“比德说”则更是在较高的理论层面对比类以为说进行了理论总结。《春秋繁露·实性》:“《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10]名物,由于结合了“物”分辨与类别的意思,所以也就具有了辨明事理或物理的意思。正因此,注重比类建构,且经常借《诗》阐发义理的孔子就非常看重《诗》中的“名物”:“《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如果将孔子的这一“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放到比类以为说要基于辨明事理或物理的基础上以为言,那么,此处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显然不仅仅是名物考据之学,或是比兴寄托之用,而是关系到“识”,亦即要辨明鸟兽草木之“物”的事理或物理。因为,它们是比类的前提和基础,关系到比类是否成行,与物性是否“必类”。
再说援类揽物。“方以类聚,物以群分”[5],以类运思中的另外一种物体系呈现形态是物以类从,并架构在一个类应系统中。这种物类体系建构,我们称之为援类揽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万象纷呈、千差万别的物世界。然而,这一纷繁复杂的物世界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古人发现,这一纷呈的物世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而客观世界就是一个物以类别,进而以类相从而形成的有秩序整体。可以说,这一看法在先秦时期就成了人们的共识。《左传·桓公六年》:“以类命为象。”[3]言类名是由与某物相象而得。《周易·乾卦》:“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5]《乾文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淮南子·诠言训》继承了这一思想“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 ”[9]是故,“名各自名,类各自类。”[9]那么,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要以类揽物呢?《淮南子》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览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沦无形也,纯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揽物引类,览取挢掇,浸想宵类,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阴阳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9]这段话提示我们,要想见识精微纯粹的道理,就要“揽物引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古人就是基于以上“远观博见”的类物考虑才讲“君子以类族辨物”。而实践中,我们发现,古人很早就开始讲万物“各从其类”,以类来连接“万物杂象”了。
早期“援类揽物”系统的物类建构有两条演进线索,一条是《尚书》中的九畴大法。一条是《周易》“观物取象”的“以类万物之情”[5]。先看“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孔传:“畴,类也。”[4]“洪范九畴”就是上天赐给大禹的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4]这九类大法连接着两个系统。一是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及六极这九项分类。这些分类涵盖了对自然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天文、历数、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一是顺用、敬用、农用、协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向用、威用这“九畴”对应的实用目的和方法。这就是说,“洪范九畴”是基于政治秩序问题而提出的实用性物类经验分类。这九类大法既分为五行、五事、八政等一系列类属,又以得自于天的神圣名义,实际上是以建构统治秩序为目的,连类于“洪范九畴”这一大的分类之下。就其获得方法而言就是自发的经验积累与天人“类应”架构下的“援类揽物”。下面,再看《周易》的“类”之运思。《系辞》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现代人不再相信伏羲氏“始作八卦”之说。但《系辞》所言“观物取象”,“以类万物之情”,应该是八卦生成的运思方式。“八卦而小成,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5]就这样,通过“触类而长”的不断附类,八卦乃演进成天下万物之代表。如在《说卦》中,万物以类相从,并以整齐排比的方式附类于八卦之下,而在《序卦》中,六十四卦又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方式“类应”连类而使万物架构于“阴阳”两仪之内。
绾合《尚书》以及《周易》这一天人“类应”架构下的“援类揽物”,再联系《夏小正》《周书·时训》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我们可以发现,基于生活经验,把天下万物以类相从,并将之记录在阴阳、八卦、五行、四方、四季、上下、十二月等等有序的时空架构下,已成为先秦时期以类运思的一个基本特征。而物体系也就在这种以类运思的世界中得以呈现。这样的以类相从,物以类现,是一种思维特征,而一旦呈现出来,它又成了一种书写策略。进一步寻绎,我们发现,这一时空架构下的物类呈现,是一种关联性秩序,塑成了一种为类所限的对称或曰秩序原则。举例来说,如果物体系以类呈现的话,说到了一月、二月、三月,联类着一年十二个月就都被排比出来(最早可溯自《豳风·七月》);既然说到了东,连类就要写到西,有了东西两端,南北自然就要被关联:“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12]孟春提到了“行夏令”遭致的不良后果,那么,基于连类原则,不提秋令和冬令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秩序世界;进一步言之,孟春提到了这些灾异反应,基于连类原则,仲春、季春,进而是夏、春、秋都需以此原则来构建。于是,一个既分类又连类的物体系就在这一“类应”的秩序世界中得以架构。
3 物以类应与离辞连类
跃入先秦文史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既连类又比类的物类呈现方式,已经形塑成了一个颇能建构的书写策略或曰作品生成方式。例如《战国策》: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13](《秦策一》)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埊,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有淮、颖、沂、黄、煮枣、海盐、无踈,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埊方千里。”[13](《魏策一》)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 ”[13](《楚策一》)
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魏之埊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13](《魏策一》)
细绎文意,不难发现,这里的物产、山川、地势等都是以连类而及的方式架构在东南西北这一空间秩序中。不同的是,苏秦要以之表现国家强盛,而张仪正好相反。由是可知,这一连类而及,援类揽物的秩序架构,既是经验世界的一种引类而从,同时在传承过程中已经形塑成了战国策士们的一种游说进言策略。正因此,苏秦可用之以彰显他所游说之国的国力,而张仪亦可以之来贬损他所游说之国的国力。正因此才有了《韩非子·难言》“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这一进言方法。要言之,援类揽物,“连类比物”在策士那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游说进言策略。就游说君主而言,“多言繁称,连类比物”是一种进言策略,而就策辞生成而言,它则是一种书写策略。这一“连类比物”,援类揽物的书写策略在先秦文学作品当中也有典型表现。其代表性作品是《招魂》和《大招》。 《招魂》全诗可分三个部分,主干是巫阳的“招魂辞”。招魂辞基本结构是:先援类揽物,将险恶和恐怖的物类呈现在东南西北上下六方这一架构之下,然后,将美好的事物以类相从在故居之中,于是,一抑一扬,在对比中召唤着魂兮归来。与《招魂》相近,《大招》也是作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经验,连类了恐怖和欢乐的两个世界。为了吓唬灵魂不要在外面跑,与《招魂》一样,在东南西北这一方位架构下连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和自然现象。而为了诱导灵魂的归来,与《招魂》一样,极连类之能事,构建了一个欢乐的楚宫世界。两个世界,两类物体系,当两类物体系得以全面呈现的时候,一个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世界也就得以塑成了。
先秦时期既连类又比类的物类呈现方式在塑成为一种书写策略后直接影响了汉代散体大赋的运思。先来看枚乘的《七发》。“吴客”游说“楚太子”时说:“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比”“属”“离”“连”是近义词,均有连缀之意,引申作归纳、排比讲,而“物”“事”“辞”“类”意义也相近,泛指相关联事物的名称、种类和言辞。枚乘所说的就是要让“博辩之士”对山川草木的不同种类和情状进行排比属辞,是故,“比物属事,离辞连类”之后就是鸟鱼林木诸物的描述。其实,从全赋来看,《七发》连类的不只是山林草木,还有音乐、菜肴、车马、歌舞、校猎和观涛这六种物类体系。这就告诉我们,整篇《七发》的运思机制就是“比物属事,离辞连类”这一既分类又连类的以类运思。具体来说,全赋“连类”的有两个物体系,一是“贵人之子”生活方式这一大类,一是这一大类下面的“七”个小类。与楚辞中的《招魂》和《大招》相比,《七发》的“比物属事,离辞连类”在体制上沿袭了《招魂》和《大招》的“援类揽物”。对此,古今学者早已发现。孙月峰说《七发》“亦是楚骚流派,分条侈说,全祖《招魂》”[14]。刘熙载《赋概》:“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15]钱钟书指出:“枚乘命篇,实类《招魂》、《大招》,移招魂大法,施于療疾,又改平铺而为层进耳。”[16]可见,《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招魂》和《大招》已有定论。区别在于,尽管《七发》《招魂》和《大招》都是连类排比饮食、歌舞、女色以及宫室游观鸟兽等,但《招魂》和《大招》中的物类是作为正面事物来出现,而《七发》把这一物体系作为否定对象来处理,意在对“贵人之子”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七发》“比物属事,离辞连类”这一作品生成方式影响深远,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号称“七体”。其实不仅“七体”的生成方式是“离辞连类”,整个汉赋就其本质特性而言都是“连类繁举”。例如汉大赋的代表性作品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对云梦山中以及上林苑里的物都是按类而从,集中描叙。凡属一类之物,均是依类放在一个段落中来写,如土石归土石,卉植归卉植,禽兽归禽兽,水果归水果。不仅如此,援类揽物的空间架构秩序在这里也有呈现,如写云梦一段就是按四方连类而述,而且南方分高、埤,西方分外、内、中,北方分上、下,秩序井然。可以说,物以类从,连类而及在这段有关云梦的描叙中得到了完美展演。钱钟书评述说:“《游猎赋》:‘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琨珸、瑊玏、玄厉、碝石、武夫。’按他如禽兽、卉植,亦莫不连类繁举,《文心雕龙·诠赋》所谓‘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也。自汉以还,遂成窠臼。”[16]“繁类以成艳”,“自汉以还,遂成窠臼”,刘勰和钱钟书的话如果从积极方面去理解,那就是,“连类繁举”“繁类”就汉赋物类呈现而言具有普适性。这在骚体赋中也能够得到支援。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在引“廉士”时就连类列举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伍员和屈原等人。而刘歆的《遂初赋》在感慨才美见妒时,也是连类排比了叔向、孔子、屈原、蘧瑗等人。骚体赋和汉大赋在连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区别是,骚体赋往往“引类譬喻”,而大赋的“闳侈巨衍”往往只连类而不比譬。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以“鸾凤”“鱣鲸”“神龙”等喻贤者,以“鸱枭”“蹇驴”“蝼蚁”等喻小人,是既连类又比类。尽管有着比类上的差异,但是,汉赋既分类又连类这一以类运思的物类呈现方式却是共通的。实际上,汉人对于赋体的这一物类呈现方式也是有所认识的。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曾如此记载道:“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17]扬雄的说法里,似乎透露汉时作赋者有一种认定,认为赋体为了要讽谏,必须用“推类”的法则,同时还是极度广远的类推,才能达到效果。由这一“推类”之说不难看出汉人对于赋体的这一物类呈现方式是有所认识的。而汉以后,赋体的这一“连类”运思方式则进一步被学界发现,进而演进成了一种学界共识。如曹丕《答卞兰教》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18],又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说“触类而长之”[18],《文心雕龙·诠赋》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于是乎,演进至刘熙载的《赋概》就有了赋要“系乎知类”这一看法:“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 ’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离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 ’”[15]在“知类”的基础上,或“举类”,或“连类”,或“依类”,或“触类”,可以说,这既是赋体的基本运思方式,也是“物体系”在赋体中的基本呈现方式。然而,细加寻绎汉人的论赋言论,可以发现,尽管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正视这一“物体系”呈现方式,但是,更多的情况下两汉论者却在着意与《诗经》拉联关系,一直以诗之比兴,作为赋体构造之原则。正如郑毓瑜所指出:“汉人针对 ‘赋’——不论是作为 ‘赋诗’、‘作赋(贤人失志之赋作)’或关于‘六诗(六义)’之‘赋’的众说纷纭,虽然看似在‘诗之六义’上达成共识,却并不以‘铺陈’来看待赋‘体’,反而让诗之比兴,更或者说是假道赋诗而来的‘古诗之义’、‘风谕之义’主导了整个汉代对于 ‘赋体’的看法。”[19]正因此,就汉赋创作实践而言,尽管“连类繁举”的物类呈现方式早已使得赋体呈现出与《诗经》完全不同的一种艺术风貌,但是,两汉论者却依然坚守“诗之六义”。于是,汉人就在与“六诗之义”的紧张中看待着赋体的“丽靡”特征。而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丽”逐渐成为正面的美学特征呼应着诗赋的创作实践。在曹丕的笔下,“丽”有了文体内在自性目的的诉求。继踵曹丕,陆机便在深化“诗赋欲丽”这一文体自性目的认识的基础上,从“物”的角度区划出了赋体的文类目的是“体物”,美学诉求是“浏亮”:“赋体物而浏亮”[20]。
综上所述,当我们追问“是什么物”,进而得知“物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凭借的是经验或体验世界里的一种以类相从或以类相别意识。中国古代物体系的建构联接着“天——人”两端,一方面基于可经验世界,以类相从,另一方面力图在“天人”架构下形塑成一个形而上的“类应”秩序。跃入先秦文史作品,这一“天人”架构下既连类又比类的物类呈现方式,已经形塑成了一个颇能建构的书写策略或曰作品生成方式。考索两汉赋体的运思模式,先秦时期这一既连类又比类的物类呈现方式在塑成为一种书写策略后直接影响了赋体的体物创作。
[1]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26、1083、1368.
[2]贾公彦.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59.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518-1519、115.
[4]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39-540、298、299.
[5]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51-54、542、53-54、623、621-623、586.
[6]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274、214.
[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45、423.
[8]郑毓瑜.类与物——古典诗文的“物”背景[J].清华学报,2011,(3):15.
[9]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54、991、606、1443-1444.
[10]苏兴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312.
[1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5.
[12]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
[13]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74、819、508、823.
[14]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52.
[15]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434、459.
[16]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9:637、361.
[1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75.
[18]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5、136.
[19]郑毓瑜.替代与类推——“感知模式”与上古文学传统[J].汉学研究,2010,(3):51.
[20]任树民.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J].兰州学刊,2015,(3):70.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VE WAY OF CHINESE ANCIENT THING SYSTEMS AND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FU
REN Shu-min
(BeiHua University,Jilin Jilin 132103)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eds to supplement the dimension of“thing”from the background of“material”.The ancient Chinese thing system connects heaven with human beings in a constructive way.On the one hand,the system is to determine th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experience world;on the other hand,the metaphysical order of object classes is expected to be formed in the framework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beings.The thing presentation way of comparing something with those of the kind under the“heaven-human”structure has formed the constructive writing strategy or works generation way from Pre-Q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orks.Taking the thinking ways of Fu into consideration,the presentation mode in Pre-Qin has become a writing strategy directly affected Ti-Wu writing of Fu’s creation.
Thing systems;Constructive way;Writing strategy;Fu;Ti-Wu tradition
I207.22
:A
:1672-2868(2017)01-0071-06
责任编辑:陈 凤
2016-12-05
吉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201588)
任树民(1979-),男,辽宁葫芦岛人。北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