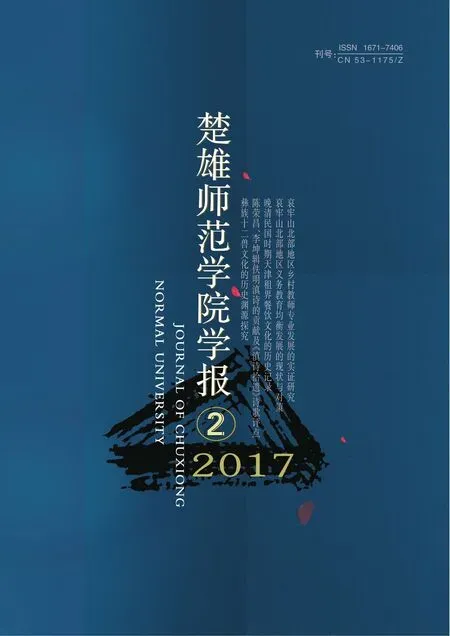陈荣昌、李坤辑佚明滇诗的贡献及《滇诗拾遗》诗歌评点
2017-03-29茶志高
茶志高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陈荣昌、李坤辑佚明滇诗的贡献及《滇诗拾遗》诗歌评点
茶志高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陈荣昌《滇诗拾遗》和李坤《滇诗拾遗补》专门辑录《滇南诗略》中所漏收明代云南诗人诗作,继袁文揆、袁文典之后辑佚补阙明滇诗有新收获、新贡献。两部总集在编纂体例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目录、作者小传及诗歌评点上。《滇诗拾遗》小传能够区别于《滇南诗略》已收作者小传的撰写方式以按语、注释和评语形式订正通行已久的错误,厘清自己所得的诗集版本源流。在评点诗作的过程中,注重不同诗人同题诗作和同一诗人不同诗作的纵横比较,并指出读诗应提倡“知人论世”,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
陈荣昌;李坤;《滇诗拾遗》;版本源流;评点
清乾隆、嘉庆年间,袁文揆、袁文典编选云南诗歌总集,后有五华书院山长黄琮编《滇诗嗣音集》、经正书院山长许印芳编《滇诗重光集》、陈荣昌编《滇诗拾遗》、李坤编《滇诗拾遗补》,再加清末云南特科状元袁嘉谷编《滇诗丛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云南省级诗歌总集序列。李坤为经正书院高材生。陈、李师徒二人辑《滇诗拾遗》与《滇诗拾遗补》,多录《滇南诗略》所未收之明代滇人诗作。学者对袁氏兄弟、黄琮、许印芳等的总集编纂情形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①f关于《滇南诗略》的研究,学术论文目前有张梦新、吴肇莉《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吴肇莉《〈滇南诗略〉的编纂与乾嘉时期云南诗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茶志高《〈滇南诗略〉目录及作者小传订误》,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思想述论》,文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李锋《〈滇南诗略〉中对白族诗人评点的特征及价值》,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滇诗嗣音集》的研究有茶志高《〈滇诗嗣音集〉目录订误——兼论〈嗣音集〉收方外、闺秀诗》,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滇诗重光集》的研究有茶志高《许印芳〈滇诗重光集〉的编纂体例及文献价值》,红河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但对陈荣昌、李坤的文献编纂活动及贡献,尚未有专门论文进行探讨。本文以《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为中心,对两部辑佚补阙著作进行研究,对集中目录、收诗数量、收诗重复等疏漏进行订正,并考察陈荣昌评点明代滇人诗作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的编纂宗旨
陈荣昌(1860―1935),昆明人。陈荣昌之生平,秦光玉有《陈小圃先生传》,传中对陈荣昌的身体力行以及崇尚笃实极为敬佩,“盖近世绩学之士,好考据者,动以繁征博引相夸。其崇尚文辞者,又以琢句追章为能事。至于身心性命之学,多未讲求,识者病焉。先生教人,于经史诗文之外,尤注重实践力行、本身作则。以程朱为趋向,以孔孟为依归,拥皋比六年,一时从游人士,观感兴起,咸知以道义德行相磨砺,而学风于是乎大昌矣。”[1](P754)这和陈荣昌心胸宽广、爱惜人才、提携后进有极大关系。
陈荣昌一生注重品行学问,著作等身,足可以一代文宗称之。袁嘉谷有《清山东提学使小圃陈文贞公神道碑铭》,对陈荣昌的诗文、书画、德行极为称许。[1](P757―758)目前,学界对陈荣昌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有几个维度:一、高国强对云南明代以来的藏书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晚清陈荣昌就是其中一位,并援引袁嘉谷评价陈氏之语“自食其力,无求于世,发为文章,其书满家”,但亦仅限于对陈荣昌的生平著述的简介。[2]二、赵蕊以陈荣昌、赵藩、黄德润三位云南绅士的反袁旨趣角度来考察护国运动时期的一些被遮蔽的史实。认为陈荣昌更加主张君主制度,在护国运动中,陈氏反对袁世凯称帝,更多的是反对袁氏本人,而并不是所谓的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共和观念也并未“深入人心”。[3]三、陈荣昌评传、传记。介绍陈荣昌生平事迹的有荆新德《陈荣昌述略》,[4]李东平《陈虚斋先生简谱》[5]《陈荣昌先生评传》,以论文形式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较为简略。[6]在陈荣昌传记方面,陈友康《一代文宗——陈荣昌》是新近较为全面介绍陈氏生平的论著,内容包括其家世和教育背景、仕宦生涯、教育功勋、游日经历、文学业绩、表彰先贤、书法艺术七个方面,认为陈荣昌是晚清民国时期云南知识界众望所归的领袖,他的作为垂范滇云,金碧有光。[7]在撰写陈虚斋先生传记的同时,陈友康教授又深入挖掘其诗歌内蕴,以《乙巳东游日记》为研究切入点,认为陈荣昌1905年赴日本考察学务,与日本当时的政教名流进行诗歌交流,彼此了解各自的“最好的思想和言论”。[8]学者较为关注陈氏《乙巳东游日记》,较早的论文还有周立英对其进行了评介。[9]紧接着,又综合虚斋诗文中所描写的内容,认为陈荣昌诗体现出“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特点,陈荣昌生活于中国社会文化剧烈震荡和历史性转折时期,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专制与共和、守节与顺世的纠缠和紧张等因素,使他的诗成为反映近代转型期诸多时代特征和精神特征的典型诗歌样本。[10]四、从陈荣昌的楹联及书法艺术、辞赋进行研究。论文有骆小所《陈荣昌及其楹联》、[11]戴志《儒家思想与遗民心态对陈荣昌书法的影响》、[12]王准《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论陈荣昌的辞赋及骈文创作》,[13]进行了简单评介,根据陈荣昌的著作篇目来看,当前的研究尚欠全面深入。五、对陈荣昌词作的研究介绍,最早的当属赵佳聪《陈荣昌〈骚涕集〉初论》有专门论述,[14]另外,尚有李钰晔《陈荣昌诗歌及其诗学研究》重点介绍了陈氏的诗学思想。[15]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陈荣昌的文献编纂活动、陈荣昌的交游、家庭诗歌以及作品整理研究是有待深入的。
李坤(1886―1916),昆明人。对李坤生平著述的研究目前较少,单篇论文仅见陈开林、曾繁英《李坤〈齐风说〉的诗经学价值》一文。文章对李坤生平著述进行考辨后,进而介绍了《齐风说》的体例及诗经学价值。[16]李坤生于甘肃,比长还滇,师事大理杨高德,后逮事石屏朱庭珍、许印芳,益治诗古文辞及经史学,这些都是誉满滇云的人物。袁丕钧《李坤传》云:“自康熙时鄂尔泰都滇,置西林学舍于五华山麓,以馆滇中之士,其后为五华书院,钱南园侍御、戴云帆诸先生皆出于是焉。光绪中,按察使贵阳陈璨,复置经正书院于翠湖之北,入者成为高材生,而以吾屏许印芳、昆明陈荣昌先后为之长,由是经正书院号多士。君自为高材生时,即以诗文冠轶侪辈,晚而弥加整饬。虽学于杨、许诸君,然其所至,非诸君所能囿也。”[1](P761―762)正因前辈学者的提携,李坤学业精进,卓然成家。
李坤与呈贡孙清元齐名。袁丕钧称:“予尝论滇中最近诗人,必推孙、李二君,孙谓呈贡孙君清元,李即谓君也。君以充栋之稿而自定其集,所存不过三卷,其精可知。文如《岩栖月谷诗序》《先考府君墓志铭》诸篇,虽茗柯柈湖为之,又何以加焉?君世居省会北仓山,予尝过君所谓雪园者,花木楼阁之属,丹彩犹昔,而居者已易其主,不胜其感慨焉。因为其传大略如此。若此坎坷困顿之迹,古今文人,前后如一,则亦暇为君惜矣。”[1](P762)袁嘉谷称他的诗“直嗣遗山,卓然成一家”,且“诗笔蕴藉,味美于回顾,亦有以质朴胜者。”又称“厚安诗境特拔一帜,婉妙细切,一时无敌。”[17](P555)李坤的著作皆精审,其著作“功深旨婉”,其文“炳且蔚”,袁嘉谷《〈思亭文钞〉序》云:“每多佳篇,震川皋文俦也。诗工力更深,源于穆清、五塘,而取材富,拓境宏,出入义山、遗山间,故一代之雄杰哉。”[17](P314)如《云南温泉志》一卷。是书将云南地方志中记载云南省44县的温泉情况一一著录,对安宁温泉的记载考订尤其详尽,体例规范、史料丰富、文词简洁。此书仅以稿本流传于世,现藏云南省图书馆。《齐风说》列举《诗经·齐风》语句,引证诸家注解及学说详加辩证,并提出己说,对同论点择善而从,论定是非,颇为允当。
陈荣昌、李坤尤重视典籍搜集传布,怀着深厚的乡邦意识和情感来从事文献编纂活动。《滇诗拾遗》的编纂宗旨,陈荣昌在《〈滇诗拾遗〉序》中说得非常清楚,要“珍护”先辈著述,不让先贤文献“飘零散落”。“故吾于乡先辈之语,凡已刊者,未刊者及已刊而复毁者,或有心访得之,或无意邂逅之,必择其尤雅者以存诸册,名之曰《滇诗拾遗》。盖欲与袁氏《诗略》、黄氏《嗣音集》、许氏《重光集》之外广其搜罗也。本欲俟积之既多,裒然成袠,乃次其时代之先后而汇刊焉。继思予之孤陋,交游不能广,耳目不能周安。网罗散佚,有裒然成袠之一日。不获已,乃随所得而录之,即随所录而刊之。积至数十叶,则别为一卷,又积至数十叶,则又别为一卷。期于入吾手者,不使之飘零散落,斯矣耳!”陈荣昌在昙华寺精心编纂《滇诗拾遗》,其《吊古集》中有《吊古楼二首》,其一云:“二袁黄许并修名,我亦摩挲剧有情。伏案一编随笔纂,下楼双履绕花行。晨钟夕梵传音节,鬼语仙心费心品。终古苍华灵气在,褰裳为尔撷菁英。”李坤《经正书院藏书记》云:“昔天纵骄子,回巢我五华,煯我书楼,笑夺我经籍图史及我赠书,地瘠道远,复之无由。生其后者,欲得闻古人前言往行,惟耆老之口说是恃。间或得之败纸堆中,盖亦已仅矣!”[18](P1027b)可见,李坤重视文献的保存,他认为,欲闻古人之言行,不能仅靠故老之口。李坤见陈荣昌《滇诗拾遗》尚有遗漏,乃就各府、厅、州志所载者,补成《滇诗拾遗补》,使成完璧,“是编之辑要,亦以有明一代滇人之诗为限,是亦踵其志,以补陈书之所未及,故此书后与陈氏《滇诗拾遗》一并收入《云南丛书》集部之八十五。”
二、《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的体例及收诗数目
《滇诗拾遗》和《滇诗拾遗补》互为补充,所收诗人诗作少有雷同,编纂体例各有优劣,最显著之区别在于陈氏编《滇诗拾遗》有诗歌点评。《滇诗拾遗》的编纂体例按顺序编排,依次为序、目录、作者小传、诗作、注释评论。所不同的是《滇诗拾遗》省去之前如《滇南诗略》等总集编纂中的“总目”项,卷首直接列每卷诗人及收诗数量。《滇诗拾遗》前五卷为陈荣昌所辑,卷六为李坤手钞。《滇诗拾遗补》则直接为作者小传、诗作、注释评论。《滇诗拾遗》各卷的诗人诗作情况如下:
卷一:明人兰茂诗35首,附赋1篇、《元壶集》一卷,未统计数量(有99首)。贾惟孝诗19首,杨一清诗61首(实应为62首)。故卷一共收诗人3人,收录诗作215首,赋1篇(《乐志赋》)。
卷二:目录标收明人杨一清诗267首,实收264首。
卷三:目录标收明人李元阳诗215首,实收214首。
卷四:目录标收明人王元翰诗130首,实收129首。另收赵炳龙诗17首。共146首。
卷五:收明滇南诗僧读彻诗130首,实为129首。收诗僧普荷诗84首。共收213首。
卷六:收郭文1首、朱玑1首、朱克瀛2首、朱凤2首、唐以敬1首、张含17首、李元阳2首、杨一清2首、李蕃1首、丁大训1首、王宗1首、赵端1首、邵圮1首、萧文亮2首、谭景2首、王昱1首、王懋1首、包玉1首、孟澜1首、萧景时1首、唐佐1首、杨士云2首、黄琮1首、黄敏才1首、黄明贤1首、黄明良1首、黄鹄1首、俞汝钦1首、木公1首、木青1首、木增1首附赋1篇、何惠1首、赵汝濂1首、周臣1首、段承恩5首(实为6首)、侯必登2首、廖楚良1首、梁佐1首、陈其力1首、罗镛1首、闪应雷1首、许滋1首、许国良1首、王琦12首、唐尧官8首附赋4篇、唐华2首、葛仲选1首、史旌贤1首、张薰8首、李萃1首、易经1首、陶珽2首、薛继茂1首、潘世澄1首、文祖尧1首、文俊德3首、李伯春1首、陆芸1首、潘嗣魁1首、杨师程1首、雷跃龙1首、赵日亨1首、廖大亨1首、杨忠亮2首、王肃1首、黄麟趾3首、黄都1首、张琮1首、杨绳武1首、周泽溥2首、张一甲1首、刘联声2首、耿希哲1首、傅宗龙2首、孙桐3首,普荷6首、古笑1首、如清1首、释禅1首。共150首诗,赋5篇。
《滇诗拾遗》卷六为李坤手抄,皆明人诗,姓氏之下有作者小传,诗下时有评语,中间杂有赋5篇。卷六因此自成体系,同时在目录中诗人的类型上亦有所区分,普荷以下均为诗僧,故标明“方外”。目录后有陈荣昌的说明云:
此卷为李厚安庶常手钞以付予者。予既辑明代乡先辈诗五卷,厚安又为旁博采,成此一册,因列之卷六。时代益远,网罗益艰。附刻赋数篇,亦以得之不易,欲其不复散失耳。厚安与予,皆婴世事,偶于暇时随得随钞。故其人其世孰先孰后不及銓次,姑存旧什,以摅怀之深情云。宣统纪元三月,荣昌识于升平坡寄庐。
李坤除了有此手钞诗一册之外,为补陈荣昌《滇诗拾遗》之收录明代诗歌之不足而辑《滇诗拾遗补》,全书收录诗人156家,诗360首,作者姓氏下附小传。卷首所录歌谣5首*分别为《妖巫歌》《永宁语》《曲靖歌》《楚雄歌》《滇中谚》。和其他诗歌,多为它书所未收,对于明代云南诗歌之采摭,用力甚勤。《滇诗拾遗补》无序、无目录,各卷收录诗人诗作情况如下:
卷一:歌谣5首、兰茂诗16首、贾惟孝诗7首、张海诗5首、张西铭诗2首、王绍宗诗2首、张凤翀诗8首、张凤翔诗3首、杨九思诗1首、杨靖诗1首、施均裕诗1首、夏尚忠诗1首、杨洪诗1首、李霖诗3首、濮宗达诗1首、徐瀚诗1首、马文荣诗1首、赵子禧诗1首、罗镛诗1首、张志淳诗5首、马玉诗1首、缪白诗1首、乔瑛诗2首、缪暲诗1首、杨南金诗5首、张云鹏诗1首、周机诗1首、朱尹诗1首、张含诗1首、缪宗周诗10首。共29人85首诗,赋5篇。
卷二:叶瑞诗1首、杨士云诗1首、杨九龄诗1首、严表诗1首、陈其力诗1首、钱若云诗1首、沈森诗1首、许凤举诗1首、王璠诗1首、张素诗1首、俞汝钦诗1首、陈爵诗2首、乔栋诗4首、陶廉诗1首、李元中1首、赵汝濂1首、曾倬3首、许子言2首、陈孟章1首、吴懋1首、涂时相2首、杨廷相1首、梁佐1首、王询1首、杨嵘1首、何思明2首、李昉通1首、樊相2首、李元阳10首、木公7首、俞纬1首、缪守之1首、萧崇业1首、王来贤2首、李居敬1首、杜克仁1首、薛继茂1首、张宗载2首、佴祺1首、陈于宸1首、何惠3首、孙思顺1首、谭继统1首、孙光绪1首、尹愉1首、王夔龙1首、朱化孚1首、杨师程1首、陈鉴1首。共49人,78首诗。
卷三:收何鸣凤5首、何邦渐2首、王元翰1首、赵日亨1首、赵以康2首、查伟2首、孙健1首、许瑞麟1首、杨忠亮1首、包见捷4首、陈铭1首、吴尧3首、张讃2首、艾自修1首、孔聘贤1首、李闻诗3首、艾廷献1首、罗九有1首、杨应桂1首、姚载典2首、马之骝2首、廖大亨1首、王锡衮1首、孙光祚1首、周泽溥3首、杨绳武3首、陈玺1首、何星文3首、张一甲5首、俞联辉1首、阚应乾1首、张垣2首、阚应祥1首、张启贤1首、张九贤1首、台衡2首、张炜台1首、陈世箕1首、孙皇之1首、杨泰1首、陈士恪1首、李友兰1首、王琦1首、何蔚文6首、何素珩1首、陶冕2首、廖楚良3首、张孔昌1首。凡48人,85首诗。
卷四:收任希班2首、向兴弟2首、李升瑚1首、张时宜1首、曾祺7首、杨资治1首、李恪1首、刘联声11首、高桂枝7首、杜莪3首、阿子贤1首、林宪1首、李献箴1首、张廷璧2首、雷石庵8首、李言恭2首、赵珣1首、丁大训1首、罗镛1首、姚咨相2首、包璿1首、施采1首、郭镛1首、赵以相5首、孙桐7首、张学懋9首、龚彝1首,附“方外”读彻诗21首、如一诗2首、如清诗3首。共计30人,107首诗。
与《滇诗拾遗》不同,《滇诗拾遗补》没有诗歌评论。另外,《滇诗拾遗补》在收录诗歌时有较为明显的疏漏,例如所选诗歌有缺题的情况,卷二所收李元中(石屏人,嘉靖年贡生,官万县教谕)诗:“乘兴探春尘外游,东风摇柳吐丝柔。几盘山路云遮寺,一带烟村水映楼。旧局寻仙梅下著,新诗迟我壁间留。兴来暂借青筇竹,直上云岑看十洲。”[19](P529b)又如卷三艾廷献诗:“禅扉不闭朝犹卧,金钥遥听夜未阑。上界芝光摇佛座,湖心灯影见渔船。世情野马忧何足,吾道冥鸿乐在先。今古闲忙谁觉是,山栖成癖自忘还。”[19](P542b)此诗亦缺题。另外一种情形是重复收诗,如卷一收罗镛(字孟宣,建水人,治《尚书》。尝从王景常、韩五云游,能诗文。隐居不仕,教子晟孙珣,俱登第,赠给事中。著有《纳轩集》《复斋集》)诗《危峰夜月》,[19](P523a)而卷四又收录此诗,[19](P555b)正如袁嘉谷所言“考订稍疏”。类似的疏漏是可以避免的。但较之“无一遗珠”的搜罗文献的功劳,此小疵又不足论矣。
三、陈荣昌《滇诗拾遗》诗歌评点
陈荣昌《滇诗拾遗》评点部分,主要有按语、注释和评语三种形式。按语如卷一杨一清诗《登舟三首》后按语云:“荣昌按:此乃公正德戊辰四月被逮后之作。”[19](P384b)又《夜坐示孙生思和》:“荣昌按:公于门生故吏多训诫之语,足征古道。”[19](P387b)《寿麓翁先生》:“按:帝遣群仙以下,乃题寿图之作,观篇末良功句自见。”[19](P390a)卷三目录之后云:“按:中溪先生以嘉靖丙戌进士,改庶吉士,出知江阴县,擢御史,巡按福建,知荆州府,拔江陵张居正于童试。厥后居正当国,功高劳赫,先生乃招其幼子入滇。居正败,幼子获全,人服中溪有先见焉。《诗略》称其致仕后,精研理学,与罗念庵、王龙溪等相印可。予观其文集,乃知中溪之讲学,合佛老而言之者也,其诗亦然。今太和人相传中溪乃仙去,虽不足信。然诵其诗知其人,自是身有仙骨者。予尝谓兰止庵,大儒也,人以为仙;李中溪,神仙也,人以为儒。恶足为定论。止庵之诗曰:‘彼哉说甚大罗仙’。中溪之诗曰:‘烟霞有分望神仙’。只此二语可见两先生之异趣矣。录中溪诗既讫,偶有所感,遂书之。”[19](P421a)此类按语较多,为了解诗歌的背景和主旨不无益处。如卷四赵炳龙诗《采菊二章寄高澹生》后:“荣昌按:澹生,昆明人,名应雷,公门下士也。”[19](P460a)同页《广烹鱼四章》后:“荣昌按:此亦将归之作。由黔返滇,故曰‘西归’。美人谓何提学闳中,曾招隐先生者。”又《无同心二章》:“按杨公虽死,吴贞毓等存,犹为国有同心。至十八,先生亦见杀,则无同心矣。”[19](P460b)而李坤《滇诗拾遗补》则似此类的按语未见。
陈荣昌《滇诗拾遗》中还重视对一些通行已久的错误进行订正,这些订正一般以注释的形式附于诗作题目之后。如卷三李元阳诗《中山》后云:“在剑川西南石宝山中,有寺曰钟寺,则以寺侧一巨石如钟形而名也,俗以钟名山则误矣。”又紧接下首《中山联句》后附月村评语云:“《通志》于题目加一‘科’字,曰‘中科山’,则更误矣!中科山自在州北,杨、李未尝至也。”[19](P433b)这样的纠正在其他滇诗总集中未见。
《滇诗拾遗》诗歌评点的特色,主要在于陈荣昌能够以自己的实际去理解和把握关于诗人的生平、性格、作品流传情况以及诗歌风格。
诗人小传中的评论部分最能体现总集编纂者编选诗作的缘由和编者识见的高低。《滇诗拾遗》在补明人诗作时,间有与之前总集同收之诗人,但所撰诗人小传却能别具一格,亦以精彩之评点附后。如《滇诗拾遗》卷一兰茂小传:“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别号和光道人,嵩明之杨林人。明洪武时布衣。学求六经,究心濂、洛、关、闽之微,旁及诸子百家,无不通晓,当时目为小圣人。后之论者,称为人英,又称其出而用世,当与刘、宋并驾。其著述散失,惟《声律发蒙》盛行,予得钞本《元壶集》及古近体诗四十余首,除《滇南诗略》已选者不复杂录,录其诗三十五首。”[19](P370b)陈荣昌写小传能够评及诗人的学术路径以及著作的留传情况,并说明自己所选诗歌的版本和缘由。试与李坤《滇诗拾遗补》兰茂小传进行比较:“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别号和光道人,嵩明州杨林人。性聪颖,过目成诵,年十三通经史,长益嗜学于濂、洛、关、闽之学,涣如也。赋性简淡,不乐仕进,尝颜其轩曰:‘止庵’,因自号焉。留心经济,正统间,大司马王骥征麓川,咨其方略,遂底于平。所著有《元壶集》《鉴例折衷》《经史余论》《韵略易通》《止庵吟稿》《安边策条》《声律发蒙》《滇南本草》《性天风月通玄记》诸书行世。与安宁张维齐名,一时学者宗之。洪武三十年丁丑生,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年八十,崇祀嵩州乡贤祠。”[19](P517b)此条可作为补充。
陈荣昌编写作者小传,通常把自己所得的诗集版本及来源交代得十分清楚。如卷三:“李元阳,字仁甫,太和人,世称中溪先生。袁氏《明诗略》选其诗五十首。予寻访先辈遗书,老友大理周霞为搜得《中溪汇稿》钞本全部,欲刻之而力有未逮,乃于《诗略》外更选其诗二百一十五首。”[19](P421b)又如王元翰小传:“王元翰,字伯举,号聚洲,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工科右给事中。《明史》称其居谏园四年,力持清议,摩主阙柱贵近,世服其敢言。御史郑继芳诬奏公奸赃数十万,公愤甚,尽出其筐箧,升置国门,恸哭辞朝而去。乃遍游名胜山水,客死南都。范凤翼为行状、刘宗周为墓志,倪元璐为立传,公之冤乃大白。荣昌闻公集版尚藏于家,乃遣人至宁州印数十部以广其传,又于袁氏《诗略》外别选其诗一百三十首。”[19](P446b)同样,卷一杨一清小传:“杨一清,安宁州人,官至大学士,谥文襄。《明史》有传。《滇南明诗略》及《续诗略》共刻其诗一百七十八首,兹所录过三百首,则从《石淙诗钞》中选而刊之者也。按《石淙诗钞》为嘉庆年间五华书院刻本,经兵燹毁矣。予友太和李文治在京师书坊购得之。其诗有公友李西涯及公门人李梦阳、康海、唐鹏评语,今并录之,以见师友渊源。”[19](P382a)此条说明了选杨一清诗的来源,同时指出杨一清与李梦阳、康海、唐鹏、李西涯之间的师友关系,为了解其生平交游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材料。同类的小传如卷五普荷小传、卷六王琦小传等。
《滇诗拾遗》的诗歌点评一般置于诗歌之后,小字双行,与诗作正文区别。陈荣昌对所选诗歌的点评往往是即兴式的,或短或长。如卷一点评兰茂诗《雪诗戏成白战三十韵》云:“神似东坡。”[19](P371a)点评《山中野人歌》云:“纵横跌宕,却毫不费力,可想其为人。”[19](P371b)点评《评诗有感》云:“六诗皆信笔写出者,洒落处自见本色,而示人学诗门径,亦略可睹矣。”[19](P373b)又评《成化丙戍(戌)予年七十岁近体诗十首》其五:“首句出自他人,则为狂语;出自先生,正可想其抱负。”其六:“五六句是周茂叔、邵康节气象。”其七:“《通志》谓《元壶集》阿好二氏,疑为伪作。读此事及下首‘丹鼎’句,足见《志》所言不谬。”[19](P373b)“成化丙戍”当为“成化丙戌”。此论可与兰茂《乐志赋》之后的跋语对读,陈荣昌亦认同兰茂喜好佛道,在诗文中可寻证。《乐志赋》题下有自注云:“缑山七十三翁和光道人书于止庵之吟室”。赋后有陈荣昌评语云:“此赋见先生之隐,非巢许之逃世,乃伊吕之待时也。得此以著其志,岂非大幸?”陈荣昌撰跋文说明选此赋的缘由:“右赋一首,本不合录于此第。止庵著述久已散佚,今五百余年而此赋与诗同时为予所得,爱之重之,赋而刊之,免其复失而已。至《元壶集》杂二氏而为言,故《通志》疑有伪托。然得之实难,并赋刊于后,聊存旧籍云尔。陈荣昌识。”[19](P374b)帮助我们推算出《乐志赋》的写作年代为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又如赵炳龙小传:“著有《居易轩诗文》八卷,经兵燹毁矣。其裔孙拙庵司马搜刻二卷,司马之子樾村观察以示予,予乃于袁氏《诗略》外更录其诗四十七首,先生之诗,风骚汉魏六朝三唐,并涉其藩篱,跻其堂奥,故各体皆佳。”[19](P459b)《石兰二章念澹生也》:“按:公文集,澹生为之序,是能传公衣钵者,宜公念之而不忘也。”[19](P461a)可以看出陈荣昌撰写这些评点文字是互相贯串和通盘考量的。
即兴式评点的最突出表现是简短,但能切中诗歌的风格特点。如评卷一贾惟孝诗《凤溪晚归》云: “秀炼。”[19](P381a)评《新春》云:“妙造自然。”评《自题扁舟小影》:“幽怀旷远。”[19](P381b)卷三评李元阳诗《鸡足山赠觉上人》:“工练自然。”[19](P440a)《滇诗拾遗》能够积极借鉴并有意识地避免和《滇南诗略》所收作家、作品重复,这也是《滇诗拾遗》的价值所在。“贾惟孝,字若曾,号东畮,嵩明人。性孝友,博学能文,不乐仕进,与兰止庵同里,与杨升庵同时。升庵赠东畮诗,与止庵同称‘杨林两隐君’。予得东畮诗数十首,选录十九首。其《滇南诗略》所著者,今所得著有焉,不复录也。《诗略》称东畮诗清隽似过止庵,以予观《诗略》所录,止庵《四时词》之工丽。余所录止庵《送春曲》《山中老人歌》《雪诗》,七古皆极其自然,飘飘有仙气。岂东畮所能过者。大抵东畮生止庵后,慕止庵之为人,谓其能踵武先正,则可耳。”[19](P379b)《归山操二章》其一:“此见东畮初亦饥趋,至是归计乃决。中写反复筹思之,跌笔妙如环。”其二:“此则归计得遂,并想归后之事。二首次第秩然,可为连章之法。诗旨与渊明《归去来辞》同而调则变矣。”[19](P380a)以上援引,均能说明陈荣昌辑录诗歌的严谨态度。
另外,陈荣昌把一些原评也附在了总集中,如卷一李梦阳等评杨一清《和杨镜川学士先生游南园诗韵》:“镜川云:‘佳作!佳作!当与西涯争衡。’梦阳曰:‘此篇果胜他作,镜川知诗矣。’”[19](P382a)又《送胡德延姊丈还京口》:“梦阳曰:‘不可无之作。’”[19](P383a)此卷李梦阳、李西涯、康海、唐鹏的评语悉数列出,如评杨一清诗《约斋为周都谏子庚赋》云:“梦阳曰:‘宋大儒诗如此作。’”又评《曹汝学擢南京太仆少卿赠别五首》云:“梦阳曰:‘头一篇另是一种,后四首遂入佳格。’”[19](P385b)《王尧卿自终南谒余镇江话旧有述四首》:“梦阳曰:‘情到理到景到笔到,然宋格也。’”[19](P386b)《南坡别墅》:“涯翁曰:‘七言古诗,此篇独佳。’”[19](P388a)康海对杨一清诗的评论如《和欧阳公禁体雪诗韵》:“此六一公敌手棋也。”又《和苏长公聚星堂禁体韵》:“康海曰:‘此东坡敌手棋也。’”[19](P389a)这些原有的评论,作者全列于上,卷二亦是。
《滇诗拾遗》除卷一、卷二中对杨文襄公的评论系原评之外,其他各卷为陈荣昌之评点。陈荣昌点评诗作,能够按照诗作的类型特点进行分析,如卷三评李元阳诗《同熊武选南沙游银山铁壁》:“游山诗末段,忽以兵警作收,大奇。”[19](P423b)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李元阳与熊南沙、任少海、唐荆川、王湛泉一起拜谒皇陵,办完公事,就一起相邀参观长城。此诗写于此期间。李元阳游银山铁壁间还写了《铁壁寺登中峰顶同熊南沙》《银山铁壁记》等。熊南沙“好奇熊武选,共我上坡陀”,面临只能容一只鸟飞过去的有“阎王鼻”之称的万丈悬崖,熊南沙能够气定神闲,快速地登了上去,李元阳亦豪气大发,到了山巅高歌一曲。在游览途中,李元阳与其他几位一起讨论了天下形势。李元阳热心修建寺观,“所得俸禄,尽归梵宫”。李元阳善于深入观察,反复构思,苦心经营,故作诗能挥洒尽意,收到奇效。对此,陈荣昌在点评中也予以阐发,评《筑台松杪壁上刻刘顾二公诗》云:“此与七古中《升真观》一篇,皆见公经营不惜费处。”[19](P424a)评论也涉及李元阳各体诗歌的横向比较。
再者,重视阐明一首诗歌的总体特色。如卷三点评李元阳诗《叶榆水》:“前段极写洱海之奇,后段俯仰古今,兴会淋漓,可谓煌煌大作。”[19](P425a)同类尚有评《送朱龙湾宪伯》:“前半写豪爽之态,后半写缠绵之情。”[19](P426a)又《天桥七夕》:“前半将天桥与七夕作一笔写,何等凝练!后半即事生感,与老杜《观打鱼歌》同意。”[19](P427b)《用韵答张愈光》:“末句殆以庾信比禺山也,后又谓其前身是少陵,盖倾倒极矣。”[19](P435a)写李元阳对张含的倾倒之情,评《柬张禺山》又云:“禺山为吾滇文章钜手,升庵、中溪亟称之,足见倾倒之意。”[19](P435b)在诗作内作具体分析时兼顾纵向的诗人间的比对,也是陈荣昌点评诗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和特色。上首与杜甫诗比较,又如与李贺诗比较的诗《观音岩》后评:“逼真长吉。”[19](P429b)同页评《九鲤湖》:“阳明诗云:‘同来问我安心法,谁解将心与子安。’与此同意。”章法和笔法亦为点评诗歌时不可或缺的要素,如《同高使君归自鸡山览天镜阁泛舟有赠》后评曰:“章法亦复奇古。”《钱参军花下饮》后评:“收笔新警。”[19](P427b)评《怀任忠斋》:“起笔健。”[19](P432b)陈荣昌还为读者指明读诗的一些门径,如卷三《寄旧令刘云峨》诗后云:“‘里居’二句当一气读下,惟其田少,故其碑亦香,所以为官不可爱钱。”[19](P437a)对诗意的把握十分到位。
根据作者的生平事迹来对所选诗歌进行精当的点评,并融入自己的阅读体验,也是陈荣昌点评的重要方法和特色。如卷四论王元翰诗《同静之兄诣东林讲席,与泾阳、景逸、本儒、启新、玄台诸君子谈〈易〉并读邸报有感》:“公生平自谓:‘于名胜山水、道义知己二者极不能忘’。此诗亦可想见其取友之益。”[19](P447a)又《长江行》后云:“公以放逐远臣,满腔悲愤,浪迹江湖。又见朝政之秕,忠良之霣。吊古伤今,声泪俱下。我读之,亦呜咽不能已。”[19](P449a)又《新郑遇朱武库年兄叙乡中事》其一:“首章以去国为主,因朱*原文作“朱”,按文意当为“未”,刊刻致误。入都而寄语都中故人,此去国后情事。”其二:“次章以乡事为主,恐因兵阻不得遣乡也。以题论,则次章乃为正面。”[19](P452b)指明同题两首诗的紧密联系。另外,于诗中发现一些前人未指出的问题,作为内证,可见陈氏读诗之细。如卷四《寄史莲匀侍御》后云:“公遍游天下名山,归后曾往游鸡足山,此诗可证。”[19](P455a)陈荣昌还有一些精辟的评论,如“豪放为牢骚”论。《滇诗拾遗》卷三论及王元翰诗《湖居》时云:“自古忠臣,无甘为隐沦者。读公诗得此意,则知放旷处无非牢愁。”[19](P456b)同样的论点在卷四评赵炳龙诗《醉歌六首》其一:“自《三百篇》以酒为解忧之物,后代诗人遂多酒狂。其实极豪放、极旷达,正其极牢骚之变相耳!读公数诗,当知此意。”[19](P463b)陈荣昌对读诗时应注意的一些方面,也予以指出。卷四《大隄隔》后云:“此等诗认作冶曲,恐终不宜。古人于君臣朋友至难言处,大半伪托为男女之词。吾谓此诗亦然。”[19](P463a)陈氏提出,读诗要注意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才能达到“知人论世”。卷四《离忧六章闵遇也》后云:“诵诗读书,以知人论世为要义。知先生之人,论先生之世。则读先生之诗,益唏嘘而不能自已。”[19](P461a)卷一至卷五均有此类评语,而卷六为李坤所辑,无点评。
四、结语
陈荣昌与李坤在兵乱之后,辑明代诗人诗作,用力为多。袁嘉谷《题〈滇诗拾遗〉寄虚斋师厚安同年》其一云:“莫向昆池话劫灰,边声字字逼邹枚。风流最爱陈父子,问字重当载酒来。”又其二云:“檐外梅花笑不禁,朔风腊雪几知心。开元天宝情如许,珍重神仙李翰林。”[17](P190)袁嘉谷对陈、李两人的才情和搜辑文献之功做了很高的评价。后来袁嘉谷在编纂《滇诗丛录》的过程中又提及此事,《卧雪堂诗话》卷二第六十五条云:“丛书馆中编《滇文丛录》《滇诗丛录》《滇词丛录》,文拟以《孟孝琚碑》为首,诗拟以《白狼王歌》为首,词拟以元高氏《寄段功作》为首。厚庵曾助小圃师为《滇诗拾遗》一书,网罗风雅,已称博洽。余在浙闻之,寄诗云:‘开元天宝情如许,珍重神仙李翰林。’即指此也。近又为《滇诗拾遗补》,凡明时滇人之诗,可谓铁网珊瑚,无一遗珠,惟考订稍疏耳。余所访者咸从归之,劝其仍入《诗丛录》中。”[17](P540)追溯滇诗总集的编纂,按照赵藩在《〈滇词丛录〉序》的总结,“滇诗总集肇始于保山袁苏亭先生,而昆明黄文洁侍郎、石屏许五塘教授、昆明陈筱圃学使一再踵事,称为大备”,[20](P287a)是十分客观的。同时,前面几部滇诗总集的陆续编纂,也激励赵藩编成了《滇词丛录》。结合陈、李两位先贤的文献编纂和诗歌创作实绩,以及他们在晚晴民国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尚有充分研究的必要和空间。比如,有关以陈荣昌为中心的云南晚清文人群体的研究,势必丰富我们对晚清云南文学的认识。以李坤诗作及其诗学思想为基点的研究亦是较具价值的学术点,比如李坤对有清一代整个诗学脉络的认识就集中体现在其《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此亦将有助于我们较好地把握李坤诗作的风格取向。
[1]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M].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2]高国强.云南藏书家拾零[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66―68.
[3]赵蕊.从云南三位著名绅士的反袁旨趣看“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说的有限性[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4):65―70.
[4]荆德新.陈荣昌述略[J].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6,(1),115―128.
[5]李东平.陈虚斋先生简谱[J].云南文史丛刊,1993,(3):78―85.
[6]闫秀冬,张诚.陈荣昌先生评传[J].贵州文史丛刊,1994,(3):59―62.
[7]陈友康.一代文宗——陈荣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8]陈友康.晚晴陈荣昌与日本人士的诗歌交流[J].云南社会科学,2015,(4):184―188.
[9]周立英.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J].史学月刊,2008,(9):37―42.
[10]陈友康.晚清——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诗歌样本——陈荣昌诗述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10―119.
[11]骆小所.陈荣昌及其楹联[J].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4):52―55+33.
[12]戴志.儒家思想与遗民心态对陈荣昌书法的影响[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6):30―33.
[13]王准.忧患意识与乡土情怀——论陈荣昌的辞赋及楹联创作[J].学术探索,2016,(6):129―134.
[14]赵佳聪.陈荣昌《骚涕集》初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5):64―66.
[15]李钰华.陈荣昌诗歌及其诗学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6]陈开林,曾繁英.试析李坤《齐风说》的诗经学价值[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2):58―62.
[17]袁嘉谷著;袁丕厘编.袁嘉谷文集(第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8]云南丛书处辑.滇文丛录[M](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15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19](清)陈荣昌辑.滇诗拾遗[M](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1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20](民国)赵藩辑.滇词丛录[M](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162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责任编辑 王碧瑶)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Anonymous Yunnan Poets in the Ming Dynasty Collected by Chen Rongchang and Li Kun and Review of Their Poems Collected inDianShiShiYi
CHA Zhigao
(SchoolofEthnicCultures,YunnanMinzu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Province)
DianShiShiYiandDianShiShiYiBuare complement ofDianNanShiLue, in which many poems written by Yunnan poets in Ming Dynasty are omitted. After the work of Yuan weikui and Yuan weidian, new contributions have achieved in collecting anonymous Yunnan poems in Ming Dynasty. The differences of two general collection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tents, author’s biography and poetry commentary.DianShiShiYi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DianNanShiLuein the way of the author’s biography; the former has corrected the long-standing mistakes with writer’s comment, note and commentary to clarify the source of poetry coll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enting poems, the thesi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making comparison on different poets with the same poem or different poems with same poet. Finally, the thesis advocates reading poems with the way of “remarking society from understanding people” and “speculating others with one’s own way”.
Chen Rongchang; Li kun;DianShiShiYi; the source of edition; commentary
2016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李坤《论诗绝句三十首研究》”,项目编号:2016ZZX131。
2017 - 02 - 05
茶志高(1986―),男,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讲师,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文献学、边疆学与中国西南民族。
I207.25
A
1671 - 7406(2017)02 - 0090 -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