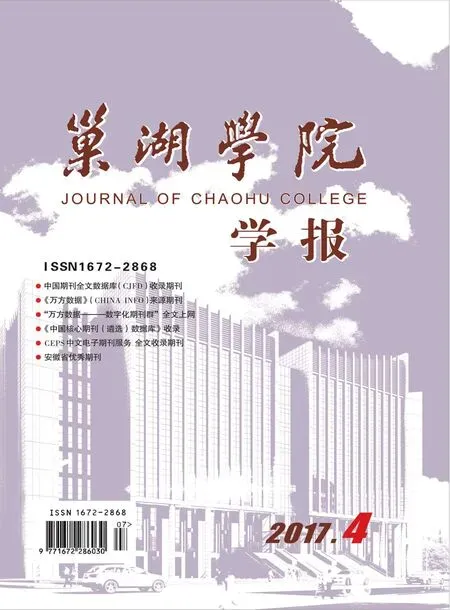吴湘案与唐大中政局的构建
2017-03-29夏威
夏威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吴湘案与唐大中政局的构建
夏威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唐武宗会昌年间,江都尉吴湘被李绅以盗用程粮和娶部曲女的罪名在上报朝庭后处死。该案在呈报过程中争议很大,御史台官员复查时曾提不同意见。宰相李德裕支持李绅并打击复查官员。围绕该案,各种政治势力深度介入,牛李二党在暗中角力。宣宗开启大中之政,最高层重审吴湘一案,定性为冤案,通过该案追责,李党骨干分子在朝庭被全面清洗,大中政局得以重构。
中晚唐政局;冤狱
吴湘是唐朝文学家吴武陵的侄子,吴武陵与柳宗元是好友,曾与柳宗元同游小石潭,名字被记录在文尾。吴湘本来默默无闻,但是,因为一起案件使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知道,并且与李绅联系在一起。李绅因为他的《悯农》诗家喻户晓。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是个仕途十分顺畅的大官僚。唐武宗会昌四年,李绅以宰相身份外派到经济重镇淮南任节度使。五年,有人举报江都尉吴湘,罪名是盗用程粮钱和强娶民女,该案先由淮南节度判官魏鉶审理,认为罪名成立,应判死刑,经朝庭核准,吴湘在淮南被处死。李绅在该案了结后不久也病逝。但他没想到,该案在其死后不久会掀起波澜,不仅影响到李绅本人的盖棺定论,而且对此后的唐宣宗大中年间的政局产生巨大影响。
1 吴湘案的事实经过
吴湘案的记载在正史中非常简略,而且不同记载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旧唐书·李绅传》这样记载:“会汝纳弟湘为江都尉,为部人所讼赃罪,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令观察判官魏铏鞫之,赃状明白,伏法。湘妻颜,颜继母焦,皆笞而释之。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兒女送澧州。”[1]根据这段记载,吴湘应当是涉嫌贪污被属下举报,又因为娶妻违反国家规定,数罪并罚,被处死刑,其妻子和妻子的继母,也受牵连受笞刑。《资治通鉴》记载:“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2]这与旧唐书涉及的罪名相似,但并非娶妻违制,而是强娶民女,罪刑明显要重,但是盗用程粮钱的事实是通过估算娶妻费用得出。《新唐书·李绅传》:“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籍,身娶民颜悦女。绅使观察判官魏铏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从以上三处记载来看,比较明确的是吴湘在江都任职,担任县令或者是县尉基层官职,被下属举报,状告吴湘涉嫌贪赃,而且娶妻违反法律规定。
江都县归淮南道管辖,经淮南节度使李绅的判官魏铏审理查明,认为应处死刑。淮南最高军政长官是李绅,李绅认为吴湘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由于死刑须呈报朝庭审核,该案上报朝庭。但是上报朝庭之后,该案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形成了舆情压力。“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3]在谏官进言后,朝庭安排御史崔元藻、李稠覆按,也就是对案件进行复查,由于该案与强势宰相李德裕有利害关系,对承办此案的崔元藻等人来说,压力很大,根据明哲保身的原则,维持原判似乎最符合个人利益,即不会和宰相发生冲突,但是,对于传统士大夫来说,名节也十分重要,如果趋炎附势,在舆论压力下,一辈子也不能抬头。最终,复查结论让宰相和物议都不能满意。“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崔元藻的复查结果触怒了李德裕,不仅吴湘被核准死刑,而且崔元藻被贬端州司户、李稠为汀州司户。按说,复查意见与原审意见不一致,朝庭不认可复查意见的话,应当再安排别人再次复查,但是,李德裕却选择了这样的做法:“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吴湘很快被执行死刑。
综上,吴湘案是吴湘因贪污和娶妻不合规定被判死刑,但是,该案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诸多不充分的地方,一是贪赃的数额是根据吴湘娶妻的聘礼以及结婚费用估算的;二是吴湘娶妻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存在很大的争议。另一方面,该案执行死刑也存在很多问题。吴湘犯罪事实并非很清楚,应属疑罪,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吴湘并非必须执行死刑的对象。另外,死刑的执行具有严格的规定,按照当时法律,春季万物生长之季,不应处决罪犯,但吴湘却在二、三月份被执行死刑,而吴湘并非涉嫌谋反等十恶不赦之罪。关于吴湘案,有的学者认为原判没有问题,如李文才先生。有的学者认为是冤案。根据《唐律疏议》规定:赃满十五匹绞,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吴湘能够确定的情节就是收入与结婚费用支出的严重不符,与“六赃”的任何规定并不符合,而且聘礼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借贷的。因此,李绅处死吴湘存在诸多违反法律之处,李德裕袒护李绅同样不恰当,等于是授人以柄。
2 关于吴湘案的政治势力角力
在无官不贪的封建社会,因为贪赃而重惩一位官员本来可能就不简单,可能隐含着政治斗争、打击报复等内在的因素。李德裕曾经重金贿赂宦官杨钦义担任宰相,“初,德裕在淮南,……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2]由此可见,李德裕显然也不属于廉洁之人。会昌年间,李党柄政,围绕吴湘案,从案件起初就牵扯各种政治势力。如果说该案是单纯的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即使在当时朝野也无人相信。通过吴湘案来打击牛党势力,应当在布局之中。首先,吴湘案发生为李党势力掌控的淮南,吴湘家族与宰相李德裕家族有过节。吴湘案在当时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吴湘家族与宰相李德裕家族有很深的过节。吴湘的叔父著名文人吴武陵曾经冲撞过李吉甫,吴湘的堂兄吴汝纳与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也有矛盾[4]。吴武纳与吴汝纳因赃先后被贬可能也是当权者的打击报复,“武陵坐赃贬潘州司户参军死,汝纳家被逐,久不调。时李吉甫任宰相,汝纳怨之”。其次,吴湘家庭与李绅也有矛盾。史载“会裴度东讨,而韩愈为司马,武陵劝愈为度谋”。从武陵替韩愈出谋划策可知,二人关系亲密,李绅与韩愈却一向交恶,两《唐书》之《李绅传》与《韩愈传》都有记载,如此,武陵与李绅之间因李、韩二人的矛盾而不洽,实在所难免,又吴汝纳既厕身牛党,他与李绅的对立也是必然的[4]。第三,吴湘家族与两李的矛盾背后是士族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唐朝传统士族与寒门之间矛盾非常激烈,虽然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进入仕途提供了通道,但是,士族不甘心丧失他们曾经拥有的特权,李德裕本人对科举制度非常反对,曾经公开发表意见指斥科举制度,并且指出这也是其父亲和祖父的态度。他平素也经常毫无隐讳地表达对科举及第的寒门士人的厌恶。不论是吴湘还是他的家族以及与之类似地位的人,都是李德裕厌恶的对象,如果他们远离官场,李德裕自然不会难为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想从高门士族那里分杯羹,就不能有把柄被人抓。第四,吴湘案背后最终是牛李党的角力。因为出身寒门,又为李德裕父子不容,吴湘家族只能投靠牛党。“汝纳怨之,后遂附宗闵党中。”这样,吴湘案中又牵扯到朋党的斗争。
吴湘案由淮南上报后,柳仲郢等大臣就上书要求复查此案,柳仲郢并非牛党分子,甚至和李德裕的私人关系还不借[5],为何由他上书而不是牛党中人出面呢?因为牛党正处于被打压的困境下,如果出面,不仅救不了吴湘,很可能牵连一大片,正好中了李党的招,作为具有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集团,不会出此下策。柳仲郢等人上书是否是牛党授意,现有材料无法反映。但是,肯定是在牛党制造的强大舆论下作出的,一方面职责所系,作为谏官,闻风弹奏是其职责;另一方面,不希望因为该案导致党争进一步加剧,甚至还有维护李德裕长远利益的考虑。但是,柳仲郢等中立人士的意见未被接纳。这一方面缘于李德裕不容易听进别人意见的个性所决定;另一方面,诛杀吴湘既可以报怨,又可以让牛党中下层见识自己的雷霆手段,压缩牛党的政治空间。但是,专横有时也会把很多中立势力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本案中复查官员崔元藻就是一例。崔元藻作出的复查决定虽然与原判有所不同,但还不是推翻原判,而且脏罪为重,娶部曲女为轻,并不能由此得出崔元藻阿附牛党的结论。
综上,李德裕存在利用吴湘案打击牛党以及报复吴湘家族的动机,但是,以李德裕当时的地位,指使李绅炮制吴湘案并无可能,从最终翻案的结果来看,吴湘是与同僚交恶被举报,李绅也是在上报之后才插手此案,在处理过程中,宿怨与党争促使李绅对吴湘进行严办,但也招来物议。笔者认为李德裕在物议沸腾之后,仍然回护李绅,还牵涉到李德裕与唐武宗的关系,牵涉到会昌政局。总之,对吴湘案的处理,政治是摆在第一位的,法律只能靠边了。
3 与吴湘案相关的会昌政局
吴湘案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并且深受案外的会昌政局影响。会昌政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李党秉政,宰相专权。由于牛党深度介入拥立安王李溶为帝的政治斗争中,招致唐武宗的极度反感,为李党上台创造了条件。会昌五年七月,李党分子陈夷行入相,九月,李党领袖李德裕顺理成章地入相。唐朝由于宰相员额较多,相互牵制,极少能够专权,中晚唐之后,宦官和翰林学士之类近臣又分去部分宰相权力,但李德裕是中晚唐宰相中的特例,他是唐武宗特别倚重的宰相,从他写的诗可以看出:“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会昌年间的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李德裕决策的结果,他的专权体现在皇帝高度依赖,大臣不能违抗,宦官势力有所退让。二是牛党失势,实力尚在。由于失去皇帝的支持,牛党在朝庭之上失去了话语权,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先后贬官,但是,牛党势力尚在。由于牛党的骨干为科举出身的士人,牛党在人才储备方面比李党更具优势,精英不断涌现,虽然头面人物被打压,中下层并没有伤筋动骨。三是会昌新政触及多方利益。李德裕全面秉政之后,强化中央集权,除打击政治对手牛党之外,对内挤压宦官集团的政治空间,对外削弱藩镇势力,在经济上打击寺院地主势力,在思想上排斥佛教等思想,实施灭佛措施,招致多方不满。但由于他的强势作风,多数势力选择隐忍,寻找机会反扑。会昌政局发端于武宗即位,武宗是在宦官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杀害了一侄一弟,即位之后,对皇室的潜在威胁者,无情打压。虽然唐武宗十分依靠李德裕,但并不代表二者不存在矛盾,唐武宗将李绅外放到淮南,实际上是对李德裕权力进行制约,李德裕坚定支持李绅对吴湘的处理决定,一方面是为巩固与李绅的政治同盟;另一方面也要捍卫自己的首辅地位。公道地说,李德裕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如果不是面对如此复杂的会昌政局,他未必会把自己牵扯到这起案件中来。
4 吴湘案牵动大中政局的重构
唐武宗逝世后,唐宣宗以皇太叔身份即位,年号大中。唐宣宗服膺科举制度,曾经以自己出生帝王家,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感到遗憾。唐宣宗信奉佛教,有记载他曾在百丈寺出家为僧,并且以游方僧的身份云游。这些个人倾向决定唐宣宗当政后必然会与会昌之政作出切割。执政在人,朝庭大洗牌势在必行。通过吴湘案翻案,可以回应舆论关切,惩处与该案有牵涉的官员,重塑官场生态,整肃司法体系,因此,为吴湘翻案可以成为清算李党的棋子。只是通过吴湘案打击李德裕及其所在的李党,究竟是经过策划,还是因吴家申冤而临时引发动议的,值得推敲。根据大中元年,白敏中使唆使李咸弹劾李德裕,导致李德裕贬为东都留守来看,牛党在搜集李德裕的罪证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吴湘案这么大的事他们肯定不会忽略。在司法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已经由最高当局定谳的案件,事隔数年,如果没有势力撑腰,吴家恐怕也断了翻案的念头,所以通过吴湘案打击李德裕及其所在的李党,应当是经过精心策划。尽管如此,还存在不少疑问。一是吴湘案究竟能否起到打击李党势力的作用。不论是淮南上报的案情,还是崔元藻复核的情况,吴湘贪污的事实基本上存在。二者主要的分歧就在于是否娶部曲女上,由于颜氏和继母生活,身世较为复杂,原审和复核出现差异,亦属正常,并非故入人罪。而且后者相比于贪污,只是个次要的罪名,即使复查认定的事实更准确,也很难达到完全翻案的程度。二是李德裕已经失势,且年事已高。李党失宠于君主,在本朝很难东山再起。冒险通过刑事案件翻案的方式打击他,是否具备合理性。三是通过吴湘案打击李德裕和李党势力,唐宣宗事前是否知晓。如果是事先策划,应当由白敏中、令狐绹等人授意或者直接参与,作为最高统治者,不可能直接介入操作层面。但是,牛党分子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吃透了唐宣宗极度厌恶李德裕的心态。唐宣宗在即位之初就表示李德裕立在身边,让他很不自在,并很快让李德裕出任荆南节度使,赶出朝廷。作为政治对立面,唐宣宗通过吴湘案清算李党,不仅能够巩固新政权的稳定,而且在很多方面有利,特别是能结束党争,如果李党不存,牛党继续存在还有何意义。当然,清算李德裕和李党是否必须通过吴湘案布局?李德裕在会昌年间的政绩有目共睹,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八百孤寒齐落泪,伤心一起望崖州”,如果不彻底打倒他,后患无穷。而重审吴湘案不仅能达到这一目的,更能让李德裕名誉扫地。另外,李德裕留给政治对手的把柄并不多,所以,唐宣宗和牛党不可能放弃这一机会。
在唐宣宗登基后不久,重审吴湘案件工作启动。崔元藻再次主审该案。按说,曾经审理案件的他应当回避,虽然唐朝还未建立完备的回避制度,但是,根据常理来说不太合适,当局之所以作出这样选择,一是崔元藻熟悉案情;二是他已经完全站在李德裕的对立面。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公布的复审结果:“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与阿颜母阿焦同坐,群自拟收阿颜为妻,妄称监军使处分,要阿颜进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监守。其阿焦遂与江都县尉吴湘密约,嫁阿颜与湘,刘群与押军牙官李克勋即时遮拦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论湘取受,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至岭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断湘处死”[5]。重审结果全面推翻原来的认定,不仅强娶民女不存在,吴湘妻子完全是良家子弟;而且盗用程粮的指控也是被诬陷的,淮南当地武官试图强占颜氏女为妾,后颜氏女嫁给吴湘,招致不满,诬陷吴湘贪腐。至此,吴湘案完全是冤案,该案昭雪后,吴湘家得到抚慰和补偿,一侄被安排官职。草菅人命是大唐王朝所不能容忍的罪行,追究责任势所难免。
吴湘案昭雪后,朝庭实施问责,此前,已被免除宰相的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这在唐朝,可能是仅比死刑略轻的处分了。李绅因为已经去世,子孙受到世代不许为官的处罚。其他与该案有牵连的李党重臣李回、郑亚都被贬出朝庭。牛党表面上大获全胜。通过人事调整,唐宣宗基本上做到了乾纲独断,改变了会昌年间宰相权力过重的状况。相比于牛党,以世家子弟为骨干的李党在领袖被打倒之后,元气大伤。另一方面,朋党相争的政治基础是弱势君主,主要集中在穆宗、敬宗和文宗三朝。作为以苛察为能的君主,宣宗不仅铲除李党,而且要让牛党散于无形。在宣宗的铁腕下,牛党宰相令狐绹和白敏中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又岂敢再挑起党争触犯天条。大中初年,通过吴湘案整肃李党集团,实现了大中政局的重构,同时,一起纷争多年的案件终于盖棺定论了。
结语
吴湘案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即使吴湘冤枉,通过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专门的司法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应当能够将案件查清。然而,由于政治的过分介入,案件事实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是最终的结论,其可信度有多少,不得而知。面对政治利益,不论是李德裕,还是唐宣宗,都没有放弃干预司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掌控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竞相利用刑事案件打击政治对手,对法制造成严重的破坏,可以说是挖掉了政权的基础,如果连司法都不能让人信任,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公信力。唐宣宗虽然通过吴湘案重构了大中政局,但是,宣宗后唐朝迅速走向末路,同其迷信个人权威,不重视司法制度的维护不可能没有一点关系[6]。
[1]刘昫.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2309-2313.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一百五、一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41-5349.
[4]李文才.关于吴湘案的几点考释[J].扬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
[5]陈磊.吴湘案的“物议”、复推及其影响[J].史林,2011,(6).
[6]黄会奇.试析“吴湘之案”[J]东南文化,2004,(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TICS OF TANG-XUANZONG DYNASTY AFTER WU XIANG CASE
XIA Wei
(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
Tang-wuzong period,County magistrate Wu Xiang was executed for corruption by Li Shen.Despite the controversial process of handling the case,Prime minister Li Deyu support Li Shen and suppressed officials of different opinions.Surrounding the case,the political forces deeply intervened.After new emperor took office,Wu Xiang case was retried as an unjust case.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trial,Prime minister Li Deyu and his companions were down,and the political forces were reshuffled.
unjust case;partisanship
K242
A
1672-2868(2017)04-0084-05
2017-04-10
夏威(1990-),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