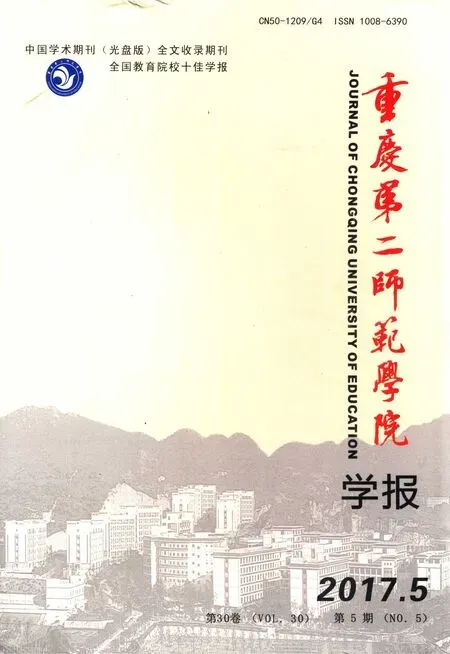孔子音乐美学与儒家政治观
2017-03-29窦琪玥
窦琪玥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孔子音乐美学与儒家政治观
窦琪玥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2)
孔子认为音乐的形式规范会内化为个体修养,使人自觉建构与理想人格同构的政治秩序;而道德本质会外化为音乐形式,音调成了政治状况的反映。孔子格外强调音调的作用,将音调从与诗乐舞合一的音乐系统中分离出来,最高的境界“无声之乐”甚至排除了音调,这既是合理政治秩序的延续,也是艺术理想化的表现。从孔子开始,“乐”出现了独立于政治道德要求而被独立感知的倾向,孔子通过分离音乐的审美与意识形态属性,提高了“乐”的地位,但这与孔子的政治主张有背离之处。
孔子;儒家;政治观;音乐美学
儒家音乐美学内化于其政治思想体系之中,与政治相互缠绕、相互渗透。“政治的目的是要拨乱反正,建立一种秩序。而美从根本上说即体现为秩序的‘和谐’,可以说,政治在其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与美学联姻了。”[1]孔子认为,作为完善人格的实现标志和中介,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音乐外在的强制性规范会内化为个体内在修养,使人自觉建构、维护与理想人格同构的政治秩序;同时,道德本质会外化为音乐形式,音调成了政治状况的反映。这是一个双向运动。孔子从不否认音乐的工具属性,然而其已经意识到音乐独立于政治内容的审美属性。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2]3孔子将音乐作为纯粹审美对象进行观照,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剥离音乐的意识形态外衣,既从感性经验角度对音乐进行直观体验,又从理性角度抽离出制乐、奏乐的基本特征。从孔子开始,音乐的音调从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格局中被抽离出来,真善美一体的艺术标准也被解构。承载情志的音乐和政治在理想状态下毫无罅隙,孔子虽已意识到两者的难以弥合之处,并力图将其统一,纯粹的形式美却还是萌芽了。
一、乐之实质:建构“文质彬彬”的政治样态
在西周中原地区,音乐首先作为政教的工具,与统治阶级达成合谋。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致力于重建西周的礼乐传统,将“仁”的内在规定性作为音乐的法度,用音乐的等级维护政教的等差,以此恢复“仁政”。
早期中国,音乐与诗歌、舞蹈合一。《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词义,如文绣然也。”“文”是线条、色彩、声音交错构成的审美形态,可见音乐含于“文”中。商周时期,“文”以“礼文”的形式确定下来,音乐也被纳入这个系统。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文”由秩序和身份的象征滑落为娱乐品,“八佾舞于庭”和“三家者以《雍》彻”的行为时有发生。为了重新确立旧贵族的身份秩序,匡正天下,孔子重建了一套以“文言”与“质言”的分立为标志、以“文质彬彬”为理想状态的话语系统。[3]王元化曾指出:“文和质的关系是由仁和礼的关系推演出来,专指道德规范和礼乐制度而言。”[4]“质”指向仁,指一种刚健质朴的为人之情性,《论语·子路》有“刚毅木讷近仁”;“文”指向礼乐,《乐记》有“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仁”是礼乐之“文”的内质,以“质”定“文”、以“文”节“质”是一个基本范式。因此,礼乐之“文”话语系统的建构与“仁政”秩序的重建息息相关,后者也是制礼作乐的内在要求。
“文质彬彬”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样态,与理想政治秩序同构,“礼”“乐”是达成这一秩序的中介。徐复观指出,孔子的立教宗旨是将乐置于礼之上,认为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2]3《论语·泰伯》有“立于礼,成于乐”,其中“礼”突出的是外在的形式对情感的节制作用,正所谓“丧不可径情而直行,为之衰麻哭踊之数,所以节之也,则其本戚而已”[5]。此时形制与情感是有区隔的。而圣贤对“乐”的规定与人的情感意向一致。《乐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更多是情感和文饰调和的产物,是“浸透着情感的表象”[6],也就是浸润着情感的“文”,学“乐”的过程也是情感被重塑、建构的过程。李泽厚认为,最早的陶冶性情、建构人性就是通过音乐实现的,是“夫乐,乐也”的感性精神和“乐以节乐也”的理性规制融为一体的结果。[7]568《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闻知道理的人不如喜爱道理的人,喜爱道理的人又不如以道为乐的人。“好之”和“乐之”的区别就在于,仅在理性层面上认可“道”,自己与“道”仍存在区隔,“乐之”则在道德理性中融入了感官的生理作用,主体人格真正浸润在“道”中,与“道”合一,如此“乐之”就与音乐的境界相类了。“礼”或许能达成“好之”的境界,“乐”却能实现“乐之”。
不过,孔子虽强调不可偏执于一端,在“乐”之“质”与“文”发生冲突时,孔子显然更重视前者,美的形式居于“仁”后。《论语·阳货》:“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乐何?”因此,当“仁”“乐”冲突时,对“仁”的高扬和“乐”的悬置便是必然的。《论语·阳货》中宰我和孔子就“三年之丧”有所争论,宰我认为,长时间不遵行礼乐会导致礼崩乐坏,提倡改用“一年之丧”。孔子问他,父母去世之初,食稻谷,着华服,内心安定与否,宰我给出了肯定答案。宰我认为,礼乐之制与仁人之心同质同构,“一年之丧”的提出,表明他试图调和“仁”和“礼乐”,调和日常和丧葬时的礼乐之制,小心翼翼地不伤及两者。而孔子指出,三年之丧合乎道理,并指责宰我“不仁”,原因是“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仁”发于内心,“礼乐”只是维护它的形制,不可舍本逐末。如此,孔子就肯定了先“仁”后“乐”的原则。《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于武城闻弦歌之声,指责“割鸡焉用牛刀”之事。弦歌之声属于大乐,奏于武城不合规制,孔子深谙音乐等级与社会结构层次相互建构的关系。子游则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是以孔子提出的普适性之“道”介入当下场域,认为君子、小人常闻弦歌之声则可各居其位,以至上下和睦。武城是鲁国边陲之地,礼法制度鞭长莫及,民众重武轻文,子游的首要任务是使民众获得仁人之心,防止叛乱滋生。而“乐”能以审美的方式直达内心,塑造情感。因而以“乐”化民,相比以“礼”教民,更能使民众建立一种与弦歌同质同构的道德意识,达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想效果。孔子最终一反前言,承认政治目的比手段重要,弦歌奏于武城的合法性问题暂时被悬置。
西方音乐悲剧是包含了歌舞、戏剧等元素的艺术形式,与中国古代诗乐舞合一的“乐”别无二致。尼采《悲剧的诞生》追溯了古希腊神话蕴含的两个精神原则——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酒神精神以理性无法解释的神秘方式直达世界本质,日神精神则能产生伟大崇高形式的美感。[8]93尼采认为,音乐悲剧是这两种精神的调和,其中音乐是世界理念,[8]94戏剧制造了一种日神幻景,避免观众受到酒神音乐的伤害。[8]103两者按照合适的比率调配,形式的优美调和了由内容过分崇高而引起的不适感。至于中国的雅乐,“文”指向“质”,又制约“质”,把对“仁”的诉求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礼记·檀弓上》:“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杨天宇将“入弹琴而后食之”注为“弹琴为散哀”[9]。孔子内心的哀痛超过了礼制允许的范围,于是借弹琴舒缓悲伤,才能全食祥肉之礼。可见,无论中西,音乐都以其包容性被看作最完善的艺术形式,看作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调和的产物。不同的是,儒家强调中和之乐,“质”与“文”也无法完全等同于崇高与优美,“质”含着些情感因素,不过“质”的实质依然是“仁”,是一种与政治同构的理性要求。因此,孔子指出:“君子之居丧”应“闻乐不乐”。酒神精神却是情绪鼓荡而毫无节制的一端。尼采调和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要求也是模糊不清的,他高度赞扬瓦格纳充沛的英雄气概和拒绝用日神精神粉饰个人意愿的行为,可见尼采哲学终究是非理性主义的。
二、音调作为政治的表征:“声音之道与政通”
“声音之道与政通”,音乐是当下政治状况的表征。雅乐合于仁政,郑声则与恶政对应。《论语·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庙堂之乐可以断定国家大治与否,淫代雅乐意味着纲常衰败。郑声的特点是淫、慢。《论语·卫灵公》有“郑声淫”。《说文解字》:“淫,浸淫随理也。”“淫”本义为浸渍,后引申出过度、溢出、邪淫、谮越等义,都包含“过分”义项。郑声旋律变化过于复杂,超出了文质彬彬的和弦音乐的范围,因而长期浸润于此类音乐会“好滥淫志”,“淫于色而害于德”。其中第一个“淫”表放纵,第二个“淫”表沉溺。沉浸于没有节制的音乐波动,会放纵自己的心志,损害君主的德行。《乐记》又载:“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郑音类似于慢音,慢音随意舒缓,善于制造气氛,气氛时而高扬,时而低沉。
不独郑声,以郑声为代表的“淫乐”都为孔子所否定。《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乐记》曾批判四国之音:“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郑、宋、卫、齐四国的音调特征分别是放荡、柔媚、急促和傲慢怪癖。《乐记》:“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漫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从音乐角度解读,四国之音动听却变动不居,舒缓而凌犯节奏,放纵沉迷而迷失本性,音调过广则能容纳多变的音节,音调过狭则引起不合理的欲望。其中,宋音“慢易”,郑音音域过广,卫音则音调过狭,从为政角度解读,四国之音皆使为政者感到快乐却内心不安,怠慢而违背礼节,放纵而忘记为政之根本,任用奸辈,徒生欲望,与“仁政”背道而驰。这两个过程是相对应的。《礼记》:“乐由中出,故静。”音乐与心灵最为切近,君主若长期浸染郑卫之声,沉溺其中,治国方略也会随之变化无常,不合国礼。此时音乐是政治的表征,也是为政状况形成的原因。
“北鄙之音”即商纣时期的乱世之音也是被拒斥的。《论语·先进》:“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说苑·修文》曾记载此事,孔子认为子路奏乐“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不合于中和之乐的品质。“北鄙之音”的特征是声音凄厉、细小,音调过高,响度过低,属于“无法之音”,虽也有动人之处,然而“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长期浸润于此类音乐不利于善德的培养,君主闻之则国家不治,不能“同民心”。
孔子对“乐”之音调极为重视,认为它可以剥离诗歌、舞蹈,以纯粹声音的形式对人格和政治样态产生影响。《乐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宫、商、角、徵、羽五声相杂而发生变化,变化成曲调而称作“音”,此时的“音”是无词之曲。按照歌曲而演唱,并拿着干戚羽旄舞蹈就称作“乐”,此时的“乐”是有词之歌。孔子认为通过无词之曲就可以通达“仁”。《史记》记载孔子学琴的经历。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十日后师襄子说“可以益矣”,孔子却认为“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习其数”后还要“得其志”,“得其志”后“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从而在脑海中构建出作曲者的人格形象“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此曲正是《文王操》。琴曲的旋律、演奏的方法是技艺层面的东西,“志”乃每一乐章背后的精神。孔子认为,习得一般性的“志”仍不是学习的终点,“得其人”才是学“乐”的最高境界,即将“志”扩展、延伸,使其充溢于天地间,发现琴曲中崇高的人格主体,并与之融为一体,最终养成同于文王的君子之德,而这种人格样态与理想政治状态是同构的。孔子认为,通过不断地对音调进行鉴赏、领悟,最终可以得仁人之心,行仁人之政。
孔子进一步指出,抛弃了形制的“乐”,才是天下之“至乐”,才可培育君子之“至德”。《乐记》:“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声”配合成“音”,“音”再进阶为“乐”,“声”、“音”、“乐”的学习需要循序渐进,孔子却提出“无声之乐”,在知“声”、知“音”而得“乐”的基础上抛弃两者,返璞归真。《礼记》:“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宥密”是宽仁宁静的政治状态,这样的状态可以在“无声之乐”中达成。孔子还认为“无声之乐”可以达到“气志不违”“气志既得”“气志既从”“志气既起”的境界,“气”“志”分别是生理和道德作用,无气之志只是本能的冲动,无志之气是虚无的理想,两者分属人格之两端,却时常发生矛盾,要想统合两者,则须将道德理性注入生理欲望,达成这一精神状态的中介就是摒弃了形制的“无声之乐”,可见“乐”的最高境界完全被心化了。抛弃了文采节奏,又抛弃了声音的音乐,只剩动心养气,“是固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如此之“乐”却足以成为“至乐”。“无声之乐”和“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一起,突破了艺术的有限性,与最高的“宥密”之政治境界达成一致,不过这种境界带有极大的想象性。此时的音乐虽仍隐含某种政治秩序,却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化了。
三、“乐”的审美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合谋与冲突
孔子时期的“乐”既然属于“文”的范畴,自然具备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10]“乐”除了维护政教的功利性质,还具备纯粹审美的性质,人可以借此获得纯粹的感官愉悦,有时“乐”甚至会排除功利的干扰,解构“美”“善”合一的政治秩序。
“乐”作为美的形式,可以建构、调和“真”“善”,弥合感性经验与理性经验。“美”“善”皆从“羊”,二者互文互训。《说文解字》:“善,吉也。”“美与善同意。”段玉裁注:“羊者,祥也。故美从羊。”因而孔子常将“美”“善”作为统一的范畴看待。李泽厚表示,音乐等艺术形式与认识或道德不同,却有利于建构后两者,实现“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音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理性。[7]526-527《论语·阳货》:“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孔子对“不为”的解释是“不甘”“不乐”“不安”,而非政治与道德训诫,可见孔子探讨闻“乐”与否的立足点是人的情感和审美态度,而这一点与政治规范是内在一致的。《礼记·檀弓上》曾记载子夏与子张服丧过后与孔子相见,孔子命二人调琴,子夏“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子张“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孔子认为,子夏的丧母之哀未能及时散去,子张的哀痛却过早消散了,两人按礼服丧,却皆未能把礼乐的形制内化为心中之仁。可见,“乐”建构评价“善”的标准,与“善”的人格与政治秩序同构。《礼记·檀弓上》还记载了两则孔子服丧中的故事。一则是祥祭之后,孔子“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孔子在祥祭之礼的五天后,弹琴不成曲调,再过一个月零十天后,即礼全之后,配合笙乐而歌就和谐成曲了。另一则是颜渊之丧,孔子悲痛而无法全食祥肉之礼,于是先奏琴曲,用琴曲中浸润的中和精神调和过哀之情,“以美储善”的目的随之达到了。
然而,“乐”与合于政治教化目的的“善”未必完全一致。《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庙堂之乐,尽善尽美;《武》是征伐之乐,美而不善。孔子意识到,“善”“美”并非不可分离,音乐的审美属性在此被单独提出。《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接舆作为隐士,拒绝与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孔子直接对话,孔子“欲与之言”,接舆“趋而避之”,取缔了世俗之“礼”的合法性。然而,接舆以“乐”的形式讽喻孔子。接舆认为,以“乐”达意并未破坏自己隐逸的生活方式,可见“乐”作为一种美的形式,对世俗生活具有超越性,可以剥离政教的内容,获得纯粹审美意义上的价值。接舆歌唱之时,“乐”之“美”相对于合目的的“善”和合概念的“真”是被优先感知的,至于接舆的目的是否在此则无关紧要了。《礼记·檀弓上》记载行禫祭中的孟献子“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可见钟磬之乐可以使人产生极大的愉悦,在一段时间内免于奏乐不合于人之常情,是较为困难的。另,对于刚行过祥祭就放声高歌的鲁人,子路嘲笑其未能全礼。因为按礼禫祭过后才可歌唱,鲁人比规定提前了两个月。孔子却责备子路,认为此人能坚持到第三个年头并能全礼,已然不易。可见孔子在能基本持礼的情况下,强调“乐”的审美性。孟献子全礼,孔子大加赞赏;鲁人未能全礼,孔子却表示理解。可见孔子在合道德的“礼”和合审美的“乐”发生冲突时,也曾产生过矛盾心理。
独立于“善”的“乐”,可以被作为一种纯粹审美对象。《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从师挚的升歌到《关雎》的合乐,充盈了孔子的感官。《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通过闻《韶》,获得了巨大的感官快乐,以至于其他感官经验掩盖不彰。《论语·述而》又有“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听见优美的清唱,必要他人反复演唱并跟唱,此时的“乐”失去了在特定场域下的神圣性和仪式感,剩下的只有优美的旋律和歌词。又有“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是日”表明孔子平日里都会唱歌。在清唱的过程中,孔子获得了审美满足。而《论语·先进》中曾晳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更是一种无目的的纯粹审美愉悦,孔子叹道“吾与点也”,表现出由“乐”带来的审美愉悦的普适性。
孔子对制乐和奏乐的研究颇深,这是将感性经验转化为理性经验的结果。《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既指情感表达的强度合适,与“哀而不伤”形成对举,又指音节变动不溢出适当的范围。孔子明显注意到了音乐的形式美问题。另有“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说文解字注》:“翕,起也。释诂,毛传皆云。翕,合也……言起而合在其中矣。”奏乐之始,各种乐器齐鸣,音声和谐。“纯如”“皦如”是雅乐在演奏中呈现的基本样态。《说文解字》:“纯,丝也。”“皦,玉石之白也。”“丝”即同色丝线,指不同乐器发出的音节相互配合,曲调一致。《康熙字典》注“皦如”为“乐之音节明也”,指不同乐器发出的音节不杂糅、不混同,历历分明。“纯如”“皦如”揭示了不同乐器同时演奏时,音色各异又音调一致的现象,可见孔子提倡的是主调音乐。《说文解字》:“绎,抽丝也。”“绎”是将整个蚕茧抽成一根丝,喻指乐器演奏过程中发生的细而不杂的变化,即变奏现象,相当于起承转合中的“转”。“绎如”又指相续不绝的样子,细而不杂的变化持续几次,大雅之乐最终完成。
在孔子这里,独立于政治内容的形式美萌芽了。孔子对旋律和音节的感知十分敏感,“美”开始被作为独立于“真”“善”的音乐评判标准。孔子的主张使审美与政治出现了裂隙,他打破了与传统政治格局同构的单一的“文”的原则,使审美的地位凸显出来。孔子的音乐美学观,建构了一种儒家政治与道德传统,将政治秩序以感性经验的方式内化为人的道德理性。同时,孔子对音乐纯粹审美属性的重视是开创性的,音乐作为最高的艺术形式,对政治意识
形态具有超越性。
[1]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21-25.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春青.论“文言与文人”[J].江西社会科学,2014(2):91-98.
[4]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1.
[5]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2.
[6]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28-129.
[7]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68.
[8]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9]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2.
[10]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61.
2017-04-24
窦琪玥(1994 — ),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I206.2
A
1008-6390(2017)05-0059-05
[责任编辑于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