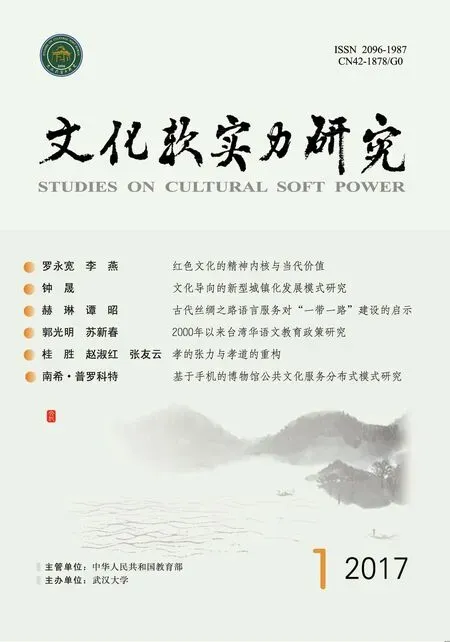孝的张力与孝道的重构
2017-03-29赵淑红张友云
桂 胜 赵淑红 张友云
孝的张力与孝道的重构
桂 胜 赵淑红 张友云
孝是百善之本,是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社会的基石,其内涵集中体现在“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三个方面。伴随时代变迁,产生并发展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有其局限的一面,同时又有其独特的价值一面,应结合时代背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下对其予以重构和创新。从核心家庭回归、物质供养、精神奉慰等三个层面和宣传教育、物质保障、制度设计、人口政策等四个维度对孝道加以维系。
孝 局限 重构 维系
一、“孝”与“孝道”

孝与忤相对。孝与忤的行为对象一样,都是下对上、晚辈对长辈。孝与忤的行为内涵不一样,两者相对、相异。孝的本义是承奉,尊崇。忤的本义是抵触,不顺从。传统社会有五不孝:“世俗所谓不孝则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民间流传《周振逆子变驴》*四川成都文殊院1990年编印《二十四孝果报图(附:忤逆不孝报应图)》,周振逆子变驴:明朝正德年间,平阳有个人叫周振。他自恃有几分才气,狂妄骄横,常常只为家中的小事就辱骂父亲,老父性格懦弱,只好忍受。有一天,周振无缘无故打骂儿子,他父亲过来劝阻,他竟然发怒说:“我打我的儿子,关你什么事?他又不是你生的!”气得老父亲含泪无语。这天晚上,周振在梦中被抓到阴间,阎王罚他变毛驴,周振急忙申辩无罪。阎王斥责说:“你常常辱骂父亲,忤逆不孝,应该坠入畜生道;而且由于你狂妄自大,旁若无人,所以还要蒙上你的眼睛,使你推磨挨鞭打。”周振醒来后,自己说要去做驴就死了。《孝者存逆者亡》*四川成都文殊院1990年编印《二十四孝果报图(附:忤逆不孝报应图)》,孝者存逆者亡:杨璞、杨富兄弟俩与母亲在一起居住,两兄弟都有妻儿,杨璞忠厚孝顺,杨富却天性凉薄。有一天洪水将到,杨富不管老母兄长死活,先用船载着妻儿往北山逃命去了。杨璞无可奈何,危急之中急忙背着老母登上一座小土坡,刚到坡顶,四面洪水滔滔而来,许多房屋都被冲毁。杨璞正为来不及照顾妻儿痛心,忽然看见有个妇女抱着孩子,乘一根大木头漂了下来,他赶快尽力救上土坡,一看正是自己的妻儿。第二天水退了,他四处查问兄弟一家人,才知道他们的船刚到北下坡,被一棵大树倒下压翻,全家都淹死了。
《逆子食鱼化骨》*四川成都文殊院1990年编印《二十四孝果报图(附:忤逆不孝报应图)》,逆子食鱼化骨:长溪人陈元,被女方招郎上门后,靠捕鱼为生。有一天父母来探望他,他见父母来了就满肚子不高兴。母亲觉察到了他的心思,怕他干出令人难堪的事丢人现眼,坐了一会就要告辞回家。媳妇心眼较好,苦苦劝父母留下。第二天陈元去打鱼,捕到了一条大鱼。他得意之极,忽然想到有父母在家,一定会同吃他的鱼,就找个托词,打发老婆送父母回家。老婆、父母前脚刚走,他就急忙把鱼烹熟,大嚼起来,不想刚吃完,他的骨肉就全部化成血水,惨痛而死。原来这鱼叫化骨鱼,逆子吃了它也是恶报,可称得上大快人心。等大量忤逆不孝报应不爽的故事。历史典籍也记载有窃母之财受车裂*四川成都文殊院1990年编印《二十四孝果报图(附:忤逆不孝报应图)》,窃母之财受车裂:前秦建元三年(367),有司奏报说,某人偷窃了他母亲的钱财而逃走在外,被官府抓获,打算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太后(苻坚的母亲苟氏)听说此事,气愤地说:“罪款三千条,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应该把这不孝之子在市朝处死,为什么却要把他流放到远方去呢?难道中国外能有无父无母的地区吗?”于是苻坚下令将不孝子车裂处死。等忤逆不孝的故事。这些故事从忤逆角度警示、规劝人们要承奉、顺从长辈或前辈。
孝与慈相成。父慈子孝,孝与慈具有不同对象。孝是晚辈(后代)尊崇长辈(前辈)的敬爱,而慈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说文解字》认为:“慈,爱也。”慈的本义是指有助人之心。《贾子道术》进一步认为慈有内外之分,对内是“亲爱利子”,对外是“恻隐怜人”,“亲爱利子谓之慈,恻隐怜人谓之慈”。《左传》将慈由爱人延伸到“恩被于物”,提出“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慈由亲人延伸到社会大众、延伸到万事万物。慈与孝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具有同等地位。
基于自然血缘情感关系,儒家以孝为百行之本,孝的三个层次成为中国人立身扬名的潜在动力。首先,孝应“始于事亲”。孟子提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章句》。“事亲”不仅要从物质方面尽心尽力地赡养、侍奉父母,还要遵循“继先祖之志为孝”。*《孔传》。“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礼纪·中庸》。。《礼记》进一步提出,“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其次,孝须“中于事君”。“事君”是“事亲”的延伸,是为“忠”。孔子认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三才》。。“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再次,孝将“终于立身”。《礼记·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孝是自身得以在社会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行为准则,是对国家、对民族建树的大孝,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所表现的“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升华到叔孙豹的“三不朽”。因此,“孝”是中国文化中原发性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中华民族整体生存方式和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宗族的生命与文化继替。
孝道是基于孝的习俗、礼仪、制度、法律等行为规范体系之上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体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孝道有其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方式。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交互中形成了承奉意识,从内容到方式的承奉行为,从个体、家庭到社会的尊崇关系,以及这些行为和关系不断叠加认同的历时性孝道过程。同时,孝道不是一成不变的,孝道的发展性表现在其所包含的长幼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以及包含着自我与外在环境(社会、自然)的统一发展。这种发展的、动态的孝道必须以解决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为指向。
二、传统孝道的时代局限
(一)孝道与法治社会
古往今来,“孝”乃百善之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普遍性与超越性。作为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传统中国以孝立国,以孝治国。“孝治”即以儒家孝道伦理作为社会控制的施法准则,以立法的形式对“不孝”予以严处。孝治是儒家政治仁德精神的体现,是维护家天下的封建皇权统治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百姓仁厚的稳定器。然而,当法律渗透过多的儒家人伦色彩时,孝治原则使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平等性和公正性,成为一味维护长幼尊卑、贵贱高低的道德戒律。
突出表现之一是父辈与子辈在法律面前地位差异过于悬殊。早在《尚书·康诰》中,就已将不孝看作罪大恶极: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袛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史书中此类记载多处可寻,如《孝经·五刑章》载,“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对子辈不孝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反之,当父辈尊长有越轨行为时,子辈却只能亲亲相隐,如此才符合孝乃“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孝经·三才》。的基本要求。
突出表现之二则是以孝治为施法原则的法律裁判缺乏理性。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宗法思想原则下的亲属容隐、存留养亲以及子弟代刑等,甚至存在法律面前孝子孝行为大的“以孝屈法”现象。在血缘、亲情的儒家伦理意识支配下,法外施仁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折狱龟鉴》卷4《宥过》:“陈矫为魏郡西部都尉,是时耕牛少,杀者罪至死。曲周(县)民父病以牛祷,县结正弃市。矫曰:‘此孝子也。’表赦之。”*转引自黄修明:《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276~282页。
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律被赋予浓重的儒家人伦色彩,以孝化民固然能够淳风俗、正人伦,却不可避免地产生“情”与“法”、“情”与“理”的冲突。因此,以孝治国对建立公平、公正的现代法律体系恐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二)孝道与市场经济
孝道是农业文明所孕育的产物,与自然经济、宗法制度有机联系,相互依存。在以家国同构为基石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农业为国家经济之本,而农业之本在于作为社会细胞的小农家庭,而维系小农家庭稳定生产的根本一定程度上说就在于孝道。在小农经济结构下,血缘纽带、亲情人伦成为维系家庭、家族安土重迁、勤勉耕织的关键,继而在国家层面上成为维系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的有力保证。
作为农业文明长期进化的产物,传统孝道对市场经济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孝道的发生土壤使现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无法成长。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视野中,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是资本主义勃兴的精神动力,而重血缘、重尊卑的儒家理性精神促使中国的家庭伦理发展到极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个人主体性和内在潜力不得彰显,重小家轻社会的社会心态成为市场经济孕育与发展的桎梏。其二,作为传统社会信任来源的“孝”不利于市场经济契约关系与诚信关系的建立。基于血缘亲属关系的人情社会,孝道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源,人无“孝”不立,交友“孝”为先。在熟人社会中与孝德之人交友、合作会大大降低风险成本,然而,市场经济是众多陌生人参与其中的信用经济,因而更是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具备良好信誉的同时必须以契约的法的精神作为保障,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唯此才能使市场经济良性运行。而以孝治国的传统社会法制精神的缺失使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更多人情阻力。其三,开放自由、平等竞争精神的缺失。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法制性,面对种种市场风险,追求利润和竞争进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这与传统孝道社会墨守成规、求稳守成、重义轻利的保守心理必然形成抗衡。
(三)孝道与先进文化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孝亲、敬老”是世人理应自觉遵守的人性规范,也是一条普适全人类的人性准则。在孝道的发生发展中,孝道逐渐发生异化。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首先,孝道的外延被发挥到极致。孝德孝行理应是人生之为人的天赋,然而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环境下,孝道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移“孝”为“忠”,且“忠孝不能两全”。遂引发历史上为数不少的愚孝、愚忠行为,有的甚至成为统治阶级标榜孝道以巩固统治的筹码。“孝”由人之本能逐步成为个体自我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的枷锁。因此,由政治利益驱动的孝行孝德失去了孝道本身的真情实感和人性关怀,孝道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道德手段,甚至沦为封建礼教损人利己的工具理性。其次,孝道对人欲过分压抑。传统孝道隐含着子女对父母意志完全的“无违”,这种子辈对晚辈的顺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纲领的具体体现,尤其体现在择偶、繁衍子嗣等方面,对女性人格的压抑尤甚,历史中不乏孝女牺牲个人幸福并承受巨大的道德负担以践履孝道之举。因此,以人为本无从体现。再次,孝道对自由进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孝道是农业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是多数人一生的生活写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父母在,不远游”已成过往,加速的社会流动成为大势所趋,人们不得不改变安土重迁、保守求稳的封闭心态,转而以更积极、更开放的进取心态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因此,传统孝道使人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孝道的重构
孝是家庭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孝道应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最大化的积极作用,矫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共同面临的价值失范、信任缺失、唯利至上等社会心理失调问题。
(一)孝道的欠缺
孝道的缺失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已成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重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比如,我国首个“城市养老指数”通过老年人口总量、老年人口抚养比等指标直观地反映出不同地区对于老年人的保障程度,结果显示测评城市中除极少数城市(如厦门、南京、深圳)外各城市养老指数普遍偏低。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家庭养老不足、子女承担赡养老年人的责任未落实到位也是致此结果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说,年轻子女对孝道的认知、认同不足是孝道缺失的根源所在。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社会目前较为强调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而作为精神文明重中之重的孝道之功能、约束力逐渐弱化,尚未形成一种尊老、敬老、爱老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孝道文化已逐渐发生异化,“厚子薄老”已见怪不怪。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成为家庭核心并受到过度溺爱,老年人特别是体弱多病老人不受重视,家庭人伦代际关系失衡。如在大多中国传统家庭,父母常常穷尽毕生积蓄为子女买房结婚,婚礼花费巨大且极尽奢侈,与平日父母的节俭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由此造成孝心“倒逼”,即行孝“倒逆”。更有甚者完全违背“终于立身”的孝道要求,成年之后无所事事,安心“啃老”,懒散无为还常常责怪父母能力不够,对父母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与诚心。有鉴于此,唤起年轻一代的敬老、爱老之心已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如浙江地区为了培养子女感恩父母、孝敬父母的基本品质,将“记住父母生日”列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之中,作为考核中小学生的指标之一。当然,行孝不应拘于形式,然而没有形式,孝道又将焉附于何?应该说,此举是通过一种中小学生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开启新生代群体孝敬之心的开端,值得肯定与提倡。
(二)回归以家庭为核心的孝
基于传统孝道张扬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现代社会孝道缺失的现状,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共建文明进步的精神家园,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构新型孝道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父母尽孝是建设和谐社会最基本、最首要的要求。在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空间社会流动的加快客观上拉长了父辈与子辈的空间距离,弱化了代际的沟通与交流,及时尽孝困难重重,随之而来的是子女个人发展与家庭养老的现实要求之间出现冲突。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盛行,产生了代际观念上的相异甚至相背,使孝文化的维系遭遇困境。因此,在时代环境下,孝道重回家庭是重构新型孝道的必然要求。
孝的最初形态发生在父辈与子辈之间,是父辈与子辈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父慈子孝”是孝道初始期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对等关系,只是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孝道逐渐掺杂了政治化、工具性色彩。新型孝道的重建,首先要做到的便是重新“始于事亲”,即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赡养。子女对父母孝道体现的第一层面是物质供养层面,包括吃、穿、住、用、行、医等生老病死方面。“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向父母提供吃、穿、用是孝的起码要求。有安身立命之所、舟车行旅之用、病疾治疗之资是尽孝的进一步物质要求。孝的第二层面是精神奉慰层面。“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礼记·中庸》记载:“孝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只是在物质上供养父母,跟饲养犬马没有区别。真正的孝是发自内心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是心理、精神层面上对父母的抚慰与满足,做到包容、尊重和理解父母。此外,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子女能够安身立命对父母而言已是尽孝。安身是前提,是子女可以脱离父母的庇护而独立存活于世的基本能力,既包括身心健康又包括基本的生存能力;立命是目的,是做人做事的秉性和智慧,是历经锤炼的修身明理,落脚到孝之“终于立身”上来。总之,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子女对父母的孝既是子女对父母最真挚的情感回馈,同时也是不断完善自我、砥砺自我的内在要求。
(三)彰显时代特色的孝
孝道的重构,应对传统的孝道有所损益和扬弃。剔除传统孝道中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庐守孝、“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不符合时代色彩的要素,理性地看待“子为父隐”“服孝三年”现象及不同版本“二十四孝”中的“弃官奉亲”“卖身葬父”“郭巨埋儿”“恣蚊饱血”“卧冰求鲤”“尝粪忧心”所张扬的极端孝行故事。
新型孝道回归核心家庭不是只顾个体家庭的重“私”轻“公”,不是摒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而是从根本上、源头上教育、引导民众首先扮演好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之角色,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有能力实现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奉献。从“小孝”为家到“大孝”为国,新型孝道须弘扬民族精神,彰显时代特色。孝,始于事亲,“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章第二》。,这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链评判标准的孝;其次,推己及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社会和谐,呈现一片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美好景象;最后,孝的基点依旧回归到“修身”“立身”的根本上来。可以说,孝道是贯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脉络。孝的多重内涵使孝道具有延展性,体现了由微观至宏观和微观、宏观的交织。结合时代精神来看,“孝道”恰恰与包含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作为引领中国人奋发有为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既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对当代价值体系的探索和要求,又需要广大社会民众自下而上的对核心价值观产生认知与认同*孙伟平:《〈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与建构〉评介》,《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3期,第159页。。传承几千年的中华孝道是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基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为维系与时俱进的新型孝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持和发展空间,而新型孝道既是服务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路径。
总之,新的时代条件为子女尽孝提供了多元化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新型孝道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被创造的过程。新型孝道既要充分考虑个体家庭的孝念孝行,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对社会的价值最大化,而维系新型孝道的现实环境既从深层次上激励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将使子女尽孝面临更多的现实挑战和道德考量。
四、孝道维系的维度
所谓孝道维系是指维持孝载体已建立的各种关系,使世人不断重复孝行或孝道的过程。孝道的维系一方面在于使世人能够渐渐将本身言行与孝念保持一致,通过多种举措,不断强化孝道的认知、认可度;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维系孝道的方法不应也不尽一样,需要对孝道做出切合社会环境与社会转型的重新阐释,顺应时代需求及社会发展。因此,孝道须与时俱进,孝道的维系应注重从宣传教育层面、物质保障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人口政策层面等四个层面着手。
(一)孝道维系的宣传教育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解构着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人们的价值观变迁可表现为: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从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孙伟平:《〈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与建构〉评介》,《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3期,第159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加强民众对孝道的认知与认同,须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良好的家教、家风是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有效途径,突出体现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上。作为子女成人成才的起点和基点,父母在对子女的德育教育中扮演三重角色:榜样、老师、朋友。作为榜样,父母对其长辈的孝念孝行对子女有润物无声的作用,父母必须自立立人,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教育、启蒙子女先做人后做事的道理,培养子女尊敬老人、孝敬老人的优良品质。作为老师,父母要善于观察子女的言谈举止,既要积极鼓励子女的嘉言善行,又要及时纠正子女的劣言劣行,引导和培养子女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思想意识。作为朋友,父母应与子女一同成长,共同进步。尊重子女,帮助子女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真诚平等地与子女沟通交流,培养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因此,良好的家庭教育首先要求父母从自身做起,改善自身的道德素质和教育观念。
学校和社会对孝道的维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学校是子女接受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子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关节点。学校对孝道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主要体现在规范、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尤其重视对学生思想品质的教育。学校通过课堂教育、定期考核、假期实践、举办孝道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学生的敬老、爱老之心。此外,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既要普及传统礼仪类教育,通过仪式感的象征性唤起子女的孝道意识,增强自身约束力,更要注重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诚意与敬重。另一方面,社会是每个人毕生学习其中的大课堂,社会对孝道的维系将对每个公民产生影响。社会应加强舆论监督与劝勉作用,通过报纸、书籍等平面媒体与电视、广播等视听网络媒体的结合,营造褒扬孝念孝行、贬斥不孝言行的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家庭、学校、社会对于孝道的维系缺一不可,三者的合力必须持久而均衡,偏颇任何一方的作用或夸大任何一方的有效性都将事倍功半,导致孝道的缺失,进而导致整体性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
(二)孝道维系的物质保障层面
孝道的维系必须将尽孝所需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考虑在内。对父母尽孝主要体现在回报父母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舒适晚年,这必然与现阶段的养老模式关系密切。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财富积累不足,加之几千年传统孝文化的浸润,现实国情与文化底蕴决定了在我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在现阶段依然是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孝道是家庭养老得以持续的心理积淀、文化动力,家庭养老模式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庭观的体现。家庭养老在老年人精神的慰藉和照料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对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家庭养老意味着社会养老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意味着子女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对老年人的物质供养,其一体现在衣食住行上,衣食住行是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二体现在医疗救助方面,也是家庭供养的主要压力来源。由于老年人自身身体机能的退化,老年人通常是疾病高发群体及高住院率群体。对患病老人的供养主要从人力、物力、时间、精力等几个方面考量着子女的孝念孝行,尤其对家庭经济状况有较高要求。随着社会物质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政府介入、社会力量在老年人养老中所发挥的功能应逐步强化,主要体现在共同分担养老责任和提高养老保障程度、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上*陈赛权:《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人口学刊》2000年第3期,第30~36页,第51页。。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服务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跟进落实相关养老政策、福利政策,降低单一养老模式的风险因子,完善机构养老的服务质量和部门监管,通过社会合力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在具体实践中摸索经验,创新实践,结合具体国情和现实条件,多元化、多角度地探索一条特色养老之路,使孝道的维系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孝道维系的制度设计层面
孝道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道德情感,理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信念,但是,为了减少和避免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缺失现象,在接受舆论监督和公众评判的同时,孝道必须有一定的立法来保障、监督孝道的施行。当下,我国立法方面对孝与不孝既无严格分野,亦无相关奖惩激励手段。国家增设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为法定节假日的制度安排旨在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视,并通过营造特殊的时空场域激发人们对家庭、对父母的关怀与感恩,触动中华民族的感性情怀,这不失为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倡导途径,然而此举恐缺一定的可监督性,在传统孝道遭遇现代冷场时难免力不从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加强孝道的维系势在必行。
201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写进立法,遂引起社会各界对此举众说纷纭。多数认为对老人尽孝作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被写进法律条例不得不引起社会的反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家庭成员不断通过职业培训、升学外出、婚姻流动等人口迁徙方式流出原生家庭,并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家族主义功能逐渐弱化,子女在对父母尽孝方面存在时间、空间、物质、精神等方面不同程度的不足与问题,导致家庭凝聚力和家庭整合力不断削弱。子女对父母尽孝甚至仅靠“自觉”或“领悟”,事实证明,当子女的道德底线不足以维护老年人应有的体面与尊严时,必须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因此,为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除了道德舆论的监督,必须通过制度约束来满足老年人最基本的物质、精神需求,制度约束是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必要武器。
关心孝敬父母不是机械性、工具性、程序性地“完成义务”,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理解、关爱与包容。子女尽孝与否除了应有一定的制度约束,还需有相应的激励措施,以做到奖惩结合,且“奖”应重于“惩”。具体来说,可参考古时传统,按照家庭—社区—单位—地方的推选路径,定期逐层推选出不同级别的孝子孝女,国家和社会对入选者给予相应的优待和褒奖,对评选出的不孝子女给予相应惩罚。评选依据以父母亲身感受为主,辅以大众可量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此举意在一使孝念孝行内化于人心,成为常态;二使道德舆论对不良社会风气的监督力度得以加强,着力构建健康文明的乡风环境。
(四)孝道维系的人口政策层面
人口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我国传统孝道的维系产生影响。在我国,计划生育既是一种个人行为又是一种国家行为,该政策有效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减少了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然而时至今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未富先老的现实业已显现,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等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孝道的维系需要人口政策的支持。目前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有利于改善现有的家庭人口结构,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同时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也是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子女数量的适当增加分散了一部分父母的注意力,降低了个体子女受到过分关爱的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分享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等;其二,多子女可共同分担养老压力,缓解独生子女的赡养负担,子女可根据现实情况灵活照料老人,为老年人享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一定的可选择性;其三,多子女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创造条件,一定程度上减少“空巢家庭”比例,同时增强家庭的抵御风险能力,改善失独群体现状,缓解老年人的物质困难和精神困境。
应该说,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不仅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举,更是重构孝道、增强人们幸福感的应然之举。然而,该政策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公众还需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和生养成本等诸多现实问题,尚需国家、社会、政府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的通力合作与支持。该政策的预期效果虽不能立竿见影,但从国家现实和社会长远需求来看,无疑是一种理性选择。
五、结 语
中国传统孝道的发生土壤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小农经济社会,新型孝道是在吸取传统孝道核心意涵的基础上融入时代色彩的再创造。于个人而言,孝道是培养人们感恩之心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经济的高度发展,金钱至上、利益至上成为一股暴戾之气横行于社会,我国社会的精神文明、道德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父母爱子女是天性的彰显,子女爱父母更是人性的体现。懂得感恩,是人立身处世的前提。于社会而言,孝道仍是现代家庭和社会应当遵守和实践的道德伦理规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不变的价值追求,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事关每个家庭成员的发展,甚或事关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由尊敬、爱护自己的父母出发,进而形成关爱他人的社会风气。当孝风孝行“推己及人”时,孝的意义得以最大化。
The Stretching For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lial Piety
GuiS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ZhaoShu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ZhangYouyun
(Hubei Masses Art Centre,Wuhan,China)
Filial piety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virtues,and it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both family and nation were dominated by patriarchal relations inChina. The essence of filial piety centralizes on three aspects:started with the relatives,then pledged the loyalty to the emperor,and finally fulfilled with the moralit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with the time goes,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which i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in the rural society has both its own limitations and its unique value in modern times. So filial piety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nd innova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demand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is essay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maintain the filial piety from three levels:returning to the core family,material support,comfortable spirit support;and in four dimensions:publicity and education,material security,institution arrangement and population policy. Key words:Filial Piety;Limitation;Reconstruction;Maintain
10.19468/j.cnki.2096-1987.2017.01.008
桂胜,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民俗文化与现代化。 赵淑红,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俗文化与现代化。 张友云,湖北省群众艺术馆馆员,《中国文化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