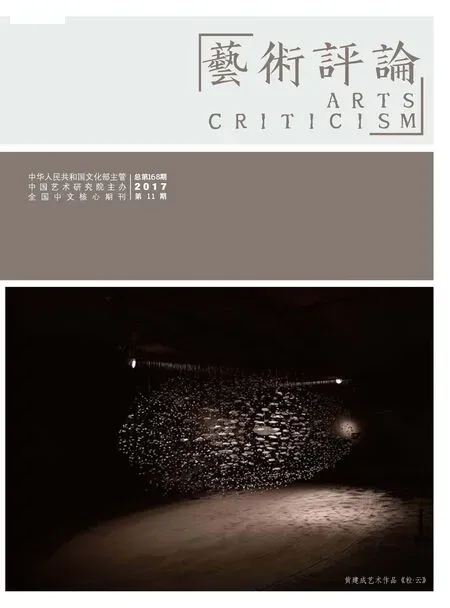芭蕾语《敦煌》
——观芭蕾舞剧《敦煌》有感
2017-03-29王洁琼
王洁琼

一、古与今的交错
舞剧讲述的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敦煌与巴黎的故事,但在这一时间线外的另一条时间线却是从十六国至元朝那漫长的数百年莫高窟开凿与壁画绘制历程。两条线索并行发展,一厢是莫高窟保护者热火朝天的劳动和巴黎街头的闲适生活,一厢是沙漠深处石窟艰苦卓绝的绘制工程。古代线索历数莫高窟建造保护的艰辛,展现无数匠人心血铸就的绝美飞天;现代线索展示新时代的年轻人舍生忘死地保护这珍贵艺术宝库,以及在这保护过程中的欢笑与泪水、爱情与友情。敦煌既是故事的发生地,又是两条线索交汇之处。从古至今,无数热爱敦煌莫高窟、热爱这壁画艺术的人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抛洒在这片漠漠黄沙中,对美、信仰与艺术的追求与奉献贯通古今,穿越时间的长河而永存。
以上是舞剧时间上的古今交错,而在更深的层面,这是古老的壁画艺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芭蕾与现代舞台技术的交错,古老的艺术在多重声、光、电现代技术的映照下,在舞台上展现给现代的观众。交响乐团的现场配乐使本场舞剧堪称真正的视听盛宴、舞台灯光的巧妙设计让观者连连赞叹、现代科技武装下的舞台装置使舞剧表现如虎添翼,但回想敦煌飞天舞的复现,不禁又使人感叹,尽管复现了一部分飞天舞的动作,但其实真正的飞天舞是怎样的,我们恐怕很难再窥得。而当被片段式复现的敦煌舞姿又被更零碎地改编化入芭蕾舞中时,原来的神韵与内涵再度被简化,只变成了一些散落的符号,缀在舞剧华丽的锦绣上,变成了一种点缀而失落了其原生的叙述语境。
二、虚与实的交织
谈及舞剧创作,真实与虚构是一般创作者使用频率较高的表现手段之一。提及舞台艺术创作的虚构,“第四堵墙”(Fourth Wall)这一概念似乎无法绕过。第四堵墙的接受是虚构工作和观众之间解除嫌疑工作的一部分。它允许观众在他们看表演的时候感受虚构。这是将演员与观众距离拉开的必要手段,让观者得以处在一个安全距离统观全剧。在大多数写实剧作中,“第四堵墙”都起着积极作用。在《敦煌》这一作品中,“第四堵墙”始终存在,作为保证剧作虚构性的重要因素,创作者甚至将“第四堵墙”实体化,创造出一个更为虚幻的迷离世界,让观者的不真实感愈发强烈,由此产生不一样的审美体验。而在舞剧表演中,创作者让“第四堵墙”在数个场景中显现——一张半透明的纱幕挂于舞台前,壁画世界里的漫天神佛于此中若隐若现,虚构性随着“第四堵墙”的显现而更为强烈。
此外,舞剧《敦煌》故事中还有保护者们的故事现实与飞天、菩萨们的神话想象,虚虚实实,交错迷离。前一刻还是保护工作者们热火朝天地展开保护工作,后一刻便是莫高窟的飞天与菩萨游走四方;前一刻是吴铭呕心沥血地临摹壁画,下一刻便是画僧带领他神游壁画中的极乐世界;前一刻是念予与吴铭在壁画前暗生情愫,下一刻便是供养人的虔诚朝拜……虚实两条线索的设计使得舞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叙述更多的内容,也大大增加了舞剧的可看性。不过虽说两者间的交错与穿插构成了作品的独特交织性时空结构,但细想起来,过于频繁的穿插削弱了舞剧的完整叙事能力,也削弱了作品的连贯性,或许适当减少一些两个世界的频繁变换更有利于作品脉络的明晰。
三、东方与西方的交汇
初闻中央芭蕾舞团要排演大型芭蕾舞剧《敦煌》,笔者便略为惊讶,须知敦煌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最灿烂华美的一章,也同样是东方文化的瑰宝,而芭蕾作为西方文化的明珠,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审美,如何将如此纯粹的东方神韵与西方形式结合起来,着实令人好奇。而在观剧时,笔者发现剧中不仅有敦煌飞天与芭蕾舞的东西碰撞,还有剧中故事发生年代的中西碰撞。
故事发生在敦煌与巴黎两地,敦煌的黄沙漫漫、神秘古老与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巴黎在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序幕中画僧描绘的飞天翩然欲去、辽阔的大漠艳阳高照、莫高窟中的壁画瑰丽繁复、20世纪40年代的保护者们衣着朴素……而此时的巴黎街头却涌动着衣着精致的红男绿女,交谊舞、照相机、小羊皮手套、小提琴充斥着眼球。中国青年们欢快的Battement tendujete和Battement frappe伴随音乐播撒他们的热情与青春,巴黎人优雅的轻步缓行与交谊舞动作的融入无不展示着他们的从容闲适。两个世界的碰撞凸显了那群莫高窟保护者的伟大,艰苦的环境与生活条件扑不灭莫高窟保护者们的热情。或许这里没有宽阔平坦的马路、没有玉树琼枝遮挡烈日,但充满色彩斑斓壁画的莫高窟却是他们的天堂。
而本剧在更深层面上的东西方交汇碰撞则是东方的石窟壁画艺术与西方芭蕾艺术的碰撞。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佛像与飞天形象无不体现着东方的审美情趣:恬淡冲融、舒展飘逸,飞天们的动作也多刚柔相济、曲线鲜明,是柔、韧、沉、曲的结合。飞天们手形丰富多彩、纤细秀丽,极富中国古典美;手臂姿态曼妙多变,且手腕和肘部常呈棱角;足部则多为赤足,其基本形状为勾、翘、歪等;体态则基本为下沉、出胯、冲身形成的三道弯。出胯动作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推胯;一种是坐胯。推胯是在提胯惹出上推出,线条较硬,动作有力;坐胯有向前和向后的不同方向,动作柔和,且较多使用长绸、腰鼓、琵琶等道具。而西方传统下的芭蕾舞则是追求对人身体的极端规训的产物,动作对优雅与对身体的极度控制的追求使得芭蕾舞相对敦煌飞天舞表现出紧张、敏捷与几何美学的强烈呈现。“开、绷、直、立、轻、准、稳、美”作为芭蕾舞的金科玉律,将古典西方追求“活雕塑”与“看得见的音乐”的舞蹈美体现得淋漓尽致。两种古典舞姿的迥异也表明了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巨大审美差异:西方对美的探讨确立于温克尔曼探讨追求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是对美的形式与美的真实可感性的强烈要求,于是西方艺术追求对真实的刻画与描摹,追求精致的形式。而古代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则是追求“不思辨”的美,这渗透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敦煌壁画虽源自佛教,但也不可避免地被这种传统同化了。加之佛教对“超脱”的追求,导致佛教艺术也呈现出恬淡飘逸之感,举手投足不会强调对身体的规训,而是以身体为媒介表达对佛的尊奉与对世俗的超脱。
作为芭蕾舞剧的《敦煌》,在用芭蕾舞动作表现敦煌飞天时,舞蹈演员的手部、肘部与体态多参考了敦煌飞天形象,而腿部、足部则仍使用芭蕾传统动作。当舞蹈演员保持静止时尚可,但当舞者们上半身是敦煌飞天舞姿的变化流转时,下半身却是经典的芭蕾动作,这使得舞剧中的飞天舞姿成为一种非常奇特的混合体——上半身的敦煌飞天与下半身的芭蕾舞者。迈出以芭蕾表现敦煌飞天舞姿的一步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要将东方舞蹈形态化用到西方舞蹈中,不能只截取特定的动作,还要兼顾舞者呈现出的整体形象与气韵风致,不然只能在两者之间的夹缝中辗转,得其形而不得其神,造成遗憾。
纵观《敦煌》全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卓越的气氛营造、优秀的服装舞美设计以及与舞蹈配合非常紧密的音乐使得作品呈现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是其最好的证明,且作为芭蕾舞创作与中国古典舞蹈形象的融合的一次尝试,《敦煌》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创作者与表演者数次前往敦煌当地学习采风,虚心听取各方意见进行创作也十分值得各界学习,但赞叹之余我们仍不能忘记其瑜中微瑕:两种审美传统下舞蹈融合程度的欠缺、叙述内容详略安排欠妥、创作心劲该如何分配等问题仍值得大家反思与改进。而只有找出缺点,不断修改更新,只有不断尝试、不断思考、明确方向、深扎稳打,我们舞蹈艺术或者更广泛的文学艺术创作才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