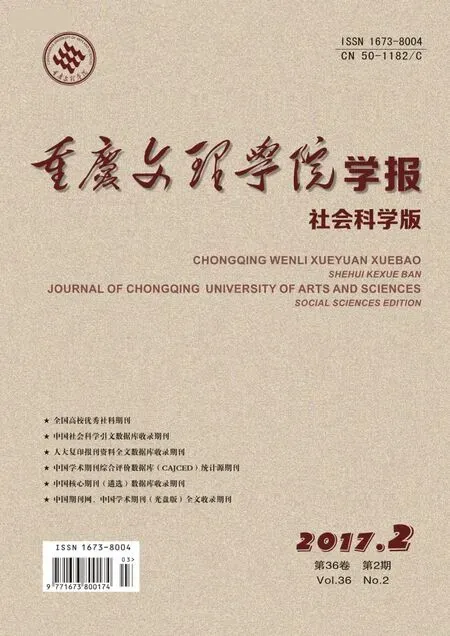作者的消逝读者的诞生
——对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探讨
2017-03-28何芳菊
何芳菊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沙坪坝404100)
作者的消逝读者的诞生
——对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探讨
何芳菊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沙坪坝404100)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出现,不仅动摇了传统文论中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地位,也暗示着巴尔特向后结构主义方向的转变。巴尔特在对作者身份问题的探讨上,延续了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中反主体性的传统,力图推翻在文学领域中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话语体系。在传统的文学历史发展中,无论是作者还是批评家都曾以解读文学作品内在的蕴含意义作为阅读的最终目标。当巴尔特明确提出将作者从文学作品中剔除时,使得我们对文学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文学本身。文学作品不再是提供某一种单一意义的载体,读者对文本的解读不再从作者身上寻找参照物,而是享有更为自由的文学空间,开启了新阅读理论的篇章。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语言;文本;阅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结构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日渐暴露,一批理论家逐渐走向了后结构主义的道路,他们开始反抗中心,反抗主体,反抗权威。巴尔特于1968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便是文学领域反中心主义的实践。在传统的文学话语模式中,作者往往充当作品的生产者,而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的附属物。与之相应,传统的学院批评方式,则立足于实证主义哲学,致力于从作者的生平及思想的角度找到与文学作品相契合的共同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文学作品的真正意义。然而,巴尔特指出,给文本一个作者,实际上不过是对文本加以限制,只有将作者去除,才能将关注的焦点真正回到文学本身。巴尔特对作者身份的关注早在与巴黎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的争论中就有显现,而后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彻底地表达了他对作者的抛弃这也与后结构主义中的反中心主义观点遥相呼应。巴尔特对作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从后结构主义反主体性的角度出发解构了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话语体系,反对将作者视为文学作品的制造者及根源。他提出将作品交给写作,文学作品不是在作者的支配下完成,而是在写作行为中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特提出的写作并非强调一种创作的实践方式,而是需要读者积极参与的阅读行为。读者的阅读不再是被动地寻找作者埋藏于文中的价值意义,而文学作品也不再是封闭的文本,而是可提供多元意义的言语活动。作者如何消逝,文学文本如何打破封闭的束缚,读者如何能够积极参与文学的创作,巴尔特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解构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话语体系
巴尔特指出:“作者是现代人物,是我们社会中的产物,它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带着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到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个人信仰,从中世纪社会产生出来。”[1]由此可见,作为现代人物的作者,是在社会历史及文学发展的变化中塑造出来的,不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作者的身份地位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即古典主义时期,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柏拉图采取的是理式论摹仿说,即诗人和艺术家只对事物的外形及影像进行摹仿,文学艺术不过是理式摹仿的摹仿,不能抓住真理。除此之外,他强调诗人也只有在迷狂状态下才能接收到来自神的灵感,得到培养人理性的诗。由此可以看出,柏拉图将精神的理式世界看作文学艺术的真正来源,而作者的地位却极其低下。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则注重真实的现实世界,他认为文艺是人行动的摹仿,可以反映世界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甚至比历史更富哲理。而在文艺创作上,亚里士多德强调将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区别开来,艺术创造更注重于一种合情理的不可能。明显地,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作者更多的创造空间,作者拥有相对的自主性。但是,二者都将摹仿理论作为诗学的重要基石,多受制于现实世界的行为范式,作者的主体地位并不高。第二个阶段即近代时期,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潮影响之后,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两大哲学派别在相互争斗中各自丰富起来,关于人的问题逐渐突出,人们将目光转移到对自身的关注。其中以康德为代表,他指出艺术犹如游戏,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自由而凭借想象力进行的虚构。“艺术活动的本质是人的有意图的建筑于理性之上的自由创造,艺术作品是人的有意图的建筑于理性之上的自由创造的结果。”[2]康德强调人的参与是艺术作品成形的必要来源,肯定了作者和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意义,作者逐渐成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和意义最终阐释的标准。此时,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话语体系也基本形成,作为理性主体的作者,经常将美的艺术作用于人的反思判断,企图从个人的感性经验中获得理性的知识,从而推进人类的精神力量修养,起到精神标准的指引,达到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以后,作为理性主体的自我逐渐被抛弃,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不再企求它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影响,而更注重于自我的理解。带领我们倾向于感性自我的人有柏格森和弗洛伊德。柏格森哲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文学理论基本概念都是以直觉为基础,它强调艺术直觉的超功利性与非理性。他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功利心和个人利益的实际需要往往会驱使我们看待事物着重于实际效果和实际利益,而只有艺术家才能掀开这帷幕看到背后的实在,因为艺术家具有与生活较为脱离的心灵,它就是直觉产生的基础。在此,我们一方面看到柏格森与理性认识逻辑的差异,同时也看到了他过分强调肯定艺术家或作家的天分,将作者的身份归于更个人化的神圣地步。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主张人的精神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人的一切行为最终是由性本能驱使。因此,作家或艺术家通过艺术创造的方式获得本能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同时也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赞扬。弗洛伊德强调了文学作品是由作者的性本能驱使而产生的满足自我的私人物品,不过文学作品在现实生活中的流行也帮助了作者在社会中的巩固。虽然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性主体的作者身份,却也是对作者个人身份的肯定。他们将作者身份的理性自我逐渐转移到感性自我,但仍没有改变作者作为文学作品来源的神圣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了这一地位。
然而,理性主体的崩塌,也导致了人们对传统先验主义的质疑。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反对基督教神学,是对以“上帝和人”为话语中心的神学体系的解构,从而达到解构以基督教为根基的理性文化。福柯在历史中表现从人之死到作者是什么,指出人是被设想、被建构、被哲学配置和产生出来的。作者不是作品的源泉,而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作为一种话语功能而不是话语实施者存在。“德里达从语言学的差异原则入手摧毁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工作”[3],在差异系统中符号间没有等级,没有决定论,只有差异,他们进行平等的自由嬉戏、自由滑动。
人们公认作品中不可少的东西:个人的天分、艺术技巧和人本思想,不过是我们对神话的真实仍保留着兴趣与爱好。然而,现在神话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盲目地崇拜了,人们需要的是打破一切限制,找到更多自由的空间。“巴尔特处决作者,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颠覆这种传统的作者研究法。”[4]他将作者的身份进行消解,提供一个开放的文本让读者在一个平等的平面内,与符号进行自由的交流。正是因为如此,作者不过是现代人物,是社会中的产物,而如今人们不同的见解也正在推翻着作者与作品这“父与子”的固定关系。
二、文学作品对符号本身的关注
巴尔特在《作者之死》的开篇中,通过引入巴尔扎克在《萨拉辛》中描写女性形象的语句,展开了他对说话者身份的质疑。巴尔特采用四个疑问句式,将说话者的身份投射在小说主人公、生活中的巴尔扎克与作为小说作者的巴尔扎克这三者之间,也正是由于分歧的存在,使我们发现文本的说话者并不能总是归咎于作者。在这里,巴尔特进一步给出他的答案,即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说话者是谁。因为,一个事实一旦被陈述为书写形式(文学作品),就是对声音的毁灭、对说话者或是作者的毁灭,无法找到一个确实可靠的声音或人物来交代所有的事实,剩下的只有符号本身。显然,从巴尔特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了巴尔特对文学本身的重视。
早在1963年,巴尔特与巴黎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就学院派批评和新兴起的解释性批评的问题产生过相当激烈地讨论。针对皮卡尔的攻击,巴尔特于1966年发表了《批评与真实》一文,明确地阐述了他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巴尔特反对传统的学院派批评,指出该批评崇尚实证,将作者生平及思想的变化作为文学作品意义的来源,力图通过达到文学作品与作者主体性意愿相契合的模式来论证批评的正确与否。学院派批评继承了古典——资产阶级社会长期以来把言语当作工具或装饰的传统,长期以来对文学语言本身的关注集中在修辞学的领域。他们简单地将主体与语言的关系看作是内容与表达形式的关系,往往希望通过言语活动的呈现抓住一个能表达某种价值意义的主体本身。对于文学作品中是否存在主体的问题,巴尔特在《批评与真实》中通过对文学的定义做出了回应,“文学的定义正是如此:加入知识经由形象去表达同样实在的主体或客体,那么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只要有违背良心的言语就足够了。”[5]由此可见,当我们选择只追求一种文学价值或是一种文学意义的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文学,因为我们并不关注文学自身,而是为了寻找一种主体性价值,文学变成了表达某种文学意义的工具。其次,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书写下来的象征符号是稳定不变的,而社会意识以及社会赋予象征的权利却是可变的。这表明作品有多种意思,每个时代都掌握着自己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标准。当作品不再是历史事实,它便成了一种人类学现象,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以彻底解释它。显然只追求某一种价值意义的批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意义掩藏在文学作品中等待人们去挖掘,意义往往来自各种社会文化的不同解读。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明白只想抓住文学作品主体性的批评方式只会加剧对文学本身的毁灭,并且事实证明文学作品并不存在一种恒定的文学意义。当人们对文学作品的主体性价值追求的希望幻灭时,人们将以何种姿态面对文学作品呢?巴尔特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性的批评方式,即回到文学本身。
自从人们发现语言的象征性的时候,便把言语视为符号或真实,对语言的丰富认识加剧了语言学的发展。同时,巴尔特也借助了语言学中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学本身。语言相当于一整套系统可知的语法规则,而言语则侧重于各式各样的言语活动,言语活动的无限性致使人们无法对所有的言语活动进行充分的把握,必须借助语言规则用以掌握言语的有效性[6]。因此,当前语言学的任务不是描写句子的意义,而是侧重于描写句子的合乎语法性。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也是一样的,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某一意义应该或曾被接纳,而是要说明某一意义为什么可能被接纳。文学作品所依附的象征语言在结构上来说是一种多元的语言,其符码的构成方式产生了整个作品的多元意义。因此,“一部作品是不朽的,并不是因为它向不同的人提供单一的意义,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几种不同的意思,尽管这个人在不同时间里总是说着同一种象征性语言:作品提供意思,而人则支配意思。”[7]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致使文学作品的产生由作家扩大到了社会,而意义是由人类象征的逻辑可以接受的方式而生成的。由此,阅读方式也应该相应地改变。批评家的阅读就是把他的语言加在作者的语言之中,把他的象征加到作品中去,他并不是为了表达而去歪曲客体,他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谓项。他不断把符号扯断、变化,然后再重建著作本身的符号。信息被无穷地反筛着,这并非某种主观性的东西,而是主体与语言的融合,因而批评和作品永远会这样宣称:我就是文学。批评家所揭露的不可能是所指,并未真正指出形象最终的真实,而只是揭露一个新的、本身也悬而未决的形象。无法找到作品的实质,因为这实质就是主体本身,也就是虚无。巴尔特通过将语言学的知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上,将文学作品从对追求意义的征途转变为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符号上来,将封闭的文本向多元化发展,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可塑性。
三、现代写作方式对作者的抛弃
当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话语模式被打破,当对文学作品本质属性的认识被改变,那些曾被视为“作者”的先锋者们对自己也进行了一场革命。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柏格森热”,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广泛引起人们的兴趣,同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逐渐进入法国文学的关注范围。人们开始改变了对实证主义的热情,而热衷于关注一种内在的真实。
首先,象征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马拉美和瓦莱里,他们在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都强调一种纯诗理论,纯诗应不带有任何功利的实用目的,而是脱离外在世界的自足的审美形式。马拉美和瓦莱里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严格的区分,由此,诗歌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诗歌语言往往充满了模糊性、暗示性和象征性,这种不确定性也造就了诗歌意义的多元化,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意图。诗歌作为一种纯粹的美学境界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显然对诗歌的解读也就不能单纯地依靠对作者的解读来达到实现读诗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要求纯粹的心灵状态,而诗歌要成为纯粹的完美艺术作品,必须是非个人化的,不能是诗人心扉的披露和个性的体现,应该抹去个人的一切。诗的意境应该是人类共同向往的审美世界,这种共同的对美的追求是诗歌产生的真正源泉。因此,诗歌应超越事物的外在形态,从而追求其纯粹的本质。从马拉美和瓦莱里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来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取消作者在写作中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唯我独尊的现象。他们文学作品中的作者不再是个体行为,并且也摆脱了现实社会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更多主动的阅读空间。其次,现代小说及意识流代表人物普鲁斯特,在艺术创造要求中,他强调对唯物主义创作方式的抛弃,文学不是在记录事物的外表,对事物仅作电影式的展示,这是离现实最远的虚假的现实主义。在其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中,小说所呈现的不是外部世界的社会文化背景或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的描绘图纸,它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人的身上,乃至于人的内心世界。文中借助潜意识、不由自主的回忆、梦幻和想象等方式,不断交叉地重现逝去的时光。普鲁斯特打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故事不再以情节的变化发展为主导,而是根据小说人物的超时空潜意识,将读者带进小说人物的世界。文学创作摈弃现实生活中粗陋的表象,而去发掘具有永恒性的东西,以求达到内在的真实。另一方面,在小说中叙述者、主人公和作者采取同名的方式,从而将作者身份进行打乱,提示着艺术的创造主体也不再是社会实践中的人,他是另一个自我、深层的自我。普鲁斯特在小说创作中将作者身份进行有意识的模糊,就是解放长期受制于作者中心主义的文学研究模式,期待文学的阅读遵从文学的内在真实,而不是集中所有的精力致力于探究外部世界。最后,主张通过精神分析寻求文学真实的超现实主义团体,他们反对在文学创作中受理智的任何监督,文学创作应该是纯粹的精神自动反应,心理的活动完全处于无意识的支配下以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任何形式,通过自由的联想方式表达思想。同时,他们对创作主体没有严格的要求,在创作中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大家共同收集材料、共同思考和写作。由此可知,他们既排除对生活现实的关注,也拒绝将作者看成神圣的权威来源。他们在文学的创作方式中更加注重梦幻与现实,意识与无意识互相渗透、互相贯穿的方法,而文学作品作为精神的自由写作将作者从理性主体的神圣地位打落下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逐渐步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带来能源的大肆开发,经济的繁盛促使交通等新兴部门迅速增长,然而,在物质资源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人们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另一方面,海外殖民地的争夺致使各国冲突加剧,而法国国内大资产阶级却鼓吹战争,导致国内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上的强势并不能掩盖社会的深层问题,步入现代创作方式的法国文人们通过他们的笔触呈现了他们的所有感受和希望。他们都明显地表现了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实证哲学被精神分析所取代,人们关注的重点从外部的世界转移到内部的真实。这也影响着人们对作者的观念变化,他们不再推崇以个人为主体的作者崇拜论,对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模式进行深刻的冲击与反思。现代写作方式要求一种比现实主义创作更为真实的方式来取得文学作品的内在真实,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所谓权威的信任,作者不再承担起对整个社会的引导作用。他们对作者的失望,也显示了他们对社会的态度。
四、结语
当我们一提到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关系时,人们总是会不经意地想到同时代盛行的以伊赛尔和尧斯为代表的文学接受理论及以费希为代表的读者反映批评,而对阅读的研究则是从文本空间和读者视野的角度出发,极少从作者的角度为读者寻找其地位。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不仅消解了作者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为读者的自由阅读打开了新的方向。“巴尔特的作者消失于语言中,逃逸于文本外,让位于读者”[8],他对作者的发难,不仅使他在理论上摆脱了传统的主体中心主义,而且也直接促成了巴尔特对文本本身及读者的极度关注,暗示着巴尔特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方向的转变。其次,巴尔特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种言语的陈述,必定受到语言系统的约束。写作作为一种言语活动,也就决定了在言语陈述中话语的构成只认识主语而并不认识作者。最后,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中,不论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拉美与瓦莱里,还是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特及超现实主义团体为代表的先锋者,他们在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上,都主张对作者的身份进行一定程度的消解,这里的作者不再是文学作品的来源,作者作为个人的形象不再具有对作品解释的神圣权威。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从以上三个角度对作者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也为读者地位的提升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对巴尔特《作者之死》的再度探讨,不仅见证了作者身份的变化,而且也让我们重新将读者的身份进行再次认识。文学作品打破封闭的意义呈现模式,应为多元化意义提供更为丰富的符号象征,读者的积极参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阅读观。
[1]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505-513.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7-524.
[3]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9-141.
[4]潘冬梅.关于罗兰·巴尔特“作者死亡论”的思考[J].中国文学研究,2013(3):15-18.
[5]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M].温晋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76.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0.
[7]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94-301.
[8]史凤晓.“作者之死”的再审视[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5-110.
责任编辑:罗清恋
The Death of Author and the Birth of Reader——Discussion on the The Death of Author Written by Roland Barthes
HE Fangju
(School of Litera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Shapingba Chongqing 404100,China)
The publishing of The Death of Author written by Roland Barthes not only influences the author-centered writing position,but also implies the transition of Barthes to the post-structuralism.In terms of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writer’s identity, Barthes carried on the tradition of anti-subjectivity in the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and attempted to overthrow the author-centered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literary field.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y,both the author and the critic have to interpret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literary works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reading.When Barthes explicitly proposed to remove the author from the literary works,the focus of our literary attention was finally transferred to the literature itself.Literary texts no longer provide a single sense of the carrier,and the readers enjoy the text without the author who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literary texts.A more liberal literary space is opened,and then a new reading theory is being generated.
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Author;language;text;reading
I026
A
1673-8004(2017)02-0046-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2.009
2016-09-22
何芳菊(1991—),女,湖南永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