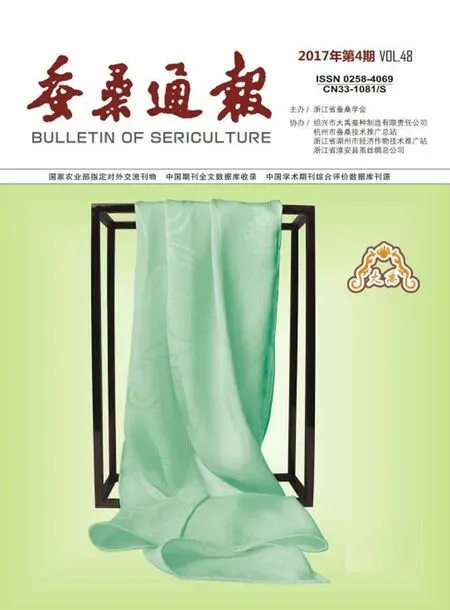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蚕业
2017-03-26蒋猷龙
蒋猷龙
周族姬姓,最早兴起在关中平原的陕西省武功县境内,后来迁徙至今甘肃庆阳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杂居。到了公刘的时候,才迁到豳(今彬县)等地定居下来。古公亶(dan)父时,周人受到豳以北少数民族的侵扰,被迫长途跋涉、弃豳迁岐,至于岐山之下的周原,定国号为周。
周文王为了作好灭商的准备,缩短了与商之间的距离,把国都向东迁徙到丰,周文王迁丰以后不久就逝世了,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1046-1043B.C。),再把国都东迁到了镐,镐京也叫宗周。丰、镝近在咫尺,隔水相望,可能就是一个城市的两个分区。直到周平王宜臼才迁都洛阳,是为东周,也是春秋的开始。西周起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春秋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公元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在中国古代史上,周是以擅长农业生产著称的部族。在周族祖先的传说中,始祖后稷被认为是出色的农业生产者,甚至奉为农业的创始人。
西周、春秋的社会,以农业经济为重心。周王藉田的生产,主要是依靠庶人(农民)和从夷戎部落战争中俘虏来的奴隶(臣、妾、隶)的劳动。庶人虽然是被统治的阶段,但他们与贵族没有严格的直接的臣仆关系,是社会上经济财富的主要生产劳动者,奴隶则失去独立的人格,他们可以被当作物品一样相互赠送。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尤其在春秋末期,处于奴隶制急剧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铁器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蚕业有了更快的发展。
蚕业既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豳地也是祖国的古老蚕区,更由于蚕丝的品质远胜于当时的衣服原料——葛和麻,因此周代的蚕业由于统治阶级对蚕丝需要的增加而较快地发展起来,奴隶和农奴在这八百多年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生产技术经验,为后世蚕业技术打下了基础。
第一节 蚕业区域
蚕树的适应性很大,因此,生长的范围非常广泛,在《诗》中看到桑树生长,养蚕和制丝的篇章很多,如:
风 豳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郑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秦、车辚:阪有桑,隰有杨。
卫、氓:氓之蚩蚩氏,抱布贸丝。
鄘、定之方中:景山与堂,降观于桑……星言夙驾,说于桑田。
曹、鸣鸠:鸣鸠在桑,北山有杨。
邶、绿衣:绿衣丝兮,女所治兮。
魏、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唐、鸨羽:肃口鸨行,集于芭桑。
雅 大雅皇兮: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桑柔:菀彼柔桑,其下候旬。
小雅、南山:南山有桑,北山有杨。
颂 鲁颂、泮水:食我桑黮,怀我好音。
在《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记载产丝的地区,有豫州和并州两处:“河南曰豫州,其利林、溱、丝、枲”;“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
此外,在《孟子》中记有孟子向梁惠王提出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建议,范蠡所着《范子计然》中记“白素出三辅,……锦大丈出陈留……能绣细文出齐……绨出河东,白纨素出齐鲁”。“吾闻先生明于治岁,万物尽丧,久闻其治术。计倪对曰:凡人生或老或弱,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斂。越王曰善。”
任昉《述异记》载“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耕桑”,《史记》载“吴王僚因吴边处女与楚边邑之女争界上之桑,而伐楚”和“蚕丛都蜀,教民桑蚕”,《国语·齐语》载“桓公代楚,使贡丝于周而反”,《晋语》载“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将为茧丝乎’”,《史记》载“货殖列传:齐带山海、宜桑麻,沂泗以北宣桑麻;齐鲁千亩桑麻,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以上这些史料合比对照起来,可见在周代不少封国和地区(豳、郑、卫、邶、周、魏、齐、鲁、曹、宋、陈、楚、秦、蜀、晋、吴、越)已有了蚕业,并且生产出各种丝织品;其他一些封国和地区,在史科中也记着桑树生长的繁茂。所有这些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等省,从丝织品的产量和质量来看,可知当时在山东,河南和陕西,蚕业是最繁荣的。又从出土文物可见,远在辽宁,西周时也已养蚕织绸了。
《史记》“楚世家”载“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又西施家世业蚕桑,可见春秋时处在江南的蚕业已较普遍。
第二节 蚕事概况
1 养蚕生产概况
上层阶级为表示对蚕丝生产的重视,在各生产环节前做出样子,然后由臣民去做。《周礼、内宰》中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意思是说,到仲春二月的时候,帝王告诉他的妻子率领着卿大夫的妻子和后妃们开始到北郊有公桑、蚕室的地方去着手蚕事。二月还不是养蚕的时候,后妃们是亲自前去进行一次洗浴蚕种的。(孙希旦《礼记集鲜》)
《礼·月令》中对于宫廷的蚕室里养蚕的描写说:“季春三月,……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是日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维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归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礼·祭义》中也有一段记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水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织,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欤,遂副袆而受之。’”意思是说,古时候的天子和诸侯,必定有靠近河边的桑田和蚕室,建筑的蚕室高一丈一尺,墙上有棘,门向外关闭。到了三月初一的早晨,君主戴着皮小帽,穿着白素绸衣服,占卜三宫的夫人和吉利的女仆,由她们在蚕室里主持蚕事。蚕种在河里浴洗,在公家的桑田里采桑,风干后再喂上去给蚕吃。到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农仆养蚕结束了,把茧给君主看了看后,随即就献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说:“这是拿来做君主衣服用的吗?”因此头戴副,身穿袆衣,郑重地接受下来。
孟子也说:“诸侯助耕,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孟子·滕文公下》)天子诸侯的妻妾,仅是在养蚕季节到来时举行一次仪式。农事上,君主带头举行藉田典礼,蚕事上便是“夫人”们行蚕缫典礼。
天子在行藉田典礼的时候,“百吏庶民毕从,……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就是说许多官员和奴隶都跟了去……天子举起耜来推了三推,约一方尺的地方,奴隶终日在千亩的地方耕种。《国语·周语》、《埤雅》载“王亲讲,三推而止;王后亲蚕,三洒而止”,是很客观的说明。
在蚕事上,劳动生产主要由召进来的女仆担当的,从下列史料可见:
1.1 采桑
由女奴爬到桑树上去采。在《左传》上记着一个故事:“僖公二十三年,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姜氏美女给他做妻子,有马二十匹。公子重耳安息下来,跟从他的人认为这是不对的。准备离开那里,在桑树下商量着。蚕奴在桑树上听到了,就告诉了姜氏,姜氏为了灭口,就把蚕奴杀了。
1.2 养蚕
《礼记·祭义》中记着:“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於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说的是择某个吉日,夫人缫丝了。她用手在茧盆里把茧淹三次索绪,这样以后,就分给三宫夫人和吉利的世奴接着缫下去。
除女奴以外,中层统治阶级的妇女们直接参加蚕事,也是极可能的。《礼记·月令》记着:“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税,贵贱长幼如一。”说的是养蚕完毕后,后妃要把茧献上去了,于是就收取近邻的茧税,以蚕期各人受桑的多少作为标准。不论高贵如公卿夫人的妻子,即使高贵如公卿大夫的妻子,下贱如内外宗的长幼都一样。
以上是统治阶级率领下进行生产的情况。但是,蚕事在周代的“皇土”范围以内是并不秘密的,同时大量的蚕业生产已在农村进行。
《诗》中对蚕农的蚕生活和蚕事情况,有详细的记载,如“豳风·七月”有两章专叙蚕丝生产全过程的诗。
2 蚕具
养蚕应用的器具,记载在史料上的有下列几处:
《礼·月令》 “具曲、植、蘧、筐”;
《诗·豳七月》 “女执懿筐”,“取彼斧、斨”。
这些器物的形制,在当时的古藉中没有记载,根据汉代及以后学者的解释:
曲 芦苇编成的蚕箔,既可养蚕,又可上蔟。
植 临时在室内竖立的直木,搭架放箔之用。
蘧 铺在蚕箔上的粗席,供养小蚕之用。
筐 浅的有缘的竹筐,底放粗席或芦苇,方形。“女执懿筐”则是一种方笼。
斧、斨 仅是装柄的孔有方、圆之分,今通称斧。
3 养蚕技术和蚕习性的记载
因为迄至周代,没有专门叙述养蚕的农书遗留下来,只能根据一般的文史资料,不断地推测当时养蚕的概况。
早晨采桑 《礼·祭义》载“风戾以食之”,意即指桑叶上有露水,凉干后饲上去,可见这里是采清晨的桑叶。
大蚕伐条 《诗·豳七月》载:“蚕月条桑,取彼爷斨,以伐远扬。”伐下的桑条是否进行条桑育,还不能肯定。
蚕室空旷 《荀子》“蚕赋”载“飞鸟所害”,既然受飞鸟的危害,可见蚕儿并不是养在可关闭、可保温的室内的。
养蚕前浴种 《礼·祭义》载“奉种浴于川”,《周礼·内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在仲春二月当然是还未养蚕,有的认为,这是去行第一次浴种的。孙希旦《礼记集解》说:“初浴种时,后妃亲往,故内宰言仲春后采桑。始采桑时,后妃又往,故月令于季春言,东乡躬桑。”
关于蚕儿习性的记载,最古而又比较全面的是《荀子》“蚕赋”,这虽是一篇文学作品,但其中确包括了许多古人对蚕儿习性认识的资料。全文如下:“有物于此:倮倮乎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焉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形家败,弃其耄老,收其后世,人属其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日。”;“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老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温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谓之蚕理。”
那时对蚕的习性的认识,有以下几方面:
(1)蛾有雌雄而蚕无雌雄(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
(2)害怕高温(夏生而恶暑);
(3)喜欢温和、禁忌多湿(喜温而恶雨);
(4)三眠蚕(三俯三起)。
“夏生而恶暑,喜温而恶雨”,对蚕的生长发育所要求的生态学因素——温度和湿度,简明地刻划了出来,历代以来在蚕习性方面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认识,事实上,这的确也正是指导生产的准绳。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即“适温干燥”。
关于蚕的种类,总括起来有吃桑或柘的家蚕和吃?的柞蚕。家蚕有一化和二化两种,大多为三眠蚕。
看来当时对蚕病还没有科学的防治措施,政府曾下令奖励征求防病的方法,“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百,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除注意消洁卫生外,药物防治还没有开始。
第三节 桑树的栽培
桑树在高燥的地方自然生长着(《诗·南山》“南山有桑”车辚“阪有桑”)。同时也看到桑树在肥沃的土壤上生长得更好:“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杨有次。……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管子·地员》)
根据桑的生理,在高燥的地方生长良好,兼由于养蚕的方便,当时把桑树种在宅地上及庭园周围是比较普遍的,如下可见:“无踰我栽墙,无折我树桑。”(《诗·郑》将仲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
此外,统治阶级还规定须在宅地种植桑、麻,否则就得罚货币。《周礼·地官司徒》载:“载师……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地种桑的习惯,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沿袭着的,试看今日许多蚕区的农村里,场地附近或房屋四周,都可以找到几棵高大的桑树。
但是,周代的栽桑已不局限于自然资源的利用,那时已有载植在农田里成片的桑树了。试看:
《诗·魏》“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在那十亩农田之间;
桑者闲闲兮,采桑的姑娘多悠闲!
行与子还兮,我要随你们回家转。
十亩之外兮,在那十亩农田之外,
桑者泄泄兮,采桑的姑娘多愉快!
行与子逝兮,你们走时要把我带。
《诗·鄘》“定之方中”:
灵雨既零,春天好雨已下淋;
命彼官人,我乃嘱咐驾车人,
星言夙驾,天晴一早就起程,
说于桑田,桑田之中好息身。
又有“子产开亩树桑”(《韩子》)的记载,可以推测当时地多人少,已开始了大面积的种桑养蚕。劳动人民之间,也有一部分以丝作为媒介的物物交换。(《诗》“抱布贸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