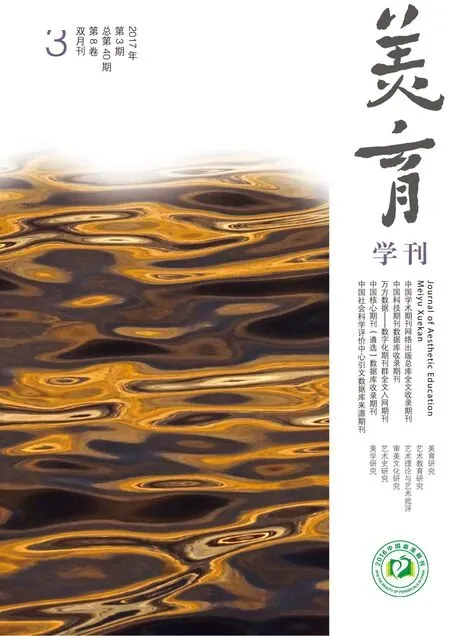萧公弼与中国现代美育的早期开拓
2017-03-25谭玉龙
谭玉龙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萧公弼与中国现代美育的早期开拓
谭玉龙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萧公弼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启超一样,为中国美育的现代转型与早期开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在《美学·概论》中,一方面明确区分了“好色(美)”与“好淫”,揭示出了“好色”是人的天性,而“好淫”则是纯粹的感官享乐与肉体欲望的满足,所以他倡导“色而不淫”的审美观;另一方面,他提出“重内而轻外”的命题,因为“内美”是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能给人持久的美感,同时还具有道德意味。此外,萧公弼推崇“忘美”之境,它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指向道德之善,它是真善美的融合为一。
美育;色而不淫;重内而轻外;忘美之境
尽管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就存在“礼乐教化”的美育思想,但直至清末民初,美育才被真正置入教育理念之中,成为与德育、智育、体育并行的一种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古典型美育向现代型美育转型的时期。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启超等为美育的转型及其宣传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现代美育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此外,萧公弼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他在“五四”以前,与其他美学家、美育家一样,倡导重视美育的现实功能,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美育观点,以提升当时中国人的精神境界。萧公弼,虽生卒年月不详、表字不详,但根据他1915年前后发表的论文看,他的落款为“四川工业专修学校正科电科一年级生”[1-2]。可见,萧公弼于1915年左右就读大学一年级,那么他大致应出生于19世纪末,年龄与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相仿佛。此外,据《寸心》杂志,他为该杂志的编辑,也曾与有“蜀中大儒”之誉的彭举(1887—1966)在成都创办《世界观》杂志。所以,萧公弼很有可能是一位川籍学者。[3]萧公弼的美育思想见于其《美学·概论》,该作连载于《寸心》杂志(1917年),是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最早以“美学概论”为名的论作。《美学·概论》分为《美学之概念及问题》《美学之发达及学说》《发生的生物学的美学》以及《美学之要义及其地位》,加上正文前面的“序”,共五部分。此作试图全面介绍西方从古到今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及其美学理论,如柏拉图、康德、席勒、叔本华、哈奇生、立普斯等。除此之外,在《美学·概论》中,他还花了大量的笔墨阐述自己关于“忘美”之境,“淫与色”“内美与外美”以及音乐艺术等的美学理论,萧氏深刻而独特的美育思想正蕴于其中。
一、“好色而不淫”
好美恶丑与维持生命、传宗接代一样都是人的天性。所以,萧氏云:“目欲穷靡曼之色,耳欲娱声色之好,口欲极豢刍之美,行欲有舆马之奉”都是“人情之常,无足异者”。[4]640同时,人的审美观念也是从这些好美恶丑的天性中生发出来的。另外,“美”在萧公弼看来具有重要的作用,美的艺术“可卜国家文野”,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可瞰民品优劣”,“美”甚至是动物、植物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保障——“物以美观而保族,花以香艳而存种”[4]640-641。可见,“美”在萧公弼的美学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同时,对“美”的追求也成为萧氏美育思想的出发点。
《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5]而“色”在萧氏笔下却被创造性地发挥为“美”。他说:“盖美感为人之天性,则好色者亦人之天性也。”[4]661另外,萧公弼在《美学之发达及学说》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理论,如:“达尔文于其《物竞篇》,谓物类之欲保其种也,则雄者常具美丽之羽毛,妩媚之态度,以诱惑雌者,使其亲己,以达其传种之目的。至于植物,则开美丽鲜艳之花,发芬芳浓郁之香,以引诱蜂蝶,使为媒介,而蕃衍其种焉。”[4]645虽然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值得探讨,但是萧公弼借用此理论足以说明人的“好色”(即“好美”)之情“出于天性,而关于物之生存竞争者大矣”[4]645。
基于此,萧公弼反对金圣叹的“人未有不好色者,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4]660的观点。因为金圣叹虽然是“绝世之聪明才子”,但是“竟将色、淫二字,混为一谈”[4]660。在萧公弼看来:“好色者,美的本质也。好淫者,美的玩赏也。好色者,精神之快感也。好淫者,肉体之欲望也。”[4]661“好色”即追求、喜好“美”,这是人的天性,也是审美活动的本质,人们通过这种追求“美”的审美活动获得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审美愉悦。而“好淫”则是纯粹的肉体欲望满足的玩赏活动。“好色”不等于“好淫”。所以,他认为金圣叹“思想简单,未入审美高尚领域”[4]661。
曾繁仁先生认为:“审美需要虽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感情要求,但如果不引导也有可能走向歧途,变成对某种怪异的‘美’的追求,甚至发展到反面,以丑为‘美’,以生理快感的发泄为‘美’。”[6]而萧公弼在当时的社会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况,青年男女的审美需要未得到正确的引导而“色”“淫”不分,他说:“余观我国近日之社会美术之缺乏,制造之简陋,已不寒而栗。乃其最者,无行文人,恒喜舞文弄墨,以艳情小说蛊惑当时。”[4]641当时的艺术家“舞文弄墨”,创造“艳情小说”就是一种“色”“淫”不分,以“淫”为“色”的现象。这让当时的“青年男女之忽于审美,而有以餔其毒也”[4]641。因此,萧公弼反对“色而淫”,倡导一种“好色而不淫”的审美观。
萧氏还借用佛教理论来阐明之:“夫好色而不淫者,是以真如熏无明。故此身常觉清净,获自在乐。色而淫者,是以无明熏真如。故此身爱染贪著,受诸种苦报。”[4]641这是佛学中非常有名的“熏习”说。“好色”但“不淫”是用真如熏无明,“好色”而“淫”是无明熏真如。我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在佛学中,“真如”指真如不虚和如常不变,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本然真实,是佛教修行者所要追求的境界。“无明”则是“愚痴”,是一种具有分别心的世俗的认识,修行者就是要钝除“无明”而求“真如”。“熏习”就如干净的衣服不香不臭,本来没有什么味道,但被人穿过后,就会带上身体的味道,如果身体有臭味,则衣服就会带上臭味,如果身体是香的,则衣服也就变香了。“真如”本身是“非染”的,“无明”是“染”的。当真如被无明熏习后,则产生业识和妄心,业识、妄心又复熏真如后,则妄念起。“色”好比真如,“淫”好比无明。人天性“好色”,但不一定有淫念,但当“好色”之天性被淫念所熏习后,“色”才会着上淫之色彩,即“好色而淫”。人如果持这种态度,则“快感不生,失美学之真谛者也”。“好色而不淫”则是“以真如熏无明”,用“真如”去熏习“无明”就会让“无明则灭,无明灭故,心相不起。心不起故,境界相灭”[4]661。也就说,如果人们怀着一颗“真如”之心去印照外界之色或感染邪淫之妄念,即以真如熏无明,一切邪淫之念都会灭绝,而得“涅槃乐”。从审美的角度讲,就是让人不要用功利的态度和充满欲望的念头去玩赏对象,这样就“常觉清净,获自在乐”,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
萧公弼认为如果不明“好色”与“好淫”的区别,则会让“我国青年男女,审美失当,沉迷声色,纵欲败度,致荒时废事,淫乱之俗,日炽区夏,种既衰微,国且不国也”[4]662。所以,萧公弼倡“色而不淫”而抑“色而淫”是让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不要把低俗的肉体欲望满足当作是高雅的审美愉悦,否则青年男女的身心都会受到伤害,甚至国家的兴亡也会受此影响。
要言之,萧公弼认为,“好色”是人的天性,是审美的本质;“好淫”则是人好色之天性受到邪淫之念的熏染而进入与审美相悖的欲望满足之路。所以,人未有不好色者,但好色不一定淫。蔡元培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7]46也就是说,人们到底是“好美”还是“好淫”关键是看人怀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去观照对象。萧公弼倡导青年男女“好色而不淫”,不要“色而淫”,因为“色而不淫,提斯警悟,乃如高尚审美之领域,而有无穷快乐者也”,而“色而淫者,断未有不精神委惫,戕贼厥身者,此又与美之原则相背驰者也”[4]662。
二、“重内而轻外”
“好色”即好“美”,是人的天性,是动植物得以生存、繁衍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保障。而“淫”则落入了肉体欲望的满足与享乐,是一种“龙阳之想”,根本就不是审美。所以,萧公弼倡导一种“色而不淫”的审美观,反对那种“色而淫”的低俗观念。但是,在萧氏的美育思想中,并不是所有的“美”(“色”)都值得人们去“好”,因为“美”还要分为“内部之美”和“外部之美”,简称“内美”与“外美”。
萧公弼说:“外部之美,则假于外物,托于色相,意觉美观,缘生爱恋,是此美为自外部发生,是谓‘外美’。若理性自适,意志修洁,天君泰然,良知愉快而感美者,是此美自内部发生,名曰‘内美’。”[4]664外物的形式、色彩等引起人们感官上的愉悦,这种物就具有“外美”,而“内美”就是人们理智把握的对象,能让人们的心情舒适,唤起人们的良知,它不是来自事物的外部,而是来自事物的内部,即“内部之美,精神之快感也,在我而已。外部之美,形式之美,求在外者也”[4]664。所以,我们可将两者分别看作形式之美与内容之美。
萧公弼倡导人们追求“内美”,而不要沉溺于“外美”,即要“重内而轻外”(《美学之要义及其地位》)。他说:“外美之至,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皆物之傥来寄者也。内美则良知莹然,心不蔽物,自适自乐,无人而不自得焉。”[4]664事物的“外美”来不可止,去不可留,因为它们是寄托在事物的形式中的,而“内美”则让人们的内心明快,心情自然愉悦,人只要想获得这种美感就可以得到。萧公弼进一步讲:“内部之美,其感快强,为时永久,外部之美,物有不足,则烦恼以生,其痛苦有异寻常万倍者。”[4]664在他看来,“内美”才是真正的美,永恒的美,感染力也极强,而“外美”由于托于物的形式,物稍有不足则“外美”受损,人就会产生烦恼,不仅不能获得美感,反而感觉不快,十分痛苦。
萧公弼倡导人们要善于捕捉、欣赏“内美”,艺术家也要创造具有“内美”的艺术作品。他说:“彼诗文者,特词章家意志之寄托耳!无声音笑貌以悦耳,无美曼婀娜以悦目,然千载之下,使人读之,或拍案叫绝,或感慨欷歔,或长言吟诵,或手舞足蹈,乐而忘倦者,何也?以其能激发人之感情、思想、内美作用故也。”[4]664诗歌等文学作品虽然没有悦耳、悦目的形式之美,但是千年以后人们读了后,却可以拍案叫绝,感慨万千,获得审美愉悦,这是因为诗歌等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寄托。而寓于诗歌之中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就是“内美”,它能激发读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让读者获得持久的美感。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也是这样,当人们欣赏完雕刻或绘画后,“暇时默念,亦常能激发人之记忆及想象活动,以思惟该对象,使美之快感情益臻强度,饶有兴味,而感情缘以深厚矣”[4]664。这就是说,人们在想象中玩味、思维的不是雕刻或绘画艺术的外形,而是它们的内在意蕴,给人以美感的也不是艺术的外形,而是内在意蕴,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就是“内美”,“内美能满足吾人知的机能要求,而起美之快感”[4]664。因此,艺术家不能只注重艺术作品的“外美”,还要重视其“内美”,欣赏者也应该欣赏艺术的“内美”,而不应只求感官享乐的“外美”,因为“外美”是有限的、短暂的,只是感官的满足,而艺术作品的内容或内在意蕴则是永恒的,能给人以持久的美感。艺术作品的“内美”是“自理性而发,非纯恃感官知觉故也”(《美学之要义及其地位》)。
萧公弼认为:“美与善,人类最高尚之生活。”[8]可见,萧公弼的“美”是不脱离“善”的,是融合了道德之“善”的美。“内美”,即“善—美”。因而萧公弼十分推崇儒家的圣人,因为他们身上就体现出了“内美”。他说:“孔子疏食曲肱,原宪瓮牖绳枢,声出金石,乐在其中也。”[4]664粗茶淡饭,以肘臂为枕头,家境贫寒,住处简陋等都不会让孔子、子思等人灰心丧气,反而他们还“乐在其中”。在萧公弼看来,孔子、子思等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内美”。另外,萧公弼引周敦颐称颜回的话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4]664颜回不因自己生活贫困而忧愁,反而还自得其乐。同时,颜回追求的不是“富贵人之所爱”的东西,而是追求“天地间至贵至爱”,获得的是一种“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则一,处一则化而齐。”[4]659这种颜回所达到的无论贫富贵贱都“处一”的境界就是一种至美的境界。因为这些儒家圣人们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的“外美”,而是一种内在道德、心性修养的“内美”。
萧公弼观察到,当时的艺术家和观众就有“重外而轻内”的倾向,他说:“吾观我国今日听剧家,每喜闻妖淫之声,而评剧家亦多为倚艳之辞,而演剧者之不学无术,昧于音乐之道,教化之义。”[4]665“妖淫之声”“倚艳之辞”等都是艺术家或欣赏者过分追求“外美”的结果。这种过分重视“外美”而忽视“内美”的“妖声绝辞”等造成了“国且不国”的严重后果。因为这种艺术不仅失于教化,而且让青年男女更加浮躁,沉溺于声色之享乐中。所以,萧公弼不仅强调艺术家或欣赏者要“重内而轻外”,同时还倡导当时的青年男女要以此为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即“我青年男女同胞之审美也,须具此胸襟气概,然后能不沈于声色货利,不淫于富贵功名,而能以美利利天下矣”[4]641。此“以美利利天下”乃萧公弼美育思想之最终指向与目的。
三、“忘美”之境
萧公弼明确区分了“好色(美)”与“好淫”,让当时的青年男女不要以纯粹的欲望满足为审美。而“美”又分为“内美”与“外美”,艺术家要以创造“内美”为己任,欣赏者也要观“内美”,因为“内美”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还是圣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但是,萧公弼的美育思想中的最高境界并不是追求“内美”扬弃“外美”,或者是取“色”去“淫”,而是一种“忘美”的境界。
萧公弼在《美学·概论》的开篇就讲:“惟太上忘美,其次知美,下焉者欲而已。”[4]660他在《美学之要义及其地位》中也说:“复因根器智慧之不同,而有太上、知之、纵欲三种之差别。”[4]657可见,萧公弼的美育思想中将审美分为了三个层次——忘美、知美和纵欲。
王国维曾说:“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9]5这说明,人如果充满“欲”是不可能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观照的,同理,进行审美观照的人也不可能带有“欲”。王国维将这种“欲”称作“眩惑”。“眩惑”就让“吾人自纯粹知识而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9]6。王国维之“欲”或“眩惑”其实与萧公弼笔下的“欲”或“纵欲”相通,即萧公弼所反对的“好淫”,它是一种“阿私所好,或醉生梦死,其去禽兽也几希”。“欲”就是一种无精神性的纯粹肉体欲望的满足与享乐,这与禽兽没有分别。在《发生的生物学的美学》中,萧公弼说:“今之青年男女,误于审美正鹄,迷恋姿色之美,沉溺肉体之欲,以致耗精疲神,戕贼厥身,年始及壮,躬若老耄。”[4]647-648这就是“纵欲”或“好淫”的真实写照。所以,这种“欲”其实根本就不是审美——“乌足以语于美哉”。
“知美”就是一般人所达到的境界。萧公弼倡导人们要好“色(美)”去“淫”以及“重内而轻外”,其实就是“知美”之境。这种境界“察物之媸妍,辩理之是非”。也就说,人有善恶美丑真假之分别,知道去追求真善美而丢弃假丑恶。这种“知美”让人们具有分辨美丑的能力,确实让社会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因为如果“媸妍同观,精粗齐等,是茅茨土阶之制,必无改于今矣,饮血茹毛之风,必相沿而不革矣”[4]646。但是萧公弼认为,人如果有了“知美”的观念后,就会心生欲念去追求美好的东西,即“故吾人观珍异则思把玩,视好花则拟攀折,见奇鸟则欲牢笼,遇美人则怀缱绻”[4]647。人们因为追求美好的东西,就会发生争斗,而且还会让自己“快感与不快感之情生”[4]641。因为,对于美好的东西,人们“得之则喜,失之则郁”。所以,在萧公弼的美育思想中,这种“知美”只能排在第二个层次。
笔者曾撰文指出,萧公弼的《美学·概论》“借用佛教理论阐发了他自己的美学观点,如忘美之境、美与丑、淫与色、内美与外美等,其论述特点是以佛释美”[10]。具体来讲,萧公弼是站在大乘佛学的角度,推崇一种“忘美”之境。佛教认为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外界后产生的色、声、嗅、味、触、法(“六尘”)不仅是虚假的,而且还刺激人们产生欲望,增加人的无明。佛教把“六根”“六尘”称为色或相,或色相。色相就是虚相、假相。佛教的最高境界就是求得涅槃,证得佛果。而要达到这一境界,首先就要否定自我,否定外物,否定宇宙间的一切。萧公弼引用《金刚经》的话讲:“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4]641。“人”“我”以及“众生”都被否定了,哪里还有什么美与丑?这就是“夫相之不存,何有于美”?紧接着,萧公弼用《大乘起信论》的话讲:“一切诸法,以心为主,从妄念起,凡所分别,皆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4]641,美与丑、善与恶都是一种“法”,这种“法”是因人的妄念和分别心而产生的。萧公弼所提倡的是一种“人我两忘,法执双融”(《〈美学·概论〉序》)、“思虑寂然,嗜欲不萌”(《美之要义及其地位》)的态度,人们褪去了妄念,消除了分别心,那么美与不美都已经不存在了——“美丑之态,无由发现”,这就是一种“忘美”的境界。
萧公弼美育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忘美”之境,而这种“忘美”之境并不是要人们不分美丑或是去美求丑。一方面,“忘美”之境需要以“知美”为基础,因为“知美”让人们区分了“色”(美)与“淫”(丑)、“内美”与“外美”。另一方面,“忘美”之境又需要超越“知美”,因为“知美”会让人们心生欲念去追求美、色,而在追求过程中会产生情感上的烦恼,甚至是争斗。“忘美”之境就是在基于“知美”又超越之的过程中,打破美丑的界限,让人自然而然地处于高尚的道德修养之境界。“忘美”之境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审美境界指向道德之善,它是真善美的融合为一,也就是蔡元培先生说的一种“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7]5。
四、结 语
萧公弼是继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之后,又一位为“美学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其《美学·概论》不仅“对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学科建构意义”[11],还对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早期建构与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我们当下的美育研究发挥着启示作用。首先,萧公弼美育观点的提出是以当时社会现实和艺术风貌为基础的。据萧氏描述,民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剧变,一些“色而淫”的艺术作品充斥着社会,青年男女的审美观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股追求欲望满足、肉体享乐的思潮兴起,所以萧氏倡导“好色而不淫”的审美观以纠时风。其次,萧公弼的美育思想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综观萧氏美育思想,他虽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美学,但其思想精髓是儒家文化,同时借以佛学而申发,其“重内而轻外”的美育思想就具有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思想的深刻烙印。最后,萧公弼点明了美育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人的境界,所以对于萧氏而言,美育之学即境界之学。美育不止于艺术创作之教育,也不止于正确的审美观的培养,而是通过这些教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以美利利个人”到“以美利利天下”。总之,萧公弼是一位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以及美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他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启超一起,为中国美育的现代转型与理论的早期开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美育观念以及方法论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1] 萧公弼.读康德人心能力论书后[J].学生杂志,1915(6):25-27.
[2] 萧公弼.释我[J].学生杂志,1915(3):7-10.
[3] 谭玉龙,朱志荣.论萧公弼的美学研究方法——兼论其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的地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9-115.
[4] 叶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近代卷:下[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748.
[6] 曾繁仁.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审美教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2.
[7] 高平叔.蔡元培美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8] 萧公弼.大战争后之新文明[J].学生杂志,1916(3):109-113.
[9]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 谭玉龙.萧公弼:被遗忘的近代美学学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43-144,147.
[11] 黄雁鸿.晚清时期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早期留学生[J].人文杂志,2008(5):19-23.
(责任编辑:紫 嫣)
XIAO Gongbi and Early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TAN Yu-long
(Institute of Media and Ar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XIAO Gongbi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 whoseIntroductiontoAestheticscontains his peculiar and deep thought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one thing, he differentiates Haose and Haoyi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er is a human instinct and the latter is the pursuit of sensual pleasur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hysical desire. So he advocates the former over the latter. For another thing, He praises the no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of Zhongnei and Qingwai, because Zhongnei is the inner meaning of arts which can give people an abiding aesthetic feeling and moral meanings. Besides, he calls for the realm of Wangmei, which is not a deliberate realm of morality but an aesthetic realm from the bottom of people′s hearts. It leads to morality and is the mixture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esthetic education; Haose instead of Haoyin; Zhongnei and Qingwai; the realm of Wangmei
2017-02-07
谭玉龙(1986—),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研究。
G40-014
A
2095-0012(2017)03-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