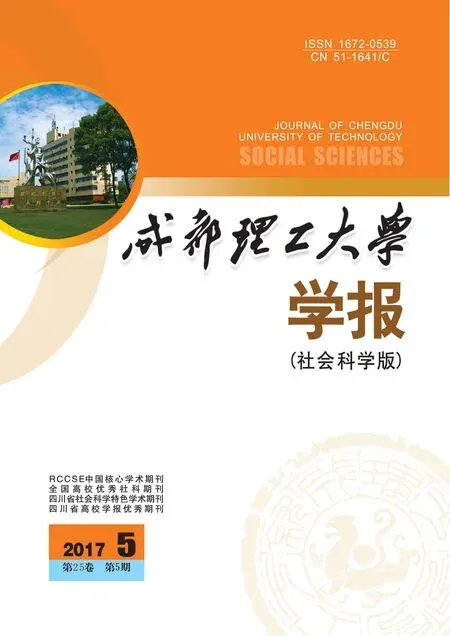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
2017-03-23万旭
万 旭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
万 旭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侦审联结”是对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种特定现象的概括提法,其可作为相对中性的工具性概念。在大陆法系传统国家的诉讼实践中,往往同时存在“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和“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理论界讨论的“侦审联结”,属于“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在实践中的一种具体类型,相应的批判则是以庭审实质化改革为语境的。对比较法的考察表明,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改革语境中,大陆法系传统国家普遍认可“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可以借鉴这些改革经验,但是在具体展开有限正当化时,要正视我国制定实践与域外的实质差异和差距,从多方面入手推进改革实践。
侦审联结;侦审连接;刑事司法改革;有限正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侦审联结”是我国学者对于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种特定现象的概括提法,这种现象即“由侦查形成的证据能够直入审判并取得定案依据资格”[1]。自2006年有学者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基本上所有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学者,均对“侦审联结”持负面评价态度,主张在刑事司法改革进程中应当“适度阻断”甚至“切断”侦审联结。应当注意到,学界对于“侦审联结”的批判是以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作为特定语境的。从逻辑上讲,如果切换到不同的语境中,“侦审联结”完全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评价。
比较法上的考察印证了这一推断——在许多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改革者们虽然在推进刑事庭审实质化时大都注意限制“侦审联结”(主要是限制案卷功能),但是,一旦转向构建以罪刑协商为核心的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时,这些国家往往就强调法官要通过阅卷来审查罪刑协商的事实基础和真实性,也就是有条件认可“侦审联结”[2]。这就提示我们,有必要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下对“侦审联结”加以更为辩证地考察评价。
实际上,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虽然以庭审实质化为重心,但同时也包含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关注庭审实质化语境下对“侦审联结”的“限制”问题,而且应当注意到在其他语境下,尤其是认罪认罚从宽语境下,对“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问题。
二、“侦审联结”与“侦审连接”——必要的概念辨析
目前学界研究中并未明确区分“侦审联结”与“侦审连接”——无论是“联结”还是“连接”,所指都是特定语境下的负面实践现象。一旦涉及到在不同语境下对类似现象的比较分析,概念工具精细化的必要性也就相应凸显。类型化研究所依靠的工具性概念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如此方能确保工具性概念在与不同语境、条件结合时的弹性,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基于不同标准而划分出各种相互对应的理想类型。考虑到“侦审联结”的含义在先前的理论研究中已经固化,本文不直接将“侦审联结”改造为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概念,而主张有意识地区分“联结”和“连接”,将后者作为工具性概念,而将前者作为特定语境下的一种“侦审连接”类型。
这一区分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这一区分在语义学上具有可行性,因为“连接”与“联结”在句法功能、词义和用法上存在明显差异,“连接”更多的是对事物之间一组特定动态关系的具体描述,而“联结”则进一步对事物之间的“连接”关系进行了抽象、或者说深入的“评价”,即这种“连接”达到了融为一体的程度。也就是说,“连接”是相对中性的,而“联结”则是对于“连接”的深化。因此,将“侦审连接”作为中性的工具性概念,而将“侦审联结”作为特定语境下的“侦审连接”具体类型,是比较合理的区分。其二,虽然学者们没有明确区分“侦审连接”与“侦审联结”,但是近年来,权威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已经明显偏好于使用“侦审联结”,而其他一些学者延用“侦审连接”的表述,其主要是对权威学者早期表述的直接引用(1)。这表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目前学界在相关研究中的修辞习惯已经为我们区分“侦审连接”与“侦审联结”提供了一定空间。
侦审连接,强调的是在事实认定层面上,侦查与审判的连接关系。现代刑事诉讼中,这种侦审连接关系是必然存在的,而基于特定基准,可以对侦审连接作进一步的类型划分。比如根据侦审连接是依托于案卷移送制度,还是庭审证据调查,可以区分出“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与“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而根据侦审连接是导向职业法官组成的一元裁判组织,还是导向由职业法官与平民法官组成的二元裁判组织,也可以对侦审连接进行划分。本文特别关注的是第一组划分。在多数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往往同时存在着“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和“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我国也不例外。在进行根本性的诉讼模式变革之前(2),实践中的真正课题并不在于这两种连接类型的存废之争,而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两种侦审连接的相互关系。
由此以观我国学者长期批评的“侦审联结”现象,其实质是,“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过于强势,进而压缩甚至虚化了“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这意味着,理论界呼吁的适度阻断“侦审联结”,其实是要限制“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进而为“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创造条件(3)。
三、庭审实质化与适度阻断“侦审联结”
庭审实质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进路,调整“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与“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的关系。限制乃至阻断“侦审联结”,就是调整这组关系的主流思路。
但是,限制、阻断“侦审联结”仅仅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期,庭审实质化就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尽管当时“侦审联结”这一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但修法时对案卷移送制度的重大限制,显然是意在弱化“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以使得庭审证据调查成为侦审连接的唯一路径。众所周知,这一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而在笔者看来,改革之所以出现反复,根本上是因为当时改革者们在试图通过限制案卷移送制度而为庭审实质化奠定基础时,并没有同步改革提升庭审自身“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的功能,这就“迫使”司法实践者们为了切实履行司法职责,不得不想方设法重拾“以案卷为依托的侦审连接”。时至今日,在新一轮改革背景下,大多数学者已经不太热衷于提议改革案卷移送制度(4),而是更多着眼于庭审调查的充实,尤其是关于庭审中举证、质证与认证规则的有效构建——道理很简单,打铁还须自身硬!
当然,尽管当前庭审实质化改革将重心放在强化“以法庭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一端,但对“侦审联结”的限制与阻断依然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保证庭审能够直接、有效审查证据。在限制与阻断的具体思路上,学者们主要强调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排除规则。这里应当注意到两个特殊问题:
首先,就限制与阻断而言,仅仅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排除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举措的阻断效果都不绝对,基于种种理由,事实裁判者仍然可能绕过庭审证据调查而接触到侦查阶段的证据信息(5)。而一旦直接言词和传闻排除的要求被“正当地”规避,它们对于“侦审联结”负面效应的防控功能就大大降低(如果不说落空的话)。其实,限制与阻断不仅应当着力于限制事实裁判者对案卷的接触,而且应当特别关注案卷制作、移送过程本身的规制,以从根本上提升案卷移送制度自身的正当性。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是后文即将论述的“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的一项关键要求。
其次,当前改革对于两种侦审连接关系的调整,还孕育着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根本转型(迈向对抗化)的可能性。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模式具有龙宗智教授所称的线性构造特征,这里界定的实际模式,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起点”。需要追问的是,由此出发,我们最终是要走向何方?或者说,我们最终是否要走向刑事诉讼的对抗模式?对改革“终点”的这一追问会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限度。目前,顶层设计者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而理论界也存在明显分歧。考虑到复杂的现实因素,以及当前改革路径与方法突出的技术化色彩,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根本性变革是最终目标,其过程也必然漫长而曲折。
四、认罪认罚从宽与“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全面依法治国决定》正式确定的一项改革目标。2016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借鉴辩诉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基础上,抓紧研究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3]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借鉴辩诉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这一要求。因为如果进行望文生义的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并非新提法,但是像辩诉交易制度所蕴含的“罪刑协商”理念,则是我国传统上没有的。可以认为,当前要推进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虽然名义上是“完善”,但实际上却极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
与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一致,我国当前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提升诉讼效率[4]。我国在展开这一制度改革时,也必然面临许多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在进行类似改革时面临的纠结与困难。马克西姆·兰格教授在系统考察德国、意大利、阿根廷、法国的相关改革实践后指出,这四个有着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在参考美国式辩诉交易进行改革时,均面临着两大方面的顾虑:一方面,是罪刑协商所体现的制度理念与本国传统的明显冲突,这里面最突出的,是罪刑协商所体现的合意性、相对性的诉讼真实观与四个国家传统上的实体真实观的冲突;另一方面,是罪刑协商制度与正当程序要求的紧张关系(这一点,即使在美国也相当引人担忧),尤其是因罪刑协商后克减被告方诉讼权利而带来的错案风险。这两大顾虑与其他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得四个国家的制度改革均没有走向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而是呈现出“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局面[2]。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在“庭审实质化改革”中注意限制案卷制度不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语境下,这些国家都比较注重利用案卷制度来调和前面提到的两大改革顾虑。所谓调和,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1)将认罪认罚的制度功能限定为程序分流,在此基础上,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诉讼进程不再导向正式的审判程序,但仍然要求法官至少基于阅卷而作出裁判(6);(2)要求法官通过阅卷等方式来审查罪刑协商案件的事实基础,确认罪刑协商的合法性,如果法官认为被告实际上无罪,可以“无视”罪刑协商而宣告被告无罪(7)。这里面,第一种形式显然体现了改革者在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同时坚守实体真实理念的努力,第二种形式则显然是为了降低罪刑协商带来的错案风险,缓和罪刑协商与正当程序的紧张关系。
当然,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在这些国家仅仅是作为一项配套性的改革举措,在更广阔视野下,限制案卷制度而贯彻直接言词,无疑是刑事司法改革的真正重心要求。而且,即便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这个语境下,适当利用案卷制度也仅仅是这些国家在改革中进行的诸多自主性调整之一。换言之,“侦审联结”仅仅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和意义上取得了优先于“以法庭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的正当性。毫无疑问,这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的改革实践,对于具有相似制度传统、面临相似改革困惑,而又在进行相似改革的我国而言,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五、我国“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的具体展开
在“认罪认罚从宽”的语境下,伴随着普通程序的简化,“以法庭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的功能明显弱化,因而才有必要依靠“侦审联结”来调和程序简化与实体真实、正当程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他大陆法系传统国家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为了在程序繁简分流的同时兼顾实体真实,可以要求法官在简化的程序中至少要基于阅卷来确认案件事实,而为了在提升诉讼效率的同时坚守正当程序底线,则应当要求法官通过阅卷对认罪案件的事实基础、被告人认罪合法性加以审查。总之,在特定语境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可能且应当认可“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
不过,论证“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一方面,具体将其妥当地展开则是另一回事。
首先,通过“侦审联结”来查明实体真实,其实是一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原本,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就是因为“侦审联结”这种事实认定路径存在诸多弊端。而在认罪认罚从宽的语境下重视“侦审联结”,仅仅是因为在庭审证据调查被简化之后,“侦审联结”至少比完全无法查明实体真实要好。换言之,依赖“侦审联结”来认定案件事实,本身是存在较大错案风险的。这就要求在有限允许通过“侦审联结”认定事实的同时,尽可能限制其负面效应。具体而言,应从三方面入手:
(1)要限制“侦审联结”的适用范围。这主要是通过认罪认罚从宽的罪刑范围来加以限定。通过罪刑限定,可以构建起一套多层次的认罪认罚案件程序从简体系,除了最极端的极简程序之外,大多数简化程序中,并不必完全取消“以法庭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当前,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就体现了这一思路。
(2)要优化法官审查案卷的方式。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所以通过阅卷来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就是审查被告人供述是否符合案件真实情况。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决不能仅仅将案卷中书面供述与其他证据信息进行机械的印证式比对,而应当将审查案卷与直接讯问被告人相结合,通过被告人直接供述与案卷证据信息的比对审查来确认案件事实。而且,要特别重视案卷中的客观性证据,在确认客观性证据来源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要尽可能按照“由证到供”的思路进行比对审查。此外,还应当注意充分保障被告方的阅卷权,并尽可能为其提供律师帮助(包括直接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以保障讯问质量,以及直接供述与案卷比对审查的有效性。
(3)要给予法官主动扩张调查范围的职责与职权。审查过程中如果有疑问,法官就不应拘泥于案卷范围,而要主动展开更为广泛的查证活动。如果疑问过多、过大,则应当要求法官将程序转回普通程序。为了确保法官有存疑时扩张调查范围的动力,一方面要给予被告方一定的异议乃至上诉机会,另一方面应当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必须列明待证事项及相关证据,并明确说明各个相关证据的来源是否查证可靠,内容是否确认属实,以及对于发现的疑问进行了怎样的处置。为了提升操作性与可行性,可以考虑在一定限度内推行表格式判决,让法官以勾划选项和填写理由的方式来完成裁判文书。
其次,通过“侦审联结”来保证正当程序底线,也属于特定语境下的“两弊相权取其轻”。从过往实践情况看,“侦审联结”恰恰是导致非法取证、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所谓“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绝对不是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回归过往那种弊病丛生的“侦审联结”。其实,在“认罪认罚从宽”的语境下,“侦审联结”之所以可能有助于保障正当程序,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方面,通过阅卷可以审查认罪案件的事实基础,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错误定罪;另一方面,通过阅卷可以审查定罪证据的合法性,进而有可能发现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这里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三个:(1)应当承认审查案卷对于确认认罪认罚合法性的意义是有限的。认罪认罚的合法性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认罪认罚的明知性、自愿性和事实基础。审查案卷主要只是对事实基础加以确认,而认罪认罚的明知性、自愿性,则更多需要其他制度设计来保障。(2)应当考虑在认罪案件审查中设置专门的非法证据调查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制度目标上明显有别于以发现实体真实为核心的法庭证据调查程序,而且政府有着尊重和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积极责任,因此认罪案件也要关注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已经有在以阅卷为核心的案件审查程序中设置相对独立的非法证据调查专门程序的做法,也就是检察环节的取证行为合法性调查核实程序。当然,为了避免程序设置繁复,可以直接规定如果存在非法证据排除争议,则整个案件应当直接转回普通程序。(3)要注意刑事司法机关“致罪倾向”的负面影响。我国刑事司法机关整体上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致罪倾向”,因此,要使得案卷审查真正体现正当程序的要求,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在审查后认为被告人实际无罪时,法官才能无视认罪协议而作出自主性裁判,否则,其判决必须受到认罪协议的拘束(8)。
除此之外,无论是庭审实质化背景下限制或阻断“侦审联结”,还是在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的“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都应特别关注案卷制作、移送过程本身的规制,以从根本上提升案卷移送制度自身的正当性。左卫民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刑事案卷在制作/形成上有官方性(单方性)和早期性两方面特征;而在案卷移送上,我国刑事案卷制度具有层递性特征[5]。前述特征使得我国刑事司法机关的“致罪倾向”能够深刻影响到案卷的内容,导致案卷内容主要反映以有罪证据编织而成的证据事实,并且使具有“致罪倾向”的案卷能够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导向侦查中心主义。
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已经对案卷制度有些微调整(9),但是我国刑事案卷制度的整体面貌并未有实质改变。这使得我国现有的刑事案卷制度与大陆法系刑事案卷制度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与我国不同,大陆法系当前的刑事案卷制度在案卷制作上明显倾向于多方参与、影响制作,而且大陆法系案卷在诉讼早期即具有公开性与可用性;而且大陆法系当前将刑事案卷的功能发挥主要限制在庭审前程序和上诉程序中,而在审判阶段,案卷的移送和使用受到明显限制,并原则上禁止使用书面化的卷宗证据[5]。这种实质性差异表明,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允许“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这对我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刑事案卷制度本身相比大陆法系制度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要想使得“侦审联结”适度正当化在我国切实可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有的刑事案卷制度。
一方面,应当进一步推进案卷制作的多方参与,由此打破案卷的官方性,使得案卷包含的证据信息更为丰富,不再仅仅反映以有罪证据编织而成的证据事实。另一方面,在案卷移送上应当对原有的层递性特征加以调整,主要是强化移送过程中对案卷中证据信息的公正审查,即对于案卷材料的增减不能仅仅将是否有利于指控作为标准,而要体现客观公正性。比如,一旦证据合法性在检察环节发生争议,那么系争证据和检察机关的处理意见是否应当,以及如何附卷移送,就是一个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对刑事案卷在不同诉讼阶段的作用加以限制,除在认罪认罚从宽等特定语境下以外,“侦审联结”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否则,如果案卷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贯通性的决定性影响力,所谓特定条件下的“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就难免受到现实的嘲笑。毕竟,无论“认罪认罚从宽”,还是“侦审联结”有限正当化,都属于庭审实质化基础上的附属性、配套性议题。
注释:
(1)2006年,龙宗智教授首次提出“侦审连接”问题时,是以刑事程序的线形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参见龙宗智:《立足中国实际有效遏制非法取证》,《人民检察》2006年第24期。刑事程序线形结构理论由龙宗智教授于1991年首次提出,根据其后来的重述,线形结构有理论分析模式与实际模式的区分。龙宗智教授对实际模式意义上的线形结构有明确的负面评价,他认为,当线形结构成为实际的刑事司法结构,诉讼就成为一种行政性程序,诉讼本身具有的公正性特征就基本丧失了。参见龙宗智:《返回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始点——刑事诉讼两重结构理论重述》,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龙宗智教授在提出“侦审连接”问题时所依托的线形结构,显然是指作为我国刑事程序实际模式的线形结构。由此可知,从最开始,龙宗智教授所提及的“侦审连接”就不是工具性概念,而是指称具体的实践现象。虽然龙宗智教授至今没有明确根据作为理论分析模式的线性结构而推导出作为工具性概念的“侦审连接”,但是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龙宗智教授已经明显倾向于使用“侦查联结”这一表述。而本文提出将“侦审连接”作为工具性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龙宗智教授已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推导。
(2)这里指的是由纠问式(Inquisitorial)诉讼模式向对抗式(Adversarial)诉讼模式的转型,本文对这组概念的理解,采用了兰格教授的见解,See Maximo Langer ‘From Legal Transplants to Legal Translatio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 Criminal Procedure ’,cited in “World Plea Bargaining”, edited by Stephen C. Thama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0,Chapter I.
(3)为行文简洁,下文在必要时将“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简称为“侦审联结”。
(4)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明确主张按照“起诉一本主义”思路限制案卷移送制度的学者不多,代表性观点参见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5)即使在美国,传闻证据规则对于证据排除也设置了太多的例外情况,以至于美国学者自己都承认,传闻证据规则最好直接理解为证据准用规则(rule of admission)。See Ronald J. Allen, The Hearsay Rule as a Rule of Admission, 76 Minnesota Law Review 797-812 (1992); Ronald J. Allen, The Hearsay Rule as a Rule of Admission Revisited, 84 Fordham L. Rev. 1395 (2016).
(6)如德国的处刑令程序(the penal order procedure),在这一程序中,检察官不会将案件移送审判,而是转而申请法官签发处刑令。这一程序一直被拿来同美国式辩诉交易相比较,因为控辩双方被允许就处刑令的具体结果进行协商。同前注,兰格教授文。适用处刑令程序之后,普通审判程序可以省略,而法官如果“认为卷宗资料显示,案件事实并未被充分调查,故裁判为不当者……则其应指定审判程序之期日”。【德】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98,第691页-692页。
(7)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于“法治国原则”,即使在德国式辩诉交易(Absprachen)中,法官和检察官仍负有发现实体真实的职责。因此,如果法官认为由必要展开进一步调查,就不必基于认罪协议而裁判被告有罪。在意大利式辩诉交易(patteggiamento)中,在接受认罪协议之前,法官可以基于审查案卷中的证据信息,而裁判被告无罪。在阿根廷式辩诉交易(procedimiento adreviado)中,法院如果接受认罪协议,其定罪裁判就必须建立在案卷所承载的证据信息之上。See Maximo Langer ‘From Legal Transplants to Legal Translatio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 Criminal Procedure ’,cited in “World Plea Bargaining”, edited by Stephen C. Thama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0,Chapter I.
(8)这也是各国普遍做法,See Maximo Langer ‘From Legal Transplants to Legal Translatio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 Criminal Procedure ’,cited in “World Plea Bargaining”, edited by Stephen C. Thama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0,Chapter I。
(9)参见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59条,第170条。主要是规定将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发表的意见附卷移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打破侦查案卷偏向致罪、偏向官方的封闭特性,可能从源头上缓和侦查案卷对法官中立定案的不当影响。但是具体实践效果还有待考察。
[1]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J].中国法学,2010,(2):152.
[2]Maximo Langer “From Legal Transplants to Legal Translatio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 Criminal Procedure ”,cited in “World Plea Bargaining”, edited by Stephen C. Thaman,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0,Chapter I.
[3]王逸吟.我国将展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N].光明日报,2016-01-24(3).
[4]Stefan Trechsel.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305-306.
[5]左卫民.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编辑:黄航
On the Limited Legitim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Trial
WAN Xu
(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trial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trial, however, can be used as a relative neutral referential concept. In the civil law nation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trial.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is a special type of connection based on files. Comparativ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civil law nations widely accepted the limited legitim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In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judicial reform, we could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ir experience and lessons,as well as face the gap.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trial; the criminal judicial reform; the limited legitimation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01
2017-02-15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刑事庭审证据调查规则研究”(16AFX011);2015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博士重点项目“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中的若干证据问题研究”(XZYJS2015003)
万旭(1987-),男,四川乐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
D916
A
1672-0539(2017)05-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