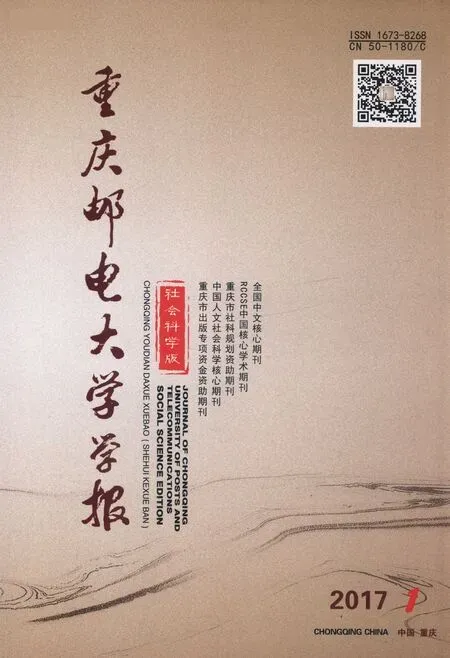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与消解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2017-03-22仝其宪
仝其宪
(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与消解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仝其宪
(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主要是因为修正前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存在设罪模式滞后、行政处罚前置失当与刑事责任配置过轻等明显的立法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大程度上放纵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不法分子。为消解这些立法窘境,《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了本罪的设罪模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正了行为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华丽转身,契合了“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向。并且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需要理清几个问题,即行为方式的正确理解、情节犯的准确把握以及本罪在司法适用时与相关罪名的界分与竞合。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刑法修正案(九);情节犯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受经济发展与通信技术的制约,我国在无线电管理立法上经历了从起步较晚、步履艰难,到稳步前进、蓬勃发展的嬗变轨迹[1]。虽然起初在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但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几近被虚置的地步。然而,昔非今比,近些年来,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无线电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和不同部门,国防安全日益凸显,民航事业蓬勃发展,资讯信息与手机用户走进千家万户,这就势必出现无线电频谱资源供需日益突出和电磁环境日趋复杂的局面。一些不法分子趁虚而上,利用“伪基站”等无线电技术和设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案件呈上升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1997年刑法典中原有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在立法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打击和规制不力。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缺陷,并赋予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最新内涵,同时更加有利于该罪的司法适用,以适应新时期我国打击与治理妨害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需要。本文结合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修订情况及其修订后本罪在司法适用时的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促进刑法立法与司法的进一步发展。
一、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为1997年刑法典中新增的罪名,由于当时无线电业务主要运用于国防、军事、航空、通信等国家重点领域,远没有现在这样如此的发达与普及,更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导致本罪在其定罪和处罚上留下时代局限性的印记,加之立法技术的缘故,使得本罪无论是在罪状的设定上抑或是法定刑的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
(一)设罪模式滞后
1997年刑法典将“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构成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结果要件,显而易见,将本罪设定为“结果犯”过于滞后,存在一定的漏洞。结果犯要求一定的违反行为和严重后果同时发生,才能成立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反之,如果只有不法行为而没有法定后果出现,则不能构成本罪。这就暴露出本罪的保护法益过于滞后,而现实中涌现的不法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仅仅停留在危害结果上,而更多地映射在行为本身的影响上和危险性上。近些年来不断爆发的鲜活案例足以证实,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等设备发送海量短信传播不良信息,虽然给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诸多隐患,但这些不法分子可以较轻易地逃避监管,进而逍遥法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擅自占有或使用无线电频率,就有可能对近年来发展迅猛的高铁、民航或航天等国家专用频率或国家重点保护的频率造成严重干扰,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存在一些境内外敌对分子或敌对组织恶意攻击我国的卫星广播电视,严重干扰我国无线电管理秩序等。诸如此类的这些行为尽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实际损害结果,但是其行为本身已经具有极大的现实危险和潜在威胁,如果再以“造成严重后果”发生为归责基础,显然为时过晚,极不利于重大法益的保护。
(二)行为方式欠妥
1997年刑法典中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规定了几类非法行为,即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站)或擅自占用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其中值得推敲且理解容易出现混乱的用语就是“占用频率”和“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其一,以“占用”表述行为方式并不妥当。根据字面意思理解,“占用”是指占有并使用或占据并使用的意思,而占有往往具有排他性或专属性。又根据《物权法》第50条和《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可见,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所有权归于国家,而任何个人或组织均不具有所有权,只能享有除所有权之外的使用权。无线电管理机构是基于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代表国家来行使管理权的,在无线电管理或使用过程中,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属性无论怎样都不会发生改变,对于任何个人或单位来说,无线电频谱资源是无法实在感知的无体物,行为人只能是暂时使用无线电频谱资源,而不可能实际占有无线电频率,也即行为人只能获得无线电频谱资源的使用权而不可能是具有排他性的占有权,更不是所有权。其二,对“频率”未作限定。我们知道,频率是单位时间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是描述周期运动频繁程度的量[2]。频率概念不仅广泛适用于力学、声学或光学中,而且也常常应用于电磁学或无线电技术中,尽管任何物体都有它本身性质所决定的而与振幅无关的频率,问题是罪状表述的为何种类型的频率并没有予以明确。其三,原罪状表述的行为方式“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也有失妥当。随着我国无线电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线电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我国通信、广电、应急、交通、铁路、航天、国防等各个领域,而且无线电业务的种类日趋猛增,新业务不断涌现,无线电通讯只不过是众多无线电业务中的一项,干扰无线电通讯也仅仅是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中的一种[3]。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行为方式并不仅仅表现于此,只要实施非法干扰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即使并未影响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也有可能妨害无线电其他业务,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三)行政程序前置失当
根据1997年刑法典原第288条的规定,“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这一行政程序是构成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只有在其非法实施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这种程序限制的情况下方可成立本罪,亦即行为人对“责令停止使用”的行政处罚不予执行是该罪成立的前置条件。这一前置性规定虽然能够提前制止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造成的危害,防止不法行为进一步升级,符合我国违法制裁“二元化”模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有机衔接,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但是这一前置性行政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障碍重重,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其一,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非法使用无线电频率的个人或单位往往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或隐蔽性。譬如,一些不法分子将“伪基站”设备安装在汽车里面非法使用,极轻易地流动到人流密集区或商业繁华区,这些违法行为人则可能是远程遥控无线电(站),严重干扰公用电信网络信号,危及公共安全。然而,行政机关对之却难以查处,即使查找到隐藏的无线电设备,也可能找不到该不法行为人,更难以责令其停止使用,缺少这一行政前置程度何谈将其入罪化?其二,“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这一行政前置性程序原本起到拔高刑法启动门槛,限缩犯罪圈进而保障人权的功能,但却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的屏障。行为人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不管其后果如何严重,只要是第一次被查处,未经“责令停止使用”的行政处罚就不会构成犯罪,在被“责令停止使用”之前大肆非法使用,或者以不断更换行为人身份的方式继续非法使用,这便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怪圈:行政执法人员发放的责令停止使用通知书为数不少,而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却有增无减,最终导致刑事立案的寥寥无几,因为不法分子获得的收益远超于其违法成本。其三,网络信息时代下,无线电管理秩序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社会一种重要的特殊秩序,它关系到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公共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一旦实施而造成的损失将无法弥补。一些不法行为被行政机关查处时往往都已经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再以“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的程序性限制已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害性,反而是放纵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极不适应于网络数字化时代的需要。其四,从行政执行效果上来说,行政监管部门往往存在执法人员短缺、经费不足等不利条件,对非法使用无线电频率行为查处不利,加之懒政怠政、保护伞庇护等现实因素,现实中造成了一些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违法犯罪暗数,这就严重制约了行政处罚程序的启动,从而阻塞了刑事司法的介入。
(四)刑事责任配置过低
1997年刑法典中,立法者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只配置了一个法定刑幅度,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显然采取的是单一而又较低的法定刑幅度,刑罚配置明显偏轻。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来看,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无线电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的行为急剧上升,其行为方式多种多样,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大有差异,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或科研,危及到公共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对此类犯罪行为法定最高刑却只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法应对复杂多样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行为,单一而又偏低的法定刑幅度难以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从本罪与其最接近的犯罪即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相比较来看,立法者为后者设置了两个法定刑幅度,对于基本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结果加重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这样的法定刑配置远重于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最高3年有期徒刑,可谓天壤之别。既如此,刑罚的惩治和威慑功能大为削弱,无法有效打击严重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的行为,反而会助长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滋生。
二、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立法窘境的消解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修订
基于上述立法窘境,结合现实实践中出现的具体情形,《刑法修正案(九)》第30条将本罪作了重大修改,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删去“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的构成要件,不再成为构成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前提条件,行政处罚亦不再作为本罪的前置性处理程序。这与其说是立法技术成熟的表现,不如说是立法进一步严密法网的彰显,不仅降低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从而弥补了法律漏洞,而且有利于对本罪的司法认定,加大了对我国无线电频谱资源的保护力度。
第二,由“结果犯”转向“情节犯”,即将“造成严重后果的”修改为“情节严重的”,有利于适应社会实践中案件的复杂多样性,起到提前保护法益的作用。并且相应地调整了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方式的罪状表述,不仅将“占用频率”修改为“使用无线电频率”,而且将“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修改为“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进一步明确了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了理论上的模糊和实践上的纷争。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明确了两类行为,并且这两类行为构成犯罪均需要充足“情节严重”的程度。
第三,增加了一个加重的量刑档次。《刑法修正案(九)》对1997年刑法典第288条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在“情节严重”的基本犯之后,又增设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犯之规定,并配置了相应两个档次的法定刑幅度,使本罪的法定最高刑由3年有期徒刑一次性提升到15年有期徒刑。很明显,加大了刑法对此类犯罪的惩治力度,从而提升了本罪的威慑效应。
(二)《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修改理念的转换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修改是在现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风险社会渐行渐近,需要刑事立法转型的大背景下做出的立法审视,体现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立法活动向纵深发展和立法理念逐步转变之演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结果犯向行为犯的转变。
毋容置疑,网络数字时代的到来正悄无声息地助推风险从幕后缓缓迈向前台。晚近以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蕴含的风险无处不在,无处不有,风险不断扩散并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成为现代社会难以割舍的组成部分。风险不仅给人们开辟了较为广阔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诸多隐患,并渗透着不确定性的危险,即风险的远程效应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一些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大幅度增加。然而,这些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我们还必须如影随形,因为它们不仅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有用性与必要性,而且对于现代人的生活不可或缺。所以,即使这种行为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或结果,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也应当允许,如果禁止所有的危险行为,社会发展将停滞不前,这就是被允许的风险理论[4]。因此,在风险社会情势下,大量的日常行为都附随着对他人法益侵害的危险或风险,甚至于大量的鲁莽地对待法益或有意识地冒不正当风险的行为与心态也形同寻常[5]。那么,刑法面对控制风险的治理在立法转型上作何调适?刑法无法简单地以风险最小化或根除风险作为追求目标,而只能设法去控制不可预测的风险,尽量放任被允许的风险或公正地分配风险[6],做到有的放矢。既如此,刑法中危险犯或行为犯将大量存在,而结果犯势必日渐式微。
人类逐步迈向工业社会以后,同时也步入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无线电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新技术在带给人们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促发了诸多风险,使得意想不到的风险不断凸显,风险的扩散化与日常化不断推进。与此相应,犯罪的形势与样态也会作与以往不同的演变:一是抽象危险犯、持有犯与行为犯将远超结果犯而在刑法中大量涌现,在这些犯罪中,“结果”已不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素,结果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性明显下滑;二是刑法中不断出现很多不以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条件或犯罪既遂条件的犯罪;三是在某些以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要素的犯罪中,结果的要素逐步被剔除,其结果的意义已不再是刑事归责的根据和基础,仅在于作为启动刑罚权的条件或限制刑罚权的射程范围;四是自然犯与法定犯存在动态的相对性,原来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的自然犯将逐步被法定犯所僭越。相对于自然犯,法定犯存在领域广泛,行为所涉及的关系更加复杂多样,于是,传统的“自然犯时代”逐步迈向“法定犯时代”[7]。
犯罪的形势与样态的变化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传统刑法理论的变革,刑法在承继追求报应的同时更加关注风险的控制。首先,在刑事立法中,结果犯所占比例将大幅度下降,而法定犯所占比例将不断飙升,立法者多采行为犯模式来设计罪刑规范,以彰显刑法的预防机能;其次,刑法介入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明显,作为结果的危害已不再是刑法视阈所关注的重心;最后,刑事惩罚的归责基底愈发不倚重于现实的危害结果,而取决于具有危险性的不法行为本身。
然而,刑法圈与公民自由权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无论是罪名的扩展抑或是新罪名的增设,还是刑罚的扩张,都意味着刑法圈的膨胀和公民自由权的限缩,因而必须理性地处理好两者的完美平衡,使得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同时亦是犯罪人的大宪章[8]。从犯罪圈大小与刑罚程度的有机组合和比例搭配来看,我国的刑法结构在顺应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向下逐步迈向“严而不厉”,注重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下沉某些具体犯罪的入罪门槛,刑事立法模式显示出由结果本位向行为本位的转向。从《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所作的重大修订中便可感知,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不仅消去了“经责令停止后拒不停止”的前提条件,使得行政处罚不再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置性程序,而且将“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结果修改为“情节严重”的行为,增设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行为,这些均表明了刑事立法由结果本位逐步向行为本位的华丽转身。因为在现代无线电技术发达的情势下,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灵活的流动性和潜在的危险性,一旦实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无可挽回。如果对本罪再坚持结果本位的设罪模式,其行为所蕴含的潜在危险一旦变为现实的危害,会严重侵害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甚至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航空安全乃至国防安全。相反,在本罪由结果犯转向行为犯之时,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刑法保护法益的早期化,使刑法提前介入,在严重危害结果尚未呈现出来的时候,果断惩治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能够更好地保护法益。
三、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需要理清的若干问题
(一)行为方式的正确理解
《刑法修正案(九)》第30条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那么,对修订后本罪的行为方式应该如何准确理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论者认为,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包含以下几类违法行为: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情节严重的;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情节严重的;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9]。对此笔者并不予认同。根据刑法规范文本表述的特点和规律,惯常以“……的,处……”的规定模式描述罪刑规范,其中语句之间有逗号隔开,整个表述为一个意思的完结。本罪中两类行为方式用“或者”连接,紧接着的“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实际上是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行为方式所共有的构成犯罪的要件。基于此,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违反国家规定,主要是指行为人违反了国家《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有关无线电台(站)或频率设置或使用的规定[10]。因为本罪属于法定犯,同时具备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两种属性,而行政不法是刑事不法的前提和基础,刑事不法是行政不法在刑法上的法律后果;二是实施了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的行为。可见,本罪的行为方式因侵犯的犯罪对象不同而分属于两类违法行为;三是实施了上述违法行为还必须达到“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
作这样的理解是基于以下法理根据:其一,作上述理解符合法律用语表述的习惯。虽然汉语用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歧义,但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习惯于一定的用语表达,并已约定俗成;其二,作上述理解有利于限缩本罪的行为方式,防止不当地扩大处罚范围;其三,作上述理解符合体系解释的基本要求。刑法条文需要刑法解释来达致通向司法适用的坦途,基于体系解释的目的来阐释刑法条文的法律意义时,不仅需要关注刑法条文本身所涵摄的意义,而且需要关照刑法文本内部之间的体系关系,甚至于需要关照刑法文本与其他法律文本之间的体系关系,以便使刑法解释达致刑法文本内部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和谐一致。从体系解释角度来看,作上述理解是与刑法分则诸多具体罪名像非法采矿罪等的行为方式具有一致性,符合同类解释规则。
(二)“情节严重”的准确把握
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由原来的结果犯转换为情节犯,这是本罪内在构造的一大变化。我国刑法分则有许多条文在对某种具体犯罪罪状描述中使用了“情节严重”,其意义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作为构成要件的“情节严重”;二是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情节严重”。对于前者,某种行为只有达到或超过“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成立犯罪;而对于后者,只要实施某种行为并符合相应的构成要件就可以成立犯罪,而“情节严重”只是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依据或从重处罚的情节[11]。不难看出,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应该属于前者,将“情节严重”作为其构成要件的程度标准,也即情节犯。这里的“情节严重”,是对某种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综合性评价,它涉及到犯罪构成的客体、主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等内容,并非独立于犯罪构成诸要件之外的他面呈现。那么,这就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情节犯”?我国刑法分则很多条文都规定了“情节严重”,并将其作为某些个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惯常的刑事立法例曾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早就指出,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随处可见的“情节严重”,其内涵和外延都极为含糊,它不仅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且也是区分重罪与轻重的界限,那么其含义为何,完全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而普通民众则无从知晓,是立法粗疏的一种表现[12]。然而,在笔者看来,刑法以“情节严重”而设置的情节犯既不是立法粗疏,也不是立法失误,而是立法技术高明的一种体现。其一,“情节严重”具有一定韧性,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避免法律的朝令夕改,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尽管这种规定模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它并不等于含混性。其实,模糊性是伴随着事物的复杂性而无法精确描述产生的,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具有生命力;其二,“情节严重”的规定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亦不同于立法的粗疏性。任何法律的规定都无法穷尽千姿百态的具体事实,而法律语言所要求的简约性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实际上法律规定的越具体,其漏洞之多也就越突出。合理地运用“情节严重”的规定模式,不仅可以避免法律表述的冗长而符合法律文本的简约价值,而且可以使司法人员乃至普通民众了解、学习和掌握;其三,“情节严重”的规定模式可以给司法人员预留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更加能够维护个案的公平正义;其四,“情节严重”的规定模式并不是无从探知,它可以依靠司法人员对法律的解释予以适用。
问题之二是如何把握修正后的“情节严重”?“情节严重”的设定模式巧妙地绕开了社会上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现象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以及立法无法预见的诸多困扰,立法者适用“情节严重”这种模糊性和抽象性的规定模式能够使法律应对复杂的现象和变化的形势。但这样的立法模式,刑事立法之后,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归类等方面的任务将会很繁重,而且适用法律的司法人员需要经常学习和吸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那么,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是《刑法修正案(九)》颁行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予以判定。
其一,通过“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结合无线电管理执法和司法实践,适时地颁布司法解释以概括或列举式对“情节严重”作如下认定:一是概括或列举在行为方式上起主要作用而提升社会危害性的情形。如有聚众、组织、策划、煽动、教唆,或不听劝阻,或威胁、殴打或暴力阻碍行政执法人员等情形;因非法设置、使用无线电技术、设备或方法等因素而导致的现实危险,足以危及到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或公共安全等情形;二是概括或列举因违法行为的地点重要而提升社会危害性的情形。如非法扰乱国家军事或国防工程设施等无线电频谱,危及到国防安全,非法扰乱机场、港口、铁路、轨道交通或国家重要工业区、重要景区、国家机关等无线电频谱,危及到公共安全的;三是概括或列举因违法行为地的环境条件恶化而提升社会危害性的情形。如在发生地震、山洪、疫情或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等;四是概括或列举因对抗行政处置而提升社会危害性的情形。如两年内因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扰乱无线电通讯秩序,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该类行为的;五是概括或列举因违法行为严重侵犯公民通信权而提升社会危害性的情形。如非法设置、使用“伪基站”、“黑广播”、移动通信干扰器、卫星通信干扰器等设备干扰公用电信或公共广播电视网络信号,造成一定数量用户通信中断一定时间的;六是与前列行为相当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其二,通过“两高”不断颁布指导性案例予以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从2009年6月1日起就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并不断颁布指导性案例。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改革。譬如,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陆续颁布了一些指导性案例,2011年,一次性颁布4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指导性案例,2013年,公布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对于促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规范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两高”何不尝试颁布一些有关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方面的指导性案例?如果有“两高”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指导性案例的公开发布,能够供各级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研究者和全国公民阅读与查询,会逐步形成一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及普通公民可以轻松地查询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的“报价单”[13]。这些“报价”最初可能不太好把握,甚至不可思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市场”中就会逐步形成“行价”。因为法官等研究指导性案例,就是一种学习、参考和借鉴的过程,最终会潜移默化地内化于心,同种情况、类似情况的非法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犯罪案件就会得到大致相同的处理。不仅如此,还有该案件的当事人、律师、媒体、学者以及普通公民同样会对这些“报价”感兴趣,而且会用这些指导性案例的“报价”来评判、权衡新的裁判。一旦两者差别悬殊,上诉、质疑、舆情等这些压力便扑面而来,这实际上又从另一侧面促使法官尽显量刑规范化,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必将越来越少。因而,指导性案例可以使得“情节严重”有章可循,不仅可以实现同案同判,而且也能够提升法官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还有意外的“收获”,在这个“市场”中,还能够减少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一旦在形成“行价”的“市场”中冒出一份“另类”的异常裁判,必然会引发更为严厉的公众声讨。
“情节严重”有了进一步认定标准之后,“情节特别严重”自然更为容易把握,它是在“情节严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社会危害性的升格性情节。
(三)本罪与相关罪名的界分与竞合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最为接近的罪名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两罪的界分主要在于:其一,前罪隶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后者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因而前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无线电通讯的管理秩序,后者侵犯的法益则是公共通讯、传播的公共安全;其二,前罪侵犯的对象是无线电台(站)和无线电频率,而后罪侵犯的对象则是正在使用中的广播电视设施和公用电信设施;其三,前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而后罪表现为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虽然两罪在理论上的区别较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可以竞合的,因为在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中,其破坏行为可以表现为直接对有关设施进行毁损,也可以表现为采取像截断线路等方法使有关设施无法正常工作,无论怎样,都有可能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危及公共安全,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就会出现一个行为触犯两个不同罪名的情形,也即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罚。譬如,近些年来对于使用“伪基站”设备的违法犯罪活动,在司法审判中适用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而有些案件却适用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还有部分案件一审适用的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而二审却改判为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可见,两罪在司法适用中往往纠缠在一起,需要进一步厘定。实际上,不只是发生这两个罪名竞合的问题,亦有其他罪名竞合的情形。譬如,一些不法分子使用“伪基站”设备是为自身经营的产品或活动发送广告或是从事广告代发活动或搜索公民信息,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设备从事诈骗活动或者进行考试作弊等。对于这些不法行为可以牵连犯进行处理,其方法行为可能触犯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或非法经营罪等,而目的行为则触犯了虚假广告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等罪名,可择一重罪处罚。这在2014年“两高”及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的意见》中足以印证,该意见明确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可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非法经营罪、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等8项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无形资源,无线电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下,加强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刑法保护,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288条规定的扰乱无线电秩序罪在立法上存在明显的弊端,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立足于我国治理破坏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现实需要,《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作了科学合理的修正,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结果犯到行为犯的华丽转身。相应的司法解释的跟进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对有效治理妨害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必将产生积极的预防作用。
[1]王文娟,朱欣.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回顾与展望[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45-50.
[2]何爱鲜.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分析[J].中国无线电,2016(2):32-35.
[3]赵远,商浩文.论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立法修改[J].法学杂志,2016(8):98-107.
[4]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37.
[5]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政法论坛,2009(1):82-92.
[6]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26-139.
[7]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
[8]仝其宪.民族刑法变通权的理论境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5-50.
[9]王文娟.浅谈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J].数字通信世界,2015(11):28-33.
[10]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37.
[1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3.
[12]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99.
[13]赵兴洪.确立先例标准促进死缓适用之规范化[J].法学,2009(11):79-87.
Legislative Dilemma and Resolution of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Radio Regulation:An Analysis of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9)
TONG Qixian
(Law Department,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Xinzhou 034000,China)
Before the revision on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radio regulation,there exists obvious legislative defects:the lagging of setting up the crime patterns,the misconduct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preposition and light sentence of criminal cases.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9)revised the crime pattern,reduced the threshold for conviction and modified the behavior element.In addition,it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rime from the consequential offense to the behavioral offense in the legislative idea to fi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riminal policy about“Strict but not Severe”.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radio regulation,we need to clear some problems,which is,th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r,the accurate grasp of plot crime and the concurrence and boundary between the crime and related crimes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crime of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radio regulation;Criminal Law Amendment(9);plot crime
D924.3
:A
:1673-8268(2017)01-0052-08
10.3969/j.issn.1673-8268.2017.01.009
(编辑:刘仲秋)
2016-09-11
仝其宪(1974-),男,河南濮阳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