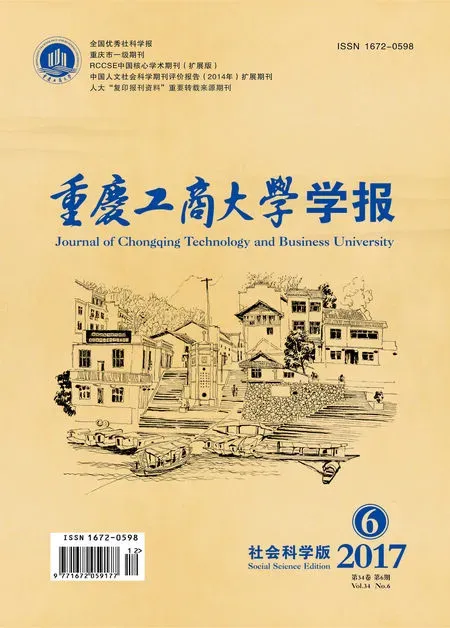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
2017-03-22罗迪江
罗迪江
(广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
罗迪江
(广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生态翻译学在翻译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贯通融合性。它以生态学作为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确立了生态思维与翻译活动之间的有效契合,并通过生态取向的整体主义方法为翻译活动提供一种新思路,它所独有的生态范式和生态结构,赋予翻译活动整体的研究视野,这使它与传统翻译学形成鲜明对比,为当代翻译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路向。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翻译;方法论
引言
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始于生态翻译学先驱者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成熟之作源于《生态翻译学:诠释与建构》(2013)。作为一种相对年轻而又成熟的生态分析方法的确立,生态翻译学迎合了20世纪70年代哲学的生态整体转向趋势,其兴起和发展与20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生态思潮与生态研究取向具有密切关联。生态翻译学大力倡导从宏观生态理性角度来研究翻译,并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的生态范式、生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平衡和谐、生态移植、译者责任、适者生存等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逐步健全了生态翻译学的学科体系,充分证明了生态翻译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就此而言,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并为考察翻译生态范式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思路。
一、翻译生态取向的路径突破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生态分析(生态取向)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日益显示出其独有的功能和巨大的魅力。它作为一种翻译活动的解释方式和翻译理论的探索方法,本身就处于动态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生态思维的引入和生态翻译学的提出,无疑是翻译学发展的路径突破与方法超越。因此,对生态翻译学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来源的考察与探究,以及对生态翻译学形成的基本脉络和理论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生态翻译学在当代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意义,更加合理地把握其方法论体系。
(一)生态翻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序链
胡庚申(2004)对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特征进行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基础上,并且接受了“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的论断。胡庚申(2010a)明确指出,翻译生态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是生态翻译学的存在性和客观性的重要理据;寻找关联、相似或同构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是一个寻找规律、逼近规律的过程。虽然国际翻译界曾经以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讨论,例如彼特·纽马克(Newmark 1988:95)的翻译生态学特征、罗森纳·沃伦(Warren 1989:6)的翻译认知和生存模式、戴维·卡坦(Katan 1999:45)的翻译生态环境,但他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系统地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翻译活动,更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构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模式。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生态”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特征,成为了构造生态翻译的新的“根隐喻”,使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获得了内在关联,使适应/选择成为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关联序链的核心概念,其意义就在于“使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构成一个新的具有动态性、层次性、个体性等特征的和谐共存、生生不息、水乳交融、互相交织的范畴”(方梦之2011)。自此,翻译生态取向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旨在回答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何为译”——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谁在译”——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怎样译”——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为何译”——适者生存、强者长存、译有所为(胡庚申2010b)。
在生态翻译学领域里,以生态的方式看待与探究翻译理论,成为了胡庚申的特识。“生态”具有了翻译方法论的意义,既成为胡庚申翻译思想的主导概念,又成为生态翻译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对生态翻译学的思维方式与翻译活动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此而言,翻译活动是生态的。那么,它要走向何处或说它生态的趋向是什么呢?对此,胡庚申(2011)为指明了明确的方向:“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视角,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归,以‘自然选择’原理为基石,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换言之,作为一个具有显著‘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生态翻译学倚重翻译‘生态’、取向文本‘生命’、关注译者‘生存’,是一项利用生态系统的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整合性研究”。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要完成真正的和谐统一与互联互动,翻译生态环境要成为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翻译存在的基础,成为对译者而言生态存在着的既关注文本生命又关注译者生存的“存在者”与“此在者”。
(二)生态翻译学建构的基础:生物进化论
21世纪初叶由胡庚申创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被视为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与经典思想。它以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分析对象,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解释翻译过程,以适应选择为机制对翻译活动的刻画作为展开过程,以适者生存与汰弱留强作为译品生存的结果,其主要工作就是对达尔文核心思想的利用与移植,以及对生物进化论思维的引入和借鉴。
生态翻译学的思想来源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与达尔文的思想相对应,生态翻译学明确肯定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通融性,强调了翻译的实现就存在于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生态翻译活动中,源于文本生命、适者长存与译者生存之中的翻译活动,从而摒弃了微观层面的单一模式的传统翻译论思想。生态翻译学特别强调翻译的整体主义思想,并且立足于翻译活动的生态环境,由此任何翻译活动不再是单一静态的,而是整体动态的。由于翻译本身是一个整体的生态活动,因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某种翻译策略而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胡庚申2004)。可见,胡庚申将生态翻译学的任务确定为“选择”与“适应”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寻找到最佳适应与优化选择的翻译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胡庚申(2008a)明确指出,将“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去就是:译者(译品)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在理论分析的基本模式和倾向性等方面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性与交叉通融性。这种关联通融性一出场就超越了传统翻译意义上对翻译活动的理解,它将翻译活动定格于一种宏观生态理性的视域里,一种翻译本质有望企及(具有深层意义的译论基础与译学体系)的理想和憧憬,为翻译生态环境下的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存在、适应/选择、适者长存等生态翻译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存在的庇护所、生命的栖息地、适者的守护人与适应/选择的优先权。
(三)生态翻译学形成与应用的理论必然性
首先,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翻译过程的整体主义思想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建构的起点。生态翻译学试图在方法论与认知论层面上建立一种关于翻译的生态范式,其实质是强调翻译作为生态取向与自然生态的一致性,并将其范式看作是从生态学视角以适应与选择为核心理念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综观的生态范式。其次,生态翻译学为不同翻译学理论与不同翻译研究途径建立了可供沟通的桥梁与渠道。从方法论特征来看,生态翻译学相对于语言学视角、目的论视角、文化学视角等翻译研究途径来说具有较大的方法论包容性和理论优势。它的立论视角是“生态”,是从生态的视角对翻译进行整体论思想的跨学科研究。它强调“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性与生态和谐性特征,它蕴含着“译学”“译论”与“译本”三个研究层次的关联,是其他别的翻译研究途径难于比拟的,因此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包容性。就理论优势而言,我们可以在一种生态系统中将翻译活动整体化与生态化,从而体现出“学”(译学)、“论”(译论)、“本”(译本),或者使“人”(译者)、“本”(译本)、“境”(译境)关联互动,有机融通、“三效合一”,构成一个平衡和谐的翻译研究“共同体”(胡庚申2013:21)。由于生态翻译学具有跨学科性与整体论性,在方法论上它力图从整体性对翻译活动进行生态介入与范式转换,并对翻译活动与翻译方法分析的整体背景下提出了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双重要求。总而言之,生态翻译学主张基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关性,将翻译活动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从适应/选择机制出发,将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等生态概念结合起来,从而对翻译活动的表征状态及其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较好而有效的描述与解释。它将翻译活动的内部翻译生态、外部生态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整合成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用以说明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共生互存与和谐统一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自始至终是受适应/选择机制调节的,因而它在本质上脱离了那种单一平面化的翻译模式的困境,给出了一条较合理的生态化路径与整体论方法。
21世纪初叶以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方兴未艾,朝向“生态”而蓬勃发展。它在其产生和演化过程中,广泛融入了现代整体主义分析的整体性思想,并与当代翻译哲学与翻译理论对译者、译文、译品、译论、译学的反思紧密相关,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因而,生态翻译学对于实现生态学与翻译学的内在融合,建构不同类型的翻译理论研究途径的融通互联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现代翻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与制高点。
二、翻译生态分析方法的创新
生态翻译学的生态分析方法具有自我完善和理论建构的特征,作为一种有效的翻译工具和手段,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对其理论本身进行修正和补充,它所具有的整体论思想和进化论思想为翻译分析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启迪性的思路。
(一)翻译的多向因果范式
生态翻译学引入了进化论思想,在方法论论题上它与整体论一脉相承,力图摒弃了单一的翻译模式,舍弃了以往翻译研究视角的单一化与平面化,力求将翻译活动的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关联起来,并由此把关注的焦点投置于翻译的生态整体性上,使翻译认识论的研究域面得以拓展。如果我们将以前的翻译研究途径看作是一种还原论视角下的单向因果范式,那么生态翻译学就是一种整体论视角下的多向因果范式。事实上,无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抑或是生态翻译学,它们都蕴含着整体论与生态学的思想。如此说来,生态翻译一开始就具有生态意义上的多向因果范式,它包含着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译者责任,彼此之间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统一体。从翻译生态到文本生命、从译者生存到译者责任,都蕴含着一种动态的互联互动与和谐共存,这种和谐共存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翻译学的窄式内容转向生态翻译的宽式内容,构成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多向因果范式。换言之,生态翻译学把翻译活动归结为一种多向因果范式,就必然地要引入生态学思想,而生态学思想则渗透了整体论的价值取向,与翻译学形成一种内在的整体性关联融通。一旦在翻译活动与整体论的价值取向之间搭取了由此及彼的桥梁,那么翻译活动的整体性及其多向因果范式就会得到实质性的贯通与强化。因此,当我们说生态翻译学具有宽式内容与整体论思想,其实就是表明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多向因果范式,既是源语、原文与译语系统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又是翻译生态环境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动态生成的宏观生态理性与和谐共生。这充分说明了生态翻译学“取向于文本‘生命’,关注于译者‘生存’,致力于翻译‘生态’”(思创·哈格斯2011),能够深入到翻译活动的各个层面,全面生态理性地把握翻译理论的整体结构。因此,开辟宏观生态理性道路和探讨创建翻译生态分析方法,已构成了当代翻译学研究与探索的译者责任与译者使命。
(二)翻译活动的生态回环反应式
生态翻译学吸纳了进化论思想,将翻译生态分析导向了语言、社会、文化、认知和交际等语境研究的广阔领域,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维度。21世纪初,基于对以往的翻译学理论的全面反思和对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阐释与借鉴,胡庚申意识到在翻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将“适应/选择”学说与翻译学结合起来,分析具有整体性的翻译生态表征过程。而胡庚申将“适应/选择”学说与翻译学进行结合分析的思路正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旨趣,它“将有望打破西方翻译理论的‘一统天下’并终结东西方翻译理论生态‘严重失衡’的局面;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东西方翻译理论平等对话的平台”(思创·哈格斯2013)。正是通过“适应/选择”学说具有翻译活动的复杂机制、内部准则与生态范式,翻译活动的生态性特征才能够得以形成。换言之,翻译活动在“适应/选择”的生态过程中形成了“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与“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可见,以“适应/选择”为核心思想的生态翻译学有助于理解翻译生态环境下翻译与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之间的协调性特征与关联序链关系。
从适应/选择的概念本质和目标来看,生态翻译学试图运用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中的核心思想,并对翻译生态的表征特征进行更加精准的理解。具体来说,适应与选择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下的本能,是翻译过程中凸显“译有所为”的实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那么,翻译就被描写为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胡庚申2008b)。译者/译品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通过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手段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在适应与选择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形成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译品、翻译生态环境与适应/选择之间所谋求的“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翻译生态回环反应式:
译者/译品为了生存和发展 (必须)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通过) 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 (达到)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最终) 译者/译品要生存和发展。
总之,在翻译学研究“朝向生态而生长”的路途中,胡庚申无疑是促成翻译学与生态学紧密结合的开拓者,使翻译活动突破了单一模式的障碍而能够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得以生态化与整体化。生态翻译学对整体论与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引入,既说明了生态翻译学理所具有的关联通融性特征,这使它能够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与其他翻译研究途径的互通和借鉴;也反映出21世纪初叶以来人们对翻译学研究的开放性态度与跨学科思维,充分展现了生态翻译学方法论的创新意义。
三、生态翻译学的整体性特征与生态范式
任何一种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整体性,是一种立足于宏观生态理性而对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何为译、谁在译、怎样译与为何译——进行根本性地回答,它强调翻译就是适应与选择,其核心理念就是以译者为中心,以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主导方法,凸显了翻译就是要以适者生存为原始目的,建构了一个将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间桥接起来的“论学一体”的同源贯通的生态范式。这种范式使生态翻译学超越了以往不同的翻译理论研究模式,与其他的翻译理论研究视角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翻译本体生态系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翻译学研究的内涵和结构。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的贯通互融
不可否认的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分析过程与展开思路与胡庚申后期的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与同源性。随着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由微观/中观层面上的适应/选择朝着宏观生态理性的转变,生态翻译的渗透力实际上是将翻译活动的理解确立在整体论性的生态取向基础上,逐渐将翻译研究从适应/选择的分析转变为翻译生态的研究、从单一的翻译研究视角转变为生态化整体的研究。由此,以生物进化论作为重要理论启示来源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和后续发展的生态翻译学,它们是“同源”的,是一种源委的关系和继承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胡庚申2013:61)。
早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也涉及生物进化论,在理论内核上并没有与生态学真正结合起来,而生态翻译学则深化与扩展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内涵,并且对翻译适应选择论具有很大的兼容性与包容性。可以说,生态翻译学从理论上突破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观与微观”层面思维,彻底系统地以生态学为“根隐喻”演绎提出平衡和谐、多维整合与多元共生等具有生态取向的翻译原则,衍生出一系列诸如翻译生存、翻译生态、翻译生态环境、群落移植、适应性选择、选择性适应、求存择优、和谐共存、共生互动等等具有生态特征的翻译术语,扩展了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视角。这样,生态翻译学的生态分析路径相比较于翻译适应选择论而言,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超越,更具有哲学理性的、宏观生态理性的和整体论思想的方法论优势。
翻译生态分析的意义在于对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翻译群落生存进行合理解释,而生态翻译学则通过翻译的生态性和翻译的整体性的拓展使这种解释效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拓展。因此,生态翻译学并没有否定以往的翻译理论研究视角的翻译效力,而是遵循宏观生态理性,以生态学为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从而更加凸显了翻译生态范式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有效度。这种生态范式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翻译适应选择论赋予了生态学的解释,并且有效地实现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的贯通互融,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空间。
(二)翻译生态化整体方法的构建
当我们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源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语言与文化、社会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生存与存在看待翻译时,我们会发现当前的翻译研究视角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向因果范式与方法立论的单一平面化。这就从根本意义上要求获得一种解决翻译研究存在问题的正确途径,使译者的存在和译品的存在、作者的存在与源语的存在、翻译的生命真正达向和谐共生,促进翻译生存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统一。这种方法就是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生态化整体方法——就是指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的存在、看待译者的存在和作者的存在、看待源文的存在与译品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适应生存”与“汰弱留强”的思维视野、思想境界、价值取向与翻译原则。
生态翻译学伴随着自己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越来越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整体思维和生态理性,正是这一点生态翻译学超越了单向因果范式的翻译研究视角,赋予了翻译理论全新的解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站在以译者为中心与整体性思维的立场上,译者必须在翻译活动中出于翻译生态的考量既要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又要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并通过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实现翻译之“译有所为”的生态化整体,这正是生态翻译学整体性特征的体现。翻译生态本身具有一种潜在的整体性与动态性,这就需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充分展示自己的适应能力与选择能力,遵从自己的译有所为。它意味着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译者要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适应性选择,就必须掌握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以及翻译与语言、文化、社会、交际、认知之间的协调性,以便做出动态的、最优的、整体的选择性适应。
翻译生态化整体方法能够遵循宏观生态理性,特别强调翻译的整体性,本质上说就是努力打破以往翻译理论研究视角的单向因果范式,除掉单向因果范式的“蔽”与“魅”,使翻译活动重新恢复对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整体和完整的思维方法与生态意识。因此,翻译生态化整体方法视域中的整体,既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整体,亦不是脱离翻译环境的整体,而是翻译生态意义上的整体。翻译的整体在于,翻译是以一种生态场的形式存在着,因而翻译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并永远是“适应生存”与“汰弱留强”的整体,最终通过译者的生态营造来实现一种翻译环境的生态完美、文本生命的和谐互生与翻译群落生存的和谐统一。
概而言之,生态翻译学是一个极为有用的“思想引擎”与“翻译研究的战略意识”(罗迪江2016),为翻译理论研究及其分析方法的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它超越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译方法,其自身在理论建构时结合了生态学的前沿成果,从翻译生态、翻译环境、翻译存在、翻译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群落生存等方面为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适应选择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而使这些术语被赋予了全新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意蕴,从而使其与生态学相容而展示出生态学的与整体论的路向,符合当代翻译学发展的跨学科性与理论交叉性趋向,受到了众多翻译学家与学者的青睐与拥护。
四、结语
通过21世纪生态翻译学所展现出的丰富理论视域和生态分析方法的梳理与厘定,我们清晰地看到翻译学家胡庚申对于翻译学及其方法论特征所做的富有创见性的生态学解释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态综观。它将翻译的生态研究方法从横向上不断扩展,从纵向上不断延伸,不仅力图实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间的融合,而且逐步有意识地将翻译生态分析的基础锚定在贯通翻译理论与翻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翻译学科与哲学理性的翻译生态语境思维基础上,实现了翻译学在宏观层面上的理论建构。生态翻译学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理论方法与研究路向,“既有新的定位和取向,更有新的发掘和超越,是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的译论新发展”(胡庚申、刘爱华2016)。这正是它能方兴未艾并应用于不同翻译理论视角的分析和解释的生命力所在。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分析方法中的一种独特研究视角和理论,它的发展和创新在当代翻译学的整体推进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整体论性与理论交叉性,与这种特性紧密相关的具有最大包容性的生态学思想与整体论思想为生态翻译学理论建构的趋向提供了高瞻远瞩的引导和牢不可破的基础,从而在未来的翻译学发展道路上开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探索平台。
[1] Katan, D. Translating Cultur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99.
[2]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Prentice-Hall,2006.
[3] Warren, R. The Art of Translation: Voices from the Field [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
[4]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J]. 上海翻译, 2011(1): 1-5.
[5]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4): 1-5.
[7] 胡庚申. 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 上海翻译, 2008a(2): 1-5.
[8] 胡庚申. 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新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b(4): 90-95.
[9] 胡庚申. 翻译生态vs自然生态: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J]. 上海翻译, 2010a(4): 1-5.
[10]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 外语研究, 2010b(4): 62-67.
[1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中国外语, 2011(6): 96-100.
[1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诠释与建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13] 胡庚申,刘爱华. 新的定位, 新的发掘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到《生态翻译学》[J]. 翻译界, 2016(1): 13-18.
[14] 罗迪江. 反合表征的辩证互补与自然生成[J]. 外国语文, 2016(3): 62-68.
[15] 哈格斯. 生态翻译学R & D报告: 十年研究十大进展[J]. 上海翻译, 2011(4): 1-6.
[16] 哈格斯. 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进展进展与趋势[J]. 上海翻译, 2013(4): 1- 4.
TheMethod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MeaningsofHuGengshen’sEco-Translatology
LUO Di-jia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Guangx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GuangxiLiuzhou545006,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s a whole, eco-translatology makes a manifestation of ever more marked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ers to ecology a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ology and constructs a useful conne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translating. In a sense, it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way to translating by means of ecology-oriented holism and endow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ng by virtue of its unique ecological paradigm and structure, which endows methods and paths which we can treat in process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ology.
Hu Gengshen;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6.016
2017- 04- 07
2017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JGY2017097)“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科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机制研究”;201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15BYY002)“仫佬语话语材料的收集与语言文化研究”
罗迪江(1974—),男,壮族,广西忻城人;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H059
A
1672- 0598(2017)06- 0109- 06
责任编校:杨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