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
2018-01-05何哲飞
王 琼,何哲飞
(常州大学 信息数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
王 琼,何哲飞
(常州大学 信息数理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家庭化流动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本文利用8个城市15998个样本,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家人随同流动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非个体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远多于个体流动群体,家庭消费率、居住社区和社会融入等因素成为影响不同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流动形式;生活满意度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2016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5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生活就业,对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不断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注重自身精神世界的建设。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是其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1],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其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以及落户的意愿[2],推动其社会融合和城镇化进程。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表明,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家庭化流动这种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相较于个体流动,家庭化流动使得整个家庭在流入地生存发展,更可能成为永久性居留的新市民家庭,从而更能反映人口流动的社会影响。
生活满意度是根据自身判断和标准,个体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评价。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是近些年才开始针对流动人口研究生活满意度的。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均可能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Watson和Clark,1984[3];Louis和Zhao,2002[4])。流动人口的休闲生活、人际关系、保险制度和社会融入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5]。文鸣和王桂新(2009)对上海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调查发现社会经济、邻里关系对生活满意度都有影响[6]。个体在正常的状态下普遍具有改变生活面貌、克服困难的信心,但社会中一些不可控因素往往会降低其心理控制力,增加其生活无助感,从而产生消极情绪,个体糟糕的健康状况将会降低生活满意度。杨东亮和陈思思(2015)还发现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生活得更幸福[7]。
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但针对不同流动形式的流动人口群体进行研究还较少。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不同流动形式下的流动人口群体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为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水平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全国8个城市(包括北京、嘉兴、厦门、青岛、郑州、深圳、中山和成都)流动人口进行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8]。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问卷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信息、就业与收入支出情况、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情况和社会融入等内容,有效样本总数为15998份。基于该调查问卷,本文将对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变量及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分析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根据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调查问卷,以被调查者对问题“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的”的同意程度(其中非常不同意赋值为1,非常同意赋值为7)测量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为方便研究,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水平,将同意程度小于4的归为生活满意度水平低,同意程度等于4的归为生活满意度水平一般,同意程度大于4的归为生活满意度水平高。
2.解释变量
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很多,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个体特征和经济社会层面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引入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家庭特征、制度特征、社会融入以及城市规模进行研究。
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以及就业身份,其中文化程度划分为初等学历、中等学历和高等学历,健康状况划分为不好、一般和好。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反映了其社会地位,为了研究方便,将就业身份划分为雇主、自营劳动者和雇员三种。流动特征包括本次流动时间、流动范围以及流动形式。流动时间指本次进入流入地后的时间,期间离开到返回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流动范围包括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流动形式分个体流动、夫妻流动(子女不随同父母流动)和家庭流动。
家庭特征方面,流动人口大部分是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选择外出打工,因此,家庭总收入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的影响。除了将家庭月总收入作为影响因素外,家庭消费支出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家庭月总支出与月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除此之外,家庭的主要休闲模式和居住状况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制度特征方面,本文选取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状况作为反映流动人口的制度特征指标。社会融入方面,选取与本地人交流的语言、与本地人相处情况、社会认同感以及主要的邻居作为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指标;城市规模以流入地城市人口数量的对数衡量。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上述定类变量取值进行合并处理。
二、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表现特征
(一)总体特征
根据受访者对问题“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的”的回答选项进行统计,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对目前生活满意的人口比例高达56.79%,超过一半;满意度水平一般的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23.56%和19.65%,其中非常不满意的仅占3.02%,如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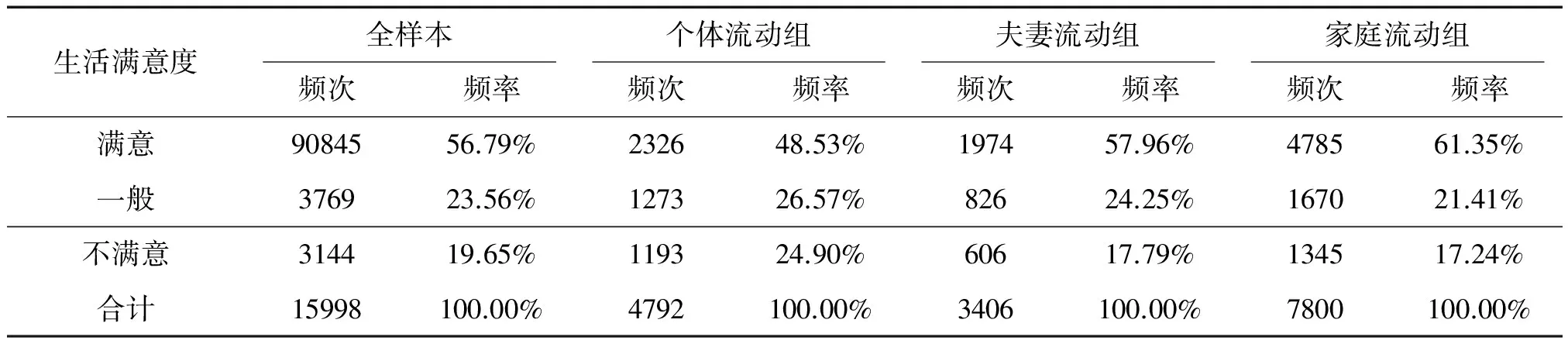
表1 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分布
流动人口的流动形式主要有个体流动、夫妻流动(子女不随同流动)和家庭流动三种方式,分别占比为29.95%、21.29%和48.76%。可见约有一半的流动人口是以家庭流动的方式进行流动的。对全样本划分为个体流动、夫妻流动和家庭流动三个子样本。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水平分布,如表1所示。
在15999名受访者中约有56.79%对目前生活满意。对个体流动子样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发现个体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表现不如全样本,感觉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均高出全样本,合计占比超过一半。夫妻流动子样本的表现与全样本的差异不大,感觉一般和不满意的比例高于全样本。相较而言,家庭流动子样本感觉满意的比例达到了61.35%,明显好于全样本的表现。这也说明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确实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本文对个体流动、夫妻流动和家庭流动这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两两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个体流动子样本与夫妻流动子样本、家庭流动子样本之间,其生活满意度的均值及其波动性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夫妻流动子样本与家庭流动子样本的生活满意度虽然波动性差异不大,但均值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些说明本文将流动人口按不同流动形式进行样本划分的假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进一步验证了我国流动人口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需要针对不同流动形式的流动人口群体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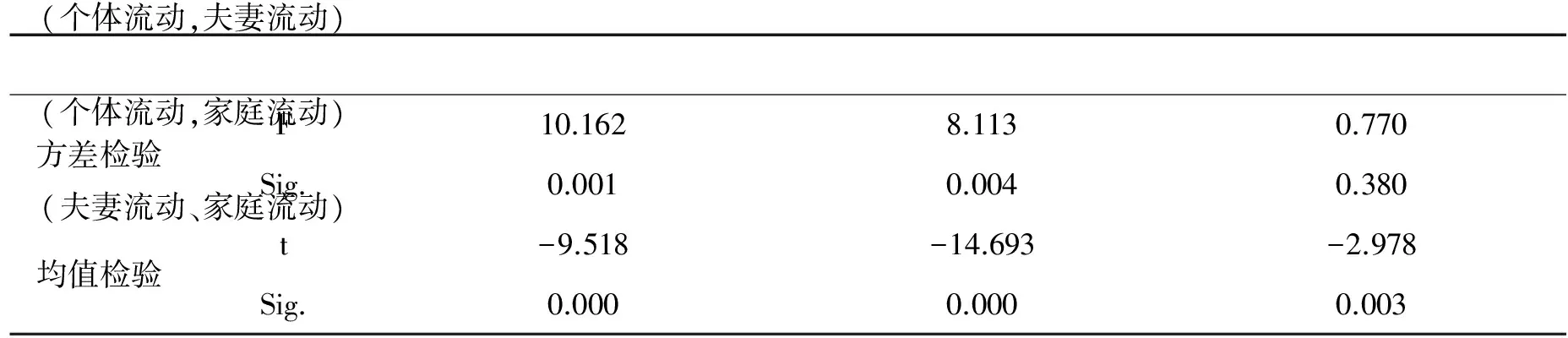
表2 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性检验
(二)异质性特征
流动人口的性别、婚姻、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等都是其个体异质性的基本特征变量,经常被用来分析这些属性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15998个样本中,有8799个男性个体,占55.00%,有7199个女性个体,占45.00%,男性样本量略多于女性。男性样本生活满意度略低于女性,平均水平分别为2.349和2.401,流动人口性别差异对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影响。
婚姻状况方面,再婚、离婚和离异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少,因此将之归于已婚群体。未婚人口有4057人,占25.40%,已婚人口有11941人,占74.60%。未婚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平均水平为2.23,明显低于已婚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2.42。
户口方面,农业户籍的有13926人,占87.05%,非农业户籍的有2072人,占12.95%。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分别为2.37和2.378。可见,户籍对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大。
从流动范围来看,跨省流动的有8769人,占54.82%,省内流动的有7229人,占45.18%。跨省流动的人口略多于省内流动,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36和2.39,说明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水平存在一定的影响。
健康状况非常好、很好和好的有14201人,占88.77%,健康状况一般的有1738人,占10.86%,健康状况差的仅59人,占0.37%。健康状况越好,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满意度平均水平分别为2.47,2.44,2.30,2.10和2.02。
三、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一)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
流动人口对生活满意度的测度指标属于有序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根据调查问卷,将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依次设定1、2、3,分别表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对应概率分别为p1、p2和p3,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其表达式,如式(1)所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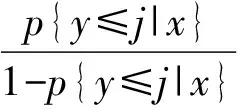
构建模型时,本文将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首先选择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等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1,分析了全样本中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然后,分别以个体流动和非个体流动为研究子样本建立模型2和模型3,考察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鉴于模型3中子样本的未婚人数较少,因此在模型3中剔除婚姻状况这一解释变量。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二)总体情况
由模型1可见,个体特征方面,民族对全样本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就业身份对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民族仅仅是流动人口的一个身份标签,不具备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能力。与女性群体相比,男性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更低,这与汤爽爽等[9](2016)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主要由于男性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较大。流动人口年龄越大,其职业级别往往越高,从而生活满意度越高。与未婚群体相比,已婚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更高,实际上,这应该理解为生活满意度高的流动人口结婚的可能性更高。文化程度方面,初等学历和中等学历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差异,而高等学历的流动人口往往拥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主要由于文化程度的高低可能会影响社会对其的认可度,从而造成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健康状况一般和好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就业身份方面,作为雇员和自营劳动者身份的流动人口拥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
流动特征方面,流动时间越长,流动人口越可能获得高的生活满意度;与跨省流动群体相比,省内流动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其生活满意度更高;相较于家庭流动形式,个体流动的群体更有可能获得低的生活满意度,而夫妻流动与家庭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根据流动形式将全样本细分为个体流动和非个体流动两个子样本,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三)不同流动形式子样本情况
从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来看,影响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大多类似,如民族、年龄、家庭消费率、居住社区、户口、主要邻居和自认本地人等社会融入方面。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主要为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就业身份、流动时间、流动范围、家庭收入、休闲方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本地人交流的语言以及城市规模等。
第一,个体特征中,民族和户口对不同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均无显著性影响。年龄大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更高。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就业身份对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同。这些因素并不显著影响个体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但却显著影响非个体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男性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女性,可能是由于非个体流动群体中男性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承担了较大的压力。中等学历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初等学历和高等学历,有着初等学历或是高等学历的流动人口,由于其较长的工作年限或较高的教育程度,往往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好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也较高,而自营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其他就业身份。通过交叉分析还发现,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更愿意选择家庭化流动。
表3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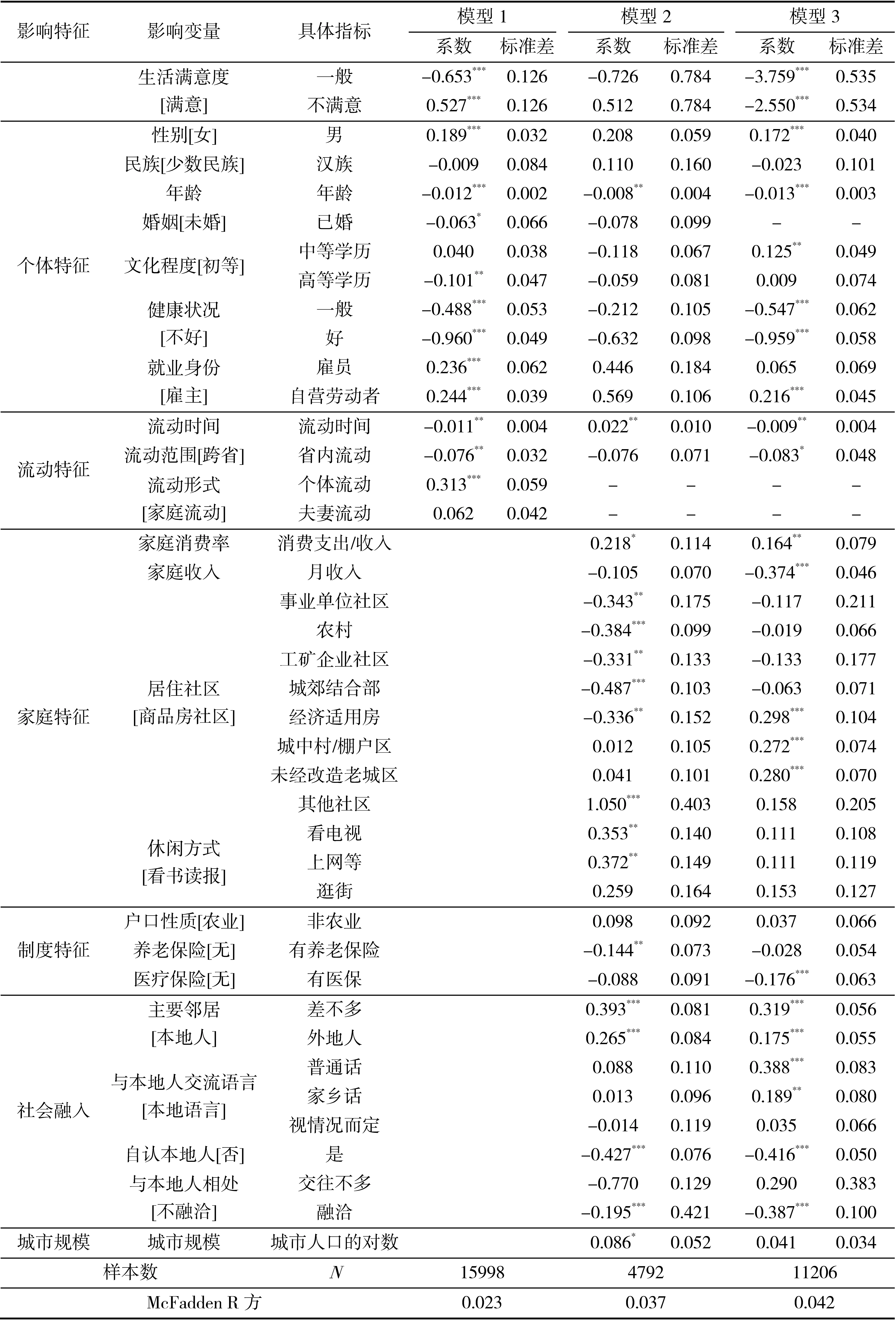
注:*、**和***分别为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
第二,流动特征中流动时间对不同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但却呈现相反的作用。流动时间越长,个体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越低,而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夫妻流动和家庭化流动的流动人口随着人力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其生活满意的概率越高。流动范围对个体流动群体无显著性影响,但省内就近流动的非个体流动人口,因相似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其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更高。
第三,收入对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同。家庭消费率低、社会融入较好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更高。非个体流动形式下,收入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增加家庭总收入能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这也支持了“收入——消费——效用——生活满意”的传递链条。而个体流动形式下却并不支持这一传递链条,收入对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群体生活满意度反而较高。可见,非个体流动群体更易受到收入的影响。此外,休闲娱乐方式对非个体流动群体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工作在非个体流动群体的生活中仍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对于个体流动群体,多看书读报更有利于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这主要由于个体流动人口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有了更多的诉求,不再是简单的“生存权”,而是“发展权”和“平等权”。他们通过看书读报,充实自己,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从而努力改善生活,提升生活满意度。
第四,制度特征方面,户口对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但个体流动群体更在意有无养老保险,而非个体流动群体更在意有无医疗保险,可能是由于非个体流动群体的健康状况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这与汤爽爽等(2016)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也说明不同流动群体对社会保障有着不同的需求,并有着希望能通过享受社会保障来提高生活满意度的强烈愿望。
第五,社会融入方面,以本地人为主要邻居、与本地人相处融洽以及社会认同感高的流动人口,其生活满意度更高。与本地人交流的语言对个体流动的群体没有显著影响,而对非个体流动群体存在显著影响,交流语言为本地语言的生活满意度较高。此外,样本中8个城市人口数量平均为958万人,城市规模对非个体流动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影响,而与个体流动的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与蔡景辉等(2016)[10]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结论
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高低不仅影响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而且对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安全与稳定等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逐渐扩大,我国已经进入以家庭化流动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家庭化流动使我国流动人口的需求已经从“生存需求”逐渐转变为“发展需求”等其他更高的诉求,收入不再是流动人口就业的唯一砝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化流动的出现,流动人口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因此,研究我国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学术及实践意义。
第一,不同流动形式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家人随同流动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满意的概率。根据调查显示,家庭化流动是未来必然的趋势,今后,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更多地要从家庭化流动考虑流动人口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管理。
第二,影响非个体流动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远多于个体流动群体。与以往研究发现收入对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的结论不同的是,收入仅对非个体流动群体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尽管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家庭特征、制度特征、社会融入以及城市规模这些因素对不同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不全相同,但除了家庭消费率和居住社区外,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高低更多来源于其社会融入的程度。
围绕上述结论,可以发现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居住社区已成为影响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不可缺少的因素,拥有自住房能显著提升非个体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相关部门可考虑逐步向非个体流动人口开放保障性住房,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等,改善其居住状况提升生活满意度。此外,社会融入也是影响不同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相关部门积极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培训和服务的同时,还要多开展社区活动,丰富流动人口的休闲娱乐方式,使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有更多的机会交往和相处。在当前家庭化流动趋势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加强流动人口就业、住房等硬件建设,同时还要对不同流动群体有针对性地完善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社会认同等软环境[11]。影响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差异,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未来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某个趋势。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的个性化、差异化的趋势将不断明显,影响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也将更加多元化,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规划等。
[1] 李丹,李玉凤.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7):151-155.
[2] 张鹏,郝宇彪,陈卫民.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基于2011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经济评论,2014(1):58-69.
[3] Watson D,Clark I.Negative Affectivity:The Disposition to Experience Negative Affective State[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6(3):465-490.
[4] LouisV.and ZhaoS.Effects ofFamily Structure,Family SES,andAdulthoodExperiences onLife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2,23(8):986-1005.
[5] 李国珍,雷洪.互动论视角下的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研究[J].南方人口,2001(3):25-34.
[6] WEN Ming,WANG Guixin.Demographic,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loneliness and satisfac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Shanghai,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2009,50(2):155-182.
[7] 杨东亮,陈思思.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5,37(5):63-72.
[8] 流动人口服务中心.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EB/OL].http.//hdl.handle.net/1 1620/10725 V1[Version].
[9] 汤爽爽,冯建喜.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6,216(3):52-61.
[10] 蔡景辉,任斌,黄小宁.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来自RUMIC(2009)的经验证据[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1):89-99.
[11] 吴如彬.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20-121.
ResearchonDisparitiesofLifeSatisfactionwithinMigrantsunderDifferentFlowForms
WANG Qiong, HE Zhe-fei
(SchoolofMathematicsandPhysics,ChangzhouUniversity,JiangsuChangzhou213164,China)
Family flow tren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mod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4,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heterogene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flowforms. Through constructing an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15998 samples from 8 c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life satisfac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flow forms. The flow with family membe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non-individual floating groups are far more than those of individual floating groups. The factors, such as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e, living community as well as social inclusion, becom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mobile groups.
floating population; flow forms; life satisfaction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6.009
2017-03-13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SJB910004)
王琼(1981—),女,浙江金华人;常州大学信息数理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应用统计学研究。
何哲飞(1980—),女,江苏常州人;常州大学信息数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统计学研究。
C96
A
1672- 0598(2017)06- 0070- 07
责任编校:杨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