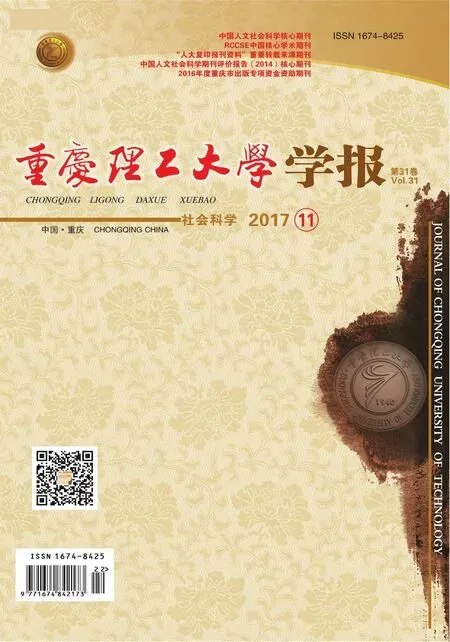论认知文学研究中的认知修辞研究范式
2017-03-22文永超
文永超
(四川外国语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重庆 400031)
论认知文学研究中的认知修辞研究范式
文永超
(四川外国语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重庆 400031)
认知修辞学把传统修辞研究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文学隐喻、文学意象以及文学想象。这种研究不单单把修辞看作一种表达技巧,更把修辞上升到了思维方式层面,当作一种语言符号、文化内容与人类认知的整合研究,是认知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认知修辞研究范式的核心理念是:文学效果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认知。
修辞;认知修辞学;认知文学研究
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修辞在西方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一种“言说的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或者“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persuasion)。修辞学在文化的框架内以及话语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和研究领域、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认知修辞学则是在人文学科出现了“认知转向”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范式观照下的修辞学。对于认知修辞学,波兰学者塔巴科茨瓦(Elzbieta Tabakowska)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认知修辞学研究信息发出者为了影响接受者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而发出‘实用目的’信息的手段和策略”[1]10。这里点出了认知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差异——思维。认知科学关注思维、大脑、人工智能等,与修辞学结合之后则探讨修辞与认知的关联。所以说,认知修辞学是一种合理的学术事业(a legitimate scholarly enterprise),研究对象是施予端与接收端的基本认知过程[1]276。既关注作者,也关注读者。这与认知诗学关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维互动模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成为认知诗学的研究范式之一。坡塔平柯(Serhiy Potapenko)认为:“认知修辞学发展了认知语义学与修辞理论的纽带。认知语义学旨在理解我们如何从总体上去概念化、想象并推理;修辞理论旨在理解我们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去概念化、想象并推理。认知修辞学旨在解释言语效果,借鉴两种概念结构:意象图式和力量流动模式(force dynamic pattern)。”[1]245认知修辞学其实是结合了认知语义学与修辞理论,将一般语境与特殊语境结合起来,探讨话语意义与效果。所谓“一般”与“特殊”的结合,指的是运用认知科学的已有成果,即对认知规律的总结,去分析各种特定语境下的话语,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
认知修辞与文学的认知研究有密切关系。认知修辞学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研究修辞、写作、教学,同时也研究语言和文学。马克·特纳(Mark Turner)是这一领域的主要人物[2]。在1989年出版的《不只是冷静的理性:诗歌隐喻的实践指南》(MorethanCoolReason:AFieldGuidetoPoeticMetaphor)和1991年出版的《阅读心智:认知科学时代的英文研究》(ReadingMinds:TheStudyofEnglishintheAgeofCognitiveScience)两部著作中,特纳将概念隐喻理论首次引入文学研究,并建议推出一个新项目,进一步通过语言表征探索概念关系(conceptual connections),这个项目被称为认知修辞学[3]163。他的研究论证了在日常用语中频繁使用的隐喻结构在文学作品中也非常普遍,共享同一种隐喻基础。由此可见,认知修辞学基于概念隐喻或者概念整合理论,汇集了认知科学、文学和修辞学理论,其囊括的学科包括修辞学、叙事学、话语分析和语用学。它的出现拓宽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打破了修辞、教学、语言学和文学的壁垒,是一门逐渐形成(on-going)的、充满活力的学科。
一、 认知修辞观的主要观点
特纳于1987年出版了《死亡是美丽之母:心智,隐喻和批评》(DeathistheMotherofBeauty:Mind,MetaphorandCriticism),该书奠定了认知修辞学的学科地位。他在该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本书是运用了来自当代认知科学和语言学深刻见解的现代修辞学”[4]9;他同时批评了传统修辞学,认为:“修辞学放弃了思想而仅仅关注风格,就使自己堕落了。不关注隐藏在语言表层形式下的心智,修辞学就使自己降格为分类登记那些可以视为表层文字游戏的东西,似乎它们与认知毫无关联”[4]9。他这里指出的把修辞看作表层文字游戏的观点,就是传统上把修辞仅仅看作修辞方法的观点。这种观点只触及到语言文字的表层形式,没有看到语符背后的认知机制,因而是片面的。实际上,认知诗学的母体学科之一的认知语言学本身也研究修辞方法(如矛盾修辞法、通感修辞法、反讽修辞法)与认知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拓展,拓展到了思维与隐喻、文学批评与认知、文学的功能、文学与文化以及文学想象等话题上。
(一)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
特纳认为,隐喻不单单关涉语词,而且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包括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思维和行动构成影响[4]9。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修辞方法的隐喻,其功能超越了修辞效果,上升到认知的层面,构成了人类认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模式之一。借助隐喻,人类可以通过具体的意象去认识未知、抽象的概念内容,从具体到抽象。语言隐喻的概念基础源于以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一著作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观点,特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修辞学观点,认为有很多因素是受众共享的——概念系统、社会习俗、共有知识、话语体裁以及共有语言的每一个部分。他强调,修辞学致力于分析受众的所有的共享认知系统及这些系统运作的方式,这与认知科学的任务是重叠的[4]10。这里点出了认知科学与修辞学能够整合的理论基础。
认知修辞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莱考夫与特纳合著的《不只是冷静的理性:诗歌隐喻的实践指南》(MorethanCoolReason:AFieldGuidetoPoeticMetaphor)(1989),该书也聚焦于隐喻。该书认为,隐喻绝不仅仅是词语的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思考:关于情感的、关于社会的、关于人性的、关于语言的、关于生与死的本质的。它在我们的想象和推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隐喻能以某种别的思维方式所不能替代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和这个世界[5]xi。 也就是说,认知修辞学视域下的隐喻不单单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人们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吉布斯(Raymond Gibbs)的《心智诗学:比喻性思维,语言和理解》同样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隐喻上,认为我们日常的思维也具有隐喻的性质,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诗人们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普通人大量的日常表达中[6]9。思维是隐喻的,是认知修辞学的核心观点。
(二) 文学评论与认知
特纳指出,对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被人知晓,在何种程度上不被人知晓,大多数文学评论家并不知道。这种意识对于文学评论家衡量其观点的内涵意义,了解他的预设是否有争议、是否安全还是错得显而易见这些方面是必不可少的[4]12。他举例说,每个人都清楚“死亡是美丽的母亲”是一个精彩的桥段,但是我们能否解释为何它比“死亡是美丽的父亲”抑或是“死亡是美丽的父母”更好?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解释文学效果,还得借助于认知。特纳强调说:“好的文学之所以强大,原因在于其精湛地激发并操纵我们的认知器官(cognitive apparatus)。当代文学评论,因为不关注这些普遍的认知能力,所以很少触及到文学作品产生的力量源头。由于放错了重心,这种做法渐渐地模糊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有力联系,这样一来,当代的文学评论就经常被视为是单一的、孤立的做法。”[4]13可喜的是,这种文学批判孤立观已经得到改善,有学者明确提出作为认知的文学批判这一论断。“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历史,又开始对各种现象进行探索,在认知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人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与文学,又开始了对文艺的批评与认知。文学创作的过程隐含着认知,文学批评则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认知活动。”[7]6
(三)文学的功能
认知修辞学强调文学与心智的关系,构成该学科的功能观。特纳指出,我们研究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解人类心智的运作,而人类心智的很多内容最适宜通过文学予以理解。庞德说过,作家是人类这一种族的天线(即文学作品收集各种信息,并传播出去),作家经常探究我们的概念和语言结构并推进这些结构以探明它们以何种方式反应,在何处断裂。作家教给我们的内容只能通过研究文学来获取,经过培训来研究文学的人是文学评论家,不是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如果文学评论家不参与这项工作,其他人没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的收益也就丧失了[4]1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点出了研究文学的价值——阅读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审美的愉悦,同时,作为一种认知建构物(cognitive construct),文学又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心智、思维的媒介。二是点出了文学评论家的职责——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在作品中呈现的信息。当代文学评论家要从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吸取养分,而不是把认知部分的任务推给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等。但是事实上,自从浪漫时期以来,文学评论家往往满足于把文学的认知研究推给科学家,包括研究心智的科学家,而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对特定文本进行阅读。在他们看来,这两项事业仿佛毫不相干。这种做法剥夺了心智科学的一种重要知识来源,同样,又让文学研究丧失了对非文学世界的影响(文学语言的很多研究是可以用于日常语言的)。特纳强调:“文学评论家与其他研究者(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等)应该共同致力于这项事业。具体而言,文学评论家要致力于分析文学的认知工具,不断涉猎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这才是修订版的、更新版的经典修辞。”[4]13-14从事日常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也需把文学也当做研究对象。
(四)文学与文化
认知修辞研究强调文化与文学的必然联系。在其专著《死亡是美丽之母:心智,隐喻和批评》中,特纳把来自各种文化、语言和时代的文学文本并置于西方的文学传统中[4]16。他之所以重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多样性,源于对结构主义者的合理批判。有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研究从表面看都是相似的,因而饱受诟病,这种批评是合理的,因为忽略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文化和语言差异。文化具身于心智之中,文化是认知人类学的主要内容。而要研究文化,则必须研究认知,即研究该文化圈成员的概念结构。认知文学研究其实也就是认知文化研究,非常重视文学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也必然是认知修辞学的重要内容。
必须指出的是,也有学者对特纳的认知修辞学理论提出了批评。认知文学研究代表之一里查德森(Alan Richardson)指出:“特纳并未将他的计划描述为建立一种文学理论,而是建立一种可以支撑多个理论的共同基础……他强调修辞以及与此对应的关于超文学文本(extraliterary texts),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很难评估认知修辞的充分性,也就无法支撑起一种文学理论本身。”[3]164里查德森之所以说特纳的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并不充分,因为从本质上讲,他更关心的是分析认知过程,而不是运用心理学的发现去建构文学理论并进行文学阐释。换句话说,特纳有一个从文学评论家到认知科学家的转变。他的重心不在于研究文学的问题,而是研究认知本身,他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展示语言研究如何促进我们对认知的理解,从而说明修辞探究在所有学科的重要性。
(五)文学想象
认知修辞学非常重视文学想象。认知修辞学的代表性著作——约翰逊的《心智中的身体:意义、想象和推理中的身体基础》(TheBodyintheMind:TheBodilyBasisofMeaning,ImaginationandReason)(1987)就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约翰逊认为:“没有想象,世界就没有了意义;没有想象,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的经验;没有想象,我们也就不能通过推理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他批评此前的客观主义关于意义和理性的理论缺乏对想象的足够重视和扎实研究,认为这是我们当前关于人类认知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深层问题。”[2]4该书出版后近30年的今天,约翰逊提出的这个深层问题已经获得足够的重视:认知文学研究学者里查德森和霍根(Patrick Hogan)都强调了文学想象的重要性[8]225-245。里查德森也指出:“想象成为了认知文学研究这一新的跨学科领域的关键地带(a key site)。”[8]232约翰逊认为:“想象涉及五个方面的要素:范畴化、图式、隐喻投射、转喻和叙述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如果我们要解释人类是如何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体验他们的世界,那就必须把叙事统一性(narrative unity)概念置于中心地位。我们不仅生来就处于复杂的公共叙事之中,而且我们以故事的形式去经历、理解和组织我们的人生。不管人类理性由哪些东西组成,它一定与叙述结构和对叙事统一性的追求紧密相连。”[2]4范畴化、图式、隐喻和转喻都是我们理解自我、理解他人的手段。叙事与想象同样密不可分,无论是对于没有文字的远古人类而言,还是对于当代人类,叙事想象对于生存、生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8]236-237。
二、认知诗学与认知修辞学的汇合
波兰学者科瓦特考斯卡(Alina Kwiatkowska)2011年主编了一部文集:《文本与心智:认知诗学和认知修辞学论文集》(TextsandMinds:PapersinCognitivePoeticsandRhetoric),该书收录了22篇在2010年“罗兹认知诗学和认知修辞学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体现了认知诗学与认知修辞学的融合趋势。科瓦特考斯卡在书中指出,“认知诗学” “认知文体学”和“认知修辞学”界限模糊,常交替使用于文学分析中。该书分为文学思想的认知方法和认知修辞学研究两部分,探讨意义——尤其是源自创造性活动的微妙和不明显的意义——生成的心智过程,具有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其所选论文的研究兴趣和出发点、研究主题和所选用的分析材料、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这表明认知研究具有开放性特征,无论认知诗学或认知修辞学都能够进行多维视角的研究[2]5。
该书在论述认知诗学时,选择的文本都是文学文本。但是,在论述认知修辞学时,则讨论的是非文学文本,如政治人物的演讲稿、布道辞、新闻稿等。这种认知修辞学,还是传统的修辞学观念。塔巴科茨瓦指出,从传统来看,修辞学一直与口头语言使用相关,其目的是罗列和描述正式的公共演讲中所用的语言手段和泛语言手段;而现代修辞学的定义涵盖了更为宽泛的体裁和媒介[1]275。紧接着,他指出要把修辞学和相邻的诗学领域划分开来既是困难的,又是没有必要的,在现代人文科学和用认知方法去研究语言和语言使用中,边界模糊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学科互涉已成为一个基础的方法论假设。诗学关注语言手段与文学效果的关系;修辞学关注语言手段与论证力量之间的关系(注意:论证的力量可以说是论证力量的一种,从性质上看,二者有包容关系)。他还指出,修辞话语与文学不同,文学是诗学的主要研究领地(所以说,修辞学与诗学不同),作为文学研究的分支,认知诗学有自己的传统,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建构物和方法论去研究文学;认知修辞学经常被视为是认知文体学的近义词,目的在于调查施予端和接受端的基本认知过程。虽然两者的终极目标不同,但都致力于探讨语言选择与认知结构和过程[1]276。
这本编著把认知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设定在非文学类文本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在2014年出版的编著《认知、文学与历史》中得到了改变,在引言中,编者明确把认知修辞学与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并置,构成认知文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其中,在该书第二章,森丁(Michael Sinding)提出了体裁整合的三层套叠框架(nested frame),第二层框架就是修辞情境框架(rhetorical situation frame)。这层框架关涉的是环境(setting)、言说者、听众和媒介的结构关系[9]41。值得注意的是,森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体裁——书信体小说,而不是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演讲辞、布道辞、广告等)。环境指的是小说故事世界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言说者指小说中的叙述者或者人物;听众指的是受叙者(narratee)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媒介指的是语言符号和形式,其中包括意象符号。虽然森丁在文章中并没有详细阐述如何从认知修辞学角度分析这四个要素的结构关系,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文学研究的分析工具,这标志着认知修辞学在逐步成熟。
三、结语

[1] KWIATKOWSKA A.Texts and minds:Papers in cognitive poetics and rhetoric[M].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12.
[2] 熊沐清.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一[J].外国语文,2015(6):1-9.
[3] EASTERLIN N.A Biocultural approach to literary theory[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
[4] TURNER M.Death is the mother of beauty:Mind,metaphor,and criticism[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 LAKOFF G,TURNER M.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6] GIBBS R W.The poetics of mind:Figurative thought,language,and understand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7] 肖谊.文学批评作为认知[J].认知诗学,2016(1):6-11.
[8] ZUNSHINE L.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9] BRUHN M J,DONALD R W.Cognition,literature and history[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4.
[10] 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OntheParadigmofCognitiveRhetoricinCognitiveLiteraryStudies
WEN Yongchao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Cognitive rhetorics combines traditional rhetorical research with cognitive science, probing into literary metaphor, literary image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rhetoric is only a mode of expression, cognitive rhetorical studies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sub-discipline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which integrates linguistic signs, with culture and human cognition by promoting rhetoric onto the level of thinking. The key concept of cognitive rhetoric paradigm is that cogni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literary effect.
rhetoric; cognitive rhetoric studie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10.3969/j.issn.1674-8425(s).2017.11.016
2017-08-11
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博厄斯·贝耶尔翻译思想研究”(SISU201644);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托妮·莫里森小说《家》的认知生态批评研究”(SISU2017YZ03);四川外国语大学一部两院特色课程项目“国粹文化英译”
文永超(1981—),四川安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翻译学。
文永超.论认知文学研究中的认知修辞研究范式[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11):111-115.
formatWEN Yongchao.On the Paradigm of Cognitive Rhetoric in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11):111-115.
I06
A
1674-8425(2017)11-0111-05
(责任编辑冯 军)